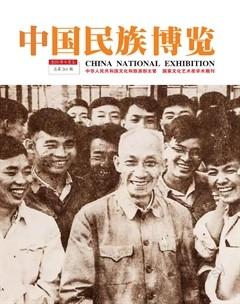民间故事中灾祸记忆装置的选择与形成
【摘 要】民间故事中存在着诸多母题变体,其中不同于灾害的灾祸母题变体与“人”的概念联系得更为紧密,是建立在集体记忆基础上、可以作用于个人的祸害与苦难,在民间故事中起着改变人物命运等重要作用,成为置入民间故事中的记忆装置。看似为非常事件的灾祸不仅具有工具性的特点,还有着其正常解析,是故事逻辑、生活逻辑和心理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灾祸母题变体;记忆装置;人物命运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3)17—080—03
民众的生活常常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是日复一日的周而复始,即“日常”,而民间文学的内容材料和功能作用也均与之密不可分。然而在“反复”的日常生活中总会有“非常”的突发事件,灾祸便是众多“非常”事件之一。灾祸中的火灾在中国民间故事中已成为一种常见的改变人物命运的工具性手段,但火灾改变命运的故事创造在逻辑上的集体认同绝非偶然所致,而受各种复杂原因长期以来的综合影响,即所有的异常现象(偶然性)都可以找到它的正常解析(必然性),之所以我们觉得异常,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异常的表象,还没有看到它必然的本质。[1]当我们继续向源头探寻,就会发现民间故事常用火灾来改变人物命运,即火灾这一“日常”生活中的“非常”事件能够成为置入民间故事中的常见记忆装置,是故事逻辑、生活逻辑和心理逻辑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多层逻辑发挥作用,火灾作为具有灵活性的一种灾祸被运用到人物命运的转变之中,这种母题变体在民间故事中就逐渐得以稳定下来。
一、故事逻辑:民间故事中的火灾具有工具性
在灾害民俗学领域,民俗学家樱井龙彦提出三类作为灾害的集合性记忆装置的传承性材料,其中“一类是以‘故事或者‘传说的形式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谚语等‘口头传承”[2],该类中的口头传承产物将“非常”事件转换成记忆进行传承,并悄然体现在故事结构之中,用故事中隐藏的记忆经验来进行传递。灾害民俗学为我们理解这种记忆装置提供了方向,而且在民间文学研究中,以集体灾害母题叙事为主的灾害民俗学已经较为广泛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民间故事中的火灾对人物命运的转变常常并非“集体灾害”,而是“个体灾祸”,这就需要我们走出灾害民俗学视角,来看并未被正式谈起的故事结构中的个体灾祸和其在民间故事中的工具性。
(一)灾祸与灾害:民间故事中的灾祸是集体记忆中灾害的反映手段
为了更好论述,我们有必要首先对“灾害”与“灾祸”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项义华在《古代中国早期的灾异书写与灾难文化》中指出,虽然“灾害”和“灾祸”都是祸害与苦难,但是“灾害主要是指对人及其生存环境造成破坏和损害的自然现象或本身,灾祸侧重于灾害对人的损害”[3],我们从现有的民俗学研究和故事材料中也可以很好地印证这种区分。但由这种区分方式我们还可以生发出另一种区分方式,即常与自然现象导致的人及其生存环境的破坏相关的“灾害”,以一种集体灾难存在并往往会产生集体性记忆;而与“人”的概念更紧密的“灾祸”,还可以指自然或人为引起的个体的祸害与苦难。这也导致“会说话的鱼”的海啸传说、“雷公复仇”的洪灾传说等以灾害为母题的民间故事中,蕴含着更强的现实性记忆,甚至可以与某次有历史文献记载的灾害相伴流传下来;而存在于故事结构之中的灾祸由于缺少具体的集体性记忆的制约,反而更具有创造性,可以在需要时随时取之对故事进行“填充”,生发出工具性的特点。
但是灾害与灾祸之间也存在着逻辑联系。从民间文学角度,我们可以把灾害分为两类,一类是难以单独作用于个体的集体性灾害,如地震、海啸、虫害等,这类灾害由于其每次常以巨大的破坏力出现,而难以实现在故事中仅将苦难作用于某一个体;而另一类是可以作用于个体的灾害,如火灾、雷电等,这类灾害的破坏力不定,故容易对故事中单个人物造成指定性苦难。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非灾难母题叙事的民间故事中坏人常常被寒潮冻死而非被洪涝淹死,常常被雷电劈中而非感染瘟疫而死。所以在这两类灾害中,后者常常由灾害转化为灾祸,被作为工具出现在民间故事之中。这也体现出,存在于故事结构之中的工具性灾祸看似仅仅是针对于故事中某一人物的个体灾难,实则是集体记忆中灾害的记忆反映手段,是集体灾害在人们意识上留下创伤的影响结果之一。所以可以说,在民间故事体系中,灾害和灾祸是共联的,灾祸在表面上看似偶然,实则在创作层面上具有必然性内核。
(二)民间故事中火灾对个体命运改变的工具性
本文谈及的火灾具有随时取之对故事进行“填充”的工具性作用,这一事件归属于“母题位——母题——母题变体”中的“母体变体”,但并不局限于某一具体故事类型,而普遍存在于众多故事类型之中,且影响结果、使用目的等均可大可小,任由故事家们使用,体现着该母题变体在民间故事情节中的灵活性和广泛性。
1.影响结果可大可小
从影响上看,在民间故事创想中,火灾在可作用于个体的灾害里,可造成的情势范围的灵活性几乎最强,小到损失钱财,大到造成人物身亡,可任凭故事需要对该“工具”进行构想和安排,故在创想中最容易被转换成个体灾祸。
如在《满善人当宝》中,“有一年大旱,七月七这天夜里闹天气,一个霹雳引着一把天火,满洛富全家人扑打,火就是不灭。一夜的工夫,全部家产都变成了灰。”[4]在这个故事中,天火造成了“全部家产都变成了灰”,但主人公其他的某些财富还有所保留:“南蛮子走到猪圈边用手向地下一指说:‘這五尺之内就有一件宝贝,刨出来拿到城里东街二当铺,至少也当它上千两银子。”[4]这里的“宝贝”就是满善人在故事中要当的“宝”,可见本质上火灾造成的是人物部分财产的丧失。
又如在孙太生的故事中,一场天火造成了人亡财空:“孙太生十岁这年,他家呼啦一下子着了场天火,不但家产烧得片瓦无存,孙员外两口子也随着大火升了天。”[5]这场大火造成的个体灾祸不仅造成了财产损失,更涉及到人物生命,但进行了设定选择:“幸好孙太生远在学堂里读书,才免遭大难。孙太生赶回家时,已是人财两空了。”[5]故事中孙员外夫妇丧生而主人公幸存,孙太生的性格善良使他躲过了天火,前后蕴含连接紧密。
2.使用目的可大可小
火灾作为灾祸的工具性使之可在民间故事中任凭创作群体根据故事叙事需要进行编排,既可以在民间故事中作为使好人命运发生转变的工具,也可以作为对坏人进行惩罚的工具,这种使用的相对任意性使之能达成的目的可大可小,可好可坏。
火灾可以作为故事中使好人命运发生转变的工具,如在《路遥知马力日久品人心》中,鞭炮把路遥家的柴火垛烧着了,进而引起了大火:“路遥家是瓦房,那瓦着了火,还真难救。瓦烧的四面八方横飞,谁来救火,那瓦片就打谁的脑袋,人们只能隔老远吵吵。那天下晚风还挺大,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嘁嚓咔嚓,眼见着就把房子烧落架了。真是火烧当时穷,家趁万贯被烧得一个不剩,片瓦无存。”[6]大火使高情厚谊、心地善良的路遥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家里有钱”的富人沦落成“后尾儿跟要饭花子一样”[6]的穷人,为其之后投奔马力和马力为其置办家产的情节做了铺垫。
火灾在民间故事中,还常常作为对坏人进行惩罚的工具。如《郎傻子和扇子参》结尾:“至于那家山货庄,在郎傻子走后的当天半夜,就起了大火,那个黑心的掌柜被活活烧死了。”[7]在这里,火灾同《鸭姑》中王财主变成孤独的老公鸭、《百鸟衣》(满族)中国王成为不被认识的卖韭菜的人而被砍头一样,成为故事中惩罚坏人的一种工具,且作为故事结构的一部分常常出现在故事结尾。
故事中对火灾的描述有的长达几段,有的仅进行几句交代描述甚至一句带过,虽然可多可少,但多以简短描述为主。然而火灾正因这种对其的简短性描述,而更体现出其在民众心中的集体记忆认同,即通过工具性的简短叙述就能为接受者带来公认性的信息,甚至成为一种创作的“自觉”和接收的“自觉”。
二、生活逻辑:社会客观现实中的火灾带来的痛感
考古发现,我国在5000多年前就有木架结构连片建筑,因此失火与防火,就成了中国古代建筑中两大“永恒的主题”。火灾频发的原因之一是自然因素,包括由地震、雷电、气候等引起的自然失火,如正德七年三月,“嶧县有火如斗,自空而陨,大风随之”[8]因雷电击中引起大火,继而“大风随之”,焚荡众多房屋。古代房屋建筑材料多以木竹为主,在农村地区还有以茅草为主的房屋建筑,据王禹偁记载,宋代黄州地区建筑向以竹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9],又如峡州:“州居无郭郛,通衢不能容车马,市无百货之列,而鲍鱼之肆不可入,虽邦君之过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趋。而民之列处,灶、廪、匽、井无异位,一室之间,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材,故岁常火灾。”[10]建筑材料的易燃间接导致了火灾的频发。除此以外,蓄意与过失纵火也是引发火灾的重要原因,并常常伴随着刑罚条文的推行与创制,如《周礼·夏官司徒》载:“凡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这是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火灾刑罚条文,体现着政治法律层面对火灾的规制。火灾留下的痛感,让人们时时铭记,失火对民众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深深置入人们的记忆之中,这让火灾在生活逻辑上成为民间故事中对人物命运起着转变作用的变体,为其成为一种记忆装置奠定了社会客观现实基础。
三、心理逻辑:用灾异说构建民间故事中火灾的底层心理逻辑
说到“灾祸”与“灾难”,就不得不谈及“灾异说”。“灾”指灾害、灾难、灾劫,“异”指异常、变异、怪异。“灾异”,旧指自然灾害或反常的自然现象,而“灾异说”则是指依据天人感应观念,由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某些变异、怪异等异常之象和某些灾害、灾难等灾变之事来推断其所预示的有关政治和人事变迁的学说。[11]但是这种灾异说在历史上却常常向上有对人君的警惧,即人君的过错、为政之失,用“灾”以其“害”谴告。若不听,则用“怪异”或“异”以其“威”来“畏”或“警惧”人君,这也是维护政权合法性的需要;若“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伤败乃至”,天命就将要转换。向下有对普通百姓的灾谴,即人的不良行为将以灾祸的形式作用于自身,反映了人们普遍的价值观要求,这也使之更好地运用于民间故事的形成之中,特别体现在对坏人惩罚的母题变体上。故事中火灾对坏人的惩罚,常常毫无来由,这一方面是因为民间故事的创作常常遵循着最简原则,即对故事发展没有过多贡献的原因、行为等常常被省略,以此实现用简单而高度紧凑的情节吸引听众注意的效果。另一方面,火灾对坏人的惩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民众灾异说的心理影响,故事创作本身和创作心理就密不可分,用“灾”以其“害”谴告坏人的灾异说就成为对坏人进行惩罚的重要底层心理逻辑。
四、结语
母题变体具有具象性和变异性的特征,所以这种故事中的实际呈现常常数量众多,但并不是所有母题变体都能广泛地运用到不同的民间故事之中。这种火灾装置逐渐演变成工具性的结构装置,在对人物命运的转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支撑火灾这一灾祸类型成为民间故事中常见的母题变体的三大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民间故事中部分母题变体能够得以广泛运用的条件所在。民间故事中运用广泛的母题变体,一是要有客观现实支持。运用广泛的母题变体一般需是深植入民众记忆中的事件,或给民众带来深刻的心理痛感,或是民众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期望的事件,同时在客观事件背后一般还有着构建民间故事时的底层心理逻辑。二是可以随时取用。得以广泛运用的母题变体能够打破某一具体民间故事的固有风格,运用自身工具性的特征,充分发挥其在故事中的灵活性。民间故事中以火灾为代表的灾祸运用,作为人类精神及其思想在特定条件下的投射物,体现了其在民众心中的集体记忆认同,成为一种创作的“自觉”和接收的“自觉”,与此同时,这种集体记忆的另类内置也将启发我们进一步探索民间故事中母题变体的运用机制所在。
参考文献:
[1]施爱东.讲故事的民俗学:非常事件的正常解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2]樱井龙彦,陈爱国.灾害民俗学的提倡[J].民间文化论坛,2005(6).
[3]项义华.古代中国早期的灾异书写与灾难文化[J].浙江学刊,2022(1).
[4]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北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3.
[5]江帆,采录整理.谭振山故事精选[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
[6]夏秋,主编.满族民间故事·辽东卷:中[M].沈阳:辽寧民族出版社,2010.
[7]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传统故事百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8](清)万斯同.明史·续修四库全书第324册:史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宋)王禹偁,撰.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小畜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5).
[10]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11]刘光本.中国古代灾异说之流变[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作者简介:王硕(2001—),女,汉族,安徽淮北人,本科,辽宁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民俗学、民间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