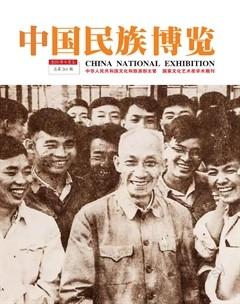浅析不同版本“赵氏孤儿”结构重塑的差异
李敏
【摘 要】“赵氏孤儿”的故事经由元代戏剧家纪君祥的艺术加工后,首次以戏剧的面貌进入大众视野,自此成为国内经典的戏曲母题。因其有着极高的悲剧性和思想价值,它先后在不同时代被改写成多重版本。由于创作者的主观思想、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观众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剧本的结构形式呈现出独树一帜的风格。故而,本文将京剧版、田沁鑫话剧版与舞剧版作比较评论,分析三者在结构重塑上的差异,进而剖析它们所宣扬的不同价值观。
【关键词】赵氏孤儿;结构情节;主题观念;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J821;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3)17—017—03
在元杂剧《赵氏孤儿》问世前,程婴救孤的故事在社会中就有很大的影响力,上至君王下至百姓皆看重故事中的“忠义”精神。在纪君祥改编成杂剧后,赵氏孤儿的故事霎时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的戏剧作品,后在不同时代受到不同程度地改编及搬演。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虽改编作品的故事情节大致相同,但不同的改编者向观众呈现的审美意识、价值取向亦有所差别。笔者选择京剧《赵氏孤儿》的原因一是看重该戏剧作品的经典性,二是深入剖析其结构形式有助于丰盈当下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选择田沁鑫版话剧《赵氏孤儿》的原因最初是被田導“我做戏,因为我悲伤”的话所触动,在观看整部话剧后,又深深地被剧中包裹的理想主义色彩所吸引,孤儿身上散发的种种焦虑、挣扎的情绪直击我心;选择舞剧《赵氏孤儿》的最大原因是被演员的表演张力所震撼,各环节间的情绪传递细腻且真实,让我不由得沉浸在此刻的历史空间中,跟着演员或紧张、或愤怒、或哭泣。
故而,本文选取这三个改编版本作对比评论,深刻剖析三者在结构重塑上的差异,以此来探究不同的价值取向。自古以来,传统意义上“忠义之臣”的“忠”指的是“报效君王”,而京剧《赵氏孤儿》却将“爱民”思想化为忠义精神的主体部分,更看重“爱护百姓”的忠,从而生发反封建、反压迫的思想意识。田沁鑫版话剧《赵氏孤儿》依托《左传》的只言片语,旨在彰显程婴身上难能可贵的诚信意识。在社会价值观歪曲、混乱的状况下,驱使程婴决心救孤的不再是誓死效忠君主的愚忠,而是一种“抱诚守真”的诚信精神。舞剧《赵氏孤儿》的剧情采用平凡化处理,意在消解传统舞剧的说教意义,突出历史洪流中小人物的生命境遇,从而向观众呈现普遍意义上的人性及道德。
一
戏曲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过:“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换言之,一部戏剧作品大获成功的关键是看创作者能否将零散的素材编织地浑然天成、紧密细致。京剧《赵氏孤儿》是剧作家王雁在1896年以剧目《搜孤救孤》为模本,并借用传统秦腔的唱法创作而成。全剧在忠奸对立的模式下徐徐展开,围绕着“搜孤救孤”这一核心从开场到结尾不断地打造各种悬念,令观众连续产生新的审美愉悦,进而将戏推向高潮。全剧共分为四部分:赵家满门遇害、程婴救孤出宫、公孙二人设计保全孤儿、孤儿复仇,而第三场《扑犬》的情节最是迷雾丛生,在极度惊险的情境下突显善恶斗争的惨烈。
首先,基于结构重塑的需要,剧作家进一步增加并变动了故事情节,以此升华爱民思想。该版将《斥贼》《行刺》《扑犬》放在戏曲的开场部分,旨在突出赵盾与屠岸贾之间的矛盾并非是私人恩怨,而是事关国家与民生的忠奸对立。其次,在新增的孤儿《遇母》这场戏中,孤儿斩杀屠岸贾的行动既不是受新君主的命令,大仇得报后也没有元杂剧里的加封情景,只有母子团圆的喜悦。这一改编虽然削减了悲剧的“悲”,却使得孤儿的身份得到了合理的逻辑支撑,并且极大满足中国人喜好“大团圆结局”的审美诉求。这种大悲后亦有大喜的创作手法也传达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为观众提供强烈的情感慰藉。除此,京剧将“爱民”思想化为“忠”的一部分,以此宣扬“爱护百姓”的进步精神。戏曲一开场,伴随着西皮快板,魏绛缓缓唱着“主公不把早朝上,贪恋酒色太荒唐……闯进桃园把理讲”,类似的唱段在剧本中比比皆是。剧作家这样安排,一是为了从侧面体现出生活在暴君统治下百姓的真实现状;二是为了表明赵盾、魏绛敢于指佞触邪、痛斥君主的“附膻逐臭”,将创作主题升华至爱民及反封建的高度。再者,由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伦理纲常一直占据封建宗法制社会的绝对话语权,这就意味着群体价值势必会逾越于个体价值之上。而“仁”“礼”更是儒家宗法制社会“群治”的根基,二者的实现均以“克己”为前提,即将牺牲个体的自由意志作为先决条件。故而,这种宏大的话语叙事体系势必会影响剧作家王雁的创作,剧中她将程婴与屠岸贾设为主要人物,在紧凑的矛盾冲突中拿捏纵横交错的人物关系,对程婴的性格塑造在审美层面上呈现出一种超脱人性的“大义”。他为保全孤儿不惜鞭打好友、牺牲亲子,这种比自我牺牲更难以承受的悲惨考验中更易彰显人物的忠肝义胆。一言以蔽之,全剧刻画的诸多游离于封建伦理框架外的、自发的复仇行为,总体表现出一种超越且试图消解封建伦理的反抗精神。
二
当代社会对于个体价值的重视及推崇,必定会引发戏剧界内对传统题材的解构与重塑。无独有偶,北京人艺与中国国家话剧院先后推出两版《赵氏孤儿》,它们皆摒除了原有的宏大话语叙事,将隐藏在价值符号背后的个体价值重新推到大众面前,让所有的忠奸善恶包裹在人性的复杂性中。而中国国家话剧院版的《赵氏孤儿》更是将赵孤塑造成哈姆雷特式的悲情角色,当身世之谜揭晓后,孤儿深陷于迷茫和身份缺失的痛苦中,犹如哈姆雷特在了解杀父真相后的进退失据。故而,田沁鑫导演对戏剧结构作了如下调整:以往剧本中的说话权都是给予程婴、公孙杵臼这样的忠臣义士,屠岸贾作为反派角色不会被赋予自我辩护的权利。在现代社会,民众对平等的渴望和呼唤愈发强烈。此观念投射到话剧中则体现出剧里每个人都有平等说话的权利。田沁鑫给予屠岸贾向孤儿陈述身世的资格,为此话剧不再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开展剧情,而是将故事的开端限定在十六年后孤儿长大成人这一时间段,期间又夹杂着往事的插叙回忆及孤儿梦境。因为有着平等的话语权,程婴和屠岸贾二人分别向孤儿讲述成人前的事情。孤儿周围充斥着两种声音、两个立场,不由得陷进无边的迷茫当中。其实此时的孤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父母双亡的孤儿形象,而是一种精神孤独的象征。而田导又敏锐地捕捉到“当下的生活虽看似繁花似锦、便捷且时尚,但人与人的交往却止于表面,没有深层的内心接触”,有着无尽的心灵孤寂。所以,她在剧末让孤儿发出了“今天以前,我有两个父亲,今天以后,我是孤儿”的呐喊声。这样安排,一是为了体现孤儿敢于走出两种权威话语牢笼的坚定信心,二是让其用人文反思者的身份去警醒世人重新认识自我、勇于对抗孤独。除此,导演还利用诗剧的表现形式,将中国的灵动意境说与西方的抽象美学原则一同融进舞台布置中,从而刻画复杂的时空结构,呈现出强劲的视觉冲击力。比如,舞台的底色为大面积的“红与黑”色块,直接体现了中国式的审美心理。因为中国人习惯把红与黑与明暗结合起来,并将其视为生命与死亡、喜庆和晦气的象征。
由于赵氏孤儿的故事有着漫长的完善过程,这期间历史记载难免充满不确定性,这种细微差异既为后世的创作者提供无限的思考空间,也给予改编后的作品必要且合理的逻辑支点。田导则凭借《左传》中的只言片语暗示这场悲剧发生的双重原因:一是晋国皇室与赵氏家族或许积怨已久;二是庄姬与赵缨的不正当关系可能间接导致悲剧爆发。故而,在保留元杂剧基本脉络的基础上,她大胆地将“赵朔弑君”的情节加入剧本中,并利用氛围式的思想传达既让观众看到了真实的春秋历史,也消解了元杂剧里“正义与邪恶”相对立的意识。纵使弑君源于庄姬荒乱被发现后的诬告,赵家满门忠烈亦会变成众人口中的“乱臣贼子”。所以,话剧颠覆原著的目的,或许不是为了廓清这段历史,而是为了彰显程婴身上难能可贵的诚信意识。在社会价值观歪曲、混乱的状况下,驱使程婴决心救孤的不再是誓死效忠君主的愚忠,而是一种“抱诚守真”精神。
除此,田沁鑫以特有的女性眼光有意识地在剧中增添庄姬的戏份,并着力挖掘她的内心情感,继而解构传统的女性形象。庄姬既是女人又是母亲,她在身体的反抗与建构中呈现出不同的心理诉求。田导这样设置是为了隐晦表达女性的身份认同危機,进而剖析出女性成长中的忧虑与反思。古代社会是父权制社会,男性往往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及凝视权,田沁鑫却在《赵氏孤儿》里用直白的语言书写了庄姬身体的反抗意识,以此彰显女性对于男权社会的初步颠覆。故事的开场,庄姬就以魑魅魍魉的模样游离于舞台上,对孤儿、程婴和屠岸贾三人进行凝视,用提醒程婴勿忘往事的办法将懦弱的女性身份置换出去,转为“复仇”中人。
简言之,程婴在话剧中被置于一个礼乐缺失的时代,身为一介草泽医生,能让庄姬托孤、韩厥与公孙杵臼赴死相助,全靠他的诚信及道义。在他身上最难能可贵的精神不再是彻彻底底的“义”,而是一诺千金的诚信意识。加之社会中普遍存在着情感缺失现象,田沁鑫重塑话剧结构与人物形象亦是为了缓解群体心灵的孤寂与不安。
三
舞剧《赵氏孤儿》采用独白的形式递进剧情,共分“屠杀夜”与“成人日”两个篇章。首先,为了让观众更容易看懂剧情,舞剧采用“线性”的剧情结构。以程婴为主线,辅以程婴妻及屠岸贾等副线,用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演绎方式讲述一个完完整整的故事。其次,舞剧采用隐喻表意、首尾呼应的叙事结构。道具是建造完美叙事策略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不仅是因为它本身具有表情达意的审美功能,更重要的是准确使用道具能够最大化地提升舞剧的表达空间,与观众形成情感上的共鸣。舞剧《赵氏孤儿》用到最多的道具是红绸及纱幕,前者作为象征性的“规约符号”存在。比如在《救孤》这幕中,红绸化为“亲子”的意象,一团红绸散落在地时,暗示着孤儿被屠岸贾无情杀死,引发观者强烈的心理联想。而后程婴妻绝望地抱起“孩子”,红绸从她手中慢慢脱落,出现一座细长的“红桥”。在这里红绸暗示着“血脉”和夫妻间的“纽带”,也隐喻着可怕的死亡。而屠岸贾被孤儿杀死时,一条红绸从天而降亦代表死亡。后者的功能在于指引剧情转变以及构建时空结构。也是在《救孤》这幕中,当舞台上“重映”程婴与妻子的恩爱日常时,后台的黑色纱幕迅速化为叙事时空的“分界线”,使观众一面沉浸在二人相濡以沫的心理空间中,一面目睹着现实世界里官兵用全城婴儿的性命威胁交孤的凄惨场面。加之道具与音乐的巧妙配合,整部作品充斥着生命与死亡的沉重感,以此升华“一义孤行”的宏伟主题。再者,编导用中国古典舞的律动方式去塑造空灵生动的人物形象,表现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为观众展现最真实的善恶形态,进而对赵氏孤儿的故事完成现代化的重塑与颠覆。此外,舞剧采用“投奔”仇人进行复仇的结局,似乎营造一种众叛亲离的氛围,从而践踏主人公脆弱的尊严,彰显这场忍辱负重的救孤行动是程婴想逃却逃不开的生死疲劳。
剧中将程婴塑造成有着普通人最平凡的情感的忠义之士,支撑他完成“复仇”全局的信念不再是被灭门的赵氏全族,而是自己的妻子及早夭的孩子。舞台上演员们用丰富的舞蹈语言书写着强劲的情绪张力,既让观众看到程婴身上“一义孤行”的不屈精神,又在忠孝难两全的踌躇中牵引出人性的挣扎。在《托孤》这场戏中,庄姬与家丁一起下跪哀求程婴收留赵孤,程婴表现出的神色不似京剧中的坚定,反而多了几分踌躇和害怕。只见演员胡阳跌跌撞撞地后退、用下跪磕头、翻身的动作来彰显程婴内心的惊慌失措。但当程婴看见家丁们被屠岸贾诛杀时,仁心仁术的他忽然就迈不开逃跑的步子,毫不犹豫地丢下药箱跑去营救……如此看出,程婴在畏惧与仁爱之间本能地选择后者。在目睹亲子被摔死后,胡阳用独舞将一个父亲的痛苦、自怨自艾及对妻子无比愧疚的心情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以上剧情的平凡化处理,皆是编导对程婴的普通人身份所作的合理申诉,同时又想消解舞剧的说教意义,使观众在强烈的情感落差下体验小人物的生命境遇。纵使程婴表现地再大义凛然,也不过是个被命运裹挟着被迫扛起道义重任的普通人。
一言以蔽之,舞剧中的人物逐渐从“大忠大义”的模板下抽离出来,聚焦于个体真实的生命境遇,对元版人物作重塑置换,以此在人文的关怀中彰显情感的魅力。
参考文献:
[1]田沁鑫.我做戏,因为我悲伤[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2]陈杰.经典戏剧作品的现代价值——21世纪戏剧舞台上的《赵氏孤儿》[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20(5).
[3]邹红.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历史剧《赵氏孤儿》的改编策略[A].和谐社会:社会公正与风险管理——2005学术前沿论坛论文集(下卷)[C].2005.
[4]宋尧.《赵氏孤儿》的京剧版与电影之比较批评[J].安徽文学,2014(5).
[5]文维丞.论“赵氏孤儿”主题的转变对剧本创作的影响——以《赵氏孤儿》元杂剧、京剧、电影剧本为例[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4).
[6]瞿锦雯.论田沁鑫版话剧《赵氏孤儿》中的女性身体书写[J].当代戏剧,2021(3).
[7]苏翔.浅析中国舞剧《赵氏孤儿》[J].民族艺林,2017(3).
[8]沈佳楠.个体生存境遇与生命经验的当代表达一浅析舞剧《赵氏孤儿》的改编策略[J].舞蹈,2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