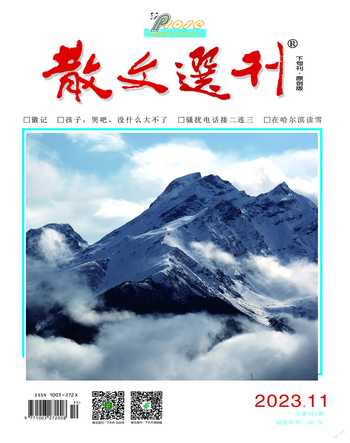稻上胭脂
冬文君
女子涂了胭脂,便有了颊边的一抹绯红,那是怦然的心动。这胭脂若是涂在了稻穗上,便成了传奇——胭脂稻。
这个名字曾在清末小说《红楼梦》里匆匆掠过一道倩影。第七十五回,富贵了一辈子的贾母,喝了半碗尤氏捧来的“红稻米粥”,剩下的半碗还要给王熙凤送去。而儿媳尤氏吃的还是白粳米米饭,惹得贾母直骂下人昏了头。而鴛鸯却道:“如今都是可着头做帽子了,要一点富馀也不能的。”在这一碗“红稻米粥”上尽可一窥曹公用笔之辛辣。贾母一出场,便是顶级贵族。这一碗粥,窥见的是一个钟鸣鼎食之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一角,盛这一碗粉盈盈粥的必然不是一只家常的碗,若依贾母以“霞影纱”配绿竹的审美来说,唯有龙泉青瓷才配得上这米中佳人罢!
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爱读《红楼梦》,把《红楼梦》当成活生生的社会历史来看,这一碗粥就是活生生的家常,就是活生生的封建社会。物以稀为贵,胭脂稻要比寻常水稻高挑美丽,高指的是较寻常稻高二十厘米,美指其稻穗为粉红色,所以当年被康熙大帝在西苑丰泽园内一眼相中,以“一穗传”的方式大加培育,成为御膳胭脂稻。
他作为资深红迷,对这一情节自然也是极为熟悉的。1953 年红学大师周汝昌确证了胭脂稻的存在,农业农村部有关方面查证产地,由此传说中的贡米再现真容。她就长在距京二百公里的唐山丰南王兰庄营田村,随即被中央部门收购十万斤送往北京,作为国礼招待国际友人。那是一个属于新中国的国际舞台,胭脂稻由此上了人民大会堂的国宴。
少时读《红楼梦》,一读婆娑悲宝黛,二读蹉跎感时悲,三读便因这胭脂稻。前两年,姊妹稀罕地拿来了一小袋粉嘟嘟的米,从未见过。与红米不同,红米皮红而肉白,这胭脂稻却是内外一色,蒸出来如同上等水头儿的好玉,粉妆佳人一般。只说这米外面买不到,托了好多的人情从地里买来,古往今来只有我们家乡本地产,还被曹雪芹写在了书里。拿来便马上用砂锅煮了粥,揭开锅来,香气馥郁,早上又把剩下的饭上锅一热,没承想这米粒却又长了一点,民间俗称“三伸腰”,回锅三次依旧粒粒饱满弹牙,而且一次比一次长。回头再去翻《红楼梦》来读,果不其然,光一个“米”便不下十种。
对食客而言,这几年的光景只是眨眼之间的事情。再见这米中美人已是今年的事情了,闲来无事,便去逛了早市,既有老农家带着露水的萝卜生菜,又有挪威进口的冰鲜帝王鲑和鲜活的波士顿龙虾。最让我欢喜的是遇见一个兄长摆摊儿,明晃晃地摆着脱壳的、没脱壳的、或深或浅的胭脂稻,这兄长年近四十,斯斯文文戴个眼镜,一看便是个读书人。
我买了几斤,便上前跟他寒暄起来,他的口音竟是南方人,是个中国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数年前投身于家乡,全身心地培育推广这胭脂稻。当时品种不稳定,产量极低,全依赖这兄长和同伴两人手工耕种,这也是这米百年来昂贵稀少的原因。胭脂稻如林黛玉,美而多病,因其高挑美丽,所以更易倒伏落粒,以致产量极低,一亩仅出一二百斤米,导致经济效益低下,所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险遭绝迹断种,大规模改种棉花。幸而,当年有一老农祖上向来种植此米,手中留下了珍贵的稻种,年年在河沿上小面积耕种,这支血脉才未曾断绝。今天的胭脂稻,正是由这留存的种子重新培育过的新品种。这位兄长和他的同行人,用尽十年光阴和数十万家财,杂交出了胭脂稻新品种,让量产与机械化成为现实。
这一把胭脂稻,当年曾卖到8000 元一公斤,终于在几代农民兄弟不断试种量产的努力下,把价格打到了每公斤百十来元,何尝不是一段传奇?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