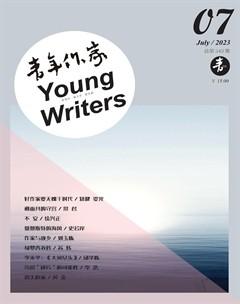绿梦青衣吟
歌头:浓稠墨绿
飞机降落前,从舷窗望出去,眼底下是一片浓浆似的墨绿。微型的道路屋宇、机场跑道,仿佛是拼力从那片浓稠绿浆里争挤出来的。抵达法兰克福后,马上就换乘火车前往慕尼黑。铁路沿线连绵的山原牧场,田畴农舍,或麦田的金黄,或玉米地的葱绿,都被这片浩荡起伏的浓绿逼压着、追赶着。仔细看,铁轨两边的密林,由一根根腰杆细直笔挺的红杉组成,搀手并肩地擎起这片绿云;远山上的浓绿色块,则是山山峦峦凝固着、积压着的一片片林海林涛,随意涂抹着浓淡深浅,显得默然而又怡然——绿色,原来可以是这么一种单一而丰富、咄咄逼人却又懒洋洋的颜色!车窗外掠过红瓦顶的村落,高高低低,错落有致。最吸引眼球的,竟是屋顶上、斜坡上并陈有序、鳞次栉比排列的太阳能光板。这是一大片浑朴、天然的乡野景观里,最“人工”“人为”的突兀影像,却每每把我心头的小鼓,撞得咚咚响。
——这是一方小小心心呵护着这片浓绿、又被这片浓稠墨绿仔仔细细呵护着的土地。难怪逢山必青,遇水必绿;见人呢,无论问路也好,路遇打招呼也好,不检票的城市交通也好,好像都因为这方浓绿氛围的环拥烘托,而变得随和、融暖与自然、自信了。
中国塔
是“休闲的狂欢”?还是“狂欢的休闲”?
说不清了。这两个词儿颠来倒去在我脑门上折腾的时候,我正在慕尼黑郊外乌泱泱的一大片“咸猪手”、啤酒盅和烤鱼片之间穿行。“咸猪手”这个词,原来就得自于这种德国无处不在的美食——烤猪肘。人声鼎沸。香气四溢。盛夏的炎暑,抵不过眼前一阵高过一阵的人潮热浪。连绵放射状排列的露天餐桌,随同着浪涛喧嚣一样的人声,海一样地铺满这个名为“英国花园”的城市中心地带。
穿越公园的小小而激蕩的溪流,竟然还设了冲浪区。一群半裸的小伙子轮流踩着冲浪板,在狭沟巨浪间起伏腾跳。
然而,被这一切狂欢热潮环绕着的中心,却是“中国塔”——一座带尖角飞檐的,据说已经有二百多年历史的五层木塔。檐端挂着小铃,塔的造型几乎融合了中式、日式、泰式诸般因素,也许是当初设计者按照他的“东方想象”造出来的这么一座“中国古塔”。二层塔台上,有一支像是由退休老人组成的小型乐队,在演奏着巴伐利亚的民间乐曲。塔下长桌环绕绵延,人流拥挤,啤酒杯碰撞,人海声浪一波一波地起伏激荡。杂色的遮阳伞错落其间,反倒成了沸腾海面上的一片片风帆。
入乡随俗。虽然平生与酒无缘,我和妻却要了一扎啤酒和烤鱼、香肠,选了一个树荫下的阳台位置,把烈日下奔波一天的疲身倦足彻底放松下来,随即,便融入到这片佻达、恣肆的人潮声浪里。
一曲终了,各成圈子的杂色人群并没有吝惜他们此起彼伏的掌声、欢呼声和口哨声。
这里是另外一个慕尼黑,和街上那个神色耿严、行色匆匆的慕尼黑迥然有别。
我想,就像学校里有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每每成年后会成为特别能干、能折腾、也能成事的人物一样,一个懂得放松、悠闲和玩耍的民族,才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民族。是的,一个善于享受“无用”之“用”——无功利地享受“无用”时光的人,才会是一个活得有生趣、有意思的人!
绿梦青衣
一潭绿酒,咕咚咚喝下去,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被一道绿色的闪电击中,噼里啪啦,心上的琴弦,会迸发出什么样的声响?
国王湖,国王湖,真的让我忌惮了。
这几乎是平生从未见识过的绿——如此清透明澈,却又如此深邃玄奥的绿!如此似梦若幻,却又如此在捧在握的绿!如此欲染欲燃,却又是如此俯首陷身、向你尽情倾吐的绿!天哪,竟是这样让人欲仙欲死又歌又哭的魔性的绿啊!
被阿尔卑斯山环抱的这座位于德国与奥地利交界的国王湖(德语:K?nigssee),据说是德国最深的湖。因由冰川侵蚀而成,故拥有如北欧挪威峡湾一样狭长的地貌,却又两岸青山夹峙,岚气相招,使人浑然不觉它巨伟的深度——那正是这“魔性之绿”的真正渊源吧。我们的自驾车穿过贝希特斯加登小镇来到这里,才登上游船,一霎间就陷身于这潭酒绿醉绿墨绿沁绿之中,真的像被一道绿色的闪电击中了。
靠着舷窗坐下,那酒样的碧涛就滚荡着傍你前行。游船可停靠三站——第一个克肖站没什么景点,一般无人下船;第二站名为“红顶教堂”,即圣巴托洛梅修道院,其间有一条远足的登山步道,下船的多是全副攀缘装备武装的年轻人;我们和大多数游客一样,选择的是水路最长的第三站——内湖飒勒特,也是为着可以一路“沉浸式”地和这汪醉人绿水盘桓痴缠吧。游船行近红顶修道院附近,两山夹峙间似有一道回音壁,一位大胡子船员举起一把小号站上了船舷,轻轻吹奏起一段莫扎特的轻快旋律。一时间山鸣谷应,连绵回荡的清响,在空间天际、心房耳畔腾跃穿越,连船头的浪花,都为之舞蹈起来了。好似又举起一支蘸满浓稠颜料之笔,再往这潭碧翠里添色加绿;又似在嚅嚅低语,解释着这片绿水青山与人之间的精神密码。我的心弦抖颤着,船舱里的掌声和着乐声节拍同奏,一时间丽日朗天豁然照心,雪浪清波荡洗襟怀,真是不知今夕何夕,在天堂还是在人间了!
都说明月清风无价。这里的明丽山水却是有价的。为着维持这潭澄碧醉绿不受玷污,据说所有来往船只都只能用电动或手动,不得用汽油、柴油等污染能源。游船的每一段旅程都计费精细(一站一计),甚至连刚才那曼妙的小号吹奏,都是要游客付小费的。据说两岸山边的许多豪宅住户都被政府搬迁走了,难怪沿岸所见的,大多是带独特徽号或航务标志的小屋。人类小心呵护般地付出,远远不足以抵消尔等对自然的巨大亏欠,而眼前自然赋予你我的心智享受与灵魂滋润,其“性价比”,却是大大超值甚亦是无价的!
一道斜阳,从山峡间如白练泻下。光,是一支魔棒,光波雾霭间的这汪绿水,娇迎傲复,笑愁多变,忽而幻化成了一个展演各种色彩角色的大舞台。最先跳入我眼帘的,是“大青衣”这个意象——眼前湲湲悠悠的绿水,绿得如此端庄哀艳又一唱三叹,可不是就化作了天地舞台间一位坦荡拂袖而来、碧翠透绿的“大青衣”?不远处,那一叠叠饱蘸光影岚气的乳色浪花,可不就是饰演慈颜母亲的“老旦”?真嗓真声、脆亮果断地呵护着绿得这汪稚嫩的新绿。嘿,那几道透着翡翠光斑的跳跃波澜,则就是功架齐全的“文武生”了;还有绿出各腔各调的老生、小生、巾生、官生等等,真是尽显“绿为百色之冠”的“角儿”的气场与才情呀!哈,岸边暗涌而来又画红映苍、飞花带卷的那片杂色的绿,于是就成为这个绿峡舞台上的“大花脸”了——无论是重“绿之吟唱”的“铜锤花脸”,还是讲究“绿之做工”的“架子花脸”,你们,都绿得如此夸张恣意、不管不顾啊!
——噢噢,山水,山水,真是宇宙的舞台,宇宙的音乐!山水以宇宙为怀,宇宙则以山川草木为其存在依据。山之高和水之深,这其实就是宇宙昭示的大理大道——时间与空间、有限与无限、渺小与浩大、付出与拥有、实体与虚无……都在山水里留痕,都以山水为教诲,都借山水作顿悟。所以人之“三观”——人生观、世界观和宇宙观,都随时需要山水的陶冶、山水的滋润和山水的洗涤。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云:“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眼前,这潭如梦之醉绿,恰是我等饱赏的醇酒而可以福乐于心啊!
“新天鹅堡”之殇
“李后主”“宋徽宗”——这两个名字嘭嘭敲击着我脑门的时候,我正行走在“新天鹅堡”的雕花甬道上。
德国巴伐利亚南部的“新天鹅堡”,被诸般旅游攻略解说为“迪斯尼游乐园”里白雪公主城堡的原型(西方有好几个古城堡都在争这个“原型”的专利)。它是最后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几乎倾毕生之力精心建造的行宮之一。可以用很多诗意和浪漫的笔调,去描述路德维希二世这位身材伟岸、长相英俊却终生未婚的年青国王。“Sentimentalism”——感伤主义色彩,正是这位年轻国王最突出的性格特征。路德维希二世在十八岁时(1864年)即登基成为国王,他与表姑——奥地利皇后伊莉莎白(即著名的茜茜公主)保持着终生亲密的友谊。两人同样热爱大自然和诗歌、艺术,互为知音知己,将自己分别比作老鹰和海鸥。 他崇拜作曲家瓦格纳并成为他的终生好友及资助人、庇护人。在他还是王子的时候(1861年),他第一次领略瓦格纳的歌剧《唐豪瑟》和《罗恩格林》的魅力,并为之着迷,喜欢在家里和至友一起扮演瓦格纳歌剧中的角色。于是这座他登基后亲自监工建造的“新天鹅堡”,便处处留下了“瓦格纳歌剧”的印迹。他想把城堡建成瓦格纳作品里的日耳曼神话世界,连建筑设计师都交给某著名剧场的舞台设计师担任。城堡内的装饰极尽奢华,变换着各种巴洛克、歌特式、拜占庭的风格,所有门窗、列柱、回廊,都遍布舞台风格的壁画和精雕细刻的图案。“天鹅”的意象自然是无处不在的,家具和房间的配饰都是形态各异的天鹅造型,连卧室、卫生间的水龙头,都设计为天鹅颈的样式。据说光是铺设“王位厅”一块由二百万块小马赛克石组成、镶嵌有巴伐利亚动物世界图案的地板,其工程就达两年之久。
可以想象,沉迷于瓦格纳幻想又痴迷于建筑的长达十七年的“新天鹅堡”工程建设过程中,王位上的路德维希二世对国事朝政是无所用心、无暇他顾的。1866年的普奥战争,登基不久的他在签署了战争动员令后,就把与战争有关的事务直接扔给了内阁部长,而自己则动身到瑞士与他的偶像瓦格纳见面。由于战败,巴伐利亚王国被迫接受对普鲁士三千万古尔登元赔款的和平条约,此外还将格尔斯费尔德地区以及奥尔布行政区割让给普鲁士。史载,“新天鹅堡”成了巴伐利亚王国灭国的最后标记。路德維希二世在他自己建筑的“新天鹅堡”中的最后逗留,是他在1886年6月被政敌软禁之时。三天后他在附近的施坦贝尔格湖因不明原因去世时,“新天鹅堡”还没有真正完工。在十七年的建筑时间里,他其实只在其中逗留过172天,那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房间是完工的。
行走在美轮美奂的“新天鹅堡”中,这位面容俊朗的路德维希二世的行为做派,无一不让我想起吾国千年史册中,那位写下千古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南唐皇帝李煜——李后主,或是创制书法瘦金体、院体画、宋瓷官窑的北宋末帝——宋徽宗——他和他们,都是艺术上有超人禀赋与惊世之才的“亡国之君”。我记得,自己很熟悉的一位兄长——哈佛荣休教授李欧梵曾把Sentimental(感伤,滥情)戏译为“酸的馒头”,并以“感伤主义与现代中国文学”为题,发表过许多振聋发聩的高论。一如不久前(2022年11月22日)逝去的林毓生先生所指出的:(人类社会)当逻辑的力量更多一点,情绪的力量更少一点,将会是繁荣与和平的时代;当情绪大行其道,逻辑无处藏身时,就是一次次的战争与苦难。
是的,“酸的馒头”——无论艺术或政治的滥情、感伤,并不能成治国安邦之器,也更不能为民生充饥,为社稷福祉奠基。眼前的“新天鹅堡”,似乎成为了烙印在“酸的馒头”之上的一个“国难”的图腾标记。
绿之梦 —— 萨尔茨堡与莫扎特
“嘚嘚嘚”的马蹄声,从拱形窗外飘进来。耳边讲解器传出的,是古钢琴脆短的键盘敲击声。眼前这位戴着白色假发的红衣少年,就坐在垫高的琴凳上,正给奥地利玛利亚女皇表演钢琴——完全是零距离的接触。手边,就是那张漫不经心潦草写下来的《小步舞曲》的五线曲谱,还有那封写给姐姐玛丽亚的笔迹时粗时细的信笺。隔着百岁烟云,我轻轻握住了他纤细的巴掌,让他止住他多动的手势和多言的嘴唇,静静陪我坐一会儿,听听此刻充盈耳膜与天地间的,那段浸透阳光和蜜汁的C小调弦乐四重奏。
——莫扎特,莫扎特。奇怪,中国的爱乐者喜欢把“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称为“老贝”“老柴”,却似乎绝少把“莫扎特”称为“老莫”的,都是直呼其名。在我看来,不是因为名字短(“贝多芬”也短),而是一个“老”字,怎么能落在那张永远一脸憨傻气、顽童气的嫩脸上?怎么可以罩在那一片片洒满朝露晨光、花馨乳香的曲谱上?听说莫扎特的乳名就叫“小狼崽”(Wolfy),那真是一匹欢跳着嗥唱着搅动文明旷野、人类星空的小狼崽啊!——莫扎特,莫扎特,人类永恒的青春之声,最青嫩、最澄澈、最纯真的生命歌吟,还有,最自然、最阳光、最痊愈的天籁之音的跳跃歌舞也!
因了莫扎特,萨尔茨堡成了全世界爱乐者神往追慕的一方梦土;又因了萨尔茨堡,莫扎特那短促的生命之光和飘渺的仙乐天音,才有了一片可触可感、可亲可近的永恒净地,与一座可以安放英灵、抚慰众生的不朽圣殿。作为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出生和长大的城市,走在萨尔茨堡的大街上,你在这里的每一扇橱窗、每一盏路灯、每一个街角里,都会遇见莫扎特——在粮食街上的出生地,你闻得见莫扎特婴孩时的乳香和牙牙学唱的稚语;在马卡特广场的莫扎特故居,你可以触摸到他闲置的乐器和频繁好动的手势和足印;那座自1842年起便屹立守护在莫扎特广场上的青铜像,在向你投来温煦而戏谑的目光;而坐到老集市拐角处那家咖啡馆里,你甚至可以听到莫扎特遗孀向你嚅嚅抱怨照应贫弱多病的莫扎特的烦恼,还有直到临终前他还欠下的一大堆债条账单……莫扎特,莫扎特。空气里是莫扎特,巧克力是莫扎特,纪念茶杯是莫扎特,路边卖艺者奏的是莫扎特,整个萨尔茨堡的旅行中,真是一分一秒都离不开莫扎特。以至于,我在登车不舍离去的瞬间,心生一念却又陡然一惊:倘若没有莫扎特,今天的世界,会是一番什么模样?
——噢噢噢,那真是一个可怕的想象也!就像不敢问也不敢想象:中华文明漫漫的历史长卷中,设若没有了李白、杜甫、苏东坡,会是怎样一幅恐怖难堪的图景一样!此刻,我的脑海笔底浮现的是:失去了地球上的一大片绿——弥满人类精神心智空间的这片嫩绿、青绿、苍绿、醉绿,被无情抹掉了!那是孕育生命的绿,又是抚养文明的绿;既是滋润生活的绿,更是拯救灵魂、维系思维和创造及成长的绿——那,真是此天此地、斯土斯人如诗如梦、不可或缺的一片澄明大绿啊!
维也纳冷落贝多芬
说是冲着音乐选的维也纳,其实是冲着贝多芬而来。如果说莫扎特属于大地青山不可或缺的那一片绿,我们忧郁的音乐圣徒贝多芬,则就是属于星辰大海须臾不离的那一片蓝了。然而,很失望,在萨尔茨堡可以随时遇见莫扎特的“绿”,我却在号称音乐之都的维也纳,很难寻觅到我心目中贝多芬的那一片——“蓝”。
不想细描述,作为欧洲桂冠城市的维也纳那众多雍容华贵的景点之面相。夏日的热浪滚滚中,我们避开了满街私人导游会用中文向我们叫嚷的那个“金色大厅”,直奔各种旅游攻略均言万不可错过的“美泉宫”——可以媲美法国凡尔赛宫的奥德帝国当年的大皇宫。无论为王超过六十年的约瑟夫皇帝的勤政业绩,或是茜茜公主的美貌和人生传奇,还有她那位母仪天下的“恶婆婆”玛丽安娜皇后(角色一如晚清中国的慈禧太后)的奇特行迹,包括拿破仑的儿子去世时所住的那个房间及其病逝塑像等,都可以用中国文化中的“兴亡叙事”来作幽思感怀。但作为华夏游子,美泉宫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偌大宫殿中遍布各殿堂、寝室的中国元素——各种精美瓷器、大小花瓶、屏风的中式装饰。有一间号称造价最昂贵的房间号称“中国蓝屋”,墙纸为手绘的中国青花图案,加以精致的中国漆画作边饰。我凑近一个大立花瓶,细读出上面的中文字——“藏春亭三保造”,可见,当年的“中国制造”在那个欧陆帝国时代,是意味着高档奢华甚至高雅品味的,也可以呼应今天的“Made in China”的世风潮变了。
傍晚,在美泉宫边角的餐厅用完晚餐后(吃了维也纳名菜——炸猪排),我们听了一场皇宫交响乐队演奏的音乐会。这种为游客准备的音乐会水准差强人意,当时我并没寄望太高,却又略感诧异:曲目基本都是莫扎特与施特劳斯,唯独没有贝多芬。剧场效果连歌带舞的很热闹,却让我有点怅然若失。
翌日大清早,参观完金碧辉煌、精美绝伦的维也纳艺术博物馆后,我们就开始了寻觅贝多芬遗迹之旅。先是到闻名遐迩的市中心公园去看各位音乐家的纪念雕塑。最精美的,自然是汉白玉拱门下那个施特劳斯侧身拉小提琴的金色塑像。舒伯特、布鲁克纳等音乐家的塑像,也都是精雕细刻的讲究。在园区寻找一圈,就是找不见贝多芬的塑像,很觉奇怪。幾经问询,终于在园外对街找到一个“贝多芬纪念广场”,却是人迹冷清,境况寥落。那个贝多芬青铜坐像落满鸟粪且污垢不堪,半圆的小石坪广场上长时间疏于管理修整,显得残破不堪(与刚才园内那些精美纪念雕塑相比,感觉尤甚)。更蹊跷的是,贝多芬自1792年二度抵达维也纳后,一直到1827年在此地逝世为止,他的大部分音乐作品和崇高声誉都完成于维也纳;而“乐圣”贝多芬在世人心目中的崇高位置,更是不言而喻的。于是在我想象中,“贝多芬故居”必定会成为此地最热门的旅游景点。可是,从网上搜到的遗迹地址,整整大半天的四处游走,几乎问遍了全城竟然都无人知晓——何处为“贝多芬故居”?最终,直到离开时我们也没能找到,想来真是咄咄怪事!我随后也注意到,各种招揽游客,遍布维也纳全城各种教堂、演出场所的夏天音乐会,其演出曲目也大多是莫扎特和施特劳斯,而完全不见贝多芬的踪影;贝多芬墓地坐落于偏远的维也纳十一区,却又因旅程太短而无暇顾及,以至于我出发前就规划的到维也纳好好瞻仰一下贝多芬的故居遗迹以及听一场贝多芬的音乐会,完全“一脚踩空”了。
实话说来,维也纳何以会如此冷落贝多芬?绿野遍地的维也纳,何以会少了贝多芬这片“蓝”?我至今不得其解也!
莱茵河上“晤”赵元任
都说我这个人有“老人缘”——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每个阶段,总会有为我指路、助我成长同时与我心灵相契相通的老人相伴。我曾与张充和、赵复三等老人家成了忘年好友,甚至有幸为其中一二老人送终。没想到,隔了洋又隔了代的,这“老人缘”,还真结到了莱茵河上。
赵元任,这位二十世纪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奇才人物,我本已有幸于那些年(1980年代)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与他非常疼爱的大女儿赵如兰结缘——我成为卞赵家中每月举办的“康桥新语”文化沙龙里的“茶童”,每次聚会必由我负责给大家沏茶端粥,被如兰教授戏称我为“茶博士”。万万没想到,这次借参与一场法兰克福的盛大演出而顺路周游欧洲四国,却在莱茵河的游船上,与赵元任的亲外孙黄家汉和北平夫妇相遇,又续成了我的另一段“老人缘”佳话。
赵元任家“一门四凤”。他的四个女儿中,二女儿赵新那毕业于哈佛大学化学系,1949年后没有随父母定居美国,而是和夫婿黄培云一起留在中国,为长沙中南矿冶学院的教授。赵元任的外孙、赵新那的孩子黄家汉与我同一辈分,都属于“文革”中的“老三届”,都有过上山下乡当知青的经历。所以,自从参与到这个和知青题材有关的合唱组曲的演出后,在辗转美国、澳洲各地的演出中,他们夫妇俩便和我这位歌词作者结下了很深的情谊。这天清晨,我们结伴一起登上莱茵河的游船,在夹岸的群山古堡之间,流水清波,美丽传说,一同荡漾在我们的谈笑风生之中。
船过一道曲弯峡岸,随着导游解说,船舱喇叭里传来一段优美的乐曲。“罗蕾莱之歌!”家汉兄轻声唤起来。这首由诗人海涅作词的著名德国民歌的曲调,大概是当年博学而跨界的赵元任在家中时时向女儿们吟唱的,因而从女儿流传到孙子辈的记忆里。我们都一起把视线投向舷窗外,那片传说是罗蕾莱出没的河面上。清风习习,流水悠悠。绿绸缎似的幽静河面,此时似乎隐现出那个名叫“罗蕾莱”(Lorelei)的金发仙女。一身白袍,长发飘飘。据说她是来自岸边的村姑,爱上了一位远航未归的水手,夜夜在河边歌唱,最后思念成石,化成了河畔一座秀美的山峰。每在月光皎洁的夜晚,路过船只的水手每每会为她魅人的歌声着迷而不慎触礁沉船,而更有众多有幸听过她歌声的人们,从此便被好运和幸福追随——“罗蕾莱”,因之也成为德国文化中一个代表安详、尊贵的象征。
“不知为了什么,我会这般悲伤,有一个旧日故事,在心中念念不忘……”那幽怨的歌声还在河面上荡漾回响,这时候,家汉兄打开了随身的背囊,把一大摞纸张陈旧的杂物轻轻摊到小桌上,有相册,也有散页。他微笑道:“知道你和我大姨趙如兰熟悉,还曾是她家的常客——那是外公回哈佛最常住的居所呢,我今天特意带了些家里的老东西、老照片,想和你一起分享。”“赵元任!”于我,这确是一个大惊喜:我万万没想到,在遥距故国千里万里的莱茵河上,一位世纪老人的面影和足迹,会如此真切地铺展在自己眼前!我轻轻翻检着眼前这一帧帧泛黄发白的老照片——赵家四女儿与父母的早年合照,赵元任早年在耶鲁雅礼协会门前与孩子盘坐着的合影(我指点着说:这楼房我很熟悉,就在我办公室隔壁!);特别是一九七三年赵元任首次回国探亲时,家汉的父母赵新那、黄培云陪同父亲一起受周恩来总理接见的合影,还有一九八一年最后一次回国期间,赵元任老人家放怀高歌《叫我如何不想她》的留影……一位世纪老人斑驳却绚丽的人生足迹,一个世纪的烽烟战火、离合悲欢,一时间都在这莱茵河面上弥散、滚荡。家汉兄特别提到,那次他父母陪同赵元任见周总理的一幕:因为气氛极其融洽喜乐,从晚上七点一直聊到十二点还意犹未尽,周总理还特意为大家安排了夜宵。历史的逸闻和时光的碎片,随着眼前的莱茵河波浪起伏,绵远流长,熠熠生光。我注意到照片里的赵元任老人家,几乎每一幅都是面带笑容的,并且每每笑得放达灿烂。爱笑真是外公的特点,家汉说,我们家人每次聚会,也都是被幽默和笑声环绕的。我便说起赵如兰先生当年叫我“茶博士”,在英语里是“Dr. T”,其实是当时一部肥皂剧里一个五大三粗的搞笑角色。家汉和北平也熟悉这个电视上光头裸身的滑稽角色,不禁和我一起放声大笑起来……
“水流天不尽,人远思何穷”(苏轼《宿余杭法喜寺》)。此一刻,历史与人文的记忆流水和着莱茵河的绿水一起滚淌,仿佛也陪伴着海涅的“罗蕾莱之歌”不息地歌唱……
此次欧洲之行——数国之间十余日的自驾行旅,日复一日,我们穿行在一片又一片漫无际涯的绿之中——是的,绿。浓绿墨绿嫩绿青绿苍绿醉绿……从机翼下那片浓稠如浆的绿,到国王湖浓酣若酒的绿;还有萨尔茨堡和莫扎特带给世界的那片青春永恒的绿,以及莱茵河上“罗蕾莱”和“赵元任”赋予天光流水的那片闪烁着史色史光之绿……
噢噢,那真是一件覆盖整个欧陆大地的“大青衣”——那是贯通此次行旅舞台的这位“大青衣”的无尽歌吟啊!我知道,自己这个奇特的譬喻,其实正属于某种“以心照物”之见。哦,这正是近时读王阳明的“心学”所强调的:“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以心在旅,以心观景,万物寓心,心寓万物。我神往沉醉于世间这片绿,消弭了肤色、地域差异的灵明之绿——这也可以印证西哲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通过认识世界的神秘而达致完全幸福。”这片“大青衣”的绿梦想象,是这个蓝色星球上,人类千百年来前赴后继,不息追求的幸福安康、自由梦想的永恒之绿啊!
【作者简介】苏炜,中国旅美作家、批评家,任教于耶鲁大学。著有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迷谷》《米调》《磨坊的故事》,散文集《独自面对》《走进耶鲁》《天涯晚笛》《听大雪落满耶鲁》等;现居美国康涅狄格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