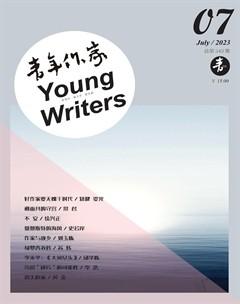旷野的风
史若岸
窗外的雨微微下着,时断时续,天空堆满了云,灰白色占据了主要视野,让人心情也跟着抑郁。无论怎么看,这都不是一个适合相亲的好天气。
不过和女生见面的日期已经提前定在了今天,且工作刚好不忙,可以早点下班,因而我还是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了餐厅。餐厅人不多,环境相当清幽,我选了一处靠窗的位置,坐下后,低头看了眼手表。时针与分针组成了一条完美的直线,六点整,刚好没有迟到。
手机屏幕也在此时亮起,我看到了来自女生的信息。快到了,请再等我十分钟。我回复了一句好的,重新把手机放下。
对于即将到来的见面,我的心态很平和。已经不是第一次相亲了,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曾瞻前顾后,觉得每一次见面都背负着极大的压力,既担心自己被对方拒绝,又担心自己需要拒绝对方。前者使我失望,后者令我负担,这二者无论是哪一种结果,我都觉得分外难堪。我不想成为被挑选的一方,却也不想拥有这个棘手的选择权。后来,相亲次数多了,熟稔随之而来,最初的压力逐渐消弭,取而代之的,成为了不断重复而产生的麻木与疲倦。
总而言之,相亲就像一场竞技游戏,匹配的人不难找到,合适的人却几乎没有。我渐渐习惯了没有结果的结果,对相亲的态度,也不再如开始时那么认真。具体而言,大概就是像那种不得不打起精神去面对一场中等规模考试的心态,也会紧张,可是熟悉了流程与结果,一切便成为了一项只需按部就班就可以完成的任务。我不必再为此有任何头疼的感觉。
与此同时,我也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一些与相亲有关的心照不宣的暗语。诸如见面之后再无后文的回复,以及所谓的有时间再聊,这些隐晦的拒绝手段礼貌而得体,既解决了我最开始相亲时的担心,也符合了大家普遍认可的体面。毕竟成年人的世界里,很多事情无需挑明,若真的执着于一个明确的答复,反而显得莽撞与不近情理。
这的确节省时间,只是次数多了,我有时也不免觉得这种方式过于冷漠,仿佛参与的是不涉及任何情感的商品买卖,而不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交流。不过感觉上是一回事,真正实行起来,又觉得它行之有效,因而尽管心存不满,我还是在行动上遵循起了这样的规则。
以沉默为主的拒绝中,当然也有例外。我见过最有趣的拒绝方式来自一个披肩发的女生,她戴一顶宽边鸭舌帽,穿宽松的黑色T恤。我们聊得很好,也很尽兴,但她最后和我说自己小时候算过命,她是观音座下的童子,观音太喜欢她,不舍得她离开,因此她一生都不能结婚。如果不是她垂下头时,嘴角露出一丝掩饰不住的笑意,我差点信以为真。我忍不住问她,既然如此,何必来相亲。她说,实在拗不过介绍人的热情。这下轮到我尴尬了,为了我的事,母亲恳切地拜托了许多人,想来这位过份热心的媒人就是其中之一。我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说看来自己也应该去算个命,兴许是太上老君的童子也说不定。
她拒绝的理由别致而新奇,一直让我记忆犹新,我曾一度想要拿它当作婉拒别人的借口,但自己毕竟不是贾宝玉,没有神璎侍者的加成,岁数也到了不宜再故作幽默的而立之年,搬出这样的借口,反而显得我这个人有些油滑,最后只好不情不愿地放弃。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感慨人生易老,上学分明是昨天的事,但就像大多数人所说的,光阴易逝,时间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消失。在这些匆匆而过的年月中,我既未做出什么大的成就,也未实现什么足以为外人道也的人生理想,日子过得就像一只永远打不翻的船,自己就坐在这安稳的船上,成為了一个比无趣更无趣的人。
在乏味的生活里,相亲有时会成为平凡生活的一点调剂,除了前面的披肩发女生,我还遇到过一个浅棕色眼睛的女孩。她的头发染成了浅金色,非常美丽的颜色,但新长出的黑色头发像海浪一样向下,打破了原有的协调性。她一边吃东西,一边向我哭诉前男友的种种劣迹。我像情感咨询专家一样静静听了她两个小时的哭诉,最后也像专家一样给了她自己的解答。你一定还喜欢他。我说。她愤愤地看了我一眼,像是在指责我没有资格这么说,但对于我的判断,她并没有否认。
临别前,我夸她的发色好看。她嫌弃地看了我一眼,说那是掉了的颜色,原来的颜色是粉色。接着她又说,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奇怪的人,就像个一点脾气都没有的王八。
我姑且把这句话当作了赞美,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她大概觉得不好意思,飞速加上一句,但不让人讨厌。
然而,也就到此为止,事实上,当时我依然没有忘记前女友,只是漫长的异地恋消耗尽了彼此的耐心,未来已经毫无可能。接受相亲,也不免带了一点逃避的心理。这个能够堂而皇之表达感情的女生是我唯一不感到亏欠的相亲对象。如果我与她见面的时间再晚一点,兴许我们会发展出一些自己也料想不到的结果,只是大家既然都没收拾好心情,也就无需再多添一个负累。
此后断断续续,我又见过一些女孩子。在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见面模式里,我发现它其实是一面很好的镜子,你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自己。这听上去有点奇怪,但我的确从相亲中感受到了一点与其他交际所不同的东西。当恋爱与结婚成为彼此见面的目的后,你总是可以见到相当多的真诚。这种真诚不掺假,灿烂如阳光照耀的湖面,明晃晃地耀眼。无论怎样,真诚难能可贵,就像天空中飘过的特定形状的云,不会是一朵,但也不会是很多朵,见到它的时候,总是禁不住想要停留。
以人为镜的好处就在这里,由于这种稀有与丰富并存的真诚,我得以见到了客观的我。这个客观的我让我觉得既熟悉又陌生,仿佛一层多重的影子,让人有亦真亦幻之感。但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最真实的我。就像老话所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我注定只能成为当局者时,清醒便只能从旁观者得来。
不过来自旁观者的自我,我看着玻璃中的自己,我又能触碰到几分呢?
发现玻璃中忽然出现了另一个人影,我方才意识到自己走神已经走了很久。
眼前出现的即是今日要相亲的女生,她没有再问我具体的位置,但靠窗处本就没有几个人,单独一个的只有我,用不着再次确认,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我。
我站起身,邀请女生入座,她点点头,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此前我已经在照片上见过她,照片中的她看上去十分文静,面容虽不能说有多么出众,但也并不丑陋。人们在设想家庭美满的妻子时,眼前往往会浮现出这样一张脸,没有攻击性,也没有什么记忆点,但很安宁,很舒适,让人觉得可以安心地在她身边睡着。
这样的女生不能说是我喜欢的类型,但也绝不讨厌,因而我主动约了她见面。
和照片相比,现实中的女孩更生动一点。她穿着一件米黄色的连衣裙,身形偏瘦,淡而朦胧的五官因为有了灯光的装点,多了一些柔和的色彩。
她落座后,看了看我,又很快移走目光。她把双手叠放在一起,一只手用力地握着另一只手的手指,仿佛不知道怎么做才合适。
我想起介绍人的话,对方是个腼腆的女孩子,不太爱说话,因而我主动开了口。
有什么想吃的吗?我问她。
她摇头,示意我随意。
有忌口吗?
她继续摇头。
我按照自己的喜好随便点了几道菜,交给了服务生。等待菜肴上桌的时间里,我试图向女生搭话。女生的应答很简单,大抵只有是或不是,声音也很低,像是在回答老师的问题。看得出,她在试图配合我,但她显然不擅长聊天,更不擅长回应。我像抛羽毛球一样抛出的话题,被女生在一回合间就倒扣回来,迅速得让人完全接不住。几个空掷的回合过后,本不拘谨的我也开始拘谨起来。
我算不上幽默风趣,聊天也不怎么在行,在大部分场合中,我都是沉默寡言的那一个。只不过一旦说话的责任落到我头上时,我也会主动做一个活跃气氛的角色,以免出现任何尴尬的冷场。由于这一缘故,我获得了一些亲切友好的评价。我不讨厌这样的评价,它让我感觉自己是个有分寸的人。这意味着成熟,以及风度。有时我也不免刻意去表现这一面,借此展现自己良好的社交能力,证明自己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正常人。
但在今天,这套周到有礼的法则仿佛失了效。在女生惜字如金的应答里,我陷入了一场尴尬而笨拙的独角戏。声音被置放在了真空中,徒留眼睛看着嘴巴不停地一张一合,耳朵却发现不了任何附和。
我安静下来,向女生看去,她没有看我,也没有对这突如其来的沉默感到不适,只是握着茶杯,双目低垂着,默默注视眼前的餐具。由于一种内在的固执,她的沉默仿佛一具古老的化石,化石周围长满了规规矩矩而又生气勃勃的杂草,在无法捕捉到杂草随风摆动的节奏前,任何话语都像是一种打扰。
我有些迷惑,我不知道女生的安静是因为面对我,还是与生俱来。如果说她对我感到不满,她的拘谨看起来是如此真实。如果说她对我感到满意,她的沉默却又如此地拒人千里,不给人留有任何开口的余地。
经历了数次相亲后,我以为自己已经能够从容应对各种各样的局面,没想到还是在这个少言的女生面前败下阵来。一种类似输掉游戏副本的挫败情绪笼罩了我,我生出一种颓丧之感。就在我考虑要不要继续表现自己的得体时,餐厅的服务员端来了菜肴。
吃饭吧。我说。
嗯。对面传来简单的回答。
周围再度安静下来,只有餐厅的扬声器播放着介于流行与过时的音乐,其中一首音乐正是我大学时最爱听的歌曲。借由这首歌曲,我可以重新想一个良好的开场白,我可以与女生聊一聊大学时期的生活,自己所学的专业,以及那些发生在大学校园里,虽然无趣却莫名记得一清二楚的往事。
我张开嘴,却顿住了,忽然觉出了疲惫,也有点想要破罐子破摔的意图。说到底,这只是一顿晚餐,我何必非得强行表现自己。既然女生保持了沉默,那么我的沉默也同样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它完全是另一种形式的通情达理。
想到这一点,我彻底放松下来。
没有再做任何事,我开始专注起眼前的食物。我已经很久没有心无旁骛地体会过食物的滋味了,重新感受起来,居然会觉得惊喜。就像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每一道菜的味道也都不尽相同。同一道菜,尝起来总会有细微的参差。甜与咸、热与凉、脆与软,交织构成了一个只有食物本身的世界。我的感知力在这个专注于食物的游戏中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它让我想起了许多童年时才拥有的快乐。但我毕竟不是美食家,无法长久地将注意力保持在食物上,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感觉游戏。
总体而言,饭菜的味道不好不坏,是标准的模板化味道,保守而穩妥,如果不是特意关注,它不会引起你丝毫的注意力。作为交际工具,这样的饭菜相当足够,不喧宾夺主的同时,它几乎是在催促你一心二用。
无须说话,无所事事的我只能走神。
窗外的雨已经停了,看样子也不会再下,天气预报说明日转晴,兴许明天会是一个好天气,我可以起得稍早一点,多晒一晒太阳。不过比起关心天气,我可能更应该关心一下股市,手里的股票一路下跌,已经绿了好多天。我的上司曾经说过,在没有逻辑的情况下,按照逻辑买股票是一件自作聪明的蠢事。既然这样,那我确实应该和他好好学习学习,但他好像从来也不打算让人知道他买的是哪一支股票。如果他坐在这里的话,我更应该学习一下他侃侃而谈的说话方式,兴许他忽悠人的能力就是在饭桌上锻炼起来的。
就这么想着,我的筷子不经意将一片装饰用的薄荷叶放进了嘴里。沁凉的苦味在口腔中漫延,仿佛是绿箭口香糖去掉糖的味道。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舌尖上有一片叶子正在发芽。
我抬起头,看了一眼对面的女孩。
她依然没有看我,低着头,沉默地咀嚼着什么,不发出丝毫声音。她的坐姿笔直而端正,吃饭的姿势优雅得体。
我重新低下头,不再有任何开口的欲望。
并非因为女生的疏离而感到灰心失意,我本来也没有抱有任何一丝想要继续发展下去的心情,只是想单纯向她推荐一下薄荷叶的味道,毕竟这种感觉很特别,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体验。它可以为这场过分沉闷的晚餐增添一点轻松的点缀,就像在黑色的衣服上别上一枚银色的小胸针。
使我真正感到失望的,是当我惊喜地抬起头时,却发觉对面的人依然陌生。
虽然职业、外貌、家庭,性格,所有可以概括的条件都已经知晓,但面对面坐在一起,也只是两个一起吃饭的陌生人。我无法轻松地将女生从沉默中拉出,女生也无法自如地在我面前展示她自己。
一切看上去都有一点荒谬,但因为相亲这一既定的规则,一切的荒谬便也理所应当起来。
柔和的灯光下,女生的美突如其来。我忽然发现,她高傲内敛的姿态宛如一幅新古典主义油画,高贵而静穆,端庄而典雅,让人不由想要静静地观赏。
但仅此而已,女生的美是特定的,也是不可靠近的,如果拿一件事物作比,那就是一支正在烛台上燃烧的水滴形状的烛火,有烛台,在燃烧,这美方才能够实现,也方才拥有意义。除此以外,一切依然是日常的苍白。因而,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美,我没有去打扰,而是将它留在了原地。
一直到晚餐结束,我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吃完饭,我们一同走出餐厅。晚风带着微微的凉意,霓虹灯下,女生耳朵上戴的玻璃坠子在灯光下一闪一闪,像两颗星,与四周的夜景交叠在一起,显得模糊而柔和。
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要一起看电影吗?
她看了我一眼,然后回答道,好。
我有些意外,这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答复,但话已出口,没有再反悔的理由,于是我们又一起去了电影院。
我们看了电影,互相说了再见,就没有了后文。和大多数相亲一样,她没有联系我,我也没有联系她,一切不了了之。我以为这就是结束,直到一周之后,我才从介绍人那里得知她对我印象颇好。介绍人问我是否愿意与她继续相处,我犹豫了片刻,没有答应,却也没有拒绝。
她的安静让人无措,但毫无疑问,和这样的女孩相处下去,一定会拥有一段安稳而舒适的关系,这是我一直以来希冀拥有的。她的沉默既然并非是在表达拒绝,那我自然也不妨再主动联系一下她。只是那时我正要出差,顾不及再与介绍人说什么,便匆匆离开了。回来之后,又忙着应付季度的工作总结,各项任务堆到一起,忙起来没日没夜,这件事便耽搁了下去,我和她也就这样错过了。
说到底,我最终没有联系她的原因,还是不够喜欢。我对她仅仅是不讨厌,不讨厌和喜欢之间差着十万八千里,喜欢是能够熄灭火焰山的芭蕉扇,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效得威风凛凛,而不讨厌只是一把平平无奇的扇子,只有正好遇到了夏天,才会让人想起它。
现代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本就纤弱,无须做什么,自然而然就会飘散向再无交集的方向。雖然我依然保留着女生的微信,但合适的时间一旦错过,便只能任由它沉入深海。这以后,我继续忙于工作,为我世俗而亲切的薪资奔波。相亲的事宜虽然暂缓,但在父母的费心张罗下,也依然有条不紊地推进着。
很久以后,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当我接起后,听筒那边传来了长久的沉默。就在我打算挂掉的时候,我忽然猜到了对方可能是谁,于是我静静等待着。又过了一分钟,沉默消失了,听筒处传来了滴的声响。我握着手机,一时有些迷惘,既不是惋惜,也不是遗憾,而是一种怅然,像一阵来自旷野的风,在我心头久久徘徊。
旷野之上,风带起全部草叶的晃动,绿色的波涛声里,鸣虫奏响不息的音乐。天地被声音包裹,呼吸的世界里,万籁俱息,万籁俱沉。
那一瞬间,我仿佛又一次看到了女生,她在灯光下静默地微笑,耳坠一闪一闪,就像夜空中的星星。我低下头,看着手机上的来电号码,拨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