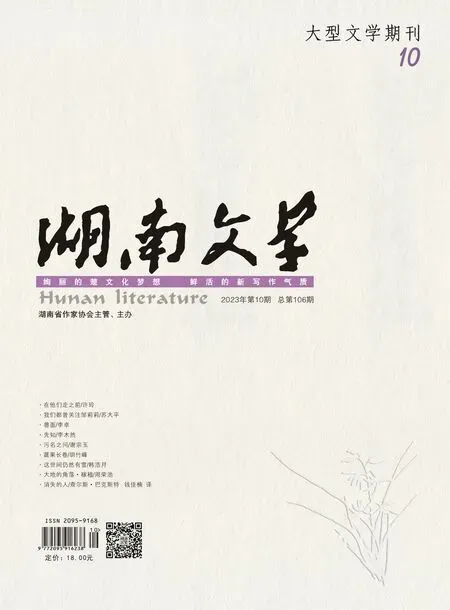大地的角落·稼穑
周荣池
庄稼并不全是粮食,耕种和收获也并非全为饱暖,也有一言难尽的滋味。尽管稻麦占据着平原的大多数时空,但生活是由更多貌似平凡的角色支撑着。那些生长在“十边地”的草木有它们自己的果实,有些也试图成为主角而最终未能如愿。但它们仍是村庄里的一部分,不管是离开了还是依旧生机勃勃地站在田野的角落。
一
油菜花开得很突然。平原上一夜之间被花朵分割成无数的独立王国。从来没有一种色彩这么霸道,铺天盖地般把土地遮盖了起来,除了村庄和麦地,菜花和河流一起在那十数天尽情铺张。
就像信风一样到来的放蜂人,在村庄的边缘安营扎寨。他们一定也见过很多珍贵的花事,但平原的花海有自己的格调。油菜是很少种在大田里的,田头路边以及所有能到达的空白地,都可以让人发挥想象。这里很多被水隔绝的地,叫作垛田。垛田上装着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把大片平坦的土地交给口粮,其余的每一处间隙都用菜花装点起来。因为油菜的播种和收割都是手工的,所以人们并不畏惧零碎与散漫。油菜也不计较什么,阳春一到便拼命地开放,就像妇人放肆地大笑。
我喜欢奔走在花丛里,让黄色的花粉沾满朴素的衣裳。这其中有一种很美妙的情绪。是执拗和倔强,在浓密的花窠里奔走。这并不是爱美的样子。但村庄里是不需要美的。譬如你要是和一个农人说这些花美,他只会说:这些花开疯掉了。花是会疯人心的。那种密集的纯黄在大地上铺陈,一直萦绕在脑海里,让人有透不过来气的感觉。所以便要奔跑,要深入,要逃脱。我不害怕父亲的指责。他可能也觉得村里的孩子不应该是那种体面的样子。他总是这样反问计较的邻居:不顽皮的怎么能叫孩子呢?
我感觉得到叶下沉积的阴凉,叶片上残余的露水,还有花瓣撞在脸上的轻柔。无边的花香令人眩晕,所以我想不停地奔走。日后回想一切如同梦呓。但这些滋味是不能说出口的,否则村庄就会笑话我煽情与蠢笨。油菜的花事很短,也似乎是一瞬间它们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几只掉队的蜜蜂在其间无聊地嗡嗡作响。放蜂人已经走了。他留给队长半斤蜂蜜,此外没有卖掉一滴。这里的村庄不信任过于甜蜜的东西,人们觉得不真实可靠。他走后还留下蜂箱压过土地的印记以及做饭时候滴下的油污。只要一场雨洒下来,这些会和花事一样突然消失。这里毕竟不是他的村庄,所以不需要留什么证据。他的村落在路上,在花瓣里才对。
收菜籽是一件辛苦的农务。一刀刀地割下来,就像是一次次耐心的谈话。植物里那些细小的种子就像心思一样绵密。在改良的种子没有进入村庄之前,油菜的收成十分艰难。一切与这贫瘠的土地境况相像,瘦弱的本地种子榨不出多少油水。人们也并不计较什么且还嫌弃新来的种子并不香,打算卖给城里人去吃。村庄里很长一段时间有这种习惯——把本地的种子单独留着自己吃,又把那些轻易得到的品种都托给城里去。其实他们大概忘记了,那些在城里扎根的人们,也曾经是老家土地长出的种子。
每一棵庄稼都是辛苦的。棉花是从另外一个遥远的村庄引进的。每一个村庄大概都有自己的特长,因为水土不同且人的秉性各异。村庄从外面新引进一种植物,有着新老更替的悲情意味。人们被一如既往的辛苦折磨得疲惫不堪。他们也并没有完全指望新来的植物会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善。种地总是被觉得是一种无奈的办法。棉花种植的过程要比粮食更为繁复,一道道手工程序在人们的忍耐中与时光周旋。农民甘心在日复一日中等待:浸种、制钵、育苗、移植、锄草、施肥、打枝、摘花、晾晒及至装袋,最后等待的是收花站里的定级。最辛苦的还有最后一道程序,要在秋风中把那些棉秆拔上来。其时它们已经一无是处,可还要一棵棵拔出来,把土地还给季节。父母们手上起了水泡,粗线白手套里有十指连心的疼。他们咬着牙,就像在努力地拔除穷根。
可是贫困是扎了根的,比任何植物都顽强。桑本是早就长在村庄里的。它们轻薄的叶片常被掳来喂鱼。除此之外,还有几枚初夏时候瘦弱的紫色果子受孩子们的青睐。长得像样的桑树会被用来制成扁担。它们也害怕承受太多的负担,所以一般都是随心所欲地生长。这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方法。看起来没有什么志气,但默默地保全了自己,可能是一种古老的智慧。后来湖桑进了村庄,人们养起蚕来。养蚕也并不是新近的事情,平原上早就有这种营生。秦家垛出生的秦少游一定是干过这种辛苦生计的。他写出了《蚕书》,又好像和他风流才子的气质不符合。农民认为读书算是才华,没有人把务农当才气。后来他的子孙有一支迁到了附近的东角墩,却又做起打鱼的营生,虽远近闻名,但也没有被认为是才华。
好日子当然也不是养蚕人过的。那些精致的茧子后来成了城里的衣裳。湖桑老了之后,叶子也就不那么精神。人们就放弃了那些肥胖的虫子那些树就被遗忘在远处,和村里的野树一样,不再值得被提起。这大概就是这些外来植物的必然命运,因为人们始终还是信赖粮食。薄荷也曾热闹过好一阵子。那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有巨大的炉灶,林立的烟囱让人误以为是城里的工厂。薄荷占据了部分良田,村庄里到处都是清凉古怪的味道,连河流里的水都变了滋味。可城里人突然降低了价格让辛勤的人们绝望起来——最后将那些清香的植物斩草除根,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念想。
庄稼不能固守自己的村庄,是充满着险情的。
二
因为经济作物总是显得不可靠,人们就认命地回想起充饥的植物。粮食不管行情如何艰难,总是可以留着果腹的。山芋就是这种实诚的植物。集市上买回来的藤苗,就着雨水栽在垄子上便不必理会,它们会自己默默地生长。要是长得太欢快了人们就会不满意地打了茎叶去喂猪。村庄里是忌惮过多快乐的,长得太欢就像孩子太闹腾,需要板起脸来教育。在农人的内心,默默无闻地生长才像个样子。茎叶长得欢天喜地,长在根上的力气就少去很多,一些无用的欲望就要被镰刀镇压。
山芋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孩子们就迫不及待地去用手扒。这是放学路上最常见的事情。饥肠辘辘的一天快要过去了,脑子里全是对于食物的渴望。沾满铅笔灰的手,插到干巴巴的泥缝里。手指的倒刺被泥块擦出血来也全然不顾。那些染了血的土非常冷漠,总不愿慷慨地拿出什么像样子的东西来。直到寒凉的深秋,农闲的人们才来理会这些野蛮的生长。在草木已经枯黄的时刻,泥土里和盘托出的一切,给了生活莫大的安慰。那些长得笨拙的块根被挖出来,成为见证一茬生长的证据,也是季节中一道附加的得分题。
山芋是一种万能的庄稼。可以生食,也可以入菜,与粥煮更有清香。人们害怕流年不利,就把它们切片晒干了装在网袋里挂在墙头,以备需要的时刻取用。山芋干煮粥似乎是一种通行的办法。有一次到得某个遥远的海边村庄,那个地方出产一种很有名气的菜刀。主人送了各人一把,嘴里说的却是:“到我们村里来别的没有,山芋干粥菜饭紧吃。”看来这种吃食已经有了代表平常事物的意思。“平常”这个词对于村庄来说极端重要。平凡或者平庸并不可怕,只要是常有,日子就能生生不息地接续起来。山芋也似乎能证实和担当这种接续。它们又会被做成山芋粉。山芋的浆汁在水缸里沉淀之后,父亲用刀切成方块,像豆腐一样放在门口的被面上晒。阳光耐心地一照,那些粉就会坍塌成细小的碎块,抓在手上就像用来育苗的酥土。
山芋粉装在布袋里。清明、中元和冬至的时候祭祖,必有一道烧山芋粉。人们平时也吃,所以做了亡人之后,还愿意歆享。至于用来做肉圆的辅料,那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人们还学着种花生,尽管知道里下河的黏土并不适合这种植物。但空白的土地有时也会生出些有趣的想法。种子也不知道哪代传下来的,反正没有断过。花生出苗的时候就显得并不蓬勃,那些瘦弱的叶子好像起了思乡之情。可是人们倔强地让它停留下来。它就像被拐卖的小媳妇,满肚子的不如意。秋后收起来晒干了,那些干瘪的种子真是令人担心。到年节来的时候,便掺了沙子在铁锅中炒。沙子也是外来的,是砌墙多余了遗在路边的,是那种粗粝的品种。它好像也不满意自己的遭遇,在锅里毫不情愿地和高温周旋。最后终于还是炒煳了,但闻着很香,足以用来应付时节。
外来的东西到底心里是隔膜的,这是没有出过远门的南角墩人难以理解的。
玉米和土豆也是远来的。玉米在村里就叫棒头,长得和本地的芦稷相像。芦稷并不多刻意去种,人们收来它的穗头制成扫帚。这是一种很繁复的手艺。芦稷的秆有甜味,孩子们折了在嘴里嚼,模拟出甘蔗一样的滋味。玉米进入村庄之后,也有孩子嚼秆子的,但粗糙少汁水。玉米还没有长成就有人惦记。掰开来那须上有清甜的味道,还不饱满的玉米粒生食很甜嫩。煮食之外,老了就不食,掰下来喂鸡鸭。对于这种作为副食的庄稼,人们似乎并没有什么热情。土豆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菜蔬,地里的产出也不饱满,谓之“洋山芋”。人们对这些庄稼缺乏热情,似乎也懒得对它们发挥什么想象。日后想到城里把土豆做成那么多样式,觉得村庄是轻视了这种可以作为主食的庄稼。说到底,人们对这些庄稼是有态度的——南角墩的人认为稻麦才是正事。土豆作为菜蔬,多和豇豆去烧。农忙的时候买了肥白的肉一起下锅,那是款待帮工的好菜。一个人家的菜好不好,也是一种态度,人们心里是有盘算的。
当然有时候人们也会突发奇想,种植一些奇怪的作物。比如父亲就曾经种过一丛甘蔗。甘蔗种是从另外一个生产队讨来的,也不知道它的老家究竟在哪里。父亲先把它窖在田头,到了开春的时候埋进土地里。庄上人对此并不看好,好像这片土地上就不可能长出甜蜜的东西。即便其他生产队也种出了甘蔗,但这似乎也并不能成为可靠的证据。人们看他忙碌着,轻轻念叨说:“还是吃些死粥死饭安心。”但那甘蔗倒也和父亲一样倔强,不消多久就真的抽出新苗来,硬是长成了田野之中的异数。在平坦的田野上,这一丛甘蔗显得很突兀,就像是一篇平静的文章,贸然地出现了一个叹号。父亲也并不管理它们,倒是我常去关注那红皮植物的生长。
到了秋后,父亲用割完稻子的刀割了一根,站在地里就咬了一口,满意地说:“谁说这地里就长不出好东西呢?”他把甘蔗砍回来佐酒,端着碗大口地痛饮。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滋味。母亲看桌上实在有些寡淡,把新收的花生抓给他一把,他摇着头说:“生花生吃了会耳朵聋。”
那些甘蔗断断续续在这个地点长了好几年。我有时候连稍子都认真嚼完——它比芦稷或者玉米秆甜多了。
三
村庄里有许多低洼的水田,像一种别扭的情绪,总是无精打采的样子。人们是通过抓阄分割田地的,拈到了那些水田也只有跺脚认命。人们也有自己无奈的办法。他们去北乡马棚湾买回来慈姑和荸荠种。马棚湾这个地方在运河边,是洪水冲出来的大湾。据说某处潭水深至七斤七两麻线也沉不到底。这个地方粮食总是绝收,但慈姑荸荠长得好。“马棚大慈姑”几乎是一种固定的称呼,还暗指一个人的夯笨。慈姑顶芽便可作种。这一段也是慈姑味道特别的地方,乡间桌上常闹笑着“以形补形”让男人吃。荸荠作种似乎更娇惯点,要用药拌了土防虫。慈姑荸荠在田头专门一块秧池育种,出苗后移栽至大田繁衍铺陈开去。
慈姑常种一大片,荸荠不过捎带几棵。荸荠其时是没有太大市场的。慈姑可以卖到城里甚至外地。荸荠好像是零食,这是村庄不在意的事情。只种几棵给孩子“杀馋”。慈姑叶子有庄稼的端庄模样,箭头一样的叶片茂密地覆盖着水田,只有青蛙的叫声可以透出来。荸荠叶子是简洁的圆柱形,一簇荸荠的叶子像土地庙插上的一炷香,很有些特别的意境,但缺少朴素的扎实。收获的时候很辛苦,慈姑都是妇女们用手扒。村里有俚语说“人之初,扒慈姑”。荸荠则更狡猾一点,要赤脚去“崴”,和采藕一般。
慈姑装满了船舱,用河水淘干净了,就装到城里去卖。有些人家为了得个好价钱,一直撑船送到下河的盐城。那个地方村里人都嫌弃,“到兴化心就慌,到了盐城不像家”。日后我去盐城,人问到从哪里来,一说对方就念叨:“那个地方出马棚大慈姑。”慈姑做汤奶白,和咸肉红烧或者切片炒,虽然味苦但清口得很。父辈们怨恨慈姑,一年饿极的时候每天都是烀着吃。到了年三十家里也不见一点肉丁。末了要吃汤圆应应时节,无奈又把慈姑削皮煮熟,圆滚滚的就算汤圆打发日子。荸荠久贮干瘪了更甜,但等不到多少时日就消耗殆尽。母亲们总骂“好吃不留种”。稻子收获了后耕田时,拖拉机后就跟着嬉闹的孩子,巴望着稻田里有些“懒棵子”的荸荠。湿润的土地被掀开来,就如翻开了书发现难得的秘密,是件很甜美的事情。耕田的二叔见我抢不过别人,低头拾起一两个扔过来,如拿到两个大苹果一样令人兴奋。不用回家洗了再吃,上手就去了泥土咬起来,很甜。
这些零散的庄稼帮衬着人们度过很多艰难的日子。人们也并非完全不想有更多的营生,只是膀子上就那么一点力气。也有人种菜,种大白菜或者大青菜,挑到城里去卖进陌生的厨房。村子里叫大白菜为黄芽菜,叫青菜为大白菜。大白菜是有些市场的,因为各家入秋之后都要腌制咸菜。咸菜有春冬两季。春天用野生的麻菜腌。野菜在河岸的护坡上很常见,往往是漫山遍野的形势,它们会欺负懦弱的野草。麻菜要在开花之前掐来,雨水足时三两日就新长一茬,但也极易开花。花一开叶片就失了滋味,大概气力都着在花事上了。切碎的麻菜吸足了盐分,不几日就丢掉轻微的麻味。挑出来淋几点麻油即可食,喷香。入冬后腌咸菜场面更壮观一点,每家门口都挂着待入缸的青菜。从集市买回来的海盐味道最好。一层层码在水缸里,最后压上一桶水,只等着熟了。
平原上有专门的村庄种菜,它们多在城市近郊的菜园。至于其他的村庄,间或也种一些但不成气象。特别像父亲这种暴躁脾性的,受不了城里人的脸色,也不会讨价还价地争辩,只能恨自己吃不了这碗饭。他也是和菜园子打过交道的。有几年他在三荡河做护林员,两岸的芦竹都由他来收割抵作工钱。收好的芦竹用船运到菜园去卖。先前说好的价格总是要扯皮,货到地头死,一咬牙就算了——都是地里长的东西,不值钱的。由此他就认为菜园子的人狡猾,自己学不来这种营生。他还种过一些大白菜。入冬后收了用草绳捆起来,放在朝阳的猪圈窝里。过两天就跳进去拿一棵出来烧咸肉吃。被吃的猪也曾是在这圈里生长的。
庄稼是饱暖也是滋味,日子就靠这些辛苦的植物得以延续。它们生长在泥土里,也生长在锅碗瓢盆的滋味里。比如一棵菜好像已经在盐水里失去了生机,其实它又是在另一个世界里开始生长。村庄有很多的办法保护这种生长。当咸菜在卤水里有了怨气,长出了酸臭的霉点,人们会把它们煮熟了再请回到阳光下暴晒。阳光就像当初爱护它的青苗一样,继续给它们以耐心和气力。梅干菜切断又回到了幽暗的坛子里,它们还能生长出很多的岁月。
这就是那些顽强的庄稼,在稼穑之中保我们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