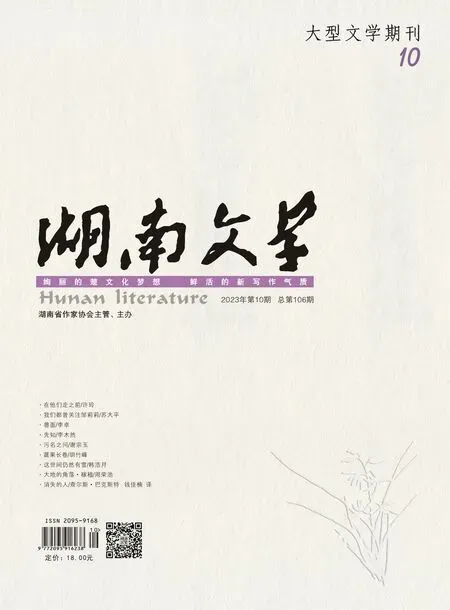能不能好好过大年
田小野
黎明时,苏步青似乎刚刚睡着就被窗外轰隆隆的摩托声吵醒了。这漫长一夜,又算过去了,这是失眠的第四天。苏步青有点恼,有点恨,恨谁呢?只能恨儿子苏周。想到儿子,苏步青心里立马又像塞了一把草。
苏周也有这样一辆摩托车,说叫“杜卡迪怪兽”,发动机声音也这样,嗡隆隆,嗡隆隆,像头哑嗓子的牛在叫唤,十来万,老伴反对儿子买这么贵的摩托车,说应该用那钱买台轿车。当然,那时老伴还在。苏步青也反对,但还是说:“让他买吧,他自己的事。”儿子很自豪,对他朋友不止一次炫耀说:“我爸和其他老头就是不一样,一点都不油腻。”苏步青一直对自己与儿子的关系很自豪,但唯独那件事,他是火,苏周就是冰;他是千军万马,苏周就是铜墙铁壁。当然,也许是儿媳妇的主意,她说过生孩子会让女人变丑的话。
苏周在纪王风景区当演员,专门演纪王,纪王拜天,纪王娶亲,纪王狩猎等,儿子长得随自己,模样不丑,为演好纪王专门留了胡须,留了长发,看上去还真像那回事。媳妇同是舞蹈演员,俊得有点扎眼。风景区人流不错,天天有演出,若是节假日还要加演,俩人天天活在热闹里。儿子长得帅,儿媳妇也好看,骑上杜卡迪,总有目光追着他俩看,苏步青也满是自豪,可现在,他俩三十六了呀,看着就让人来气。
老伴三年前去世,苏步青紧接着生了场病,胃被切除了大半后,人像被风干的萝卜,迅速瘪了下去,心律也不稳定,腿脚像抽了筋骨,不听使唤,身体简直成了破烂机器,没一处妥帖。
这几天,他那地方又不舒服,他不敢告诉苏周,胡乱找点药吃,他怕再住院,那可真不是好地方。两个月前,因为此处毛病,他住院二十多天,那地方的病,儿媳妇护理起来有不便,只能儿子陪护,把苏周眼看着熬瘦了。苏步青不希望儿媳妇来,在她面前,他总是为自己衰老感到惭愧。
老人有大把时间,苏步青也是。更多时间,他都在考虑怎么说服儿子。读过那么多书,民族传统,孟子的孝道,加缪的西西弗斯他都想了个遍。这件事上却显得很无力。苏周两人忙,忙演出还拍摄微电影,最近苏周提了副团长。偶尔过来,看看他身体没事,扔下些东西就走,苏步青根本没机会说,真让人上火。
那地方又作妖,已经三天了,白天似乎好点,晚上根本无法好好睡觉,翻来覆去如架在火上烤,骨头咔咔作响,似乎一不小心就会散架成粉末似的。
苏步青动动腿,再动动胳膊,试着动一动腰,艰难爬起身,慢慢进了浴室。他努力低下头,想去看看那里肿成啥样,揉了几遍眼睛,也没能看清楚。半夜已经加过一次止疼药,胃里很难受,嘴巴里也苦得很,不能再吃了。
他慢慢进了厨房,他想喝点小米粥,像老伴熬的那样,汤水足却黏稠黏稠的那种。他扶着橱柜,慢慢弯下腰,拽出小米袋子,慢慢站起来,倒进锅里一点米。小米看上去结了块,似乎有些黑点。他捏起点闻了闻,没闻出什么味道。最近鼻子要失去功能了似的,闻什么,都像隔了层玻璃。他扶墙出去,找来老花镜,又扶着墙回来,盯着小米看了一会儿,才发现小米上有些黑黑的小虫子,他连同米袋子扔进垃圾桶,气愤地盖上了锅盖。也是,他已经很久不做小米粥了。一个人似乎不配熬小米粥,要熬那么久,米少了不值当,米多了又喝不掉,剩下的不好喝又舍不得倒掉,每次都让人纠结。但总得吃点东西才有力气。苏步青找到了一罐放了很久的八宝粥,他看不清保质期也懒得去看,弄了点热水泡了,不温不凉喝了下去。
打开冰箱,他却非常清楚地闻到了发霉的味道。一侧是半玻璃瓶豆瓣酱,上面生了一层白毛,下层有几棵发黄的油菜,上层放了两个馒头。他拿出馒头闻了闻,又放到眼镜下看了看,馒头有了裂口。他突然发现两个馒头方方正正的,这让他很吃惊,再扶正眼镜仔细看,还是方方正正的。苏步青从来没记得买过方方正正的馒头,馒头不都是圆顶的吗?不管是买的,还是以前老伴儿做的,都是圆顶的,可今天馒头为啥是方方正正的?苏步青想不清楚。他的脑子里似乎有些迷雾,怎么也拨不开,晕乎乎的。他把两个奇怪的馒头扔到垃圾桶,去沙发上想了一会儿。馒头有方方正正的么?为什么他会看见两个方形馒头?他很生气也很难过,气得心脏突突跳。他不知道是生馒头的气,还是生自己的气。最近老爱生气。他想出去一趟,省得一个人在家生气。也该去趟超市了,冰箱里的食物没了。
出门后,他又想起两个方形馒头,又重新摸出钥匙打开门,去垃圾桶拎起那两个馒头,他要把这两个该死的方形馒头扔掉。
富源超市老板娘是个体形高大的女人,笑起来嘎嘎响,胸随着笑起伏,苏步青原来觉得她很漂亮,今天却发现,她竟然有两条文上去的粗眉毛,就像两条大青虫趴在额头。她的上唇很短,嘴唇外翻,露着青紫色的牙龈,看起来有点凶。
苏步青挑了面包,挑了一截莲藕,想到莲藕难嚼碎,又放了回去,挑了四个西红柿。他把面包和西红柿拎在手里,小心翼翼问老板娘:“咱有没有方形的馒头?”
老板娘看了他一眼,用手一指,说:“馒头在那里,要几个自己过去拿就是。”
苏步青过去又看了一遍,没有方形的馒头,只有圆顶的。
他又过去问老板娘:“我说,方形馒头,没有方方正正的馒头吗?”
老板娘正在为别人结账,她停下来,眼睛眨巴眨巴地看他,秃顶男顾客也张着嘴巴看他。老板娘生气地剜了他一眼,没说话,重新低头给顾客算了一遍钱,结了账。然后对苏步青说:“方形馒头怪蹊跷啊,你咋不要方形鸡蛋、方形皮球?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呀?”
苏步青吓了一跳,他后退了一步。周围人都看他,他可是个爱体面的人,瞬间恨不得缩进鞋子里去。他只是想确认一下,有没有那种方方正正的馒头。他记得上次是在这超市买的馒头。但他不敢问了,逃似的离开了。他急急往回走。他要去垃圾桶里找回那两个馒头,让她看一看是不是方形的让她知道自己不是无理取闹,也不是老糊涂了。
垃圾桶已被清理干净了,像张开的大嘴巴收垃圾的人简直是和他对着干,这么一会儿就收走了。他叹着气回家,拽着栏杆爬上二楼,却发现自家的门洞开着,这么说,他根本没关门。他狠狠关上门。今天是怎么了?难道真是老糊涂了,还是最近吃药太多出现了幻觉,把方形面包看成了馒头?但明明记得是馒头的。他气呼呼躺在沙发上,轻轻抽泣起来。
小区门口有个小广场,广场有凉亭,连着凉亭有回廊,回廊爬满紫藤,藤下一溜木凳。老人小孩都喜欢在那里扎堆。对门老孙夫妻俩会用婴儿车推着三岁孙子,他孙子真可爱,又白又胖,脸蛋肉乎乎的;青光眼的鲁婶则推着两岁多的孙女,孙女细软的羊角辫简直像两根豆芽菜,谁都想捏一捏脑血栓拖着腿走路的老王只能拖根拐棍,老王媳妇陪着他,她手里闲不住,总是有鞋垫要缝。苏步青本想到小广场坐一坐,和老朋友说一下方形馒头的事,还有,明明是冬天,为啥他会听见蝉叫,为啥他厨房那个老橱柜突然变了颜色?但上次过去,老王又问他儿媳妇怀上没,这让他很气恼。
苏步青去附近天和堂药店买消炎药。路边有个公厕,去年才建的,进门有洗手池有镜子,男左女右,很干净。他把塑料袋里的药品挂在手腕上,紧走几步,急急拉开门,正要伸手掏出,一声女人“啊呀”的尖叫,吓得他后退几步。他捂着胸口,有点蒙。黑衣女人站起来,像一头黑熊,指头伸在他眼前,骂句:“土埋到脖子了,还进女厕所,老流氓!”女人狠狠踹了厕所门出去了。苏步青恨不得抽自己嘴巴。他搞不明白怎么就走错了。他心里像生吞了一枚橄榄,像吞了一把沙子。
苏步青出来,厕所外接了长水管洗车的矮个男人,看着他嘿嘿笑。他对男人说,人老了,活着真的是没有一点意思。
天气越来越冷,连续几天阴雨后,大风起,气温骤降。窗门紧闭让室内的空气稀薄而浑浊,苏步青窝在家,混混沌沌,简直要喘不过气来。心情也像窗外的天气,阴郁寒冷。他不知自己哪里出了问题,感觉像突然把头伸进空缸里,耳朵里装了个放大器似的,轰轰作响。他那里还疼,他又加了两片消炎药。日子还要一天天过。
腊月二十三这天,太阳出来了,苏步青下了楼。小区的人都在忙着打扫卫生。本地人都喜欢小年这一天大清扫。老孙媳妇很爱干净,花窗帘和花床单都洗了,晒了出来在风里摇。苏步青看她正在擦窗户,玻璃擦得透明,从外面看着就很亮堂,过年贴上窗花会很好看。
自己家的窗户,自从老伴走后,就没有好好擦洗过了,窗帘上的黄色小碎花已经看不出颜色,灰突突的,玻璃也灰突突的,真像主人死了很久没有人居住的房子一样。这种想法让他自己吓了一跳,他赶紧摇头甩掉这些可怕的想法。
苏步青想让自己家也变得清爽一点,亮堂一点。他回家开始收拾东西。他把沙发上散乱的衣服收到了衣橱里,把一些纸盒子踩扁了码在门口,又把八宝粥空罐子、牛奶盒子、啤酒瓶子收进了一个大塑料袋。家里怎么堆了那么多他以为会用得着的东西:破旧相框,掉抓手的锅盖,塑料桶,沾满污垢的塑料筐,空花盆……他把它们归拢进一个废弃的红色塑料大澡盆里。用一个旧毛巾蘸上了些水,擦了一下电视柜,又擦了一下茶几,随着把一层厚厚的尘土抹掉,家具发出光亮,屋里也亮堂起来。苏步青有点兴奋,亮堂了多好,自己平时太懒惰了,今天也要像个过年的样子,把屋子里彻底打扫一下,这样,等过年儿子儿媳过来,儿媳妇也许不用像往常一样,每次一踏进家门,先挽起袖子打扫卫生。
苏步青搬了一把椅子到窗边,又搬了一个方凳,他想把窗帘拿下来洗洗,上面的灰尘实在太多了,黄色小碎花几乎看不清了。老伴在的时候,每年过年都会洗一下。那时,他还年轻,不用小凳子,直接一步就能踩到椅子上,再一步踩到窗台上,一会儿就能解下窗帘。老伴放上洗衣粉,洗干净后喊自己挂上去。
窗帘是不用晾晒的,洗完直接挂上去,开着窗,风一吹,洗衣粉的味道还没有散尽,半晌工夫,窗帘就会干了。
苏步青也没弄明白,自己还没有登上去,脚一滑,怎么就一下坐到了地上。屁股着了地,疼痛从腰传上来那一瞬间,他以为自己的腰杆断了。他默默躺在了地上,地面冰凉。他绝望极了,不知怎么和苏周交代,恨不得就这样死去算了。
过了一会儿,他试着动了一下,再动一下,竟然慢慢地站了起来,虽然腰椎还很疼,但这已经让他很欣喜,这样就不用麻烦儿子送他去医院了。他知道儿子牵挂他,愁眉不展,却在他面前装作很轻松的样子。他也疼儿子,只要能自理,慢慢地会好起来,重要的是能安安稳稳过个大年。
这里疼,那里也疼,多吃点止疼药一块儿止疼吧。苏步青也记不得一天吃几次药了。他最近格外想念老伴,老是梦见她。
腊月二十六这天,儿子过来,带了些炸肉丸子,丸子太过整齐,应该是外面买的。丸子的香气几乎催出他的眼泪。老伴在的时候,过年总要炸很多丸子,茴香肉的,萝卜的,豆腐的,很多花样。他也很烦自己,越老越没出息,动不动就像个娘们儿一样想哭,似乎只有哭,才能让自己心里好受些。他坐在沙发上没敢动,怕儿子看出他的疼痛。儿子看他有些憔悴,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他沉着脸说,没有,头发长了显的。他不想和儿子说,他还在生他的气。
儿子又说:“年三十下午,我俩过来,咱一起吃年夜饭,饭菜我从饭店订好了,到时候也带着,你不要操心弄,安心等着就是。”
苏步青没说话,把头扭到一边。
大年三十,天气阴沉沉的,要落雪的样子。苏步青还是一夜没睡好,浑身疼。他忍着疼痛在门口贴了福字和一副红对联——过年不能不贴新对联。若谁家没换新对联,必是家里近一年内有白公事。贴完对联,他又找出老伴照片看了一会儿,心里乱得很。
他拄着根拐棍,去了远一点的万圣隆大超市,准备买些年货,没有年货,一点不像过年的样子。儿子儿媳妇越过节日,越要加演节目,景区游玩的人增多,忙得很。当然,他给儿媳准备了一个大红包做压岁钱,是一张卡,里面是自己的全部积蓄三十多万,上面写了密码。如果儿子不要,他就和他说,自己年龄大了,老忘事,怕弄丢了,让他们替他保管,等花钱的时候向他们要,这样他们肯定会收下。他买了一大包香肠,给儿子吃,王香堂家香肠小茴香多,特别香,儿子从小就喜欢吃,他还记得儿子小时候,给他一根香肠,总是不舍得吃快,用门牙咬下一点点,放在嘴里吧唧吧唧嚼半天,小馋猫的样子。他出了超市,又回头进去,他想买瓶酒。他竟然挑了两瓶五粮液。这酒贵得吓人。很久不喝酒了,今天,他想喝酒。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真说不清,但就这么做了。
大大的雪花开始落下来,苏步青艰难地挪回家,疼出了一身汗,他赶紧找出两片止疼药吞了,又吞下两粒头孢克肟胶囊。他现在吃药不是一天两次或者三次,完全随了他的感觉。无论如何,先止住疼痛,今天晚上要和儿子喝一杯。
对面老孙家的炒菜香味飘过来,有小孩子打闹尖叫声,女人呵斥孩子声。老孙有两个孙子,儿子孙小俊一家回来过年了。
天一点一点暗下来,儿子儿媳还没回来。苏步青给儿子泡了杯红茶,他总是进门就找水喝他觉得他要回来了,把茶冲泡上。一会儿过去摸一下玻璃杯,一会儿再摸一下,觉得有点凉,后悔冲泡早了。他倒掉了一半,又添了些热水,去窗前看了看。一会儿又看看。
他有点着急,到小区门口转了转。雪还在落地下已经厚厚一层。孩子们在家藏不住,在雪地里尖叫着撒欢。本地人吃年夜饭前,有放一串鞭炮的习惯,说是用鞭炮声请老祖宗和神仙一起来过大年。提倡新风尚后禁止放鞭炮,但还是有些人家图喜庆,偷偷拿一串鞭炮,找个角落点上,在鞭炮噼噼啪啪中,嘻嘻哈哈跑回家吃饭去了。鞭炮的碎屑红红的,散落在雪地上,像盛开的花瓣满地欢喜。
茶水又凉了,他把茶水倒掉,重新给儿子泡了一杯。
六点多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儿子打电话过来,告诉苏步青他在陪媳妇打针,临时加了一袋,如果饿了,先找点东西吃着。
儿子儿媳大概不会过来了,啥大病非得这个点挂针,肯定是借口罢了。年轻人总是不愿意和老年人一起多待的。何况自己最近老骂他。苏步青不怨他俩,他们两个除了不想要孩子,其他方面真的不错,对他很敬重,细心孝顺,钱也舍得花。
苏步青突然又有流泪的冲动,他感觉眼角有热泪流了下来。他把老伴的照片摆在餐桌对面找来酒起,坐下来,把酒打开。他看着眼前的酒心里很难过,他不知道四粒头孢和酒一起会发生什么,他真的不知道。他怕给儿子添麻烦。这让他很纠结。酒就在那里,就在香肠旁边,那瓶酒让他很心慌,简直让他透不过气来。
他懊恼地点上了一支烟,打开门,站在门口吸。他很久不吸烟了。烟抽到一半,对面的门打开了,孙小俊提着垃圾出来,看见了苏步青,问“苏大爷,我弟苏周回来过年没?”
苏步青说:“本来说好过来的,这不,媳妇挂针了。”
孙小俊说:“哦,那您过来和俺一块吃吧,和俺爹喝一杯。”孙小俊小时候在路上玩,差点让车撞飞,幸好苏步青及时拽了一把才没伤着,两家很要好,孙小俊没正经工作,出去拜师学了推拿,年底和媳妇开了家按摩店,据说生意不错。
苏步青说:“不用了,一会儿我煮饺子。”
孙小俊说:“过来吧,热闹,我不喝酒,你陪俺爹喝一杯,恁老哥俩拉拉呱。”
苏步青无法拒绝,只好答应。他回屋抱上了那瓶五粮液。
他那瓶五粮液把老孙吓了一跳,他戴起老花镜,盯着看了一会儿,又看了一会儿。苏步青知道他怀疑是假的,就编了个谎话说:“这是苏周工作干得好,老板年终奖的,两瓶,还有一瓶呢。”
这么一说,老孙立马露出了羡慕的神色。说:“老板奖的呀,那肯定是正宗的。今晚我沾苏大哥光,尝尝五粮液什么味。”又回头对儿子说:“你看苏周,还能挣得五粮液给爹喝,你这小子,我是甭指望了。”
孙小俊说:“你不能怨我呀,苏大爷是当老师的,写一手好毛笔字,您是抡大锤的,大字不识一箩筐,还想喝五粮液,种豆还想得瓜啊。”大家哈哈大笑。
孙小俊看苏步青走路不得劲,问他怎么了,苏步青和他说了擦窗户摔着的事。
孙小俊让他坐到凳子上,让苏步青脱下粗绒线马甲,又脱绒衣,他顺着他腰椎摸了一会儿,让苏步青趴到他家沙发上去。孙小俊让他侧卧着,一手枕在耳朵下,一手放在腹部。苏步青照做,孙小俊一手摁住苏步青的肩朝里,一手摁在他臀部朝外,猛一使劲,咔吧一声响,苏步青心里一紧,接着身体一松。如此再翻身,还是这个动作,又是咔吧一声响。苏步青似乎觉得自己的腰杆被掰断了。孙小俊把苏步青摆正,啪啪啪敲打了一会,说:“大爷您站起来试试。”苏步青慢慢站了起来,左右扭了扭,再扭一扭,竟然不那么钻心疼了。
孙小俊说:“大爷这是腰椎扭错位了,你是不是天天吃止疼药,要不,咋能挨活这么久啊,早找我就好了,我学正骨推拿,正儿八经学了九个月呢,回头再给您按摩几次就好了。”
苏步青确实感觉不那么疼了,他嘴里一直啧啧啧啧,简直不相信孙小俊突然学会了这本事。
老孙媳妇和儿媳妇忙着上菜。苏步青坐在沙发上,老孙找出孙子写的毛笔字让老苏看,说从年轻时候起就馋老苏的毛笔字。花了三千块钱,给孙子报学习班学书法,让老苏看看花三千块钱学的大字怎样。
苏步青给老孙的孙子说了些写字要领,小孙子听得很认真,说:“苏爷爷,我书法老师像您这么教我的话,我早就是我们班最厉害的啦。”
苏步青很高兴,说:“得空到我家来,我教你呀。”
孙小俊说:“那哪行,麻烦您老人家。”
苏步青说:“不麻烦,他跟着学习班,该怎么练怎么练,回来的时候捎回几张我看看,我就知道他问题在哪里。”
菜上齐后,大家围桌坐下。因为给苏步青治腰,孙小俊一家也都很开心,也因为五粮液的缘故,孙小俊让媳妇也倒了半杯尝尝,老孙又给老伴儿倒了几滴,非让她尝尝,老伴抿一口,两颊立马生出两朵红晕。老孙用筷子沾了,让两个孙子舔一下,孙子舔了,都伸着小舌头,一边跳着脚呀呀叫,大家都笑了起来。
苏步青看着面前倒满酒的酒杯,来回搓着手。他犹豫要不要把酒推给老孙,告诉他今天不能喝酒,吃头孢药了……
苏步青口袋里的手机响了,《好日子》的歌声很大。苏步青接起来,电话里苏周喊:“爸,在哪?我们回来了。”
孙小俊赶紧去开门,楼道里站着苏周夫妻俩。苏周大包小包提着,苏周媳妇包着头巾穿着棉大衣,冷脸站在身后。
“弟妹病了,咋还挂上针了?”孙小俊问苏周。
苏周咧着嘴笑,一脸讨好地看向媳妇说:“没病,挂的营养针,了不得,她现在比熊猫还珍贵,这么瘦,还怀了俩……”
苏步青嘴唇哆嗦着,抬手捂住了脸,一股温热溢出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