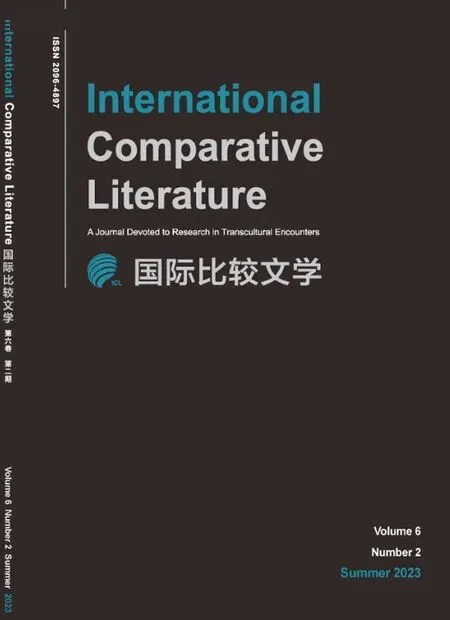论“意象派”内部的分歧及庞德对“意象”理论的贡献*
张同铸 南通大学文学院
在英美乃至全世界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上,“意象派”占据着一个枢纽性的关键地位,而庞德(Pound,1885-1972)在其中又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大卫·珀金斯指出:“在接近50年之久的时间中,他(庞德)是三个或四个最好的英语诗人之一。尤其在现代文学史最关键的那十年,也就是1912年到1922年间,他还同时是英美诗歌世界里最大的、也差不多是最好的批评家。”1David Perkins, A History of Modern Poetry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1987), 451.正是在他所谓的“最关键的十年”中,“意象派”作为一个流派从成形到全盛,最终解体。庞德既是该派理论上的倡导者,又是创作上的实践者,同时更是挖掘许多年轻而又具有潜力诗人的伯乐。但由于该派内部纷争, 庞德很快就离开了“意象派”,而该流派的全盛期也只有短短数年。这期间,该派的另一位重要理论家弗林特甚至公开否认庞德的作用和影响。这仅仅只是个人意气之争吗?还是牵涉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尤其是理论主张的不同?为了更好地厘清这些问题,有必要考察一下该派的形成过程及其理论来源,而其中的重点便是,厘定庞德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
一
1915 年,刚刚编辑出版了“意象派”第一部诗集之后,庞德就离开了这个诗歌团体,与刘易斯等人成立了一个全新的诗歌组织,洛威尔继庞德成为新的组织者,她刻意与庞德切割,继续编辑出版了几本“意象派”诗歌集,之后该派就自然解散了。作为庞德离去之后该派的主要理论家,弗林特在庞德刚离开的时候撰文回顾“意象派”的成立,应该带有一点争夺领导权的意味。他突出强调“意象派”与以休姆为主的“脱离者”诗歌俱乐部之间的继承关系,并且特别指出正是由于自己批评之前的“诗人俱乐部”浅薄的诗风,引导大家向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学习,才导致休姆脱离了该诗人俱乐部,成立一个全新的俱乐部即“脱离者”俱乐部。他强调即使对于这个后成立的诗歌俱乐部而言,庞德也是后来的加入者,几乎没有对俱乐部的诗歌理论做出过实质性的贡献。弗林特说:“(在刚加入团体的时候)庞德甚至不相信自龙萨(Ronsard)之后法国还有诗人!他只知道他的那些吟游诗人……第二年冬天(1911年),该俱乐部在经历了较长的停滞之后最终解散。”2F. S. Flint, “The History of Imagism,” Egoist 2, no. 5 (May 1, 1915): 71.弗林特的言下之意是:“意象派”理论主要来自“脱离者”俱乐部,尤其是来自休姆,而休姆又是在受到了自己的启发之后从法国象征主义那里取得了真经。
实际上,虽然一直自居为“意象派”的创始者,但庞德从来没有掩饰过休姆对他的影响,也不讳言法国象征主义。他作为“意象派”理论主要创建者的名号,并非像弗林特所暗示的那样是僭越的结果,这里的原因在于,正是他把休姆的思想和实践加以完善和发扬,并最终使其脱离了法国象征主义走向了一条理论上独立的新道路,而这一点是弗林特并没有意识到的。要想弄清楚这一情况,得从事情的源头谈起。
在20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英国尤其是伦敦的诗歌界仍然处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趣味统治之下,美国作为英国文化上的学徒自然也不例外。有研究者指出:“对世纪之初的那些‘有名的’诗人进行调查是一件让人沮丧的工作:他们中的大部分现在都已经无法卒读。他们使用夸张的措辞和扭曲的句法,用规定的方式重复着相同的陈腐主题和虔敬的陈词滥调。”3Joseph Parisi and Stephen Young, Dear Editor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2), 19.而庞德自己则是这么描述的:“1890到1910年,一般情况下来说英国诗歌是一个可怕的肥料堆……济慈和华兹华斯的模仿之模仿,伊丽莎白时代铿锵语言之模仿的模仿的模仿,毫无锋芒,软得不成形状。”4Ezra Pound,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54), 205.当然与之相应的是,新的风格与原则正在酝酿形成之中,只不过没有人明确地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模样,正如庞德后来回顾这一时期时所言:“一部分极其明智的年轻人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有些东西错了,但是没有人真正知道答案。”5Ezra Pound, Polite Essays (New York: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66), 9.
这时,年轻的诗人休姆站了出来。起初他参加了一个叫“诗人俱乐部”(the Poet’s Club)的组织,但该俱乐部的诗歌受到法国文学专家弗林特的激烈抨击,认为这些诗歌缺少生气。休姆赞同弗林特,从原“诗人俱乐部”脱离出来之后,在伦敦又办了一个被称为“脱离者”的俱乐部,意在和流行的庸俗趣味告别。参加者大多是艺术家和诗人,除休姆外弗林特是其中的主要人物,此外还有诗人斯托勒,以及从美国刚到英国的年轻的庞德也被吸收进来,但他加入的时间比其他人都要晚一点。休姆作为新俱乐部的核心人物,在弗林特的影响下,开始关注法国当代诗歌。并且发愿用法国诗歌改造英国诗歌面貌。休姆把这种即将产生的新诗体称为是“视觉的艺术”,认为它的效果“依赖的不是(像旧诗歌那样的)让人半睡半醒的状态,而是抓取人的注意力,这种抓取是如此强烈,以至于那种连续的视觉形象会让人筋疲力尽”6T. E. Hulme, Further Speculation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2), 73.。
休姆的这些观点很有创新之处,但他本人兴趣多样,在发表了短短几篇体现了这种诗学新思想的诗作之后,就对诗歌创作和理论失去了兴趣。此外,由于一战的爆发,他参军去了前线并最终牺牲。因此就理论本身而言,休姆并没有将意象主义诗学发展得非常完备,在他那里很多概念还处于比较模糊的形态。庞德自己从来没有否认过休姆对自己的重要影响,在1912 年出版的他的一部诗集《回答》(Ripostes)的最后附上了休姆的几首诗,并且加上了附言,表明了自己所受的影响。而休姆这几首诗最早发表于1911 年的《新时代》(TheNewAge)杂志,其命名方式有点奇怪,一共只有五首短诗,却称为《休姆诗歌全集》(TheCompletePoeticalWorksofT.E.Hulme),原因在于这时休姆的注意力已经发生转移,不再致力于诗歌艺术及其理论了。
当庞德逐渐引起英国主流诗坛注意的时候,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哈丽特·门罗正在芝加哥筹划创办《诗歌》刊物。门罗写信向庞德约稿,并请他担任期刊的海外通讯员,负责推荐新作者和稿件。庞德告诫门罗,要“让美国诗人知道诗是一种艺术,有它的技巧;而且诗一直在变化,需要革新”7Ezra Pound, The Letters of Ezra Pound (1907-1941)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1), 43.。他表示愿意给刊物提供在艺术思想上有活力的东西,并决定以《诗歌》刊物为阵地,宣扬自己的诗歌新观念,创立“意象派”。这些想法得到了门罗的积极回应。
于是,1913 年3 月刚刚创刊不久的《诗歌》杂志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署名弗林特的文章《意象派》,另一篇是庞德的《几条禁例》。当时正是大力宣扬“意象派”的初期,读者对于这个新生的流派抱有兴趣,同时又有许多误解,极需要理论上的阐明,而这两篇就是为回应读者的这些问题而做的。《意象派》一文列举了所谓“意象派”创作的几个原则,《几条禁例》又重述了那些原则,并且对“意象”下了一个定义。正是这两篇文章标志着“意象派”的正式出场。加上庞德编选的《意象主义者》诗集于伦敦和芝加哥陆续出版,第一次向公众集体展示意象主义诗人的诗作,取得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两年之后,当意象派内部发生纷争,庞德离开,弗林特站到了庞德的对立面艾米·洛威尔那一边,发表了《意象派的历史》一文,在其中他坦承《意象派》其实是庞德的作品,之所以署他的名,大概是因为庞德需要找一些有力的同盟者,为刚刚面世的新流派营造声势。
二
1915年5月,弗林特在《自我主义者》杂志上发表了短文《意象派的历史》,回顾了“意象派”的创立过程。在这篇短文中弗林特冷嘲热讽,基本上否定了庞德的作用。他指出庞德首先不是倡导者,而是之后才加入休姆所主导的诗歌俱乐部的。在加入的时候,他甚至完全不了解法国当代诗歌。这里隐含的意思是,在弗林特看来“意象派”的主要原则其实来自法国,尤其是来自于象征主义,有关这一点,弗林特在同时期其他很多文章中都表达得相当明确了。第二,在庞德加入之前,诗歌俱乐部的很多诗人就很注重表达“意象”。言下之意,庞德没有为这个概念作出什么特别贡献,更不说什么首倡之功了。
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
就是弗林特也不能否认,是庞德不遗余力地在宣传意象派主张,他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杂志上预告这一全新的诗歌流派,并且征集诗人诗歌作品,出版了《意象主义者》诗歌选集。此外,“意象”(Imagisme)这个法语词是庞德所创造出来的。他的作用并不仅仅体现在作为一位组织者上,他同样对“意象派”的理论贡献了自己的很多创见,这可以首先从“意象派”的核心主张“意象”上看出。
中文研究者在这里首先会遇到一个语言上的问题:法文词“Image”(在英文中有对应的词“Image”),在庞德之前,这个词主要所指的应该是“影像或形象”,是庞德使它具有了我们所熟悉的“意象”这个涵义,他创造了两个全新的法文词“Imagisme”(意象)以及“Imagistes”(意象主义者)。
在休姆那里,“形象”才是“脱离者”诗歌俱乐部追求的准则。用弗林特的话说就是:“这个俱乐部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于当下英语诗歌创作现状的不满。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提议用一种纯粹的自由诗来取代它 ……关于这一些我们讨论了许多,也有不少实践,斯托勒是主导者,而讨论的核心便是形象。”8F. S. Flint, “The History of Imagism”, 71.
弗林特应该正是根据这一点否定了庞德的理论贡献,但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尽管该诗歌俱乐部讨论的核心是“Image”,但它只能说是指“形象”,还没有发展为庞德所指的“意象”(Imagisme)。
休姆是柏格森学说的热情宣传者,他所提倡的作为诗歌准则的“形象”来源于柏格森哲学。19世纪末,“形象”在法国艺术界、学术界,尤其是在心理学领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最终在柏格森哲学中得到充分体现。柏氏认为人类认识世界主要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分析的,一种是直觉式的。前者主要运用概念,以推理为主,后者则是一种意识之流。前者适用于科学,后者适合于诗歌等艺术。从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上来说,后者优于前者,因为通过智性的分析,人们顶多只能接近真相,而通过直觉,人们可以直接进入体验真实之流,从而对其获得更为真切的认识。“形象”是直觉的富有表现力的具体体现,成为柏格森哲学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这可以从他的《物质与记忆》一书中看出,该书分为四章,分别讲的是对于“形象”的选择,“形象”的回忆,“形象”的持续,以及“形象”的固定,借助于“形象”讨论了身体与心智问题。人们通过感知“形象”来认识世界,而这个世界就是所有形象的集合。在诗歌中“形象”是交流的中介,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这本书中这么描述诗学创造:“诗歌的明媚动人是怎样来的呢?诗人是这样一个人,他把情感发展为形象,又把形象发展为字句,而字句把形象翻译出来,同时遵守节奏的规律。读者在心目中陆续看到这些形象,于是就有了诗人有的情感,这情感可说是这些形象在情绪上的等值量。”9(法)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吴士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11 页。[Henri Bergson, Shijian yu Ziyou Yizhi (Time and Free Will), trans. WU Shido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 11. ]柏格森的《形而上学导言》还阐述了形象与直觉的关系:“形象最低限度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使我们停留在具体的东西上。任何一个形象都不能代替绵延的直觉,但是,由不同种类的事物,可以获得许多不同的形象,这些形象的作用会聚起来之后,就可以正好把意识引向获得某种直觉的地方。”10(法)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7 页。[Henri Bergson, Xingershangxue Daoyan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trans. LIU Fangto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63, 7. ]可以看出,尽管柏格森重视“形象”,但“形象”在他这里只是一个中介,最终导向的是情感和直觉。休姆后来把《形而上学导言》翻译成了英文,同时在英国也做了许多关于柏格森的讲座,推广其哲学。在《柏格森的艺术理论》一文里他特别强调了诗人的视觉感知和捕捉能力,他说:“从好的形象中你会不断获得一种确信:诗人总是处于一种生动感知到的自然的和视觉的场景中。”11T. E. Hulme, Specu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36), 164.并且认为无论是诗还是散文都以“形象”为基础,但前者注重的是其最生动活泼的一面,后者则满足于单纯的指称。他说:“粗略地说,有两种沟通的方式,一种是直接的方式,另一种则是常规的方式。前者是诗的语言,因为它直接用形象来处理;后者则是散文的语言,它们使用的是已经死去的或者成了修辞格的形象。”12T. E. Hulme, Further Speculations, 10.休姆补充说:“一个人如果不能清晰地看到眼前的事物,那么他就不能够写作。形象在写作活动之先,并使其基础坚实”。13Ibid.可见休姆眼中的诗中之“形象”是读者借之以感受事物的中介,借助这个“形象”,读者可以更生动地感受到事物,而不是其因符号化而变得抽象的那一面,后者属于散文,不属于诗。
可见在庞德之前,“形象”还没有获得其独立的价值和地位。无论是柏格森还是休姆都将“形象”视为某种中介,直到庞德这里才将“形象”视为主观情感和客观物体的统一体,具有了独立的价值,从而真正发展成为“意象”,成为“物”本身(主观的物)。他给它下了一个定义:“所谓意象就是那在瞬息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14Ezra Pound, Early Writings: Poems and Prose, ed. Ira B. Nadel (New York and London: Penguin, 2005), 253.在柏格森那里,“形象”是“某种比唯心主义者所说的‘表象’更多的存在,但是却比实在论者所说的‘事物’更少的存在。”15Henri Bergson, Matter and Memory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 9.什么是“比‘表象’更多的存在”?什么是“比‘事物’更少的存在”?柏格森没有明言,因此留下了理论上的模糊地带。而从庞德的定义则可以看出,表象只是“象”,“意象”则添加了“理与情”,这“理与情”或许就是柏格森所谓的“更多的存在”。从这里或许看出庞德经由休姆继承了柏格森的某些理论。但他没有止步于此,在柏格森那里,“形象”是导向情感的工具,读者借之可以体会到作者的情感。而到了庞德这里,情感就蕴含在“意象”之中,两者一而二,二而一,不可分割。此外,柏格森和休姆皆强调一切“形象”都是“事物”的一个反映,而庞德则将“意象”视为“物”本身。无论柏格森还是休姆都没有指出这个“形象”有它能动的一面,而庞德则指出“意象”是主观情感和客观物体的统一体,具有能动一面。这一点在意象派时期尚只是萌芽,后来他则进一步发展出了自己的“漩涡”理论。这么一来,庞德并不是简单重述了柏格森的理论,而是对其加以发展,并使它更为清晰。这种理论创见,无论如何都是不能一笔抹杀的。
弗林特没有意识到庞德的创新之功,因此在《意象派的历史》一文中,他在引用庞德的说法“Les Imagistes”(意象主义者)和所谓之前的提法“形象学派”(School of Images)时,完全没有对其加以区分。
三
在对待法国现代诗歌理论尤其是象征主义的态度上,庞德与弗林特也有着重要不同。
1918 年,当意象派作为一种组织已经结束之后,庞德发表了一篇文章回顾了这个运动,声明这是自己作为“老艺术家”对年轻艺术家的一种经验之谈。他说:“在1912 年春天或初夏,H.D.理查德·奥丁顿和我都认为我们在下列三项原则上是一致的:一、对于所写之“物”,不论是主观的或客观的,要用直接处理的方法。二、决不使用任何对表达没有作用的字。三、关于韵律:按照富有音乐性的词句的先后关联,而不是按照一架节拍器的节拍来写诗。”16Ezra Pound, Early Writings: Poems and Prose, 252.
在这段话里他重述了意象派创作原则,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他没有提及弗林特(要知道这几条规则本来是以弗林特的名义发表的),这或许是因为事实上他确实只是和H.D.、理查德·奥丁顿这两个人讨论了这些原则,可是也可能有其他的意思。因为紧接着他就特别提到了弗林特,然而这么一提反倒更明显地拉开了距离:“我们想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称为一个流派,至少像弗林特先生在哈里特·门罗主编的杂志《诗歌》1911 年8 月号上公开称呼的一些法国‘流派’一样。”17Ibid.
庞德并不讳言自己所受的来自法国的影响,1914年出版的《意象主义者》更是直接采用自己创造的法语词汇“Des Imagistes”为书名。不过与弗林特不同的是,他一直否认“意象派”是法国象征主义的附庸。虽然自1913年左右,庞德就开始撰写不少论述法国象征主义的文章,尤其推崇戈蒂耶、古尔蒙、拉法格等人,甚至可以说他是除弗林特之外介绍现代法国诗歌最热心的人。但是,庞德坚持宣称:“意象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象征主义着眼于事物间的‘联系’,也就是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暗示,差不多可以说是寓言。他们将符号降格为语词,使其成为某种形式的转喻。”18Scott Hamilton, Ezra Pound and the symbolist inherit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3.语词是外在的,没有和所描写的物成为一体。这与庞德之强调“意象”为“情与理”的统一,且意象直接就是“物”是相悖的。这些话似乎主要是针对马拉美而说——马拉美重视的是“观念”,语词是其外壳,在庞德看来这些语词是花里胡哨的装饰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庞德不认同象征主义,他在1913年给未来的妻子多萝西·莎士比亚的信中说:“我一直在读你的马拉美。对于我来说,他的散文比亨利·詹姆斯要差得多了,至于他的诗歌,我还压根没看。”19Scott Hamilton, Ezra Pound and the symbolist inheritance, 4.对于波德莱尔和魏尔伦,他也同样没有好评。
从对于物的态度上似乎可以看得更清楚。马拉美本人爱用一个关于“花”的例子来说明他的理念。在他的笔下花不是真实的花,而是完全不存在于自然界的花,是本体之花。也就是说诗歌的目的是创造出不为现实所囿的纯粹本质。“于是,那朵不存在于任何花束中的花,从我的音声也未曾留下痕迹的遗忘之外,作为某种绝非我们熟悉的花萼的东西,音乐般地升起来,它是美妙的观念本身。”20Stéphane Mallarmé, Divagations, trans. Barbara Johnson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26.所以在马拉美那里,任何有形的花都被遗忘了,或者说他要的是关于花的完美的理念。而庞德强调直接处理物本身,“确切、完美的象征是自然的事物”,和马拉美完全不同。
受庞德的影响,辛克莱在《自我主义者》上撰文称:“意象主义不是象征主义。它和制造影像没有一点关系,它痛恨影像(Imagery),这是意象主义者试图抹去的老式的、被用破了的装饰。”21May Sinclair, “Two Notes,” Egoist 2, no. 6 (June 1, 1915): 88.意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现实(或物体)的符号,它自身就是现实(或物体)。这一条成为庞德对意象派所定下的原则中的第一条:直接处理所写之物。所谓影像,是朦胧的,模糊的,用庞德的话说就是“象征主义总是和那一团浆糊一样的技术联系在一起”22Ezra Pound, Early Writings: Poems and Prose, 282.,从而是一种“印象主义式”的东西。有一点很值得一提,在庞德蔑视马拉美的时候,同时期法国诗坛也在反思马拉美的晦涩诗风,在他的作品中私人化的东西太多,给阅读和理解造成了较大的困难,这也许就是庞德称之为“浆糊化的技术”的原因吧。马拉美强调要暗示出事物,他对象征主义的界定是要么“一点一点地引发一种事物以便呈现某种情绪”,要么“选择一种事物并从中提炼出一种情绪”,对于读者而言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破译”来体验这种情绪。总之,事物(形象)在这里和情感是分离的,事物(形象)是手段,读者通过这种手段抵达诗人要表达的情感。他有这样的名言:“在诗歌里命名一样东西,就意味着压制了诗歌带给人的四分之三的快乐,因为诗歌的快乐就是由一点一点的猜测带来的。”23Scott Hamilton, Ezra Pound and the symbolist inheritance, 3.这显然也与庞德所强调的直接及简洁的诗风相悖。
而弗林特则始终坚持学习法国现代诗歌理论尤其是象征主义,虽然他对日本古典诗歌也感兴趣,但日本俳句、和歌对其理论建构的意义有限。而庞德之所以能够将对“意象”的理解推进一步,与他对东方文化的了解逐渐增加,并积极吸收其养分有关。
虽然庞德主要是通过费诺罗萨的遗稿来了解中国诗歌的,而他发表意象派宣言的时候,还没有接触到这些遗稿。他所创作的意象派代表诗作《在地铁车站》,时间也在接触遗稿之前。但他其实在读大学时就已经接触过翟理斯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古典文学给他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日本和歌和俳句也对他有所影响。
众所周知,他的那首意象派名作《在地铁车站》,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是在日本俳句的启发下创作出来的,尤其是当时在伦敦的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对庞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4Ezra Pound, Early Writings: Poems and Prose, 214-215.我们知道在16-17世纪,西欧的确曾经产生过相当广泛的“中国热”,但是后来渐渐消沉。19世纪中叶日本在西方的压迫下打开国门之后,很快由被动转为主动,积极向外推广自己的文化。西方尤其是法国,沉迷于日本式的东方之美。在绘画领域,日本的“浮世绘”甚至引起了法国美术界的革命,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画家都受到了影响。在文学领域俳句受到欢迎,仿作者众多。“形象”成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法国文化界的讨论热点,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与日本文化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不过日本诗歌又受到中国诗歌注重“情景交融”的特征的强烈影响,这应该也是后来庞德真正接触中国文化的时候,马上就迷恋上的原因吧。
根据已经发现的资料,庞德在1913年接触到了费诺罗萨遗稿,他开始了解中国文化和诗歌,并终生热爱,且随着认识的加深而愈加尊崇中国文化。1915年对中国诗歌有了初步了解之后,他在一家周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意象派与英格兰》的文章,一开头就指出有两种诗歌,一种是音乐性的,一种是绘画性的。“第二种诗歌和第一种诗歌一样古老和清晰,但是一直不曾有过正式的命名。现在我们把其称为‘意象主义者’,但这不是一个发明,它是一个辨别。”25Ezra Pound, Ezra Pound’s Poetry and Prose: Contributions to Periodicals, vol. 2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1991), 19.随后他模仿一个反对者的声调说:“那是法国的(那一套),你们休想在英国也这样搞。”26Ibid.而庞德本人的回应是:“是的,先生,确切地说这是法国的;但也是中国的,也是希腊的,也是拉丁的,当然也是英国的。”27Ibid.在该文稍后一点,他承认中国文字在绘画性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过借助于费氏的理论,他宣称英语是欧洲语言中最接近汉语的语言,其结论是:英语也适合于表现“意象”。
因此,庞德的“意象主义”主张里有着直接或间接来自中国文化和诗歌的影响,这也许才是他能将 “形象”向前推进一步到发展为“意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