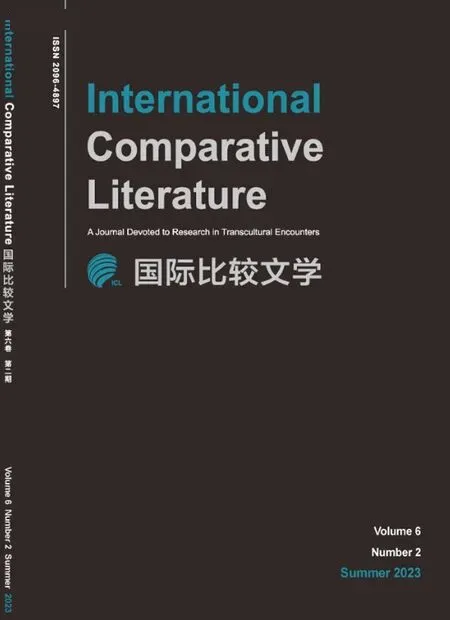真诚还是伪装?
——莎士比亚对十四行诗传统的反讽式改写
徐梓贤 北京大学
1609 年,伦敦书商托马斯·索普(Thomas Thorpe,c. 1569-c. 1625)出版四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Shakespeare’sSonnets),书中包括154首十四行诗和一首329行叙事诗《情女怨》(ALover’sComplaint)。由于约翰·本森(John Benson,?-1667)出版于1640年的版本距离莎士比亚时代较为遥远且深陷争议之中,索普版本成为了现代学者校勘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时最重要的底本。令人困惑的是,尽管十四行诗获得了莎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广泛认可,《情女怨》却长期不受关注,被隔绝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解释传统之外。然而,不存在“脱离了任何物质性的抽象、理想化的文本”1Roger Chartier, “Laborers and Voyagers: From the Text to the Reader,” Diacritics 22 (1992): 50.,读者手中书籍的结构和形态决定了他们对作品的诠释。被剥离了物质形态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无疑是不完整的。在克里根(John Kerrigan,1956-)出版于1986年的企鹅版把十四行诗和《情女怨》一起编辑出版后,2详见The Sonnets and A Lover’s Complaint, ed. John Kerrigan (London: Penguin, 1986), 7-18.将这两个在同一本书中出版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已成为当今读者的一项迫切的任务。
历史上,导致《情女怨》受到冷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多数早期学者认为这首诗在艺术造诣上难称一流。其次,部分学者怀疑它并非出自莎士比亚之手。20 世纪初最重要的莎学家之一锡德尼·李(Sidney Lee,1859-1926)的意见颇具代表性:“它的标题在伊丽莎白朝诗歌中相当寻常,风格传统,语言造作……它很可能是某二流诗人就常见题材的习作……被一个野心勃勃的抄录者署以莎士比亚之名。”3Shakespeare’s Sonnets, ed. Sidney Lee (Oxford: Clarendon, 1905), 49-50. 关于《情女怨》作者问题的早期学术史论争,参见A New Variorum Edition of Shakespeare: The Poems, ed. H. E. Rollins (Philadelphia and London: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38), 584-603.上世纪末,邓肯-琼斯(Katherine Duncan-Jones,1941-2022)撰文从索普的出版经历、诗集结构完整性等方面论证1609 年四开本经过莎士比亚授权,4Katherine Duncan-Jones, “Was the 1609 Shake-Speares Sonnets Really Unauthorized?”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134 (1983): 151-71.杰克逊(MacDonald P. Jackson,1938-)等学者又利用风格统计学方法证明《情女怨》在用词习惯上更接近莎士比亚,520 世纪后利用风格统计学讨论《情女怨》作者问题的单篇论文和专著逾20 种,其中杰克逊的专著塑造了当前学界的主流共识,参见MacDonald P. Jackson, Determining the Shakespeare Canon: “Arden of Faversham” and “A Lover’s Complai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情女怨》的作者问题大体上已经尘埃落定。其中,邓肯-琼斯特别提到原书与16 世纪90 年代出版的丹尼尔(Samuel Daniel,1562-1619)《狄莉娅》(Delia,1592)等诗集在结构上的相似性,6Katherine Duncan-Jones, “Was the 1609 Shake-Speares Sonnets Really Unauthorized?” 165-70.克里根明确“狄莉娅结构”(Delian structure)通常由三个部分组成、涉及六种16 世纪90 年代出版的诗集,并指出莎士比亚的读者在阅读他的诗集前早已“熟识了阅读它的框架”。7The Sonnets and A Lover’s Complaint, ed. John Kerrigan, 14.但既往研究往往只关注狄莉娅结构在形式上的共通性,未能就狄莉娅结构在主题上的连贯性展开充分讨论。笔者认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必须放在全书结构内部才能得到深入理解,而对十四行诗和《情女怨》关系的讨论必须放在狄莉娅结构这一具有连续性的话语传统内部加以探讨。沿着这一线索,可明确莎士比亚发展了伊丽莎白晚期十四行诗诗集结构中的反讽式结尾,进一步阐明莎士比亚对十四行诗传统的革新性所在;若从全书结构反观十四行诗本身,则可提炼出对部分诗篇加以重新阐释的可能。
早期十四行诗诗集的结尾模式:维持、和解或反讽
学界认为英国十四行诗包含三种话语,即“激情,或欲望的话语;反思,或斯多亚主义的话语;阿那克里翁风格(Anacreontic),或诙谐、博学的话语”。8Michael R. G. Spill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nnet: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124.但后两种话语仅占极少数;基于彼特拉克十四行诗在文类上的规定性,“欲望的话语”总是构成其主导性的话语模式。伊丽莎白时代十四行诗组诗通常以单恋的失败结尾,以锡德尼(Philip Sidney,1554-1586)的奠基性诗集《爱星者与星》(AstrophilandStella,1591)为例,作为抒情主人公的诗人在最后一首诗中感叹:“可一旦对你的思念令我欢畅,/当我年轻的灵魂振翅飞向你,它的窝巢,/鲁莽的绝望,这不速之客,就会到来,/钳住我的翅膀,把我裹进他的黑夜……”9The Poems of Sir Philip Sidney, ed. William A. Ringler (Oxford: Clarendon, 1962), 236.但具备狄莉娅结构的诗集通常在十四行诗组诗后附有其他文类的诗歌,因而能挣脱十四行诗的文类规定性,为十四行诗的单恋之“结”给出不同的“解”。以丹尼尔《狄莉娅》为例,全书由50 首十四行诗(在同年出版的第2 版中增补为54 首)、两首抒情短诗(在第二版中并为一首)和叙事诗《罗莎蒙德之怨》(TheComplaintofRosamond)共同构成“十四行诗—过渡片段—叙事诗”的三分式结构。丹尼尔被认为开启了“一种出版潮流,一种在文本上结构这种历史悠久的形式的方法”。10Wendy Wall, The Imprint of Gender: Authorship and Publication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253.在莎士比亚的诗集出版前,共有6位作者的十四行诗诗集具备类似的结构,均出版于16 世纪90 年代。11罗伯特·帕里(Robert Parry,1540-1612)、亚历山大·克雷格(Alexander Craig,1567-1627)、大卫·默里(David Murray,1567-1629)、玛丽·罗思(Mary Wroth,1587-1653)也被近期学者列为狄莉娅传统可能的参与者,参见Thomas P.Roche, Petrarch and the English Sonnet Sequences (New York: AMS Press, 1989), 343;Heather Dubrow, “‘Dressing old words new’? Re-evaluating the ‘Delian Structure’,” in A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s Sonnets, ed. Michael Schoenfeldt (Oxford:Blackwell, 2007), 91;Katherine Jo Smith, Ovidian Female-Voiced Complaint Poet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hD diss.,University of Warwick, 2016), 79-84。但他们的诗集或接近苏格兰传统、或结构归属牵强,同莎士比亚诗集结构可能的相关性较小,兹不作考察。这些诗集中的过渡片段和叙事诗(作为“结尾部分”)往往和作为主体的十四行诗组诗形成丰富的对话关系,笔者将其归纳为维持、和解和反讽等三种结尾模式。
维持的结尾模式在结尾部分中维持了十四行诗组诗的矛盾,没有给出解决方案。林奇(Richard Linche,活跃于1596-1601)的诗集《狄埃拉》(Diella,1596)在38 首十四行诗后附有叙事诗《唐·迭戈与吉内芙拉的爱情》(TheLoveofDomDiegoandGynevra)。林奇在《狄埃拉》最后一首中请求心上人继续阅读他的诗集:“狄埃拉,请聆听一会儿故事……把它通篇读完……但请特别关注结局……”12Elizabethan Sonnets, vol. 2, ed. Sidney Lee (Westminster: Archibald Constable, 1904), 320.这说明《唐·迭戈与吉内芙拉之爱》是林奇有意设计的诗集结尾;另外,这首诗“错彩镂金的辞采、精巧构思的堆叠无不令人回想起伴随它的《狄埃拉》”。13Louis R. Zocca, Elizabethan Narrative Poetry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0), 129.林奇在诗歌结尾处宣布他恋情失败,决心不再写作:“再见吧;风已催动征铎。/我低劣的秃笔,将不再/向世人播扬你的美丽……”14Seven Minor Epics of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1596-1624), ed. Paul W. Miller (Florida: Scholar, 1967), 102.但他并未否定十四行诗欲望话语的逻辑,这一宣言不过是对诗集在形式上的结束的象征性解释。
和解的结尾模式在结尾部分中解决了十四行诗组诗中无解的矛盾。一般认为,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53-1599)在《小爱神与婚颂》(AmorettiandEpithalamion,1595)的前89首十四行诗中记录了他追求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博伊尔(Elizabeth Boyle,c. 1565-1590)的过程,在《婚颂》中记录了他和博伊尔结婚当天的心理过程。在组诗中,斯宾塞在对博伊尔的身体之爱和新柏拉图主义式精神之爱的矛盾之间挣扎:“唯有那束天光留下的形象,/依然留存在我的眼中……但当我用这束光芒充盈了心灵,/我却身体挨饿,双眼无神。”15Edmund Spenser’s “Amoretti” and “Epithalamion”: A Critical Edition, ed. Kenneth J. Larsen (Tempe, AZ: MRTS, 1997), 104.这种两难的痛苦在过渡性的九首阿那克里翁体诗中得到讽喻式再现,诗人再次被“爱情的利箭”16Ibid., 107.贯穿的形象证明了“感情的不稳定、脆弱、延宕和推迟”17Catherine Bates, The Rhetoric of Courtship in Elizabeth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47.。但斯宾塞在接下来安排了《婚颂》。作为文类的婚颂(epithalamium)被视为宣泄受挫情欲的“安全阀”,18Leonard Forster, The Icy Fire: Five Studies in European Petrarch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88.斯宾塞借用这一和解性的文类将彼特拉克式不稳定恋情祝圣为合法的基督教爱情,解决了十四行诗组诗中的两难。
反讽的结尾模式在结尾部分中对十四行诗话语加以模仿甚至戏仿,以取消矛盾合理性的方式消释矛盾,其代表是丹尼尔的诗集《狄莉娅》。在作为《狄莉娅》结尾的叙事诗《罗莎蒙德之怨》中,罗莎蒙德的鬼魂首先要得到“世上情人的叹息”才能被允许渡过冥河。她提到“狄莉娅也许会偶然惠阅我们的故事,/继而奉上她的叹息”;19Motives of Woe: Shakespeare and ‘Female Complaint’: A Critical Anthology, ed. John Kerrigan (Oxford: Clarendon, 1991), 166.在结尾,罗莎蒙德请求诗人“告诉狄莉娅她的叹息能帮到我,/也让她明白我们天性的软弱(the frailtie of our blood)”。20Ibid., 189.但在诗中,罗莎蒙德遭年长妇人诱骗,沦为亨利国王的禁脔,最终被王后毒杀。显然,听完这个故事后“狄莉娅”拒绝诗人的决心只会更加坚定。年长妇人劝说罗莎蒙德的手法也令人想起《狄莉娅》组诗。例如,妇人利用“美好的事物终将凋零”的道理来劝说狄莉娅接受国王的求爱,21Ibid., 173.同样的道理也被诗人用来劝说狄莉娅接受他的求爱。22Poems and A Defence of Ryme, ed. Arthur Sprag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26.罗莎蒙德的悲剧结局于是为狄莉娅提供了一个警示性的预演,“为少女的贞洁辩护并打破了对诗人的认同”23Carol Thomas Neely,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Renaissance Sonnet Sequences,” ELH 45 (1978): 381.。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丹尼尔在《罗莎蒙德之怨》中不断诱导着读者质疑《狄莉娅》组诗所基于的十四行诗话语的道德合法性。
洛奇(Thomas Lodge,c. 1558-1625)、弗莱彻(Giles Fletcher the Elder,c. 1548-1611)和巴恩菲尔德(Richard Barnfield,1574-1620)在他们的十四行诗诗集中沿用了反讽的结尾模式。例如,在洛奇诗集《菲莉丝》(Phillis,1593)所附叙事诗《艾斯垂德之怨》(TheComplaint ofElstred)中,女主角艾斯垂德将自身的悲剧归咎于国王引诱她时使用的修辞话术:“种种蜜糖般的语词枷锁,/由一条狡诈的赫拉克勒斯之舌操纵,/足以迷惑所有耳朵、驱逐一切忧伤。”24The Complete Works of Thomas Lodge, vol. 2, ed. Edmund Goss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883), 71.弗莱彻在《黎西娅》(Licia,1593)组诗后附上抒情诗、对话、拉丁对句、怨诗等多种文类的作品,呈现出关于爱情的复杂声音。在其中一篇译自公元2世纪讽刺作者路吉阿诺斯(Lucian)的诗体对话的结尾,一位海中仙女嘲笑她的同伴对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的迷恋:“如今我们见识了爱能有多愚蠢,/竟把丑的看成是美的。”25The English Works of Giles Fletcher, the Elder, ed. Lloyd E. Ber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4), 115.这一反讽性的警句促使读者修正先前对作为诗集主体的十四行诗的接受。巴恩菲尔德的诗集《辛西娅》(Cynthia,1595)所附叙事诗《卡珊德拉》(Cassandra)展现出同样强烈的反十四行诗倾向,女主角在被囚禁后哀叹“愿一切少女以我为鉴……保住无瑕的贞洁”26Richard Barnfield: The Complete Poems, ed. George Klawitter (Selinsgrove, PA: Susquehan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6.,为占据诗集主导地位的欲望话语引入对抗性的道德话语。
《情女怨》中的指环、十四行诗与赠送的隐喻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书可分为“十四行诗(前152 首)—过渡片段(2 首阿那克里翁体诗)—叙事诗(《情女怨》)”三分结构(或“十四行诗—叙事诗”二分结构),同16世纪90年代出版的六种狄莉娅结构诗集显示出强烈的继承—模仿关系。若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放回到这些诗集的延长线上阅读,就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杂凑性的诗歌结集,而需要考察全书结构中不同部分之间的对话关系。表面上看,《情女怨》讲的是一位无名的少女向一位老者自述被一位英俊青年追求后抛弃的故事,和之前十四行诗的主题缺乏明显关联。那么,这首收绾全书的叙事诗在全书结构中是否承担了某种功能?《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结尾是否继承了前述狄莉娅结构诗集的结尾模式?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意识到《情女怨》明确提到了作为一种文类的十四行诗。在诗中,青年曾把他的追求者送来的信物转交给少女:“看这些秀发结成的塔兰特27原文作“talents”,注者或释为“贵重物件”(克里根、罗伊[John Roe]),或解为“珍贵信物”(伯罗),或校订为“爪状物”(邓肯-琼斯),但乡健治(Kenji Go)证明更可能指《马太福音》第25 章中的货币“塔兰特”。参见Kenji Go, “Samuel Daniel’s The Complaint of Rosamond and an Emblematic Reconsideration of A Lover’s Complaint,” Studies in Philology, 104(2007), 100-106。青年的追求者把秀发编成钱币状。,/温柔地缠系着贵重的指环,/是我从许多个美人那儿得来。/她们噙泪哀求我答应收下,/另有镶嵌其上的美丽宝石,/附上精心结构的十四行诗(deep-brained sonnets),/详述每颗宝石的珍贵价值。”28The Complete Sonnets and Poems, ed. Colin Burr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708. 以后引用,随文括注“CP”加页码,不再另外出注。在全诗开篇,被背叛的少女绝望地“撕扯纸页,掰断指环”(CP695),克里根正确地指出青年转送的“精心结构的十四行诗”和“贵重的指环”就是少女在开篇毁坏的“纸页”和“指环”。29Motives of Woe: Shakespeare and ‘Female Complaint’: A Critical Anthology, ed. John Kerrigan, 46.“指环”和作为指环衬垫的发圈在传统上被视为浪漫爱情的物质象征。在莎剧《威尼斯商人》中,鲍西亚赠给巴萨尼奥指环作为信物。《情女怨》中的指环“由金、骨制成,镌有铭文”(CP698),而尼莉莎也给葛莱西安诺送过一枚金质指环,镌有“爱我毋相弃”的“铭文”。30William 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 ed. Richard Proudfoot et al. (London: Bloomsbury, 2021), 975. 以后引用,随文括注“CW”加页码,不再另外出注。在《仲夏夜之梦》中,伊吉斯指责拉山德赠给他女儿赫米娅“押韵的诗”和“秀发结成的腕环、指环”作为“爱情的信物”(CW1009),而十四行诗作为“押韵的诗”中最显要的文类,在形塑浪漫爱情想象的文化话语中承载着极高的符号价值。在《爱的徒劳》中,国王、俾隆、朗格维等人都为心上人创作了十四行诗,俾隆甚至承认正是恋爱教会他“写诗和忧郁”(CW877)。但当《情女怨》中的少女掰断指环、撕毁情书和诗歌时,这些爱情的物质或精神载体反而成为了“谎言的记录”“禁不起考验的证明”(CP698)。《情女怨》给出了十四行诗在现实中的一种可能的危险用法:不怀好意者利用它动人的修辞和真诚的表象来骗取他人的情感。
对青年转送的“精心结构的十四首诗”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伯罗(Colin Burrow,1963-)提出这些内容未知的十四行诗“并不揭示情感”,“只是提供了某种体验的入口”。31Colin Burrow, “Life and Work in Shakespeare’s Poem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97 (1998): 28.笔者认为莎士比亚通过此处的留白引导读者把这句话视为对作为一种文类的十四行诗整体的指涉,继而引导读者反思《情女怨》和之前的154 首“精心结构的十四行诗”之间的关系。当前学界通常认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献给彭布罗克伯爵威廉·赫伯特(William Herbert,1580-1630)的,而后者也很可能是诗中青年的原型。32支持“Mr. W. H.”为威廉·赫伯特的最详尽论证参见Shakespeare’s Sonnets, ed. Katherine Duncan-Jones (Walton-on-Thames: Thomas Nelson, 1997), 55-69。柯林·伯罗认为“Mr. W. H.”是基于小圈子的首字母游戏(CP 100-103)。诺顿第三版《莎诗》编者琳恩·马格努森沿用1987 年唐纳德·福斯特文章的观点,认为“W. H.”是对“W. S.”(即“威廉·莎士比亚”)的误印,参见Donald W. Foster, “Master W. H., R. I. P.”, PMLA 102 (1987): 42-54;Lynne Magnusson, “Thomas Thorpe’s Shakespeare: ‘The Only Begetter’,” in The Sonnets: The State of Play, ed. Hannah Crawforth et al. (London: Bloomsbury,2017), 33-54.莎士比亚在组诗中多次提到赠送的行为,如第26首诗:“我寄给你这纸质的讯息,/为的是向你述职,而非夸耀才智。”(CP433)又如第77首诗:“这些空白纸页将记录你心灵的痕迹,/这本书会使你体验到这种学说。”(CP535)在这些语境下,《情女怨》中青年对少女的赠送行为构成了诗人—莎士比亚对青年—赫伯特的赠送行为的一个隐喻。在这一意义上,轻信了这些十四行诗的少女被背叛、抛弃的悲剧结局为同一本书中的十四行诗的真诚性投下了阴影。它让读者想起这些诗歌只呈现了诗人的单一声音,比起戏剧性的对话更接近一种“能听到但无法回应的独白”33Heather Dubrow, “Shakespeare’s Undramatic Monologues: Toward a Reading of the Sonnets,” Shakespeare Quarterly 32 (1981): 62.,继而将《情女怨》作为十四行诗文本和读者之间关系的一个寓言来阅读。
戏仿修辞与不可靠叙述者
《情女怨》的叙事结构本身是经过多重中介的。诗歌主体是不知名叙述者对少女的忏悔的转述,少女又在忏悔中转述了青年追求她时的长篇告白。高度复杂的叙事结构提示我们关注这些叙事本身的特点。首先是青年的告白。青年在转送指环和“精心结构的十四行诗”时恳求少女:“把这些比喻(similes)都收归麾下吧,/它们因我肺部烧出的叹息而变得神圣。”(CP710)“这些比喻”即前述十四行诗中的比喻。34Shakespeare’s Sonnets, ed. Katherine Duncan-Jones, 446.这让读者想起莎士比亚本人就是一位擅长“比喻”的行家:他是第18首十四行诗中脍炙人口的“夏日”喻的作者;在第35首诗中,他连用四个“比喻”(compare)为对方的不忠开脱(CP451)。研究者未曾指出的是,后一行中“肺部烧出的叹息”模仿了英国十四行诗传统中的一个常见比喻,如丹尼尔《迪莉娅》第8首:“你可怜的心已被献祭给最美的人,/把你叹息的焚香奉上了天空。”35Poems and A Defence of Ryme, ed. Arthur Sprague, 14.青年之后又把少女比作深不可测的“海洋”(CP712),这一修辞见于丹尼尔《迪莉娅》第1首:“朝向你的美的无垠海洋,/奔流着这条小河。”36Ibid., 11.莎士比亚自己就在第80首十四行诗中效法过丹尼尔:“我冒失的轻舟虽相形见绌,/却也莽撞地到你的茫茫大海上争流。”(CP541)在《情女怨》中,莎士比亚借少女之口特意强调了青年的修辞学家属性:“在他压倒群伦的舌尖,/各种论据和深刻的论题37关于“论题”,参见Quentin Skinner, Forensic Shakespea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2-25.……为他的便利时而清醒、时而沉睡……他了知辩论术(dialect)和修辞技巧(different skills),/凭他塑造欲望的技艺(craft of will)俘获一切情绪。”(CP703)但在诗歌的语境下,“辩论术和修辞技巧”不再是受人尊敬的学问,而是一种“塑造欲望的技艺”,是操纵他人情感、欺骗少女献身的不义手段。透过青年—修辞学家这一形象,莎士比亚不仅戏仿了英国十四行诗话语的传统修辞,而且质疑了他自己的十四行诗中的一些类似用法。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原创性修辞也在《情女怨》戏仿的范围之内。例如,青年在告白中说要把他的追求者送给他的“所有款项(sums)”(比喻“所有的爱”)“悉经汇总”后一并交给少女的“账目”(audit;CP712),乡健治指出莎士比亚第4 首十四行诗也提到了“账目”,38Kenji Go, “Samuel Daniel’s The Complaint of Rosamond and an Emblematic Reconsideration of A Lover’s Complaint,”115-18.但第49首中的账目隐喻在表述上更接近:“当你的爱抛掷了最后一笔钱(sum),/被深思熟虑唤去把账目(audit)核对。”(CP479)把爱的多少比喻为金钱的多少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独创的修辞,而它在《情女怨》青年的爱情谎言中的重复无疑为前者的真诚性带来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讽刺感。又如,《情女怨》中的少女说青年“统治着众人的心”(CP703),青年在对少女的告白中说“看这些炽烈恋情的纪念碑(trophies)……这些礼物注定是给你的供奉,/因我是她们的祭坛,而你是我的主保圣人”(CP709-10),并描述一位被他抛弃的修女被“虔诚之爱(religious love)剜去了虔敬之眼”(CP711),这些表述几乎复制了莎士比亚第31首十四行诗:“你的心为众心所爱……有多少哀毁的圣洁泪珠,/曾从我眼中偷出虔诚之爱(religious love)……你是容纳已葬爱情的坟墓,/缀满我昔日爱人的纪念碑(trophies),/他们把我的部分奉赠于你,/而今你独享众人应得的爱意……”(CP443)这两首诗的高度相似性促使读者把《情女怨》中诱骗少女的青年和歌颂青年—赫伯特/黑肤女郎的诗人—莎士比亚等同起来,而诗中青年“塑造欲望的技艺”(craft of will)可能的双关义“威尔(莎士比亚)的技艺”(craft of Will)39James Schiffer,“‘Honey Words’: A Lover’s Complaint and the Fine Art of Seduction,” in Critical Essays on Shakespeare’s “A Lover’s Complaint”: Suffering Ecstasy, ed. Shirley Sharon-Zisser (London: Routledge, 2006), 145.进一步揭示了这一点。
再回到少女的忏悔。不知名叙述者一开始说这是一个“善变的少女”(fickle maid;CP695)4019 世纪编者哈得孙(Henry Norman Hudson, 1814-1886)将“fickle”释为“激动的”(A New Variorum Edition of Shakespeare: The Poems, ed. H. E. Rollins, 333),但《牛津英语词典》并未收录该义项,罗伊由此提出排字工之误或新造意义两种可能(The Poems, ed. John Ro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64),但该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鉴于莎剧中出现的“fickle”均表示“善变的”,可以认为这层含义在《情女怨》中至少被暗示了出来。,提示读者对少女作为叙述者的可靠程度保持怀疑。克里根写道:“少女言辞的藻丽使我们对她困境的认识变得复杂。”41The Sonnets and A Lover’s Complaint, ed. John Kerrigan, 59.“藻丽”体现为高度的修辞性。在《情女怨》结尾,少女自述当时被青年的泪水感动:“但当被他双眼中的泪水所淹没,/哪一颗顽石般的心不会被击穿?/哪一块冰冷的胸膛不会被温暖?/噢,多么分裂的效果!冰冷的矜持被融化,/火热的愤怒却被冷却。”(CP714-15)“滴水穿石”是当时的谚语,但也是英国十四行诗传统里的常见修辞,如斯宾塞《小爱神》第18首:“滴落的水珠也能漫溢,/长此以往可击穿坚硬的燧石;/可我却不能以无数的泪滴/和漫长的哀求软化她坚硬的心。”42Edmund Spenser’s “Amoretti” and “Epithalamion”: A Critical Edition, ed. Kenneth J. Larsen, 75.恋人在冰与火之间的分裂性体验则是源于彼特拉克的一种程式化表述。由此可见,少女的自述本身也是高度修辞化的。这让诗歌叙述者的价值倾向变得含混不明,也削弱了《情女怨》作为一首文艺复兴“怨诗”(complaint)被期望持有的道德化立场。罗奇(Thomas P. Roche,1931-2020)把《情女怨》开篇叙述者所听到的“双重声音”(double voice)视为一个“象征戏法”43Thomas P. Roche, Petrarch and the English Sonnet Sequences, 440.——作为莎士比亚诗集的结尾部分,《情女怨》为全书引入了“双重声音”,打破了十四行诗中的单一声音叙事。
综上,莎士比亚发展了16世纪90年代迪莉娅结构诗集中的反讽的结尾模式,在《情女怨》中对同一本书中的十四行诗组诗加以丰富的互文指涉,从而戏仿了传统的十四行诗话语及其自身的原创性话语,甚至传递出对叙述者可靠性的质疑。其反讽程度之强烈在英国十四行诗传统中无疑是革命性的。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真诚与伪装
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整体结构的重新诠释为我们阅读前154 首十四行诗提供了新的角度。传统观点认为,莎士比亚的一部分诗歌显示出对英国十四行诗传统的反讽甚至决裂的态度。例如,莎士比亚在第130首诗中“公然利用了读者对十四行诗传统的期待”44Stephen Booth, An Essay on Shakespeare’s Sonne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80.,直言黑肤女郎“绝不像太阳”(CP641),表现为嘴唇不够鲜红、皮肤不够白皙、秀发不够金黄云云,戏仿了寻常十四行诗作者对心上人千篇一律的刻画。这一态度也体现在第21 首诗中,莎士比亚批评其他诗人“使用一对对浮夸的比喻”,唯有自己“真诚地爱,真诚地创作”(CP423)。可以说,“真诚”构成了诗人—莎士比亚这一“人格”(persona)以传统十四行诗作者的“不真诚”为参照系展开的自我形塑过程中的核心概念。正是基于这一印象,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说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揭开了他的心灵”,45William Wordsworth: The Major Works, ed. Stephen Gi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356.奥登(W. H. Auden,1907-1973)则说这些诗最惊人的特点是“自传式的直露坦白”。46W. H. Auden, Introduction to The Sonnets, ed. William Burto (New York: Signet, 1964), xxxiv.
但这部诗集的结尾提示我们修正对这些“精心结构的十四行诗”的直觉性印象。无需否认,莎士比亚在大多数诗歌中是真诚的。但至少在诗集中的某些时刻,他的真诚是伪装出来的;他向读者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感受。这种不一致性造成了滑稽和反讽的效果。在前126 首诗中,诗人—莎士比亚多次提到青年—赫伯特对他的疏远或背叛。但他极少控诉对方,在多数情况下选择为其辩护,或至少表示顺从。这些顺从的结果往往是一些公认的“劣诗”。例如,温特斯(Yvor Winters,1900-1968)批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常常体现出“诗人一方奴隶式的软弱(servile weakness)”,使得读者“对主人公的同情式理解几乎不可能”。47Yvor Winters, “Poetic Styles, Old and New,” in Four Poets on Poetry, ed. Don Cameron Alle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9), 47-48.温特斯承认这是宫廷诗歌传统的特点,但他认为莎士比亚对此是认真的。第57-58 首诗或许最能代表这种“奴隶式的软弱”。在这两首诗中,诗人把自己描述为青年的奴仆,默默地等候对方主动差遣他。莎士比亚的用语是极为谦卑的:“作为你的奴仆,我还能做什么,/除了等候你心意(desire)所及的时机和场合?/我根本没有珍贵的时间可消磨,/也没有事情要做,直到你需要我。”(CP495)但这种谦卑似乎超出了应有的限度。第57 首诗的结尾增强了这种怪异感:“爱真是一个道地的傻瓜,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往坏了揣测你的意图(will)。”(CP495)诗人意识到自己是“傻瓜”,一方面表明他的“软弱”,一方面暗示他意识到对方可能对他不忠。“will”隐含的双关义“欲望”和“任性”48The Sonnets and A Lover’s Complaint, ed. John Kerrigan, 245.进一步提示了可能的真相。在遵循表面上的“主—奴”构思同时,莎士比亚显示出一种清晰的自我意识,一种对自身在这段关系中的境遇和所扮演的角色的反思性自觉。马丁(Philip Martin,1931-2005)认为,借助一种“自我知识”,莎士比亚得以“从另外的角度观照自身,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他的困境”。49Philip Martin, Shakespeare’s Sonnets: Self, Love and 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73.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超越性是双重的——不仅是对诗人自身在一段不平等恋情中所处境遇的自觉,也是对内嵌于十四行诗传统中的“主—奴”话语模式的自觉。莎士比亚作为十四行诗这一文类游戏的局内人,暗示他知晓幕布后运作着的一切。
这类反讽在诗集中并非孤例。在第35 首诗结尾,莎士比亚总结了他矛盾的心情:“我的爱和恨打起了内战(civil war),/最终我不得不做了那迷人窃贼/的帮凶,尽管他残忍地劫掠了我。”(CP451)有学者认为这首诗前4行逐步恶化的比喻表达了一种“酸涩的自觉”,而最后的“内战”比喻说明诗人为对方辩护的理由是“扭曲的”。50Michael Cameron Andrews, “Sincerity and Subterfuge in Three Shakespearean Sonnet Groups,” Shakespeare Quarterly 33 (1982): 318.需要补充的是,“心灵内战”(psychomachia)这一可追溯到古罗马诗人普鲁登修斯(Prudentius,348-c. 413)的主题在英国十四行诗传统中相当常见。锡德尼在他的十四行诗中呼唤“睡眠”来终止他的“内战”,51The Poems of Sir Philip Sidney, ed. William A. Ringler (Oxford: Clarendon, 1962), 184.斯宾塞则把他对博伊尔的“情欲”和他的“理智”之间的冲突描述为“持久而残酷的内战”。52Edmund Spenser’s “Amoretti” and “Epithalamion”: A Critical Edition, ed. Kenneth J. Larsen, 86.锡德尼和斯宾塞的“内战”是在新柏拉图主义式的“理智—欲望”框架下展开的,心上人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保持纯洁。但在莎士比亚诗中,传统的“内战”比喻被创造性地挪用于一种新的情境:是否原谅心上人的不忠?通过把习惯于神化恋人的彼特拉克—锡德尼十四行诗传统中的常见比喻挪用于一位“不忠的恋人”,莎士比亚完成了一次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所说的“克诺西斯”(kenosis):“曾经有过前驱者的地方就会出现新人——但其出现的方式是以不连续方式倒空前驱本人的神性,而表面上似乎在倾倒自己的神性。”53(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第94 页。[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Trans. XU Wenbo (Beijing: SDX Joint, 1989), 94.]
最尖锐的“克诺西斯”出现于第94 首诗。莎士比亚把对方描述为“神圣恩惠”的继承者,理由是他“使人动情,自己却像磐石,/无动于衷,冰冷,无视诱惑”(CP569)。论者认为“无动于衷”无法推出对方“继承了神圣恩惠”的结论,因而把这首诗称为“反讽性赞美诗”(mock-encomium)。54Michael Cameron Andrews, “Sincerity and Subterfuge in Three Shakespearean Sonnet Groups,” 325.但这一观点未能解释这种反讽的感觉缘何而来——这需要把这首诗放在和十四行诗传统的关系中看待。对诱惑“无动于衷”是彼特拉克式心上人的典型特点,但几乎总是一个负面的特点,诗人的目标往往是恳求对方不再“无动于衷”。弗莱彻在《黎西娅》第8 首中写道:“我的眼泪太轻微,难以感动你的心,/我的叹息像风,难以撼动那磐石[指“你的心”]。”55The English Works of Giles Fletcher, the Elder, ed. Lloyd E. Berry, 85.“黎西娅”的冷酷促使弗莱彻在结尾哀求她温柔一点。但莎士比亚却改写了这一形象,把“无动于衷”作为赞美的理由。这种大胆的改写迫使读者反思传统心上人形象的“合法性”。通过看似真诚的赞美,莎士比亚实际上“倒空”了传统形象的“神性”,以一种“伪装”的方式反讽了这一传统。
余论:文学与社会批评
如果说莎士比亚的“伪装”揭示了十四行诗写作的一部分秘密,那么了解他的“伪装”的深层动机则需要对伊丽莎白时代文学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入体察。十四行诗缘何在伊丽莎白时代兴起?莎士比亚缘何写作,又缘何在诗中反讽十四行诗传统?这些问题的答案尤为复杂,一文难以穷尽。但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把伊丽莎白时代的十四行诗视为纯粹的“抒情”文类。相较于其他文类,十四行诗的独特优势在于它天然地适于“表达欲望——不仅指某种特定的欲望(对性、对爱、对庇护),而是作为欲望实体的自我”。56Michael R. G. Spill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nnet: An Introduction, 125.而在由一位女王掌权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男性作者虚构的“追求”(courtship)故事“被视为在政治赞助体系内部的自我定位的表达”,“追求”不再指向个人的内心情感,反而“把真诚和表象的关系问题化,让一个追求情境的‘真相’变得难以索解”。57Catherine Bates, The Rhetoric of Courtship in Elizabeth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 44.因此,当时的诗人可以借助十四行诗的欲望话语把爱情转化为关于经济状况、社会阶层或政治升迁等方面的广义的“欲望”的寓言。1591 年锡德尼的遗作《爱星者与星》出版后,得益于这位“殉难的文化英雄”的显赫声望,十四行诗的文类地位得到了提升,这一方面“授权了不同阶层的诗人参与十四行诗创作”58Arthur F. Marotti, “‘Love Is Not Love’: Elizabethan Sonnet Sequences and the Social Order,” ELH 49 (1982): 397.,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扩大了十四行诗作者施展政治“腹语术”的空间。弗莱彻在他的诗集题辞中为读者给出了他的心上人“黎西娅”原型的各种可能,但最终承认很可能不存在现实原型:“它可能只是我的构想,没有什么意义;不管是什么,如果你们喜欢,就请接纳它,并感谢这部诗集的促成者莫利诺夫人(Ladie Mollineux)。”59The English Works of Giles Fletcher, the Elder, ed. Lloyd E. Berry, 80.莫利诺夫人是弗莱彻希望凭借这部诗集打动的贵族赞助人——他需要一部写给女性的诗集来为他邀取经济上的赞助,也需要借助这种时兴的体裁以赢得伦敦文坛的入场券。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写作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而他自身也处于(或想要处于)和某位贵族赞助人(例如威廉·赫伯特)的赞助—被赞助关系之中。在征用、提炼传统的同时,莎士比亚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写作被这一关系所规定——十四行诗中常见的不平等的恋情关系正是现实中他和赞助人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文学镜像。正如麦克劳德(Randall McLeod,1943-)所说,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叙事“对爱情政治的强化使其更接近于社会政治”,“暗示但从未释放出他所指向的全部批评”。60Randall McLeod, “Unemending Shakespeare’s Sonnet 111,” SEL 21 (1981): 92.这种社会批评在某些他过度“真诚”的时刻中隐约地呈现出来,并最终成为了结构整部诗集的思想倾向。利用真诚与伪装的修辞游戏,莎士比亚不仅以反讽的形式改写了彼特拉克十四行诗传统,而且隐秘地批评了这一传统所植根的不平等社会秩序及其造成的后果。
———“人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