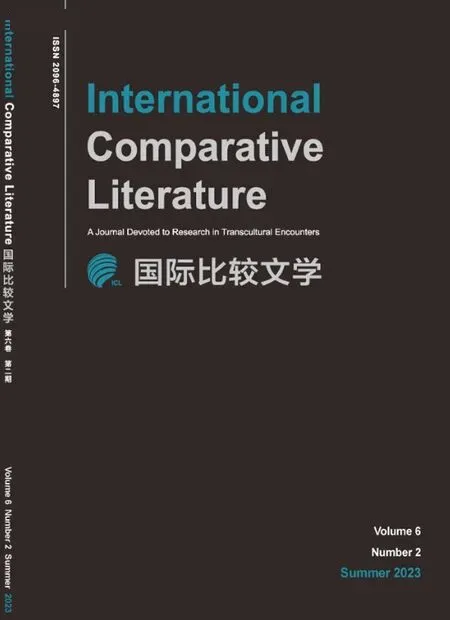叶维廉比较诗学中的古诗意象问题*#
刘亚斌 浙江外国语学院
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和诗学观念体系的主要论题,其所具有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表现,自然是当代中国传统诗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近年来,随着“美在意象”、“美是意象”等理论话语的提出,意象再次引起国内美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汉字及其传统诗歌对欧美现代诗歌运动颇有影响,如英美意象派和法国象征主义等诗歌流派,都曾在中国诗歌意象上作过探索,以此构建新的书写模式,意象又成为国内外比较诗学的研究热点。作为“学者化的诗人,作家化的学者”1古远清:《学者化的诗人,作家化的学者——评叶维廉的诗论》,《叶维廉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3月,第37~41 页。[GU Yuanqing,“Xuezhehua de shiren, zuojiahua de xuezhe—pingyeweilian de shilun” (Scholar-Poet, Poetic Scholar—On Wai-lim Yip’s Poetic Theory), Yeweilian shigechuangzuo yantaohui lunwenji (Collected Papers of Wai-lim Yip’s Symposium on Poetry Writing), March 2008, 37-41.]乐黛云在叶维廉文集序中也提到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学者和学者的诗人”,在中西诗歌传统的杂糅和冲突等复杂情况下对诗学把握得“更为深邃,更为自觉”,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的成分显得越来越重”。就此而言,诗人与学者不能仅视为一种简单的双重身份,其具体创作和诗学研究关联密切。参见叶维廉:《叶维廉文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5 页。[YE Weilian, Yeweilian wenji (Collected Works of Wai-lim Yip), vol. 1,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2002, 5.],叶维廉(Wai-lim Yip)早年在象征主义影响下从事诗歌创作,逐渐喜爱传统诗歌及其意象方法,还对意象派主将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的创作和诗学有过精深的研究,其博士论文即以庞德《华夏集》(Cathay)作为研究对象,发表过大量的诗论文章,还有一本专论《庞德与潇湘八景》(PoundandtheEightViewsof XiaoXiang)的小册子,庞德意象诗学可谓伴随其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的大半生涯。因此,在比较诗学视野下,叶维廉对意象问题的阐述值得学界更多重视,本文拟就其意象、行动和语言的诗学关系作些反思,以抛砖引玉。
一、意象自身的时间性
叶维廉在《中国现代诗选》(ModernChinesePoetry)英译本绪言,即《中国现代诗的语言问题》一文中所阐述的中英语法之根底不同,是其整个诗学构建的理论基础。在文章中,他说到印欧语系与汉语的区分,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中文动词没有时态(tense)变化,而时态变化在字母型语言里的意义便是限定时空,将其具体化,不作无限的延伸。“印欧语系中的过去、现在、将来的时态变化,是一种‘人为’分类,用来限指时间和空间的。中文的所谓动词则倾向于回到‘现象’本身——而现象本身正是没有时间性的。时间的观念完全是人为的实用目的硬加在诸现象之上的”2同上,64页。[Ibid., 64.],在现象学视野下比较中西语言,力求诗歌语言回到现象本身,景物、事件等通过语言而让自身呈现,无需人为的、主观的和实用目的的干预和强加。借助西学理论,叶维廉发现汉语表达在诗歌创作及诗学上的优势,对中国诗学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在突显中国语言和诗学特色时,依然难以摆脱西方理论视角,在某种程度上也证实其科学性、合理性和普世性,但是在语言及诗学方面,中国古典诗歌更接近、更容易达到认定的规范。
叶维廉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在现象学与道家文化、中西语言和诗学等方面着力于差异中的融通。因此,抛开比较诗学的权力话语,让我们将目光集中在诗歌本身的问题上。就语言、现象和诗歌创作关系而言,叶维廉深知,诗歌创作是无法离开语言的,只能让语言无限接近现象,在诗中现象本身要通过语言才能显现。换言之,诗学只能追求语言指义前的状态,难以直接呈示前语言的现象世界,要尽量减少意义元素、逻辑概念和思维框架等对现象的染指与遮蔽,将可感、可触和可视的事物本身交给读者去感发。由此,时空结构作为人类对现象世界的整理和秩序化,便在叶氏比较诗学里遭到某种程度的批判与弃置。但是,现象自身是有其时间性的,万物生长在世界里,便标示着某种时间的到来和在场,草木开花是温暖的春天,落叶飘零则是秋冬之季。当语言呈现事物时,其本身就有时空性,且恰恰是其时空性质,“俯仰自得”、“无往不复”、“节奏化的音乐化了的中国人的宇宙感”3就“宇宙”的理解而言,今人更倾向其空间观念。然而,古人早有“上下四方谓之宇”、“往古今来谓之宙”的说法,“宇宙”是时空结合的,历史的沧桑巨变总是离不开世间一切。《论语·子罕》中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语录多为“子曰”,此处特意提到“子在川上曰”,传达出时空整全的宇宙观念。宗白华在该文中进一步指出,“宇”是“屋宇”,“宙”是由“宇”中出入往来,这就是中国原始农人的世界,空间和时间合成其宇宙,并安顿其生活;对他们来说,时空是不能分割的。参见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423~431 页。[ZONG Baihua, Zongbaihua quanji (Complete Works of Zong Baihua), vol. 2,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2008, 423-31.],才使得中国古典诗词打破具体的在地限制,穿透历史、跨越时空,上升到普遍的精神高度,从而打动古往今来的人们和全世界的读者。
在叶维廉提到的元代马致远小令《天净沙·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古道”“瘦马”等意象就暗含时间性,“枯”、“老”、“瘦”等形容词都表明生命、劳作快至终点的时间跨度,且内藏在事物自身中,用以暗示羁旅之人“终生”难归,“古道”则显示出古往今来都是如此,未来还将如此,这便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命中注定的悲苦,从而使词中意象穿越时空,上升至决定论的形上高度。还有“西风”意象,如果只是单独出现,可能不具有时间性,只是具有时节性,即秋冬之际,可联系全篇则有“又到了秋天”之意,春夏秋冬、时间往复,漂泊在外的旅人年复一年而无法归家。看上去,这些词句都在写景物,实则都是写人类。“枯藤老树昏鸦”,全是纯然的自然景物;“古道西风瘦马”,更多社会痕迹的写照;背后都是历史的沧桑变化、孤独的人间旅程和永恒的生命轮回。整首词从藤蔓、树木、乌鸦和夕阳等自然风物,从道路、秋风、马匹和天涯等人间羁旅中抽取出时间的介质,取得某种抽象化的同一。无论是植物成长,还是动物劳作,抑或人类羁旅,都寓于时间流程之中永不停息,直至生命“老”去,此后世界万物又周而复始,这便是永恒的必然。换句话说,作家对准的不是单独的自然景物、生活场面或环境处所,也不以意象呈现个别事物或具体事件,而是将所有意象直列出来,用时间介质构造一幅整体的图景,达到对羁旅和时间关系的参悟,进而直观历史的本质。作品展现的不仅是观照、触摸和感知的历史、自然物和人类场景,更有透过感性意象所传达出的精神本质,以浓缩的羁旅图景道尽人类历史轮回不已、永无归宿的不尽沧桑。所有意象既是事物,又是心境;既是物质,又是精神;既是具体,又是抽象;既是形而下,又是形而上。这种充满无奈的、跌入深渊的、愁苦异常的时间观或历史感才是本首羁旅小令所要表达的终极意义。
时间性在整首小令中有两种表现:其一是意象暗含各种时间性,如动植物的老去、一天劳作的结束、季节性的时间、古道的历史、羁人的旅程和天涯的遥远等等;其二是时间同一的介质化作用,将所有意象串联并给人以终极性的体悟。叶维廉曾在《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中认为中国古诗“呈露的是具体的经验”,即“未经知性的干扰的经验”,并将其概括为九条特色,其第二条便是“超脱时间性→空间的玩味,绘画性、雕塑性”4叶维廉:《叶维廉文集》第一卷,第72页。[YE Weilian, Yeweilian wenji (Collected Works of Wai-lim Yip), vol. 1, 72.],时间与空间对举,构成了中西诗学的差异,中国诗学重视空间性,西方诗学偏向时间性。不过,叶维廉在《语法与表现——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美学的汇通》中再次列举中国古诗的十条发现,其第四条又云“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视觉事象共存并发→空间张力的玩味、绘画性、雕塑性”5同上,118页。[Ibid., 118.],似乎对上述观点有所修正,但仍然侧重空间性。其实,在中国古诗中,时间性是与空间性相互关联的,时空交织才构建古典诗歌的无限境界。一片秋叶是一种现象,是纯粹自然的产物,这种现象本身就内含时间性,即所谓“一叶知秋”,且透过一片树叶已知整个秋天,从一个现象再扩展到包含所有现象的空间。因此,出现在古诗中的意象既是时间,也是空间,是时空的集合,时间空间化或空间时间化都是时空割裂后的审视和反思。换言之,古代诗人通常是将时空融合在一起的。时间是可以看到的,如枯藤;时间是可以听到的,如西风;时间是可以触摸到的,如瘦马;时间是可以感知到的,如古道;所有意象都是可以整体感知的,是处身性的、具身化的,是在周边的,与人的身心不远的。从字面意思看,“断肠人在天涯”与“小桥流水人家”相隔最远的距离,“天涯”在哪里,没有确指,它是一方想象的处所,无法与诗中其他意象构成图画。然而就整体来说,从周身最近的“人家”图景、“人家”外的旅途状态、推至所能到的“天涯”尽头,囊括了整个空间,最远的也是最近的,目击道存,何来远近。更何况,图景既有虚实,联结亦有虚实,虚实结合、空间同一,因而能共处于整幅羁旅图中而不见生分、尴尬与物理阻隔。最远的距离要花最长的时间,所以,旅人难以归家。词作将两者并举构图,最远的就在眼前,时空不分、时空化合。一旦归为羁旅者,便永远是羁旅之人,即便眼前在家,却总是要离家并走向天涯的。最终,人类历史与宇宙空间都融入其间,绵延无尽头的时空通过眼前的、简单的和自然的意象及其完整图景传达出来,这可能是中国诗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二、意象背后的行动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马致远小令《天净沙·秋思》说,“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6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6页。[WANG Guowei, Wangguowei wenxuelunzhu sanzhong (Three of Wang Guowei’s Literary Treatise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36.]。在《宋元戏曲考》中再次品评道,“纯是天籁,仿佛唐人绝句”7同上,138页。[Ibid.,138.]。该词直追唐诗妙境,得自于时空无限拓展,揭示出人类历史普遍的羁旅凄苦之情。时空的层层拓展使诗歌意境不断升华,最终臻至“天籁”。古典诗歌除却意象拥有的时空交织和宇宙意识外,还有其背后的行为和事件,它们不仅隐藏在单个具体意象中,如“瘦马”便有“旅人骑马良久,人困马乏;且常年如此,马匹变瘦”之意;也暗含在诸多意象所构成的张力图景中,如村边“小桥”下,河水从“人家”旁边穿过,“断肠人”骑着那匹“瘦马”走在“古道”上,“西风”凄紧,一路伴随直至“天涯”。因此,中国意象诗学并没有放弃行动,不顾及行为和事件,反而是想方设法将其置入意象及其所关联的场域内,取得静中藏动、动内有静、动静结合的审美效果。
在早期论文《静止的中国花瓶——艾略特与中国诗的意象》中,叶维廉并没有意识到古典诗歌意象的动静关系,似乎只是看到表面上的静态性,又急于去印证艾略特(T.S.Eliot,1888-1965)曾多次表达过的观点:“最醉心的诗”是那种能“‘延长静观的一刻’使‘一连串的意象重叠或集中成一个深刻的印象’的诗”。为此,叶维廉选择唐代孟浩然《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作为解读对象,诗中“客”和“日”及其他外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存在于一种使我们无法确切决定何者特别明显的‘暧昧不清’之中。它们融合成一种充满着‘不可名状’的愁的‘静态戏剧’(static drama)”,并说到类似效果的诗“在中国诗中数不胜数”,意象静止是其常态化的表现,诗人“把现实中一个插曲或片断的‘真性’和‘原形’捕捉和记录于诗中”,成为一个纯然的存在,也就是“密尔顿的所谓‘默而言’(silent yet spoke)的绕绕未尽的静态”。文章最后强调说,经过这样的例证和阐发,他希望读者已了解中国诗对艾略特诗学目标的真正抵达8叶维廉:《叶维廉文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65~71 页。[YE Weilian, Yeweilian wenji(Collected Works of Wai-lim Yip), vol. 3, Hefei:Anhui Education Press, 2002, 65-71.]。客观上讲,孟诗确实展现出“自身具足的意象”(self-contained images)及其所营构出的天地氤氲、整体静态的情境,具有一种张力和戏剧性,但诗中明显地将叙事线索隐藏在意象画面的背后,船家将小舟停靠在烟雨迷蒙的洲边,正值日暮时分,新愁涌上心头,主角(谁?)出船抬头,刚巧眺望远方(家的方向),无边旷野下,天比树还低,回首低身(还在旅途中)看到江水青青,只有月亮(水中之月还是天上之月?)与人相近(月亮代表对家乡的思念,亲人却与自己共享月一轮),整个过程自然有序,诗人邀请读者沿着潜在的行动轨迹进入眼前景物,于此在场的羁旅之思便油然而生。
在美景如画中隐含行动线索,邀约读者参与进去,并最终体悟诗人所要表达的情志,杜甫《望岳》在这方面有其出色的表现。诗篇伊始就说“岱宗夫如何”,诗人熟悉泰山在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早已心驰神往,“看他的口气,泰山还没有出现呢,他期待的感情就写出来了”9叶嘉莹关注到杜甫以儒学和作诗之家世传统而自豪,特别点出孔孟泰山之论和《诗经》“嵩高”诗篇。在阐述登山观景中则先提及陶渊明“悠然见南山”,却不爬上去而采取远观态度,与其腿疾亦有关系;谢灵运则非爬上山顶不可。接着说起杜甫《百优集行》中“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与孔子所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相对照,点出杜甫精力旺盛及其爬山志向,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但杜诗却没写爬上顶峰,而是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并以此推定诗写于“半山腰”,其论就创作而言过于切实。唐代王维山水诗中常写山中回来以表现其“王孙归不归”、“隔水问樵夫”等隐士情怀。就此,诗人爬山及其精神旨向具有文化差异,或许可从意象、行动和文化关系角度延伸叶维廉的思考。参见叶嘉莹:《叶嘉莹说杜甫诗》,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4~27 页。[YE Jiaying, Yejiaying shuo dufushi (Ye Jiaying’s Commentary on Du Fu’s Poem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8, 24-27.],用“赋”的手法直接叙说,其感发力也打动了读者,急于跟随诗人去登山游览一番;接着,诗中呈现远望之景,齐鲁之山蓊郁苍翠、绵延不绝;之后走进泰山,造化神秀、阴阳分明、白云飘荡、归鸟入林;到“半山腰”便立下决心,一定要爬上山巅,俯瞰脚下群峰。一路与诗人游历过来,读者既欣赏泰山美景,也体悟到传统文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卦》)的人生哲理,还有一种儒家心怀天下的胸襟气魄。整首诗歌并无半点说教色彩,只有风景秀丽所带来的审美愉悦以及登上泰山之巅的崇高情怀。如果联系到杜甫漫游泰山前遭遇进士落榜,那么其不畏艰难、勇于攀登的人生信念,自然更有一番体会,读者也会像杜甫那样收获那份文化自信和人生自信。行动轨迹连同其精神价值都被潜藏、被隐去,呈现的是如画的景物、情感的抒发,即便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也是心中所想,是意志的体现,并非实际行动。整首诗中,虚实结合、有阴有阳;动静关联、或明或暗;景行统一、亦隐亦显,重点在于意象在行动里蕴藏机巧,于叙事中关联情志。
平心而论,作为诗人的叶维廉不可能意识不到诗歌中的叙事性及其行为要素,只是囿于中西诗歌比较视野,在其所说的文化“模子”里展现异同,而没有对中国古诗之意象和行为的关联作更深入的思考。换句话说,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确实容易跌入为比较而比较的陷阱,将比较文学局限于“X+Y”模式的浅层次对比分析,寻找文化“模子”则能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从文学的文化深层来说明其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但“模子”结构本身同样有其理论视角的限定性,以语法规律的差异去观照文学和文化现象,难免会出现偏差。叶维廉说道,“在原诗里,诗人仿佛已变成了水银灯,将行动和状态向我们展现,在英译中或Gautier 的说明性的程序里,由于加插了知性的指引,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叙述者向我们解释事情。”10叶维廉:《叶维廉文集》第一卷,第66页。[YE Weilian, Yeweilian wenji (Collected Works of Wai-lim Yip), vol. 1, 66.]“原诗”指的是李白《送友人》诗的首联“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两句,他通过对比英、法译文,强调中国古诗意象呈现的特色。的确,诗中没有出现更多的双方离别行动的叙事,反而侧重于状态的描写,送别环境也是状态的一种,即便没有那句“挥手自兹去”的行为描写,想必通过其他诗句也能知晓此诗的送别主题。诗人不想去叙述送别双方所行之事,是否意味着中国古诗就有意忽略叙述者及其所叙之行为呢?在叶维廉所作的评论中,“行动和状态”指的是诗中描写的阔大的送别环境,却忽视了两者在传统诗歌中的互动和结合,尤其是意象与行动的隐秘关联。整首诗中,首联和末联以写景为主,中间两联则以情感表达为重,尾联中“挥手自兹去”系行动话语,即挥手告别,真的要上路了,此时萧萧马鸣、无限深情。第二联中写道此地一别,召唤读者进入离别场域,“孤蓬万里征”是想象友人离别后的情况。诗中描绘了送别的场景和行为,别后的孤独以及双方的挂念。送别作为事件,在行为话语中潜含一位叙述者,那些行为叙述更是其中的引子,引导读者身心在场、体会情感,甚至替双方去想象往后的生活。自然秀丽的场景、故人离别的情感和游子漂泊的虚构相互交织、气韵悠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比西方诗歌类型,中国叙事诗的确不发达,但古诗并没有取消叙述、行为和事件等行动性要素,更常见的是隐藏在状态或环境的描写中。就拿“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来说,这是一种状态的描写,可以是一幅静止的画面,但里面却包含了自然社会的生命行动,“横”、“绕”都是动词。中国诗学是动静结合的,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主静的景物中并非没有行动,其内里都是活跃的、有生命的,但是从更高更大的视角观察,却是静止的;就如同仰观天象,星空完全不动;俯察大地,河水像条白练;天地的一切都像是静止的,其实是昼夜不息、持续变化的。因此,由于叙事性文学更多的要求叙事者现身,并用某种视角去讲述故事,蕴含其特有的说明和理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等都必须清晰化、有条理,更富有知性之美,叶维廉便局限于西方文化的叙事模子,有意无意抹去古典诗歌中事件的叙述者及其行为的呈现,只看到其静观可视的自然画面。实际上,中国古诗中事件和行动经常隐藏或包含在单个意象和意象群所构成的意境中,且是读者能否进入诗歌审美世界的关键所在,是体悟诗歌情志表现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三、语言与意象诗学
晚清以来革故鼎新,在中国学人纷纷向西方文化取经,主张拿来主义,以实现自身社会和文化文学的现代性之际;西方诗人却反向行之,到非洲、东亚等国家的传统文化里去寻找语言的原初之美、诗歌对历史的穿透力和建构更具普遍性的诗学体系,以展示诗歌领域更广泛更深层的现代路途,象征主义、意象派等西方现代诗歌都有中国古典诗学的痕迹。叶维廉深处其境,难免受其影响。一方面,学习、仿作和倡导西方现代诗歌和诗学;另一方面,译介、突显和改写中国古典诗歌和诗学;在两者之间寻找比较诗学的出路。他自己“喜欢中国那种很丰富,很含蓄,不依赖陈述,由意象构成多层次意味气氛的短诗”11叶维廉:《叶维廉文集》第七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375 页。[YE Weilian, Yeweilian wenji (Collected Works of Wai-lim Yip), vol. 7,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2002, 375.],其诗歌创作借用西方交响乐的架构让意象互动,应对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其诗学观念则认同庞德“称赞传统中文的优美,称之为最适合诗的表达的文字”,觉得“它可以去掉很多抽象的意念,而具体地将意象呈露出来”12同上,351~352页。[Ibid., 351-352.],意象成为两者交织和会通的着力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庞德的诗歌创作、诗学观念确实青睐中国古诗,受其意象观念的影响,并以此进行了独特的“译创”行为,但他并不懂汉语,也不熟悉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区分,无法对此详加阐述,只是以诗人的艺术直觉,认为方块汉字直呈意象,借助其象形、会意等造字手法,构建自己的意象诗学。回过头去,索绪尔(F. Saussure,1857-1913)将所有语言当作一种符号,析出能指与所指两个层面,有助于理解语言之符号性质。任何文字都能传达抽象的意念,与欧美字母文字相比,汉字的特性在于其图像性。实际上,叶维廉所说的去掉抽象意念,将意象具体呈露的观点也是自己比较中外语言,尤其是中英语法所得出的独有贡献。换句话说,庞德在汉字图像性和中国古诗特色的基础上所构建的意象诗学,进一步得到了叶维廉给予的汉语语法方面的证实。但问题在于,他并没有像庞德那样重视诗歌意象,并以之为中心构建诗学体系,而是以语言为根基来阐述中西诗学的差异与会通。总之,叶维廉看到了中国古诗的意象特性,却以比较语法来加以阐明。
一般而言,如果要通过中西语法比较其诗学观念的异同,那么应该对中西语言或中西诗歌语言进行分析和对比,叶维廉却从中国古诗的英译来阐述其诗学主张,其视角着实独特,令人印象深刻。在李白诗作《送友人》(青山横北郭)英译中,他发现中国传统诗歌语言的特点:(1)几乎没有跨句(enjambment),每一行都有完整的意义;从句式上说,英诗、英译的跨句是常见的,是英语轻重音、押韵等韵律、节奏与诗歌分行、意义组合等规则关系的体现。(2)没有人称代词、冠词和动词变化;这些语法在西方语言中的使用都是为了所指具体化和清晰准确的表达目的。(3)如上所述,动词没有时态(tense)的变化。(4)经常缺乏连结媒介(动词、前置词、或是近乎动词的形容词),西文却以此来“拉紧前后两个单位的关系”13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三联书店,1994 年,第248 页。[YE Weilian, Zhongguo shixue (Chinese Poetics), 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248.];叶维廉在《艾略特的批评》、《静止的中国花瓶——艾略特与中国诗的意象》等论文中都表达过类似观点,如在前文里具体说到中国“诗中‘连结媒介’明显的省略——譬如动词、前置词及介系词的省略(但却是‘文言’的一种特长),使所有的意象在同一平面上相互并不发生关系地独立存在”14叶维廉:《叶维廉文集》第三卷,第62页。[YE Weilian, Yeweilian wenji (Collected Works of Wai-lim Yip), vol. 3, 62.]。显然,文言文的独特性表现在词语的使用、句式的变化和单元连结等语法规则上,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自然也有其中西文化上的差异性。
正是由于汉字本身的图像性和语法的灵活性、超脱性,使诗歌创作具有事物的自呈性、视觉化效果和意象并置的戏剧性张力,因而更富有现代诗意。与此对应,西方语言则表现出语法上的逻辑性和分析性特点,陈述性较强,其主语的介入、时空的限定和冠词、连结词的使用等,容易构成主观化和概念性的世界,有时则显得过于呆板和局限,只能给读者提供某种解释,或使读者透过某种视角去观察和阅读。叶维廉将语言结构的模式拓展到思维方式、逻辑结构、诗歌创作与赏析等方面,构成以语言结构为根基的跨文化比较诗学体系,而语言结构主要指语法规律,是其倡导的比较诗学“模子”论的具体运用。“模子”被视为一种具有行动能量的结构,文言文拥有的未定时、未定向的语法特征,决定了中国古诗意象的可视性、画面感和超时空的关联构建,体现出暗示的、细化的和纯粹经验的美感活动,生发出中国古诗独有的特征。赵黎明指出,“从语法角度研究中西诗歌语言结构的差异,正好触及了两种语言文化‘模子’的根本”15赵黎明:《“模子”互照与“第三种诗学”——论叶维廉对现代汉语诗歌语法的发明》,《中国文学研究》2022 年第2期,第1~8 页。[ZHAO Liming, “‘Muzi’huzhao yu ‘disanzhongshixue’—Lun Ye weilian dui xiandai hanyu shige yufa de faming” (Correlation of “Model” and the Third Poetics—On Wai-lim Yip’s Invention of Modern Chinese Poetic Grammar),Zhongguo wenxue yanjiu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2 (2022): 1-8.],成为比较诗学中文明互鉴的金钥匙。叶维廉也由此种“新批评的‘语言的结构’的内在应合的关注”16柯庆明:《现代中国文学批评述论》,台北:大安出版社,1987 年,第129 页。[KE Qingming, Xiandai zhongguo wenxue piping shulun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Taipei: Da’an Publishing House, 1987, 129.],在传统文学上广涉李白、王维、孟浩然等唐代诗人作品,在诗学观念上申说司空图、严羽和王士禛等人的诗论,最后宗于庄子的语言观和自然论思想,集语言、诗歌、诗学和哲学等多学科于一身,其诗学理论相当完整、颇具创新性。
总的来看,叶维廉比较诗学赓续传统、跨越中西,回应当代诗歌创作与诗学发展。在中西诗学比较视域下由语法决定意象,其具体程序是先确定中西语言在语法上的差异,然后将语法差异贯彻到中西诗评和比较诗学的构建中,最终以此来观测、剖析中西诗歌意象的运思方式和指义行为。然而,其结构、模子式的语法诗学无疑具有某种局限性,除了上述潜隐的、内在的时间性和行动性外,难免对中国古诗意象中的其他内容也思虑不足。叶维廉在论文《中西山水美感意识的形成》中将王维《鸟鸣涧》和华兹华斯《汀潭寺》(Tintern Abbey)进行比较分析,夏志清(1921—2013)曾对此提出过专门批评,认为把王维四句诗说成是景物直现读者面前,而长达150 多行(叶文说162 行)的华诗却难达合一境界,这种说法是不公平、不正确的。首先,《汀潭寺》里部分诗行具有“天人合一”、怡然自得的神秘之境;其次,中国传统诗评、创作都要求情景并重,王维那种“带有禅味的有‘景’无‘情’的绝句”在中国诗中绝不多见,即便在其本人诗集中亦不多见;再次,古代诗人受其形式和syntax 的限制,无法创作出华兹华斯那样复杂的长诗,华诗中所表达的对妹妹的真挚情感亦是中国诗少见的,中国诗即便有亲友情感,也是以应酬居多,毫无个人面貌;最后,夏文指出,叶维廉“太偏爱中国诗”,其喜欢的国外诗歌都是“带些中国味道的‘意象诗’(imagist poetry)”,然而“意象诗”在欧美诗界是“末流,不能算数的”17夏志清:《人的文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150~151 页。[XIA Zhiqing, Ren de wenxue (Human Literature),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1998, 150-51.]。即便叶氏偏爱中西意象诗,但并没有给意象以足够的重视,反而被中西语言的结构性差异所限制。换言之,叶维廉集中于中西语法上的自由与严谨、灵活与守序、超脱与呆板、自然兴发与主观参与、事象呈现与条理说明、视觉经验与逻辑安排等二元对立的结构形式,其诗学观念连意象自身所暗含的情志表现(情、景被称为中国诗学的二元质)也被忽略了。
退一步讲,就算认同叶维廉的语法诗学,我们也会看到中国古诗中并非不用那些定向、定时和定义的连接要素。明代谢榛(1495—1575)曾用摘句批评比较过三首唐诗,它们都用相同意象来造境、写境,“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四溟诗话》)。“三诗”分别是:韦应物《淮上遇洛阳李主簿》里的诗句“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居易《途中感秋》的颔联“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和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的第二联“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在谢氏的评论中,“同一机杼”是指三句诗都表达同样的对岁月流逝的无限凄感,其主题表现所使用的意象都为“老人”与“秋树”,三位诗人试图抓取日常的、熟悉的生活场景,按照中国古诗固有之自然物和时间性的结构来传情达意;其“善状目前之景”、“见乎言表”等评语正是叶维廉所看重和推崇的诗学观念。但是,在考察“司空为优”时就会发现,当“白头”意象能传达出“人老”的时间性时,就无需“将老”、“欲……时”等词来表示时间的延展;同样,当“黄叶”意象已经内含“秋天”之季节时,就要删除“已秋”、“初……日”等词来表达时间的确定。此外,司空曙诗“雨中”、“灯下”意象明显有助于表达主题,两个日常空间的并置体现其“如在目前”、“自然呈现”的画面性,其情感兴发自在其中矣。但是,如果没有表示方位的“中”、“下”,此诗根本无法构成目前之景,只会给人零乱之感。也就是说,当传统诗歌仅靠意象难以达到诗学目标时,就不会拒绝使用表示方位、时空和指义的词语,此时的需要是毫不含糊的。
结 语
叶维廉年青时就喜欢诗歌创作,作为学者则从事诗歌翻译、批评和理论研究,跨越中西文化,其诗学研究视野开阔,又有诗歌实践的支撑,故能深入不同语言文化的内在结构,既在西方文化面前肯定了道家美学、文言传统及其诗歌意象、视境与艺术精神,“对盲目西化的诗人,更有如暮鼓晨钟,振聋发聩的作用”18张汉良:《语言与美学的汇通——简介叶维廉的比较诗学方法》,见廖栋梁、周志煌编:《人文风景的镌刻者——叶维廉作品评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第374页。[ZHANG Hanliang, “Yuyan yu meixue de huitong—Jianjie Yeweilian de bijiao shixue fangfa” (The Convergence of Language and Aesthetics—An Introduction to Wai-lim Yip’s Comparative Poetic Method), in Renwen fengjing de juankezhe—Yeweilian zuopin pinglunji(The Engraver of Humanistic Landscape—Commentary on Wai-lim Yip’s Works), eds. LIAO Dongliang and ZHOU Zhihuang, Taipei: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Publishing House,1997, 374.],又在中国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中借鉴西方文化与诗学观念,在语法“模子”的基础上辨别异同,力求不同文化诗学的出位与会通。不过,“模子”论本身就带有结构主义的弊端,在比较语法上去阐明中国古诗的意象,在两者所搭建的诗学大厦的阴影下,古诗意象的时空性及其视镜的价值、事件和行动对审美阅读的引领与感发力,还有其意象之情感包孕、具体化方位和旨义暗示等都变得晦暗不明,更不用说儒家诗学、意象用典等阙如的问题。叶维廉曾自陈理论研究开放之必要性,“真正的理论家”要警惕自己的“提法”,它是把“双刃剑”,在“坚持自己理论主张的中心性”时,就已“暴露其否定性”19Wai-lim Yip, Diffusion of Distances: 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185.,其学术精神辩证、通达和自由创造,强调诗歌经验的阐发,勿用理论作茧自缚。于此,我们或许可以从语法诗学转向意象诗学,在比较诗学视野下通过“意象—文化”视角去理解中国古诗,进而发现其精义所在,呈现中国诗学的世界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