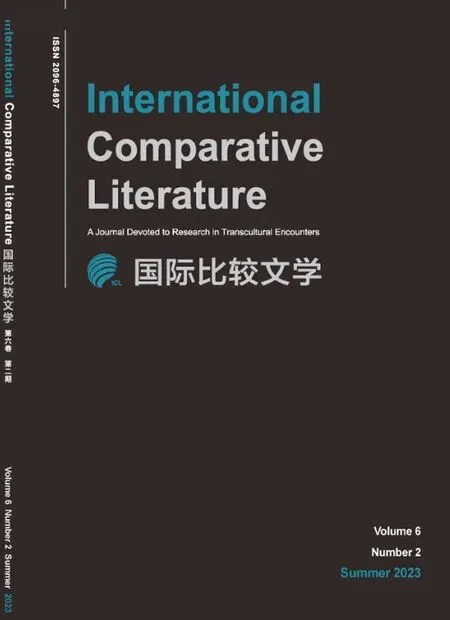“天之上何物?”
——塞韦里尼与中国经典及其对于“朱子问天”的回应
范狄 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
安特尔莫·塞韦里尼(Antelmo Severini,1828-1909)是意大利汉学研究的先驱者1塞韦里尼并非意大利第一位教授中文的大学教授。在他之前的1757 年至1819 年间,朱塞佩·哈格(Giuseppe Hager 1757-1819)于1806/7 年在帕维亚大学担任东方语言和文化教授;1849 至1865 年期间,朱塞佩·巴德利(Giuseppe Bardelli,1815-1865)在比萨大学、佛罗伦萨的劳伦佐图书馆(Biblioteca Laurenziana di Firenze)和佛罗伦萨皇家高等学院担任该领域的教授。尽管哈格和巴德利都曾教授过中文,但与塞韦里尼不同的是,他们对中文的了解不够深入,仅能讲授有关不同东方语言的基础理论知识。因此,他们未能创造出汉学传统。。1860 年,他前往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impériale de France)和东方语言皇家专院(École impériale et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学习远东语言,并拜师欧洲最著名的大师。在巴黎学习的三年里,他向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及其学生安托尼·巴赞(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1799-1862)学习汉语,并在第二年开始向莱昂·德·罗斯尼(Léon De Rosny,1837-1914)学习日语。这些年来,他在学习汉语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
儒莲在1863 年6 月6 日写给意大利政府教育部长米歇尔·阿马里(Michele Amari,1806-1889)的信中,表达了对塞韦里尼的高度评价。儒莲表示:“安特尔莫·塞韦里尼先生已参加我在法兰西公学院开设的汉语课程三年。在过去32 年里我所教过的所有学生中(其中一些人已发表受业界赞赏的译作),没有一个人像塞韦里尼一样在这项艰苦的研究中付出如此多的努力,并同他一样取得惊人的成就。……如果意大利政府将在中国设立一些正式职位,我认为安特尔莫·塞韦里尼先生是这些职位的不二人选”2儒莲的推荐信并不是塞韦里尼杰出成就的唯一证明。其他著名的法国东方学家,例如朱尔斯·莫尔(Jules Mohl,1800-1876)、欧内斯特·雷南(Ernest Renan,1823-1892)和约瑟夫·图森·雷纳德(Joseph Toussaint Reinaud,1795-1867)等人也写了褒奖信给部长,并建议为塞韦里尼寻找一份适合其能力的工作。。。
阿马里于1864 年在佛罗伦萨皇家高等学院(Regio Istituto di Studi Superiori di Firenze)设立了意大利首个远东语言和文学教授职位,并聘任了塞韦里尼。他担任该职位直至1900年。塞韦里尼在当时最重要的意大利学术期刊(包括《意大利文学与艺术期刊》《意大利大学》《新文集》《综合科技》等)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并且是词典编纂作者、中文和日语教学材料、论文和小说的翻译家。在汉学领域,他的主要贡献包括语言学和儒家思想3塞韦里尼关于汉学主题的作品包括:《中文文法的前言》《孔夫子和他的学派》《中国文学的精神与艺术》《关于图都兰语与汉语两种语言的共同起源》《中国哲学家孟子的道德与政治》《每门语言的最短却最重要的词》《单音节性的语言真的存在吗?》《中国人的神》《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责任感》等。塞韦里尼关于中国的作品列表可以在Vacca(1913)中找到。,并且培养了意大利下一代主要的汉学家。其中,卡洛·普意尼(Carlo Puini,1839-1924)和洛多维科·诺森蒂尼(Lodovico Nocentini,1849-1910)分别在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罗马担任中国及东亚语言文化的教授。
本文旨在分析塞韦里尼在1867年课程设立仪式上所作的发言。该篇发言于次年1月在安杰洛·德·古贝纳提斯(Angelo De Gubernatis,1840-1913)4该人物是梵语语史学家和比较神话学家,同时也是佛罗伦萨东方学社团的积极参与者。主编的《东方杂志》(Rivista Orientale)上刊载,题为《中国人的神》(Il Dio dei cinesi)5Antelmo Severini, “Il Dio dei Cinesi” (The Chinese God), Rivista Orientale (Oriental Magazine) 11 (1868): 1090-112. 在将意大利语单词“Dio”翻译成中文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问题。通常情况下,“Dio”被翻译为“上帝”或“天主”,但这两个词汇并不符合塞韦里尼对中国宗教的分析。,专门探讨中国宗教。刊登塞韦里尼的演讲论文之前,安杰洛·德·古贝纳蒂斯进行了简要评述,宣布即将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这篇论文。他评述道:“这次演讲博学而精妙(......)理所当然地收获了听众潮水般的掌声”,并同时夸赞了“塞韦里尼的学识和严谨的怀疑精神”6Angelo De Gubernatis,“ Prolusione del Severini al suo corso di cinese” (Severini’s Prelude to His Chinese Course),Rivista Orientale (Oriental Magazine) 10 (1867): 1058-59.。塞韦里尼采用了创新的研究方法,他的分析直接建立在中文原文材料的基础之上,而非基于其他传教士和到访过中国的西方人的二手资料。
一、对先前有关中国人的宗教研究的批判
《中国人的神》主题是中国人的宗教。这是欧洲汉学最为经典的讨论话题之一。自天主教传入中国初期以来,耶稣会士、道明会士和方济会士对中国宗教信仰的性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引起了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即使1742年教皇本笃十四世发表了《自从上主圣意》(Ex quo singulari)的训令,辩论也未完全平息。18世纪下半叶,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角们也参与了这场辩论,有关中国宗教的话题再次浮现。19世纪新教在中国传播时,新传教士、德国学术界和英国学术界之间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与此同时,持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似乎时而支持耶稣会士,例如卡尔·约瑟夫·希尼穆斯·温迪施曼罗(Karl Joseph Hieronymus Windischmann,1775-1839)、约瑟夫·赫尔曼·施密特 (Joseph Hermann Schmidt,1804-1852),时而赞成道明会和方济会的观点,例如阿道夫·伍特克(Adolf Wuttke,1819-1870)、彼得·费德森·斯图尔(Peter Feddersen Stuhr,1787-1851)、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
塞韦里尼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西方汉学家有关中国宗教的争议,简述了主要观点,并将此争议称为“不愉快的故事”7Antelmo Severini, “Il Dio dei Cinesi”(The Chinese God), 1090.。他认为没有必要逐一反驳错误观点以捍卫他认为正确的思想,因为他不想“卷入众说纷纭的神学问题”8Ibid., 1090.。这在他试图解决中国宗教问题的文本中,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
塞韦里尼认为,如果将基督教视为唯一真正的宗教(即奥古斯丁所说的“vera religio”),并总是试图将其作为中国宗教的参照点,那么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宗教。讨论“上帝”或“天”是否与圣经中的“Deus”相对应,会导致人们无法认识到这些术语的特殊性。因为这些观念是在完全独立于基督教传统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只有通过参考原始资料,才能真正理解它们。因此,传教士采用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们以形而上学信仰的僵化体系为前提,试图强行容纳中国宗教。此外,传教士的动机与纯粹的学术研究是不同的。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证明其传教模式的合理性。因此,他们在作品中可能会遗漏或扭曲许多值得探讨的内容,降低了研究成果的可信度。传教士在关于中国的著作中所犯的错误已经污染了整个欧洲汉学世界。因此,以前欧洲人所写的作品对于了解中国几乎没有用处,尤其是在涉及宗教这样敏感的话题上。幸运的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欧洲人可以更容易地学习中文和获得中文书籍。为了对中国宗教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研究,就必须阅读权威资料,即中文原文书籍。
塞韦里尼未曾远赴中国,仅在巴黎学习三载,尽管对汉语略有涉猎,但其汉语熟练程度仅限于书本知识,且未能够用中文进行口语交流。不过,这种情况跟几个世纪前的传教士汉学家们截然不同。后者曾在中国居住多年,沉浸于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之中,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如今,学者们对于一个缺乏直接接触和语言知识有限的教授对传教士汉学家进行严厉批评并否认其著作的可靠性感到惊讶。但是塞韦里尼的批评源于其对汉学提供科学依据的期望。为此,必须纠正过去的错误,摒弃先入为主的观念,依据权威资料,全面依赖中国文献,并采用严谨的语言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塞韦里尼在儒莲门下获得了研究文言文和白话文所必需的语言学和文献学技能。儒莲是中文著作的杰出翻译家,主张采用分析的方法研究中文文本。意大利汉学传承了法国学派的文献学研究方法,但巴黎汉学家的著作并不像塞韦里尼那样严厉地谴责传教士汉学,可谓是全盘否定。在儒莲的著作中,有时会出现对传教士汉学家的批评。例如,在其为《道德经》翻译所写的序言中,他批评了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因为这些传教士认为自己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再次发现了圣经中的上帝给予古代启示的迹象:“出于在中国迅速传播基督教的值得称道的愿望,以及无可置疑的信念的推动,一些耶稣会学者尝试证明,中国古典文学中包含许多明显是从圣经中借用的段落,甚至包含天主教教义。如果他们说的是正确的话,根据最正统的信仰进行推理,我们不得不承认上帝已经给了中国居民一种预期性的启示”9Stanislas Julien, Lao Tseu Tao Te King. Le livre de la voie et de la vertu (Lao Tzu Tao Te Ching. The Book of the Way and Virtue)(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42), 4.。儒莲批评传教士汉学家的研究,显然是为了证明中国经典与犹太教和基督教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如此,儒莲确实曾多次表达对许多传教士汉学家的高度敬意,并承认自己对他们的亏欠。儒莲认为,“要想理性研习中文,分析法是必要的,也就是按照哲学方法剖析由传教士和追随传教士的欧洲学者翻译得最好的文本”10Stanislas Julien, 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A New Chinese Syntax) (Paris: Librairie de Maisonneuve,1870), 3.。相反,塞韦里尼对传教汉学的文本传统持极度批判的态度。他的态度可能有些过激,认为应全盘否定传教士汉学。
塞韦里尼强烈批评传教士汉学的原因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他倾泻了反对教权的激烈情绪,这种情绪在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和统一后的知识分子圈子中广泛流传。新生的意大利王国政府正处理着伟大的问题:为一个刚刚赢得独立并建立起民族团结的国家提供新的制度。罗马教会试图阻止统一运动后,继续反对意大利王国,并积极影响公众舆论。自由主义者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政治辩论十分激烈且两极分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许多知识分子,正如塞韦里尼一样,倾向于批评与天主教文化有关的一切。这种态度在他的学生及其他学院同事的作品中也经常出现。这种态度是当时意大利东方主义的一种特征,更广泛地说,是当时意大利知识界的一种特征。塞韦里尼并没有将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而是利用中国古典权威支持自身的政治主张。结果是他所描绘的古代中国形象相当理想化,对于今天的专家来说显得抽象且缺乏历史准确性。
塞韦里尼明确表明,谈中国宗教研究,他认可的唯一一位西方汉学家是德国学者约翰·海因里希·普拉斯(Johann Heinrich Plath,1802-1874)。他指出:“这位来自德国的汉学家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的研究,将这个古老国度宗教的每个细节介绍给了欧洲”11Antelmo Severini, “Il Dio dei Cinesi”(The Chinese God), 1095.。 普拉斯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汉学家,于1864 年发表了一部重要著作《古代中国人的宗教与崇拜》12Johann H. Plath, Die Religion und der Cultus der alten Chinesen (Religion and Cul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München: 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864).,这是一部完全基于中文原文文献的大型研究。普拉斯采用的方法符合塞韦里尼提倡的科学标准。《中国人的神》则可以看作是对普拉斯著作的评论。塞韦里尼不仅直接提到了普拉斯的观点,而且读者可以在他们两位的作品中找到许多平行、相互对应的段落。显然,在谈论中国人的信仰时,塞韦里尼借用了普拉斯在书中提到的许多内容。虽然两位作者分析的文献材料大致相同,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有所不同。塞韦里尼承认普拉斯的研究“非常准确、富有智慧”13Antelmo Severini, “Il Dio dei Cinesi”(The Chinese God), 1095.,但也批判了他的观点。塞韦里尼不同意普拉斯将中国的宗教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有着单一的体系和教条的观点。在讨论儒家经典时,普拉斯认为“天”和“上帝”是同义词,表达了所有中国人虔诚信仰的明确、独特的神学概念。但是,塞韦里尼认为普拉斯默认中国人的神是一个神学体系的基础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普拉斯没有认识到中国宗教的特点:中国人的宗教是一种礼仪制度,强加了对礼节的遵守,但是不强迫人们相信任何教条。塞韦里尼指出,中国宗教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包容各种信仰和哲学思想。他认为:“中国宗教的显著特征在于它可以容纳各种信仰和哲学思想。中国人比其他任何种族都更具有认知和科学自由。”14Ibid., 1091.
二、论中国人的宗教
塞韦里尼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儒家文学。在探讨中国宗教时,他不涉及佛教文学,因为佛教并非本土宗教。此外,他还将道教排除在外,承认自己对道教仍存在诸多困惑。塞韦里尼主要详细研读了五经,并将其定位为“中国人的圣经”15Ibid.。19 世纪下半叶,将东方文学经典描述为“圣经”(Sacred Books、Bible)成为一种新趋势。此前,欧洲知识分子认为旧约和新约是唯一的圣经。19 世纪比较宗教学提出了如下思想:宗教学家应该将旧约、新约、古兰经、阿毗达摩经、五经和道德经视为同一水平,并对其进行公正的分析16Norman J. Girardot,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Berkeley, Los Ange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252-54.。塞韦里尼使用“圣经”一词来指代儒家经典。他于1867 年翻译了《圣谕广训》的部分内容,并准确地翻译了其中的第7条(“黜异端以崇正学”)。他将这个翻译命名为《一个中国人审判之下的三大宗教》并进行出版,在注释中解释了“圣经”一词的用法,即指代儒教经典:“我采用了这个词词源意义上的定义”。该词源于古希腊语的βιβλίoν,复数形式为βιβλία,简单地说就是书的意思,通常指的是圣书。“毕竟,意大利语词语没有比这个词更能忠实地呈现中文‘经’的含义”17Antelmo Severini, “Tre Religioni Giudicate da un Cinese. Il capitolo settimo del Santo Editto parafrasato da Wang-Yeu-Po”(Three Religions Interpreted by a Chinese. The Seventh Chapter of the Holy Edict Paraphrased by Wang-Yeu-Po), Rivista Orientale (Oriental Magazine) 7 (1867): 133.。这也反映了早期欧洲东方学的普遍特点,即将亚洲语言和文学视为经典语言和文学,就像古希腊语、拉丁语或圣经希伯来语一样。当时的汉学家对中国的兴趣并不在于现代或中世纪的中国,而是在于中国古典时期。他们通常将中国古代文明与其他过去的文明进行比较研究。
1.民间信仰与哲学思想
五经不是一个连贯的著作,而是由多个古老、权威的作品组成,其中融合了著名学者的注解和编纂,并涵盖了不同时代的历史。此外,这些作品中的观点来源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且并不总是相容的。因此,有必要“区分大众信仰与哲学家的观点,但同时也不能排除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18Antelmo Severini, “Il Dio dei Cinesi”(The Chinese God), 1092.。根据塞韦里尼的观点,中国的民间信仰主要体现在《诗经》中。该书视为“古代人民的乐曲合集”19Ibid., 1095.。在《诗经》中,最常见的神的名称是上帝。中国人民所信仰的上帝似乎是以皇帝为模型,是一种人格化的神。皇帝在他的宫殿中统治整个中国,而上帝在天空中统治万物,颁布天命。就像“天子”中的“天”隐喻上帝一样,“在圣经中,在我们的古典和现代语言中,也通常用具有天穹隐喻的表达方式替代神的专有名词”20Ibid., 1096.(Severini 1867:1096)。在民间信仰中,“天”不是指物质层面上的天空,而是指上帝,一种精神的、人格化的存在。这种人格化不同于希腊神话中的神或旧约中的神。上帝的行为永远不会被愤怒或其他人类情感驱使。塞韦里尼说:“中国人民的上帝,虽然是一种人格化的神,但是如此雄伟,如此威严,以至于我们在其他人民的信仰中通常找不到一位更崇高、更值得人类关注、拥有更纯洁品格、更不受情欲影响的人类思想的产物。毕达哥拉斯指责主神朱庇特过于人性,神圣性不足,他应该愿意向这个中国民间的上帝鞠躬。这使中国民间的上帝充满威严。这种说法也许没有诗意(也有人会说缺乏戏剧性),但上帝一定比圣经中的雷电或令荷马颤抖的奥林匹斯威严”21Ibid., 1107-8.。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上帝是完美的原型,对所有事物和人都进行正义的统治,对善良之人慷慨,惩罚罪恶之人但不带有仇恨。它始终代表着中国和所有民族的利益。中国传统的上帝跟圣经旧约的神和古希腊神话的神都不同,因为只有上帝对所有民族不偏不倚。
上帝是中国皇帝必须效仿的理想典范,同时也是一个比皇帝更为强大的存在。尽管上帝是最强大、无与伦比的存在,但这一点与圣经中上帝的全能概念不同。在中国,上帝并非人民唯一信仰的神祇,因此,供奉其他神灵是必要的。在中国宗教信仰中,人们崇拜多个对象,如地神、山神、海神、祖先等。这足以证明中国宗教信仰不遵循一神论,“至少不是在清真寺、犹太教堂和天主教堂中所理解的严格意义上的一神论”22Ibid., 1104.。
然而,塞韦里尼认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中包含了一种不同形式的一神论概念。就像上帝是皇帝效仿的对象一样,整个中国万神殿的结构类似于帝国社会的等级制度,而上帝处于这个结构的顶端。虽然上帝不是唯一值得信仰的神灵,但在所有神灵中,他是最具权威和最值得尊敬的一个,就像皇帝是人类中最具权威和最值得尊敬的一样。中国宗教信仰中的隐喻意象、语言、仪式、等级制度等与政治世界密切相连。上帝的神圣优越性与皇帝在平民中的优越性非常相似,这进一步反映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制(monarchia)。从广义上讲,中国人的古代宗教是一神教(monoteísmo)。总体而言,中国人承认上帝是唯一最具权力的神灵,但并不排除其他神灵的存在,也不排斥对其他神灵的崇拜。塞韦里尼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定义为一神论的一种形式。然而,他认识到上帝的概念只是在广义上是一神论的。他所描述的概念更像是一种君主多神论(monarchic polytheism)或“单一主神论”(henoteism)。或许塞韦里尼的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护中国民间宗教无法创建一神论的概念,以免受到原始宗教的谴责。
对于民间宗教,上帝代表中国人的神,而天则是上帝的一个简单隐喻。然而,中国哲学家的宗教思想则恰恰相反。哲学家常用术语“天”而不是“上帝”。这是基督教神学传统和中国哲学传统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一般情况下,西方神学家和哲学家直接使用专用名词来表示“神”,这也暗示了西方“人格化”的神学概念。他们很少使用“天”,如果使用,大多数也是在隐喻的情况下使用。相反,在中国哲学著作中,使用“天”一词是普遍的。按照中国的传统,这不是隐喻,而是在哲学意义上的用法。儒学中的“神”并不指人格化的上帝,而是指宇宙的原理。天不仅仅指物质层面的天空,也不仅仅指精神意义层面的上帝,而是同时存在于两个层面。哲学家使用“天”这个词来表达一种泛神论的观点,即“有精神的自然”的意义,它不是一个存在于宇宙外部的、脱节的“神”的概念。
2.宇宙起源
“天”并无人性或意志,因此也不是造物主。中国哲学传统没有讨论创造神的概念,也没有探讨宇宙起源的问题。中国哲学运用物理学术语来解释宇宙的起源。关于这个问题,塞韦里尼阐述了宋代哲学家们的观点:“学者们研究人类和世界的起源,他们经常提及原始的混沌、以太、重与轻的物质、细微的液体以及五个元素(而非我们古代人所提及的四个元素)。在此之后,他们主要讨论了两个主要的原则:阳和阴。这一原则代表了自然界中相互对立的主体,如男女、光明与黑暗、生长与衰退、生命与死亡。阳和阴的运行遵循了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五个元素。在分离、融合、转变的过程中,“它们在和谐的过程中创造并维护了世界和人类”23Antelmo Severini, “Il Dio dei Cinesi”(The Chinese God), 1101-2.。
在塞韦里尼看来,这种物理学的宇宙起源理论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为什么儒家要参加祭祀和其他宗教活动呢?塞韦里尼使用了“三才”理论来回答这个问题。 “三才”是指三个基本存在:天、地和人。地从属于天,从而诞生了和谐的自然规律(如四季、自然产物等)。人或多或少地服从于地和天,这有助于或扰乱地与天之间的和谐。因此,人的行为是造成富裕或饥荒的原因。因此,献祭和赎罪是必要的。这种宇宙观也是物理学的,是一种“将世界的起源置于世界本身中”的系统24Ibid.。
然而,“三才”学说在宗教和道德层面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为普通人和哲学家一起实行宗教崇拜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使得在宗教实践中协调不同的宗教理论,例如对“天”和“上帝”的不同理解,成为了可能。
3.中国宗教是宽容的宗教
中国哲学家的智慧在于他们不强迫人们接受他们的哲学思想,而是鼓励参与者信仰他们选择的神灵。中国哲学家更喜欢使用“天”这个中性的词语来表达宇宙和神性的概念。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对不同宗教信仰的容忍程度。“尽管天具有广义的神祇观念,但它同样适用于任何哲学和宗教系统的表达方式”25Ibid., 1112.。
塞韦里尼在演讲中旨在回答朱熹小时候向他父亲提出的“天之上何物?”的问题。这里指的是清《南溪书院志·年谱》中著名的故事“朱子问天”。塞韦里尼的答案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天上有一个类似于皇帝的上帝,但又比皇帝强大得多。然而对于文学家和哲学家来说,天上什么都没有。那么,什么才算是中国人的神呢?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物质;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精神;而对于少数人来说,两者都不是。每个人心目中的神是什么样,那个神就是什么样”26Ibid.。塞韦里尼认为,中国宗教的主要特点是宽容。中国人的宗教通过仪式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但不会强加任何信仰教条。
结 论
在《东方研究期刊》(RivistadegliStudiOrientali)上,诺森蒂尼公布了他的导师塞韦里尼逝世的消息,并回忆了塞韦里尼如何让学生爱上“难度高、刚跨入科学领域的科目”27Lodovico Nocentini, “Antelmo Severini (Necrologio)”(Antelmo Severini [An Obituary]),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II(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II) 3 (1909): 716.。诺森蒂尼指出,远东研究应被归类为科学研究领域,这是一个近年来终于变成现实的观点。事实上,塞韦里尼自担任远东语言和文学第一主席伊始,便早已成为科学“征服”这一新学科的最佳象征。他是欧洲促进汉学科学研究进步的先驱之一,也是意大利这方面研究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塞韦里尼认为,要使汉学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放弃先入为主的观念,并以权威的资料为依据,直接研究中国经典著作。这与将人文(历史、神学、哲学、心理学、法律等)转变为人文科学的实证主义计划是一致的,也是当时欧洲学术界的主流趋势。在对中国传统意义中“上帝”概念的分析中,塞韦里尼试图摆脱西方视野中有关“神”的观点,即圣经中上帝的特点,其中包括唯一的上帝、造物者、万能的、永恒的等概念。他认为,要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承认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尊重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然而,塞韦里尼是处于一个以学术辩论强烈政治化为特征的文化背景中的知识分子。为了支持自由主义和通俗主义思想的主张,有时会危及他对中国资料解释的准确性。
在《中国人的神》一文中,作者未明确提及当时意大利政治局势、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信仰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世俗或宗教教育等热门话题。然而,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他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在政治改革的年代,政治热情是整个意大利知识界的特征,也可以被认为是意大利早期学术汉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塞韦里尼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其他欧洲学术机构的汉学家也是如此。然而,塞韦里尼并不打算向政府提供有助于扩张殖民主义政策的历史和地理信息。在中国文学中,塞韦里尼寻求对公民进步有用的知识。如果中国文化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塞韦里尼避免不了将其理想化。在介绍论文主题时,他提醒读者道:“我将难以做到公正和真诚,难以避免将个人意见视为普世观念”28Antelmo Severini, “Il Dio dei Cinesi”(The Chinese God), 1091.。与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偏见相反,塞韦里尼并不认为中国宗教是不完美的宗教,也不认为它处于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婴儿阶段。《中国人的神》最后一句话总结了这个观点:“在一个民族的宗教中我们可以找到其智力的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