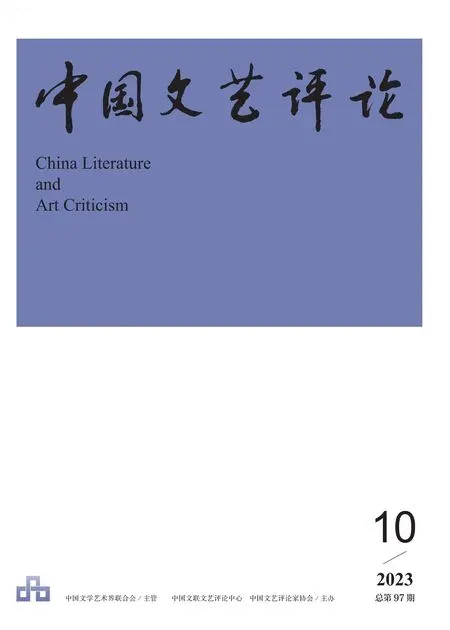网络亚文化失范与新媒体文艺评论网络暴力
■ 郑焕钊
网络暴力是通过言语攻击、形象恶搞、隐私披露等形式所产生的网络舆论的手段,对个人或群体的人身权利进行攻击侵害的网络失范行为。[1]关于“网络暴力”的概念界定,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界定方式。本文将“网络暴力”界定为:网络技术风险与网下社会风险经由网络行为主体的交互行动而发生交叠,继而可能致使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受损的一系列网络失范行为。从具体形态上看,它主要以言语攻击、形象恶搞、隐私披露等形式呈现。参见姜方炳:《“网络暴力”:概念、根源及其应对——基于风险社会的分析视角》,《浙江学刊》2011年第6期,第183页。作为网络话语的一种特殊类型,新媒体文艺评论[2]新媒体文艺评论是相对于报纸、杂志等媒介的传统文艺评论(包括专业评论和媒体评论)而言,主要指在互联网新媒体中所进行的各种文艺评论行为,是网民利用各种新媒介所提供的互动参与的方式,对文艺作品及其相关因素所进行的评价,是一种泛文艺评论。中同样存在着网络暴力的现象:网民在对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开展评论时,对文艺作品进行恶意抹黑、差评、抵制的话语暴力,甚至对文艺创作者、表演者的人格、名誉和隐私等进行造谣、攻击,从而产生人身侵害。
网络暴力的产生,是中国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的必然产物,是网络技术固有的风险特性和不断积聚的社会转型风险经由网民交互行为而发生共振、扩散的结果,涉及网络技术发展、社会急剧转型和网民群体结构三个风险源。[1]参见姜方炳:《“网络暴力”:概念、根源及其应对——基于风险社会的分析视角》,《浙江学刊》2011年第6期,第181—187页。具体到新媒体文艺评论中的网络暴力行为的产生,除了网络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风险,如不同群体由于“信息茧房”所带来的信息封闭和圈层区隔所导致的价值冲突问题的凸显,以及匿名发言所带来的言论暴力等原因之外,无良媒体和资本对媒介注意力的过度追求、对相关暴力议题的推波助澜正是不断激发网络暴力的外部原因。但如果从新媒体文艺评论的新形态、新现象及其与网络亚文化之间所存在的紧密关系来看,网络亚文化发展的失范是网络暴力产生的文化内因。
网络亚文化是以互联网为载体,特定社群通过年轻人所熟悉的技术呈现和表达方式,形成具有特定价值主张、文化理想和独特风格的亚文化类型。[2]网络亚文化不同于网络亚文化现象,而应在“青年群体”“观点或主张”和“新媒体”特征三个关键词上进行明确的提炼。参见马中红:《国内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现状及反思》,《青年探索》2011年第4期,第8页。可以说,网络亚文化天然所具有的媒介性与话语性的特征,正是其与新媒体文艺评论难解难分的关键。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便捷与交互极大地赋予了网民文化参与的权利,以及利用相关的文化产品进行再创造的能力。一方面,无论是“病毒式”传播的网络模因、同人创作现象,还是网络粉丝应援行为的勃兴,乃至各种恶搞文化的产生,都是技术赋权下网民文化生产力的体现,呈现出网络亚文化意义生产的多样形态。不满足于文艺文本所提供的单一意义,网民可以充分利用技术带来的便利,对各种文化文本进行“盗猎”与利用,以产生各种网民所需要的意义,既可以通过“鬼畜”视频、表情包、弹幕等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交语言,也可以通过同人社群与粉丝社群来表达社群意义、获得身份认同,并反过来影响商业文化及其意义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媒介的赋权促进了新媒体文艺评论与网络亚文化的深度联接,网民可以通过转发分享、弹幕参与、粉丝应援和模因传播等亚文化实践方式,参与到对文艺作品和现象的讨论中,带来了复杂多变的网络文艺舆情。黎杨全借鉴媒介环境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沃尔特·翁的“次生口语文化”概念,用于对网络文学的讨论,认为网络文学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书面文化的“次生口语文化”。[3]参见黎杨全:《走向活文学观:中国网络文学与次生口语文化》,《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0期,第148—161页。这一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文艺评论与新媒体文艺评论的区别:传统文艺评论更多是基于书面传统而产生的严肃话语,而新媒体文艺评论则是一种“次生口语文化”,是对文艺文本的盗猎、征用而进行的各种交流实践——其所拥有的社交分享、娱乐戏谑、身份认同与区隔的亚文化实践意义,要远远大于对文艺的解释评价意义。换言之,作为一种审美活动,新媒体文艺评论既呈现出“由相当纯粹的‘个体认识’转变为带有介入性(interventional) 色彩的‘社会实践’”,具有相当强烈的“行动取向”[1]参见常江、王雅韵:《审美茧房:数字时代的大众品位与社会区隔》,《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第102—108页。,从而成为网络亚文化实践的一部分;又因为其“消弭了文化公共性在审美实践中得以形成所必需的批判性距离”而“全面导致了大众品位的私人化”[2]同上。,进而对专业严肃的传统文艺评论产生消解。
然而,由于亚文化行为本身的边界存在着较大的模糊地带,网络亚文化不仅容易触碰到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更容易因为言语、行为的越界而对相关个人或群体带来人格、名誉和隐私的侵害,由此引发网络暴力的失范行为。
第一种是溢出正常文艺评论的恶意抹黑,以及对创制人员所进行的人身诽谤和攻击的暴力行为。对文艺作品叙事情节、人物角色及其价值观进行评价,是文艺评论的正常现象,但如果争论变成对某些创制人员及其作品的刻意抹黑和抵制,甚至逾越作品本身而扩展到对演艺人员本身的诽谤和攻击,则构成对演艺人员的网络暴力。如演员因饰演的角色跟原著不符、部分观众因不满演员饰演的“恋爱脑”人设及其价值观等,而对演员本人进行全方位的人身攻击,就属于这类人身侵害的暴力现象。诚然,剧情是否合理、人物塑造是否成功、演员的表演是否到位,都是值得讨论和争议的文艺评论话题。但在上述现象中,观众显然已经越出想象和情感的边界,超越剧情的范围,而将演员与剧情等同起来,将想象的不满直接转化为在现实中对演员的攻击,这是一种话语的越界与人身的侵犯。又如,近年来大量出现网络小说、动漫的原著粉因为对小说、动漫改编的影视剧选角的不满,而对演员展开各种造谣和抹黑,则属于粉丝权力的过度膨胀。每个人都可以对文艺形象进行想象和阐释,因影视演员选角与观众自身想象存在分歧而引发不满的现象,从文学改编以来就一直存在。但凭借新媒体技术的便利,通过粉丝集结而形成有影响力的话语,以此对演艺创制人员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则是典型的网络语境中的话语暴力行为。这同样是由于亚文化群体在文艺与现实之间的认知混同以及行为越界所致。
第二种是不同亚文化圈层由于价值冲突而产生的群体之间相互攻讦的网络暴力行为。随着互联网的逐渐发展,文化分层、分众的趋势日益加强,不同群体基于不同兴趣而产生各种各样的趣缘社区,形成审美价值迥然有别的各类亚文化社群。由于“信息茧房”的封闭与算法推荐技术的缺陷所带来的群体性认知偏狭倾向的加强,难免导致“审美茧房”与审美冲突的产生。在特定媒介事件的刺激下,原本各行其是的各亚文化社群,会因为价值、利益的冲突而产生割裂和对立。近年来,随着网络小说影视改编的日益普遍,小众文艺题材和亚文化因为影视改编而“破圈”的现象频频出现,使原本各行其是的不同趣缘社群产生交集。由于不同亚文化圈层在文化价值、审美追求和身份认同等方面存在差异,不同文化的媒介相交往往也容易因为对作品处理认知的差异,而产生价值的冲突和话语的纷争。比如,网络小说的原著粉与影视演员的粉丝之间可能因为对原著、影视作品的各自捍卫而攻击对方,产生激烈的话语暴力。又比如,小众亚文化的捍卫者不满某些演艺人员对其喜欢作品的通俗化演绎,而在演艺人员、节目粉丝和亚文化原粉丝之间形成冲突。在不良资本、媒介对粉丝群体的策动和诱导下,不同趣缘亚文化群体的冲突容易逾越事件本身而上升为极端情绪宣泄,甚至不惜披着维护正义的外衣进行党同伐异的相互攻讦。他们不仅以一种群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对涉事双方演艺创制人员的作品进行刻意差评、“踩踏”,甚至通过各类抵制的方式影响文艺作品的正常生产和播出,更加恶劣的是,通过向管理部门恶意举报,不惜以毁灭对方生存的方式进行打压,从而造成亚文化群体之间的相互伤害。这种现象既可以发生在不同粉丝群体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同一粉丝群体内部的不同人群之间(比如偶像团体粉丝与明星个人粉丝之间的冲突),呈现出互联网时代亚文化群体之间撕裂和对抗的失范特征。
第三种是由于流量经济的畸形发展所带来的粉丝控评及其话语“踩踏”现象。珍惜和爱护自身名誉,本是文艺工作者追求德艺双馨的一种表现,但在互联网时代,通过粉丝有组织地对评论进行控制——策划控评文案,有组织地进行点赞和跟风评论,使之占据评论区的前排位置,以“好评”与“热度”为自家偶像制造虚假繁荣的景象——以实现对演艺资源的争夺,可以说是互联网流量经济的畸形产物。事实上,粉丝为自家偶像的新作品进行应援,在自身新媒体账号下面进行宣传评论,本来属于正常的粉丝文化现象。但为了自家偶像的利益而一味追求好评,排斥其他不同声音的发出,到其他媒体和文艺评论公共空间“攻城略地”,对有异见者进行谩骂、侮辱和打击,甚至“人肉搜索”,则已经超出正常的粉丝应援和文艺评论的范围,而涉嫌网络暴力、触及法律底线。饶曙光就曾尖锐地指出:“控评本身变成了一个不断在违法边缘试探的危险行为,在评论中‘互相拉踩’、对他人进行谩骂侮辱,实质演变成一种网络暴力。”[1]饶曙光:《粉丝控评就是一种网络暴力》,《光明日报》 2021年9月3日,第11版。
最后一种最为隐秘、但也最为广泛的网络暴力行为是因网络模因传播的越界而带来的侵害。模因是能够被人迅速理解而传播开来的对象,可以是语言、文字、图像和视频等。网络文化中的模因传播已不是简单的对象复制,而被视为一种意义的再创造过程,体现出用户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互联网参与文化的一种最广泛的形式。网络流行语(梗、热词等)、表情包、“鬼畜”视频等都具有模因“病毒式”传播的特质,最典型地代表了如今网民的亚文化实践。比如锦鲤表情包成为一种网络锦鲤亚文化的具体实践,在网民面临考试等场合时发挥着心理慰藉的作用。但由于图像、视频等原初模因大多来自特定的文艺作品,因而这种“盗猎”“恶搞”不仅容易触碰相关作品的知识产权,也因为演艺图像、视频涉及演艺人员的肖像权和名誉权等,从而稍不注意就容易陷入网络暴力的泥淖之中。如广为流传的社会公众人物表情包,就因为传播过程中过度丑化形象而侵犯了其肖像权,引发他们的起诉。
互联网流量经济的畸形发展、亚洲偶像产业模式的负面影响,是新媒体文艺评论网络暴力产生的重要根源,也是导致网络亚文化行为失范的主要原因。与传统基于作品而产生的偶像文化不同,亚洲偶像的“养成系”模式更注重网络流量与偶像明星资源之间的捆绑关系;而流量经济的畸形发展,则透过“粉头”引导的粉丝暴力、无良媒体的推波助澜、不择手段的营销造势等,带来网络亚文化发展的失范,催生新媒体文艺评论的恶劣风气,带来不良后果。
首先,是对相关演艺人员肖像权、名誉权和其他人身权利的侵害,对相关亚文化群体言论空间及其生存空间的侵蚀和打压。无论是言语的诋毁攻击、肖像的丑化,还是“人肉搜索”所引发的暴力行为,从法律上看都是网络暴力对演艺创制人员所产生的侵权行为,触及了法律的底线。而各种亚文化粉丝群体之间因为话语和利益的争夺而产生的相互攻击,也将严重地干扰青年亚文化正常的发展生态,极端化地呈现了亚文化社群的负面特征,引发了相关公权力的介入,导致亚文化生存空间的严重压缩。实际上,那些处于舆论风口浪尖上、被粉丝维护的偶像,往往也因为自身粉丝的暴力行为所引发的舆论反弹而受到反噬和损害。
其次,新媒体文艺评论的网络暴力,将破坏文艺评论的正常环境,扭曲文艺评论的价值尺度。互联网文艺评分平台的出现,是新媒体时代文艺审美话语大众化的具体表征,有利于形成专家评价之外的大众评价和市场评价,是当代文艺评论话语生态构建的重要部分。但对影视文艺作品的评价,一旦被用于不同粉丝团体之间的相互攻讦或者粉丝控评对异见的排斥,那么大众文艺评论场域也就将失去其独立性和存在的价值,而沦为流量和利益争夺的斗争领域,这将极大地破坏新媒体文艺评论的生态环境。而因为对演艺人员的不满就对其参演作品甚至未上映作品的刻意抹黑、低星评价和粉丝控评,对不同评价意见的攻击和“人肉搜索”的暴力行为,则是对文艺评价的价值尺度和评论体系的扭曲与破坏。
最后,新媒体文艺评论的网络暴力,将导致文艺公信力的丧失,最终将影响到文艺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事实上,文艺是一个包含创作生产、传播营销和接受评价在内的整体生态,也是主流文艺与各种亚文化亚文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的生态。正如有研究指出,在新媒体传播语境下,主流文化、商业利益与青年亚文化之间的关系模式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形,它们之间不再泾渭分明,而是彼此互为对象、互为存在。[1]参见马中红:《国内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现状及反思》,《青年探索》2011年第4期,第5—11页。新媒体文艺评论以各种亚文化的方式分布于当代文艺传播和消费的各种具体语境中,以其网生话语的生动形态,借助社交媒介的强大影响,对当代文艺的创作引导和消费指引产生重要的舆情作用。而控评、抹黑、“人肉搜索”等新媒体文艺评论网络暴力行为,正借助文艺评论亚文化实践的影响力,极大地冲击文艺评论的公信力,进而冲击着文艺评论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调节”作用。正如有些影视平台可能忌惮于粉丝所控制的舆情,而改变其影视作品生产的专业考量,这将对文艺生产的正常生态带来冲击,甚至导致整体文艺生态的失序与混乱。
因此,我们要对新媒体文艺评论的网络暴力行为予以高度的警惕和关注。与一般网络暴力行为不同的是,新媒体文艺评论的网络暴力因为其亚文化的实践性而显得更为隐秘与复杂。正是这种行动取向的实践性,使其不同于传统文艺评论话语的作用方式,而参与到商业利益、社群认同与意义创造的过程中,从而与当代流量经济和娱乐工业产生了复杂的关联。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新媒体文艺评论与亚文化的深度关联,是网络数字文化时代的必然现象,是“次生口语文化”语境下审美话语新形态的具体表征;也要高度认识到,正是这种关联带来了大众性的文艺评论话语的活跃与丰富,它们是新技术、新媒介所带来的大众评价体系构建的基础;更要认识到,其潜藏的网络暴力实际上源自于网络亚文化在新技术、新经济语境中的失范与越界。因而,制约新媒体文艺评论的网络暴力失范行为,就需要回到网络亚文化与当代娱乐经济、工业的复杂结构中,探索作为亚文化实践的新媒体文艺评论的边界与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