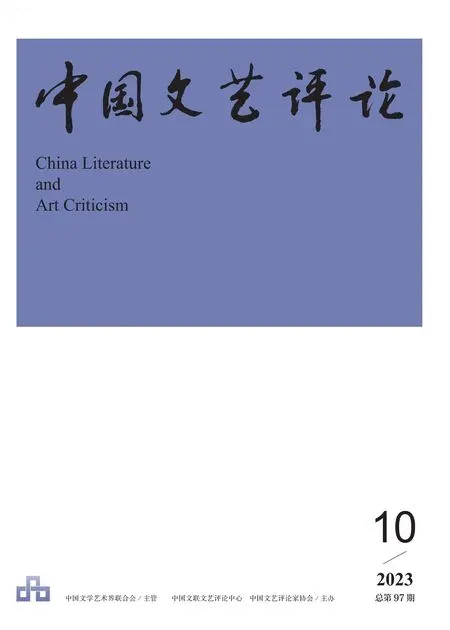从“巫舞”到ChatGPT:艺术科技融合发展的历史与当下
■ 孙晓霞
现代西方文明兴起的一个结果,即艺术与科技这两个极具想象力、创造力的职业在知识分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分裂为“理性王国”与“感性王国”,各自的专业化令对方望而却步,艺术与科技宛若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今日,处在新技术革命的历史节点,艺术与科技在实践领域愈益向对方敞开,融合态势日益凸显。不过,二者在学理层共通融合的相关研究却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对二者的历史分合关系更缺乏可靠的认识,“我们长期不愿以同样的历史视角去看待艺术与科学共有的那些做事方式”[1][美]乔治·库布勒:《时间的形状:造物史研究简论》,郭伟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3页。,这实在是令人可悲的事实。下文将从艺术与科技的历史统一性、有机性出发,解读艺术与科技重新链接、融合发展的内在动机,在认识论层面对二者在当代融合发展的形式及其必然性予以揭示。
一、个体书写:艺术与科技的有机一体
即使依技术、博物学和理性科学三者构成的科技谱系[1]参见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页。来体察历史也会发现,科学在艺术史中从未缺席,反之亦然。古代社会形态中的人文艺术与科学技术在知识层经常表现为混元合一的有机态,二者间不分轩轾,彼此呈现为弱边界的一体化,在一种同一化的知识结构中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以多种形式凝结于个体性的知识书写。
(一)缠绕于“技艺”
无论中西,概念史中的艺术都源出于“技艺”。西方的技艺(techne)、自由技艺(ars)与中国的“六艺”“艺术”等概念——既部分包含时下的现代艺术意指,也充分体现为人文艺术和科学技术多类知识的源头,中西两方之艺术在词源学的历史结构方面高度重合。中国先秦“六艺”主要是指礼、乐、射、御、书、数,汉魏时期的“术艺”则主要包括统一于“礼”的“阴阳卜祝之事”“诗书礼乐”“方术伎巧”等;[2]参见[北齐]魏收:《术艺列传》,《魏书》卷九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17页。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笼统的技艺(τέχνη)概念,既指技术和技艺,亦指工艺和艺术,还指向城邦治理等政治学、社会伦理等内容。造物技艺方面,作为技术之目的是生产有实用价值的器具;作为艺术之目的是生产供人欣赏的作品。[3]参见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21页。技艺囊括了全部的学问、知识、智慧等,构成艺术与科技两类知识的共同起源。
科学受限于观测,依据经验事实与逻辑的协调性;而艺术面对的是所有可想象的空间,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超脱逻辑和经验的,但是二者在早期知识的滥觞期汇通于技艺这一范畴,流布于巫术、神话、宗教、哲学等形式之中,发展出道与技、道与器、人工与天工、自然与技艺等多个范畴簇群,并通过巫舞、神话传说、文学、诗歌等媒介生成一种超验性知识得以传播。
中国哲学强调人工之技艺与作为自然之天道之间存在着一种形而上的依存关系。《庄子·养生篇》庖丁解牛以“道近乎技”,强调不以“官知”而以“神遇”,并突出“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从而举天理——道为技艺之本质,为科技与艺术两个现代知识前置了一个共同命题:道通于技。而据《说文解字》,“凡工之属”——法式、技巧及规矩等“皆从工”[4]《说文解字》(二),汤可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962—963页。。《尚书·皋陶谟》有言:“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宋应星以《天工开物》来命名自己的科技著作,强调人以天然之工巧而开物。同样,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对技艺理论进行的全面论说,阐明技艺这个统揽艺术与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等多学科范畴的神秘主义来源,即以人类自身拥有的知识技能与雅典娜等神灵所掌握的“自然”相对应,认可技艺对于真理的无限趋同。[1]参见孙晓霞:《柏拉图技艺理论的本质、内核、分类及艺术学启示》,《艺术百家》2020年第4期,第15—21页。技艺是人类被逐出“伊甸园”后构建自主世界的重要路径,由其所分化而来的艺术与科学则同样受限于人的感知力、可理解性和创造性等。
(二)发端于巫神
人类各大文明中巫术往往是多种职业及知识的发端[2]参见Leslie White,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o the Fall of Rome, New York: Mcgraw-Hill, 1959, p.1.,艺术与科技亦不例外。在中国,巫史祝宗凭借个体的聪明智慧,较常人更为敏锐地感知外部世界,更准确地把握自然规律,更合理地制定人文规范,因而成为最早的知识分子。而他们围绕祭祀所进行的各类活动,不仅孕育了社会伦理秩序等,也交织着科学、技术、艺术等各类现代知识因子。古代天文台称灵台,从巫,正是巫史掌握天文学的佐证;巫还在数学的加持下衍生出阴阳五行、老庄哲学等。巫史又兼艺术家,其行为涉及舞蹈、绘画、雕刻、诗歌、戏剧等。[3]参见何平立:《略论先秦巫史文化》,《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第70—76页。《说文》称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象人两袖(褎)舞形,与工通意”;《尚书·伊训》中有曰:“歌有恒舞于宫,酣舞于室,时谓巫风”,祭祀乐舞中的巫觋发展为宫廷乐舞祭祀的领导者与组织者[4]参见李希凡主编:《中华艺术通史简编·第一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2页。;“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郑玄《诗谱》),“舞法起于祀神”[5]刘师培:《舞法起于祀神考》,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5—109页。;“在绘画雕塑方面,具有宗教神秘意味的图腾、神鬼、纹饰、壁画、岩画、面具、偶象、随葬品等等,都是巫史的精心杰作”。[6]何平立:《略论先秦巫史文化》,《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第73页。作为一个群体,巫者的共性是以超凡的智慧被神明降临,巫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神明降之”(《国语·楚语下》),外显为预知、医治及社会秩序管理等各种技能。
神话学认为,神话是所有知识的起源,是早期人类通过推理和想象对自然现象作出的解释,它沉淀在宗教、科学、艺术、历史、文学等各学科中。将自然力视为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此乃几乎所有文明民族都会经历的一个特定阶段,“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72页。。神话中不仅有艺术性的恣肆的想象力,也有基于科学精神的经验性洞见。中国神话中开天辟地的伏羲、女娲、三皇五帝在后世不仅被解读为宗教人文形象,也是具有因应自然规律而推动科技发展的神秘技艺。《尚书·尧典》记载:“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允厘百工,庶绩咸熙”,而《淮南子·天文训》中则有太皞、少昊执规治春、执矩治秋等记载。
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带来了“技艺”,人得到了神传授的“技艺”;雅典娜将特殊的猜度能力赠予了制造器皿、器具和饰物的男人们,并指明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并不限于手艺人和工匠,而是所有精于制造、擅长业务、能够主管事务处理的人。[1]参见[德]M.海德格尔:《艺术的起源与思想的规定》,孙周兴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1期,第4—11页。“神”给人类传授的知识技能是不可见的,却又是指引形态、给予尺度的,从而让人类所生产的作品成为可见可闻的,故此是一种预先洞见的知识。这种预先洞见的知识所指向的作品不仅是艺术工艺之物,也可能是科学和哲学的作品、诗歌等。天才的“艺人”具神性、灵性与悟性,其行为既包括科学技艺,也包括人文艺术。
(三)同构于数理
基于追寻真理这一终极目的,数理原理与技艺乃至艺术规则形成一种同构关系。自然之数作为一种量化的秩序、比例和法度,不仅左右着科学思维的高度、文化心理的模式,也是世界多个文明的艺术依据和标尺,成为早期艺术的主要基底。
毕达哥拉斯相信数是万物的本原,美在于数学的比例与尺度、规则与纯粹。他发现音程与弦之间所构成的协和音程的比例关系,为音阶的音调关系找到数的规律。数是万物的本体,这一观念反应在视觉方面则以立体的几何图形作为事物的本体,数和几何图形是比具体事物更实在的东西,是组成具体事物的本原,即本体。[2]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修订本)》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45—449、231—250页。柏拉图将这一观念应用到美的形式问题中:“我说的美的形式不是大多数人所理解的美的动物或绘画,而是直线和圆以及用木匠的尺、规、矩来产生的平面形和立体形。……这些事物的本质永远是美的,它们所承载的美是它们特有的。”[3][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9页。这种既有形而上学美学又有数学的思想在中世纪基督世界中发展出了比例之美、光之美等理论[4]参见[意大利]翁贝托·艾柯:《中世纪之美》,刘慧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年,第51—81页。,在文艺复兴时期则发展为透视学,并被造型艺术家们奉为圭臬,在科学史的道路上衍生出异质性的艺术史。
与西方这种寻找数的结构、以数为本体的路径略有差异,中国古人主要用数来取法天道,并为天道立法,数彰显着自然天命与科学规律,数的关系与文化、精神及社会秩序联结在一起。如在《周易》中,人们“通过分析占卜所揭示的事物代形结构间的相似性,来确定真实不可见的结构之间的同源性”,使得自然之数潜入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践;在审美方面,“一方面重视物色及与外物的接触和感发,另一方面讲求形式的尺度和秩序,并以构建以自然为理想的审美境界为目的”。[5]李瑞卿:《自然之数与儒家价值秩序及其诗学意义》,《国际儒学(中英文)》2022年第1期,第92—95页。再如中国古代将音律与数学、度量衡乃至礼乐相关联。《汉书·律历志》记:“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权衡。参五以变,错综其数,稽之于古今,郊之于气物,和之于心耳,考之于经传,咸得其实,靡不协同。”[1][东汉]班固:《汉书·律历志》,颜师古注:《二十四史》(简体版),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33页。音乐与阴阳、节气、月历及数、度量衡乃至礼乐等勾连为一种同质性的知识网络。顺应自然之数同样也体现在诗学、画论之中,“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2][北宋]苏轼撰,郎晔选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下·卷第六十,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第997—998页。。以灯取影,以影成像,顺自然之法度,成自然之物象,然又在法度中取出新意。基于科学与数理的绘画路径内化于画家乘变应物、随物赋形的因应尺度之中[3]参见李瑞卿:《自然之数与儒家价值秩序及其诗学意义》,《国际儒学(中英文)》2022年第1期,第86—99页。,成为中国传统画论中不多见、但尤为珍贵的一场关于绘画与数理同道而行的理论表述。
(四)重合于文献
历史中的艺术与科技并不乏专业文献,但更多时候是以弱专业化的有机方式将艺术、文化、科学、技术等多重元素混合,科技内容与人文性浑然一体,重合于个体式的知识书写中。
博物学是典型的多面相知识。以《山海经》为例,“在《家语》成书时人们已承认《山海经》是一部地理书了”[4]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5页。;朱熹称此书与《天问》一样系摹写图画而写成;明代胡应麟视此书为古今语怪之祖,而鲁迅则认为中国神话古书最重要的就是《山海经》[5]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21页。;现代人更多倾向于它属于自然地理志与人文地理志的综合体[6]参见陈连山:《〈山海经〉“巫书说”批判——重申〈山海经〉为原始地理志》,《民间文化论坛》2010年第1期,第12—19页。;甚至建议将其中的图画、图赞展览出来,“既可让群众当作艺术品欣赏,也可学到些历史常识”[7]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236页。。而西晋张华的《博物志》“撮取载籍”,遍引经史子集各部之精要,被后人定义为以地理学为经纬铺叙的博物志怪小说[8]参见郑晓峰:《博物志》前言,[西晋]张华著,郑晓峰译注:《博物志》,郑晓峰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页。。同样,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一方面洋溢着浓郁的人文诗意,如形容大地是仁慈的、温和的、宽容的、可信任的慈悲女神;另一方面也在技艺的层面将阿基米德与建筑家、机械师、造船师、测量员、雕塑家、画家等一同视为艺术家(技艺家)。[9]参见[古罗马]普林尼:《自然史》,李铁匠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106页。
化学方面,古代炼金术作为一种复合型知识,包含着今天现代独立学科的许多主题,如化学、医学、神学、哲学、文学、艺术等,笼罩着各种神异的秘密传统,渗透在文化的各个角落,反射为诸种艺术形象及多个哲学性隐喻,如寓意化学嬗变的“衔尾蛇”(Ouroboros),寓意引发嬗变的“哲人石”(hō lithos tōn philosophōn),寓意制备哲人石需要的“太阳和月亮结合”[1]参见[美]劳伦斯·普林西比:《炼金术的秘密》,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6—34、111页。等,因而艺术家的著作中大量留存有对炼金术的观察、理解、想象、描绘等内容;相关隐喻在文艺作品中亦常见。
其他学科如地理、物候等文献也铺陈有浓郁的人文色彩。《诗经》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地方来组织结构的,而《左传》《季札观周乐》简扼阐明各国诗乐风格,《汉书·地理志》则增益了音乐史的地理学特征,如郑声淫,盖因其地势地貌中“土陿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2][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二十四史》(简体版),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18页。。文震亨的《长物志》以园林构造为旨,或借金鱼的花纹、眼睛和背部颜色来给金鱼分类,以对色彩的敏感性组织出一种兼具诗性趣味与生物分类的知识形态;或以人格化来区分石品的雅俗高下。[3]参见李瑞豪译注:《长物志》,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129页。这些人文性内容虽然并不出于实验或记录目的,但同样体现了一种科学思维。
技术类文本往往包纳有艺术、工艺的科技知识。《考工记》既清晰地显示了先秦时期与手工业息息相关的数学、力学、流体力学、声学等综合知识体系,也存录了具体的工艺技术规律,颇为重视天时、地气与材料等自然因素,是了解古代色彩学、音乐声学及工艺器物制造流程等的重要文献。沈括《梦溪笔谈》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地理、医药和乐律等多个领域,也兼及考古学、美术与音乐方面。《天工开物》弘扬天人合一的能工巧匠,究天人之际,合道器而一,涉及彰施(服装染色)、杀青(造纸)、丹青(朱墨)、陶埏(陶瓷)、乃服(纺织)等艺术生产制作方面的知识,同属艺术史研究内容。古罗马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呈现的则是技术基石上的艺术知识;12世纪初西奥菲勒斯神父(Theophilus Presbyter)的《不同技艺论》在彼时的定位中属于科学著作[4]参见[英]乔治·扎内奇:《西方中世纪艺术史》,陈平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53—154页。,但其中同样包纳有多种知识并体现了人文思想。这类文献叠合了艺术与技术,是艺术科技史的重要历史基础。
(五)统一于媒介
科技发展也很大程度地依赖于图像和声音等直观的媒介方式,以展示万物的规则和原理,艺术与科技的交集在很大程度上沉淀于图像这一媒介中,这在各类科学著作中俯拾皆是,天才科学家兼顾了知识的图文表达。
达·芬奇之外,艺术与医学之间最值得一提的是解剖学家安德烈亚斯·维萨留斯的《人体的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其插图精准再现了人类生理特征及其依据“自然法则”的运行方式,不仅成为医学史上的重要用图,也是杰出的艺术品,充分地将艺术性的人文关怀交织于医学解剖图谱中。化学方面,《哲学家的玫瑰花园》(Rosarium Philosophorum)的寓意插图,既强化炼金术的神秘玄奥,也同时成就了艺术图像的隐喻手法。艺术与植物学交会也呈现出类似的媒介特性,西方如1680年梅立安出版的《新花卉图鉴》(Neues Blumenbuch)就是一本“刺绣、铅笔画、钢笔画、油画和制版等装饰艺术的图样参考书”[1][英]海伦·拜纳姆、[英]威廉·拜纳姆编著:《植物手绘艺术:关于热爱、探险与发现的自然之旅》,潘莉莉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8页。。我国如《本草图经》(1069)、《履巉岩本草》(1220)、《本草纲目》(1590)、《三才图会》(1609)、《植物名实图考》(1848)等文献中的植物图像也是后人了解古代艺术表现手法的重要内容。插图的目的并不单一,除科学知识外,其中还兼备艺术想象与表达的多重功能。
技艺的缠绕、真理的汇通、文献的重合、媒介的同一,前现代的知识一体化特征高度地体现为个人的身份复合性。这些知识大量集中于中国传统文人士夫和西方博雅教育所塑就的人文学者群体,艺术与科学多源于同一个体的知识书写——天才论大盛其道。同时,凝结于一个个“天才”之书写,艺术与科技或以直觉的方式保持一致性,或在文献典籍中以隐喻的方式形成语言性联系,或以图像的方式建立起一种兼具艺术与科学特性的图文关联,构成了人文艺术与科学技术的有机知识结构体。
二、分道而行:艺术与科技的价值博弈
18世纪以降,西方步入劳动分工和知识分化的世代。伯纳德·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肯定了劳动分工的意义;受其影响,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强调“社会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和思维得到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2][英]亚当·斯密:《国富论》,胡长明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4页。。与生产分工同步,各专业知识皆追求自我体系化发展,日益走向独立,艺术与科学亦不例外。
(一)失衡与纠谬:为艺术的认识论价值辩护
19世纪,经典物理学分支日臻成熟,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心理学等取得长足发展,新的现代科学体系登场,科学成为了通向真理的唯一门径。知识科目化导致了人文和科学的加速分离,极端情形是形成了狂热的科学主义和卑微的人文主义。至20世纪,径直出现了对艺术认识论价值的全盘否定。哲学家杰罗姆·斯图尼兹发出哀叹,认为艺术对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并不产生什么影响,对知识领域也作不出什么贡献;艺术与科学和数学不同,艺术没有通达真理的方法和可确证的知识,它们各自离散互不相关,因此不构成信仰或知识的主体,故不能产生真理。“与科学相比,尤其是与历史、宗教及其他种知识相比,艺术真理这项‘运动’发展迟缓,毫无竞争力。”[1]Jerome Stolnitz,“ On the Cognitive Triviality of Art,”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vol.32 (July 1992),pp.191-200.艺术在科技面前不堪一击,孱弱非常,二者在认识论上严重失衡。
针对杰罗姆的悲观论调,约翰·吉普森指出,当谈论知识时,我们描述了与世界的某种智力关系,人文艺术有一种独特的能力,令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不仅仅是概念性的客体,而且是一个生动的世界。艺术可让人在理解自身的语言和概念如何将我们与世界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吸收那些枯燥乏味而脆弱的东西,并为其注入理解的基本活力,使人类的知识充实起来。[2]参见John Gibson, “Between Truth and Triviality,”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vol.43, no.3 (2003), pp.224-237.我们赞同这一判断,因为二者的关系史呈现的是一种与现代人看待和思考世界截然不同的方式,它们既为我们理解科学技术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也让我们发觉被整饬为仅为审美功能的艺术在古代所拥有的那些异乎丰满的触角。这种整合科技与艺术人文的、自然而然的、意义丰赡的世界观,在古代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在我们今天却是一种被遗忘的陌生能力。
伊瑞丝·范德玛也指出,现在认识论者不断强调证据在知识传播中的重要性,而艺术与文学一样,是一种证据,是证明世界、他人以及遥远时空中的事件或关系的知识来源。一方面,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虚假和想象的艺术,所有的艺术创作都以不同的形式暴露出其现实根系;另一方面,科学的世界观一直在变化。19世纪经典物理学式微后,科学中没有什么是完全完成和已发掘穷尽的了,没有确定的答案和最终结论,连原子都分裂成更小的粒子,科学的世界观一直在变化。我们不应该仅局限于追求真理和命题知识,我们还应努力追求其他认知价值。总有一些新事物可以融入我们的“世界图景”,总有一些我们还没有想到的事物会挑战我们自以为是的假设,而虚构性的艺术提出新的“假设”,提供不同立场和动机,这正是艺术的认知价值所在。[3]参见Iris Vidmar, “Against the Cognitive Triviality of Art,”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Aesthetics, vol. 2 (2010), pp.516-531.
(二)精神的护卫者:艺术对科技的“反动”
同样是在科学横扫天下的19世纪,古典的、以模仿自然为原则的精神世界构建方式被彻底改写,工艺革命与科技进步让人类的身体前所未有地得到解放,艺术以浪漫主义回应启蒙运动之理性主义症候,现代艺术给传统感受带来新的冲击,专注于自我表露的艺术将自我探索的行为“从反常的边缘地带转移到现代文化产业的中心位置”[4][美]彼得·盖伊:《浪漫派为什么重要》,王燕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3年,第3页。,至20世纪,试验艺术、先锋艺术等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颠覆性介入科技。
最初的印象派绘画因不忠实于自然而遭诟病,对科学充满敬仰之情的画家如修拉和保罗·西涅克都对印象派大加反对,并希望通过对光学规律和色彩知觉的观察,使艺术赶上科学的步伐。但是,在这些极富挑战性的作品中,人们却提取出科学与印象派的另一种关系。1875年印象派画家引入一种用色方法,以如彩虹一般纯粹而明亮的效果展示一定幅度的光谱色,夏皮罗据此认为印象派系统运用对比色(simultaneous contrast)、对分色(divided color)、有色小笔触建构画面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延续了14世纪以来画家所投身的以实验、探索精神来解决再现问题的做法,他们“发明了复杂方法以更为充分地再现他们所画主题的那些可见的方面”[1][美]迈耶·夏皮罗:《印象派:反思与感知》,沈语冰、诸葛沂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3年,第210—266页。。科学未能完全地强制艺术,画家倚仗艺术史中的实验和发明传统改变自身的历史。
同样,面对极端工具理性主义,艺术显现出强大的反思批判能力。如19世纪中叶,摄影术曾在生物学和早期民族志的考察中大量用于“科学”记录、归档,将人类个体类比为动物并进行存档的记录方式盛行于人类学与生物学界。瑞士生物学家路易斯·阿加西在巴西拍摄大量的“标本”性意义的当地居民图像,为其“多源人种论”寻求证据;生物学家赫胥黎要拍摄“大英帝国疆界内各种族系统图”[2]参见邓立峰:《揭示混杂“记忆”:后殖民语境下当代艺术家的种族影像再生产》,《艺术学研究》2022年第6期,第86—95页。等。对人类进行动物物种意义上的标本式信息采集和记录,这种殖民影像既是海德格尔意义上技术对人的促逼[3]参见[德]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海德格尔文集·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7页。,也是技术对人性的反噬。21世纪以来,此类殖民影像在当代艺术中成为种族影像再生产的重要素材,实验艺术家们利用殖民影像及其内在元素颠覆和批判种族主义,曝光极端科学主义反人性的暗黑一面。
艺术对科学的“反动”不胜枚举,而围绕人文主义精神这一核心,现代思想者对于艺术于科学的强大历史反思及其自身的精神护卫功能有了高度认同,艺术“以比任何其他人类实践都更深刻的方式锻炼我们的认知能力,即我们自己的反思部分”[4]Iris Vidmar,“ Against the Cognitive Triviality of Art,”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Aesthetics,vol. 2 (2010), pp.516-531.,内容统一和价值互补则成为艺术与科技在当代走向融合发展的认识论基石。
(三)对观与互补:艺术与科技的握手
20世纪科技史研究的人文化、科技实践及理论向人文领域的不断延伸和开放促生了全新的知识样态。乔治·萨顿的《科学史导论》中对科学史研究方法、理念、规范要求及评价标准等的设定就超越了科学主义立场,将神学视为科学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将科技史的研究投放在人文学科领域;罗伯特·金·默顿在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把科学知识视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历史结果[5]参见[美]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托马斯·库恩则从科学史的视角进入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的本质,将视野放大到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宗教史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1]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提出了范式理论以及不可通约性、学术共同体等;伯纳德·巴伯认为理性的、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系统也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和方式,科学同样是社会性的历史概念[2]参见[美]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2—5页。;彼得·哈里森则指明,“在公元后的1500年时间里,对自然物的研究几乎都是在人文学科中进行的”[3][澳]彼得·哈里森:《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导言”,第14页。。小说家兼分子物理学家C.P.斯诺在1957年、1963年先后宣称,西方知识界分裂成科学与艺术,且两种文化并不去理解对方的方法论和目的,而人文知识分子侥幸成功地排除了异己,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鸿沟的伤害性,希望在二者间架起桥梁,打造一种所谓“第三种文化”的融洽关系。[4]参见[美]约翰·布罗克曼:《第三种文化——洞察世界的新途径》,吕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2页。此外,亦有大量学者探讨艺术对科技的启示和催化意义,化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坦承艺术是“科学的预兆”[5]转引自[德]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1页。;特洛尔奇笃信“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个性在艺术上的解放,是科学的预备阶段”[6][德]特洛尔奇:《基督教理论与现代》,刘小枫编,朱雁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53页。;梅森认为“近现代科学的产生缘于学者传统与工匠传统的结合”[7][英]斯蒂芬· F ·梅森:《自然科学史》,周煦良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导言”,第1页。。1968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创办《莱昂纳多》(Leonardo)杂志,集中关注当代科技在艺术和音乐中的应用,以及艺术和人文科学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影响。科技在历史中的社会性、人文性被认可,不仅带来了科技界的思想震荡与理论转型,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科学观念和思维范式,也使得科技知识在历史和学理层面大幅度地向人文和艺术开放。
艺术与科学之关系很早就成为中国科学界的重要论题。早在1980年代,钱学森就发文呼吁“我们应该自觉地去研究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的规律”[8]钱学森:《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顾吉环、李明、涂元季编:《钱学森文集》卷6,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121页。。嗣后在李政道的主持下,学界就此展开讨论,特别强调了艺术具有理性认识世界的可能和科学中想象与灵感之不可或缺性。杨振宁用“性灵”理论来诠释现代物理学家狄拉克创造性的理论风格,用诗歌,用哥特式建筑中崇高的、庄严的、灵魂性的宗教的终极美,来描绘物理学方程带给人的美的感受。[9]参见杨振宁:《美与物理学》,李砚祖主编:《艺术与科学》(卷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页。此外,我国还设立了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创办了《科学文艺》《艺术科技》等杂志。
进入21世纪,国内关于艺术(特别是美术)、科学、技术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的认知有了实质性突进。在科技哲学领域,吴国盛强调科技的人文性,认为科学的思想根基在于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1]参见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页。以艺术为主体的相关研究也日益兴起。2005年《艺术与科学》创刊,并广泛涉猎艺术、美学与科学、技术多个角度,涵盖了艺术与科技知识的大部分矩阵。其间,李泽厚以形式感为纽带,为艺术与科学“联姻”并指出,形式感就是秩序、单纯、对称、均衡、比例、节奏,这些形式源于人们的操作实践,并且人也是依靠这种形式上的规律维持着自身的生存活动。美感和形式感都具有极大的科学性,可以引导到事物的本性。[2]参见李泽厚等:《李泽厚访谈:艺术与科学》,李砚祖主编:《艺术与科学》(卷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21页。艺术的科学性一面亦逐渐被认可,艺术与科学在理论层面打开了全新的对话空间。
三、团队协作:艺术与科技的重新融合
置身知识爆炸的现场,某一微小的专业知识相对个人也可能是无限的。现如今人们已很难奢望如传统社会那样,依凭个体无意识的、单兵掘进式的知识书写来承载艺术与科技,不同专业间的跨学科合作成为主流。这种合作有学术的、实验的,也有艺术内部生发的创作,团队间的协同合作成为艺术与科技融合发展的现代形态。
21世纪,以激发创新力为旨,科技和艺术在实践中双向奔赴,各大机构及高校纷纷设立艺术科技专业。如2017年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和达尼埃尔&尼娜·卡拉索基金会设立了艺术—科学讲席。各大科技研究机构和项目也将艺术嵌入自体,设立科技艺术实验室,如“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 (Ars Electronica Festival)、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跨界混搭,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旗下的艺术项目Arts@CERN,荷兰的测量公社(Waag),法国的“利希”研创中心(L' 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 INNOVATION[IRI]),日 本 真 锅 大 度的Rhizomatiks公 司,豪 瑟 沃 斯「艺 研 室」(Hauser & Wirth Art Lab)等[3]参见凡琳:《艺术领域都有哪些尖端的“黑科技”?》,2021年3月11日,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772929.html。,皆致力于将艺术的多元创造力与科技动人心魄的革新力量相结合。艺术科技的融合甚至被上升到区域未来发展格局的高度被予以重视,如欧盟委员会自主计划“地平线2020”(Horizon 2020)研究和创新计划下启动的STARTS(Science Technology Arts)项目,期望通过整体性的、以人为本的研究方法整合艺术与科技,支持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之间的协同合作[1]参见https://starts.eu/。,从而激发出极高的创新性潜力,来应对欧洲未来可能会面临的社会、生态及经济的挑战。
将目光收回国内,艺术领域的工艺设计史论研究、艺术考古学的科技应用、艺术地理学的兴起[2]参见颜红菲:《当代艺术地理学文献研究》,《艺术理论与艺术史学刊》2021年第1期,第10—24页;张慨:《艺术地理学的振兴及重构》,《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117—128页;等等。等都在昭示一种与科技交叉的艺术研究发展趋势。中国美术学院创新设计学院以“艺术、科技、商业”高度融合的创新设计学科为主体,开设艺术与科技、工业设计和数字媒体艺术三大专业;2019年四川美院组建实验艺术学院突出强调艺术和科技、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融合;202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科技艺术研究院[3]参见苏新平:《关于成立中央美术学院科技艺术研究院的思考》,《美术研究》2020年第6期,第26—29页。,并形成“科技艺术”(Science Technology Arts)概念以打造系统的科技艺术生态圈[4]参见邱志杰:《科技艺术的概念》,《美术研究》2020年第6期,第30—44页。;2021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成立;等等。艺术与科技在教育及创作领域的对话合作狂飙突进,蔚为大观,新的理论激活与跟进势在必行。
走进21世纪20年代,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纠葛更为复杂而耀目。“元宇宙”哲学奇点的到临,ChatGPT的问世,不明朗的伦理与社会后果挑动着科学技术的脆弱神经,人类纪文明边际被颠覆前夜,艺术被视为全人类文明抵御人工智能风险的最后防线。如果说科学发现是人类破解宇宙奥秘的钥匙,技艺是人类利用宇宙规律改造和创建自我物质世界的工具,那么艺术就是人类在精神层面构建自我诗意世界的最高级形式;科学是人发现“神”之未知世界的通道,技术是人建构“人”之现实世界的手段,艺术是人打造“人”之精神世界的神异法物——人用自己的感官感知、认识、改造乃至重建一个世界,抵达人之本质意义上的精神栖居所,即所谓“元宇宙”。艺术与科技的协作发展真正启动了人类的“元宇宙”征途。
艺术与科技间的团队协作、融合发展在中国艺术创作中已展露出其强劲之力。一方面,以电影《流浪地球》、小说《三体》为代表的中国科幻文艺作品,在力求精准再现或阐释科技原理的基础上,以高度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精心设计叙事逻辑与结构,以隐喻的、诗意的手法来表达对人类未来之忧思,展现出宏阔的宇宙想象、深邃的哲理思考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艺术凭借与科技团队的合作不断实现自我更新与蜕变,如最新上映的国产电影《长安三万里》《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中所呈现出的科技与艺术的高度契合,在强大的科技团队助力下,艺术作品以史诗般的视角细腻深刻地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辽远而恢弘的当代气象。艺术既为冰冷的科技带来激情和灵感,也从技术的迭代中擢升自我。
承载人类经验感悟的艺术洞察力与探索宇宙奥秘的科技想象力无界合体于“创造”,此乃知识在变迁动荡中不断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只不过,今日的艺术科技更仰仗于专业团队间相契无间的协作。
结语
在历史的长时段中,艺术与科技高度交集、深度融合,它们凝聚在天才个体的知识书写中,在话语起源、基本原理、文献载体、叙事表达等方面呈现出高度一体化的特征。即便在近现代分化、失衡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博弈中,艺术与科技也不断从各自领域为对方提供灵感与动能,推动彼此的更新与迭代。时至今日,艺术与科技间的链接、对话、协作、融合的浪潮已至,曾经的观念坚冰正在消融,理论交流、实践互动及组织机制合作日新月异,艺术与科技正以团队协作的方式相向而行,拥抱彼此。我们要看到,艺术科技的再融合带来文明形式的重组与更新,以此为契机接续中华传统文化基因,重启中国艺术精神之强力,我们正处在最好的时间节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