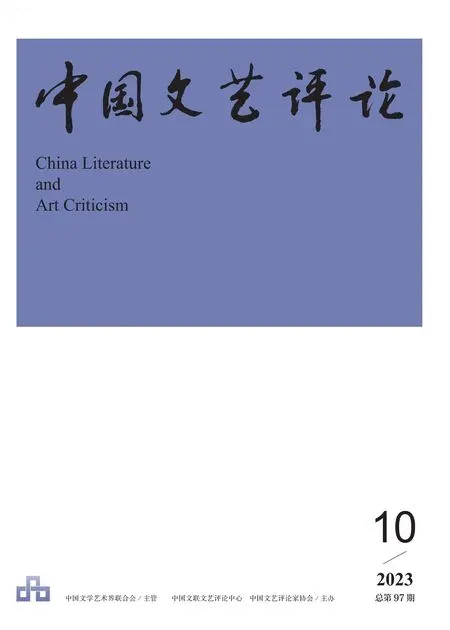“游于艺”:诠释历史与意义世界
■ 刘强强
近年来,从命题角度研究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艺理论渐成一种引人瞩目的新模式。[1]早在2010年,汤一介即发表《“命题”的意义——浅说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的某些“命题”》一文(《文艺争鸣》2010年第2期)。近年来,张晶在不同场合提及命题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断有研究成果发表。吴建民曾发表多篇有关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命题的专题文章,并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命题研究》一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命题研究之所以具有新意,关键在于其提供了不同于以往常见的范畴研究的视角,而这又根植于命题与范畴之间的基本差异。在《工具论》中,亚里士多德将由范畴结合而成的判断视为命题。[2]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上册,余纪元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6页。与前者相比,后者的构成更为复杂。一种新命题的产生,说明了至少两种不同的范畴被关联起来,而这种关联往往意味着一种新观念或新思想的破土而出。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所用、所思的命题指号就是思想。”“命题能传达给我们一种新的意义,这是命题的本质。”[3][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陈启伟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3、206页。孔子所提出的“游于艺”正是命题的一种。在孔子之前,“游”和“艺”两种范畴均已存在,是孔子首次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即《论语·述而》所载:“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礼记·学记》中虽然有“士依于德,游于艺;工依于法,游于说”的说法,但《学记》晚出,因而其说当为对孔子思想的延续。[1]关于《学记》的成篇年代,学界有战国、汉代的分歧,但无论如何均认为其晚于孔子。参见王锷:《〈礼记〉成书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3—65页。由于孔子的圣人化和《论语》的经典化,“游于艺”在历史上获得了不同思想流派的关注,形成了差异化的诠释模式。且随着“游”的意涵变迁和“艺”向书法、绘画等艺术的扩容,“游于艺”逸出了儒家经学之外,构成了古人对待艺术的基本态度,对中国古代艺术思想产生了深刻且广泛的影响。而在目前的研究中,对于“游于艺”这一命题的专门探讨依然是阙如的。本文首先从儒学史的角度出发,追溯“游于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内涵,其次考察该命题在书法、绘画领域的蔓延及影响,通过对“游于艺”诠释历史和意义世界的揭示,彰显中国艺术的修身传统与人文精神。
一、从玄学到理学:诠释模式的转换
“游于艺”由“游”和“艺”两种范畴所构成。《说文解字》释“游”字:“旌旗之流也。从㫃,汓声。”段玉裁注曰:“引伸为出游,嬉游。”[2]在先秦文献中,“游”与“遊”异体而同在,且前者之频率远高于后者,故《说文解字》仅收前者。《玉篇》曰:“游与遊同。”《广韵》道:“遊同游。”可见二者在语义上其实并无区别。也正因此,虽然不同的《论语》版本存在着“遊”与“游”的差异,但对于文意并无影响。可见“游”有自由、游戏之意。“艺”的古字为“埶”,其原始语义为种植,后被用来泛指普遍的技艺。对于孔子所说的“游于艺”之“艺”,后世均作“六艺”解。“六艺”为周代国家教育的重要内容。《周礼》载:“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大司徒》)“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礼·保氏》)通过孔子的生平来看,其对于“六艺”无疑是熟悉的。如《孟子·万章下》所载:“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3][汉]司马迁:《史记》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709—1710页。由此可见,孔子颇为擅长礼、术、书等与“六艺”相关的技艺,并曾经以此谋生。然而对于这些技艺,孔子的评价在整体上并不高。如其所说:“吾少贱,故多能鄙事。”“吾不试,故艺。”(《论语·子罕》)且在孔子的实际教学中,已经发生了由礼、乐、射、御、书、数所组成的“旧六艺”向礼、乐、诗、书、易、春秋所构成的“新六艺”的转型。技艺性的射、御、书、数不再占据教育内容的核心部分,对《诗》《书》《易》《春秋》等经典的研读被增设为重点。如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史记·孔子世家》曾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1][汉]司马迁:《史记》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734页。然而,将“游于艺”之“艺”视为“旧六艺”,在古典时期已成定势,由此也就使文本呈现出复杂、矛盾的状况。此种状况既造成了解释的困难,同时也意味着诠释空间的预留和敞开,呼唤着后世解经者的创造性工作。
汉代解《论语》者虽多有其人,但其著作均未传世,仅有部分文字保留在何晏编著的《论语集解》中,且其中关于“游于艺”的部分又是缺失的。因此,现今可见最早的对于“游于艺”的专门诠释当为何晏自己的发挥。何晏之学祖述老庄、以无为本,对于《论语》的诠释有着鲜明的玄学色彩。且由于《论语集解》在历史上的广泛传播与长远流传,所以何注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北宋初年。何注云:“志,慕也。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据,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据。依,倚也。仁者功施于人,故可依。艺,六艺也。不足据依,故曰游。”[2][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5页。所谓的“道不可体”,即将“道”视为无法感知与把捉的玄虚之物。相比之下,“德”为具体而有形的道德法则,故而是可“据”的。“仁”为仁者所施之功,故而是可“依”的。“艺”虽然同“德”和“仁”一样具体,却“不足据依”,只堪于“游”。在何晏的观念中,“艺”的重要性不仅无法与前三者相比,且与之呈现出深刻的割裂关系。该倾向亦为此后疏解何注的皇侃、邢昺所继承。皇侃虽说“此章明人生处世,须道艺自辅”,但又认为“仁”劣于“德”、“艺”轻于“仁”,“艺”终究是“不足依据”者。[3]参见[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56—157页。北宋初年的邢昺更是援引王弼的“道者,无之称也”之论,直接将“道”解释为“虚通无拥,自然之谓也”,其中的玄学倾向相比何晏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对于“艺”,邢昺更是等闲视之,将其称为“所以饰身耳”“劣于道、德与仁”。[4]参见[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5页。由此可见,自何晏以至邢昺,关于“游于艺”一章的解释均具有浓郁的玄学气息,正如清代的陈澧所评论: “何注始有元虚之言……自是以后,元谈竞起。”[5][清]陈澧:《东塾读书记》,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19 页。在此种论虚谈玄、崇本息末的语境中,作为现实技艺的“艺”自然是无法获得重视的。这一状况待到宋明理学的产生才得以扭转。
在二程、张载等北宋理学家那里,关于“游于艺”的解释虽然简略,但均对该命题在儒者修身成德过程中的重要性予以认可,从而显现出与上述玄学诠释模式的不同。程颐的《论语解》开创了以理学思想解释《论语》的先河,其中解释“游于艺”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学者当如是,游泳于其中。”[6][宋]程颢、程颐:《论语解》,《二程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44页。从该句所表达的意图来看,“游于艺”已经获得了基于修身维度的肯定与重视。此外,《河南程氏遗书》录二程之语:“子曰:‘志于道。’凡物皆有理,精微要妙无穷,当志之耳。德者得也,在己者可以据。‘依于仁’者,凡所行必依着于仁,兼内外而言之也。”[1][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7页。该语虽未论及“游于艺”,但其中关于“道”“德”“仁”的解释却为后来的朱熹所继承和发扬,间接地影响了其对于“游于艺”的理解。作为宋明理学的先驱和关学一脉的代表人物,张载对于“游于艺”曾有专门的解释。其说道:“艺者,日为之分义,涉而不有,过而不存,故曰游。”[2][宋]张载:《正蒙》,《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45页。“分义”有恰如其分、得其所宜之意。《荀子·强国》在解释礼乐时曾道:“礼乐则修,分义则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3][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86页。张载所说之“分义”当源于此。后面的“涉而不有,过而不存”则表示出“游”之活动的自由宽裕,无凝滞、无阻塞。同时张载又道:“志于道,道者无穷,志之而已。据于德,据,守也,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依于仁者,居仁也。游于艺,藏修息游。”[4][宋]张载:《张子语录》,《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23页。“藏修息游”之语源出于《礼记·学记》。《学记》曰:“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5][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58页。其中的“兴”为喜欢之意,而“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则是对学习过程的循序渐进、起伏有致等特征的描述。上文已提到,《学记》曾化用孔子的“游于艺”之语,所以其中的相关言论亦被后世儒者拿来解释孔子思想。在此之外,张载还曾说“依仁则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6][宋]张载:《正蒙》,《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9页。,此种在“仁”与“游”之间建立联系的做法虽未直接涉及“艺”,却给后来的朱熹以潜在而深入的影响。
除二程、张载之外,北宋的理学家如范祖禹、谢良佐、游酢、杨时、尹焞等,亦对“游于艺”的修身意义作出过诠释,这些诠释均保留在朱熹所编的《论孟精义》中,如范祖禹言:“艺者可以广业也,故游之。”[7][宋]朱熹:《论孟精义》,朱傑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 修订本》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9页。然而,北宋理学家对于“游于艺”的解释多是只言片语,未成体系。对于这些解释,朱熹在《四书或问》中曾先后两次说到“程子、张子至矣”[8][宋]朱熹:《四书或问》,朱傑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 修订本》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20、661页。,可见其对程、张思想的服膺。正是在二程、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朱熹对“游于艺”一章进行了系统性的解释,进而促进了理学解释模式的正式成立。
二、经典诠释模式的确立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道:“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朱傑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 修订本》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21—122页。朱熹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卓著,《四书章句集注》在元、明、清三代又被悬为令甲,故而上述段落可谓历史上关于“游于艺”最为著名的解释。有别于何晏等人对于“艺”的轻慢,朱熹将“艺”视为“至理所寓”的“日用之不可阙者”,且从“志道”到“游艺”呈现出一种有机联系、不断递进的工夫论链条。这些观点与过去的诠释相比无疑是颠覆性的。由于此前士子所使用的《论语》均是何晏注本,所以朱熹的诠释颇为时人所不解,《朱子语类》和《四书或问》中便收有多条弟子献疑的记录。而通过朱熹的回答,我们可以更为具体地探知其关于“游于艺”的理解。
首先,不同于何晏“道不可体”的观念,朱熹将“道”解释为“日用当然之理”。其在《朱子语类》中更为具体地解释道:“事亲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与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2][宋]朱熹:《朱子语类》,朱傑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 修订本》第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213页。因此,朱熹所谓的“道”即道德之意。“道”贯穿于日用常行中,不仅是可“体”的,同时也是必“体”的,用朱熹的话说便是“至诚恳恻,念念不忘”。而既然“道”为道德,那么其与“德”和“仁”的区别何在呢?朱熹对此解释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如臣之忠,子之孝,只是统举理而言。德者,己之所独得,如能忠,能孝,则是就做处言也。依仁,则又所行处每事不违于仁。”[3][宋]朱熹:《朱子语类》,朱傑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 修订本》第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214页。又曰:“‘志于道’,犹是两件物事。‘据于德’,谓忠于君则得此忠,孝于亲则得此孝,是我之得于己者也,故可据。依仁,则是平日存主处,无一念不在这里,又是据于德底骨子。”[4]同上,第1215页。依此见解,“道”与“德”分别为群体所共有与个体所实现之道德。由“道”而“德”,呈现出从抽象原则向具体德性的演进。相比之下,“仁”的含义较难理解。朱熹将其称为“每事不违”“无一念不在这里”,故我们可推知“仁”当为具体生活情境中道德意识的显现与道德行为的生成。“仁”具有着随事而发、随心而动的时间性特点,意味着德性在全体此心的充满与流布。而也正是由于“仁”的这些特点,使得“艺”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朱熹道:“虽然,艺亦不可不去理会。如礼、乐、射、御、书、数,一件事理会不得,此心便觉滞碍。惟是一一去理会,这道理脉络方始一一流通,无那个滞碍。因此又却养得这个道理。以此知大则道无不包,小则道无不入。小大精粗,皆无渗漏,皆是做工夫处。”[1][宋]朱熹:《朱子语类》,朱傑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 修订本》第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216页。在此段论述中,朱熹首先说“六艺”的理会与贯通,随后将其扩展至一切细微的事物与道理,从而将“游于艺”视为义精仁熟之状态的象征。当然,“游于艺”如果仅仅作为虚拟的象征而存在,那么其与其他三者相并列的理由依然是不充分的。实际上,朱熹还将其视作具体的儒家工夫。如其所说:“是其名物度数,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无者。游心于此,则可以尽乎物理,周于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间,非僻之心,亦无自而入之也。”[2][宋]朱熹:《四书或问》,朱傑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 修订本》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41页。“六艺”包括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其不仅仅是儒家的教学内容,同时也涉及到日用常行的许多方面,故朱熹称其“日用而不可无”。通过自由、从容且伴随着愉悦的情感体验的“游”,儒者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悠游自在、与物无对的身心状态,进而体验到“仁”的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故而朱熹说:“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朱傑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 修订本》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21页。“工夫到这里,又不遗小物,而必‘游于艺’。”[4][宋]朱熹:《四书或问》,朱傑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 修订本》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78页。此处的“小物”既专指“六艺”,同时又扩展至现实生活中种种细微而琐碎的事物,其所达到的最终境界即“无一物之非仁”,不自觉地“入于圣贤之域”。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总结朱熹勾连“道”“德”“仁”“艺”的逻辑理路。“道”为道德的总体与抽象形式,“德”为道德的具体与在身状态,“仁”意味着在身之德的融会贯通。“艺”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特点使其与“仁”具有着共通性,故而可促进“仁”之实现。此即朱熹所说的:“至‘依于仁’既熟后,所谓小学者,至此方得他用”[5][宋]朱熹:《四书或问》,朱傑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 修订本》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80页。。在其中我们既可以发现二程的影响,同时也可以见出张载的影子。朱熹不愧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关于“游于艺”的解释汇聚了二程、张载思想的精华,并建立起完整、圆融的逻辑体系。在此体系中,本为末节小物的“六艺”成为了“至理所寓”者;与之相应,“游”亦不再是何晏等人所说的“不可据依”,而是成为了“玩物适情”“从容潜玩”,具有了相当于“据”与“依”的地位。此后理学家关于“游于艺”的解释,概不出于朱子之外。如王阳明曰:“艺者,义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皆所以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也。”[6][明]王守仁:《传习录》,《王阳明全集》上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94页。再如刘宗周曰:“德之体即仁,非二物也,然非偏内而遗外者也。志道之后,其所得力于六艺之途者深乎?故终以游艺合焉。”[7][宋]刘宗周:《论语学案》,吴光主编:《刘宗周文集》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41页。随着清代考据学的大兴,关于“游于艺”的诠释曾呈现出注重训诂、消解义理的倾向。[1]如黄式三:“学者高言志道、据德、依仁,而不亟亟于礼,其能不违道贼德而大远乎仁也邪?”黄怀信主撰:《论语汇校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74页。然而此种倾向多缘于一时之学术风尚,在《四书章句集注》被悬为令甲的情况下,朱熹关于“游于艺”的注解依然是天下士子耳熟能详的“普遍性知识”。
三、话语的迁移:艺术语境中的“游于艺”
通过对“游于艺”诠释史的考察我们可以见出,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理论体系中,“游于艺”所承载的思想内容有着深刻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背后又关联着广阔的意义世界。在玄学解释模式中,“游于艺”尚未被纳入修身的系统中来,“艺”处于被忽视的位置。而在理学解释模式中,“游于艺”不仅被诠释为完善道德境界的象征,同时也是修身成德的最终途径。但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艺”只有在与“道”“德”“仁”相联系时才具有以上地位,如朱熹所说:“‘游于艺’,盖上三句是个主脑,艺却是零碎底物事。”[2][宋]朱熹:《朱子语类》,朱傑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 修订本》第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219页。在卫道者的思想世界里,“游于艺”始终是无法获得独立的领地与价值的。且由于理学家所提倡的道德境界取法乎上、微妙难言,故而“游于艺”的设想难以落到现实中,其更多地是作为一种道德理想而存在的。也正因如此,朱熹在具体实践中对于“游于艺”持相当的保留态度,动辄以仁义道德约束之。而当“游于艺”处于艺术的语境中时,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诠释机制与意义世界。
在孔子之后的思想史中,《庄子》一书对“游”之范畴的阐发最为丰富与深刻。如:“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逍遥游》)“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人间世》)其中的“游”内含着堕肢体、黜聪明、与天地万物为一的自由精神。“艺”在先秦时期已被用于指称普遍的技艺性活动,在此后的历史演进中,书法、绘画、琴艺等均进入“艺”的范畴之内。“游”和“艺”的话语联结既已由孔子所确定并被广泛接受,那么二者各自内涵的演化便促使“游于艺”处于不断的变迁中。正如伽达默尔所说:“通过文字固定下来的东西已经同它的起源和原作者的关联相脱离,并向新的关系积极地开放。”[3][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56页。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道:“艺者,道之形也。学者兼通六艺,尚矣。次则文章名类,各举一端,莫不为艺,即莫不当根极于道。”[4][清]刘熙载:《艺概》,薛正兴点校:《刘熙载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3页。其所说的“艺”除经义外,还包括着诗、文、赋、词曲和书法。随着“艺”之内容的变化,“游于艺”的对象不再限于“六艺”,而是向着广泛的艺术领域迈进。在儒家经学语境中,“游于艺”尚需要特别的意义建构和价值赋予,而在艺术领域,“游于艺”反而成为了价值与意义的输出主体,从而显示出话语权的变更与流衍。关于此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书法和绘画两种艺术形式进行集中的考察。
根据《周礼》的记载,“六艺”中的“书”原指“六书”。关于“六书”的解释最早载于西汉刘歆的《七略》,后保存在班固依据《七略》所编的《汉书·艺文志》中。其中道:“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1]施丁主编:《汉书新注》第2册,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264页。此后,许慎的《说文解字》亦大体延续了这一说法。由此可见,所谓的“六书”也就是对汉字构造规律的总结。但由于“六书”是国子之教的重要内容,所以其也就不仅仅是理论方面的解说,同时还必然包括着识字、书写等教学实践。在汉代,书法理论尚包孕在文字理论之中。如同陈振濂所论:“在那个时候,六书也好,‘六艺’里的‘书’也好,实际上所反映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事实,因为当时书法与应用文字的书写不分彼此,所以当时书法的研究也必然表现为偏向于应用和实用,即文字理论研究。”[2]陈振濂:《中国书法理论史》,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第15页。正是由于“六书”包含着书写的实践以及早期书法理论与“六书”的紧密关联,所以后世在论及已渐趋独立的书法艺术时,亦常常与“六书”相联系,并由此将书法视为“六艺”之一。虞龢《论书表》道:“臣闻爻画既肇,文字载兴,六艺归其善,八体宣其妙。厥后群能间出,洎乎汉、魏,钟、张擅美,晋末二王称英。”[3][南朝宋]虞龢:《论书表》,潘运告编注:《中国历代书论选》上册,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51页。在此,书法正是经由“书”而被归于“六艺”的。唐代徐浩说:“《周官》内史教国子六书,书之源流,其来尚矣。”[4][唐]徐浩:《论书》,潘运告编注:《中国历代书论选》上册,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46页。更是将书法的源流明确地诉诸于《周礼》中的国子之教。正是因此,“游于艺”往往为倾心书法的文人所挪用,充当了为书法艺术正名的理论话语。刘禹锡曾如此描述书法的尴尬地位:“吾观今之人,适有面诋之曰:‘子书居下品矣。’其人必逌尔而笑,或謷然不屑。有诋之曰:‘子握槊、奕棋居下品矣。’其人必赧然而愧,或艴然而色。”[5][唐]刘禹锡:《论书》,《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下册,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1309页。书法在正统观念中为工具性的末节小道,文人士子不仅不甚重视,亦不会因他人的否定性评价而过于动心,其影响甚至不如博戏、弈棋之流。此种对于书法的轻视态度,正是刘禹锡所着力批判的,而其从事批判的理论工具正是滥觞于《论语》的“游于艺”。刘氏道:“《礼》曰:‘士依于德,游于艺。’德者何?曰敏、曰至、曰孝之谓。艺者何?礼、乐、射、御、书、数之谓。是则艺居三德之后而士必游之也;书居数之上而六艺之一也。……语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是则博奕不得列于艺,差愈于饱食无所用心耳。”[6]同上。在刘禹锡看来,孔子虽然提倡在闲暇之时从事博弈,但博弈并未被列入“六艺”,故而书法相比博弈要更为高尚和重要。可见,正是与“书”的通约,构成了书法艺术之合理性与正当性的理论前提。
目录学反映着一定时代的大众对于事物的普遍认知。从目录学的角度来看,《旧唐志》子部的“杂艺术类”已包含绘画的内容,编于北宋时期的《崇文总目》进一步以“艺术”替代了“杂艺术”,绘画与投壶、弈棋、射术、相马等技艺同列于子部“艺术类”。[1]参见苏金侠:《中国古代目录学书目中“艺术类”类目的设置及其演变》,《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年第5期,第83页。然而,画家以及理论家并不满足于绘画与投壶、弈棋等相并列的局面,他们往往借助书画同源、同体的观念,将绘画与“六艺”相关联。北宋郭思在《林泉高致》的序中说:“《语》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谓礼、乐、射、御、书、数。书,画之流也。”又形容其父郭煕:“先子少从道家之学,吐故纳新,本游方外,家世无画学,盖天性得之,遂游艺于此以成名焉。然于潜德懿行,孝友仁施为深,则游焉息焉。”[2][宋]郭思:《序》,[宋]郭煕:《林泉高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3页。在此段论述中,郭思将书视为画之流衍所生,书法既然是“六艺”之一,那么绘画亦可位列“六艺”之内。绘画由此与“游于艺”相贯通,进而适用于“孝友仁施”“游焉息焉”等一系列的理论建构。在传统社会,画艺通常为占据正统地位的士大夫所鄙薄,郭思在其父著作的序中将他与儒家思想相联系,无疑有着提高其父身份地位的良苦用心。当居于正统地位的“游于艺”被移于书画之时,也就形成了社会权力的变更与授予。此种变更与授予一旦发生,艺术家的身份色彩亦会在客观上产生变化。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解释谢赫的“气韵生动”时道:“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3][宋]郭若虚著,俞剑华注释:《图画见闻志》,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17—18页。其中的“依仁游艺”之语被用来表示画者的修养、人品以及生存状态。在郭氏看来,“依仁游艺”所促成的人格境界正是“气韵生动”得以生成的必要条件。画者的身份不再是技术性的工匠,而是混合着多重思想背景的品格高尚者。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张彦远不同意谢赫将带有文人高士气息的宗炳、王微置于第四、第六品的做法,并说道:“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4][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25页。在文人所主导的评价体系中,技术往往不占据最重要的位置,而是替之以画者的品性,如此也就使艺术的人文维度和修身价值得以开显。
四、“游于艺”与中国古代艺术的修身传统
中国古代的“人文”一词源于《周易·彖传》对贲卦的解释。“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对此《周易正义》解释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1][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5页。就个体生存层面而言,“人文”即表示对于自然状态的脱离和对于道德状态的提升,而这必然需要特定的修身策略和持续的修身活动,以实现对于自我身心的改造。在“游于艺”之话语的指引与影响下,艺术被纳入到整体性的修身语境之中,发挥着自身的人文化成之意义。元代刘因曾道:“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矣,艺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谓艺,与古之所谓艺者不同。礼乐射御书数,古之所谓艺也,今人虽致力而亦不能,世变使然耳。今之所谓艺者,随世变而下矣,虽然,不可不察也。诗文字画,今所谓艺,亦当致力,所以华国,所以藻物,所以饰身,无不在也。”[2][元]刘因:《叙学》,《静修先生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明代陈献章曰:“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吾所以游于艺也。”[3][明]陈献章:《书法》,《陈献章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0页。刘因曾编著《四书集义精要》,广泛辑录并注解朱熹的“四书”学言论,陈献章则是明代心学的先驱和代表,当他们以“游于艺”来形容书法、绘画等在修身养性方面的作用时,也就将本作为儒家话语的“游于艺”所负载的人文意义和修身价值迁移到了书法与绘画等艺术中。康熙亦曾说道:“书法为六艺之一,而游艺为圣学之成功,以其为心体所寓也。”[4][清]世宗胤禛纂:《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7册,第191页。将“游于艺”视为圣学法门和心体所寓,明显是上述理学诠释模式的创造,康熙以此来诠释书法,也就形成了视域的再次融合与效果历史的层累。由于《论语》的影响和经典解释模式的确立,“游于艺”已成为了凸显艺术之修身价值的思想标志。当书法、绘画等艺术活动以“游于艺”表出之时,其所负载的技艺性在无形中得到了消解,发生了从技艺性活动向修身性活动的转变。个体从事书画等艺术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人格境界的提升,与之相关的技术性要素则成为了实现此目的的手段。在上文所引陈献章的言论中,书法艺术与人格修养之间的关系亦得到更为具体的建构。在其看来,书法艺术亦动亦静、亦巧亦拙、亦刚亦柔、亦立亦奔的特点可以使主体的心境收放自如、无拘无束,从而发挥诚意正心、调节性情的作用。由此可见,书法等艺术活动之所以能够与“游于艺”相关联,是以其自身的特点为深层原因的。“游于艺”为名,其自身的活动特点为实,名与实彼此契合,相互激发与印证,进而使书法等艺术的修身价值得以彰显,获取并确认了自我在文人生活中的意义和在文化系统中的定位。
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发问的是,刘因、陈献章等通过书画艺术所达到的修身效果,与朱熹藉由“六艺”所达成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吗?换言之,在刘、陈的观念内,是否纯粹是道德的成分?通过二者的具体表述来看,其所指向的是整体的生存状态,而不是像朱子那般专于道德。道德虽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但并非内容的全部。刘、陈作为儒家中人尚且如此,对于艺术中人来说更甚。“游于艺”向艺术领域迁移所导致的,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理论效果。庄子虽然对“游”之范畴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并对后世艺术影响深远,但由于其消解了外物的差异性并否定礼乐,所以“艺”未能成为“游”之对象。后世论艺者将庄子思想融入“游于艺”之中,从而促成了“游于艺”理论内涵的微妙变化。《宣和画谱》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也者,虽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然特游之而已。画亦艺也,进乎妙,则不知艺之为道,道之为艺。此梓庆之削鐻,轮扁之斫轮,昔人亦有所取焉。”[1]王群栗点校:《宣和画谱》,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6页。作者虽然以“游于艺”论证了绘画对于志道之士的不可或缺,但之后的“梓庆之削鐻”与“轮扁之斫轮”均是《庄子》中的典故。梓庆削鐻,先要忘却庆赏、爵禄、非誉、巧拙、四肢形体,而后入山林,观天性,以天合天。轮扁斫轮,不疾不徐,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因此,《宣和画谱》所说之“游”当为《庄子》中的心斋坐忘、物我混化之“游”。其中的“道”在本质上亦是庄子的“道通为一”“道进乎技”之道,而非儒家的道德之“道”。“游于艺”的思想内涵实际上已被改变。晚清的金绍城曾如此论道:“所以画学虽属小道,列于艺术中为最高尚者,因其旨趣之深邃,学理之高妙,其底蕴似浅显而实精微。从可知游艺一端,为至理之所寓,而人之习焉,不可不察。吾人学画,万不可以画之为画,不过玩物适性之事,是当以察其理而穷神,探其微而揆要,尽其义而悟真,内外交养,本末兼赅。则得心者,自无见有强致假借之弊,所谓应物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2][清]金绍城:《画学讲义》,王伯敏、任道斌主编:《画学集成 明—清》,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947—948页。通过引文中的“至理所寓”“内外教养”“本末兼赅”等用语可以见出,金氏之论对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进行了广泛的移植。然而,金氏思想中的“理”却与朱子理学有着深刻的差异。在朱子理学中,天理、物理与性理是相互贯通的,理兼具认知与道德方面的意义。而在金绍城那里,理被表述为“造化天机之理”或“物之法理”,其中的道德意味不甚显著,反而更接近于庄子的自然之理。正是因此,“游于艺”的指向不再仅仅是道德人格的养育,同时也包括理想画者的形成,其最终的目的在于生存状态的整体完善。
余英时在评论张充和的书画时曾说道:“后世对于‘游于艺’中‘游’字的解读大致都是通过《庄子》而来,因为这是‘游’字用得很多的一部子书。……通过《庄子》以解《论语》的‘游于艺’,我们于中国艺术的根本精神便‘得其环中’了。”[1]余英时:《序》,张充和著、白谦慎编:《张充和诗书画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2页。孔子提供了“游”与“艺”之间的原始联结,后世将庄子的“游”之精神置入孔子的“游于艺”中,从而构成了中国艺术的关键命题。而《庄子》之“游”之所以能与《论语》中的“游于艺”相结合,不仅仅由于二者用语的相似,更有着复杂的诠释学背景。通过张载、二程、特别是朱子的诠释,“游于艺”自由、从容、无物无我、无滞无着的特征得以开显,从而具有了与《庄子》之“游”相沟通的基础。而这些特点又并非来自于外界的强行赋予,而是早已潜藏于“游于艺”的文本中,为其自身所蕴含的思想张力。作为艺术学命题的“游于艺”,一方面在客观上赋予了书法、绘画等艺术以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当主体以“游”的方式对待艺术时,便会让艺术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得到消解,使之转化为与人的精神存在息息相关的修身活动。刘因说道:“古人于艺也,适意玩情而已矣,若画则非如书计乐舞之可为修己治人之资,则又所不暇而不屑为者。魏晋以来,虽或为之,然而如阎立本者,已知所以自耻矣。”[2][元]刘因:《辋川图记》,《静修先生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页。在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之下,文人士子表现出对于绘画的矛盾心态。他们既为绘画的审美性所吸引,不可抑制地参与到绘画活动中去,同时又对工匠性质的社会身份充满警惕。“游于艺”提供了一种方便,顺应了绘画由技艺性活动向修身性活动的转变,从而有助于消解文人士子面对绘画时的矛盾心态。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命题是事实与世界的投影和图像化。正是在命题的指引之下,人们达成对于事实与世界的最初理解。“游于艺”何尝不是一种图像式的解释。它象征着古典时期的文人对于艺术的理解与定位,构成了他们对待艺术的基本态度。而在儒家思想失去制度建构和一尊地位的现代社会,“游于艺”的儒学背景更是尽数褪去,其作为纯粹的艺术学命题被大众使用着,成为了另一种“百姓日用而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