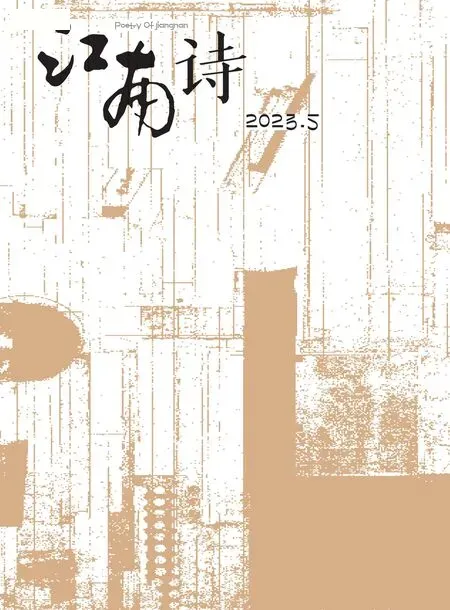未来的读者(六首)
牧 斯
在环球公园一位出版家的院落里
在环球公园一位出版家的院落里
诞生一位小姐。准确说是一位
小姐的前身。她被抱到第一处
又抱到第二处。整个环境保持
她未知的状态,她毕生无法了解的
一段。里面的人和事,物和景
在暗中移行。或者被一只带记忆的
暗箱保管。她的母亲如此年轻、美丽
而父亲,细心地抚弄她糖果般的脸
这与她日后对父亲的看法大相径庭
父亲似乎总是蛮横无理,是个不懂
技巧的角色。而此刻,两人慈爱地
欣赏着自己的小宝宝,灯光祥和,天启
神明。他们争论哪一块是自己的肉
哪一块是宝宝自己长的。日夜过去
时光上浮。只有一个人的记忆会保留
这些。但也有另一个人的记忆,会彻底
忘却。一个人尚未记忆之时,所经历的
事。一个人在尚未记忆之时,这段日子
就像林中的阴影,或阴影中的林木
存在,但未知。是一个可以研究但不能
复述的难题,它们含混地归入未知。
陪妻子去陈山林场补记
就像我家乡的那些弯道。也就是说,看不见
前面的路;虽然看不见,迫近又显现出来。
山上尽是木荷、栗树,微笑着似迎客人。
尽是结构复杂的荆团、藤条和绿色的火焰……
参天大树立于村口和村中央,田垄宛如大自然
散落的小吃。妻子觉得这里也熟悉,那里也熟悉。
我想象她做少女的时候,是怎样在这里挑水、
濯足和凝望。我想多看一眼她以前的光景——
她说许多地方不记得了。但看起来是风水宝地。
一条河溪似原始森林的封存,岸和石全然碧绿;
从最需要的地方流出来,从想象的美学流出来。
她说她以前常在这里洗澡。她越说,我越想象。
终于找到以前居住过的林场的房子,完全破败。
一根朽木故意抵住烂屋的心。但房屋越破败,
屋边的大树越繁茂,以战胜者姿态派发幼苗。
只有小径还在。像拉直的花环,有名和无名的
小花,轻易地爬上了坡地。也可轻易下到谷底。
妻子激动地欢跃,被遗忘的,又跑出来。不像
在我老家。我没法知道是哪些片断俘获了她的心。
去恒湖农场看妻叔补记
已经十年。我们热烈地去看他,
以纯洁之爱给他以安抚——
但他已经不像十年前那样
一见到亲人就哭。那是一种
强烈的对人世和健康生活的向往。
现在只是笑笑,有瞬间的感动。
——独坐枷栏的那一刻,
我看见他有一种奇怪的眼神;
目光与大家相接时,有某种逃离。
他熬赢了他的好朋友和我的父亲。
等待死亡十年。他的身体僵硬、
冰凉,但无所谓。成为一生
被谨慎欺骗了的人,也无所谓。
符合卡瓦菲斯对老人的描述,
也无所谓。他是一个木板人。
思考了死亡十年。我觉得他
不需要我们的回馈了。
那种漠然,对死亡不再恐惧的眼神
在我们离去时,尤为强烈。
完全不是他享受美食时的样子。
老人与鱼
他的鱼
仿佛同他共呼吸过,
依偎在他的破布衫里。
老人只卖从赣江里捕来的鱼,
干净又赤条。
我,多年来,
也只买他的鱼,我们
有着一种无法言说的信任。
我买他的鱼,
仿佛买回他的一个朋友、一个魂灵、一个精灵,
鱼心痛地跳跃,
同他分别。
我小心翼翼地维持它的原状,
在我的心里,
在我的身体里。
四方井[1] 四方井,地名,即将被新建的水库淹没。另,袁州古城传为唐朝袁天罡所设计。——与木朵、与陈腾、与刘义
我的理解是泉,地中水龙。
数条水龙从词语中蹿出。
它们隐藏的秘密,就是我们的友谊。
我们用脚去探引,
如果袁天罡在,还会建水坝吗?
词语并不廓清山野,也不为
我们的行脚负责;
河流也不需要澄清,
需要澄清的是人。
词语只构建语言中的四方井,
游离于我们行脚的四方井。
所以,当我们看见乡村
只有少许几人,
也不见得是归兮的寻访。
事实上,旷野仍然准备了碧绿、深绿,
准备了词语所需要的一切。
——我们各归其是
渴望捉住别样的水龙。
未来的读者
我,可能因诗闻名这座城市。
在死后百年寂静偏僻的小巷里,
她有美丽的裙子,甜蜜的微笑,
她朝这边看过来的时候,
我咯噔了一下,在天堂里。
她读到我的诗篇,
她的父亲儒雅,这一会儿在做学问,
她的母亲不失高贵,这一会儿在忙家务。
她的那条小狗,从童话中跑出来一样。
而我的故居就在附近。
她从文字中感知到我的想法。
我的诗篇刚刚再版,这城市的精魂。
两条心灵已然交汇,
我猜这就是我未来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