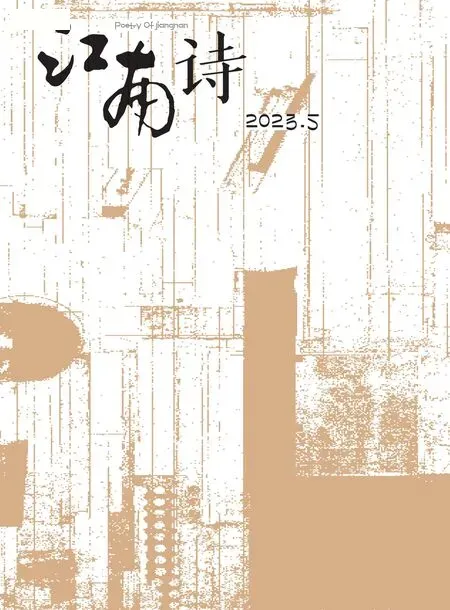生活在无尽的住址(八首)
◎张雪萌
秋 日
我们曾经在体内制造夏天
蔷薇火,旋转着,自花蕊
飞逝的舞蹈,为那仍愿停留
却必要的谢幕
夜晚就要倾倒下来。而我们
两道还会加深的车辙,不能拥抱
不能覆盖彼此。最亲密的
是节令,命我们共享的振动
那辆车会驶来,载装着
巨大的欣喜与丰获。驾驶员
歌唱吧,当月亮滚动在车篷上
像一枚静默的小银龛
待到他们走入会议室,走入
掌声鸣奏的剧院。我们
就用步子,认领黄叶洇湿的街道
——那是树木,对着空旷创作
想想这些馈赠也属于我们
水波,钟声和被遗忘的地址
在乌鸫的啼叫里,如果
不是这样的,又会是怎样的秋天
现在你注视我,清醒地注视
直到无尽的空开始将我们哂笑
我没有与湖面,与凝视
相对应的悲哀。
小镇上的作家
日常工作没有谈及必要:邮差
文秘,安保员,诸君想象之
在这一点上,他感到与伟大同行之间
某种幸运的共性。隐而不宣的身份下
该有骇浪惊涛,撼动着发生
他行使一个丈夫应尽的义务:沉默,惧内
修一些简单电器。家庭疆域内的
消极自由。夜晚在她身上时,脑海里
他想,剧院包厢里擦肩而过的女人
她未交出的姓名,触感如何
这段婚姻,不配合他快感的生产,所以
偏好独自的运动,“我转而写诗。”
小说以外,他写诗剧。可惜
欠缺统帅天赋,韵脚东逃西窜
像过于涣散的士兵。抽屉里的台本
不见天日,“哦,事实是
他们看轻没有门路的人。”
他的小儿子,较于以上作品,更显
粗制滥造。主要出自性格。在集市,大街
跟在他驼背的身后,仿佛仓促中
缀上的一截阴影。
实际上他更爱,先前夭折的女儿
未曾到来的天使。每一部小说,他致意她
一次又一次。关于这一点,他没有告诉妻子
个人消化沉重,对忧郁的特权,显得吝啬
何必烦扰她?厨房里,叮叮吭吭,她摆弄炉灶
里外穿梭,像只轻盈的蛾子。她是个好妻子
只是,不比缪斯的好,无所谓进行
文学意义上的还原与提纯。
看重灵感,偶尔学海明威,福克纳
试图理解,“始于蒸馏的文明”
一杯淡啤酒,浑身的弹簧
开始摇摆作响,像面对狂野的异性
同样手足无措。数般尝试后,连带对于
发表的热情,将息下来。
而写简化为写的本身。不然
“我又能去做什么?”一种欲望
依然紧束着他,如上浆的衣领,这隐秘的
只对他显露的庄重。
日子又这么过着,几十年后,迎来
平等造访的病痛。具体年月
不记得了。没有奖项的备忘,唯一的发表
是镇上报纸的两小条载录
(还是读者来信栏目)
床前是他的小儿子,握着他的手
中指和拇指间,凉而开裂的茧
那个影子一般的他,有着深海鱼
一样的双眼,温度,接近病态的淡蓝。
正是盛夏。窗外,那棵被他观察过半生的
花楸树,浓烈饱胀,筛来风新鲜的响动
那是它的节奏。对于窗内发生的一切
它不曾了解,没有暂停,从未对他
抒发的思绪,感到烦扰。
它轻柔地摇动,像某种发光的轮廓。
像一个梦。
牡 蛎
她从未思考过栖居的方式
她的壳层,他的岩面
相轭得如此熨贴
自出生起,一如所是
某个夜晚,她感到潮汐
环绕她,那种荡漾的诱惑
“我必须脱身,”
她想,“生活在无尽的住址”
乘着水波的飘逸,她轻轻
撬下自己,第一次,触碰到
身体的赋形。她爱自己
不规则的沉默,坚硬
与藻草、珊瑚和贻贝邂逅
穿梭,在那些发光的鱼群
很少交谈,共振足矣,她几乎
能抚摸到体内,那珍珠色的心情
这天,她涌向海岸,冲刷出
新异的边界。这是城市
来自另一种经验。人们来来往往
像固定的风景
疲倦极了。发呆的桅杆,过于
苍白的旗帜。低气压,卷积云
一对男女,抛接老套的情话
跛脚的环卫工,从堤岸这头,走到那头
海浪俯身向她,曳来应季的纱裙
又匆匆退去,像个徒劳而返的织女
她躺下,一粒小小的硬壳
扎入世界失活的肉身
而一切将继续浮肿。不会有人
抬起沉闷的眼皮,不会有人
打量惊诧,并捧起她多茧的肌肤
“多么破碎,又生动的
一小片贝壳,在沙堤
无垠的虚空上,几乎像个隐喻。”
夜晚,谢菲尔德
我们倾向谈论破碎,倾向回避
章节与章节间浮现的迟疑
阳光同样不是完整之物,在写字楼
公寓和市政厅的玻璃镜面,像
金黄的蜗牛,敷盖着下午的粘液
什么能让你解脱?至少不是
欢乐,让夜晚摇曳,鼓风机吹出
诱惑的火舌。不是加入醉酒的青年
用呓语嵌入他们的吞吐,那种龃龉
开始在酒精消解时,缓缓滑动
上膛——慢性的不安在积聚
你感到它像迷路的孩子,寻找并
回击着一具身体。这城市中
唯一的确信,最贴身的行囊
陪伴你穿越陌生,和陌生的下一站
晚点的列车,依傍着归意与焦虑
而月亮,静静落在车厢上方
不能被驮运,不能探入
隧道的暗处。像你期待的故事
不能任性,撕下并携走圆满的尾页
而章节如常推演,在这里
等待阅读的下一次重临。
在你离开的每个夜晚,月亮
它尖锐的箔边,从云层挣出
分割体内隐形的风暴。如同
一枚遗留的句号,被磨损
滑落,从誓言书的边角。
克莱尔
穿过,牧原泌出
珠串般的小镇
午后,巡行的光照
田野挪移着云的阴影
白金色的麦地,涣散着光线
好使日神歇息。越过
大地驳色的织锦,远处隆起
列兵般的巨树林
时间流淌,像某种奶制品
夜晚到来,再也没人关心
纹章学的事情。换了种姿势
拥抱,没有人下楼,把那盏灯熄灭
灯罩覆着尘埃,不为了
什么擦拭。盲蛛和飞蛾,还有
木头味道的地板,细小裂缝
发出的嗡鸣
酒吧桌上,一杯淡皮尔森
跑了气。方言听起来像小曲儿
有人对我微笑,出门前
将衣领竖起
寒暄的语气会更熟练
而袭来的一阵急切,难以名状
在黑暗里,摸索那条灯绳
恐惧,对于可感流逝的,含混
失控的往日。夜里
记忆和当下,相抵着躺在一起
像橱柜里两把随意摆放
并不配套的餐具
学 究
没什么值得热爱,哪怕是
等身的著作,只能视为
对十八岁冲动的彩排。
后来,是毕业典礼、就职签署
以及回答见面会上,一个又一个
傻瓜提问。对待课题,像个过早
选定终身伴侣的鳏夫
该活的都已活过,鲜被思考的问题
大体是自扰之。走在街上,想寻找一样
生动的叙事,非要命名一种
那个下午,日光反射在后排
女学生的胸脯,让他感到莫名的羞耻
(他们正讲授到俄耳甫斯)
他叫她回答。“Eurydice”,“eu-ry”
双唇上,她撅起一个圆形的嗔怪
似乎说着,关于失去所爱的艺术
她预习又复录,一次又一次。
他在台前,听力变得虚弱
被她身体的弧线,声音的弧线
逐渐淹没。她还不清楚自己
正作用着什么,像岩浆的潮浪
如此轻易,溶掉了,他分散如零件的
典故与感官。是一声缩小的叹息
然后是夜晚,复制的困怠接踵而至
一架键盘,几根烟头,细微的
语义差别。突然间他感到呼吸困难
想打开窗户,加入曾经远拒
又远拒过他的一切。
房间里,二十年前的声响
还在走动:推拉门半掩,衣架划过
铁质挂钩。玻璃罐,磕碰声,散落成绺的湿发
拍落在后背的肌肤。他坐在浴室外
鞋跟抖动着,沙发上,蹭出不安的凹陷
他担心那阵吱呀响起,可能的说辞
也许是“太晚了”,或者,“不太方便”
先被撤稿的程式,其次,欲望。
她离开时,沙发依然固定着他的姿势
没有争吵和叮嘱,回过头,哪怕一次
像这些年来,他的知识,在研讨会门外
候在走廊,等待世界抱歉地告知:
本世纪发明了太多冗长的条款
(而你要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收益?)
必然有一句,翻找得到
以取消他的希望,瘦弱而具体。
暂 时
走在学院的路上,牵着狗的中年情侣
骑行的人,移动中的车辆,开始
向我显露,他们合奏中的休止。慷慨而克制
伤春只好是暂时性的,像是悲秋
演出前的序曲。充满预见,为着
尚未到来的情绪,留下位置。
一株晚樱,沐浴在下沉的光线里
暂时飘落,暂时允许你聆听到
朝向枯萎的,收紧的发声
那时我还小。面对失败,该预备怎样
适当的反应。父亲或是母亲,告诉你
“那都是暂时的。”(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陌生人闯入你的生活,总为了
摆弄些什么,身体,或者思绪。
你躺在原地,观摩他的尝试。
离开,不带着任何预兆:送给他
书架上的小玩意儿,感到体内
焊进一把新的钩子。某种
意外的抓痕形成了,在空气里
我的生活,本可以对我抱怨些什么
但它维持沉默。寂静中,只有
狡黠的瞳孔,反射着,一闪而过
一个秘密,因其暂时性,得以成立
虚弱袭来了,试图解答的时候
反倒愈发掌握,一种困惑的精致
意 外
爱是那辆加速驶入火光的列车
惊叫的铁轨,失控的乘客
开始哭喊,绝望撞击着窗户。
不,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那。
一定有什么先被烧毁了,车身
裹满死亡到来前的噼啪声。
像两个只为了赶路疲惫的行人
那样近乎放肆的宁静:他握着她的手
她微渗出的汗,掌心小小的肉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