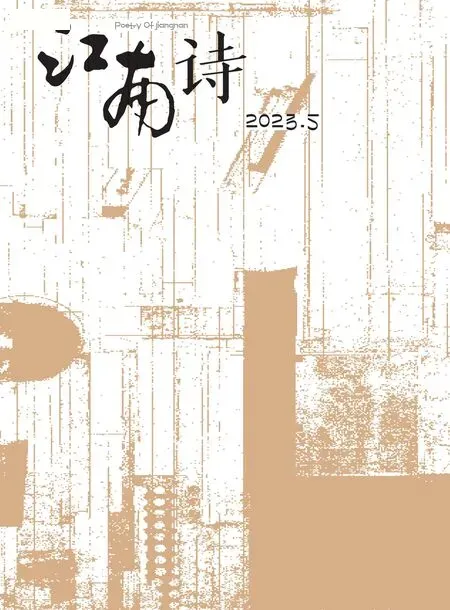安多河流考(二十五首)
◎阿 信
鸣
在空气阻力的作用下,流星自燃。
陨石,化为粉尘、蓝烟。
但鸟鸣却能精确命中耳涡深处某根
纤细的神经。
一生中,有多少鸟鸣呼啸而过
就有多少座身体的废墟,在疼痛中慢慢复苏。
孤 独
知道月亮里面有一扇开向桂树的门。
知道大河奔流受制于一种神秘的自然宗教的驱使。
固执地想把大海写入诗歌,想把一种
人类无法根治的毒素,植入此生。
唐·一个诗人的消息
写作是一种生活,抚琴也是。
他的后院长着一株融入月光的桂树;
阶前,几簇新竹。……青春作伴
美好的春天和诗酒岁月,在这里度过。
其余的日子,则形同梦游:
在一座座幕府和残山剩水之间。
晚年,他带着疲倦的身体回到破败的故乡。
偶 遇
在郎木寺的山道上,一个略显肥胖的僧人
与我相向而行。错身经过的瞬间,他向我
微微颌首。
僧人渐行渐远,消失在山道另一侧。
我站在原地,怅然若失。
——我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了解
他身体里面
微微晃动,却没有溢出的东西。
我在想:一颗星辰,和另一颗星辰之间
神秘的联系。
安多河流考
舟曲把夹岸的花木介绍给我们,我们欣然认领。
碌曲把嵯峨的群峰指给我们辨认,我们惕然心惊。
玛曲把旷野的星空交付给我们,我们竟至于无措,陷于失语。
我们没法从一场春天的游戏中退出来
瞎子看不见杏树在开花。
唇裂的孩子,也有在山岗上高声呐喊的冲动。
我们搬开石头,露出粘附虫卵的骨头。直到
我们中间的一个,被她的母亲喊回。另一个
脸上长满痘疱的男孩,被早早淘汰出局……
我们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尽管参与者,
已经所剩无几。
山顶的祭坛
大地的乳突:一座祭坛。
一堆
肉色、神秘、静静辐射的石头。
一座时间的仓库:光芒贮存,寂静敞开。
飞鸟在其间刻下淡淡的影子。
大风吹灭一堆堆柏枝。
旋转。
神秘旋转。
群山奔走环列,村庄浮若星辰。
低处,一片奔腾的青稞地
离开地面,终又
稳稳飞落。
一队马匹,无声蹚过河水。
我麻木、冷静,混合着泪水
环绕祭坛而行。
宿命的感觉如此真切:即使一阵
最轻的微风
也能把我这空空的躯壳吹散。
兀 鹫
镜头里的大鸟,传说中的猛禽。
远观,冥想,植入诗句。不提倡
抵近观察:影响食欲、带来
噩梦和坏心情。
草原上的清道夫,自然界的超能力。
位于食物链顶端,不知天敌为何物。
无名圣徒。非凡的培训师:训练出
一代代高空滑翔师、超音速飞行员、最后的
“斩首行动”执行者。
禽类中的忍者,高处不胜寒。
时时拷问灵魂,拒绝道德绑架。
精通天象,俯察生存。
不立一派,不著一字。
神秘的死亡大师,不设疑冢,
但没有一个人
可以接近它的领地,获取衣钵和传承。
嘛呢石墙
一个人是有局限的。一个人的信仰
也不能搬山填海。
集万人之力,在无尽岁月中
垒砌一堵低于寺庙但高过草原的长墙
是有可能的。
穷人的悲伤短暂,欢乐也是。
石墙基座,一块阴刻经文彩绘度母的
石块,是他亲手搁上去的。
他长年蒙面山中
剥离岩石。他的父亲拙于言辞
却精于雕刻。他的儿子,师从盲眼大师
在另一个州,学习彩绘……
马
今天午睡
又梦见马。
罕见的黄色(有黄色的马吗?)
从一片青绿山水中,
踩着碎步,
一路小跑,
经过我身旁。
我感到温暖,兴奋,又有点
想哭。
我确定它会在十步之外停下来,
慢慢地回头。
一切,
和想象一样。
它狡黠地冲我眨巴两下眼睛;
它猛甩一下头颅,一片
金光飞舞;
它“咴儿咴儿”地昂头鸣叫起来。
我像孩童一样扑向它,紧紧
搂住它的脖颈。
在俄合拉村雨中观“南木特”藏戏
嫁女场面。
来自雪域王廷的使臣、侍者和侍女……
银色服饰的大臣在转述、接受礼物,迈着
奇怪的步伐。
国王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
王后掩面,做出拭泪的动作。
尼泊尔公主先是摇头,继而哭诉,最后
垂首、顺从,背向观众,跪辞双亲——
肩膀久久起伏,身体不停颤动,仿佛
有一只小羊羔在里面挣扎、咩叫……
法号和铙钹骤然响起,
一程程山水即将展开……
雨越下越大,观众在退场,我和朋友们
也回到了车上。
隔着玻璃和雨幕,
我看到人间一场大戏,正在上演。
俄合拉村的演员们,仍沉浸在角色中,如痴
如醉……
黄鸭的鸣叫
怪柳后面的泥沼地里,有人
压低声音说话。
——那是黄鸭在鸣叫。
我看不见它,眼神不好。
很多黄鸭!宝华和豆豆
喊了起来。
我看不见它们,只听见它们在鸣叫。
我深一脚浅一脚踩着草甸靠近,
树篱后面
水域渐渐扩大;
湿地之上,连片阴云
——野生黄鸭在那里呱呱鸣叫。
我听得很真切。我假装
看到了它们。
坛城那边,有人在等我们
(我们离人群已经太远了)
是回去的时候了。
我确实看见过它们,在一段视频里:
野生黄鸭把头扎在水里觅食。
美仁草原
当我低头,向你指认
阴郁草甸上一朵
火焰般跳动的
红花绿绒蒿时(我把它称作荒野奇迹)
雨就落了下来。
我绝望地意识到:当雨滴
从你睫毛滚落的一瞬,
我内心浮现的
竟是另一张
瓷器般洁净、不朽的面容。
记 梦
在森林里,不停地跑。
躲避着尖刺、枯枝,从高空射下的
箭簇一样密集的松塔……
灵魂拖着身体在暗影中狂奔。
终于,站到一条黎明的大河边。
诘 问
狼毒花成片的河滩,草地在退化;
苏鲁花盛开的山坡,是最优质的牧场。
我来到青海果洛的久治,不知道
会给这里带来什么?
在花湖听雨
一盏灯亮着,心的湖底。
所有的灯被浇灭,这一盏,也要亮着。
它支撑起一个不大的空间:
养蜂人和他的蜂群,住在里面。
土拨鼠
草原属于土拨鼠
圆滚滚的屁股,旁若无人。
什么是岁月静好?两只小不点
追逐一只花蝴蝶。
另一只,心无旁骛,
伏在草丛啮食。
鼠辈之中也有智者,甚至统领——
它含胸挺背,长立在高处,观察着远方。
诗人说:
“土拨鼠一再挑衅,频频闯入视野。”
事实是:一群闯入者,
乘观光小火车,进入尕秀草原腹地。
湖畔·黄昏
穿过油菜花地的一条沙土路把我们一直送到湖边。
清晨,不时有小鱼
跃出谧静湖面。……现在是黄昏
高原深处的风,推送
钢蓝色液体
砸向堤岸。
没有赞叹、颂祷。没有
神。
……仅余呼吸。
和这天地间寂寞之大美。
穿过油菜花地的一条沙土路把我们一直送回
星光披覆的路。
察尔汗盐湖
整个下午
他看见絮状云朵在天空和湖面上悠闲地飘浮。
自始至终,没有一只鸟的影子出现
——哪怕只是,在瞬间逗留。
风暴在万里之外的洋面形成。
大陆腹地,一个人交换着两种心情:
刚被丰沛填满,又被贫瘠掏空。
致友人书——赠燎原
那每日裸浴海滨的长者,
那筋骨如石棱,通体被夕光涂抹油脂的长者,
岁月沉积的一场场大雪,在如此
金汁涌动的海水中缓慢融化——
是皮壳粗糙玉质细腻沁色丰富的原石籽料?
是结构致密的诗性结晶体?
我在遥远西部向你致意:
只因曾坐拥高原的厚重,故而
黄昏视域中的大海
才显得如此瑰丽、辽阔!
蒿子沟
路基下的村庄被厚雪深埋。
只有黢黑的屋檐一角露出破绽。
有些人注定要在这里度过整个冬天
和随之到来的春天。
我与他们没有交集。
我只是深冬岁末,行色匆匆,偶然
穿林而过的路人。
这个冬天
这个冬天没有写一首诗。
这个冬天终结了疫情,但战争
仍在欧洲腹地艰难地进行。
下了三场雪,考取了驾照,旅行计划
继续搁置。
这个冬天读完一部七卷本著作,
它躺在书架的积尘里已有多年。
这个冬天,在土耳其
数万人埋在废墟下面,失去呼吸。
一座休眠百年的火山突然高调喷发。
这个冬天,去了一趟美仁草原,
没有奇迹发生。原野上
积雪盈尺,天空阴沉,
不知什么人比我早来一步,
留下一溜车辙印。
没有雪豹没有雪豹也没有雪豹。
这个冬天,不想写一首诗。
狻猊帖
无眠。无一字可写。抽很多烟。
辗转反侧,长夜不得伸展。
——这种情形已有多日。入冬以来,
似乎鲜有安宁的睡眠。
是什么让它烦燥如此,默诵百遍清心密咒
尚不能令其片刻宁静——
这孽畜,这荆莽丛中伺机而动的潜伏者,
这来自西域伏象食虎的大猫?
内宇宙的爆炸,
比三个嗜血部族的叛乱还令人心惊!
酒浇不灭。
铁棒僧,无法使其慑服。
潭门手册——给古马
来吧,在这里,飞雪和蛱蝶的异乡
构筑如云船屋
在明快的风中畅饮
看捕鲸船驶出避风港。从底舱
扯出一挂挂新鞭
在这里建立一种新秩序
语言的群岛,内心深处的钟
砗磲回归大海
牡蛎新鲜出炉,菜蔬
自带咸味
移植北方的暴雪在入海的长堤上
在飞溅的鱼群身下
加油站
它的内部构造只能借助想象:
一间巨大的心室,连接动脉、毛细血管,
持续泵出燃烧的液体。不能想象
一夜之间所有的加油站发生类似短路或
血栓堵塞那样的故障,道路瘫痪
像一截截被打断脊椎的蟒蛇,
紧紧缠绕在这个星球上:直到窒息。
这种情况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事实上
很难发生,但并非完全不能——
如果有个疯子,在每一口油井,
插入一根捻子,在圣诞或平安夜同时点燃。
但这关乎石油资源和人类安全,
不便讨论。我只看见它的外部
一只巨大的红色蟾蜍,蹲踞在必经的路口
不避晨昏,吞进、吐出各种车辆。
我遇见它时,它就这样,绕也绕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