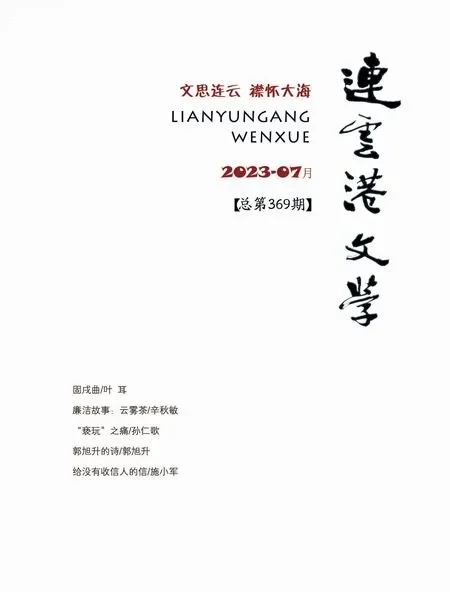散文两则
三月
是的,月光很好,夜晚也好,适合冥想,也适合孤独。一切都沉醉在迷离中。在夜里,我抚摸着晚风,也抚摸着往事,一些与之相关的记忆也纷至沓来。于是在凌乱的思绪里,呢喃成文字,就像一声凝重的叹息。
——番外
敦 煌
记得十年前,我读完余秋雨先生的《摩挲大地》便产生了去往敦煌的念头。一个月后,收拾了行囊,前往敦煌。
母亲在我儿时起就常唠叨的一句话:“你这丫头,总是想到哪就做到哪”。从前以为是母亲爱唠叨,现在终于细品母亲的唠叨是对我一言之锤的定论。是的,母亲没错,我是个随心并且十分任性的人,随着年龄的递增,锋芒却没有褪去,反而越来越锐气。
厚厚的云层,飞机张着坚硬的翅膀,载着一颗自由而热烈的心。景至如画,山水共鸣,千年古都,你若不去,你又怎拾得起那颗困顿许久的好奇心呢。
凌晨四点十五分,鸣沙山内的导游挨个打了房间电话,似睡非睡的迷糊被黑暗笼罩,看不清陌生的地方,所幸也没有人潮如涌的游人,离地面最远的西域地带,风沙、干燥常年为伴,地宽、物稀的自然气候相对拒绝了游者,黑暗中,接过导游手里的编号牌,与屈腿而息的骆驼对号。沙漠,沙子盘居而成了漠,是梦里的画廊。骆驼形成了队,每五只排列,由壮年男子牵着,他们都同属沙漠,彼此懂得,所作也是顺其自然吧!提起绳子的那一刻,领头的那只骆驼便蹬起前腿,立直,待稳稳地踏入地面时,再撑起后面的两条腿,一跃而起,那两堆冲天而去的驼峰像黎明前的铠甲,高大英勇。
没有路,尽是沙漠,一段由长形的段木合拼成的路,在茫茫沙漠上显得奢华另类,踏进沙漠的骆驼,像鱼儿回归了大海,生命的浩瀚只有在对应的环境里,才能显现张扬雀跃的气势。木头路的尽头,是跨上骆驼脊背的地方,只只沙漠使者,蹲埋在沙地里,平和地等待生命里的过客。近了,骆驼的身体宽大粗壮,两只硕大的驼峰倒是软塌塌的歪斜在一边,骆驼的主人扶我跨上驼峰中间,坐稳后,吆喝起身,揪住骆驼脖子上的绳,骆驼顶起左前腿起身,那一瞬,仿佛把我一下推至空中,这刻,吃惊难忘,与沙漠的宽阔相比,倒是低估了它的高度。
牵着绳索,稍稍适应了晃荡的沙漠行,便迫不及待地放眼望去,天将黎明,月亮清澈地挂在天上,圆盘似的,通体散开的月色轻柔地落在金色的沙粒上,天上人间,赤裸着彼此的美,守望千年!骆驼的主人牵着手里的绳,每拽动一下,便在沙漠里留下一串串清脆的驼铃声,骆驼无畏沙漠,沙漠静止无声,在冲向黎明时的自然中充满了静默相守的和谐。
到了,骆驼载着我们来到了沙漠中的一小块平坦地儿,蹲下,跨下身,一脚踏进沙漠,细沙热情蜂拥过来,两只鞋里剩余的空隙不停地涌入、溢出,溢出、涌入。恼了,怎么了?你是再也推脱不开它的热情了,既然喜欢,那么,就让它肆意吧!东方出现了一道光,太阳就要出来了,用尽力气向上攀登,只是理想太过庞大,细细的沙子在沙漠里像个调皮的劲敌,你越跨大脚步,它便示展着柔弱让你倒退半步,这样努力不久,便会在心里暗暗泄了气。再抬头看那一道呼之欲出的金属光,不由得又加快了脚步。登上高处,放眼望去,沙漠的高度由多个平线组成,但都是棱角分明,看似山一样的气概,却是由无数的沙粒形成,自然界的神奇,呈现出了纵多惊艳的奇迹。很快,太阳露了个点儿,在沙漠上盛着一团金色火焰,燃烧起黎明前的黑暗,火焰的四周一片通红,如新生的天使把绚烂撒在了沙漠上,把光和热馈赠给了沙漠。安静的沙漠上有了阵阵悸动,“沙漠日出,太阳出来了!”安静等待,终于敌不住美好的呈现,轻呼声,呐喊声,也许一生你只见一回,也许下一次再见你早已不是现在。
终于,太阳跳出了整个沙漠,随之而来的是热浪,是骄阳似火,是人们面对汪洋沙漠的惊叹声!鸣沙山,古有“神沙山”之称,为流沙积聚而成,东西长约40 公里,南北20 公里,海拔最高点为1715 米,天气特别炎热时,沙粒干燥温度增高,稍有摩擦便发出爆裂声,众多汇合,乃至沙漠间有轰轰隆隆的鸣响,这样的自然奇迹,不得不与“神”字扯上牵连,是啊!自然的玄机,有时候,必要附以答案的,否则,怎么让追寻的人得以释怀呢?
归来,大漠的浩瀚和狂奔的喜悦久久不曾平息,在繁华拥挤的城市,每有闲静,沙漠的回响便在心中绽开了宽广博大,偶尔在闹市听闻驼铃声,四处张望,却寻不到影踪转身,嘴角淡淡的笑意填满了任性后的欢愉。
敦煌已不是我心里的敦煌,它在我的脸上,在我的呼吸里,在我的语言里,似乎,我就是敦煌。在我的吞吐风雷之间,可能是飞沙走石,可能是风和日丽。
玩 具
我有别人没有的玩具,别人亦享受不到我玩具的滋味。
父亲是个军人,也是个铁石心肠的人,我一贯这样评价他。不懂他心里柔弱的地方在哪?也不懂这个丫头是不是他亲生的,我曾问过我母亲。
一棵树的S 型弯处被人剁成了段,到了父亲手里成了块,最后躺在地上成了我双膝下的刑具。树长着的时候已经生了病,上面好多的洞眼,我那时候是每回跪着就习惯数数上面的洞眼子,一遍又一遍看着树块的形状,等到父亲气消了,在他心里觉得差不多时间才可以站起来。之后会乖一阵子,且父亲也会待我特别好一阵子。但时间太短,往往化解不了我还未消散的怨恨又进行到下一轮去了。
一根像柳条般细的竹枝,带着韧性,大约超过手臂的长度,细小且又有老气横秋的模样很是听人使唤,它仗着人的威风,尽显妖气。它闲着时,我也不敢折它,怕它主人因为它的离奇失踪而糟来更大的灾难。恨也不行,它无生命。
两样配套的玩具亦是我的刑具,同龄人不识它的滋味。
记不清也看不懂自己是不是调皮,总之每犯有父亲内心规则的事就得受训,通常是先反手掌脸,小时候的脸蛋儿还未长成父亲的手大,乃至青紫色常呈现在左右腮上,引来老师的厌弃,说我是个脏孩子,问我洗不洗脸,我回她说洗的,她终于忍不住斜着眼朝我说:“洗个脸都洗不干净!天天都这样。”我老实回她:“报告老师,这是挨爸爸打的印子。”抬头时,老师惊讶的表情还没消退。
夏天的傍晚,我喜欢挨着墙角看蚂蚁,蚂蚁的行军很有序,小的食物可以单独搬了就跑,大一点的便倒着拖,虽然吃力,但最后百分百弄回家去,再遇见巨食,邀来同伴,大家齐心协力一同扛回家。我是它们中的巨人,我是可以随意操控它们生命的,只要我高兴,但我往往不曾惊动它们。那次我照旧看蚂蚁,父亲和村里人说笑,耳朵里飘来了他的声音:“我丫头我打她巴掌时她两只大眼睛死盯住我看,一眨都不眨,有时候都忍不住要笑出来,但我忍着不笑,万一笑了,这教育就白费了。”我听着心里骂声大恶人。
树块有没有被我双膝磨去一层我不知道,竹枝有没有抽细我也不知道。直到有天,我的大爷爷来我家玩,他坐在灶膛边上烧火,通红的火在灶膛里乱窜,大爷爷用推草的火叉搂了搂灶膛,顿时火苗像爆发的小宇宙窜到了灶膛外。这时候大爷爷背靠着后墙,双手拱着放在膝盖上。我肤着大爷爷的一只膝盖,同爷爷一起看火苗,突然想起我膝盖下的板子,随即告诉爷爷:“爸爸给我做了块板子,是专门跪的,每次打完再拿出来跪上面,我还有一根竹枝……”话没说完,就看见爷爷的眼睛里滑下了泪珠,在面颊两边打了个滚落进枯草堆里。我好奇地盯着爷爷的眼睛,这是多么平常的事啊,爷爷为什么要哭呢?爷爷抹去泪和我说:“宝宝,去把跪的木板和条子拿来给爷爷看看。”我快活地站起来,熟练地拿来这一套“老朋友”。爷爷拿在手里正面反面看了几遍,突然快速的扔进了灶膛,火苗一下包围了这个新来的同伴,包得那么稠密。
我惊呆了,傻傻地看着这突如其来的一瞬,正愁着怎么向父亲交代时,爷爷拍拍我小小的肩:“宝宝不要怕,有爷爷在,今天我就等你爸爸回来好好问问他。”
父亲干活回来,放下手里的农具,恭敬地叫声:“叔叔。”他叔叔随即叫他到身边,责问跪地板、竹枝的事,之后严肃地训斥了父亲,并让父亲以后家规从轻,再不允许用处刑的工具,我看见父亲一一应答。
从此,告别了伴随我很久的“老朋友”,知道这世上的人和物都是一物降一物的,他没有最狠,他只是还没遇见。
让人跪下很容易,让人学会站立确实难,父亲不知道,余下的半辈子,我都在努力学会站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