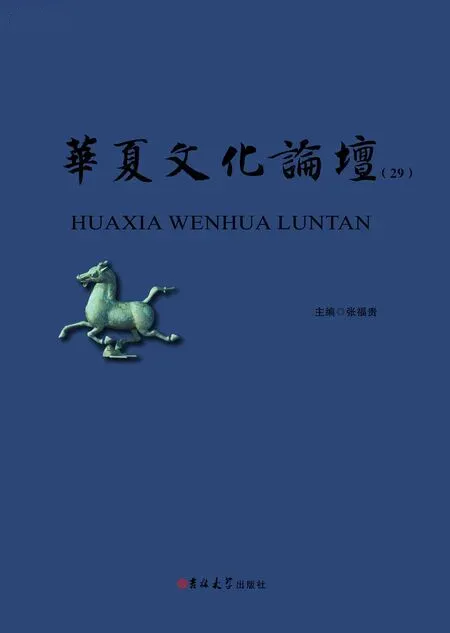气味与阿来小说的空间建构
邓丽娜 高 玉
【内容提要】阿来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气味书写,它们对阿来小说的空间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学者倾向从时间的维度分析气味与记忆、历史的关系,而弱化了气味与空间的联结。实际上,气味不仅与个体的记忆有关,还具有一定的空间属性。气味书写使阿来小说呈现出多层次的空间感:首先,气味与藏区的自然地理空间密切相连,传递出浓烈的藏地气息;其次,气味建构着一个独立的社会空间,影响着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后,气味搭建了人物的心理空间,有时充当着情感与欲望的催化剂。
1945年,约翰·弗兰克的论文《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发表,他将空间形式引入小说,至此,小说中空间问题的讨论已经延续70多年。然而,气味与空间的联系并没有得到研究者的充分关注。阿来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气味书写,从早期的短篇小说到20世纪90年代的成名作,再到21世纪以来当下的创作,“气味”一直是阿来小说中的高频词,他对气味的书写兴趣从未改变。①气味描写在阿来小说中非常普遍,涉及气味描写的小说有:《老房子》《鱼》《尘埃落定》《随风飘散》《槐花》《奥帕拉》《三只虫草》《河上的柏影》《蘑菇圈》《云中记》《旧年的血迹》《格拉长大》等。同时,阿来也很强调小说创作中的空间感,他说:“我们生长在一个地理空间里边,就要了解这片土地,了解这片土地上的语言。那么,中国当今很多小说为什么软绵绵的,立不起来,就因为里边没有一个确切的空间,作家们写了这个村,但你读完连这个村子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他们写了一个市镇,你读完仍然面目模糊。地理环境都不行,你的写作就缺少空间感么。反正我自己的写作,空间感是从来就有的。”②阿来、傅小平:《阿来:连语言都不好,即使作品能红极一时,也不会传之久远》(上),《西湖》,2020年第9期。空间不仅是人物存在的前提,也是小说能够立起来的支架。除了通过描述地理环境来体现小说的空间感,气味书写也是阿来建构小说空间感的重要手段。表面上看,这些气味“附着”在植物、动物、人物的身上被一笔带过;实际上,气味与小说中的地理环境、社会背景、人物心理密切联系,建构着小说的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与心理空间,使阿来小说呈现出一种多层次的空间感。
一、气味:地理空间的标识
气味具有一定的空间属性,特定的气味能让人联想起或定位出某些特殊的场景。道格拉斯·波图尔(J.Douglas Porteous)在smellscape一文中提出smellscape(嗅觉风景)的概念,他将嗅觉与风景、景观联系起来,指出嗅觉景观就像视觉景观一样具有空间秩序或与地点相关联。①J.Douglas Porteous,”Smellscape,”in The Smell Culture Reader.ed.Jim Drobnick(Oxford:Berg,2006).p.91.从构词来看,smellscape由smell(闻、嗅)与scape(风景)组成,字面意思是与嗅觉有关的风景,或翻译成嗅觉景观。与陆地风景(landscape)、声景(soundscape)、街景(streetscape)的构词法一样,smellscape强调与嗅觉相连的景观,景观的背后展现了一种空间属性。换句话说,气味不是凭空出现的,一种气味的发出必有其“空间”所在,人们可以根据气味的来源、方向、距离等因素定位出气味的“空间”所在。再加上其他感官(视觉、触觉)的配合,嗅觉感官的空间感与空间特征得到了加强。波图尔结合自身经验,阐述了气味与地理空间的联系,“大陆、国家、地区、社区(尤其是‘民族’社区)和房屋都有其独特的嗅觉景观。例如,我能回忆起印度的异国情调;希腊乡村的野草味;亨伯塞德泥土的异味;复活节岛上的马、海和草的味道;波士顿北端的意大利面食和八角茴香;南端的阿拉伯和中国食物以及我木屋里的雪松火种和干桤木的气味”②J.Douglas Porteous,“Smellscape,”in The Smell Culture Reader.ed.Jim Drobnick(Oxford:Berg,2006).p.96.。不同的地理空间有其独特的嗅觉景观,凭借特殊的气味,人们能建立起气味与空间的联系,甚至通过特殊的气味就能识别不同的地理空间。例如,消毒水的气味能让人联想起医院,美食的香味能让人想到餐厅或者厨房,青草的芬芳能让人想到绿油油的草地。简言之,气味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标识出地理空间并建构着人们对空间的想象。
在小说中,阿来描绘了许多与植物、动物有关的大自然气味,这些气味带有鲜明的藏地气息。值得一提的是,阿来在表达气味时通常使用“味道”一词,严格来说,味道对应的是味觉器官,人们想要尝出某种味道必须要用舌头去品尝,被品尝的东西还需在唾液中得到溶解。“气味”一词对应的是嗅觉感官,人们要嗅出某种气味,被闻嗅的物体需要具有挥发性,将微小的分子散布到空气中,然后再由空气传达到鼻腔。从数量来看,味觉的种类少,人们能品尝出来的味道主要有酸、甜、咸、苦等,然而嗅觉的种类却千差万别数不胜数。“食物的味道多半来自其气味……我们只能尝出四种味道:甜、酸、咸和苦,也就是说我们感觉到的其他‘味道’其实都是‘气味’,而我们自以为闻到的许多食物,其实只能品尝。”③[美]戴安娜·阿克曼:《感觉的自然史》,庄安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3页。因此,在阿来小说中,他书写的是“味道”实际上偏指气味。在《三只虫草》的开头,阿来一连写了六种味道:冰冻的味道,尘土的味道,水汽的味道,冻土苏醒的味道,青草的味道以及迟来春天的味道。这些源于自然的气味汇聚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气味,在空间上联结着高海拔地区。此外,小说中还多次描绘虫草新芽的气味,虫草是藏区盛产的一种植物,其气味鲜明地指向了西藏这一地理空间。从波图尔的“嗅景”说来看,气味的背后都有其相连的嗅觉景观,独特的气味能带来不同的空间联想,自然的气息、虫草的气息标识着西藏独特的地理空间。
作者选择气味来彰显西藏的自然地理空间有其深意。首先,这与阿来的生长环境以及重视自然的理念有关。阿来出生于藏区马尔康的一个小村庄,他从小触目可及的就是河流、森林、群山,还有一些不知道名字的动物和植物。他所生长的村子在地域上非常阔大,人口稀少,每一户人家之间隔好几里地,经常都是孤零零的一家人。这种村落结构,削弱了人与人的关系,凸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也让阿来更早地意识到一个叫“自然界”的东西,并影响了他以后的创作。身处大自然中,人类的感官也更容易被唤醒,这有利于在书写中建立嗅觉与自然空间的联系。阿来说:“自然能把我们的感官打开。现在我们局部感官的反应特别敏捷,但别的感官都被抑制了。因为你根本没有使用它。但在自然中,你的每一个毛孔都好像被打开了。”①阿来、陈晓明:《藏地书写与小说的叙事——阿来与陈晓明对话》,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编:《秘闻与想象:2015春讲:阿来、陈晓明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02页。在所有感官中,视觉、听觉是反应最敏捷、最受人关注的感官,而嗅觉最容易被忽视,这种现象在文学中也有表现,例如在展现自然空间时,我们更倾向于从视听方面来描写与倾听。然而,随着新媒体的涌现,小说的表达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在声音呈现、状物写景、描图画色等视听艺术上,小说比摄影、录音、电影艺术略逊一筹。嗅觉感官的“觉醒”以及与地理空间的联结,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自然的方式。
其次,嗅觉是一种极富生命气息的感官,气味展现的地理空间别具生命感与真实感。在所有的感官中,嗅觉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感官。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视觉、听觉、触觉、味觉感官的开启与关闭。闭上眼睛我们可以不看,把耳朵堵住可以不听,不去接触就不能触摸,不去品尝自然就不知其味,然而对于嗅觉,我们如果不去闻嗅,就要停止呼吸。可以说,嗅觉与我们的生命密切相关,嗅觉与呼吸的共振加强了嗅觉感官的生命感,这种生命感能带来一种真实性。莫言在《小说的气味》一文中提到,我们在记录生活中真实故事时,应当将我们的嗅觉、视觉、听觉等全部的感觉调动起来。②莫言:《小说的气味》,《小说的气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页。视觉、听觉感官在小说中的运用比较常见,反倒是嗅觉感官调动的比较少,嗅觉的调动更能营造出小说空间中的真实感。换句话说,只有作者身处藏地,真正地闻嗅过那些气味,他才能在小说中描述那些气味,他的小说才能带给读者一种真实感。
最后,建立自然真实的地理空间是对妖魔化浪漫化的藏地空间的反拨。长久以来,人们对西藏的空间想象是幽远的、神秘的、荒蛮的,甚至有些作家靠贩卖西藏的神秘与落后收获丰厚的利润。这不仅误导了读者,还造成了一种市场乱象:那些不描写西藏落后、神秘、圣洁的书籍渐渐失去了读者和市场,于是作家们只好继续贩卖西藏的神秘来挽留读者和市场,导致大众对西藏的误读越来越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正因为西藏被误读至此,阿来在自己的作品中力图表达一个原生态的西藏来对抗被神秘化的西藏。他说,他希望他所有的作品,终其一生,所有的东西叠加起来“能让大家慢慢慢慢接近一个藏族……就是西藏的这个真切的形象”①邱晓雨、阿来:《阿来:浮华时代之中的本真质感》,邱晓雨编著:《用文字呐喊》,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1年,第6页。。这个真切的西藏底色之一,就是呈现一个自然的地理上的西藏。同时,建构自然的地理空间体现了阿来对现代化商业与科技的批判与反思。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的入侵,树木被砍伐,森林被毁灭,山洪暴发,藏地自然空间受到前所未有的挤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受到挑战。因此,文学要重视自然,那么必然要关注地理空间,而阿来在对气味的书写中建构自然空间的方式更是值得肯定和进一步探究。
二、个体、集体、社会与气味
气味不仅参与了阿来小说地理空间的建构,还影响着个体的自我认知,人物与所处社会的关系。西美尔在感官社会学理论中提出:“同视觉和听觉相比,嗅觉感官历来就是一个着眼于较近距离的感官”,“我们闻到某人的气味,这是最亲密地察觉到他,他可以说是以空气形式的形态进入到我们的感官的最内心深处,显而易见,在对嗅觉印象增强刺激性的情况下,这必然会导致某种选择和某种距离保持,这种保持距离对于现代个人的社会学上的审慎来说,构成感性的基础之一”。②[德]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492页。从距离上看,视觉主体与客体即使相隔很远,主体也能看见客体,然而嗅觉主体距离嗅觉客体相隔很远不一定能够闻到客体,一般来说,闻嗅主客体必须保持在一定距离,主体才能闻嗅到客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嗅觉感官相对视觉、听觉感官来说是一种“近”感官。其次,从闻嗅这一动作来看,闻嗅比看、听更暧昧,闻到某人的气味比看到某人,听到某人声音更亲密。在闻嗅过程中,他人“以空气的形态”与闻嗅主体进行“接触”,这是“看”与“听”所不具备的。气味的舒适与否直接影响着主体对事物、人物的选择与评价。近距离感官赋予嗅觉感官更多的社会意义是:它在传递愉悦的情绪时也容易传递排斥感,特别是在某种刺激性、令人不悦的气味加强时,主体可能会对客体进行一种距离保持。在现实中,气味在很多时候不是拉近而是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从而造成个体、集体与所属社会在空间上的疏离与矛盾。
气味在个体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气味或“嗅觉护照”,“嗅觉护照在形成和维持社交网络上有很重要的作用:它们有认同的功能”。③[荷]皮埃特·福龙等:《气味:秘密的诱惑者》,陈圣生、张彩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30页。这种认同包括他人的认同和自我的认同。在《云中记》中,气味以一种细微的方式影响着人物的自我认同,并加强了人物内心的疏离感。主人公阿巴具有多重身份:地震之前,他是云中村的祭师,这是家族、云中村赋予他的责任与身份。同时,他也是宗教从业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是政府登记册上他的身份,是官方对他身份的认可。地震之后,阿巴搬到了移民村,他有了新的身份,移民村的村民,李老板家具厂的锯木工人,这是现实生活给予他的身份。在移民村生活久了的阿巴,他发现自己身上只有“竹子的味道”“木头的味道”,他向仁钦诉说道:“我不是阿巴,我是移民村家具厂的锯木工。……我都没有云中村的味道了,也没有非物质文化的味道了。……我是移民。我是家具厂的锯木工人。闻闻,闻闻。竹子的味道。木头的味道。就是没有传承人的味道。”①阿来:《云中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3页。在阿巴的认知中,气味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嗅觉是一种唤醒认知的重要感官,这一点与视觉和听觉的基本功能并不相同,某些气味对个人来说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云中村的气味之于阿巴就非常重要,甚至影响着阿巴的自我身份认同。锯木厂里潮湿的木头味道,身上散发的竹子味道让阿巴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云中村的气味,这种气味的丧失不仅削弱了他作为云中村人、祭师身份的认同感,还加剧了他内心的孤独。后来,阿巴不顾劝阻,冒着生命危险重返云中村。在云中村住下后,他发现自己“浑身都是云中村的味道了。马匹的味道,他枕着睡觉的鞍子的味道。一身祭师行头的味道。熏香的味道。木材燃烧的味道。以及现在就包裹着他的云中村尘土的味道”②阿来:《云中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30页。。在找回云中村气味的同时,阿巴也找回了自己的身份,他逐渐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祭师,发自内心地祭拜神灵,安抚亡灵。阿巴回归云中村的过程既是一个“寻味”过程,也是一个自我的发现过程。
从集体来看,云中村人的气味不仅没有拉近他们与山下人的距离,反而让他们陷入孤立与冲突。阿尼克·勒盖莱在《气味》一书中提到,“同一种气味,标志着某一个体隶属某一群体,有助于该个体融入该群体,表示该个体与其他群体无关,并在该个体和其他群体之间立起一道障碍。因此,气味也就成了种族歧视、社会抛弃甚至道德抛弃的工具和证明,或简单说,是标志”③[法] 阿尼克·勒盖莱:《气味》,黄忠荣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7页。。云中村人因为生活方式与饮食的差异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味,对云中村民来说,这种气味能让他们更好地与其他云中村人融合,同时也在他们与其他群体之间立起了一道屏障。当云中村的人带着这种气味走向山下,融入社会时,他们遭受的是别人异样的眼光。“云中村的人和东西,包括食物在内,总是带着特殊的气味。衣服上有陈年油脂的味道。茶水和食物中,有着动物皮毛的味道。云中村人带着这些味道走到县城里去的时候,人们会说,哦,蛮子的味道。”④阿来:《云中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28页。受职业、健康、遗传、饮食、情感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群体的气味是不一样的,成年人与孩子的气味不同,健康之人与患病之人的气味不一样,吸烟的人与不吸烟的人气味不同。因此,不同的个体或群体之间存在不同的气味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气味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在人际交往中,气味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意义。波图尔在其文章中也强调群体气味因种族、文化、年龄、性别以及阶层而不同,“不同的阶层可能存在不同的气味,在上一两代人中社会阶层还很容易被气味区分开来。从事体力活的人,他们的工作比较脏且容易出汗,加上卫生条件的限制使他们得不到彻底的清洁。相反,富裕阶层出汗少,能够得到有效的清洁”①J.Douglas Porteous,“Smellscape,”in The Smell Culture Reader.ed.Jim Drobnick(Oxford:Berg,2006).p.93.。因此,气味中隐藏着阶层、种族、年龄等个人身份信息,对某一种气味的排斥暗含了对某一阶层、种族、年龄的排斥。云中村人的气味将他们从社会群体中区别出来,导致他们成为孤立的对象,甚至带来矛盾和冲突。《云中记》中曾提及一个故事,云中村人一进城,城里的人就会议论他们身上的味道。于是云中村人就和山下城里人打架,他们不明白这种在云中村“很自然的味道”为什么到了镇里就成了一种“奇怪的味道”。由此可知,气味不仅区分个体,还识别了群体,造成了社会对某一群体的孤立与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气味在小说中具有丰富的内涵,阿来不仅书写了一种具体实在的气味,还写了一种看不见的抽象气味。他在《云中记》中反复提及的“云中村的气味”实际上是指云中村人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从这个角度再回看,气味与人物的自我认同、气味与集体社会的关系,不难理解影响人物身份认同与他人认同的背后,更多的是传统文化、宗教观念、民族品格等。
三、情感与欲望的心理催化剂
气味是情感与欲望的一种心理催化剂。闻嗅这一行为包括闻嗅主体、气味、散发气味的闻嗅客体。气味在这一过程中以一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着闻嗅主体的心理反应。从生物学来看,“由于嗅觉系统与大脑情感区特有的联系,身体气味的侵入,将产生一种自然的本能反应,积极的或消极的反应,接受或放弃。嗅觉一下子就成了辨别讨人喜欢的人和不讨人喜欢的人、已知和未知的一种工具”②[法]阿尼克·勒盖莱:《气味》,黄忠荣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4页。。可以说,闻嗅主体对气味的反应既是一种本能反应,也是一种潜藏的心理映射,气味在某种程度上能加强闻嗅主体对气味客体的情感态度与心理认知。
气味在传递主体的心理映射时,有时比较隐秘,甚至连闻嗅主体都没有察觉。小说《血脉》的主人公多吉根据气味将他周围的人分为不同的人群。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气味。奶奶身上有藏人的气味,护士身上有医院那种干净而又奇怪的味道,村里的人都有汗水和牛羊肉、酥油、奶、盐的混合气味,自己身上有青草的味道,爷爷是一个没有气味的人,而从汉地来的章老师身上则有花的气味。显然,和其他气味相比,花的气味是一种特别的气味,不仅充满了芳香、柔美与令人愉悦的气息,还富有一种女性的气质,暗示了章老师在多吉心中不一样的地位。多吉对老师的情感也隐藏于闻嗅之中,多吉与老师告别的时候,作者两次书写多吉闻嗅章老师身上的气味。一次是章老师头发的气味,她刚洗完头,多吉闻到了老师身上那湿漉漉的头发的淡淡的芬芳。另一次是章老师手掌的气味,“老师湿润而馨香的手抚摸着我的头”。这两次气味描写都提到了湿度,带有湿度的气味比一般气味要浓烈,散播得也快,更能刺激嗅觉感官与传达情绪。从散发气味的客体来看,这两种气味都源自身体的一部分,女性的头发与手具有一定的隐私性,这意味着一种近距离的闻嗅,具有一定的暧昧性。因此,此处的气味书写暗含了多吉对章老师复杂而微妙的情感,除了对章老师即将离开的不舍,多吉对章老师还有其他的情感,这种情感甚至多吉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是一种晦涩暧昧又难以言说的情愫。
如果进一步探究气味中的暧昧情愫,这种情愫可追溯到性欲或性冲动。早在人们发现外激素与犁鼻器官之前,性行为与气味之间就已经建立了联系。以动物为例,很多低等动物,发生性行为必备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具备完整的嗅觉器官。对人类而言,气味与性行为之间也存在密切联系,“脑中与性冲动及性行为有关的区域,嗅脑都和其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结;此外,嗅觉器官、下视丘(控制情感表达及生殖器的膨胀)、脑下垂体及产生性激素的腺体间,彼此亦有非常密切的联结”①[美]范岸姆路、迪佛里斯:《嗅觉符码:记忆和欲望的语言》,洪慧娟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因此,特殊的气味能诱发性冲动,将受理性支配的人还原到动物性的本能阶段,嗅觉与爱欲共享着同一个大脑,一次闻嗅就能引诱一次欢愉。
《尘埃落定》中的罂粟花气味如同情欲的催化剂,与人物的性心理密切相关。从播种到结果,罂粟花的气味一直与欲望密切联结。罂粟刚播种时,种植罂粟的泥土就飘散着浓烈的芬芳。夹杂着泥土芬芳的罂粟花种子既富有生机,也酝酿着诱惑与爱欲。人们在地头里的小憩成了一场疯狂的游戏,女人们将男人推倒在地,男人们则追逐姑娘们剥去她们的衣裳。罂粟种子播下去以后,人们隔三岔五就来到田间观察种子发芽情况,它的魔力把人深深吸引住了。两三个月后,火红的罂粟开花了,花朵散发出浓烈的气味,二少爷与卓玛的情欲也不断膨胀。在两性关系中,闻嗅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暧昧的行为,气味则如同欲望的催化剂。卓玛身上的香气暗示着闻嗅者与被嗅者距离上的亲密,来自女性身体的气味被男性闻嗅时,女性容易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成为男性欲望建构的对象。罂粟花绽放时,如同一片火红的花海,高饱和度的色彩呼应了气味的浓烈。从植物学来看,花朵的气味夹杂着马匹腥臊的气味,罂粟花朵本身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而腥臊的气味又与动物的性器官相联系,此处的气味具有很强的性暗示。当罂粟成熟时,田野里飘满了醉人的气息,父亲和哥哥比往常有了更加旺盛的情欲。土司和三太太央宗多次在罂粟地里野合,土司杀了查查头人,为日后头人儿子的复仇与大儿子的死埋下了罪恶的种子。这时期的土司仿佛丧失了心智,完全被情欲支配。罂粟果实成熟后,炼制的鸦片散发着魔鬼般醉人的气息。翁波意西第一次嗅到土司宅子炼制鸦片的气味后,他就察觉到了屋子里的空气不对,觉得这种令人感到舒服同时又叫人头晕目眩的气味是比魔鬼的诱惑还要厉害的气味。鸦片的到来暗示了土司太太的悲剧,她吸上鸦片后愈发放纵堕落,最后吞食鸦片自尽。罂粟花从播种、开花到结果,气味由芬芳到强烈再到醉人,人物的情欲不断增强,膨胀到失控,气味充当了爱欲的催化剂,逐步将人物引向深渊。简言之,闻嗅主体对客体的气味反应透露了主体对客体的真实态度以及主体内心的隐秘情感。基于气味与性的先天生理联结,这种隐秘的情感又通常与主体的性心理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阿来小说中的气味展现了一个充满自然气息、具有西藏特色的地理空间。同时,阿来小说中的气味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学意义,个体或集体的独特气味,将人物或空间标识出来,造成个体或集体与所属社会空间的疏离。从闻嗅主客体的关系来看,气味与闻嗅主体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影响着闻嗅主体的情感态度与心理认知。小说不仅是时间的艺术也是空间的艺术,气味与空间的联结值得关注。阿来小说通过气味营造出多层次的空间感,不仅增强了气味的表达,还拓宽了小说的空间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