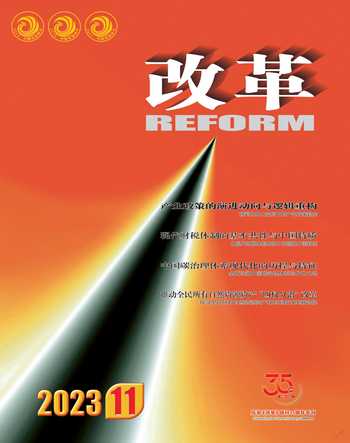世界大变局下的产业政策:演进动向与逻辑重构
摘 要:新一輪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大国竞争升级、地缘冲突加剧以及重大风险事件频发等因素交互叠加的世界大变局给各国产业转型发展和政策体系重塑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世界范围内产业政策随之再掀理论和实践热潮,其演进呈现一系列新动向新特点。各国加大产业政策实施力度,旨在促进前沿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并兼顾抢占前瞻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制高点、防范竞争对手、维护产业链安全等多元化目标。为此,应着力加强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竞争政策、贸易政策、环境规制、区域发展战略的机制性体系性协同,在产业政策选择性与功能性导向再平衡的演进逻辑下,塑造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新型关系,探寻产业政策的动态合理边界,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推动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产业政策;世界大变局;大国竞争;未来产业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3)11-0002-13
在经济学众多研究对象中,产业政策无疑是相当独特的领域,呈现关注度高、话题多、争议大的突出特点。然而,争议和质疑没能阻止各国政府大量采用产业政策[1]。抛开争议背后的价值观分异与长期缺位的充分学理依据,近年来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及其在各国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地位和活跃度大大提升,而在这之前的二十余年中,产业政策及相关研究经历了相当长的低谷期。直到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产业政策才又重新受到各国政府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重视,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实践和研究热潮[2]。
考察此轮产业政策的重点目标、作用对象及工具组合,可以发现,一方面,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颠覆性创新催生出未来产业群,同时,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加快带来了新的监管和治理需求,这些都给产业政策创新运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大国竞争升级、地缘冲突加剧、重大风险事件频发加快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和国际生产体系深度调整,各国产业政策呈现内向化战略导向不断凸显和防御性日益强化的特征。
产业政策实践的新动向给学术研究提出了新课题。若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那么有如下问题值得思考:首先,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的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激烈竞争,产业政策为何会保持强势地位,被主要经济体竞相施用?且不管长远来看政策失败和结构性扭曲是否必然会发生,决策者都对产业政策的实用性持强烈偏好。这其中除了基于比较优势塑造有为政府的出发点外,是否还存在与新兴产业发展更为契合的逻辑脉络和选择依据?其次,发达国家不再继续无视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产业政策的经验,转而高度重视其对不同类型产业成长所具有的动态战略价值,并主动投身产业政策实践之中。美国推出以《基础设施促进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以下简称“三大法案”)为代表、兼具进攻与防御功能的一揽子战略性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又将对全球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发展和竞争格局嬗变产生怎样的影响?最后,大国博弈正在改变产业政策的工具箱,在较短时间内世界各国如此密集地投放安全性导向增强、选择性显化、战略意图鲜明,甚至以打压竞争对手为主要动机,且与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不兼容的产业政策,对于产业政策而言,是时代性、阶段性、螺旋上升式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还是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演进方向?
上述问题折射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是其在全球产业发展环境和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反映。本文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出发,尝试揭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产业政策演进的特征事实、内在逻辑及其影响,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产业政策体系、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建议。
一、重回研究热点的产业政策:文献评述
回溯产业政策演进历程,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西方经济学界对以东亚为典型地区的产业政策实践并未表现出太多的理论“兴趣”。主流经济学家惯以“旁观者”的姿态对热衷于产业政策运用的政府给出种种批评,“在经济学家眼中,很少有比产业政策更容易引起自发反对的经济政策”,他们指出产业政策“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无效的,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则是有害的”[1],这显然源自主流经济学对市场机制的笃信以及对政府天然警惕和深刻疑虑的传统,带有明显的“二分法”判断倾向[3]。其中,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以补贴为主要工具的产业政策造成市场扭曲,进而导致要素配置效率受损。而在后发国家,即便产业政策的积极效果一再被赶超实绩所验证,学者们往往也只认可产业政策仅在特定阶段(如竞争前或产业化初期)或有限领域(新兴领域、幼稚产业等)的有效性。进入后赶超时期,随着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配置资源转型发展,那些曾经为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赢得机构肯定和国际赞誉的产业政策逐渐褪去了“光环”,即使在产业政策运用成效较为明显的日本,也一度出现了“全盘否定”产业政策的声音,认为日本高速增长期的产业政策实则没有发挥作用。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引发对产业政策的评价转向否定和批判,学术界将日本保守封闭的金融市场、居高不下的外国资本进入门槛、滞后低效的服务业以及缺乏竞争力的农业等结构性矛盾和不充分的开放经济归为政府推行产业政策并对选择性领域过度保护的后遗症[4]。
产业政策在中国同样遭遇过诸多质疑,多项研究显示产业政策特别是直接补贴对创新效率、公平竞争造成了不利影响[5-8],但负面评价也并未妨碍中国依然循着东亚地区的经验,将产业政策作为加快推进工业化、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后发赶超的核心工具。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一批日本学者的产业政策研究成果相继引入国内,不仅对中国产业政策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决策者起到了类似工作手册的作用。其中,小宫隆太郎对产业政策的分类,即从产业政策的对象来看,分为产业(间)结构政策和产业(内)组织政策;从产业政策的实施机制来看,分为间接诱导政策、直接限制政策和信息传递政策[9],至今对产业政策体系构建仍有参考价值。此后的数十年间,中国本土理论不断深化,增强了产业政策研究的学术性和独立性[10],进而带动了各级政府积极践行产业政策,并在处理复杂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与中国体制机制高度契合、逻辑相通的特色范式[11]。林毅夫与张维迎展开的“林张之辩”使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议成为舆论焦点。这场争辩非但未能弥合双方的立场分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围绕如何看待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深植于产业政策理论和实践之中的核心命题引发的矛盾对立。争论一方一再强调作为产业政策实施依据的市场失灵本身就是“伪命题”,政府干预产业发展必然会导致竞争受抑、政府失范的败局[12];另一方则基于新结构主义理论和比较优势视角,分析产业政策的时代演进,探讨产业政策的拓展方向,以推动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共赢的产业政策与环境规制协同[13]。
应该看到,上述争议和分歧的出现以及长期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很大程度上在于产业政策相关研究其实并未建立起能够形成共识的基础性理论框架。而随着产业政策再掀实践热潮,相关领域学术研究趋于活跃,近期国内外学者产出了一批更为系统、成熟的高质量成果。American Economic Review、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等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相继刊发了有关产业政策的研究成果[14-15]。其中,Criscuolo等[14]的研究发现,政府提供的最大投资补贴能够带来同比例的就业增长,但这种效果仅发生于中小企业,大企业则不存在就业提升情况,且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反映在投资扩大和就业促进方面而非改善全要素生产率。在继Lane[16]对韩国产业政策进行较为充分的经验分析之后,来自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学者以“产业政策的新经济学”为题,对产业政策执行效果开展了因果识别的定量分析,对产业政策效果提出了细致、情境性的理解。在此基础上,重新评估了中、日、韩三国不同时期产业政策的成效,总结了产业政策在治理理念、政策工具(不局限于补贴)以及“去工业化”现实新认识下的重塑进展,指出总体而言近期一系列学术论文对产业政策持更为积极的态度[1]。这一研究一改主流经济学对产业政策缺乏正面反馈的状态,对产业政策理论和实践给予了迄今为止可能是来自西方经济学界最为肯定的评价,这种转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学术界为发达国家政府或启用或“重拾”产业政策提供的理论注解和立场上的支持。
对于国内学者而言,中国日益丰富深化的产业政策实践为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研究素材和创新动力,对产业政策效果给出了趋于多元化的分析视角和具有肯定性倾向的判断[17]。余明桂等利用中央“五年规划”关于一般鼓励和重点鼓励产业的信息以及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专利数据,检验了中国产業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得到了产业政策能显著提高被鼓励行业中企业的发明专利数量,并且这种正向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的结论[18]。杨瑞龙、侯方宇则认为对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不应停留在其“是否有效”,真正的问题在于“产业政策什么时候有效”,即确定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质上看,产业政策可以视为政府与企业签订的不完全契约,剩余控制权分配有助于缓解不完全契约环境下的“敲竹杠”问题,是外部性内部化的途径,由此可以通过构建不完全契约模型找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边界和条件,从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19]。同时,尽管实证结果存在差异也有争议,但一些研究指出,比较优势有利于产业政策产生积极效果[20-21]。近年来,受中国高铁、5G等领域成功经验的启发,国内学者对产业政策的角色特别是政府与市场在后发赶超式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及两者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对典型案例的理论解析将中国产业政策的学术研究带入新维度新范式[22-25],拓展了理论深度和方法体系,提升了决策影响力。尤为值得肯定的是,这些研究不断尝试突破“二分法”的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有助于形成对产业政策及其效果的更加客观、全面、动态化的理解和把握。
国内外研究进展表明,产业政策的学术研究始终与其现实应用有着很高的贴合度,理论与实践相互加持、互为促动。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中国产业政策研究主题的涌现已经深度嵌入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之中[10]。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产业政策的新一轮实践热潮,学术研究的深化将延续上述特点和规律,持续关注、多视角研判产业政策演进方向、逻辑重构及其影响,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产业政策演进的新动向及多重影响
产业政策自出现之日起,似乎就被贴上了“后发赶超”目标定位的标签,在相当长时间内被视为后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专属”经济政策,即便这些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心开始由主导产业选择、出口促进、重点企业扶持转向解决结构性矛盾,相应的决策机制仍然很难抹去产业政策惯有的政府高介入性印记。然而,这种传统正在被新兴产业群体性涌现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形势所打破。随着发达国家纷纷“下场”,在作用对象、重点领域、工具运用、政策目标等多个实践维度上,产业政策演进呈现一系列新趋势新动向,由此产生的多重影响尚在生成、累积,并向前沿科技创新、未来产业培育、数字经济发展、气候治理与低碳转型、贸易秩序与地缘安全等诸多领域渐次释放。
(一)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成为产业政策实施的重点领域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重构全球创新版图,代表着前沿科技创新方向和经济新增长点的未来产业新赛道层出不穷,拓展了现代产业体系的内涵和外延。作为各国积极培育扶持的先导性产业群,未来产业成为大国竞相布局、激烈争夺的焦点领域。政府培育发展新科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则与产业政策的出发点有很高的契合度,其动机涵盖幼稚产业扶持、快速产业化、提高新技术市场接受度、规避国际竞争风险等方面。由于未来产业与前沿科技创新互动紧密,兼具前瞻性、战略性、引领性与幼稚性、不确定性的突出特征,且关乎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这类产业属于产业政策最适合施用的领域之一。同时,政策引导与政府资金投入能够撬动更多企业资本和社会资源,减少发展风险和不确定性,而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生命健康、空天探索等基础性前沿领域则需要政府较长时期在调动创新资源中发挥前置作用。基于未来产业突出的引领作用和战略地位,解决“市场失灵”、破解成长过程中“幼小化”发展难题是政府将产业政策作为核心工具扶持未来产业的理论依据,从这一意义上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然是相关领域产业政策的前提和基础[26]。
目前,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培育未来产业无一不在高频次地运用产业政策或类似的政策工具,锁定以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命健康、清洁能源、空天科技、先进材料等主攻方向,政策措施和激励机制具有较高相似度,涉及关键技术突破、技术路线识别、创业激励与产业化促进、要素适配、构建产业联盟、基础设施更新等产业生态塑造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提供长期、持续性资金支持,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建立国家创新平台,改革教育体系和加强人才培养等政策手段。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针对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的产业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干预意愿和选择性导向。如美国在2020—2023年连续4个财年中,明确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等未来产业作为国家科技发展的优选方向,列入研发预算优先领域备忘录;德国则在新能源、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关键领域,采取政府补贴援助甚至是接管重要企业的方式深度参与相关产业发展[27]。
中国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同样带有一定的选择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前瞻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各地方政府在其“十四五”规划中确立的未来产业也多有重叠,在有利于形成政策引导和投资预期的同时,再现重复布局、同质化发展的迹象。需要强调的是,有别于参与者甚众的“二次创新”,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颠覆性创新门槛高、风险大,对现有产业体系及在位企业的市场势力具有破坏性,这就决定了未来产业必然呈现大国角力、战略较量、分化加剧的竞争格局。未来产业发展水平取决于综合国力、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外部发展环境,是科学技术自身发展和科研组织方式变革的结果。因此,产业政策要突出未来产业的“未来”属性,强调选择性与战略性兼备,科学预判前沿创新失败、市场潜力释放不到位、赛道选择偏差、商业化模式创造效应受限等风险和障碍,推动未来产业高起点布局、高水平发展,为赢下新工业革命下科技和产业的全球竞赛提供要素、市场和制度保障。
(二)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对产业政策创新提出了新要求
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人类社会进步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和影响最为深远的趋势之一。《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的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中国、德国、日本、韩国五个世界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总量为31万亿美元,宽口径的数字经济规模占上述五国GDP的比重高达58%,较2016年提升约11个百分点。其中,产业数字化占五国数字经济比重达到86.4%。2016—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4.2%,是同期美、中、德、日、韩五国数字经济总体年均复合增速的1.6倍,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在实体部门,伴随着数据要素化、资产化进程的提速,数字技术作为新工业革命通用技术的角色趋于固化,数字化在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澎湃新动能的同时,数字资产确权、安全隐私保护、数据定价及其交易规则等重大技术和监管问题给产业政策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算力算法等关键技术和核心能力自我迭代非常快,政府监管和市场规范跟不上技术更新及场景拓展的节奏,而监管缺位和制度建设滞后进一步导致公共资源浪费或分配失衡,一些新型业务及其盈利模式借此游离于市场规范、商业法律和税收体系之外,成为监管“死角”,暴露出数字经济时代原有产业政策和监管机制的局限性。
从各国针对数字产业的政策导向来看,欧盟延续了相对保守的立场,秉持立法先行的理念,在风险预警、场景设限、私权保护、垄断防范等方面做足文章,试图将数字经济及相关产业发展带来的利益分化、安全隐患和制度冲击关进法律的“樊笼”,这种发展思路和政策取向虽然有利于形成较为平稳的竞争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信息技术領域上一轮专用资产投资生成的沉没成本和数字转型的社会成本,但也有可能抑制数字经济发展活力,导致新兴产业竞争力受损。相较之下,中国和美国采取了更为包容的态度。应该看到,数字经济发展既能对产业政策创新产生显著的倒逼效应,又能为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提供经验案例以及技术和数据支撑。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众多行业的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处于探索之中,特别是受制于要素匹配度、投入规模、转型理念等因素,传统行业数据要素积淀速度和数据资源整合路径难以适应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以及行业智能解决方案开发的趋势,加之数据垄断的危害暴露得不彻底,对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监管约束方式应设有较大的制度弹性和政策空间。政府不宜急于干预,而是要摸清规律,强化顶层设计和政策储备。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细分领域不断延展,有必要在进一步营造宽松有利政策氛围、保持数字部门发展活力的同时,加强市场化、法治化建设,创造全新的政策供给,着力克服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固有矛盾,完善监管体系,有效防范数据垄断,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翼齐飞,走上规范有序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三)绿色产业政策助力能源转型、产业低碳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
数字化和绿色化是全球产业转型发展两条清晰的主线。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确立碳中和目标,碳中和由生态学意义的概念逐渐演变为被各界接受的理念,再到上升为国家战略乃至全球目标和行动方案。然而,从近期全球实践来看,落实碳中和目标的难度似乎超出了各国政府和产业界的预期,阻力主要来自巨大的资金、技术缺口以及能源转型的高昂成本。一方面,应对疫情和通胀的财政支出挤占了绿色投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研究指出,2020年,在世界主要经济体推动的经济复苏项目中,仅有约18%属于绿色项目。另一方面,欧洲、北美遭遇能源供给短缺和价格急涨以及中国发生限电风波放大了可再生能源安全的全球性信任危机,引发了对于政府过度激进推动碳中和的争议,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升级大大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安全风险。高企的能源价格并未对传统油气开发投资构成强有力的刺激,相反,全球石油、电力等大型能源企业越来越关注低碳业务,资本市场对于脱碳项目投资表现出更高的热情。目前各国产业政策的力度显然未能消除市场主体因低碳技术研发和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而对绿色项目产生的顾虑。绿色转型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世界范围内绿色技术尚未实现系统性、整体性突破并获得稳定的技术经济性,导致技术减排的效果远未释放到位。
在大国竞争升级的背景下,鉴于应对气候变化具有强外部性特征,低碳部门因此成为各国仍抱有合作意愿、出现“竞合”局面为数不多的领域之一。中美两国发表《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反映出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的潜力。随着电力、钢铁、化工等传统工业领域减排空间缩小,结构减排的潜力势必转向服务业以及新兴的数字经济部门。全球能源转型和气候治理呼唤绿色产业政策。近期研究表明,政府对特定行业的扶持能够降低行业碳排放强度,在这方面地方政府的政策效果相对更为显著[28]。陈艳莹等则发现绿色声誉提升了企业股价,意味着资本市场能够与绿色产业政策形成有效联动,进而共同促进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29]。构建绿色产业政策体系应以理念创新为先导,加快结构纠偏,推动实现绿色低碳技术群体性突破,完善绿色发展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培育统一碳市场,建立碳交易机制,发展绿色物流,倡导绿色消费,带动企业“零碳”管理创新。
绿色是新型全球化的主基调,现阶段全球低碳治理仍难以摆脱重大国际议题推进的机制性障碍。实际上,相关领域的产业政策尚未促成基于碳中和共识的国际协同。各国围绕绿色转型的制度建设和政策实施,非但没能保障低碳领域的合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绿色转型的不确定性,原因在于各国产业政策在扶持本国低碳产业发展、扩大国内绿色产品市场的同时,还将很大一部分政策工具投入清洁能源市场竞争、绿色技术产品标准和贸易规则主导权争夺等方面,包括干预企业ESG评价体系构成。从主要国家的布局重点来看,就欧盟的偏好而言,担当全球气候领导者一直是其核心战略目标。欧盟于2020年5月通过为期7年1.1万亿欧元的中期预算提案和7 500亿欧元的欧洲复苏计划,启动了大规模绿色投资,意欲成为引领全球绿色经济发展新的风向标。作为绿色转型的先行者,欧盟低碳技术、排放标准以及绿色管理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在能源革命、循环经济、生态园区、无废城市等多个领域贡献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典范例。为进一步巩固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优势地位,欧盟在其传统强项上再施“重术”,充分发挥“建制”能力,率先抛出了碳边境调解机制,试图以“扎篱笆”的方式迫使他国接受其绿色标准和转型要求。而在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确立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虽然出现了“骗补”等政策漏洞,但以坚持创新驱动、提高市场接受度、释放消费潜力为导向的产业政策经由各级政府强力推行,与国内活跃的创业氛围、强大的制造能力、巨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充分结合并快速传导至消费端,迎来了市场爆发期,在较短时间内打造出世界第一规模的光伏、风电、大容量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市场。接连遭遇的“双反”倒逼中国企业将市场开拓重心由国际转向国内,反倒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出工业化新阶段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先发条件和后发能力。产业政策实绩反映在出口市场上,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出口“新三样”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2023年上半年,“新三样”合计出口增速达61.6%,拉动我国出口整体增长1.8个百分点,形成了地方经济新增长点和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储能技术等领域的“先手棋”以及技术、产能、市场的全方位发力对美国、日本、欧盟构成了强烈刺激。一方面,这些国家启动数轮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贸易救济手段,阻挠中国企业全球市场占有率持续攀升;另一方面,加大补贴力度,加紧发展本国绿色产业。其中,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对其国内清洁能源产业提供高达3 690亿美元的补贴,并设置了十分具体的国产化要求,这部以法律形式出现、以削减通胀为主题的文件,却几乎通篇都在展示美国政府的产业战略规划,且出台了一些歧视性规定。可以看出,美国现行产业政策对中国以往采取的选择性產业政策进行了某种对标。在这些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指导下,在部分领域美国有可能出现所谓产业“逆向”追赶的局面,引发绿色产业政策比拼升级,加剧全球低碳市场竞争,同时也为产业政策研究增添了新素材。
(四)产业政策运用出现泛化倾向
在此轮全球实践热潮下,产业政策被赋予突出的战略导向和多元化政策目标,其实施进程及结果正在对国际竞争格局和贸易秩序产生深远的多重影响。回顾过去十余年全球产业竞争的主要事件,应对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力全面崛起,产业政策似乎并不是美国的“首选”。如前所述,美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密集使用的仍是“301”调查配以“双反”为主的传统贸易救济措施。当美国意识到现行多边体系的机制和效率难以达到打压竞争对手的目的时,转而尝试依托新型FTA谈判,在全球贸易规则中导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所谓“三零”原则,试图绕过WTO突破现行贸易规则,协调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产业补贴的立场,在占据区域性开放制度和“道义”制高点的同时,形成对以中国为主的竞争对手“对等贸易”的要价。然而,此举同样没能阻挡中国产业赶超的步伐。鉴于绝对意义上的“三零”并不具备在世界范围内全方位实现的条件,美国等发达国家认识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领域,积极的产业政策和防御性的非关税壁垒很难全身而退,而阻挡不住中国追赶恰恰是因为那些以往被认定会导致市场扭曲的产业政策工具。美国的一项研究估算出中美之间在产业政策运用方面的差距。保守估计2019年中国各类产业政策的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73%,占比是韩国的2倍,以美元计的总支出则是美国的2倍,这种巨大反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刺激美国产业政策全面重启的依据之一。即便如此,在奥巴马执政时期,除了与创新政策有更深入的互动之外,产业政策在美国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和角色并未严重偏离传统范式,美国政府对产业组织的监管(或干预)主要通过竞争政策和市场规范实现,且其竞争政策和市场规范通常以法律的形式出现,与市场的兼容性更强[30]。随着大国竞争升级,美国政府推动再工业化,引导制造业回流,重塑供应链体系,其支持前沿创新、提振美国先进制造业、打压竞争对手的政策手段逐渐表现出异于传统的做法,特别是拜登政府推出的“三大法案”,使得产业政策的角色不断显化,大规模财政补贴及选择性工具运用不再“遮遮掩掩”,有悖于美国社会契约的“重/显”型产业政策,即政策资源投入规模大且与公平市场竞争原则高度不相容的产业政策开始登场,“当别国技术赶超威胁到美国战略性产业的领先位势时,常常被视为自由市场经济典范的美国则必然动用高强度产业政策、甚至非经济手段对竞争国加以抑制”[3,31]。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尽管一些正统经济学家嘲笑产业政策,但在美国几乎所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中,政府都在技术开发和转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报告特别强调作为美国主要竞争对手的中国实施了重点突出的产业战略,以成为制造强国和创新领袖,因而在现代背景下,美国政府应积极支持被认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技术开发[32]。可见,面对国际竞争格局嬗变与激烈的全球创新比拼,“优惠+威胁”模式强化了以产业政策应对大国竞争的政策逻辑,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紧密结合、深度捆绑的特征进一步增强,但也由此带来了产业政策应用泛化的隐忧。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国竞争下趋于泛化的产业政策体系中,基于安全导向和防御性动机,出现了一类与贸易政策相配合、以“封锁打压—反制—再反制”为手段的产业政策,此类产业政策可以称为“对峙型”产业政策。从其实践的特征事实来看,集成电路产业无疑是对峙型产业政策应用的典型领域,产业政策在该行业“攻守”格局中的角色十分“显眼”。一方面,备受“卡脖子”之痛促使中国各级政府在短时间内动员了大量资金和各类资源,为实现集成电路自主可靠安全的战略目标发起了强力投入。尽管产业大基金作用并不显著,但中国企业仍通过对产業链相对门槛较低环节的“点”突破,掌握了成熟制程技术,并形成了中低端芯片制造的体系性能力和快速扩大的市场份额;而作为“守成者”的美国等则动用了“重/显”型政策工具,在高端芯片制造及其上下游的光刻机等关键设备、EDA等明显优势领域步步为营,筑起“小院高墙”,对这一关系到国家工业体系和先进制造命脉的领域严防死守[33]。集成电路与以往成功赶超的产业大不相同,高门槛、快迭代等特征导致传统产业政策无用武之地,但这种“围城”式的产业竞争范式已然超过20世纪90年代美日半导体之争的激烈程度,在多轮“攻守”中,“技术民族主义”“资源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如影相随,“打压—反制”的反复深度博弈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工具的交互运用渗透到了产业链前端的资源环节及各个细分领域,进一步加剧了对分工交换、效率公平等市场化政策目标的偏移。
应该看到,对峙型产业政策绝非丧失理性之举,相反,这恰恰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产业政策演进的矛盾特征之一。产业政策泛化及对抗性增强的危害不容忽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突破涉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需要各国长期投入和共同努力,现阶段国际科技合作机制却在很多领域难以继续发挥作用。同时,安全和韧性偏好凸显给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带来了高昂成本,对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贸易秩序的冲击逐步显现。WTO的最新研究表明,尽管地缘关系收紧已持续数年,但全球化发生逆向演进的证据并不充分。然而,进入2023年,多项数据显示“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在提速,制造业回流和“同位共振”趋势得以强化。2023年第一季度,全球中间品贸易占货物贸易的比重降至48.5%,2023年上半年美国进口份额有所提升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分布在北美和欧洲,中国以及“中国+”范围内的东盟国家在美国进口的份额下降。墨西哥作为近岸外包的主要受益国之一,成为中国间接对美贸易的重要中介,但由于《通胀削减法案》的补贴条款对原产中国的零部件限制十分明确且严苛,墨西哥作为中国对美间接贸易“跳板”的作用有限[34]。以“三大法案”为代表的产业政策及其主要手段与现行多边体制的基本宗旨并不兼容,反映出美国基本上放弃了在WTO等多边体制下寻求维护其产业链安全及经济利益的常规做法,而是通过加强产业政策运用,重新搭建美国主导可控的产业链,这将进一步损害多边体制的权威性,给WTO改革带来阻碍和不确定性。
三、多元化目标与产业政策逻辑重构
不可否认,无论是培育未来产业、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还是打压竞争对手、遏制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后发赶超、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性,当下各国推出的产业政策难免带有较为明显的“选择性”。一直以来,产业政策的选择性或者选择性产业政策是产业政策饱受诟病的“槽点”[35]。诸竹君等[36]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具有的“选择性”特征会引致“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并将其视为企业加成率下降的重要原因。钱雪松等的研究采用自然实验的方法,验证了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得到了负面结果[37]。但现实是世界范围内选择性产业政策似乎又出现了“回归”倾向,主要经济体出于安全、韧性、防御等功能和需要,均或主动或被动地强化了产业政策的选择性,这是否意味着产业政策正在发生逻辑反转和价值逆变?产业政策体系又应遵循怎样的逻辑,完成在大变局下的重构与再造,从而兼顾发展与安全的需要?
(一)产业政策的选择性抑或功能性
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学术界,有关选择性产业政策还是功能性产业政策的争议似乎已早有定论,对于产业政策进行选择性的纠偏,进而确立功能性导向成为产业政策调整、完善、改革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方向[38]。就地方性产业政策而言,以“五年规划”为政策文本的代表性文本往往被视为集中反映地方政府选择产业发展方向的典型实践,基于这类文本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产业规模偏好总体上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产业规模偏好通过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抑制市场竞争、阻碍企业进入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通过促进集聚效应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虽然产业规模偏好带来了一定的效率损失,但也有效增加了企业层面的投资、销售收入和税收[39]。这一点倒并不难以理解,选择性产业政策通过释放政策信号,尽管损害了投资效率,但在短期内吸引大量不同类型的资本进入政府意图扶持发展的领域,能够快速形成产能乃至上下游配套的能力,其对消费侧的引导也有助于市场接纳新技术新产品。实际上,选择性产业政策有效的条件是在不严重破坏市场机制的前提下,与产业竞争战略等决定产业长期发展绩效的战略性因素形成正向互补[24]。从这一意义上看,当下产业政策选择性增强不过是多了一重在市场扭曲之痛与错失新兴产业发展机遇、放任潜在竞争对手追赶、确保产业链自主安全之间的取舍,在某种意义上实则也可以看作一种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收放。
归根结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产业政策选择性的特征事实是其实用性的集中表现,甚至可以被视为产业政策天然属性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际环境下的反映。需要强调的是,认可选择性的现实存在并不等于否定多年以来学术界推动产业政策功能化的持续努力,恰恰是对功能性产业政策和竞争中性原则的不懈探索在理论上为产业政策的市场化改革找到了方向[40],在实践上也大大丰富了中国产业政策体系的工具箱。研究发现,尽管中国重点产业政策整体上显著抑制了相应行业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完善以及要素市场扭曲的改善仍有助于缓解重点产业政策的负面作用[41]。由于产业上下游市场化改革进程存在差异,现实政策组合“下游市场化改革+上游产业政策”对经济产出的促进作用最大,这为理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管理相互配合提供了新视角[42],也是如何实现选择性产业政策与功能性产业政策适配的力证。
总体而言,中国产业政策演进基本上沿着两条逻辑线索展开:一条逻辑线索是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另一条是经济快速发展中产业发展、产业结构转换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变化,前者对于产业政策取向、政策工具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而后者则会影响产业政策的重点任务。由此可见,选择性在某种程度上显化的倾向是前一条逻辑线索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延伸。因此,在不确定性增大的外部环境下,要从“发展中的问题”与“螺旋式”上升规律的角度看待产业政策取向的演变,通过寻求选择性与功能性的再平衡,完成產业政策的逻辑重构。
(二)多元目标下产业政策的合理边界与政策协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产业政策正在被赋予新的目标和使命,后发赶超和结构优化等传统目标向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拓展。多元化目标给各级政府扩充产业政策提出了新需求,然而,尽管世界范围内此轮产业政策实践确有泛化倾向,但这仅仅意味着产业政策的合理边界具备了动态调整的必要性,并不是滥用产业政策的借口。
一方面,边界是否合理直接决定了政策的有效性,而确定产业政策合理边界的首要任务是给政府行为及其决策机制划定边界。以往产业政策争论的焦点虽然落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但忽视了“政府与市场”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更好地兼容。一般情况下,与市场不相容的政府,没有意愿朝着建设性方向改革完善产业政策体系。与市场不兼容的政府越是“有为”,对市场机制的破坏性越强,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越差。因此,产业政策的合理边界应以在法律上对有为产业政策作出规范为前提,而非对任何产业政策都采取立法形式以体现其权威性。相反,对未来产业等不确定性大的领域,在产业政策上不宜急于推出硬度较高的法规性治理措施,而应给予创新活动及市场主体足够空间和耐心,充分体现战略宽度和包容性。
另一方面,服务于多元化目标的产业政策要加强与财税金融、投资贸易、竞争政策、绿色发展等战略、政策及市场规范的协同,更好地兼顾技术与要素、发展空间与战略纵深、产能释放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需要,其中重点要放在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环境规制、竞争政策、区域发展战略的协同上。政策协同的必要性不仅仅局限于丰富政策工具,而是更利于在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打出“组合拳”。当新兴技术产业在国家间具有直接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而产业发展又需要市场主体形成一致行动时,则产业竞争战略就是重要的[10]。政策协同需要体系性的能力和更高质量、高层级的制度供给作支撑,从而在化解外部发展风险的同时,助推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切换,塑造新质生产力。
四、结论与展望
虽然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不成功,但是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必然不成功[43]。如果放在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盛行时期,这一观点可能显得夸张和突兀,但在当下充满变数的全球格局和国际关系中,却与各国产业政策制定实施的出发点和真实动机颇为契合,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产业政策研究和实践的波动事实。总体来看,伴随着经济的周期性变化,产业发展环境呈现较大的差异性,导致世界范围内产业政策演进在热潮与遇冷之间延宕。从这一规律出发,今天被推到重要地位的产业政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结果,在新工业革命初期,主要经济体对科技创新投入巨大,势必强化重大研发及其产业化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将高附加值、最前沿的创新活动控制在本土。在此时期,产业政策理应是显化、密集、内向化和带有一定对抗性的。而当主导产业逐步进入以成本驱动的规模扩张阶段时,促进竞争、提升效率、破除要素流动障碍便会再度成为产业政策的主基调,在实用性导向下,随之而来的可能是选择性产业政策的退出,这符合国际竞争格局变化和产业政策演进的规律,也是此轮产业政策逻辑重构的基本脉络。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产业政策在不少领域有过成功实践,在钢铁、液晶显示器、新能源、LED照明以及高铁、5G、盾构机等行业,先后填补技术空白,实现进口替代,完成了后发赶超,并在产业政策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相对明晰的作用机制:政府组织选择产业方向、技术路线和市场主体→重点补贴、迅速扩大规模→产能过剩、产品价格下降→其他竞争者因收益过低而退出。同时,“中国实践对产业政策研究的需求与中国经济学学术供给能力一道, 共同塑造了中国产业政策的创新发展”。在充满了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全球生产体系和竞争格局中,内向化、安全性成为大国未来产业研发和产业链供应链战略的导向,产业政策的角色显化,主要工业国“重拾”或者正在“找寻”产业政策,工具选用也不再顾忌多边体制的约束。尽管如此,着眼于长远,仍应在与市场机制兼容前提下,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开放与安全的关系,探索产业政策的合理边界,寻求选择性产业政策与功能性产业政策的动态平衡,在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同时,为产业政策理论创新作出大国的时代贡献。 [Reform]
参考文献
[1]JUHáSZ R, LANE R, RODRIK D. The new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policy[Z].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31538, August, 2003.
[2]江飞涛,沈梓鑫.全球产业政策实践与研究的新进展——一个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的评述[J].财经问题研究,2019(10):3-10.
[3]贺俊.制度逻辑、竞争位势与政府干预:美国产业政策的分解与合成[J].国际经济评论,2023(4):70-92.
[4]方晓霞,杨丹辉,李晓华.日本应对工业4.0:竞争优势重构与产业政策的角色[J].经济管理,2015(11):20-31.
[5]黎文靖,郑曼妮.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6(4):60-73.
[6]钱学锋,张洁,毛海涛.垂直结构、资源误置与产业政策[J].经济研究,2019(2):54-67.
[7]郑世林,张果果.制造业发展战略提升企业创新的路径分析——来自十大重点领域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2(9):155-173.
[8]蒋冠宏.中国产业政策的均衡效应分析——基于政府补贴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2(6):98-116.
[9]小宫隆太郎,奥野正宽,铃村幸太郎.日本的产业政策[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10] 黄群慧,贺俊.赶超后期的产业发展模式与产业政策范式[J].经济学动态,2023(8):3-18.
[11] 江飞涛,等.理解中国产业政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
[12] 张维迎.产业政策争论背后的经济学问题[J].学术界,2017(2):28-32.
[13] 林毅夫,蔡嘉瑶,夏俊杰.比较优势产业政策与企业减排: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J].改革,2023(5):1-17.
[14] CRISCUOLO C, MARTIN R,OVERMAN H G, et al. Some causal effects of an industrial polic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109(1):48-85.
[15] LIU E. Industrial policy in production network[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9,134(4):1883-1948.
[16] LANE N. Manufacturing revolutions: Industrial poli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South Korea[Z]. CSAE Working Paper Series, 2022.
[17] 韩永辉,黄亮雄,王贤彬.产业政策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J].经济研究,2017(8):33-48.
[18] 余明桂,范蕊,钟慧洁.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16(12):5-22.
[19] 杨瑞龙,侯方宇.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基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J].管理世界,2019(10):82-94.
[20] 张鹏杨,徐佳君,刘会政.产业政策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有效性研究——基于出口加工区的准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19(5):76-95.
[21] 赵婷,陈钊.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效果:区域差异及制度成因[J].经济学(季刊),2020(3):777-796.
[22] 贺俊,吕铁,黄阳华,等.技术赶超的激励结构与能力积累:中国高铁经验及其政策启示[J].管理世界,2018(10):191-207.
[23] 吕铁,贺俊.政府干预何以有效:对中国高铁技术赶超的调查研究[J].管理世界,2019(9):152-163.
[24] 黄阳华,吕铁.深化体制改革中的产业创新体系演进——以中国高铁技术赶超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20(5):65-85.
[25] 贺俊.新兴技术产业赶超中的政府作用:产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22(11):105-124.
[26] 杨丹辉.未来产业发展与政策体系构建[J].经济纵横,2022(11):33-44.
[27]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未来产业:开辟经济发展新领域新赛道[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23.
[28] 余壮雄,陈婕,董洁妙.通往低碳经济之路:产业规划的视角[J].经济研究,2020(5):116-132.
[29] 陈艳莹,于千惠,刘经珂.绿色产业政策能与资本市场有效“联动”吗——来自绿色工厂评定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22(12):89-107.
[30] 杨丹辉.精准与兼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下的产业政策创新[J].区域经济评论,2017(4):7-9.
[31]薛澜,魏少军,李燕,等.美国《芯片与科学法》及其影响分析[J].國际经济评论,2022(6):9-44.
[32]SHIVAKUMAR S. Priming the innovation system: A new age of U.S. industrial policy[R/OL].(2023-11-16)[2023-11-17]. https://features.csis.org/priming-the-innovation-system/.
[33] 渠慎宁,杨丹辉,兰明昊.高端芯片制造存在“小院高墙”吗——理论解析与中国突破路径模拟[J].中国工业经济,2023(6):62-80.
[34] 牛播坤,黄雄.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新变局[R/OL].(2023-10-31)[2023-11-05].https://www.163.com/dy/article/IIC8SENJ0519G72C.html
[35] 叶光亮,程龙,张晖.竞争政策强化及产业政策转型影响市场效率的机理研究——兼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J].中国工业经济,2022(1):74-92.
[36] 诸竹君,宋学印,张胜利,等.产业政策、创新行为与企业加成率——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研究[J].金融研究,2021(6):59-75.
[37] 钱雪松,康瑾,唐英伦,等.产业政策、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009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8):42-59.
[38] 江飛涛,李晓萍.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产业政策演进与发展——兼论中国产业政策体系的转型[J].管理世界,2018(10):73-85.
[39] 王海成,张伟豪,夏紫莹.产业规模偏好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省级政府五年规划文本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3(5):153-171.
[40] 刘戒骄.竞争中性的理论脉络与实践逻辑[J].中国工业经济,2019(6):5-21.
[41] 张莉,朱光顺,李世刚,等.市场环境、重点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差异[J].管理世界,2019(3):114-126.
[42] 林晨,陈荣杰,徐向宇.渐进式市场化改革、产业政策与经济增长——基于产业链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3(4):42-59.
[43] 林毅夫.产业政策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148-153.
Industrial Policy under World's Profound Changes: Evolutionary Trends and Logical Reconstruction
YANG Dan-hui
Abstract: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ogether with the escalation of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geopolitical conflicts, and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risk events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reshaping of policy systems in various countries. Along with this, industrial policies worldwide have sparked a wav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with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policies showing a series of new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Governments are increasing their efforts to implement industrial policies, aiming to promote cutting-ed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accelerate industrial digital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while also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iversified goals of seizing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forward-looking glob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reventing competitors, and enhancing industrial chain security. To this end, it calls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al and systematic coordin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innovation policies, competition policies, trade polici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long with the logistics of rebalancing the selective and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ies,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mising government and effective market should be shaped by exploring the dynamic and reasonable boundaries of industrial policies, so as to better serve the integrity, progressiveness and security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dustrial policy; profound change in the world;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industry of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