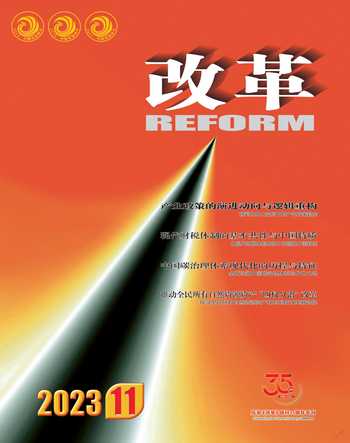论构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
卢现祥
摘 要:大科学时代的科学研究活动具有大投资、大规模、多学科、参与人员或群体数量庞大等特征,需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保障科研项目的持续运转。大科学时代科技自立自强是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关键。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主要目标是实施“大科学工程”和“大科学计划”,并解决国家科技创新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前沿及重大科技创新问题。构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要实现四大转变,即大科学组织的国家模式要从中心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转向网络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国家大科学组织的约束机制要从控制约束转向契约约束;国家大科学组织的治理机制要从科技管理转向科技治理;国家大科学组织的协同机制要从产学研的自上而下的产学研协同转向自下而上的产学研协同。
关键词:大科学时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3)11-0015-13
大科学时代的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建立在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的基础之上。当前,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创新活跃期和产业变革期。我国只有全力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制高点,才有可能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跃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有利于实现科技制高点上的重大突破,从而带动一系列相关领域的创新发展。构建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必须尊重科研规律,改革科研组织管理模式,充分发挥体系化建制化优势。构建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涉及组织的国家模式、约束机制、治理机制、协同机制四个方面的转变。
一、大科学时代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组织模式的关系
“大科学”概念是由美国物理学家温伯格在1961年首次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大科学是规模很大的一类科学研究项目。接着,普赖斯把“二战”之前开展的科学研究称为“小科学”,“二战”后则迈入大科学时代。“小科学”主要通过科层管理模式进行研究活动,参与人员较少。而大科学时代的科学研究活动通过系统化的组织模式来保证科研项目的持续运转,需要顶层谋划、分工明确,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协同,需要大投资、大规模、多学科,参与人员数量庞大。“大科学”主要分为“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两类,并最终演化形成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两种组织模式。
2016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指出:“我们将力争在重大项目、重点方向率先突破,积极牵头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大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纳入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科技自立自强的“高水平”应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突出战略性、长远性,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具有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定力与毅力;二是突出原始性、基础性,即应当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前沿科技研发、原始创新等方面保持领先,不断积累高质量发展的动能与势能;三是突出竞争性、安全性,即应当在全球范围形成科学技术话语权和规则标准主导权,始终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韧性稳定与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五项重点任务:一是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二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三是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四是构建开放创新生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五是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建设全球人才高地[2]。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关键。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撰写的政策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成为“二战”后阐述科技自立自强对国家实力至关重要的经典文献。这个报告的根本意义在于最终促使美国将战时科学体制转变为和平时期的常规科学体制,创立了国家资助科研模式,并深刻影响了一些国家的科技政策。范内瓦·布什的“范式”在过去数十年间超越了国界成为各国组织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2020年,在意识到中国技术迅速发展并步入全球技术发展第一阵营之后,美国政府又发布了《无尽的前沿:未来75年的科学》报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也发布了《技术大较量:中国与美国》报告,这些报告不仅将中国定位为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强大竞争者,而且对中美两国的科学技术投入、技术发展模式和科学发展水平作出了全面评估,最终给出了美国应对中国科技竞争、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策略。2022年7月,欧盟委员会出台的新版《欧洲创新议程》明确指出,深科技创新(Deep Tech Innovation)是指植根于前沿科技和工程,并高度融合物理、生物、数字领域技术突破的创新成果,在面对全球挑战时有可能提出革命性解决方案,变革商业和市场格局,推动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创新;深科技产业即应用深科技创新成果的新兴行业,包括人工智能、高新材料、生物科技、光子学和电子学、无人机和机器人学等行业。
大科学时代要求对基础研究活动进行有组织的科研攻关。从科技创新与组织模式的关系来看,发达国家在制度/组织框架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这一制度/组织框架能够攫取整合分散知识所固有的潜在生产率,而分散知识是在一个专业化的世界中有效率的生产所必需的[3]。从深层次看,组织模式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创新不是发明,而是以技术为基础的“条件”的新组合。创新必须抓住市场需求,创新只有满足和扩大市场需求,才能成功形成创新的良性循环。钱德勒认为,组织创新是“技术”进步的组成部分。新技术提供的生产率潜力只有通过组织创新才能变成现實的生产率。施蒂格勒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组织的效率可能与技术变迁同等重要。组织模式是一种社会技术,即社会制度创造行为模式的方法或机制,而生产技术则是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方法,即所谓的技术创新。生产技术取决于社会技术,后者可以为前者提供激励机制,这也就意味着组织模式和技术创新之间存在互动机制。美国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欧盟的“伽利略计划”等均是实现了集科学、军事、工业于一体的有组织大科学计划。这种有组织的大科学计划以国家行为推动科技研究选题、研究工具手段、研究协同创新及组织模式体现国家意志,凝聚国家力量。
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构建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19世纪末科学步入国家化发展的轨道,日本、德国、英国先后设立国家研究机构或科学管理部门。国家科学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科学发展的模式,出现了通常所谓的“大科学”。20世纪30年代,默顿首次提出,科学是一种体制化了的社会制度。大科学发展与国家发展模式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发展型国家模式源自美国政治学者查默斯·约翰逊所提出的发展型国家的概念,后续学者在查默斯·约翰逊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发展型国家理论的研究范式。发展型国家模式以“二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奇迹为研究基础,系统分析了日本与战后两大阵营经济发展模式(英美市场经济和苏联计划经济)的区别,研究发现,相较于英美模式和苏联模式,日本模式的独特性体现在以国家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由政府制定创新目标和产业规划,积极实施各类产业政策,集中资源加强对优先产业的培育和扶持,在短期内迅速实现产业规模化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查默斯·约翰逊将日本的这一独特模式总结为发展型国家理论,并认为要实现该发展模式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管理能力突出的官僚体制;二是具有安全阀功能的政治体制;三是具有明确的经济领航计划;四是依据市场规律进行行政干预。事实上,在查默斯·约翰逊之前,也有学者认识到了经济追赶阶段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发现,为实现经济追赶,缩小与先进工业强国之间的技术差距,需要国家动用行政权力集中资源进行重点产业扶持。但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会随着技术差距的变化而有所侧重,发展型国家与先进技术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国家在经济追赶中扮演的角色越重要,这就是中心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当技术差距逐渐缩小、经济追赶任务基本实现时,市场力量会超越国家力量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网络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埃德蒙·费尔普斯在研究人类创新史中发现了两种创新组织模式,即自上而下的创新组织模式和自下而上的创新组织模式[4]。自下而上的创新组织模式比自上而下的创新组织模式更有效,这是因为,自下而上的创新组织模式发挥了更多人的创造性。创新组织模式实质是科技资源配置与制度结合的问题,它涉及激励机制与创新的关系。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产物。近些年来,随着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的提升,我国在零部件、元器件等中间品方面的创新需求和能力明显增强。从以集成创新为主向集成创新与中间品创新并重的模式转换,意味着产品特征、技术特征以及知识、产业、市场、技术获取方式等方面的明显变化,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以及组织方式都需要作出相应调整。技术成功并不必然意味着产品成功,成功地开发出产品也不等于在市场竞争中产品一定会取得成功,这是技术逻辑与市场逻辑的一个重要区别。要解决好这一问题,一方面,在以市场竞争为导向的技术研发中,要建立稳定持续、多元化的长效投入机制,切实落实攻关单位的主体责任和权利,更好支持自主创新产品的早期市场开拓,以一揽子政策解决好关键核心技术的“有无”问题,更多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来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及其产品的“好用”问题。要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让竞争倒逼企业研发创新,让企业从研发创新中获益。另一方面,政府要更多支持体现国家重大需求以及企业不能做、不愿做的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前沿技术研发。发挥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协调各方面力量集中攻关,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创新科研组织方式,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国家科研机构具有学科领域全、创新链条全、保障体系全的体系化优势,具有成建制、有组织的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是最有基础和条件承担抢占科技制高点攻坚任务的战略科技力量。必須坚持系统观念,促进政策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相融合。要积极争取承担和组织实施一批全局性战略性重大科技任务,以国家战略需求和重大科学问题为牵引,加快调整优化科研力量整体布局,打破学科、领域、团队壁垒,把相关研究机构组织起来,把创新链上下游的研究力量贯通起来,加快形成分工明确、协同高效,分可独立作战、聚可合力攻关的大团队科研攻坚模式。
二、大科学组织的国家模式:从中心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转向网络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是一种网络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长期以来,我国在科技创新上主要采用了中心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这种模式以国家(政府)为中心,科学技术创新方向由国家决定,国家根据动态效率前沿选定目标产业并配置资源,通过对目标产业的大规模投资、技术引进和技术改良来培育产业竞争力,从而实现产业发展。然而,随着技术从成熟阶段(产业模仿阶段)转向流动阶段(产业创新阶段),中心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难以满足新阶段创新发展的需要,政企互动机制也应该从“中心化”转向“网络化”,即网络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当一国想要突破现有的成熟产业技术体系、取得颠覆性创新成果、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步入制造强国和更高价值链水平时,科技创新的组织模式便发生了本质变化。前沿技术的发展方向难以被准确预测,创新的相关要素和知识也处于多种参与指向性的互动机制中,使得创新活动的主体必须进行自身组织模式的调整,参与到复杂的知识和信息交换过程中,并不断地适应新的外部环境,构建有利于创新的互动组织机制;需要通过各创新主体自主实验、独立决策来开展创新活动,市场力量由此将占据主导地位。
从中心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转向网络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最重要的是政府角色实现两大转变:一是政府的角色应该从“领航员”转变为“乐队指挥”,由于创新方向的不可预测性,政府不再通过行政指令来干预创新主体的决策,但需要在市场秩序、产权保护等方面做好保障,充当整个创新系统的有效构建者和协调者。二是政府的角色从挑选“少数赢家”的创新资源分配者转变为市场规则的维护者,从占据创新中心地位的主导者转变为与分散创新主体建立网络化互动关系的协调者。在政府职能上,应通过深化改革使科技管理理念和政府职能满足新形势下科技自立自强的需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当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前沿科技研发、原始创新等方面保持领先,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和多部门、多主体的参与,需要借助超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团队协作才能完成。面对如此复杂的创新体系,需要有足够的政治权威用以调度各类资源、统筹各方力量实现系统的平稳高效运行,而这一角色只能由政府来承担。尤其当出于国家战略考虑执行重大任务或重大技术攻关时,现有的运行体制可能难以满足重大任务要求,因而需要借助于举国体制,超越现行组织体系和运行体制,由中央成立特殊机构用以协调跨部门决策来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5]。从中心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转向网络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也即从自上而下的创新组织模式转向自下而上的创新组织模式。
从横向来看,网络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建立在许多网络化的发展型地区模式基础之上。像美国硅谷这样以网络为基础的工业体系中,公司是为了不断适应市场和技术的迅速变化而加以组织的。该体系下企业的分散格局鼓励企业通过技能、技术和资本的自发重组谋求多种技术发展机遇,其生产网络促进了集体学习技术的过程。硅谷的以网络为基础的支持体系支持了分散试验和学习的过程,从而培育起成功适应变化的能力[6]。在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于2011年被首次提出,此后成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有力支撑。科技创新体系改革是我国2023年党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改革前的国家顶层科技创新体系是“集中模式”,改革后国家顶层科技创新体系是“多主体整合模式”[7]。
从纵向来看,网络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在科技自立自强中要解决“谁来组织”中的三大问题:
一是科技自立自强要解决国家研究与试验发展(R&D)预算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问题。美国的R&D预算是自下而上的,政府先期出台科技政策、科技规划,确定优先发展的领域,各联邦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国家发展目标编制本部门的R&D预算。不同的联邦机构对于本领域和研究方向最了解,具备相应的基础条件,其部门科技计划也有一定的连贯性和延续性,在政府预算中还规定一个联邦机构的研发项目通常只能填写一项功能,需求单一、功能单一,从而确保了R&D预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R&D投入在美国的财政支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各级行政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并以法律制度作为保障[8]。在我国,科学技术部负责制定国家层面各科学领域的科技政策和规划,科学技术部在编制R&D预算时会提前征求研究机构、高校和企业的意见,但这种征求缺乏法律、法规的约束,也没有监督和审核机制,只是形式上的。国家层面的R&D经费主要由少数部门管理。就研发经费管理的类型而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经费全部用于基础研究;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研发经费主要用于重大项目;农业农村部则将经费主要用于应用研究。近些年来,我国主要通过科技体制改革解决科技资源配置中的“条块分割”以及科技资源高度分散问题。下一步,我国要深化科技资源配置体制改革,着力改变科技资源平均配置、惯性配置的倾向,推动科技资源向抢占科技制高点任务集聚,向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机构和团队集聚,向挑战最前沿科学问题和攻克最关键核心技术的科学家集聚。
二是科技自立自强要协同好经济发展水平与研发经费增长之间的关系。2022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达30 782.9亿元,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比2021年增长10.1%,自“十三五”以来已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9]。从总量上看,我国的研发经费投入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从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占某组织或地区当期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我国研发投入强度继续提升,2022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达2.5%。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位于G7中游位置,并进一步接近日本和德国水平。科技创新是关乎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而研发经费的投入量和强度是衡量创新发展的重要指标。经济发展水平与研发经费投入增长的关系是有规律的:一是研发投入强度的发展轨迹是一条类S曲线,类S曲线第一个拐点大约是研发投入强度为1%时,第二个拐点大约为2.5%;二是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发展轨迹也呈现一条类S曲线,其第一个拐点大约是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为7%~8%,第二个拐点大约为15%[10]。我国的研发投入强度已达到第二个拐点,但基础研究投入强度才刚超过6%,还没有达到第一个拐点。因此,我国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必须提高基础研究投入强度。
三是科技自立自强要协同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之间的关系,构建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2021年,中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仅占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的6.5%,而这一指标数据在美国为17.2%,在法国更是高达25%。从经费投入来源结构看,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约90%以上来自中央财政。从2000—2020年研发经费投入结构来看,美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平均占到研发经费投入的17.2%,而中国这个指标数据仅为5.2%;再考虑到美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约是中国的一倍,而中国全时当量科研人员数量约是美国的1.5倍,中国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力度的必要性更加凸显[11]。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的重大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技术方面,而不是科学方面,即使是在科学方面的重大成就也与大科学装置有关。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问题,根源在于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为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产业技术难题而组织开展好基础研究,已经成为一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12]。现阶段,我国研发投入强度偏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不相匹配。政府公共投资滞后致使其引导作用逐渐弱化,而政府资金重点支持的科研机构和高校科研布局更偏重创新链条后端,加之企业作为研发经费最大的来源和执行部门,对基础研究参与程度严重不足,致使我国研发经费配置结构呈现“重试验发展、轻基础研究”的失衡状态[10]。根据过去20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18%的增速计算,未来5年要使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达到10%,从而更接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需要2.36万亿元的资金投入。除了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外,还要通过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的创新解决我国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顶尖战略科学家较少、科技资源配置方式低效、评价激励机制不完善、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有待提升等问题。
三、国家大科学组织的约束机制:从控制约束到契约约束
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可将创新组织分为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约束组织模式与自下而上的契约型约束组织模式。契约型约束类似于康芒斯讲的买卖交易,而控制型约束类似于康芒斯讲的配额交易。控制型约束是命令,而契约型约束是法律。在控制型约束下,受命者没有自己的自由选择权。对于一项法律,每个具体行动的目的由行为人自己设定,行动的知识也仅仅由行为者支配。法律之所以没有确定行为者的目的和知识,是因为法律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的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取代命令能更有效地保障个人的自由,也更有利于创新[13]。
我国自上而下的创新组织模式主要由政府主导、行政控制及国有企业构成。这方面的代表机构包括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它们的决策模式大都与大行政系统的科层制模式相配套。我国科研体制中还有大量的高校和企业,其中具备较强科研实力和影响科技决策能力的佼佼者,基本上都是公立大学和国有企业。在我国科研经费的投入、科研管理和决策过程中,政府机构拥有绝对的优势。自上而下的创新组织模式在我国技术追赶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在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中必须改革完善我国创新组织模式。
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约束创新组织模式与自下而上的契约型约束创新组织模式在创新来源上存在本质区别,前者着眼于政府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并且主要是通过命令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行政指令和行政目标的实施具有计划性、强制性特征,导致创新目标或产业项目在实施之初便“计划”了创新步骤,这种“计划”创新不利于发挥科研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不利于产出独创性的成果。创新方向集中化的选择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因为创新活动具有不可预知性,特别是前沿技术创新,更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特征,这一特质决定了创新方向需要分散决策。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约束组织模式具有集中创新资源的本质特征,在技术追赶阶段和方向明确时,能够带来规模优势,进而加速技术的进步,但在创新前沿领域这一优势反而成为集聚风险的助推器。当企业家不再直面创新风险,而是遵循着程序合规、按计划行事的创新法则时,创新活动便不再是颠覆性技术进步,创新成果也难以驱动科技发展。而自下而上的契约型约束创新组织模式着眼于市场的需求,更偏重于市场机制本身的竞争调节和内在激励,更强调制度结构(法律和契约)对创新的激励作用。虽然在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上,自下而上的契约型约束创新组织模式更优,但政府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作用并非体现于对创新资源的分配,而是法治和市场环境的营造,政府在法治环境和产权保护领域对创新的积极作用远大于其本身对创新方向的选择和创新资源的配置。
从政府对创新资源的分配来看,自上而下的控制型创新组织模式的直接分配会带来以下问题:一方面,这种组织模式依托专家信息和专家知识所作出的创新资源分配难以了解市场的真实需求。专家信息与专家知识往往通过“挑选赢家”来进行创新资源分配,这一模式使得作为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主体——中小企业在面临创新资源分配时具有天然劣势,可能带来资源的错配。另一方面,这种组织模式存在较为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究其缘由,创新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当技术发展到前沿领域时,很难从现有的创新模式中找到一般性规律和可资借鉴的经验,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便失去了信息决策依据,这使得上级无法对下级给出明确的指令,下级也会因为任务目标的模糊而缺乏执行标准,考核、问责、监督的压力传导和激励机制受阻,监管的低效会催生较为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甚至会滋生政策寻租行为。自下而上的创新组织模式则对创新资源的配置采取了契约制度。
从对创新成果的评价来看,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约束组织模式的产出成果评价是一个难题。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沃尔夫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13]从我国这些年产业创新的结果来看,在数量、形式、规模方面的创新有很大的进步,但在质量、实质、颠覆性创新上仍然不足。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约束组织模式有一定的关系。当前,我国学术评价指标体系过于量化和功利化,科研工作者对快速产出成果的需求较为强烈,盲目追逐政策热点或者跟风国外理论的现象较为普遍,“改进式”研究多、“原创性”研究少。自下而上的合约型约束组织模式下的创新产出成果,由市场来评价、定价。革命性新技术的产生,靠的是大批的独立研究在市场上“比赛”,通过优胜劣汰决定。
构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应采用明晰的产权制度与契约约束形成战略科技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多出战略性、关键性重大科技成果”[2]。要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基于明晰的产权制度与契约约束构建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让最强的科研力量在最适合的攻关领域发挥最大作用。构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必须建立在支持科技创新的法律基础性制度上,从控制型约束转向契约型约束。下一步,要推进以信任和绩效为核心的科研经费管理改革,完善科技创新人才全链条培养机制,在重大科技任务中培养造就领军人才,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當主角,要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改进科技评价体系。
四、国家大科学组织的治理机制:从科技管理到科技治理
国家大科学组织的治理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相关政府部门通过研发投入、人才等方面的科技政策,以及针对项目或机构的评议制度来进行外部治理,以此营造有利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着力基础研究的宏观科技创新环境;二是机构的内部治理,涉及股权结构、治理结构、激励机制等。能否把创新的资源真正配置给创新主体,是检验一个创新组织模式优劣的关键。
(一)外部治理:有效配置创新资源
政府主要用“行政计划”的方式将研发费用投给国有科研机构及其研发人员。我国当下的基础研究以中央财政支持为主,其特点是科研人员主要通过项目竞争的方式获取,这些项目分布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科研管理机构中,每类项目对应不同的资助额度和周期,项目评审也由政府机构组织临时性的专家委员会进行。这种自上而下的分配科研资源的方式会导致以下问题:一是科研人员自主权缺失。基础研究当下的根本困境,实质上指向经费分配结构问题。基础研究的典型特点是基础性、长期性和难以预测性。就基础研究而言,这种以竞争性项目为中心的支持模式会造成科研人员的功利主义倾向加重,在选题上更看重能否在短期内出成果,使得基础研究有限的经费可能并没有流向真正重要的原创性研究上,以致经费投入产出效益不高。二是政府主导的学术评价替代了学术共同体评价。政府主导学术评价主要强调论文、职称、学历和奖项。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的调研报告和中国工程院课题组的《我国高层次工程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研究综合报告》显示,影响我国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成长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科研资助体制机制上的过度市场化、过度竞争化和短期化问题;二是评价制度不完善、非创新导向问题;三是科研人员分配机制上的稳定保障与创新激励不足问题;四是科技人才成长中的官本位和行政化倾向问题。
现阶段,我国政府研发投入主要投向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投入不够,民营企业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的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国有企业在国计民生及公共产品供给上有优势,但创新是国有企业的短板。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由于预算软约束和企业负责人在资产保值增值短期考核压力下往往选择求稳,加上创新中的不确定性,因而国有企业开展创新的动力不足。在构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中,政府财政助力企业基础研究必须实现非人格化政策支持,既要支持国有企业创新,又要支持民营企业创新。构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要发挥民营企业的创新优势,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经受了时代的考验,证明民营经济是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主要力量。政府应积极鼓励、有效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创新,推动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重大原创技术突破中发挥作用。科学技术部的统计显示,2021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有584项由非公有制企业牵头承担,占总项目数的67.9%,业已形成大中型民营企业参与重大创新的一股“新势力”[14]。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发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灵活性优势。对于国家级、省部级重大或重点科研项目、科技工程和军民融合战略需求项目,应进一步对民营企业开放,给予民营高科技企业一视同仁的参与机会,对能切实解决国家高精尖缺技术需求的企业给予优先支持。
当前发挥民营企业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的作用仍然存在瓶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能力但渠道还不够畅通”。我国头部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巨大,但常态化、体系化的政企沟通不畅,以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在重大创新需求问题凝练、创新任务设计决策方面缺乏话语权。二是“有意愿但环境还需要优化”。在理论上已经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但是,民营企业在重大创新平台、资源汇聚和技术路线选择方面呈现被边缘化倾向。三是“有作为但回报还不理想”。国家大科学发展涉及多主体参与,缺少高能级创新平台支撑的民营企业对于技术路线和研发进度缺少话语权,造成最终成果与企业和市场的需求有一定差距,带来的经济回报小于预期[14]。
(二)内部治理:科研机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欲使技術创新变革卓有成效,就必须让创新者有充分的自主权、选择权、决策权。最大限度、最低成本地利用社会中分散的知识,需要依靠市场有效的价格机制,同时为了克服可能出现的外部性、信息不对称、搭便车等问题,还需要良好的制度和组织结构加以辅助。在当下以竞争性项目制为核心的科研管理体制中,科学研究的组织事宜主要由政府机构负责,它们拥有立项、组织评审、审批等权力。这种管理体制忽略或跳过了科研单位这个关键的中间层,难以充分发挥科研单位的作用。由于各类项目来源不一,都有各自管理部门,科研单位对科研工作者所在的课题组只有保障义务和财务管理责任,而没有权力对项目任务进行调整。这一模式可能会导致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科研单位既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又没有足够资源布局。这是基础研究多年来经费使用效益不高的原因之一。因此,科研单位的内部治理要按照以需求定任务、以任务定项目、以项目定资金的方式,逐步构建以稳定支持为主、竞争性经费为辅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赋予科研机构更大的资源配置自主权,同时压实法人主体责任,做到责权利统一。要树立“大资源观”,围绕抢占科技制高点攻坚任务,加大人员编制、人才计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仪器平台等各类资源的统筹调配和动态调整力度,一体强化对抢占科技制高点攻坚任务的支持和保障。
五、国家大科学组织的协同机制:从自上而下的产学研协同转向自下而上的产学研协同
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越来越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注重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军作用和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构建国家大科学组织的产学研协同机制,应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一)从自上而下的产学研协同转向自下而上的产学研协同
构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可按照万尼瓦尔·布什法则,选择某些领域,将政府的执行重心下移,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再建立产学研协同机制,最后找到专业的人来执行(组织者)。长期以来,我国研究机构、大学、产业三者都被自上而下地垂直管理,缺乏沟通协作,仅通过政府行政单位和技术官僚来把控创新走向,导致创新质量不高。创新投入由政府主导,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教育和研究系统,产业领域的科技人员偏少,这导致科技转化成本增加,转化激励机制缺失,转化产出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学研协同及合作水平不断提高。
“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利于产学研深度融合。政府发布相关政策和组织开展技术创新项目,通过寻找企业、高校或科研机构作为代理人推进项目实施。而一些项目本身并不是基于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缺乏真正的经济效益。只有推进“自下而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才能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自下而上的产学研协同需要产、学、研之间有一套人才(创新资源)合理流动的制度安排。我国自上而下的产学研协同最大的问题是不利于人才(创新资源)合理流动。在公共财政的支持下,我国科学成果取得显著成绩,科学影响力稳步提高。但是,高水平的论文转化为科技成果的较少,尤其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贡献有限,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科学界与产业界的人才流动率较低。以从事科研工作的博士生为例,数据显示,2015—2020年,我国博士应届毕业生去企业工作的比例平均为10%左右。但是,在英国,2006年此比例已经达到33.5%,法国约为24.1%;2016年发布的《从研究生院到职场之路》报告显示,美国应届博士毕业生去企业就业的比例超过50%。由于科研人才缺少向产业界的流动,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更多表现为科学影响力稳步提升,但是没有形成产业竞争力。从人才结构来看,2016—2020年,我国企业研发人员中硕士、博士学历人员占整体研发人员的比重较低,五年平均占比分别为7.04%和0.84%,且均呈下降趋势[15]。为此,应畅通科技创新人才在体制内外流动的机制,实现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创新成果互通互认,探索形成人才在校企间“能进能出”的新机制新路径。
自下而上的产学研协同需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产学研合作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并加强各类创新要素在创新联合体内的流动。相较于国外采取“共建实体”的组织模式,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投入资源,采取股份制公司的形式进行产学研深度融合,我国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还不够紧密。由于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融合度不足,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信任机制缺失导致交易成本较高。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目标往往是科研成果和发文量,而企业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和经济实绩。二者目标的不一致加上产学研合作组织的松散,使得技术和经济往往是“两张皮”。只有完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信息和资源共享机制,让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才能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自下而上的产学研协同需要完善大学的制度环境。构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政府的角色必须从挑选“少数赢家”的创新资源分配者转变为市场规则的维护者。大学的基础研究应从纯自由探索模式,向瞄准国家重大需求的定向性、系统性、有组织的科学研究模式转变,开展跨学科的科研协同创新和集成创新,聚焦从“0”到“1”的原创性和颠覆性技术探索,有力推动科技创新突破。要依托高水平大学布局建设国家实验室。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建设国家实验室没有必要另起炉灶,依托高水平大学现有资源来建设是现实可行的选择。这样既可以实现大学基础研究和国家实验室战略导向研究之间的有效耦合,又可以实现高水平大学建设和国家实验室建设的合作共赢,延伸拓展“基础研究—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地,主要从事具有原创性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是基础研究活动的主要执行部门。
自下而上的产学研协同需要培育和发展专业技术转移机构,鼓励创新创业,促进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向企业转移;以重点实验室为基点,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要加强我国基础研究供给,同时加快构建与基础研究特征相符的激励和考核体系,增强基础研究动力。探索建立基础研究多方合作研发平台,构建由财政拨款、基础研究基金、企业资金共同组成的资金池,更好支撑长周期的基础研究项目。探索组建由大学、科研院所和产业协会等共同参与的企业创新扶持机构,促进基础研究等成果在产业中的应用落地。持续优化科研政策,显著激发创新活力。
(二)建立在知识产权明晰基础上的产学研协同
熊彼特曾指出,企业才是关键的创新主体,他将配备了研究和开放实验室的现代企业视为创新的核心主体。根据现实经验来看,从17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有80%以上的创新都是在企业产生的,近70%的专利和2/3的研究开发经费均来自企业。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需要企业牵头搭建起创新联合体系。
在现实中,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活力的主要来源。一个地区只有将民营经济充分发展起来,拥有发达的民营经济,经济才会拥有活力。不仅如此,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现实中,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代表性企业,有不少就是民营企业,如华为、大疆、比亚迪等。在构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上,可以让更多的民营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民营企业应主动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实验室、联合申报科技计划项目、共同研发产品、联合培养高技能人才等。2022年,腾讯公司宣布10年内出资100亿元,长期稳定地支持一批杰出科学家潜心基础研究、实现从“0”到“1”的原始创新[16]。民营企业贡献了我国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构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应该把民营企业作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主体。全国工商联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研发投入前1 000位的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1.08万亿元,占全国研发经费投入的38.58%;截至2021年底,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国内外有效专利合计超过63.3万项,较2020年增长53.6%。2022年,“中国制造业500强”中民营企业占72%;光伏产业全球前10强中8家都是中国民营企业;4 300多家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达84%[17]。
产权是否明晰决定着创新的多少,革命性创新的产生、最前沿的革命性创新,大部分产生在小公司,而不是大公司。革命性创新大多数产生在小公司,主要是因为小公司产权更明晰。大公司的作用,往往是小公司的资助者和整合者。当小公司有重大突破时,有些自己变成大公司,如苹果、脸书等;更多的是大公司将其整合进来,如谷歌兼并人工智能公司Deep Mind。产权明晰及保护程度还决定着企业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从整体研发投入来看,在中国,企业是主体,占全国研发总投入的比例接近80%,与日韩相近,但是在基础研究投入上差距还较大。在基础研究领域,中国企业执行比重较低,2009—2019年长期在2%左右,2020年才有所提升,但也不到10%;而韩国占比接近60%,日本接近50%,欧美等国家则为20%~30%。这还是执行的部分,如果是企业自有资金就更少了,中国企业内部研发资金分配到基础研究的不到1%,而韩国在10%以上,英国接近10%,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在6%以上。从研发投入来看,我国企业的研发密度不够高,普遍存在重开发、轻研究的现象。即便进行基础研究或者应用研究、开放试验等,也基本上都属于重复性、低水平的研究,经费使用的效率偏低,产学研融合度不高。我国企业不重视基础研究的投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过去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路径主要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对基础研究的需求和重视程度不足;二是我国产权保护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还不完善。构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大科学组织模式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加强企业基础研究,尤其要提高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在总体研发投入中的占比。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明确大企业是需求驱动的基础研究的主体。理解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的作用和不同创新主体的科学能力配置是有效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关键。唐纳德·斯托克斯通过四个象限定义了不同的研究类型,其中基础研究包括纯粹的基础研究(波尔象限)与由应用驱动的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波尔象限和线性模型下的基础研究基本一致,代表由科学家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但是,在巴斯德象限中,基础研究具有通过尖端的基础科学研究来解决迫切、強烈且巨大的产业需求的特征,具有需求驱动的基础研究的特点[18]。
我国科研院所和大学的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研究成果数量位居全球前列,但是,在诸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我国产业竞争力仍然薄弱,其深层的原因是需求驱动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大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够。需求驱动(或应用驱动)的基础研究增强了科学与产业的协同性:从具体需求切入,知识的选择效率会更高,创新目标更明确,可以提高科学知识的产业转化效率。但是,创新的不确定性仍然是普遍存在的。为了降低这种不确定性,一个有效的措施是发挥大企业在需求驱动的基础研究中的主体作用。事实上,我国大企业在需求驱动的基础研究方面的主体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1995—2019年,我国企业来源研发经费从300亿元增长到近1.7万亿元,增长约55倍;但是,1997—2019年企业研发经费中基础研究投入比例从1.12%降至0.3%。2020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尚有60%以上的企业没有开展研发活动[18]。2021年,我国60%以上的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和30%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均由大学牵头建设。但是由于缺少大企业从需求端发挥主体作用,科技与经济的“两张皮”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这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长期以来,我国企业通过“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模式获得一定的后发优势,尽管模仿或兼并的方式对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产业核心技术供给不足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其二,我国很多大企业已经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制度激励方式相对单一,难以达到鼓励大企业长期投入基础研究的目的。国有企业往往认为在长期项目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存在经营风险和盈利压力,在国企领导干部任期制和现行考核激励机制下,企业缺乏与高校开展长效科技成果转化合作的动力[19]。大企业不仅是技术创新和产业竞争的主体,也是科学研究的关键主体。当前,我国需求驱动的基础研究投入过低,大企业科学创新能力低,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短板。为了弥补这一短板,我国需要从人才激励、体系建设和机制完善等方面进行改进。 [Reform]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EB/OL].(2016-09-03)[2023-09-03].https://www.gov.cn/xinwen/2016-09/03/content_5105135.htm.
[2]习近平.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J].求是,2022(9):4-15.
[3]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47.
[4]埃德蒙·费尔普斯.大繁荣[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7.
[5]路风,何鹏宇.举国体制与重大突破——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的历史经验及启示[J].管理世界,2021(7):1-18.
[6]安纳李·萨克森尼安.区域优势:硅谷与128号公路的文化和竞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
[7]上海复斯管理咨询公司.从创新理论视角解读国家2023科改Ⅰ:创新发展模式的再次组织转型[EB/OL].(2023-03-31)[2023-09-03].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186028
3071216780&wfr=spider&for=pc.
[8]陈实,王亮.中美财政科技预算的比较与启示[J].中国科技论坛,2013(8):153-160.
[9]李旭冉,柳玉梅,刘玥杭,等.中国年研发经费突破3万亿,钱从哪里来?又流向哪里去?[EB/OL].(2023-08-15)[2023-09-05].http://www.cima.org.cn/nnews.asp?vid=40831&f=0.
[10]孙莹.R&D经费投入趋势演变与启示——基于交叉结构视角的国际比较[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3(1):100-111.
[11]李侠.诺奖是对坚持长期主义与良好科研生态的回报[N].中国科学报,2023-10-06.
[12]王腾,关忠诚,郑海军,等.着力基础研究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治理——来自美德日的经验启示[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23(4):410-422.
[13]张立民,李晗.国外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研究综述[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2(3):9-17.
[14]尹西明,吴善超,魏阙.民营企业参与重大创新的困境与对策[J].科技中国,2023(9):7-11.
[15]金锋,秦坚松,刘雅琦.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EB/OL].(2022-09-07)[2023-09-0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9631436521908481&wfr=spider&for=pc.
[16]施一公:原创性基础科研大有可为 支持尖端科研也是企业对社会尽责的表现[EB/OL].(2023-11-01)[2023-11-0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1335820060032
493&wfr=spider&for=pc.
[17]尚城.江小涓:新的有利条件提供新机遇 我国数字经济竞争力较强[EB/OL].(2023-07-13)[2023-09-07].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3/0713/c1004-40035271.html.
[18]柳卸林,常馨之,杨培培.加强企业基础研究能力,弥补国家创新體系短板[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6):853-862.
[19]王雪瑩,薛雅.加快突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瓶颈问题[J].科技中国,2023(9):41-44.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Sci-tech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of National Big Science Organization Model
LU Xian-Xiang
Abstract: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in the era of big science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investment, large scale, multi-discipline, larg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or groups and so on, which requires the national big science organization mode of high-level sci-tech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to ensure the continuous oper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In the era of big science, sci-tech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are the key to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countries. The main goal of the national big science organization model of high-level sci-tech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is to implement "big science projects" and "big science plans", and to solve the basic research, frontier and major problems of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order to build a national model of high-level sci-tech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four major changes should be realized, that is, the national model of big science organization should change from the centralized developmental model to the network developmental model; the restraint mechanism of national big science organizations should change from control restraint to contract restraint;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national big science organizations should change fro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national big science organizations should change from top-down "collabor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 to bottom-up "collabor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
Key words: the era of big science; high-level sci-tech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national big science organization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