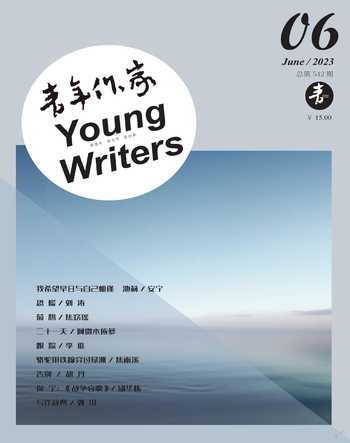在生活之外舞蹈
宗永平
缪塞在《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开头说:“要写自己的生活史,首先需要有生活经验;所以我现在所写的并不是我自己的生活史。”当然,接下来,他写的恰恰就是他的生活,甚至也不隐晦——也许因为并不复杂?李谁通过对名字的差别化戏仿——“隹”,告诉我们,似乎《跟踪》是生活的映照(至少部分地、某种程度地模拟),但事实绝非如此。如果非得说《跟踪》缺少什么小说的因素,那只能是真实的、经过个体经验的生活。
我们先来看小说的谜面。
《跟踪》的结构和叙事的不确定性(而这,成了一种确定性的追求),很容易让人想起卡夫卡的城堡,或者博尔赫斯南方阡陌交通的迷宫。但又略有不同——小说本身就隐藏着供词:那就是,佩索阿无穷复制的自我虚构。只不过对“隹”而言,并不进行诗歌写作(不能确定他是否写诗,只能说没有交代),而是生活衍生出无数的枝杈。
让生活变得不可究诘的第一步,是取消自我。“隹”对李“谁”的不对等复刻,其实是对小说主人公主体确认的取消,因此这个叙事者在现实和虚构的双重维度上变得模糊不清,似乎他可以随意穿梭在两个空间,令人无法把捉。“隹”无论工作日还是周末,都会到十字大街靠东那间名叫“梦”的酒吧里露面——从后面来看,观察跟踪者至少是主要目的之一。但是这本身就是十分主观的猜测,除此之外几乎就是白待着——没有必要的日常生活目的,而这让生活的真实性受到质疑。等到“隹”从公司辞职(也可能是变相的解雇),叙事者的职业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性,也消失殆尽。一个人从职场退出,丧失社会功能,而生活的内容只是无所事事,在一个叫“梦”的酒吧发呆。而他所在的城市,既没有明显的特征,又竭力排除现实的指涉——比如,城市里竟然有晚祷的钟声,这显然是对我们现实身份的否定。最终,在一片被抽空的空白之地,躲在玻璃窗后面,我们好像就变得可以为所欲为。
下一步,则是行为和空间的抽象化。不单单“梦”的命名具有幻想色彩,而且酒吧在现代生活中就是一个标准配置,而它的位置除了强调的“市中心”之类,只用街道来描绘——位置、命名、功能,三位一体,都是模糊和虚幻的。而在酒吧里的人,除了场面背景的酒和歌舞(戴着面具演奏),他们的行为只是“来交朋友”的,而且似是而非地“交谈”之后,不但不涉及身份,甚至面貌身材特征,也随之消失——多数是从“梦”酒吧的门口落入黑暗。这样,“交朋友”的行为,就可以无限复制。相似的还有周末例行去图书馆“阅读”。除了被人“监视”,更令人觉得奇葩的是:“隹”阅读的目的竟然“是通过阅读与冥想,将自己拉回一个清晰而敏锐的世界中。”在一种被抽象化的氛围中,小说里的行为和环境,都显得模式化,而模式化是復制最简便的形式。
最后,是复制、粘贴。简便的复制是“交朋友”、阅读和对“监视”的重复,不但让生活变得没有内容,而且生活本身也已经被取消。整个小说看起来变成一个粘贴想象的游戏——细节和观察的准确,是唯一挽救的努力,而且效果不错。这让小说读起来虽然叙事没有进展、近乎停滞,却还不至于沉闷,甚至还很生动(这要看各人的兴趣)。但也已经接近极致——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突破。所以突破来了:离开常规的“梦”酒吧,开始了一场街上的追逐。追逐的结果就是另一个被跟踪的故事——蛇的哥哥尸体化妆师的处境和“隹”十分接近,包括跟一个疑似跟踪者的会面,应对的是“隹”跟公司辞职青年的会面;甚至,也导致了一场追逐,甚至凶杀。所以,所谓突破,其实只是一个对已有文本的更复杂、也许不精确的复制,就像“隹”相对“谁”。
最后的结局,只是对这些幻想、复制、粘贴的解构——也许,这只是一个被解雇的员工,因为心情抑郁而产生的幻想。只要回到岗位,一切也就成了梦幻泡影,回归常态。
看完谜面,我们无法揭示谜底,也不必要。倒是可以来看看一段锦绣背面的针脚。
就像开始说的,如果非得说《跟踪》缺少什么小说的因素,那无疑是真实的生活。不仅仅因为生活被虚化,也不仅仅因为它不涉及具体的经验,主要是说——在背面穿针走线的人,本身就缺少生活的折磨或提炼。音乐、文学,阅读、喝酒、看演出,说到爱情,那是没有经历过的,即便简单到欲望的“男女”,也只是想象的。其实是不经意地看见,这么有天赋的作家,其实只有二十出头。所以,一切都理所当然,也就释然。这样一个完全靠想象编织的小说,已经足够惊艳,但是并不令人感动,原因其实就是单纯得透明的四个字:“真情实感”。让我们怀揣期待,看看生活会成熟出一个怎样的结果——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还是一场好的故事的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