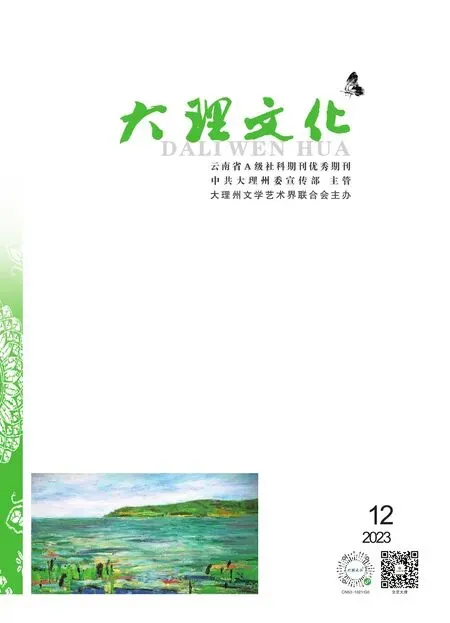古乐
●杨腾霄
其实,赵森声并不在乎谁死了,只关心手里的这套傢私(锣鼓)和那两根弦的蛇皮二胡,只要是小杨一有电话,赵师,你来门前等我,我十分钟后到。他就会连忙捻了捻山羊胡,去拿两片锣,一个鼓。扶着桌子,连忙把挂在墙上的琴盒(他根本不用挂起,是担心有时孙女回来玩,把二胡琴弦扯断)习惯性地打开“行头”,看琴弦松紧,蛇皮疲软。拿上水杯就在外面等小杨的车子了。
这套程序,十多年了,一次未变化。原因是他很在心,随着年岁的增大,他一次又一次提醒自己,二胡,二胡,锣鼓,锣鼓,水杯,水杯,毡帽,毡帽,眼镜,眼镜。确实十年如一日,他并不像乐队中的老人们那样丢三落四。
他的几个老人伴讲,他们在家就晕乎乎的,电视开着瞌睡了,关了,眼睛睁开,清醒十倍。经常拿着水杯盖子找盖子。
洞经小乐队的人都很喜欢他,一些小零碎常问他,赵师,伞呢?伞呢,门背后。他总知道。
今天是绕三灵的日子,好些搞乐器的人,都约他去玩,均被他回绝了。
未料,小杨突然来电,有人死了,帮忙,要去搞锣鼓傢私。赵师,赵师,快点出来,帮帮,死者家属一再提你名,请来,请来!
他确实不在乎谁死了?也不想多问。只是觉得小杨这人太好了,热心快肠,对他鞍前马后,善解他意,让他老年时光有整场,无病无痛,快乐打发。
赵师,对不住了,人家一天要你来,敲锣,拉琴,绕三灵也不让你得闲,要跑到水帘村的,在大理西头。
他上了车,再想,给有拿忘什么东西?现还赶得及,对小杨的话也不客气,也不问是哪家?哪个人死了?
小杨的车子是面包车。他把乐器放在后排,很熟练地坐到前排,系上安全带。就专请赵师大驾了,他们村里有老年洞经协会,其他人不参加了,就请你一人了。他并不理会小杨的话,仅嗯了声。
家里闷得慌,这晨曦天空,苍洱之间,人生几回?他要好好享受很养眼的银苍玉洱间的人生。他经常对同龄人讲,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无所事事,也不能无事找事做。要有事带不有事。此刻,赵森声正是有事带不有事。小杨,慢慢开,我好久没看苍山洱海了,他说了声。
不知亿万年前苍山从古生海中钻出背脊头颈,露出面额时,为什么双臂紧拥,屏列如弓,十九峰紧紧怀抱翡翠一样的洱海,二不能缺一?造化啊,造化!从小在这毓秀灵水中长大的赵森声总感到有什么声音在他心扉鼓噪涌动。白云,清溪,海浪,山溪,井水?他总玩不倦,看不够,想大喊些什么。还好,他的老爹很懂敲打。他们家在古城古楼下开了一片础石铺,也就是大理石画像的门市铺。他老爹闲来无事,总找一些街坊邻里搞些“洞经”。从小他就听惯了那些像苍山峡谷飘出的声音,又似洱海湖面扑涮扑涮的奇妙音响。所以,每每见苍山洱海那种微澜,感受一次次新鲜的奏响,心灵是无法比拟形容的。

它们没有音符,没有乐章,没有歌谱。是上苍给白族的一种亘古空灵,那是人性的永远。有一次,半夜他突然听到一种非常非常激昂的声音。看看床上,没有老爹,他从格子窗看见,老爹一个人两腿夹鼓“哐哐”地敲打,不时又扑打鼓槌敲,对着他爹(森声的阿爷)的大理石础石画像。他阿爷手握战刀,军装笔挺,那满挂的勋章似乎也在摇晃。他知道他阿爷是贺龙军长手下一个功勋卓著的团长。北伐时,不幸身亡。老爹是在想他的老爹啊,半夜实在控制不了,是用锣鼓宣泄。那一夜,让他真正感到什么是音?什么是乐?它是人性的一种悲怜,一种不可代替的对山水亡灵的倾诉。
还没到苍山中和峰时,就往西拐了。
死的这个人,是我亲亲的表孃。小杨说。
典型的一套“三坊一照壁”的院落。下车后,赵森声走进水帘村老年洞经音乐协会的吹丧队照壁下。那些戴毡帽戴墨镜穿领褂的老头,早在最前面的座位上给他留了个位置,点点头。他把傢私放好,习惯性地先上台阶,在正中堂屋的灵堂上拜了下,鞠了个躬。顺眼,他也瞟了眼遗像。
不瞟则已,一瞟傻眼了。
他如踩在棉花上,有点站不稳,他有些晃,再看眼遗像,有点踉踉跄跄,忙拉住身旁的小杨,问,是你表孃?
是的。昨天下午从医院拉回来,是晚期子宫癌,无救了。小杨一边说一边扶着他,来,来,坐坐!喝茶。
临坐,他又扭头看了她一眼。
别人不注意,但赵森声是看清了张淑兰的鼻梁边那一颗颗雀斑和嘴角上的笑纹。
他有些气喘,坐在椅子上,好一会才回过神来。他对洞经负责人说,邓师,今天我精神有点差,不想打铲鼓了,只想拉拉二胡。
不怕,不怕,我们有打鼓的。老邓说。
唢呐响了。照例是白族的大哭板。唢呐是不需要胡琴的。他趁势端起茶杯,坐在了一丛茶花树后。
阿兰啊阿兰!你咋个死在我前?我是一直在找你,一直在找你!
赵森声,长得很俊,读书时一表人才,口才,肚才也好。出身也不坏,小手工业者。当然,曾经有段时间,把他爹当旧军阀处理,大字报,戴高帽游街揪斗,也没幸免。他爹一气之下,一口气上不来,远离人世了。破“四旧”时,造反派砸烂了他家的将军础石画像。他爹临终时,把他吹拉弹奏的器材摆在床边,对儿子说,你要学,你要学!
赵森声声泪俱下,嗯,嗯,嗯。
其实,葬了他爹后,他把这些傢私一股脑儿锁在了一个木箱封存了。
由于他出身不坏,“文化大革命”后期,革命小组里还待了会。这期间,派往苍山脚某农场守护。饥荒之年,那可是个肥差事。也就是这段时间,大约二十一二岁吧,他认识了淑兰。淑兰家姊妹多,常来山脚偷瓜刨豆。一次被赵森声抓了个正着,他一口一声毛主席语录,正儿八经地一条一条最高指示念着,看见她的两个妹妹面黄肌瘦,从箩筐里拿出四五个洋芋,递给她们,说,你们先回去,我带你姐去写检讨,再教育。
淑兰也很乖巧,进屋就把他脏鞋脏袜洗了,还把他那些烂衣烂裤缝补干净。
外强内柔的小伙子果然被感动。
一回生二回熟,他俩没有煮夹生饭,一次就煮了锅像熟透了的“山药蛋”。
那种干柴烈火的日子,当然是会怀崽的。他这人还粗中有细,就近卫生所,请了个赤脚医生,人流了事。当然他也顺手拿了农场母鸡和蛋补了她身子。
山茅野菜的这对恋人,还想第二胎时,他姐在人武部认识人,把他草草招兵入伍。
在部队,他算文化兵,通讯,文书。被一位首长相中,做了快婿,迅速提干,副团时,首长急了,他想当姥爷,让他到地方上把个位子,结婚生子。
他的老婆也是兰,只不过是叫玉兰。山西人。那个淑兰曾来营房找过他,第一次还见了下面,第二次见不了,借口外地培训,第三次军校不准假。本来就是良家妇女,无什么证据,山毛野地是两人初恋青春时光,保留吧,自动退场。这也可能是岳父大人的先知先明,老辣吧,让事实说话。结婚后,他偷偷给淑兰写了封声泪俱下的信,还寄了些钱。后无人查收,退回,当然也被玉兰截获。以后他也不再寄信。渐渐,有了个位置,一男一女,另一番情趣和世界,把自己忘记,更把淑兰忘到爪哇国了。
老实巴交的淑兰也找了个工人,有三个孩子。
生活是首歌。你不唱,它会唱。生活似舞台,一幕幕总要轮回。赵森声与大玉兰的生活是公式化、现实化和人为化的,就像她是盆栽的玉兰,他走进屋子了,屋子和花是人安排给他的,你得要生活,这就是现实生活。而那棵小玉兰是自然的,是属于自己日子里的玉兰。她脸上的雀斑是花蕊,是让他的人生荡漾别人不可能享有和领会的神曲。
他与盆景花本来就格格不入,现在已退休了,他时时刻刻想回归自然,回到苍山脚下,何况两个儿女也大了,各自为家。儿子与媳妇尽讲北方话,他不属于他们的世界。妻子本来就是盆景,很入流,花枝招展,穿红披绿,出入超市,涂脂抹粉,特别是她找了个“吃软饭”的舞友,他再也不想在省城待了。想起了父亲留下的傢私,想起苍洱之声,借口回家照看九十老母,十多年前,就回来了。
妻子也落个自在,这个“老土”不麻不穿不舞不有音乐细胞的“老公”靠边站吧!
回到大理,赵森声深深感到回来晚了。家乡是一首歌,精深博厚,是上苍给白族的造化,谁人比得了?他一直在弄这“洞经”,越弄越深,它是让人回归自然、颐养天年的灵丹妙药。
不用听懂它,也不需听懂它,只需那氛围,那场景,那山水间,老有所居,有所归了!越弄父亲的“傢私”,他越深深感动,忘乎所以。
开始退休那几年,大玉兰约他跳摇摆的音乐,特别是KTV,他嗤之以鼻,那些说、吼、叹之类的人间烟火,怎比洞经。而且他老婆那个胸无点墨的男友,他更恶心。
想想也好,小杨请他参加丧乐队,也是原汁原味感受白族的洞经音乐。
越感受他越想淑兰。
老来就想与她过日子。
未料今天在灵堂上看见她。
他不想吃饭。只想对她拉二胡,如诉如泣地在照壁下,爬到墙上,回音至她的灵魂。
几天后,妻子在省城也传来噩耗作古,她的骨灰安放在岳父母大人墓旁。
他的母亲没有作古,还活着,快100 岁了。吃素,在老屋,静静的。月亮和太阳伴着他的二胡,洞经不时响起。
临走那天,离开淑兰的灵堂时,赵森声鬼使神差样,在淑兰遗像前连续用手机按了几张,半个月来,他不敢看相册。
反正他以后的日子就这样过了,不是孤人的孤人。尽管妻子曾与他生儿育女,那是一种公式,现在他对妻子的肉身一无所想所知,别说语言的沟通了,所以她连骨灰都安放在她的老家,山西的父母旁。至于儿女嘛,早成家立业,过着自己小家庭的生活,那两个孙子,偶尔,他们给他发个视频,也是在过生日时,他只知道是要个红包。他看着手机里的孙子,感到像超市大橱窗里的大玩具,没有感觉,兴趣索然。
他的身体很好,当然老年人的基础病是有些,但不碍事,标准的体重73 公斤,1 米73 个子,历来如此,何况还有军营生活经历,现在也很板扎。同龄人大多“三高”,手杖,东倒西歪,他没有。特别是他的思维,还很有条理,反应快。前久,70 岁老人的驾照增加了三力(判断力,反应力,记忆力)电脑测试,他仅20 分钟就100 分。好多同龄人因两三次都不及格,因此而吊销了驾照,连考监考的警官也惊异。赵森声咋个了,20分钟20 道选择题,他ABCD 的勾勾叉叉几下就搞完了,别人1 个小时都搞不出来,补考两三次也无济于事。但最近他也不开车了,因为有小杨,包接包送,加之在古城开车,那简直是浪费,是锦衣夜行。
母亲吃口也细,偶尔他带回给她点饭菜,面食之类,足矣。加之在古城散步,买点青菜红萝卜,很惬意。一句话,现在他衣食无忧,陪母尽孝,似乎很悠哉游哉,十分淡定,副厅级待遇,退休工资也高。不时还有一些慰问,大家都说老赵好过了,什么都不缺。
好过?一样也不缺?
但是他缺。赵森声缺一种上天给予的悠扬,缺一种人生:一种他本来得到,后又因世俗烟火名利的原因失去的原汁原味的“爱”。
从那天张淑兰的灵堂回来起,他彻底失眠了。隐隐约约,还会梦见,他与她在卫生所强行扭下的那个像蝌蚪一样的小娃。
终于,有一天半夜,他一骨碌翻爬起,开始翻箱倒柜。他在找,他在翻,除了翻出些父亲留下的半截半截,圆的,方的,不同形状的落满灰尘的础石(苍山大理石)的碎片,好像其他也没有什么发现。但他激动了,我就是要这些碎片,这些碎片。他自语着,一小块一小块小心翼翼搬到天井里,那天刚好是月亮升起的夜晚。
赵森声借着月光,把几十块大理石碎片一字排开,迎着月色或牛或马或人或山或水,在高低花台和青石地板上一览无余,用井水细细喷上,仲夏之夜,一幅绿莹莹的奇异人间美景展现在他面前。恍若隔世,奇异光泽,让他亦幻亦真。他拿出胡琴轻轻拉起《病中吟》。
他很清醒,不想了解父亲收藏的这些碎片为什么一片也没有题字,一片也没有画像。也许,父亲早知今日,今夜,儿子会用乐,来思念,遐想,游走。就两根弦,他不用锣铲,也许是怕惊动母亲。弦足矣!只要一根神经,十个指头,他就会从“病”中愈。
他在每块碎片中间留了条道,人可以慢慢走近,他不想再奏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他掏出手机,终于开始看相册,一张一张地翻过张淑兰的相片,定格脑海,提起二胡,半闭眼,轻悠悠地拉起自己思念的苍山脚下那些冬瓜,扬丝瓜,长缨穗子花的玉米,马铃薯的芬芳。起风了。
啊呀呀
砍柴莫砍水冬瓜
做人要做金南瓜
啊呀呀
金南瓜
……
他似乎看见阿兰在山坡地走来,一晃一揺,她像金色的南瓜一样在风中摇摆,她饱满的胸脯一晃一颠,手里夹着他的脏衣服。
溪水潺潺,她弯腰时那身姿,也是熟透了的金南瓜。偶尔抬头,茂密的亚麻色头发下,是点点闪烁的雀斑。赵森声不知道他在拉些什么,他只知道他在如醉如痴,他不知道,他放下手机时,已顺手按下录音键。
他想起了《聊斋》,想起了蒲松龄写的《张牧过点苍山》的故事。见一奇异女子从大理石中走出……他定睛一看。有块斗方形的大理石上,宛若张淑兰的女子突然向他走来……
第二天,他发现了手机上的音乐。他拿给小杨听,并让小杨参观了那些大理石碎片。小杨一遍一遍听,不绝于耳,爱不释手,无意翻出了赵森声的内存,他那亲表孃的照片,小杨是个精灵鬼,他什么都明白了。
这样吧,赵师,我教你搞个平台,把这些形状各异的大理石画面都拍照,配上你的音乐,发到抖音上。你的段子保证点击率飙升,你也自娱自乐。
怕不得,不得!说归说,他还是请小杨手把手地教了几天,也有了“森声古乐”平台。
恰好,近来大理成了个“有风的地方”,络绎不绝的人来寻风追风。大家都想见“森声古乐”,但始终没见到。他留言,母亲刚逝,身有重孝,改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