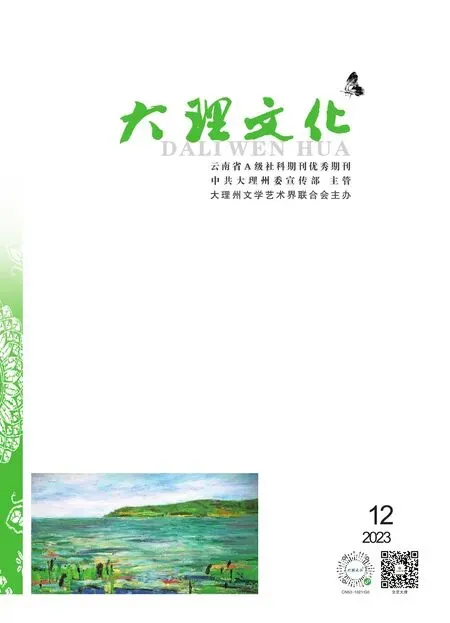苍洱之间氍毹美
●晓风
一座戏楼,甚至是覆顶倾梁的老戏楼,往往是村镇中的一大景致。从苍山之麓到洱海之滨,散落于热闹集市或较大庙观附近的古建筑,大多是属于邑人的乡土戏台。每当逢年过节、本主寿辰及庆会诸事,村镇里都会演上台戏:本土艺人弹三弦、拉板胡,唱俚曲;有时也延请城里头的班子来演上台滇戏,滇戏唱腔老辣阴柔,胡琴高亢激越,只觉得怪怪的、嗲嗲的,除了让人心底发颤外,更有一番难以言传的受用……
身穿五斗秧田,头戴一口铁锅,脚穿一对公鸡。
——这句赶场的拿彩俏头,是出自江尾民间的俚曲。其含意是:乡人去看戏还是去演出,事先就得卖掉五斗谷、一口锅、一对公鸡做盘缠。收拾利落后露面,才不致于在场面上丢人现眼。由此可见,这参与者心情是何等地迫切与较真啊。记得早些年间,那本主庙边的戏楼,甚至是覆顶倾梁的老戏楼,都是一个村庄的中心和大景致。邻村青索村的戏楼比别处讲究,我和爹妈多次前往。正月庙会时,青索村都请外地的滇戏班子来唱大戏。那几里天,临近几个村落也跟着过戏瘾,汉子家割肉买酒、打牌抽烟,招待前来听戏的远路亲朋;而那帮婆娘们,则会殷勤地给各色演员们端茶递水,打扫戏楼子;每当村公房大门敞开,几声吆喝后,便有年轻小伙扛着卷成长龙般的猩红地毯登高铺台。好彩头,大戏快要登场了!整个场子一下就沸腾起来。这红毯可是专门到滇北藏区定做的“氍毹”。氍毹指毛织地毯,古代演戏,地上铺地毯,是以用“氍毹”代指舞台。
白族的乡村自古尊重传统习俗,最晓得:“新媳妇看鞋,戏班子看台。”这道理。戏比天大,敬人便是敬己,这氍毹可关乎一村子人的脸面哩!
节会的正戏演三天或五天不等。在民国某年,张冲师长杀了巨匪张结巴,悬贼头于城楼,远近的民众欢腾唱大戏。单周城的大青树下,戏台子就连着开了七个昼夜。耄耋之辈至今记得,当年的演出时,这戏楼前拥挤着观众,有卖各种吃货玩具的小商小贩。孩子们串来串去,看戏的大多半是中老年人,男的喜欢戴副墨黑眼镜,女的就戴顶麦秸编成的草帽。尽管正在上演的剧目是《灵官开台》,大家都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情节和唱词都烂记于心,但每次再看都饶有兴致,不到戏演完,一般很少有人半道离场的。戏里的王灵官这个神道,在老大理特别受崇拜。古城南门楼上还有灵官殿。民家人把灵官当作除暴安良,保一方平安的天神。灵官演得最好的得数花脸王海洲,他是四川人,一直在昆明的滇戏班里挂单,商会要专门派车去请他。其实,这地方戏里连唱、念都没有,但王海洲把它演活了:重彩脸谱,全新盔铠;口吐烟火,云雾缭绕;金鸡独立,稳如泰山;拈须颤腮,神采飞扬。故他一登场,台下就挤满黑压压的粉丝和票友……
滇戏本由川戏派生出来的,融合其他地方剧腔特色而演变出的地方戏种。据云南戏曲史料记载:其产生与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遗老大力倡导戏剧有关;长期以来,杂戏社团的兴起,也与蒙古贵族干预传统汉文化有一定干系。从元的《长生殿》、明的《牡丹亭》到明末清初著名的杂戏《燕子笺》《长生殿》《桃花扇》等剧作的出现,反映出我国舞台艺术上戏曲的极盛时期。当时的达官贵人,不讳忌农民起义军带来的动荡局面,长期痴迷于戏剧娱乐活动。此风逐步发展成市井习气,由中原向边地不断地拓展,演变成多种地域行派别以及分枝。而云南的滇戏的兴起还有原因,清顺治三年(1646 年)冬月,长期盘踞四川的张献忠军中出现叛徒。次年正月三日,这个农民义军领袖在冲出重围时,突遭飞箭射死。其溃部将领孙可望、刘文秀等人南下,经贵州入云南建立政权,又联合南明永历帝共同抗清,曾颇有些气候。这批蜀中的军伍大汉,常借破嗓吼老三板杂腔,点缀枯燥的军营生活,那便是滇戏的最初雏形。
滇戏传入大理的最早时间,大约在光绪七年。当时鹤庆商帮称雄滇西,其分支机构遍及省内外和印缅。这些商号的先生掌柜们,空闲时喜欢哼唱几句,充票友,挥霍银票从省城或外地雇用戏班,把滇戏当作时髦输入境内。上行下效,随着滇戏的流传与兴盛,从城镇到乡村,从泽地到山区,大凡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几乎都设有或大或小、或繁或简的戏楼或戏台。这些在苍洱间数以千计的氍毹之地,见证了地方戏剧昔日的繁荣,也目睹过当年大理人最活生生的民俗生态。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农村永远的最贫困和落后的地方。那些能够用红毡绒铺就的戏楼台,一定是村民心中最豪华的文化圣殿。但时过境迁,从20 世纪80 年代起,那些录音机、半导体、电视机等逐步在乡村登场,戏剧演出,早已不是农村里唯一的娱乐活动;随着数字化时代来临,文化娱乐活动更加多元化。戏曲只得衰落,戏班子也越来越少,楼台也便遭到了冷落,无奈地闲置了起来,时间一长,也就淡出人们的视野……
戏楼的数量越来越少了,剩下为数不多的残存,寂寞地蹲守在乡村的角落里,无人问津。在满是尘土的台面上慢慢挪步,慢慢思考,会窥见一些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会窥见亮亮的珠花儿、颤嘟嘟的绒球儿、绚丽的靠旗和拂动的飘带,还有长长短短的兵器。风来了,伴着极有力的风声,也就听到了隐隐约约的行腔弄调声,那所有越来越高亢!渐渐地,又听出了戏文中可歌可泣的内容,听见古人们在哭在笑在吼喊。随后,他们又都趁着夜色,低吟着正气之歌,缓缓隐而去。

20 世纪30 年代算得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大理的滇戏也不例外,这时也出现过空前的繁荣与璀璨。据地方史料述,仅仅大理古城里,便有七、八家滇戏班子。其影响较大的,一家是“清华班”,另一家是“云福班”。
“清华班”班主晏华清。四川人,圆圆的脸,笑口常开。他满肚子都是戏,既能演,又能编,人称之“烂肚皮”。他主演须生,擅长于苦戏。在《陈婴拾子》中扮演公孙杵白,演得声泪俱下,观众亦会泪流满面;班里有个旦角叫张月楼,是一瘦高的中年男子,听说曾有过辉煌岁月。但他演戏时,无论扮相、唱功都使人不敢恭维,特别是他的尾腔总带一个“唉嗨哀”或“唉嗨嗨”的,缺乏美感。“福云班”班主束云程,也是四川人,专演须生(黑须、白须、红生),拿手戏数十种。辛亥革命期间,束云程在南方带着班子跑码头,对帮会语言极为熟悉,他的拿手戏《巴九寨》就是一出地道的洪门戏。他扮演巴老九,一口江湖话,语如连珠,行云流水。福云班能久负盛名,就在于有他这根台柱子。
两家班子里,云南人也不少,但两位大牌班主都是川籍。所以,当时大理的滇戏中有浓辣的川味,也就不足为奇。这两班都长住苍坪街南排几院,大理古城虽为滇西重镇,也养活不了百十号人。他们经常轮流到丽江、鹤庆或下关、喜洲、凤仪、周城等地演出。
时间到1943 年9 月12 日,紫云街大戏院落成头一天的夜里,戏楼里突然有煞神大喝一声,顿时灯火大亮,女鬼从后台跑出,煞神、四灵官出台追之,煞神手洒五色粮、五色线,用宝剑剁碎黑碗,拧得一只活公鸡的脖子出血。女鬼被追出戏院前后门,煞神在戏院各处涂抹鸡血,然后返回戏楼。这是旧时戏院惯例的破台仪式,意在祈福驱邪。这也是一种仪式,暗合了中国戏起源于祭祀……当然这也是大理最早的城镇专业剧院。
远在上古时代,华夏大地就出现了以歌舞为职业的人——巫覡,其中女的称巫,男的称覡。巫覡的工作在当时很受尊重,因为人们相信他们的舞蹈与酣酒能招徕鬼神,并让神灵高兴。《诗经·陈风·宛秋》中有“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宛丘”,就是四方高,中央低凹的地方,人在宛丘中,手持羽毛群舞,观众在四周斜坡上坐着,居高临下观看着表演。
一编书是帝王师,小试去征西。更草草离筵席,匆匆去路,愁满旌旗。君思我,回首处,正江涵秋影雁初飞。安得车轮四角,不堪带减腰围。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1944 年秋,中国远征军开始腾越反攻:9 月14 日,攻克腾冲,11 月3 日,收 复 芒 市;次 年1 月24 日 夺 取 畹 町镇,友军胜利会师,怒江西岸沦陷国土全部光复了。为庆祝抗日战争的西线的胜利,十多家戏班子在各乡镇举行近百场义演。其间,“福云班”的束老板在大川宫里的一阕《木兰花慢》令曲,字字血泪斑斑。让台下近千名父老热泪沾襟,凭添出一腔怀乡报国的豪情……
世事如烟,转眼已逝百年;该来的已经来过,该散还是散去罢。在邑人依稀的记忆深处,大理所剩下的老戏楼也屈指可数了。一座夕阳峰麓的将军庙,靠景区的修复,其三进的院落里,尚保存着像模像样的戏楼子,前几年的农历八月十五,除表演传统民俗“上刀山”“下火海”外,尚有村庄或老协组织的滇戏社来助兴:在千年青树的浓荫之下,演出《火烧松明楼》《铡美案》《三岔口》等传统剧目的片段,登台者十分投入,有滋有味;但不多的观众总是走来走去的。另一座大戏楼,在蝴蝶泉边的周城古镇中,最热闹的时分是“火把节”之夜。广场上持火把者多达数千人,熊熊光亮让戏台黯淡了。台上延续着老戏或其他剧目,角儿一直咿咿呀呀来回地唱,远远地很缥缈,联想起小说《故乡》,鲁迅称之为“那夜似的好戏”。一下子,人仿佛回到童年时光,夜空里有了桨声和清凉的青蚕豆气息……这样的文化通融,我觉得很恬淡,也真的很美!
今年深秋,我回了趟洱源弥苴河畔的老家,整个村子显得异常安静。青砖碧瓦的老人协会,艳日之下,几个耄耋之年的老人闲极无聊。突然间,几人忆起当年鹤庆唐贡三老板来村里演滇戏的趣事,便自娱自乐的打起曲词“莲花落”来。
苍头(唱)打板阱子来唱戏,草鞋脱下丢满地,土台就地无高架,踢一脚来唱一句。门子(净)小儿,带马来!童(答)马儿啊无有!(净)拿根扫把棍也得哩!(答)是。(净)我尼卡虚(白语“渴水”)啰!(答)花虚(白语“开水”)支无有。(净)拿点格虚(白语“冷水”)也得哩!(击场面)咚呛咚呛咚格龙宫呛……
尽兴玩耍一番后,几位老人笑得流下热泪,用手揉着眼,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那位唱苍头的长须老者拖声道:“献丑了,莫见笑,登不得台盘哩!”我连忙解释,说自己就喜欢这样的乡土戏,唱得还有板有眼,蛮好听的哩!但他们并不留心赞扬的话,突然沉默下来;也许,寂寞的心灵需要更深度的沟通和理解,他们除去对乡土舞台艺术的痴迷外,更有对流金岁月的痛苦偏爱与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