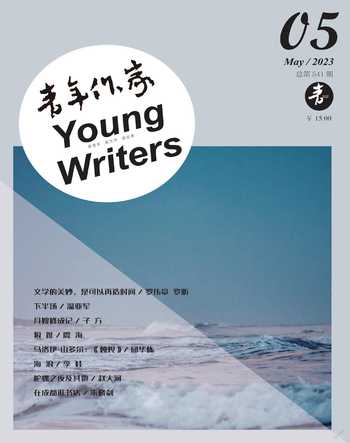狼 趾
她像一只灰蝴蝶。第一场雪飘来又飘走。
院子漆红的大门已被我拆下来,把它们靠在院墙的两侧。门梁上那盏长明灯已点亮了三天。我想象着门、长明灯和周围一切我所熟知或不熟知的事物,它们连日来都在随意且无限地延伸着。空气里弥漫着雪和泥土混合的气息,纷纷扬扬的大雪把房前与屋后的沟渠、树林、群山都覆盖得岿然不动。而我预先就把这些事物想象成某种生长在花园里的微缩生命。在园里,在枯枝和败叶的混沌里,在灰暗稠密的阴影与白色强光的交替中,我偶然完成了一场与她心灵的碰撞和交换。我和她完全处于两种相悖道德的交会之处,来认知周遭的一切事物。比方说,我分明看到雪花不是在飘,而是在飞翔;她不是在笑,而是在焦虑中陶醉逝者的嘲弄;我亦分明看到事物无知的影子,只有它才使我重新寻回胆量和适合与人共存的方式。
我形单影只地独居在这间房里,却形同于无。我透过窗户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雪,任何事物都看不见,院子里的一切都于雪光之中,岑寂于无。雪花如絮般飘到第三天傍晚,短暂停歇之后,于次日凌晨五点钟,又下了一场鸿毛似的大雪,之后,天才开始慢慢放晴。我推了推屋门,外面厚厚的积雪已把门堵得严严实实。
我踩着一把椅子,身体探出挂满雪花的窗欞,像一片叶子迅速坠落到雪地上。我没有迟疑这非偶然的过程,站起身立马蹚着厚厚的积雪朝正屋走去。我打开正屋的窗户,忽然,一阵犀利的冷风卷起一颗颗靓丽的雪粒吹到屋子里,落到炕头上、被褥上、八仙桌上、樟木箱上、阿旺身上。
冰冷的炕头上,阿旺睁开眼,双耳机警地立起来,观察周围发生的情况。三天前,也就是在我离开这间屋的那一天,阿旺就趴在炕头上,从那一天开始雪下大了,直到现在阿旺一直守护着它的主人。当窗户被我打开的那一刻,阿旺的舌头不再舔舐自己前腿上的狼趾,后来它双眼通红,怒目圆睁的刹那,我仿佛从它红宝石般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或者说,看到了它期待想看到的什么。
一座座坟茔就在离院子不远的地方。院子西面有一座小花园,花园外侧是一条从外界伸进大山的羊肠小路,这段路总能让我感到,会有某些变异的物种,深夜里,从深山老林里悄无声息地走出来,来到现实世界里。
秋冬时节的夜晚,坟茔上空总有趋蓝或趋绿的点点浮光闪现出来。有时这些光被风吹散,散落在山路上、树林间、沟渠中、公园里。壮观时,它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不熟悉的人看到这些影影绰绰的亮光,准会以为是萤火虫们出来活动呢。
她上身穿一件单薄的艳色外套,下面是一条磨白的牛仔裤和一双高帮皮靴。她从一辆迷你的汽车里刚钻出来,一只脚就陷到了雪里。她提起修长的腿,足尖轮番在轮毂上磕了磕,刚磕掉雪的皮靴,落下时,再次没到雪里。她看上去有点恼,她不再磕靴尖上的雪了,大步朝我走来。
“你挡住了门前的路。”我抢先说道。
“我怎么挡住路啦?”她不耐烦地回敬我。
“你的车挡在了门前。”我手指着她的车说。
“关你什么事?”她说。
而后她走到院门口,站在长明灯下,光线从她头顶直射下来,瞬间与自然光糅成一种特殊的颜色,而这种颜色把她的脸一下子衬到了暗处。
她摘掉头上扎有蝴蝶结的毛绒帽,然后弯下腰,黝黑细密的长发打她的头顶滑落下来,发丝贴近雪,她伸出五指轻快地梳理它们。接着,她把长发甩到脑后,重新戴上扎有蝴蝶结的毛绒帽,某一瞬间,我不经意地看到,她嘴角上端,自然而然流露出两个深圆的酒窝。除此之外,她脸上的其他特征都被那副与她脸型极不相配的墨镜罩住了。
“这里没有旅馆,这里是坟地,你走错路了,”我说,“去县城得绕过前面的这座大山。”
她没言语,这时屋里传来阿旺瓮声瓮气的叫声,那叫声似要召唤谁。
她摘掉墨镜,露出一双细眉小眼。她从长明灯下走开,回到车前关上车门,然后又像一只懵懂的小鹿,寻着自己的足迹,重新回到院门口。
“你是谁?”她冷不丁地问。
她见我没有理她,把手伸进艳色上衣的口袋,她的腿还陷在雪里,她单薄的上身看上去如此轻盈,宛如毛绒帽上那只欲飞的彩蝶,欲飞越这些坟、沟渠、树林,飞到大山的深处……她从口袋里摸出一部手机。
“这里没有信号!”我说。我还想说,这里只有雪,雪下面都是死人……
她很惊诧!同时吓了我一跳。“门呢?!”她尖声叫道,接着像头急红眼的母兽目不转睛地看我。
我停下手里的活,“门?让我给拆了,”我说,“喏,就立在那儿。”
她环视四周,目光落在院墙两侧。“你干嘛把大门给拆了?”她眉头紧蹙地说。
我狐疑地望着她,站起身说:“这儿是你家吗?关你什么事?”
阿旺立在炕头,前腿扒住窗棂,头探到窗外,它的叫声连续且洪亮,让人振聋发聩,像是有紧要的事情发生。
“你是谁?”她问我,随后拳起手指凑到嘴边哈气为自己暖手。
我拾起铁锨,一锨锨铲院里面的雪,我把雪铲到院两侧,慢慢亮出一条雪道。
“我手冷……腿和脚好像也给冻住了……不听使唤了。”
她站在原地,孤零零地站在冰天雪地里,她在说话,声音很轻,断断续续,如果传来其他声响,她的声音肯定会被淹没。而我确实听到从她嘴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好像是向着我的怯弱的求助声。
“谁让你把车开到人家坟地上的?”
她转过身,望了望埋在雪下一个个凸起的坟茔。
“我没有,再说那又怎样?”她好像突然恢复元气,在我的指责下不屑地反驳。
“你说那又怎样?不好呗,对你对死者都不好。”
“这儿我比你熟!”她趾高气昂地说。
“喏,是吗?这我倒不知道,也许吧,”我说,“不过这里没活人,只有死人,你跟死人很熟吗?”
“跟死人熟怎么了?你以为我害怕吗?告诉你,死人活人我都不怕!”接着,她喊,“阿旺——阿旺我回来啦。”
阿旺听到她的声音不再叫了。我看见阿旺伸出舌头又开始舔自己前腿上的狼趾,腑中还不时发出“呜呜呜,呜呜呜”低沉的叫声。
一阵风穿过院子,跟着又是一阵风吹过。我铲出一条宽窄适中的雪道,铲到一旁的雪,被我弄上了一层黑黢黢的脏土,我觉得对不起这些白雪,我玷污了她们的圣洁。
“帮我一下吧,把我从雪里弄出来。”她说。她换了一种和气的口吻对我说。
“你的腿和脚会被冻伤的,冻伤了的皮肉会变得黢黑,甚至还可能会被截肢。”我吓唬她说。
“你吓唬我!”她说,“你别以为我没见过,我见得比你多呢!”
“你还是快点离开,把车开走!车停在这儿特碍事!”
“那好,我把车开进院。”
“那不行。你以为我拆掉大门,为的是叫你把车开进院?”
直到黄昏。
她一直坐在夕阳笼罩下的一根笔直的圆木上。这里是花园,圆木旁边的石灰凳上,有几只爪印,和某人画像般的图案。爪印很大,像是兽类留下的足迹;画像也很大,在不大的花园里显得格外壮观,像是一个陌生人清冷的迷宫。还有,三五只麻雀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凝视她,为不吓到它们,她故意眯起眼睛,像死人一样屏住呼吸看着它们。
我唐突地蹚过她面前的雪。我感到她在自言自语,她默默在心中自由喧哗着自己的声音。她垂下眼睑与外界隔绝开一道峡谷、一条长河,有许多流水在峡谷和长河中暗潮涌动。与此同时,我无法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按照她自己的意愿正在实施的某些规则,这些规则不能干预我,而群山、树木、花园和花园里的枯枝烂叶,却能被她的规则和意志所转移或影响。还有,她的所属领地之外,幼兽们的足迹正快速穿越这片洁白的雪地,像是惶惶恐恐地要远离她,不去干扰她,或怕被她侵犯。
我本想停下脚步站在原地不动,继续看她,继续用我本性中的狡黠和诡诈来理解她,但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从我脑际一闪而过,旋即我不由自主地向她走去。此时,她好像正不动声色地隐藏着自己的想法和心事。不管怎样,我继续走向她,她还是没有看我,快接近时,我好像听到她嘴里发出沙哑的话语声,像是在渗透她压抑很久的情绪,同时我还察觉到,在她微弱的目光里,隐含着某种憎恶与忧郁,并在昏暗的微光里若隐若现。我开始犹豫要不要跟她说话,我想止住脚步,如果继续向前或许会打破眼前的平静,破坏她那特有的悲剧性气质,而只有她的这种特有的悲剧性气质,才能让周围的环境变得如此奇妙和虚幻……
越美的事物,越危险!我以为,她是冰天雪地里长得最完美的“毒菌”!
我仍然看着她,她脸色有点苍白,在这个地方,任何生命都注定有一种残缺的气质。“人人心存险恶。”她突然扬起脸认真地说。
“什么?”我怔怔地问,其实我听懂了。
“这里很冷,你总不能一直在外面坐着,你到底想上哪去?”我说。
“你错了。”她斩钉截铁地说,像是对一个很熟悉的人的质问。这时,她眸子里放出某种不确定性的光。接着她又说:“我是被阿旺从坟里刨出来的……”说完,她哭了,眼眶却没有湿润。
这是一场阴谋?她没能打动我。我甚至怀疑我们不处在同一时间和地点上。她在我眼前好像是凭空幻化出来的一个影像,或者是一朵打天外飘来的孤云。
“真的,我真是阿旺从坟里扒出来的,我没有撒谎,”她刻意压低声调平缓地说,“当时,我趴在妈妈的身上,周围泛着绿色和蓝色的光,像萤火虫一样的光在飞,它们一直在飞,后来我把头顶上的雪用手指抠出一个小洞……”
她逐字逐句,我能听清她说出的每一个字。而且她一點也不犹豫,每一句话就像风一样围着我低吟。我背靠一棵年长的树坐下,她的话就像要把我领进她内心世界的某个地方……很快,夜色拉下帷幕,我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显得微乎其微了。
“死人的骨头发出绿色和蓝色的磷光,阿旺看见了光,便跑了过来……”
她的出现,如同把花园、坟茔和时空,隔成若干条河流,她就像某一座河流上的孤岛。夜雾轻袭时,我仿佛看到夜晚的光芒,夜晚的河,她就是我所追寻的那条河流上的光。
“阿旺兴致勃勃地去追那些光,它跑过来,然后发现了我,它用舌头添开了小洞,够到了我的眼睛。”
后来,我和她坐进车里。车里也很冷,我们蜷缩在车里,我一定是丧失了判断力,那些属于我的想法,好像都在这冰窖一般的车里消失了。我们就像悬挂在冰窖壁上的两个钟乳,被迫等候野兽嗅到我们的气味,然后把我们吃掉。我们最后的结局将在这冥界似的世界里无从谈起,甚至缺失了被审判和被漠视的痛苦,因为,我们正处在同一恐惧中战栗。
“当时我没有感觉到冷,不像现在这样,”她说,“厚厚的雪像毛毯一样盖在我身上,就像待在雪的子宫里一样温暖舒适。”
我轻抚车窗,她坐在一旁,我们的想法似在你追我赶,她冥想到的事情我在同一时刻同样也冥想到了,然而我们又彼此平行跨越同一时空。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不说话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当我再次想起先前那条河流时,她却突然对我说:
“准是天气太冷了,车子才发动不了。”
她接着又说:“你真的不要相信我,我只想按自己的方式去做。”
我们又彼此看着对方。我情不自禁地将手伸到车窗外,我感到外面的世界好大,许多星辰都在坠落,我仿佛踮起脚尖去够散落在深渊里的头发。“你说星星上面有深渊吗?”她问我,那声音仿佛是从渊底发出的回声——天籁般浑厚的回声。趁我喘息之际,真的很幸运,我的目光已然捕捉到日月星辰万花筒般的天象……此时,她呼出温热的湿气,纯洁无瑕,我看着它们飘到各处,忽然,这个陌生人让我不经意地察觉到,隐藏在她恬静外表下面那种惴惴不安的渴求,这种渴求,就像是烙在她身上的某种擦拭不掉的徽案——刻骨铭心的徽案。
此时我无言以对,每一瞬间的奇迹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我无意揭秘她高大如要塞般的内在世界,并且她那“个性”的面罩是我们绝佳和最理想的屏障。无论她内心是阳光还是邪恶,我没再跟她交谈下去,我不时注视一下她的眼睛,她把车窗打开又关上。虽然无法预料,但我确实看到了某种封闭已久并贯穿她周身的光,那一闪即逝的光,就像她皓洁的牙齿,等到我沉溺探究它如何形成的时候,她就会闭上嘴巴,把我想要知道的一切都隐藏到她心灵的深处,事实上,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是她某种迫切需要救赎的渴望。
她推开车门跳下车,如梦方醒般冲天长啸。
我们重新回到花园,坐在刚才那根笔直的圆木上。我不经意碰到她的手,不由令我信服地以为:她内心如梦般忧郁和迷茫的深处,却是与我刚才的思索相悖的,因为我忽然觉到她心房跳得如此从容和淡定,手温热无比。
我准备了篝火,火焰腾起那一刻,足够照亮花园里的一切。花园外面光秃一片,白雪泛起微红的光泽,褐色的枝丫被无尽的夜色吞噬殆尽,而她孤寂的眼神像是映出另一座孤寂的花园。这时,她走到离花园不远处的一个凸起的坟旁,拾起一根粗细均匀的树枝去刨那个坟……夜空晴朗无比,火光已燃到半人之高,令人惊诧的一幕突然发生了。她指着一处坟茔,镇静地说:“这是我弟弟的坟,但不是我亲弟弟,小时候他被拖拉机碾死在花园外面的山路上。”
她还说:“这一切或许是心灵感应吧,我猜老家伙已死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莫名其妙地回到这里。”
当晚,我恍惚记得,整晚,星空展现出从未有过的灿烂。直到后半夜天上忽然又飘起雪花,成双结对地飘下来,落到篝火里,落进大山、树林、花园、坟地,落进我们的躯体里。现在她只顾看着篝火,身体已经濒于垮掉边缘,她无法再后退一步,我注意到她迷惘无措的神情,时而振奋,时而又陷入死亡的深思。
“我恨他!”她最后说。
这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思索:她一直活在某种痛苦的逆境中,刻骨铭心地恨着他。
她好像对任何事物都不以为然,尤其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这一段非同寻常的时光,竟空无所有。她把时间全给肢解了,无所作为,她宁愿不要它们伴随身边,她觉得它们是累赘,是在劳役自己,是永无休止周游中的绊脚石。尤其在她激动时,火堆溅出的星火跃上她的指尖,她把指头贴在唇边,我亲眼目睹她指尖骤燃的情景,可是她却无情地把骤燃的火焰吞到了腹中。
“老家伙是看坟人。”她说。
“我知道。”我说。
“阿旺舌头够到了我,它舔醒了我,我眯起一只眼,另一只眼从小洞里看见外面湛蓝湛蓝的夜空和数不清的星星,说明我还活着,”她说,“后来,老家伙过来把我从坟里拽出来……”
一瞬间,火,跳到她的身后,像是一股神奇的力量驱使她止住话语,她猛然将手伸向火堆。
那夜,她反复从起点返回终点,又从终点重回起点,过去的旅程一直在她脑海里周而复始,这反倒使她更加精神,使她在夜空中投落出她在过去与现在两个世界的影子:一是归罪于她命中注定难以逃避的旧世界;二是她美丽而又难于接近的新世界。不论想要进入哪一个世界,她都必须适应和接受双重命运的考验。而这两个投影般的世界让我望而却步,我不断往后拖延时间,放慢时间的脚步,而时间一经过去,无论是谁,再想找回那非同一般的时刻,恐怕比登天都难。
“后来,我成了看坟人的童养媳,但他儿子短命死得早,再后来我就成了他的奴仆……从此,我每天活在恐惧之中,每天我都在死亡与逃避死亡的幻觉中徘徊……白天他带我去坟地,还有阿旺,一走进这片令我胆战心惊的坟地,我就怕得要命,怕死人从地下蹿出来夺走我性命。还有,他是个非常恶毒的人,几乎每座坟都被他刨开过,搜罗里面值钱的东西。如果棺椁里没有值钱的东西,他就气急败坏地把人家的坟敞着不管,等野狗来把死人尸体拖走吃掉。另外,他还贪得无厌地经常拿走给死人上贡的酒,晚上喝多了,就强暴我,往死里打我!我恨他,诅咒他!诅咒他有朝一日也被野狗们叼走吃掉,最好吃得連一根骨头都不剩!”
“那你怎么不逃走?”
“到了晚上他就把我关在樟木箱里,去坟地的时候就用一根绳子把我拴在他腰上。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我怎么哭怎么喊,来坟地的人都以为我在哭丧呢。”
她还想继续往下说,但欲言又止。她低下头,看着白雪皑皑的地面,忽然我们两人又陷入静寂无声的沉默之中。
我漠然看着她,渐渐感到弥漫在她身上的那种情绪,正悄然抬升周边的景物。此时夜色愈显清透了,零零星星的雪花仿佛在夜色微澜中飘然起舞。她那明媚的面庞正以一种激奋狂热的神情冲击着我。事实上,天空已渐清渐明起来,现在雪花只零星飘下来几朵,而我只等着篝火完全燃烬。
或许,她什么都不是,只是在我百无聊赖时意外闯入我生活的一阵清风、一场游戏、一场梦。不管她以何种方式出现,不管我从中获取多少使她慰藉和伤感的回忆,我都不想再听她述说了,她只会耽搁我,扰乱我的思维,况且她也会把我从现实世界中剥离出去,而我只希望她是一个普通的过客,短暂停留在这里,与我消磨一段时光,调侃几个真真假假的玩笑,或讲几个耸人听闻的故事。
我决定不再跟她聊下去。
现在我已做好最坏打算,甚至把生命当赌注押上去。
清晨六点钟,我忽然睡着了,在此之前我感到周身麻木,一种悲凉从内心袭来。现在花园里已经没有任何可燃之物了。我双臂交叉在胸前,紧紧抱住自己。我知道,总不说话会让她感到不安,半梦半醒间,我试图让她不要走远,并且想告诉她我的想法。
清晨车里冰冷异常。梦,有时也能让人感到舒适和可靠。可这一切却似乎预示着不祥,或存在某种欺诈与被欺诈的可能。我该跟她谈清楚,我会为她着想,但不会为她做她想做的事情。而她那种让我难以觉察的心思和举动,委实让我感到不自在,并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困惑和焦虑。我甚至难以辨认,她与我真实存在的可能。
我说:“我有一个想法……”
她笑了,不让我继续说下去,然后专注地看着我说:“别担心,我来只是想看一看阿旺而已。”
她还想解释。我冲她笑笑,为缓解一下她紧绷的神经和消除对我的戒备,我闭上眼睛重新回到睡梦里。
下第一场雪的那天,西伯利亚冷风长驱直入灌进这间屋子,整个屋子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冰冷的冰窖。但阿旺依旧不离不弃地日夜守在主人身边不准任何人靠近。
阿旺是一只狼性十足的苏联红犬。前不久,我见阿旺跟一群刨坟的野狗撕咬在一起,最后一死三伤。阿旺虽然咬胜了,但它前腿的狼趾却被野狗们咬得血肉模糊。
阿旺抬着被咬伤的前腿一蹦一跳地回到家。那段时间,阿旺看上去总是昏昏沉沉、萎靡不振,后来又变得暴躁不安,有时还会突然间狂吠不止,再后来,有几次它竟突然倒地,像被电流击中那样抽搐不停。“阿旺恐怕得了狂犬病。”看坟人这样对我说。有一天,主人在给阿旺缝合狼趾上的伤口时,阿旺突然回头咬了主人一口……
就这样,看坟人被阿旺咬后不久便开始高烧不退,死前还口吐白沫,浑身剧烈抽搐,直到咽气。
“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魔鬼!活该被阿旺咬死!”她说。脚下的雪被我俩踩得嘎吱作响。
“那你还来找他?”我说。
“他该补偿我!”她说。“我恨他!他罪有应得!”她愤懑地又说。
……
我们两人一前一后,走在白雪覆盖的坟冢间,在这个封闭的花园的迷宫里——我感到透不过气、说不出话来。
“阿旺才是我真正的救命恩人。”她小声重复前面的话。
“我没有否认,但它只是一条狗,现在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了。”我说。
“记得逃出去的那天,阿旺跟我走了很远,它舍不得我走。”她伤感地说。
这时,有一户人家正在迁坟。今天是个吉日,一大早坟前人头攒动,挖出来的土堆在坟的四周。大概过去一个时辰,早已腐败的棺椁才被挖到,接着有人从棺椁里小心翼翼地取出里面的骨骸,再小心翼翼地移入另一口新棺椁里……孙男娣女一族人都跪在坟旁,或许野狗也在不远处正盯着他们,伺机而动。
鞭炮把地上的雪炸开一道道裂痕,六个壮汉四平八稳地抬起棺椁,迁坟一族人的神情木木的讷讷的,全部跟在新棺椁的后面缓慢行走,尔后鞭炮声再次响起……
我知道,她始终不满我拆掉她家院子的大门。另外,阿旺还一直卧在冰冷的炕头上,期待着她回来。她走进院子时,笑了,笑得有点勉强,其实,她快要流泪了。阿旺像突然从逆境中惊醒过来,它用前腿支撑起身体,眼睛睁得大而圆亮。果然,她哭了,泪流满面,让我没有能力再去判断她。她眯缝着泪眼跟阿旺对视了一会儿,直到阿旺滞重、颓废的眼睑转向别处。
她端详着阿旺,她站在炕前,像爱抚亲人那样抚摸阿旺的头。阿旺没有像先前那样狂吠,它准是认出了她,任凭她对它的怜惜。
夜色再次变得浓重,她突然问道:“那个死鬼留下了什么?”
“留下了什么?”我錯愕地反问,“你指的是遗产?”
“反正是他该补偿我的东西!”她说。
“他好像就这些家当,”我说,“据我所知,他就留下这个院子、两间房子和阿旺,再有桌椅板凳、樟木箱子和被褥,就这些了,够补偿你吗?”
“这些东西我全不要,我要的是他真正留下来的遗产!你别跟我装傻,”她厉声说道,“你到底是谁?为什么待在这儿?”
“反正他就留下这些,”我无奈地说,“我想静一会儿,不想跟你吵。”
那天晚上她疯了一样地跑进跑出,四处闻味,到处乱翻乱找。我无法阻止她,她歇斯底里地折腾了大半宿,到了后半夜,她终于累了,精疲力竭地坐在炕头,抱着阿旺小声地呜咽。
“是啊,只有阿旺才知道你过去的境遇,”我说,“但你还是快点走吧,这里真没有你想要的东西,他确实没留下什么值钱的遗产。”
“不,我不走,我哪里也不去。”她呜咽道。
“你在这是自讨苦吃。”我宽慰她。
“那个死鬼不补偿我,我就哪也不去!”
“那又何苦呢?他已经死了,况且他于你也有救命之恩。”
“他救了我就拿我当畜生一样糟践我——我生不如死!”
“可是他已经死了,噩梦也已经过去了。”
“他是个魔鬼!折磨了我那么久,我诅咒他——咒他永远不得好死!”她恶狠狠地说,“你把门给我安装好,我要住在这里!”
“门是给他做棺材板用的!”
“他不配有棺材,让野狗叼走他吧!”
后半夜我困得实在受不了了,眼睑重得像在上面拴了两个铅坠儿。我对她对我的请求实在无能为力,我一再对她解释:我怎么晓得看坟人有什么贵重遗产?显然,我已跟她形成对立。她相信一切贵重的东西还在,而我认为这里一切皆空,而且我真的无法深入她的内心去揣摩她的心思。此时此刻,我别无选择,只能和她一起挨到天亮。直到远山浮现出一抹殷实的红光,她还在想进行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看得出来,她非常急切想要拿到这份遗产,失败前,她脸上流露出自命不凡的表情,而我无动于衷地守在屋子一隅看着她。其实,我并不否认宝贵的遗产对她未来生活的重要性,至少能够给她带来一点物质上的补偿和精神上的慰藉。
清晨,她独自走向空旷的花园……很快,她的身影便延伸到花园外面,她开着车在茫茫雪色中渐行渐远。当晚阿旺死了,移动它时,忽然,一张叠得非常紧凑的小纸条打阿旺狼趾的缝合部位掉了下来。我拾起纸条,打开它,上面模模糊糊地写道:谁把我葬在花园里,遗产就归谁。阿旺知道东西藏在哪,它会带你找到。
我把阿旺和看坟人的尸体殓入用门板做的同一棺材里,再把棺材移入花园。雪又下了一层,两天前被我和她踩踏过的地方,现在只露出一点微不足道的破绽。我静坐在圆木旁的石凳上,一边想着一个没有尽头的问题,一边观望那几只残留的动物爪印和那幅令人心悸的画像。我相信这个梦是真的,真相就混迹在白雪皑皑的花园下面,那源于痛苦的一切分支终将隐没在无望之中,消亡在深邃的时间之中,等到那个时候,花园里的一切还会在一种持续壮丽的色彩中沉浮,当她再次光顾,以一种无畏神情和姿态,坐在石凳旁的圆木上凝神时,便会感知。
【作者简介】震海, 生于1970年,诗人,小说家;著有诗集《蓝镜》,长诗《我飞越海洋》《万世沧海》(上、下部),中短篇小说集《遗落是风》,长篇小说《谲海苍狼》等多部;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