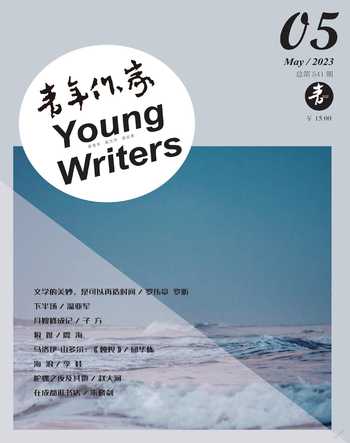为柔弱的人心造象
生活在岳阳水边的作家李娃,擅写忧伤的心灵故事。故事的背景大约是些临水的小城、乡镇,一些柔弱的男女,在冗长的生活之海里,内心涌起的却是滔天大浪。作者依着角色的心,写出他们的柔肠与狠戾,恍惚间,让人看到余华、废名和伍尔夫的影子。这么说并非抬举,因为李娃与这些文学大师们走着同样的探索之路——为那些柔弱的人心造象。
心之象
“传说中有一座城,古时名‘琴棋望,在水中央,只有一座长桥与外界相连……琴棋望人没有关于过去的记忆,也不能离开那里。除非掌灯人驾来了他的船——须在一个星辰之夜,等一道奇异的光出现。”(《传说》)
“‘我坚信我的船还清醒;不过它要是沉了,它或将很好地答复那喋喋不休的推理,那些阻止我向你抵达的海浪。她给他念了一首诗。她说,她几乎被这里边的几个句子给迷住了。因为那层层的海浪。”(《海浪》)
“下山喽,正是好时候!噗——低低的一声,悠长悠长的,徒弟觉得脖子一凉,疼痛从那儿裂开了一条口子,咝咝地把他裂开了。他站在悬崖,狂风呼啸,深不见底,脖子上有一把刀。”(《下山》)
几个短篇小说的文眼并不难找,小说家几经裁剪,为角色们最刻骨的希望、痛楚和心念精心造象。作者用如水的笔触,随着人物的心境敷衍流转,最终撇下了事件的表层,走向了角色的心灵深处。对于三三来说,她的心象被镌刻在一个有关“琴棋望”城的传说之中,小城女性的生与死、幸与不幸,都宿命般地被安排在“传说”里,传说于是成为了三三的梦魇,她将一直按照“传说”的命运预言去安排自己的心(《传说》)。对于无名的男人,他的心象是海,与一个女人所写的海浪的诗有关。海浪是他们婚外情感的化拟,一波又一波地推攘男人的心弦(《海浪》)。对于屠夫的徒弟,他的心象则是杀猪的情境,杀猪是徒弟心中最深的障碍,作为屠夫的徒弟,手刃生灵,背负着成人礼式的象征意义,在封闭的山中也与尊严,特别是在心爱的女人面前的尊严相关(《下山》)。作者意识流一般看似随意挥洒的笔意,却是内里藏锋,熔化成雕刻刀,造出一方人物之心境。小说的意味,人物的情与念、爱与恨、决绝与侮辱,都化入在这片幽冥的心境之中。王夫之把诗所做的事情称为“象其心”,写诗,就是要去摹写“视而不可见之色,听而不可闻之声,搏而不可得之象”。李娃的小说写作,倒是很贴切古典诗学中纠缠着心学的一脉,呈现出虚幻恍惚的美感来。
说作者的小说有虚幻之美,并非是空言,在故事里,无论有关“传说” “海浪”和“杀生”的情境与造象如何夺目、撼人,却始终是茶杯里的风暴而已——或者说,只是人物内心的惊心动魄,对角色的现实生活几无改变。徒弟复仇式的杀生,只是屠夫弟媳悸动之下的一场午梦,真实的场景不得而知;三三拼命去寻找离开琴棋望城船只与掌灯人,大约也是生病了的主人公,躺在卧室床上的臆想;《海浪》的现实感会更强一点,但无论女人给男人的信件中海浪的诗句如何撩动男人的内心,男人最终也曲终梦醒,回归到自己曾经厌恶的家庭。心之象在小说中迷离恍惚的美感,也就是人物在动念与退却,在入梦与梦醒,在秘境与现实的辗转游移之间。
患上歇斯底里症的人
心象的虚幻,与故事里的人物有关。这些生活在不同场景里的人物,都是些柔弱之人。因为柔弱,所以缺乏真正决绝的行动力,他们无法向外介入,转而向内筑起心的美学巫术。被家庭生活和妻子的关系网深深困住的男人,一位没有胆量拿起屠刀杀生的屠夫徒弟,因为好友的死而永远被一个本地传说俘获的三三。“柔弱”在这里并不是贬义,在人性的层面上,它甚至指向了一种底层的善良,以及对不合理的人际、社会,既微弱也用尽了全力的抗辩。在李娃以心写心的写作中,我们也能看到,作者费心血去辩护的,是怎样的一种人性。
在三个小说主人公中,《传说》里三三的性情要更独特一些。她自然是柔弱的,打小就被学校的同学欺负,必须在小桃的庇护下才能拥有正常的青春生活,长大后又与病症相伴。不过,与徒弟和男人相比,她刻骨的忧伤显得更加无所来由,看不出有什么外界的壓抑:在小桃殒命之后,三三似乎就难以正常维持她的生活了,她着魔一般地陷入小桃曾告诉她听的传说故事里去,把所有精神的寄托,都投入到一个缥缈的传说故事里。她的忧伤也更炽烈,一股脑地,誓要将自己的命搭进去。这个与沈从文小说同名的人物,带有李娃小说的典型气质,一种过分投入的情绪臆想。文化研究领域曾把这样的精神状态称之为歇斯底里症。
在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患有歇斯底里症的代表人物。亲近一点的,有《简爱》里那个被关在阁楼上的疯狂女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郁达夫笔下那些在日本报国无门、空有一腔热泪的青年男孩子。不过,三三没有郁达夫笔下的感时忧国的情愫,也没有勃朗特那些欲说无言的性别压抑,她的壮烈忧伤,连着故事发生的虚无缥缈的水边小城,看不清头绪、理不清逻辑。三三所展现出来的特质在作者的写作中是很典型的,李娃的小说人物,总是处于一个更幽闭的情境当中尽情地沉溺于忧伤,个人的情愫就是个人的,而与周遭的世界与社会的节奏无涉,此刻的忧伤也只停在此刻,没有伤痕过去形成的脉络,也看不到情愫在未来转换、调试的可能。这倒是能在李娃身上看到中国90年代以来先锋小说的一些痕迹,又或许,仅仅是因为作者在水边生活,因而沾染上了水的耽溺与漂移。
植一点“土”
似水的写作是李娃的特色,自由游走于人心的深处,为人心幻化出美的妙境,但也可能成为作者的缺憾。因为似水,故事的逻辑,都往往随着语言的舟筏任意游走,少了一些更坚硬的骨节;因为似水,人物成为情绪的蓄池,沉溺、走不进更大的天地;因为似水,故事的情境也过于漂浮,缺少了一些与现实语境的关联性。换句话说,李娃可能需要给自己的写作植一点“土”。
我仍然想从三三的故事来说明。在故事里,三三与她的女性朋友小桃的关系,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少女时期的丁玲和王剑虹。王剑虹就像小桃,勇敢、开朗、积极,热烈追求着“革命”的“传说”;丁玲就是三三,一直是王剑虹影子般的存在。丁与王爱上同一个男人,王剑虹的早逝,这都与小说情节特别相像,只是,在现实的历史之中,丁玲在王剑虹逝世后永远走出了女性窄小的情愫,将无法排遣的痛楚推向了更广阔的写作事业。讲述丁玲的故事,并非是要幼稚地褒一贬一,而只是想说,正如丁玲的生命所展现的那样,个人的情愫、忧伤、痛楚,的确能被导引入大的社会空间,奔赴更广大的土地。真实的三三,那个没有在绝望之中死掉的三三,她要追寻的“传说”,都会显出历史与社会的参数来。
希望李娃的小说能植一点“土”的意思,也就在这里。作者的灵气是毋庸置疑的,倘若能为这份灵动培育一点历史感,增加一些心灵故事与社会的互动与共振——以任何的方式,比如情境的描摹、人物的选择——这份灵气大概会收获更多的读者,也会在让更多人心有戚戚的阅读中,变得更绚烂、更飞扬。这亦是一个批评者对写作者的祝愿。
【作者简介】刘启民,土家族,1993年11月生于湖南张家界,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供职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以及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在《当代文坛》等刊发表研究与批评文章若干;现居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