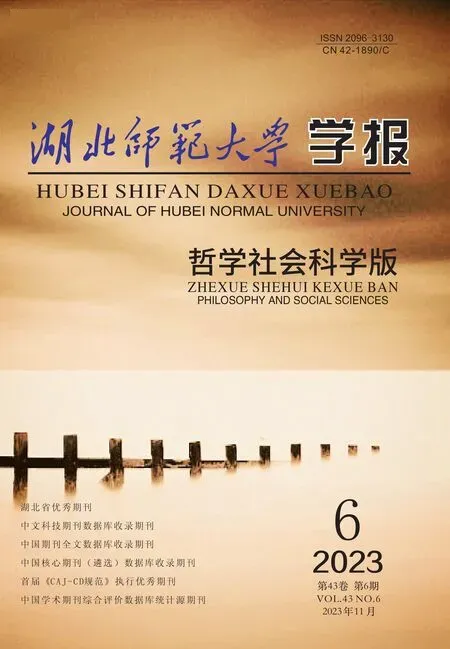繁钦之个性与其文学创作之关系
李洪亮,张宸睿
(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一、繁钦“无俭格”之个性申论
曹丕《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一观点是时人对文学与作家个性、作家气质关系之普遍看法,它揭示了文学风格形成的内在机制,成为考察作家文学风格形成的重要途径。繁钦身上有着建安时人普遍存在的通脱之风,《三国志》卷二十一记载他“以文才机辩,少得名於汝、颍。”[1]宋代崔敦礼《宫教集》亦云:“繁钦流咏于东都”[3]卷一,具有典型的才子型文人的特征。后因中原战乱,与杜袭、赵俨等人避乱荆州。常理言之,繁钦远走他乡、寄人篱下,行为当以静默自守为上策,然而,据《三国志·杜袭传》记载,当时繁钦的行为却十分张扬,“数见奇於表”,以致杜袭直接对他劝喻,曰:“吾所以与子俱来者,徒欲龙蟠幽薮,待时凤翔。岂谓刘牧当为拨乱之主,而规长者委身哉?子若见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与子绝矣!”听闻此言,“钦慨然曰:‘请敬受命。’”[1]繁钦如此躁动自显,虽经“通财同计,合为一家”[1]“时人号为管鲍”[4]卷二的关系极为密切的同郡友人的劝说,才表面上应允,改正自己“数见奇於表”之露才扬己的张狂行为,但繁钦真实之个性却也由此得以彰显。
在避居荆州期间,繁钦和避居于此的王粲往来密切。晋人习凿齿《与桓秘书》称:“吾以去五月三日来达襄阳……裴、杜之故居,繁、王之旧宅,遗事犹存,星列满目。”[5]《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引《襄沔记》称:“繁钦宅、王粲宅,并在襄阳,井台犹存。”[6]金人李俊民在《庄靖集》卷六《仲宣井》一诗称:“谁把石栏移便坐,并邻又得一繁钦。”自注:按《耆旧传》:“王粲与繁钦,并邻同井。”[7]卷六这说明,繁钦、王粲在荆州期间是比邻而居的。而王粲本人的性格恰也是“率躁”的,并因之“见嫌”[1]于人。《三国志·王粲传》记载:“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1]《三国志·杜袭传》记载:“袭尝独见,至于夜半。粲性躁竞,起坐曰:‘不知公对杜袭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岂有尽邪?卿昼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1]所谓物以类聚,繁钦与王粲在刘表处,同朝为官,退朝之后,两人又“并邻同井”,如此朝夕相处的、关系密切的生活,两人之性格要么原本就接近,要么后来相互影响后才趋同。王粲“躁竞”之性格也必然会在繁钦身上落下印迹,理所固然。
《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鱼豢曰:“寻省往者,鲁连、邹阳之徒,援譬引类,以解缔结,诚彼时文辩之俊也。今览王、繁、阮、陈、路诸人前后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论者,时世异耳。余又窃怪其不甚见用,以问大鸿胪卿韦仲将。仲将云:‘仲宣伤於肥戆,休伯都无格检,……如是彼为,非徒以脂烛自煎糜也,其不高蹈,盖有由矣。’”[1]认为繁钦之“不甚见用”“其不高蹈”,主要是缘于其“无格检”之性情。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谈到“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时,特举繁钦“性无俭格”为例。关于“俭格”,王利器解释曰:“俭格,犹言法式。”[8]
“性无俭格”,即性格之无法式,犹言性情通脱、随意者也。如此个性之人,其政治上“不甚见用”“不高蹈”,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在汉末那个风云激荡、“风衰俗怨”、而思想渐趋自由的时代,也必然导致其为文的不拘常规、新异,从而促成其文学创作上的斐然成就。
二、繁钦文学创作的开新
个性之不落俗套,在汉末这个“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的时代,在文学创作上必然会表现出不甘流俗、出奇开新的局面。繁钦的创作正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特点。繁钦作有《明口赋》:“唇实范绿,眼惟双穴。虽蜂膺眉鬓,梓……。”[9]
关于此赋,钱钟书先生评论曰:
按题与文皆讹脱,而一斑窥豹,当是嘲丑女者。同卷尚有钦《三胡赋》,描摹胡人状貌之恶,则钦此篇题倘为《胡女赋》耶?“眼惟双穴”与《三胡赋》之“黄目深睛”、“眼无黑眸”剧类。“蜂膺”或是“蜂准”之误,杜甫《黄河》所谓“胡人高鼻”。目深鼻高乃胡貌特征,《世说·排调》即记王导笑胡人康僧渊之“目深而鼻高”;《南部新书》戊卷载唐睿宗咏壁画胡人头:“唤出眼!何用苦深藏?缩却鼻!何谓不闻香?”;《云溪友议》卷中载陆岩赠胡女诗:“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睿宗下句谓鼻塌亦能闻香,故不须高耳。“范”疑“规”之讹……,画也……;“眉”疑“蝟”之讹,谓鬓毛森刺,犹李颀《古意》之言“鬓毛蝟毛磔”。宋玉《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刻画美人丽质妍姿,汉魏祖构,已成常调,《好色赋》旁及丑妇,以资烘托:“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钦此赋殆本此意,进宾为主,改衬笔为专写,遂开《先唐文》卷一刘师(笔者案:查严可均《先唐文》“师”当为“思”)真《丑妇赋》等俳文矣。[10]
如此,则此赋应为《胡女赋》,赋文当为:“唇实规绿,眼惟双穴。虽蜂准蝟鬓,梓……。”繁钦又有《嘲应德琏文》:“应德温云:昔与季叔才俱到富波,饮于酒肆,日暮留宿。主人有养女,年十五,肥头赤面,形似鲜卑。偶说之,夜与通奸。便住足下。”[9]
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多是光彩照人的美人。从宋玉、司马相如开始,历代赋家,各显神通,不知精心撰写过多少美女、佳人、娇色之赋,而描写丑妇的作品却为数甚少。虽则《庄子》《淮南子》《韩诗外传》《列女传》《东观汉纪》等典籍中,有描写丑妇的文字,然大抵叙述女子容貌虽丑陋,德行则有可取之处,对丑妇少有嘲讽者,故而,这类形象描写的意义,在于引导人们重视内美,即所谓“好德”者也。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写登徒子之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可以说是赋中最早写丑女的文字。中经两汉四百余年的消歇,直至繁钦的《胡女赋》,这类作品才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由此,亦可见繁钦在文学题材上的开拓意识。《文心雕龙·谐隐》曰:“潘岳《丑妇》之属,……尤而效之,盖以百数。”[11]说明晋代以后,写丑妇的作品为数不少。然而汉晋之时,此类作品导源者却非繁钦莫属。同时,包括潘岳的《丑妇》在内,这“盖以百数”的作品大都失传了。由此,更可彰显繁钦之《胡女赋》《嘲应德琏文》在文学史上之重要价值。
此外,繁钦还有不少嘲谑文,如《三胡赋》,赋云:“莎车之胡,黄目深精,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頞,高辅陷口,眼无黑眸,颊无馀肉。罽宾之胡,面象炙蝟,顶如持囊,隅目赤眦,洞頞仰鼻。硕似鼬皮,色象娄橘。”[9]嘲笑大异于中土的胡人,运用对比、夸张的手法,对其容貌进行肆意的戏谑,令人捧腹不已。又如繁钦《嘲杜巨明》文:“杜伯玄孙字子巨, 皇祖虐暴死射之, 神明不听, 天地不与。降生之初, 状似时鼠。厥性蟊贼, 不文不武。粗记粗略, 不能悉举。”[12]《文心雕龙·谐隐》曰:
“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于是东方、枚皋,餔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嫚媟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亦有悔矣。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虽抃推席,而无益时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辔。……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玚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亏德音。岂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欤?[11]
这种文体渊源有自,由来已久,虽无关大道,亦时有讽谏之意。但自汉武帝时东方朔、枚皋以来,社会思想渐趋禁锢。在汉儒思想一统天下之时,就连人们的笑容似乎也僵化了。故而,文学创作上,“谐隐”一类自然也就少有人作。直至汉末三国之际,随着社会思想从儒家定于一尊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人们似乎也能展示自己的愉悦的笑容了。人们对一些新异的人和事进行有异于儒家正统的嘲讽,或许这种嘲讽,在他们而言,纯粹是为了调笑,此外,再未有任何附加的意义。但是,我们认为,繁钦的这种创作出现于“魏晋滑稽,盛相驱扇”的盛况之前,开创之功故是不容小觑。这些作品与曹丕“因俳说以著”的《笑书》一道,促进了这一时期文体的解放,解放了人本身固有的自由精神。
繁钦有《与魏文帝笺》①,文中对年仅十四的薛访车子高超之演唱技艺及此种技艺带给听者的感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摹,尤其是对薛访车子“潜气内转,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细不幽散,声悲旧笳,曲美常均”,“曲折沈浮,寻变入节”的“喉啭引声”艺术的描写,其新异、幽微之程度都超越前人,曹丕在《叙繁钦》中评该文曰:“其文甚丽。”[13]《三国志·繁钦传》注引《典略》评曰:“其所与太子书,记喉转意,率皆巧丽。”[1]这直接启迪了唐代李贺《李凭箜篌引》、白居易《琵琶行》、韩愈《听颖师弹琴》中的音乐描写。其中对薛访车子演奏效果的描写,特意用了“哀感顽艳”一词。该词的内涵,曾引起后人很大的探索兴趣,钱钟书先生认为:“两句相对,‘顽、艳’自指人物,非状声音;乃谓听者无论愚智美恶,均为哀声所感,犹云雅俗共赏耳。”[10]缘于该文的巨大影响,薛访车子的“喉啭引声”便成为善歌者的代名词,如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十九《虎山桥夜泊》诗:“薛家车子十四,白傅歌童一双。”同书卷二十四《红娘子》词:“唤薛家车子近前歌,胜名倡謇姐。”[14]卷十九此外,在某些用语的使用上,繁钦也表现出不同凡俗之处。如“自左马真、史妠、謇姐名倡”句,“其史妠、謇姐,盖亦当时之乐人。”又《说郛》卷十七上“妇女称姐”条曰:“繁钦《与魏文帝笺》曰:‘自左……’以是知妇之称姐,汉魏已然矣。”《文选旁证》亦云:“其史妠、謇姐盖亦当时之乐人。《能改斋漫录》云以是知妇人称姐汉魏已然。张氏《云璈》曰:似是当日女伎。”[15]卷三十三而此前的文献则没有发现“妇女称姐”之例,可见这种用法,虽则“汉魏已然”,然进入文学作品,繁钦虽不能说是最早的例子,也是较早的例子。
繁钦之《定情诗》也是一新时人耳目之作,郭茂倩《乐府解题》认为:“定情诗,汉繁钦所作也。言妇人不能以礼从人,而自相悦媚,乃解衣服玩好致之,以结绸缪之志。若臂环致拳拳,指环致殷勤,耳珠致区区,香囊致扣扣,跳脱致契阔,佩玉结恩情,自以为得志。而期於山隅、山阳、山西、山北,终而不答,乃自悔伤焉。”[16]《玉台新咏·定情诗》卷一清人吴兆宜于题下注此诗曰:“魏杂曲歌辞。唐乔知之《定情篇》、施肩吾《定情乐》,皆本此。”[17]明徐祯卿《谈艺录》曰:“繁钦《定情》本之郑卫……张衡《同声》亦合关雎,诸诗固自有工丑,然而并趋者,托之轨度也。”[18]清人田雯《古欢堂集·艳体诗序》:“艳体诗缘于《毛诗》……汉唐以来,张衡有《同声》之作,繁钦著《定情》之句,下暨子夜清商、西昆香籢诸篇, 温、李、段、韩诸人,亦云艳矣。”[19]序本诗渊源于《诗经》之“淫”诗“郑风”“卫风”,我们姑且不论此诗是否有别的微言大义,单就诗歌描写本身而言,其对两性关系大胆热烈的描写,就强烈地冲击时人耳目,和东汉社会在即将动乱、思想即将解放的时期张衡创作的《同声诗》一起,接续中断已久的《诗经》“郑”“卫”之传统,对汉末建安时期的思想解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此等创作和建安时期的曹植的《洛神赋》《塘上行》②一样,在对男女关系的热烈的描述中,有这样那样的寄托,陈沆《诗比兴笺》评曰:“夫休伯在魏,书翰见优,宾僚燕好,未为不遇,何哀苦若此哉。观魏文《与吴质书》,历数存没诸人,不及主簿,得无情好不终,骚怨斯作乎?彼甄后结发,尚至塞糠,子建连枝,犹泣煮釜,繁与二丁、德祖俱摒七子之列,知此《定情》之作,必非无病之呻。始合终睽,彼凉我厚,君臣朋友,千载同情。渊明《闲情》之赋,此导其前修;平子《四愁》之章,此申其嗣响。昧思比兴,遂等闲情,辄复举隅,以当论世。”[20]如此可见,繁钦虽则“性无俭格”,但也和王粲一样,不乏在政治上积极作为的心志。在不便明言理想之时,也会吸收屈原以来的以美人喻己的创作模式,以女无佳配隐喻自己政治上的幽微失意,这种模式在中国以后的文学创作中被大量采用。而且,该诗形式上,亦有民歌风味,刘知渐先生就认为:“他的《定情诗》描写……这说明繁钦是曾向民间文学吸取养料的,”[21]此亦可见繁钦诗歌主题创新之一斑。
三、繁钦文学作品中的通脱特征
刘师培曰:“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22]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赞同刘师培的意见,仅易数字,表述更为确切,曰清峻、通脱、华丽、壮大。“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23]繁钦因其“性无俭格”,行为通脱随意,这种个性一方面在创作文章时,能够不落窠臼,在新的时代大潮的影响下,在文学的题材、体裁上,在某些具体的表述上、用词上大胆创新。同时,他的文章能够独抒己见、己情,而不受固定思维、思想的桎梏,从而不仅文章,而且诗歌的风格都显得较为通脱。
上引繁钦《三胡赋》《胡女赋》《嘲应德琏文》《嘲杜巨明文》等文,已看出其创作这种不受儒学桎梏的通脱特点。此外,这种创作方式,在其《与魏文帝笺》中也得以体现。关于《与魏文帝笺》的写作时间、写作地点,学术界颇有争议,我们认为刘知渐、傅亚庶、高华平等人认定该文作于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的说法,较为合理。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曹操驻兵居巢,曹丕留守谯郡,而繁钦也同在谯郡,“繁钦很可能就是在此时被曹丕派到谯郡的地方上搜寻声色俱佳的女倡,并写下了这封向曹丕汇报情况的书信的。”[24]“(建安二十一年)冬十月,(曹操)治兵,遂征孙权,十一月至谯。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军居巢,二月,进军屯江西郝谿。权在濡须口筑城拒守,遂逼攻之,权退走。三月,王引军还……”[1]我们知道,曹丕、繁钦短暂留守“五都”之一的谯都时,曹操正率大军南征劲敌孙权,虽则“权退走”,但曹操也未取得战略上的胜局,形势可谓依然险恶。然而,在这短暂的形势逼人的仓促时间内,繁钦却写下了如此一篇与战事毫无关系的、标准的“声色犬马”类文章,我们认为,也只有性情通脱之人,才会有如此率性之举。
《古今姓氏书辩证》记载:“……汉魏间有繁钦,文集十卷。又汴州人繁氏世居梁孝王吹台之侧,其家富盛,人谓吹台为繁台,今东都天清寺即其地也。……”[25]卷十二梁孝王吹台是战国时期著名的音乐建筑,繁氏聚居于此台之侧,很有可能与其家族对音乐的爱好有密切关系。“门阀制度下,家族成员的一个主要心理特点是他们往往对家族荣耀念念不忘。”[26]这种家族文化积淀下来的爱好,同繁钦“文才机辩”的个性相结合,使他在以文学表达内心情愫时,更具有艺术的感性的特征,而少了政治的、社会的束缚。繁钦的这种性情也易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前方战事如火如荼之际,繁钦没有去赞美曹操的赫赫军威,却津津乐道于一个无名小卒“喉啭引声”的绝技。
繁钦又有《愁思赋》(《初学记》作《秋思赋》),赋从开始至“怅俯仰而自怜,志荒咽而摧威”,抒发寒秋已至,自己“行之多违”“志荒咽而摧威”的忧凄心情,这种悲凉的调子是建安时人普遍的情感,也是建安文学的特征之一。繁钦此赋为《愁思赋》(又作《秋思赋》),同时的曹植亦有《秋思赋》(《艺文类聚》作《愁思赋》),繁钦此赋的新异之处在于,赋既为“愁思”,则“叙愁”故其宜也。然而,此赋的结尾却有“聊弦歌以厉志,勉奉职于闺闱”二句,“聊弦歌以厉志”表明繁钦欲从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凄惨氛围中走出来,用一种激越的乐调振奋自己,此亦易于理解。但最后一句“勉奉职于闺闱”就很令人费解了,该句一方面使赋作从之前的抒发个人沉重的情感中解脱出来,让人在正经的叙述模式下看到了繁钦笔触的灵动、率性,这最后一句完全解构了先前的宏大正统的叙述模式,让我们看到了繁钦“性无俭格”,从而“文”亦无“俭格”,即通脱、随意的一面。
繁钦有《丘隽碑》,《文心雕龙·碑诔》曰:“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11]繁钦此碑确实符合刘勰对碑文文体的界定。碑文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丘隽的“峻伟之烈”,但“都尉乘隽马得免”的描写,似乎又在对两人命运云泥对比的描写中,感到丝丝滑稽。都尉“乘隽马得免”的结果,固然衬托丘隽行为之崇高,但在本应严肃的碑诔文中,如此描写,让人们不由想起曹丕在王粲墓前学驴鸣的场景。此等写法,不正是繁钦不拘格套,率性、通脱性情的映射吗?
繁钦之“性无俭格”,在愈演愈烈的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他的这种通脱、率性的行为,使他在文学创作的题材上、形式上,不会墨守成规,而是和其时众多作家一起积极开拓,形成建安文学这一新异于汉代文学的繁盛局面;同时,繁钦这种通脱的个性,也渗透到具体的文学创作中,所谓“文如其人”者是也。他的诗、文、赋中多体现着他通脱的个性,而“通脱”又是建安文学的重要特征。故而,我们认为繁钦缘于自身之个性,在时代大潮的作用下,他的文学创作如盐入水样汇入建安文学的浩繁星空中,然亦不坠明亮之色泽。
注释:
①揆诸史实,篇题“只能称为“与魏世子曹丕笺”或“与魏五官中郎将曹丕笺。”(高华平《繁钦〈与魏文帝笺〉的写作时间及相关问题》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二辑,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页)
②关于《塘上行》是否甄氏所作,历来有争论。《文选》陆机乐府《塘上行》李善注曰:“歌录曰:‘塘上行,古辞。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玉台新咏》定为甄氏所作;《艺文类聚》认为是甄后作;《乐府诗集》虽在目录标出《塘上行》为魏武所作,但在注中又认为:“按本书解释则认为甄后作,……朱秬堂《乐府正义》:‘凡魏武乐府诸诗皆借体寓意,于己必有所为,而《蒲生篇》则但为弃妇之词,与魏武无当也,知道其非魏武作矣。’”《乐府诗集》注引《歌录》曰:“《塘上行》,古辞。或云甄皇后造。”注引《乐府解题》曰:“前志云:‘晋乐奏魏武帝《蒲生篇》,而诸集录皆言其词文帝甄后所作,若晋陆机‘江蓠生幽渚’,言妇人衰老失宠,行于塘上而为此歌,与古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22页。)朱绪曾《曹集考异》卷六《蒲生行·浮萍篇》引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云:“直以为甄后作,又信《洛神》为感甄,且谓子建以《蒲生》当其《塘上》”,又引梅鼎祚《古乐苑》云:“甄后叹以谗诉见弃,犹幸得新好,不遗旧恶,盖初见弃而作,似非临终诗……。”朱序曾详实考证后,认为《塘上行》乃曹植所作,本文从之。(朱序曾考异 丁晏铨评《曹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