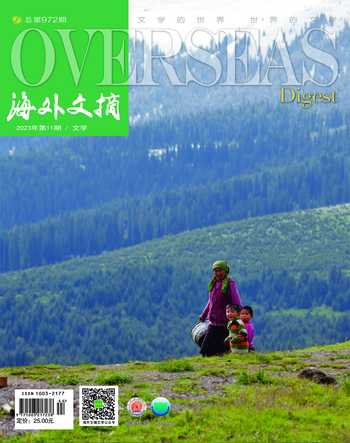梅雨过,家家晒红绿
吴蔚芳

老屋地面是泥巴地,逢梅雨天,就回潮得很,整天湿漉漉的,即便穿着布鞋,稍不留神,也会脚底打滑,人猛地向后仰去,接着是一屁股坐到地上,裤子已被粘上两块巴掌大的印渍,这是儿时常有的事。
黄梅时节家家雨。母亲坐在门边的小木凳上,轻轻翻动一簸箕已经长了霉的蚕豆块,小声道:“等这场雨收了,梅天就过了,该晒霉了。”每年母亲都要在黄梅天做一坛子蚕豆酱,前前后后要忙好些天。母亲做的酱,色泽正,味道醇。如今已鲜有人自己在家制酱,超市里有卖,蚕豆酱,黄豆酱,辣椒酱,花生酱,琳琅满目,但为了提鲜,几乎都放入了添加剂,既不环保,也不健康。
儿时,就盼着晒霉。梅雨天一过,又是好天,村子里家家开始晒霉,忙碌得像要过年似的。先在自家门前的大树上拴麻绳,晒厚重的棉絮、棉衣,再将夏日纳凉的竹制晾床抬出来,还有的把门板卸下,擦拭干净,用四条腿的大板凳支起来,在上面晾晒轻薄一点的衣物。小孩子们则三五结伴,从东头到西头,指指点点,叽叽喳喳,看看谁家晒了啥稀罕物。彼时,女人们要把平日里收在柜子、箱子里的四季衣物,一一取出,在门板和竹床上陈列开来,相邻的两家女人还暗暗较劲,比比谁家的衣物干净,好看。晒出来的衣服若是一团皱,这家女人会遭人嫌弃,做事窝囊。条件好一点的人家,一件粗呢子上衣,一块丝绸被面,也让人羡慕得很。整个村子就像开展览馆,浩浩荡荡,红红绿绿,还有栀子花的白和芬芳。那些衣物在太阳下暖暖晒着,慢慢将它们身上的霉味一点一点吐尽。此刻,樟脑丸好闻的香味已盖过了霉味。晒了一天的衣物收回家后,再放置新买来的樟脑丸,抵挡一年的虫蛀。
家里有件大衣柜,一人多高,上下两层,放着全家六口人的所有衣物。柜门外漆暗红色,门里贴一张约一尺见方的长方形大红纸,父亲用毛笔清晰记下我们兄妹四人的生辰,以至于参加工作后,得知有的同龄人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准确出生日期,方知父亲做事的细心。想起读书时,父亲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在我后来的学习,乃至工作中,这句简单而又朴实的话语始终伴着我。父亲不知,他的很多话语已成了他女儿一生的财富。
蝉在泡桐树上卖力地演奏,母亲把柜子里的衣物一件一件取出来,然后整齐地放在竹床和门板上,叮嘱我不要用手去摸,有手汗,会留下汗渍,母亲一直很爱干净。我跟在母亲身后,看她把棉絮展在绳子上晒,棉衣、棉鞋摊开在门板上,被里、被面和一些夹衣、单衣放到竹床上。生活匮乏,衣物大都是旧的,有的还打了补丁,接了袖头和裤腿,但每一件衣服都被母亲浆洗得纹理清晰。70 年代,人们盖的被面都是从供销社扯来布料缝制而成的,大红大绿底子,被面上有凤凰飞舞、牡丹花开,很喜庆的样子。我的目光粘在一块被面上,这床被面非红色,也非绿色,是金黄色底子,上面开五彩的花,朵朵硕大,开得欢天喜地,几只蝴蝶在花间起舞。小小年纪的我,被深深吸引了,又觉得很神奇,心里还有些许得意,这是别人家没有的东西。我家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布呢?这块布将来要做什么用呢?记忆中,母亲每年都会把这块布拿出来晒,然后叠成方块,再藏进柜子。小时盼晒霉,只为了看一眼这块布料。经年之后回想起,不觉笑了,是单纯幸福的童年时光。上中学后,专注于学习,也就不太去想这块布料了。80 年代初,我考上师范学校,行李中,有母亲亲手缝制的一床棉被,被面金黄,上面开五彩的花,几只蝴蝶在花间起舞。我以为,世上的母亲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她的孩子们,我的母亲亦是。
老屋门前牛背塘的水面更阔了,下雨时,塘面水汽缥缈,胜似仙境。黄昏时,雨渐渐收了,遥见对面枣林岗几户人家,屋顶上飘出细细的炊烟,灰黑色,如村姑的长发在空中曼舞。临水的塘埂曲曲折折,岸边树木葱翠浓密,柳丝低垂至水面,白色长嘴水鸟从泛着银光的水面上掠过,“扑棱棱”飞到西北角一片芦苇丛中。涨水期,岸边的芦苇只露出小半截身子。水中长一大片菱角菜,叶片肥亮,有坐腰子船的乡人在采菱。池塘西南角有一排青石板,垒成台阶状,上下有七八层,村里人淘米洗衣都在这里。石阶最底层砌有涵洞,涵洞经马路下穿过,抵达路西的沟渠,沟渠一路向南绵延数百米,下游农田灌溉倚靠它。渠水常年不断,时有村民赤脚下水摸鱼,也把鱼笼、黄鳝笼固定在水中,笼子以竹编的居多,长约50 厘米,小口粗肚,鱼虾黄鳝随着水流游进去,很难再钻出来。
枯水期,塘水浅,村里的孩童喜在涵洞口玩耍,男孩子能一个纵身跨越洞口,引得小女生崇拜他们,隔壁二五子胆量就大,敢这样做。他还经常单手托着一只比他头还大的粗碗,边走边扭过头喝稀饭,稀饭上卧几根长长的酱豆角。雨季来临,塘水日日上涨,大人都吓唬自家小孩不要下水,当心被涵洞吸走,有说的更吓人,会被水鬼拖走。哪里看得住呢?村西头有个男人,单身,驼背。听老人说,他小时候被大水卷进涵洞,所幸命大,在黑暗狭长的涵洞里没有淹死,被湍急的水流冲到马路西侧的沟渠,后被人救起,捡回一条命,落下了残疾。
雨季后,塘水泱泱,几乎漫过9 成台阶,水清凉,不时有小鱼儿在水面游动,鱼极小,两三寸长,有的会游到村妇正淘米的篮子里。主妇们把家里的小桌子,小板凳,大锅灶上的锅圈,锅盖,筷笼,砧板,刀具,只要能搬出来的物件,统统搬到水塘边,用刷子刷,用水冲,再在烈日下暴晒几个时辰,闻闻,都是太阳的味道。记得我家的碗橱很小,平日放在灶间的一张小矮桌上,梅雨季灶间格外潮湿,屋顶的亮瓦暗淡无光,感觉人也要长出一层毛。母亲把碗橱里的碗碟放到大竹篮里,父亲抱起小碗橱,两人一起来到池塘边。母亲弓着腰,低头洗碗碟,不时抬手撩一撩齐耳短发,那样子真是好看,石板前的水波一浪推过一浪。父亲卷起裤腿,站在被水淹没的石阶上刷碗橱,烈日下的脊背晒得发光,两人没有说话,却很默契。那场景记忆深刻,不曾淡去。
旧日时光,飞花一般。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多东西都变了。儿时住的房子,不再是原先的土墙、泥地,已被砖墙、水泥地所替代,有讲究的人家还贴上了带花纹的地板砖,装上了抽水马桶,不用在大半夜打着电筒上茅房。要是搁在寒冬,上个茅房屁股都会被冻僵。空调已款款走进普通百姓家,还具备去湿功能。滚了布边的旧蒲扇冷落在墙角,寂寥地回忆它的前尘往事。城里高楼林立,人们搬进干净的套房,通风,敞亮。如今,那些晴天晒霉,户户晒霉的壮阔场面,已难寻踪迹。许是念旧吧,时常想起儿时晒霉的那些日子。记不清在哪里看過这样一句话:最好的画卷只出自乡间。深以为然。这最好的画卷,一年只有一幅,在乡间,在心间。
还好,牛背塘还在。归乡时,乡音还在。那日回老家,脚刚踏进哥嫂家门,耳畔便传来:“大妹回来啦!”坐在哥嫂家沙发上的妇人,是我儿时的同龄玩伴,叫二妹,虽过了数十年未见,但我们几乎同时认出了对方。犹记得,小小的我和她一起偷邻家未成熟的柿子,塞进秧田烂泥里,过几天再去看熟了没有,青柿子已不见踪影,或已被淘气的小男生掏走。初中毕业后,我选择外出学习,然后在县城工作,她和我的很多小伙伴一样,在这里婚恋、生子,过寻常日子,半辈子也就过来了。聊天中,得知几年前她不幸中风,几乎卧床,坚强的她硬是坚持每日锻炼,先在家里扶着墙挪步,再拄着拐行走,如今已能给家人煮饭,尽管没有常人做得麻利。用她的话说:“我不能就此倒下,哪怕能给家人减轻一点负担,都是好的,你说是吧。”我看着她,笑了,笑出了泪花。无论走多远,都感动故乡带给我的一切。
梅雨过,家家晒红绿。这样的时光,真叫人舍不得。是真的不舍呀,天好的日子,习惯捧了衣和被出来,在太阳下照着。隔窗,看过去,棉被里藏着多少回不去的童年啊,有快乐,也有惆怅。
责任编辑:杨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