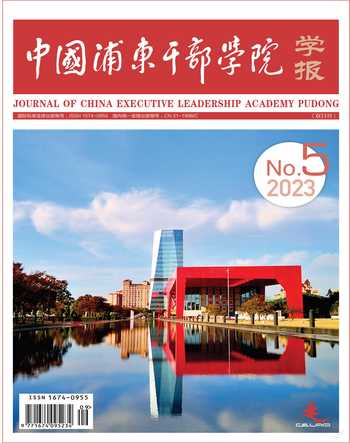新型集体经济只能是新型合作经济
摘 要:实行传统集体经济并非马克思的初衷或本来设想。它违背了合作经济原则,在实践中遭受挫折,在理论上、法律上也存在问题。以“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来定义“新型集体经济”,面临逻辑上的困难,也不能適应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化。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应当回归合作经济本源,以“合作与联合”为重点,加强社区依托,特别是要大力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社区合作基于地缘纽带,与地权归属(土地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而传统集体经济的地缘纽带仍在并且基本保持完整,是不容忽视的组织资源。在新型合作经济体系内兼容原有的集体经济因素,有两条路径,即横向兼容和纵向兼容。这两条路径并不矛盾,可以先易后难,也可同时推进。
关键词:新型合作经济;新型集体经济;合作社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1]在2023年2月召开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坦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说了很多年,到底什么样、怎么发展,以前没有明确规定”。[2]之所以很多年“没有明确规定”,是因为在理论、实践、政策和法律上存在很多困扰。传统集体经济被认为存在严重弊端,事实上已经基本解体。而对于新型集体经济,人们在不知其为何物的情况下,却常闻“发展”“壮大”之声,各种牵强附会、移花接木之事屡见不鲜。本文拟就新型集体经济、新型合作经济相关问题展开论述,在厘清基本概念的同时,提出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可能路径。
一、传统集体经济违背了合作经济原则
探讨新型集体经济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传统集体经济是什么。习近平指出:“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在解放初期完成土地改革后广泛建立起来的”,“在当时起到了避免小农经济有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有效地保护处于恢复时期的农村生产力、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的历史作用。由于随后实行了高度集中统一的‘人民公社式的集体经济,违背了合作经济发展的自愿入退、农民主体、民主管理、利润返还等原则,形成了产权不明、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体制弊病”。[3]
张晓山(2023)认为:“以往农村集体经济主要的问题是代理人掌握资产控制权,使集体成员的所有权虚置。即由集体之外的主体(例如地方政府)来支配成员集体拥有的资产,或集体成员的代理人(村干部)‘反仆为主,来支配成员集体拥有的土地及其他资源或资产,集体经济蜕变为‘干部经济。”[4]这里提到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不过,代理人问题虽然很明显,但它并非集体经济所特有,而是诸种经济形态下都会产生的问题。传统集体经济更深层的症结,习近平已经明确点明,即它违背了合作经济的原则。
合作经济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本质是交易的联合,它建立在财产权利和市场规则的基础之上。传统集体经济主要是一个所有制范畴,指向的是财产的充公或合并。二者显然不是一回事,但的确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一些交叉。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倡导和推广的合作社,多属于合作经济范畴。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农业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还大致按照合作经济的本来意涵在发展,后来则迅速转向集体化,进而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完全背离了合作经济的精神实质。合作社被作为集体化的组织载体,传统集体经济借用了一部分合作经济的思想资源和形式外壳。而集体所有制是和计划经济体制相伴而生的,实际结果是集体所有制经济排斥或代替了合作经济。
当年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曾被冠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名。而“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至今尚存,几经沿革后,早已不符合合作经济原则,距离集体经济也日益遥远,只是徒有其名而已。但有人却时不时将其归为合作经济或集体经济,特别是在争取更多政策支持的时候。如此种种,都使人们在认识上产生歧义,在实践中走入误区。
二、对相关法律规定的梳理
1982年《宪法》第八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5]111993年《宪法修正案》将此句修改为:“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5]511999年《宪法修正案》又将此句修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5]57
对《宪法》第八条进行多次修改,主要是为了解决家庭承包的法律地位问题。修改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集体所有制经济”这样的表述,这体现了历史的局限性。后来的表述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至于“分”的层面即家庭承包是否属于集体经济,则留给人们作不同的理解。承包制或责任制,是诸种经济形态下的常有形式,不能认为是集体经济所特有的。特别是当集体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土地经营权流转至其他主体(可能是其他农户家庭、下乡市民,也可能是私人企业)手上时,这又是什么经济形态呢?如果私人企业在流转的集体土地上开展经营活动,被认为属于集体经济(或其“分”的层面),难道占用国有土地的私人企业也属于国有经济吗?因此,要继续探讨集体经济,应当主要关注“统”的层面,否则就将其混同于家庭经济或一般私人企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统”,只能是合作与联合,也就是合作经济及进一步联合。
《宪法》第八条关于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基本表述一直没有变化,即“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集体所有制经济”。这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普遍观点。如杨坚白(1989)就认为“合作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名称”。[6]14,15问题在于,世界上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公认的发达的合作经济,难道它们也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可见,用合作经济来定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是行不通的,反过来用集体所有制经济来定义合作经济也是不合适的。
除了《宪法》第八条之外,数十年来,各种单行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经常将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区别对待。1986年公布的《民法通则》中只有涉及集体经济的条款,不涉及合作经济。1988年依据《民法通则》制定的《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并未提供合作社或者合作经济组织的注册登记程序。2002年修订的《农业法》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并列,统称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2006年公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把农民专业合作社定义为“互助性经济组织”,回避了其是否属于集体经济的问题。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7]这可能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把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区别开来。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将二者并列,提出“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和“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8]12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9]2021年开始施行的《民法典》,将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并列。
2022年12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进行审议。该草案第二条为“适用范围”,明确排除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这与《宪法》第八条的精神并不相符,两者不可能都是适当的。该草案第二条还把农村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排除在外,但这两者一向被视为也经常自称为集体经济组织。一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辗转多年仍未正式出台。这并非偶然,原因就在于人们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疑惑。
三、实行传统集体经济并非
马克思的初衷或本来设想
很多人习惯性地以为,集体经济、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配置,是马克思的本来设想,其实不然。马克思、恩格斯论及的“集体所有”,并非由某一部分社会成员组成的集体来占有,而是等同于全社会所有,相当于后来的“全民所有”。对此,学界已进行了不少文献考证和概念辨析,形成了一定共识。①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10]3631880年,他在《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中写道:“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形式”,即“个体形式”和“集体形式”,社会主义工人在经济方面的最终目的是“使全部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10]818這里的“集体所有”,是“全社会所有”的同义语,并不同于后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那种由部分社会成员占有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可以说,实行传统集体经济或集体所有制,并非马克思的初衷或本来设想。
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合作经济(合作社、合作制)是广为接受且备受期待的。合作经济的正式出现,要稍早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至少可追溯至19世纪前期。有一个经常被援引的合作经济范例,即1844年在英国曼彻斯特成立的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该组织是工人运动的产物。合作经济思想的萌芽,受到了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合作经济为弱势群体团结互助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而它之所以能够充分实践,是因为它与市场经济环境完全兼容。无论是早期合作社还是现代合作社,凡是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运行的,都承认和保护财产权利和交易自由,与特定的所有制和意识形态并没有必然联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广泛吸收了当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很早就关注并重视工人合作社、农民合作社在社会变革中的积极作用和广阔前景,特别指明了以合作制团结和改造小农的道路。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合作制实践被强行转向集体化,主要发生在苏联和受苏联模式影响的国家,这并非合作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这是战时体制及准战争状态下,或者说“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的一种高强度资源汲取安排。在优先发展、保障城市和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下,在“全能体制”的严格管控下,农产品统购统销和由工农业剪刀差造成的价格扭曲,已经决定了农业和农民的历史命运。集体化只是实施手段,对于合作社更只是借用其名号而已。我们不应把责任归咎于合作经济(合作社、合作制),更不应产生杯弓蛇影的心态。
从认识根源来看,将合作制实践转向集体化,主要源自对生产合作社的偏好,以及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执念。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尤为重视生产合作。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其短期执政实践中,较为重视流通合作。斯大林掌权后,则完全转向生产合作,并很快全面推行集体化。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具有较强的“生产决定论”色彩,虽然承认流通反作用于生产,但更强调生产对于流通的决定作用。这对于在短缺经济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们来说,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但从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只掌握了生产而没有充分拓展销路,企业就会陷入经营困境,老板会赔本,工人会领不到工资;而如果掌握了需求,却可以影响和控制生产,OEM代工、订单农业、大型连锁商超乃至新兴电商平台等商业模式即为明证。在经济过剩、资本过剩、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此种现象更为普遍。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和货币信用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通过调整分配和流通(包括信贷流通等)来引导或整合需求,进而影响以至控制生产,已日益成为常态。这里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能掌握规模足够大的面包消费人群,就完全可以通过联合采购的方式,向厂商争取更大优惠,不需要自行开设面包店或组建“面包生产合作社”。这属于消费合作或供销合作的一种形式,在操作上较为简便有效。
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合作,可以理解为劳动合作(劳务合作)的延伸形式。最简单的劳务合作,并不涉及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和使用。人们以互助经营的方式共同向外承揽劳务、协调内部成员履行劳务,这实际上是一种劳动力营销合作。一般来说,辅助性、临时性的劳务合作居多,在核算和结算上也很简便,成员自备简易工具(如履行搬运劳务时需要的扁担、麻绳、垫布等)即可。如果要完成更为复杂高频的任务,就往往需要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如在搬运时使用车辆),以便相对稳定可靠地提供产品或服务。这样,就进一步构成了生产合作。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合作而言,其与集体所有制并不等同,成员自由进退,所涉及的生产资料或所有者权益是共有的。这些生产资料既可以是共同所有的,也可以是共同租用甚至借用的。由此,可以总结出两个公式:生产合作=劳动(营销)合作+生产资料供应(利用)合作;生产合作(产品自用)=劳动(营销)合作+生产资料供应(利用)合作+消费合作。
生产合作当然有其存在价值,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属于合作经济中的特例。从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实践来看,生产合作难成气候,不如流通合作盛行和持久,只有以色列的基布兹等极少数案例可算成功。生产合作在日常管理和监督上面临很大困难,需要付出较高成本。此外,生产合作内含着劳动合作,劳动力要素的配置较为固化,劳动者与合作成员身份重合,不利于管理者灵活调整劳动力的使用(如增减员工)。
生产合作应当慎行,流通合作大有可为。经济学理论上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在流通环节中,信息的透明度和对称性较有保证,合作组织可以保持效率。例如在一个销售合作社中,你交售1吨小麦,我交售2吨小麦,数字容易计量(有时可能需要采取一定的产品分级标准,但这种标准也是相对客观、容易操作的),相关的市场价格信息也容易掌握。而在生产合作中,大家都在锄地,锄得多点、少点、深点、浅点乃至每一锄头的边际产出,是难以准确计量和监督的。其他农业生产劳动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这很容易助长“搭便车”行为,进而导致合作难以为继。
生产过程的监督成本较高,很多时候人们不得不借助于企业制度,即便企业制度指向的是“资本雇佣劳动并获取剩余”。在农业生产领域,由于在劳动监督和计量上存在特殊困难,所以雇佣经营的比重不高,古今中外多是以家庭经营为主。这与所有制和意识形态无关。在公有制基础上搞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劳动,效率相当低下,如果沒有政治高压环境,很容易走向解体。在私有制基础上搞大规模雇佣农场,同样是比较困难的。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种植园,实行的是农奴制而非雇佣制,勉强维持一定的经济效率,但面临着人道谴责,没有坚持多久。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大地主主要把土地租给佃农,而不是雇佣大量长工来种地,这也是例证。近年来,国内一些所谓农业龙头企业到农村“圈地”,集中了大量土地,其中极少有雇人种地取得成功的,大多是采取各种形式让内部员工或周边农户重新搞了一轮“承包”。
片面强调生产合作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很容易从生产合作走向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推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这恰恰是走入了把生产合作社与集体经济组织混为一谈的认识歧路。生产合作社一旦取消了“成员退出权”,即不再承认私人财产份额,就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集体经济组织。这种情况可以用公式表示为:生产合作-成员退出权=传统集体经济。
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里,所有制是与劳资支配关系相联系的。至今仍然有一些学者坚持合作制是“劳动联合起来对抗资本”,甚至是“劳动支配资本”(生产合作社或许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这样)。这其中存在严重误解,可能与早期合作运动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有关,甚至与当时的劳资冲突事件有关。合作成员可以共同劳动,一部分合作成员可能同时是合作组织雇员,一些合作组织的管理服务工作也可能由部分合作成员志愿承担,但合作成员与合作组织雇员是两码事。合作组织与其雇员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是普通的劳资关系。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作社(包括生产合作社),乃至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合作社,都是建立在一般财产制度基础之上的。至于集体经济,则可以给出一个标准意义上的理论模型:集体经济=生产合作+集体所有制(所有者权益不可分割转让)。这样的集体经济在现实中很少有完整对应案例。因为在现实中,生产合作基本消失,而集体所有制因素(集体土地)仍然长期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生产合作”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特定含义,一般指向20世纪50年代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之后的人民公社(其实是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农村改革之初,之所以搞“包产到户”,就是因为此前的“生产合作”(其实是集体经济)并不成功。如果不恰当地滥用“生产合作”这一概念,就很容易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也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政治上的误会。但在中国现实语境中,“生产合作”一词仍然被很多学者、媒体和官方文件不加辨析地使用。有的人把生产要素的结合、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协作甚至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合同关系,通通称为“生产合作”,这是没有对合作制与一般企业组织进行区分。还有一些人把农民合作社的日常业务理解为生产合作。究其所指,其实是生产服务,涉及农技、农机、农药、农田水利、种子种苗、统防统治、仓储物流等。其中,统一购置或租赁生产资料(如生产设备、器具、设施乃至土地)供成员共同利用的合作社,属于“利用合作社”。从广义上讲,金融(信用合作)、流通(供销合作)也属于生产服务的范畴。
如果一定要继续使用“生产合作”的提法,应从生产服务合作这个角度来重新诠释。比如,下文所讲的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合作经济,可以理解为建立在合作制基础上的生产服务、供销服务、信用服务“三位一体”,这样在文字表述和理论逻辑上都更为严谨自洽。
四、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应当回归合作经济本源
随着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制不断改革、城乡经济进一步市场化、人口大量流动和农民进城、一部分市民与企业下乡,集体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016年12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农村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同时,该文件还提出要“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现“新型集体经济”。[11]同一个文件中,“农村集体经济”与“新型集体经济”两个提法并用。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上述文件中的“农村集体经济”,可能更多地指向传统集体经济,尚不足以认定其为“新型集体经济”。但我们可以将此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苑鹏、刘同山(2016)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特征总结为所有权关系明晰化、所有者成员主体清晰化、组织治理民主化、分配制度灵活化。[12]方志权(2023)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就新在不是传统“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而是产权明晰、成员清晰、权能完整的农村集体经济。[13]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人也表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须“推动构建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四条途径:“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2]
其实,“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抑或“所有权关系明晰化、所有者成员主体清晰化、组织治理民主化、分配制度灵活化”,这些都是各种经济形态的普遍要求,远不足以阐明什么是新型集体经济。对于“产权关系明晰”,也不能作简单划一的理解。“集体”对外产权明晰,对内则并不总是那么“明晰”(即不分割量化),这恰恰是其重要特征。这一特征还将长期存续,否则就不是集体所有,而是一般民法意义上的“共有”了。
至于“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所谓的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途径,无非是吃祖宗饭、吃孳息,很难说有什么“新型”之处。这可能是因为担心市场风险,也担心基层干部滥权,所以采取了比较守成的思路。在现实中,只有极少数村集体由于历史和地缘因素,能够获得可观的资产收益。而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彰显所谓的集体经济的效益,采取堆砌项目资金的办法,在表面上暂时性地完成了任务指标,却并没有真正形成造血机制和拓展生长路径。
上上下下的各种文件大力强调发展集体经济,而“集体经济”究竟所指为何,并不明确,不能仅凭字面描述或理论想象来理解。对于某些部门和地方的干部来说,他们理解的“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村级财政问题或者村“两委”可供支配的经费而已,跟“集体”和“经济”都关系不大。
张晓山(2023)认为:“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和资产开展各类經济活动的综合体现,是农村集体所有制在经济上的反映。”[4]这是学界长期流行的观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则将“农村集体经济”定义为“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这里的核心关键词是“合作与联合”。
方志权(2023)提出:“所谓新型集体经济,是指在农村地域范围内,以农民为主体,相关利益方通过联合与合作,形成的具有明晰的产权关系、清晰的成员边界、合理的治理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实行平等协商、民主管理、利益共享的经济形态。”[13]这一定义完全没有提到“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而是强调“以农民为主体”“联合与合作”,但也还没有旗帜鲜明地点出新型合作经济。
可能正是为了化解理论上的矛盾,孙中华(2021)提出:“农村集体经济即集体所有制经济包括两种形态,一是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形成的经济,二是农村中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14]笔者认为,将上述“两种形态”并列,考虑了历史的联系,却没有考虑内在的逻辑联系;“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形成的经济”很难构成一种单独的经济形态,在农村改革后并不等同于“集体经济”,更谈不上有任何“新型”之处。
传统集体经济已基本解体,只有集体传承的资源、资产尚在。资源、资产本身不是经济,只有当资源、资产进入生产和流通领域,牵涉分配、消费活动,才构成了经济过程。控制权、收益权的安排是区分不同经济形态的关键。如果要提“新型集体经济”,就只能回归合作经济的本源,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其重点是合作与联合的机制构造,难点是集体所有权本身不可交易,“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只能通过其派生权利与市场经济无缝衔接。
资源要素的利用,主要发生在生产过程中。这首先是微观经济主体(农户、企业)内部的事情,可以采取购买、租赁或者股份制、合伙制等方式。合作与联合则主要是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事情,属于合作制范畴,通常发生在流通过程中,这样比较灵活有效。合作与联合的核心内容,并非集体所有或非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本身,而是众多微观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同需求,例如共同的供销需求、生产服务需求和信用服务需求等。对这些分散需求进行整合,可以有效提升其在市场格局中的相对地位,有助于增加收益或节约成本。
在市场化程度不高、单个主体经营规模普遍偏小的条件下探索合作经济,一时间难以充分体现联合对外的经济优势(如集中销售,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供销合作,也是合作经济的一般基础)。人们的着眼点有时在于微观经济主体内部土地、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结合(如土地经营权入股、农民受雇等),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结合(如公司股东之间的合作),以及不同工序和劳动力之间的协作。这些经济关系确实是重要的,应被规范和受保护,但严格来说它们并不属于合作制范畴,却经常被冠以“合作”甚至是“生产合作”之名。如方志权(2023)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村集体经济主要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而新型集体经济不仅包括劳动者的劳动联合,还包括劳动与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联合。”[13]把生产要素之间的结合和农民的合作与联合混为一谈,并不利于集体经济的改革与合作经济的发展。
如果把生产要素之间的结合,或者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合同关系,混同于合作制意义上的“合作与联合”,甚至以此充作“新型集体经济”,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不是集体经济了,也就不存在什么集体经济了。难道《白毛女》里面的杨白劳(佃农)与黄世仁(土地出租者)也合作并构成了集体经济吗?他们之间只是生产要素的结合(当然其间还存在主导权和支配地位的问题)。
一国公民(或可理解为国家这个全民共同体的成员即国家成员)利用国家所有的资源要素(如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矿产资源开采权),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并不会因之变成国有经济,否则所有国有土地上的经济活动都是国有经济了。同样的,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也不会自动成为集体经济。公有(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经过一定的产权安排,可以由公民个人或集体成员在一定期限内和条件下利用(使用、受益)。此时,这种使用权、受益权在法理上就是私权,与其他形式的财产权没有本质区别。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如土地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从事家庭经营、开办个人独资企业,可以参与组建合伙企业。这些经营形式和经营成果不受集体干预,不能牵强附会地将其认定为集体经济。只有在上述经营形式(特别是家庭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与联合,才称得上集体经济。无论是传统集体经济还是新型集体经济,无论如何定义集体经济,有一条标准是恒定的,即在集体(合作与联合)层面要存在实质性的经营活动,否则就既没有“集体”,也没有“经济”。
以“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来定义“新型集体经济”,面临逻辑上的困难,也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化。集体成员利用非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如私有财产)来开展合作与联合,岂不是更加值得鼓励吗?而非集体成员(如外来租地农民,这是更值得期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合作与联合,也是应当倡导的。以上两种情况更有资格被称为“新型集体经济”,这其实也就是新型合作经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集体成员的分化与流动成为常态。集体所有或非集体所有的各种资源要素,需要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如果拘泥于原来的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的范围边界,经济活动就会日益封闭、僵化、萎缩。新型集体经济是农村改革后在家庭经营为主的基础上重新构建的,应当回归合作经济本源,更多地按交易贡献进行分配,积极开展多层次的合作与联合,成为新型合作经济。对此,可用公式表示为:新型集体经济=(传统集体经济成员+非传统集体经济成员)×(集体所有+非集体所有)生产要素×多层次合作与联合(按交易贡献分配)=新型合作经济。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资产管理的主体,是特殊的经济组织,可以称为经济合作社,也可以称为股份经济合作社。”[11]坚持以“合作社”来命名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正是对社会主义合作经济思想的呼应。
五、“折股量化”本末倒置,不具可扩展性
一段时期以来,在集体经济改革中,人们固然强调“坚持集体所有制不动摇”,但在实际操作时较多受到了股份制思维的影响。由于生搬硬套,结果不但没有做到优势互补、融会贯通,反而搞出了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
把集体经济改革的重点放在经营性资产的“折股量化”上,是本末倒置。对任何一个经济实体(包括集体经济组织)来说,定期或不定期地清产核资、摸清家底是必要的,但这不是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或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正式成立的先决条件。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时,并没有也来不及对旧中国的资产来一遍清产核资。至于土地确权,也是类似的道理。
在经济意义上,资产是指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特定主体能够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资产一般按照取得时的历史成本或原始价值计价。按此标准计量资产,要以实际发生的业务为依据,这样容易查证,具有客观性,简易可操作。但农村普遍缺乏这样的历史成本资料。此外,只有在市场成交活跃的情况下,才有公允市价可供参考,对于农村而言这同样是奢谈。农村资产大都难以进行市场估值,很难计价,即便强行计价也只是胡编乱造,没有什么意义。至于净资产的真实价值则更加难以测算,也可以说它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之中,所以不必纠结于此。
如果对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从计算公式上来说,分子就是净资产,分母就是成员数量或成员份额数量。化繁就简的思路是,不追求净资产的确切数字,只需要厘清成员资格和份额就可以了。比如,在法定继承情况下,配偶、子女、父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原则上是平等的。继承人的身份资格逐个得到确认、总人数n确定后,每人享有的份额就是1/n。被继承的财产需要清理分割,但并不都需要通过折价或变价的方式来分配。又如,很多单位的工会福利一般按照人头平均分配(有时需适当考虑员工资历或实际生活困难等因素),这一方法简便易行。只要每次被分配的福利是清楚的即可,并不需要以整体上的清产核资为前提。再如,股份公司给股东分红时,按照股东持股份额进行分配即可,与其所持股份的市价、原值无关,更不需要搞清楚每个股东持有股份所对应的经营性净资产及其真实价值。账面上的每股净资产只是某个时点上的数字而已,只有账面意义。
假如搞“折股量化”果真能够增强凝聚力、推动集体经济发展,那么为何不如法炮制,对国有经济也搞“折股量化”呢?全国人民、全省人民或全市人民搞个大公司,人人确权持股,难道就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了么?如果一個商场乏人问津,把这个商场的净资产“折股量化”给周边居民,这个“股”不能卖,居民也基本拿不到分红,那这又有什么用呢?如果要提升商场人气,还不如采取发展会员、消费返利等手段。这就是合作制思维与股份制思维的不同。合作制思维更注重经济参与形式和投入回报机制。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折股量化”,而是核定成员身份及其份额。一般可默认每个成员的份额都等同,也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在份额上有所区分,如有些地方设有“劳龄股”“村龄股”等(为避免将其误解为股份制意义上的“股”,仍建议称其为“份额”)。集体经济成员的身份确认要有严格标准和规范程序,对特殊群体(如外嫁女、入赘男、新生儿、服兵役人员、在校大学生、回乡退养人员、农转非人员等)的集体经济成员身份确认都要有所安排,做到不漏一户、不掉一人。截至2021年底,全国确认村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9.2亿人。谁是成员、是哪一级成员一目了然,为解决成员集体权益“两头占”“两头空”问题奠定了基础。[15]
一方面强调集体所有制产权不可分割,另一方面推行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所谓“股份”在转让、退出上存在障碍,而最重要的土地资产并没有“折股”,这里面有着种种难以调和的矛盾。由此,集体成员身份有所淡化,股份概念有所强化;集体成员似乎不是因为集体成员身份而有权获得分红,而是因为持有股份才具有了集体成员身份;而在现实中,又不可能真正实行股份制。在此基础之上运行的集体经济组织,在结构上是封闭的,难以增减调整成员,在入股和退股的对价上无法操作,不利于吸纳新的资金,在业务交易上也缺乏合理的投入回报机制。这在底层逻辑上决定了其很难成为经营性组织,不具可扩展性,最多只能起到保障性组织的功能。要对传统集体经济进行改革,就不能在原有思维框架里面打转。
六、加强社区依托,发展“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1984年1月,正当家庭承包普遍推行、传统集体经济(人民公社)走向解体之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当年的一号文件即《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为了完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体制,一般应设置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可以叫农业合作社、经济联合社或群众选定的其他名称;可以以村(大队或联队)为范围设置,也可以以生产队为单位设置。”[16]200这明显表达了中央政府通过合作经济改造传统集体经济、以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替代人民公社的政策意图。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进一步指出:“乡、村合作组织主要是围绕公有土地形成的,与专业合作社不同,具有社区性、综合性的特点。”[16]425
农业离不开土地,中国的所有土地都是公有的(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在宽泛的意义上,整个农业农村经济活动(当然也包括合作组织的活动),都可以说是“以土地公有为基础”,“围绕公有土地形成的”。囿于长期以来的所有制观念,一些人习惯性地以为土地公有是社区合作的前提条件或本质特征,其实并非如此。土地不可移动,天然具有稳定的相邻关系,也就是所谓地缘。社区合作基于地缘纽带,与地权归属(土地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好比同一个小区的左邻右舍,应当互帮互助,互相提供便利,而租户也可参与其中。上述1984年文件中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1987年文件中的“社区性”合作组织,都只能是围绕地缘形成的。
地缘关系是客观地理条件,与所有权归属没有必然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合作经济的主要内容是农产品销售、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供应以及相关生产服务、信用服务等。只要这些产品与服务背后的产权明晰且可流转,农村合作经济就能够有效运行。无论合作经济成员(农民)是自有土地、租用土地还是承包集体土地,对于合作经济的开展都不具有决定性影响。而现行的基于地缘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对于发展合作经济是个有利因素。“集体”这个组织资源,是弥足珍贵的,哪怕是个“空壳”,也有“壳资源”的价值。
习近平很早就提出:“要从健全集体经济组织入手,建立起以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经济技术服务部门和各种专业协会互相配套的服务体系。特别是要建立各种技术协会和行业协会,探索像日本农协、台湾农会的机制。”[17]代序11这里列举的日本农协、台湾农会,是东亚小农社会条件下的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功典范。它们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以多级社区合作为主干,同时开展各种专业合作。参加这些组织的农民,其土地大都是自有的,有些是租用的。
过去一段时期,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制度设计上简单模仿欧美大农(农场主、农业资本家)在本身高度专业化基础上的合作模式。这并不适合中国以小农为主的国情、农情,由此造成了合作社的发育不足和假冒横行。①有鉴于此,在当代中国探索发展合作经济,就不能局限于松散、单一的专业合作,而必须加强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重建合作经济的社区依托,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体系。这就是新型合作经济,可用公式表示为:新型合作经济=(生产服务+供销服务+信用服务)×社区合作。
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部署和推动的重大改革举措。在“三位一体”合作经济先行试点之初,区域性合作经济联合组织主要以合作社联合社(包括供销联社、信用联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或协会以及乡镇联合社)为核心成员,在形式上“条”(专业合作)与“块”(社区合作如乡镇联合社、村经济合作社)并重,事实上“块”的方面较为薄弱。这主要是为了迁就既有的拥有特殊地位的供销联社、合作银行,同时给未来新型合作社联合社不断进入预留增量空间,逐步“稀释”供销联社、合作银行的权重。同时,因为当时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尚未全面展开,所以不得不把重点放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方面,仅吸收了部分履行集体经济职能的村经济合作社参加联合组织,它们起到了象征性作用。这一方式可能更适用于经济体量较大、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因此专业合作更有基础)的区域。但在专业合作社及联合社本身基础不牢、规范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如果缺乏社区合作层面的支持,联合组织就不容易巩固。
发展新型合作经济尤其是社区合作,必须面对如何处理传统集体经济遗产的问题。传统集体经济虽然名存实亡,但其地缘纽带仍在并且基本保持完整。这是不容忽视的组织资源,可以且应当改造利用。农业农村经济日益超出原来的集体成员、集体所有资源要素的范围边界,只有新型合作经济能够将其容纳。合作经济社区全覆盖的意义不仅在于规模效益,更在于普惠和公平,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同时正因为全覆盖,这样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经济组织,就不能是普通的民商事组织,而必然具有半官方性质或公法性质。为此,需要进一步突破部门利益的束缚,加强政府的领导和推动。
七、以新型合作经济兼容传统集体经济
在新型合作经济体系内兼容原有的集体经济因素,有两条路径,即横向兼容和纵向兼容。这两条路径并不矛盾,可以先易后难,也可同时推进。
(一)横向兼容:村(社区)经济合作社兼容原有集体经济因素
采取横向兼容(同体兼容)路径,意味着要在同一经济实体内兼容合作经济和原有集体经济因素,其组织载体可以是在传统集体经济遗产基础上改制后组建的村(社区)经济合作社。这些村(社区)经济合作社要继续履行集体所有制职能,同时开展合作经济事业。其间涉及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在操作运行上会比较复杂。
集体经济成员与合作经济成员未必重合。原集体成员参与合作经济的程度各有不同。随着合作经济不断发展,当它超出原集体成员的范围后,其新吸纳的股金以及在经营中形成的财产和产生的收入,属于新的产权关系。在同一个法人实体内部,为了保护新老成员的正当权益,有必要将原集体经济成员单设为“原始成员”,亦可称“创始成员”。设置原始成员,是为了承继传统集体经济的职能和资源,维护传统农民的利益(有些农民可能已不再从事农业甚至已离开当地了,但其作为集体经济成员的权益应予承认和保护)。为了以示区别,可将一般意义上的合作经济成员设为“联系成员”。联系成员的主要权利和义务是与本组织进行交易,或通过本组织开展对外交易。对于联系成员,可不要求股金投入。如果涉及股金投入,可称为“基本成员”。上述原始成员、基本成员、联系成员的身份,可以是交叉重合的。
原始成员的权利受到特殊的限制和保障。特殊限制主要是指其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及相应权益不能自由转让,在身份认定上也有严格的程序和条件。特殊保障主要是在表决权、受益权上另有安排。例如实行分类表决时,可赋予原始成员否决权。成员大会上的表决事项,应经所有成员过半数同意(重大事项为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且原始成员过半数同意(重大事项为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通過。有关法规和政策规定明确由集体经济成员享有的权益,或者仅限于传统集体所有制范畴内的权益(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权益等),专属于有关的原始成员。村(社区)经济合作社使用集体土地等资源,应向原始成员提供合理对价(特别是在原始成员占比降低的情况下)。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传统农区,原始成员、联系成员的重合度较高。同时,由于农民的分化与流动,在某些地方特别是较发达的农村,留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原集体经济成员数量和比例下降,新型农民的作用上升。具备集体经济成员(原始成员)身份的当地农民,如果通过土地流转受让了其他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其作为原始成员的权益也并不会相应增加。而外来的新型农民,则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始成员)身份。其利益和诉求,应通过联系成员身份来体现。
未来集体经济产权制度还可能进一步改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型合作经济的发展,原有集体经济的权重会相对下降(其绝对值仍可能继续上升)。在集体土地全部被征收、集体经济成员均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前提下,对集体权益及相关事项作出适当安排之后,可不再设置原始成员。原集体经济成员可以继续作为联系成员,长期存在和发挥作用。
在上述过程中,合作社权利和义务的重心如向原始成员倾斜,则更接近传统集体经济;如向基本成员倾斜,则更接近通常的股份制;如向联系成员倾斜,则更接近标准的合作制。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操之过急,要有历史耐心。
以上做法,试图在同一个法人实体内部兼容新型合作经济与传统集体所有制职能,在操作上多有不便。另一个思路是:村(社区)经济合作社主要行使集体所有制职能,避免涉及经营性业务;同时另外重新设立或参与组建村级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法人实体。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可以在村一级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相关人员也可交叉任职。这样更为简便高效。当然,还可以向上参与发起乡镇联合社,这是另一个层面的兼容。
(二)纵向兼容:乡镇联合组织兼容村级集体经济
在纵向兼容(分层兼容)路径下,基层集体经济组织可向上发起组建合作经济组织(如乡镇合作经济联合社)。原有的集体经济因素可留在基层组织内维持不变,或者通过改革逐步消化。而新组建的联合组织,从一开始就应当按照合作经济的原则运行。
我国的很多地方在发展合作经济的思路上局限于村集体层面。这不仅给处理传统集体权益带来许多不便,而且由于村一级体量普遍偏小,土地、农户和产业不足,所以不容易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从同属东亚小农社会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来看,发展基层合作经济的重心应放在乡镇一级。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可由若干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作为核心成员发起组建乡镇联合社,同时吸收辖区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作为基本成员。为了平衡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可以对成员进行分级分类。
传统集体所有制因素可留在村级内部逐渐消化。现在各地大都将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按照“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进行注册,但其结构在运作中有很多不明确、不统一之处。姑且不管这些传统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渊源、内部构造与未来前景如何,其对外就是一个独立法人实体,对于上级联合组织来说就是一个单位成员。它们作为核心成员(发起成员、创始成员),具有一些特殊地位,比如可通过联合组织章程赋予其否决权。成员大会上的表决事项,应经所有成员过半数同意(重大事项为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且核心成员过半数同意(重大事项为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通过。这是对原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涵盖绝大多数传统农户)的历史地位和权利的承认和保障。
联合组织应按照合作经济原则进行规范,同时吸收部分股份制因素,如募集设定好投资回报上限的优先股。至于合作社、联合社对外参股的公司,则是完全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此中奥妙在于,入社、入股行为本身就伴随着资源、资产(也可包括资金)的集中与整合。
联合组织的资格股额度,可由各村平均分配,也可根据当地务农人数、农用地面积、对联合组织的贡献度等进行适当安排,总体上不要有太大差距。至于辖区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自愿加入联合组织。其中确有业务需要、较为规范的,可以参与出资(认购资格股),作为联合组织的基本成员。对于其他不适宜参与出资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应打消其积极性,可将其作为联合组织的联系成员。如果没有实质性业务往来,那么它们就只具有挂名性质,其权利和义务都是象征性的。
笔者建议,以行使集体经济职能的股份经济合作社(主要是村级合作社)作为核心成员。在当地集体经济组织全面改制为合作社的情况下,由政府推动,将行使集体经济职能的合作社普遍纳入联合组织,可以迅速做到合作经济组织的全覆盖。这一方式,其实是以“块”(社区合作组织,包括村级合作社、乡镇联合社)作为联合组织的核心成员,以“条”(专业合作组织,例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联合社)作为联合组织的基本成员。在总体设计上,可以兼容集体制、股份制、合作制因素,使其具有高度弹性。对于传统集体制因素,应尊重和保留;对于股份制因素,应有所引入并加以限制;对于合作制因素,应预留最大空间。即使合作制因素没有大的发展,基于上述框架设计形成的一个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相对平等的合股实体,仍然可以发挥较大作用。如果它与成员的业务往来不断增加,交易返利不断上升,合作制将逐渐趋于主导地位,这并不影响其原有功能的发挥。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合作经济联合组织,严格来说并非《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意义上的联合社,所以可能并不方便在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注册,但可以在农业农村局进行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登记。它实际上是兼容传统集体所有制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其性质可以通过组织章程上的特殊设计来体现。
八、结 语
传统集体经济改革是个老大难问题。集体所有制属于公有制范畴,有着特殊的政治历史渊源和意识形态内涵。集体所有制产权对内不可分割,集体成员身份不可自由转让,集体成员范围不能自由调整。这些特征有其历史合理性,对于维护农村稳定也有现实意义,却难以适应复杂多样的利益关系调整、人员变动和经營扩展需要。前些年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采取了土地确权(进而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等措施。这些措施有利于摸清家底,但是无助于充实集体经济组织本身,更难使之成为责权利相称、便于运作、富有活力的经营实体。
習近平主政浙江期间高度重视合作经济。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于2004年通过《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于2007年修订通过《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这两个条例是全国同类地方性法规中最早制定的。习近平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亲自听取农村合作协会(信合联盟)“三位一体”试点工作汇报,并亲自部署、专程出席全省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工作现场会。他指出:“实践证明,这种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合作与联合,是农民在保持产权相对独立的前提下自愿组成的一种新型集体经济,是在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的又一个制度创新。”[18]让我们深入体会其中的核心逻辑: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合作与联合……是……新型集体经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农村经济日益超出原来的集体成员、集体所有资源要素的范围边界。在此条件下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唯有回归合作经济本源。这既是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初心所在,也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在世界上也有不少成功范例可循。实践和理论都表明,把集体经济改革与合作组织建设割裂开来、分头去搞,不容易成功。新型集体经济与新型合作经济内在相通,殊途同归。在这个意义上,新型集体经济就是也只能是新型合作经济。
参考文献: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人民日报,2022-10-26.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什么、怎么干[EB/OL].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302/14/WS63eb7104a3102ada8b22f012.html.
习近平.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1.
张晓山.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J].农业经济与管理,202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杨坚白,主编.合作经济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N].人民日报,2007-10-25.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〇
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2013-11-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2016年12月26日)[N].人民日报,2016-12-30.
苑鹏,刘同山.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路径和政策建议——基于我国部分村庄的调查[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10).
方志权.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之我见[J].上海农村经济,2023(1).
孙中华.社区合作经济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J].农村工作通讯,2021(16).
徐向梅,何安华,吕之望,仝志辉,崔红志.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N].经济日报,2023-03-0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习近平,主编.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习近平同志听取农村合作经济“三位一体”先行试点工作汇报后的讲话要点(2006年10月24日)[Z].瑞安市金融工作委员会编印,2007年12月.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杜润生.中国农村制度变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陈锡文,赵阳,陈剑波,罗丹.中国农村制度变迁6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陈锡文,主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陈林.合作经济的成员分类分级与相应权益设置研究[M]//邓国胜,主编.乡村振兴研究(第3辑):合作经济、共同体建设与乡村振兴.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23.
徐祥临.三农问题论剑[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黄云龙]
The New Collective Economy Can Only Be a New Cooperative Economy
CHEN Lin
(Shoufu Think Tank, Beijing 101100;
Heilongjiang Local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Bureau, Harbin, Heilongjiang 160000)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not Marxs original intention or idea because it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cooperative economy, suffers setbacks in practice, and has both theoretical and legal confusions. There are logical difficulties to define “new collective economy” by “collective members utilizing the elements of collectively owned resources” and it cannot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rural economy. To develop new collective economy, we should return to the origin of cooperative economy, focus on “cooperation and unity”, strengthen community support, and, in particular, vigorously develop the trinity of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of production, supply & marketing, and credit. Community cooperation is based on geographical ties and is not necessarily related to land belonging (land ownership). The geographical ties of traditional collective economy still exist and remain basically intact, which are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There are two paths to include existing collective economic factors within the new cooperative economic system, namely horizontal compatibility and vertical compatibility. These two paths are not contradictory and we can begin with the easy one or push both of them simultaneously.
Key Words: new cooperative economy; new collective economy; cooper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