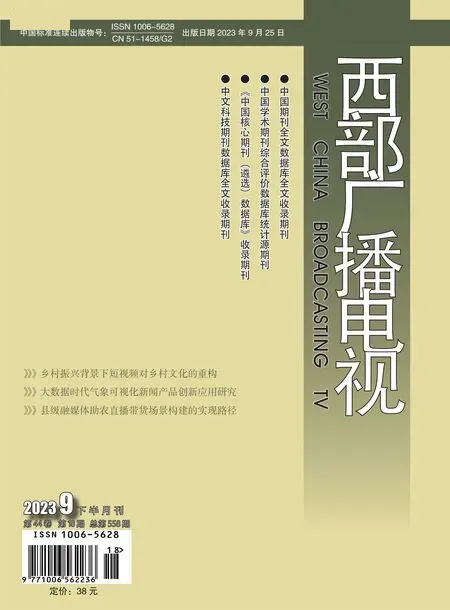意与象合、情与景谐:电影《小城之春》中的意象读解
张婷婷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
“意象”这一概念在中国美学史上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周易》中便有“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立象以尽意”之述[1],确立了意象理论最本质的内涵,即“通过感性直观的形象去表现幽深精微的情感和思想”[2]。东汉王充在《易传》的基础上,于《论衡·乱龙篇》中首次将“意”“象”进行整合,提出“礼贵意象,示义取名”,“指出了仪式表象所蕴含的文化意义”[3]。然而,“真正赋予‘意象’这个词以重要美学价值,并赋予其方法论意义的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4]。他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到“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揭示出了创作者构思“意象”的重要性。之后,王弼、司空图、陆时雍等人对“意象”内涵的继续思考和研究,推动了中国意象理论逐渐成熟,既在诗歌、音乐、书法、戏曲等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还随着《定军山》的问世,逐渐渗透于中国的电影实践之中。
1 中国电影意象论与费穆的“空气”说
近年来,众学者以探索、创建中国特色电影理论话语为目的,致力于从传统美学中寻找符合中国本土创作与欣赏心理的艺术基因。其中,张宗伟教授提出“生生”“意象”“阴阳”三个中国美学话语[2],并在《中国电影意象论》一文中进一步就电影意象展开了深刻论述。此外,潘源教授从比较视野出发,对西方电影符号学进行反思。他认为,将电影总结为一套类似于自然语言的词汇系统和语法规则会忽略电影艺术表意、感性的特征,而强调“喻意象形”的中国电影意象论融具象和抽象、理性和感性于一体,则是突破电影符号学研究瓶颈的新的理论路径[5]。可见,将意象论延展到电影领域确有其理论意义和价值。
实际上,通过有限的电影意象来揭示无限关乎人生、关乎宇宙的奥秘,不仅是中国电影的美学追求,更是中国电影艺术家的生命自觉。以费穆导演为例,为吸引观众,他提出“必须使观众与剧中人的环境同化”,即必须在剧中创造“空气”[6]204。费穆所说的“空气”即影片氛围,具体体现于人物与环境的渗透与融合,这与古典美学中的意象论脉脉相通。那么,该如何创造“空气”呢?费穆提出了四种实现方式:其一,由于摄影机本身的性能而获得;其二,由于摄影的目的物本身而获得;其三,由于旁敲侧击的方式而获得;其四,由于音响而获得。其中,旁敲侧击的方式则指“利用周遭的事物,以衬托其主题”[6]205。也就是说,创作者在重视电影镜头、场景、表演、音乐等具体细节的同时,还要对电影的整体气质有精准的把控,必须注重情境合一,寻找电影的象外之象与味外之旨。作为银幕诗人的代表,费穆在《城市之夜》《人生》《香雪海》等多部作品中都运用到了创造“空气”的方式,但影响最为深远、技法最为成熟的当属《小城之春》。影片处处可见导演在“空气”生成上的慧心巧思,大到颓败的小城,小到一盆兰花、一道涟漪,甚至是人物的命名、一包中药,都无不流露出费穆电影诗情画意、蕴藉隽永的写意情结。
2 《小城之春》中的主要意象
《小城之春》的故事围绕着戴家男主人戴礼言、女主人周玉纹、妹妹戴秀、仆人老黄,以及客人章志忱几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开,深入刻画了人物苦闷且矛盾的心境,揭示出中国文人在特定时期的现实困境和心理上的灰暗情绪,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不仅被公认为是费穆探索中国电影民族化道路上的顶点之作,更是中国诗学传统在电影实践中的一个无与伦比的典范。对《小城之春》中的重要意象再解读再分析,一方面有助于电影民族化的创作实践,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电影特质之所在。
2.1 空间意象
2.1.1 残破的城墙
城墙,本有坚固、磅礴之势,向来具有抵御敌人入侵的军事功能。然而,《小城之春》中的城墙却显得荒芜破败。影片伊始,镜头由左及右缓缓横移,一道颓残的古城墙如画卷般铺展开来,凸显出一种故垒萧瑟的荒废之感。这也是全片唯一展现城墙全貌的远景镜头,既隐喻了饱经战火的国家,又烘托出了人物的生活背景与心理状态。此后,伴随着女主人公周玉纹的内心独白,镜头的焦点从断壁残垣转向缓步行走于残破城墙上的忧郁女人,她挎着菜篮,走走停停,似乎但凡有一点选择就会逃离这沉闷的生活,向城外的春天奔去。荒凉的环境与人物流露出的情绪融为一体,奠定了影片惆怅、感伤的整体基调。
城墙虽破,却又连接着城外广阔的天地。站在城墙上不仅能看见通往火车站的道路,更可以使人得到在死水一般的生活中继续活下去的勇气。一如妹妹戴秀所说:“沿着城圈走,就有走不完的路,往城外一看,你眼睛使劲往远处看,就知道天地不是那么小。”影片还多次用仰拍镜头拍摄周玉纹站在城墙上的状态,荒凉的城墙被广阔的天空取代成为人物身后的全部背景,由此含蓄地传达出一种难得的轻松与自在。
总的来说,古老残颓的城墙象征着打破与封闭对峙时的独特形态[7],既是隔绝城里城外的屏障,又是城里人看向外部世界的“窗口”。城墙“开阔”与“封闭”的特点也恰好和影片人物矛盾复杂的情感相对应。由此可知,影片中的残破城墙不仅是具象的写实性空间,而且是一个意蕴丰富的感性世界。那个由城墙包裹起来的“小城”也不再只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城镇,更是一座具有文化寓言意味的意象之城。当破败凋零、荒草丛生的城墙出现在眼前,不由叫人生出几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怅惘情绪。
2.1.2 倾颓的戴宅
除“残城”之外,“废园”是影片的另一核心空间意象。开篇不久,随着仆人老黄的脚步,一个满是破砖烂瓦的废园缓缓展现出来。房子的男主人戴礼言独自坐在断壁残垣的院落中,惆怅、压抑。6 年病痛使他虚弱不堪,与眼前的戴宅一样凋零颓废。费穆借助戴礼言的台词“我的身体怕跟这房子一样,坏得不能够收拾了”,将人物的身体与戴家宅院联系在一起,揭示出戴礼言身体与心理上的双重苦痛。此外,电影中还多次出现戴礼言在墙壁的豁口处垒砖的画面,暗示他试图修补被炸毁的祖业、恢复昔日荣光的幻想,以及疗愈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的愿望。荒废的院落即是戴礼言心境的“外化”,“情”与“景”的和谐统一使破败的戴宅构成了一个颇有“味外之旨”的意象空间。
再看戴家的其他房舍,虽雅致却陈旧,墙上斑驳的树影、脱落的墙皮,无不透露出一种灰暗沉郁的气息。为营造能让观众身临其境的“空气”,费穆不仅在镜头设计上采用大量抒情式长镜头、慢动作以“传达古老中国的灰色情绪”,而且在房间和庭院的设计上也颇有巧思。周玉纹的房间整体光线偏暗,鲜少有植物装点,呈现出落寞孤独的氛围。戴礼言的房间中存放着大量药瓶药罐,这是疾病缠身的隐喻。客人章志忱的房间,原本是戴家的小书房,陈设简单,但在他住下的当晚,周玉纹送来一盆兰花,至此,兰花便成为整间房屋最显眼的点缀,就连戴秀送的小盆景也比之不过。兰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是“君子品格”的象征,其反复出现,实际已经点明章志忱和周玉纹的最终结局。与哥哥戴礼言、嫂嫂周玉纹了无生气的房间不同,妹妹戴秀的房中不仅有书画、纱帘、植物等装饰,更重要的是有一扇向阳的窗,这与她活泼开朗的性格形成呼应,透露出年轻人的蓬勃朝气。
总之,影片中的每个场景、每件物品都具有深刻隐喻。整部电影仿若一首闺怨诗,寄托着一部分文人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思考,充满着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独特韵味。
2.2 时间意象
《小城之春》是发生在春天的故事。“春”作为电影中重要的时间意象,主要包含三层内涵。
首先是季节之“春”。城墙上长起的杂草、小桥前盛开的桃花、戴宅的断壁残梁中冒出头来的郁郁葱葱的枝条等景象都点明了当时正处于万物勃发的春季。但与春意盎然相对立的是城墙上、戴宅中大面积的废墟之景,加之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以乐景衬哀情,更添几分怅惘。
其次是人物的情感之“春”。费穆“喜欢揭示人物的内心,尤其是人物内心的复杂过程。他影片中的情节,主要的不是以事件贯穿起来,而是以人物的心理过程衍生出来”[8]。当章志忱还未“闯入”戴宅时,周玉纹的生活如一潭死水,每日与戴礼言“见不着两次面,说不到三句话”,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过过来,再一天又一天地过下去”,充满了压抑与绝望,无奈和凄凉。章志忱的到访重新点燃了周玉纹内心的热情。送去的兰花、去找志忱时迟疑又坚定的脚步、平静的水面荡开的涟漪、缓缓点燃的洋蜡、情不自禁的牵手,无不反映出周玉纹对爱情和自由的强烈渴望。春天来了,周玉纹那冰封多年的心已然开始融化。然而,无奈的是,二人虽彼此有情,却终究难以挣脱伦理道德的束缚,章志忱与周玉纹在小径上散步时分分合合的场景,早已暗示了两人在“情”与“礼”之间的挣扎和犹豫。这无疑与费穆用“废园”“春天”这一对立的时空意象来调动更大悲怆情绪的手法类似。周玉纹与章志忱“发乎情,止乎礼”的结局也颇有“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伤意味。
最后是社会时代之“春”。影片诞生的1948 年正值中国历史的拐点。以费穆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经历了14 年抗战,本以为迎来解放就是迎来了不再有战火的春天,可国共内战的重开打破了他们和平的美梦。祖国的锦绣山河仍在无尽的硝烟之中,“城外”已然迎来了世界的春天,可“城内”实际的春天究竟何时才会到来?待真正体会到费穆等人的这种苦闷与彷徨,也许就不难理解《小城之春》为何总弥漫着化不开的感伤和沉郁情绪了。
2.3 人名意象
除上述所提及的意象之外,影片中人物的命名方式也颇有韵味。姓名一般被认为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艺术中,人物的姓名往往承载着创作者的艺术匠心。《红楼梦》中主要人物的姓名都有其典故,或关联其性格,或暗示其命运。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姓名也有其独特内涵,是鲁迅思想的巧妙投射。那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经历西方文化理论洗礼的费穆,在创作之际借由人物姓名实现对自我思想的言说,便不足为奇了。《小城之春》中的人名不仅起着指代某一具体人物的作用,而且具有历史文化层面的指涉。
以戴礼言和周玉纹为例。戴礼言这一名字不由使人联想到“大小戴,注礼记”之说,代表的是传统儒家“礼”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典型象喻。影片中,戴礼言穿着长衫,疾病缠身,那虚弱的身体象征着中国传统秩序历经战火的洗礼与新文化的冲击后逐渐没落,走向衰弱的状态。此外,周玉纹这一名字也极具深意。拆解开来看,“周”字代表的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礼乐”文化逐渐定型并成熟,中华文明的根基就此奠定,费穆导演以“周”作为人物的姓,不免让人再次将女主人公与中国传统礼乐文化联系起来。然后是“玉”字。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玉被看作神圣之物,有沟通天地鬼神之能,因此常被用作祭祀的礼器,往往象征着宗教的神秘与皇权的至高无上。同时,美玉还有君子美德的象征。例如,《卫风·淇奥》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又如《礼记·娉义》言“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无不在歌颂君子的高尚品格。类似之言,数不胜数,在此不过多列举。总而言之,玉是中国传统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费穆在此取“玉”字作为人物的名,其深意不言而喻。然而最有趣的,是导演又在“周”和“玉”后面加上了一个“纹”字。这大概有两种解释:其一,代表玉上绘就的花纹;其二,代表裂纹。名字的多义提供了多重解释空间。不过结合影片中周玉纹一边向往自由一边难以逃离小城的状态来看,“纹”字大概取自第二个含义,代表着尽管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已经出现裂纹,但终究还未真正瓦解。影片中周玉纹在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戴礼言和象征西方新文化的章志忱之间徘徊纠结,何尝不是费穆等知识分子在面对新旧文化冲突时,欲弃旧从新的愿望的情感外化呢?最终周玉纹并未离开小镇,离开礼言,又何尝不是在传达当时知识分子面对中西方的文化冲突时,坚定地站在中国传统文化一边的决心呢。
总之,通过系列意象的并置,费穆突破了有限的象,创造出了一个超越现实生活之“实”的感性世界,一个意与象合、情与景谐的有意蕴的空间,完成了一次既包含理又包含情的不可言说的言说,其余韵一直延绵至今。
3 结语
具有诗人情怀的费穆,创造电影意象的灵感既汲取自诗词绘画,又来源于中国传统戏曲。基于多次戏曲片的拍摄经验及他对戏曲美学时空观的深刻认识,费穆拍摄的《小城之春》,场景高度简洁,全片以城墙、废园、屋内为主,出场的人物也仅5 人。“小城”的全貌什么样,戴家周围住了些什么人家,这些信息全未言明。这显然并非真实的世界,而是导演借以抒情的一个“与世隔绝”的舞台。为展现这一舞台,导演尝试用中国画的方式进行拍摄,极少使用正反打镜头,极少拍摄单个人物的近景和特写,而是以长镜头、单镜头为主,这种拍摄方法尽可能地保留了舞台的完整性,甚至还产生出一种写意感。
此外,费穆在电影创作中借用大量意象,完成了将写意与写实、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的创造,集中体现了中国古老而又生机盎然的艺术精神,与无数坚持以民族化为创作导向的电影人一道,为中国电影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值得被反复学习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