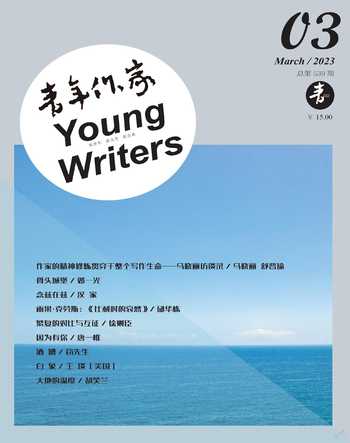作家的精神修炼贯穿于整个写作生命
马晓丽 舒晋瑜
读书、思考、写作,是毕生的功课
舒晋瑜 :您是怎么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文学的熏陶来自什么?
马晓丽:应该是读书吧,我猜想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读书爱上文学的。
我读书还算早,小学时突然没学上了,整日无所事事,就开始翻我爸的书架。我爸的书架上主要有三种书:马列著作、鲁迅的书和古典文学著作。我基本把鲁迅全集都翻遍了,不仅看小说、诗歌,也看杂文、书信、日记。虽然生吞活剥看不懂,但能在里面感受到一种气息,有一种犀利的存在,这对我是有影响的。看完鲁迅没东西看了,就硬着头皮啃古文。好在有《中华活页文选》,里面对原文有逐字逐句的注解,硬读些日子逐渐就能读出大概意思了。之后,我就磕磕绊绊地把《左传》《战国策》《东周列国志》和四大名著等书都囫囵吞了一遍,直读到简体字繁体字没区别,横排版竖排版无障碍。
我是在入伍之后才开始大量阅读外国文学的。那时很多世界名著都被列为禁书,爱书人只能通过地下流转的方式,偷偷地互通有无。几乎每个爱书人手里都有个世界名著的长书单,在那个书荒的年代找到一本书都很难,即便找到了一本,书在手里滞留的时间也很短,因为后面还排着长长的一串人在等着看呢。我带着书上夜班偷偷看,下夜班后立刻抱着馒头躲到上铺,钻进被窝里看。饿了就啃口馒头,整整一天除了上厕所就没下过床,抢着把五百多页的小说看完了。虽然那时我经常因为偷看受批评,很是影响进步,但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读书过程中,文学逐渐潜入了我的意识。其实从很早开始,我心里就隐隐地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迟早会写点东西。只是我把文学看得太重,所以开始提笔创作很晚。
舒晋瑜 :您喜欢的作家有哪些?能否谈谈您的阅读喜好?
马晓丽:中国的作家我还是喜欢鲁迅。虽然说自己喜欢鲁迅很像有附会的意思,但我还是得说,因为是真喜欢。
我最喜欢鲁迅的小说不是他最著名的那几篇,而是《孤独者》和《在酒楼上》,今年我还把这两篇小说翻出来又重读了一遍。这两篇小说都是写知识分子的,写知识分子的失意、绝望和自我沉沦。每当看到魏连殳那般傲世的人不得已折腰,看到他最终沦落到连大良们也躲避嫌弃的地步,心都会酸楚疼痛颤抖。
我不太喜欢鲁迅的《故事新编》,特别不喜欢鲁迅的翻译语言,《死魂灵》被他翻译得简直不忍卒读。
日本作家我喜欢远藤周作,特别喜欢他的《深河》。远藤周作的目光里有着一种超越种族、宗教和所有政治形式的大悲悯。他的文字不激越、不喧嚣,只静静地搅动着你,令你心底深处的淤积不断泛起。于是,你就如蹚入了污浊的恒河一般,看到了河流之中漂浮着的无数善恶灵魂,你会因此感到不安、感到痛,会心情沉重寝食难安,会不由自主地检省你身处的环境,检省你自己……如此一来,阅读《深河》就如同去恒河朝拜的信徒一样,在这条圣河中洗涤了自己的灵魂。
有一次我在日本京都逛旧书店,看到了日文版的《深河》。虽然不识日文,因为太喜欢,我还是忍不住买了本带回来留作纪念。顺便说一句日本的旧书店。不用的书拿过去,店里当场给你估价付钱。两层楼的书店,摆满了整理后上架的旧书,标价便宜得令人瞠目,我当场就感慨万分。
我还很喜欢拉什迪的《午夜之子》。这本书我看的是电子版,因为这本书当时在国内还出不了。电子版的名字是《午夜的孩子》。可能是先入为主吧,我至今还是觉得这个名字更好。五十多万字的书,我竟然在电脑上一口气把它读完了,直看得眼酸脖子痛,按鼠标的手都抽筋了。看完之后我欲罢不能,嫌在电脑上翻看费事,干脆把整本书都打印出来。我很惊讶拉什迪用看似无关的小事连缀大历史的能力,很喜欢他灵动跳跃的思维和语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本打印书都摆在我的电脑旁。我常常随手翻看,在我打上记号的段落和涂上颜色的句子里找感觉。
喜欢的作家还有很多,比如茨威格,他是个全能型的作家。还有安德森,他的《小城畸人》里的人物个个都是有精神诉求的人,他让我懂得了小说应有的精神叙述追求。还有马尔克斯,他的《百年孤独》那句:所谓一个幸福晚年的秘诀,就是与孤寂签订一个体面的协定。一句话就把人的心扎透了。还有福克纳,那枝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花,道尽了人在世间的寂寞、孤独、无助和无奈。我还挺喜欢毛姆的,他太聪明了。他的《巨匠与杰作》如同洞察人性的眼睛,用机智幽默的语气告诉你,你所仰慕的那些文学巨匠与你一样,也是有着人性缺陷的普通人:巴尔扎克把借钱当馈赠的不顾廉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嗜赌与无可救药的挥霍;司汤达一生虚荣而坎坷的爱情追求;托翁拈花惹草不幸染上了性病;福楼拜的癫痫症和暴躁、傲慢,竟让情人去打听自己发现的新猎艳目标;简·奥斯丁的缺乏优雅和喜欢拿别人缺点讽刺取乐;亨利·菲尔丁的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而把十位不同年代不同国籍的作家集合到一起,让他们在同一个客厅里相聚聊天,则是毛姆导演最精彩的一场戏。
舒晋瑜 :作为军旅作家,是否对军旅题材格外偏好?您喜欢哪些军旅题材的作品?
马晓丽:谈不上偏好,只是因为我是军人,所以才对军旅題材更关注一些吧。比较喜欢的军事文学作品大概有: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梅勒的《裸者与死者》、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巴别尔的《骑兵军》、奥布莱恩的《士兵的重负》、保宁的《战争哀歌》等。
舒晋瑜 :哪些书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有什么书曾激发您的写作欲望吗?
马晓丽:这个很难回答的,因为很多书对我的影响都很大,都曾激发过我的写作欲望。不仅是写得好的书,写得不好的书也会激发我的写作欲望。我常开玩笑说,对自己的写作没信心时,如果看看烂书,就会发现自己好像没那么烂,相信自己还是可以写下去的。
最终在文学中找到了最好的自己
舒晋瑜 :处女作发表在哪里,是自然投稿吗?
马晓丽:我的第一篇小说是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当时《中国青年》搞了一个全国青年短篇小说大赛,我试着写了一篇题目叫《夜》的小说投了出去。这篇小说是通过描写一个去南方参战的女兵,找回丢失了灵魂的故事。此前我曾经采访报道过参战女兵。在与她们相处的那段日子里,我感受到了很多。我当然看到了热血和勇气、理想和荣誉,但我也看到了在热血和荣誉背后追逐利益的人性表达。这些日常无法感受到的东西给了我很大冲击。虽然我的任务只是新闻报道,但新闻报道无法表达我对个体生命的感受,无法延展我的思考。就在这时我想到了小说,想到小说有可能释怀我心中的淤塞。这篇小说写得很顺,我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一下子就投入进去。小说寄出去后,我其实没抱很大的期待,没想到在大赛中得了个一等奖,对我来说还是挺意外挺惊喜的。
舒晋瑜 :有过退稿吗?
马晓丽:退稿肯定是有的,应该不是太多,所以记忆不是很深。其实我写东西本来就不多,而且又习惯自我枪毙。常常不等发出去等人家退稿,自己就先把自己的稿子给毙掉了。我电脑里应该藏了不少这样的东西。从这个角度上讲,也不能算顺利吧。
舒晋瑜 :最初的写作如《夜》和《长大了》,被评论家称为是您创作的“少女期”?
马晓丽:那时的创作是很盲目的,没有想法,随意性强,碰到什么写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只是有一种写作的冲动,这种冲动里既有对文学的热爱,有表达的愿望,也有名利的追求。创作早期这种名利追求是有益的,助燃了我的创作热情。我那时就与跟我一起获奖的人一样,沉醉其中,觉得小说没那么难,我写第一篇就获得了成功嘛。当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跟著名作家对话座谈,与文学泰斗同桌进餐,让我得意洋洋地晕了很长时间。其实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文学为何物,根本不知道小说为何物。所以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飘飘然地写了一些不知所云的质量不高的东西。
“挣脱”,军事文学现场最常说的一个关键词
舒晋瑜 :从新闻干事到专业创作,当时的创作心态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马晓丽:从新闻干事到专业创作是我人生中一次最重要的改变,这个改变不是形式上的,不是从一种写作转变为另一种写作,而是观念意识上的,是从一种生命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生命状态。
刚开始从事专业创作时,新闻干事的思维和眼光一直制约着我,使我无法进入文学本身。加之当时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社会变得越来越浮躁,各种诱惑纷至沓来,这种情况对我这样一个基本文学观念还没有形成的作家来说是很致命的。那时我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谁找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这个找我写电视剧,我就去写电视剧;那个找我写报告文学,我就去写报告文学。我好像永远都在按别人的意愿写作。我想摆脱这种状况,但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回想起来,那时我的精神是不健全的,文学品格是不健全的。记得山东作家刘烨园曾写过一篇文章《以大陆的名义》,是他读伊姆雷获诺贝尔文学奖感言的一些感想。文章大意是说,作家应该像伊姆雷那样,在精神上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大陆,应该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力量,只遵从自己的内心而独立于世。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这里面有一种鼓舞我的力量,鼓舞我从长期的精神束缚中挣脱出来,让自己的精神变得强大起来,有能力抵御干扰摆脱诱惑,进入真正的文学状态。
当然,作家的精神修炼是长期的,是贯穿于整个写作生命过程的。不仅从新闻干事转到专业创作,其实时至今日我还在不断地从精神束缚中往外挣脱。挣脱,是这些年我在军事文学现场最常说的一个关键词。
舒晋瑜 :《手臂上的蓝玫瑰》收入了八个短篇小说,开篇《舵链》中,您塑造了两个英勇又无私的军人形象,一个是在惊涛骇浪中抢修舵链的矮个子兵,一个是在风浪中将自己绑在舵位上的艇长。这篇小说读来酣畅,尤其是语言,和您过去的作品相比有极大的反差。
马晓丽:我得说您的阅读感觉很准确,真就是从《舵链》开始,我的语言有了改变。之前我一直习惯书面语。写这个短篇之前,我已经对自己的语言产生了厌倦,特别渴望改变,渴望让自己的表达更自如、更自在。所以写《舵链》的时候,我就开始试着放松自己,不再约束口语,结果发现这样写作特别自由舒畅,有快感。后来写长篇小说《楚河汉界》时,我又加入了一些方言的味道,感觉上灵动多了。《手臂上的蓝玫瑰》写的是一个东北女人,她的语言基本就是比较生猛的东北话,小说发表后还有文章专门评论这篇小说的语言表达。
舒晋瑜 :似乎军旅作家都有这样的特点:比较善于在战争和灾难中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您的作品弘扬军人的正面价值和崇高精神,写得非常流畅自然,没有丝毫拔高之感。
馬晓丽:不仅军旅作家喜欢把人放在战争和灾难中来表现,其实很多作家都乐于展现人在极端环境下的精神样貌。这可能是因为战争和灾难往往是生活的横断面,会把日常生活撕裂开来,以极致的方式把人逼到死角,使人性的不同面向凸显出来。这正是最吸引写作者进入,去挖掘人性更多可能性和深刻性的地方。
我觉得作品有没有拔高之感,可能与写作者的目光、价值判断和对个体生命的关切有关。军事文学历来推崇英雄主义,我不否定英雄主义,也赞成卡莱尔对于英雄主义是人的生命的要素、是我们这个世界中人类历史的灵魂的说法,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过度提纯英雄的概念。英雄也是常人,只是在特定情境之下,会做出超于常人的高尚举动。所以我一般不会以弘扬定位,我更愿意从关切个体生命的角度出发,平视人物,发现常人身上的崇高。更何况并非只有在战争和灾难中,只有流血牺牲才能更好地表现英雄主义。我喜欢的军事文学作品大多是关注人在战争中命运的。所以我能记住的往往是,分别在背囊里带着好运鹅卵石、一条兔子腿、尸体上割下来的大拇指、女朋友的连裤袜等的那几个美国兵(奥布莱恩《士兵的重负》);那只被踩断了脖子的鹅、那封由男孩子口授给母亲的父杀子子杀父的家书、那位用一双蜡黄的大耳朵倾听战斗进程的奄奄一息的团长、那个在团长出殡队伍里被揪住头发打得满面鲜血的寡妇(巴别尔《骑兵军》);越南那个从战场上回来后始终感觉自己不是在活着,而是被困在这人世间的阿坚(保宁《战争哀歌》)……
舒晋瑜 :您在《舵链》中借人物之口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互相走近的。是否有特殊的意味?
马晓丽:那倒没有,这只是我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感受。常有这种情况,你认可一个人,认为对方与你是同类,但你们没有机缘走近。或者是你发现对方对你没有相同的感受,抑或是对方虽然也有感受,但你们谁都找不到切入的那个口。这可能就是被说得烂俗的有没有 “缘分”吧。
舒晋瑜 :最打动我的是您在小说中对于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和刻画。您是如何把握人物心理活动的?
马晓丽:首先是敬畏吧。我曾经在一篇创作谈中表达过这样的意思:那生长着无数细密的毛孔、蒸腾着热烘烘气息的鲜活的灵与肉是不可辜负的。你得敬畏,你得带着敬畏去理解笔下的人物。你得竭尽可能地用你全部的情感、全部的心智去贴近那些生命,感受那些生命,与他们一起冷、一起热、一起忧伤、一起落泪、一起流血、一起愤怒,甚至一起生、一起死……写《楚河汉界》的时候,我就与小说中的那些人物在一起相处了整整两年,感觉那两年间真是挺熬心力、挺耗体力的。
《楚河汉界》是最费心力的作品,也是最命运多舛的作品
舒晋瑜 :文坛对《楚河汉界》评价很高,但是很遗憾,并没有像之前的几个中短篇有很好的命运,未能获得大奖。
马晓丽:《楚河汉界》是在评上全军最高奖后,被作为问题小说拿下来的。《 楚河汉界》受挫之后,我个人的狭隘功利目的基本落空,这给了我很大打击。我所说的个人狭隘功利目的就是获奖、出名、立功、晋级等利益。在那之前,我一直是很渴望得到这些利益的。幸运的是,我的目的没能达到。
我把这说成幸运,是因为由于《楚河汉界》的受挫,才逼着我开始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反省,对军事文学创作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才使我在追问、反省和思考中从狭隘的功利写作中清醒了。它至少给我带来了两方面的好处:一是使我沉静下来,避免了因获奖而可能造成错误的自我认定。否则我会以这篇小说作为自己的军事文学创作标杆。以我现在的眼光,已经能够很清楚地意识到《楚河汉界》中带有许多我多年精神捆绑的烙印,带有我文学意识和文学思维的诸多局限了;二是使我对文学奖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在我看来,其实任何文学奖项都与文学本身无关,它既不是文学的目的,也不可能促进文学质量的提升。从某种程度上讲,任何我们看重的文学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游戏。你可以去参与,但切不可当真,不可把这些东西当成文学追逐的目标。如果真的把它当作文学的理想去追求,就必然会陷入狭隘的功利写作中。其实挫折也是修炼,而且往往是更为有效的一种修炼。
舒晋瑜 :周东进身上体现着现代军人的生存状态、精神处境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和围困,他的桌子上摆着一个跪式兵马俑,他说这是“中国军人和中国军队的现状……但他永远在蓄势待发。”这些书写意味深长。
马晓丽:如果读者从中感受到了什么,也只是读者自己的领悟。也许我想说,从精神处境方面讲,我几乎一直都是跪着的,我的精神蜷缩着,从没有完全地舒展开过。我不想抱怨外力和环境,跪着是无奈,但也是自己的选择,谁让我不能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大陆,没有能力遵从自己的内心而独立于世呢。
舒晋瑜 :《楚河汉界》对于把握现代军营生活,包括军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都非常细腻到位,正如评论家林为进所评论的:“符合了军旅文学的一个特点:一种浪漫、传奇、理想和激情的特质”,他称这就是“军旅文学灵魂性的作品”。您认为写作中这部作品最难把握的是什么?
马晓丽:从写第一个字开始到画最后一个句号为止,整个过程都很艰难。起初有人告诉我,长篇小说写出三万字以后就好了。我写了三万字后,发现并没有出现好的感觉。又有人告诉我,写到五万字以后就会一马平川了。好吧,我坚持写到了五万字,结果根本没有什么一马平川,还是坡,还得继续爬坡。我好像在整个写长篇的过程中一直在爬坡,好不容易爬过了一个坡,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呢,就发现前面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坡,就这样整整爬了两年。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当天,我的腰就不能动了。我很羡慕那些才思泉涌下笔千言的作家,可惜上天没有赋予我那样的才力和体力。
在写长篇的这两年间,我与自己笔下的那些人物整天生活在一起,为他们的命运所牵扯纠结,心力交瘁,寝食难安。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赋予他们灵魂性的东西,但正如我在扉页上写的那样——追随着一个个生命历程,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鲜活是怎样在成长过程中失去水分,一次又一次地看着个性是怎样在成熟的修剪中得到规范。但理想从不曾泯灭,个性从不曾消亡,再艰难也还有人在坚守,在拼全力拒绝人的植物化蜕变。
舒晋瑜 :您是否也属于“理想主义”?又如何看待筆下这批具有理想主义的军人?
马晓丽:我没那样的勇气,但我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注重精神追求的人一直怀有浓厚兴趣。在世俗的社会环境中,理想主义者通常都会受挫、会失败,有精神追求的人也总是会被视为异类。正因为有了这些人,暗夜中才有了燃灯者,才有了些微光,才使如我这样怯懦的人,也有了对彼岸的向往和前行的勇气。
《云端》被称“特立独行”,直面如何对待革命进程中文明的丢失
舒晋瑜 :《云端》好评颇多,这个作品人物有原型吗?您的写作,设计情节或人物,是否理念在前?
马晓丽:《云端》是迄今为止我自己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作品当然是虚构的,但任何虚构都必然会有现实投射。写这篇小说的起因是我婆婆。我婆婆是个1938年入伍的八路军,有一次,她看到有些老干部家属的不文明行为时,对我说了一句:太没有知识了,还不如我看管的某些国民党小老婆呢!她的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通过交谈我发现,我婆婆对“某些国民党小老婆”怀有非常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她鄙薄她们,因为她们是敌人;另一方面,某些国民党小老婆颇有文化,她又暗暗地欣赏她们言行举止中透出的文化气息。我想知道,是什么使我婆婆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会时不时地超越阶级意识看待不同阵营的敌人。我婆婆不可能跟我探讨这些,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突然又冒出一句:我还从一个国民党小老婆裤裆里搜出了金条,被大会表扬了呢!我心头一震,在满脸自豪的婆婆后面,我看到了另一个女人,那个被婆婆称为国民党小老婆的女人。我突然很想知道,这样两个不同的女人之间究竟会发生些什么。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理念在前,但在开始下笔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她们的走向和结局。
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的确想让叙述缓慢一些、绵密一些、小资一些。我觉得这样会更女人,觉得这应该是一篇很女人的小说。
舒晋瑜 :《西厢记》在《云端》中是否有象征意义?
马晓丽:大概因为我喜欢过《西厢记》吧,而《西厢记》又恰巧是传统文学中的经典,曾经为那个年代的许多小知识分子所喜爱。共同的喜爱会唤起共同的文化记忆,而共同的文化记忆会让人产生认同感,在看起来并不相同的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
舒晋瑜 :《云端》中两个女人涉及私密的对话,我觉得似乎不大能够理解。那个年代,包括她们的特殊身份——总觉得不大真实。我想知道的是,您如何看待虚构的合理性?
马晓丽: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不能理解女人之间的私密话题。也许您认为在那个年代不可能有那样的私密话题,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无论是在哪个年代,女人对私密话题的克制和释放都是一样的。就如同男人之间常在私下谈论女人一样,女人也会在适当的契机下谈论男人,包括谈论自己的身体感受。当然,契机很重要,即便她们的身份不同,但只要给了她们合适的契机,就会唤起她们探究身体和生命秘密的兴趣和热情。这是一种来自生命本身的自然驱动力,是任何环境和外力都无法彻底遏制的。
说到虚构的合理性,我认为虚构通常都是建立在作家自觉的合理性上面的。当然,作家的自觉未必一定能与所有读者的他觉相吻合,在这里我的自觉与您的他觉显然就不吻合,这很正常。其实,您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建立在您的虚构基础上的。您虚构了一个那个年代的现实,以您虚构的现实来衡量,认为在那个年代,这两个不同身份的女人之间进行私密对话是不真实的。那么问题是,您的虚构是否就具有合理性呢?
舒晋瑜 :这反问来得很有力量——不论如何,《云端》对于军旅题材是一种突破和超越。是否影响大的作品,在写作中也是比较顺畅的?
马晓丽:这篇小说刚发表的时候影响并不大。《十月》起初准备发头题,但因故最终发在了末题。发表后只有《中篇小说选刊》选了一下,别的选刊都没有选。是在后来,这篇小说被评论家打捞出来,不断地分析、讲述,这才引起了注意,有了好的反响。说来惭愧,我写东西从来都很费劲,从来都没有下笔千言一挥而就的时候。而且我是个很不自信的人,写完东西立刻丧失判断能力,常常是在得到别人的肯定之后,才对自己的作品有了点信心。
总能把世俗生活写得活色生香
舒晋瑜 :您在200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舵链》,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后被《小说选刊》转载,并获得全军的一等奖,引起广泛关注。能谈谈这个短篇对您的意义吗?
马晓丽:这个短篇之前,我开始对自己的语言产生了怀疑。之前,我受新闻写作和阅读翻译作品的影响,语言一直很板。那段时间我对自己的语言越来越感到厌恶,急需寻找一种令我的表达更舒服、更自然、更个性化的语言方式。现在想来,其实任何改变,都是从怀疑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当时自己还没意识到。写这篇小说时,我试着让自己放松,不再绷着,不再刻意修饰生活语言,结果发现笔下的文字和人物一下就活起来了,有了生气。这种改变令我很享受,就像打开了一扇门一样,连思维都变得自然流畅起来。所以我想,语言与思维大概是二位一体的,也许语言的变化原本就来自思维的变化。从这个短篇开始,我的小说语言有了新的变化,也为接下来我的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经验。
舒晋瑜 :《俄罗斯陆军腰带》《云端》的叙事方式中暗含冲突和对立,但并非是两个军官之间或两个女人之间的较量。在创作中您比较擅长设置戏剧性的冲突?
马晓丽:我没觉得自己擅长设置戏剧性冲突,只是觉得小说中的矛盾冲突应该有所选择。生活中有很多冲突和对立,但不是所有的矛盾都适合入小说。小说撷取的冲突和对立应该是那种并非两个当事人之间个人意气的较量,而应该是背后有着历史的、文化的、世俗观念一类东西支撑着的对抗,其中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价值观的冲突。这样的矛盾设置更有可能引发思考,更有可能把思考引向深处。
舒晋瑜 :您的很多中短篇小说,几乎都由内心的误解导致矛盾和冲突,最终达成和解。
马晓丽:我并没有刻意这样做。但是,如果我的很多中短篇小说都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这个问题在我的潜意识中非常突出,否则我不可能下意识地一次次进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更关注人的内心冲突而不是外部矛盾?也许,我对人性的阴暗面和人性的不可挑战更为悲观?也许,我对人与人之间的无法理解、无力沟通更加敏感?其实,我笔下的结局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解,顶多是部分的和解。即便没有了矛盾冲突,即便有了好感甚至敬意,也不一定就能和解,也不一定就能成为朋友。我曾在《舵链》中借人物之口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互相走近的。其实,敬重一个人和与一个人交朋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舒晋瑜 :您的很多小说,从叙述方式上看有很大变化,而且每一篇都有从形式到内容的探索。
马晓丽:说老实话,我的文体意识是比较差的。我不是一个对叙述策略、结构有设想、对小说技巧有研究的作家。我的写作很随意,很缺乏规划性和目标性。曾经有朋友劝我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应该把住一个题材不断深挖,说这样的创作才有整体面相,才有评论价值,才容易被关注。我明白朋友的意思,但是我做不到。我只能随心所欲,对什么感兴趣就写什么,对什么厌倦了就放弃,然后寻找新的兴趣点。
比如写《催眠》这篇小说时我就不想叙述了,突然想能不能用对话的方式结构一篇小说。虽然对这种写法我没多少信心,但这个想法令我感到兴奋。我就决定先试着写写,大不了写不下去放弃重来。没想到这篇小说竟然写得很顺利,通篇没有一句叙述,都是用人物对话推进情节,竟还算是自然顺畅。由此可见,我的所谓“创新”可能并非主观意志,很可能缘于我容易厌倦的个性,缘于厌倦导致的下意识变化吧。
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悲观主义者
舒晋瑜 :在您的作品中,比如《手臂上的蓝玫瑰》《云端》《杀猪的女兵》等,伤痛感和绝望感特别触动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您对人生的一种基本认识?
马晓丽:我的确是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悲观主义者。在我看来,所有人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困境之中,无论是生存困境还是精神困境。如鲁迅先生所言,“无数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所以大华、云端、洪潮们的困境都特别能触动我,令我伤感。也许,总想把这种伤感表达出来,说明我的悲观主义并不彻底,说明我对这个不堪的世界还抱有一絲希望。或者也可以说我的悲观主义不是叔本华式的,而是更接近尼采式的。
舒晋瑜 :无论短篇《白楼》《覆水难收》,还是长篇《楚河汉界》,主人公都是在权力角逐中失败的理想主义军人,您为什么总是塑造这一类人物?
马晓丽:大概是因为现实中太缺乏理想主义,太缺乏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人了吧。在当下,这种趋利弃义的社会环境中,理想主义很不合时宜。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在人群中平时会显得很傻、很幼稚,到了关键时刻就可能会因为傻和幼稚的抉择触犯众怒而被抛弃。所以,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通常都不会有好的结局。我也常常希望笔下的理想主义人物获救、获胜,哪怕只有些许获得,无奈总是不能,总是走着走着就无路可走了。这成了我心中的痛,成了一种无望的希望,所以才会忍不住总朝这个方向张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可能也算是有点理想主义色彩的,只是我不愿意承认,害怕承认了会露出自己的愚蠢相,会被人嘲笑。
用心灵去感知并书写真实的生活
舒晋瑜 :谈谈您的散文创作吧,最新出版的《不堪的朋友》,收入您的多篇散文,让我了解到真性情的马晓丽。军旅题材的散文也占了一定比例?您的散文都是从内心流淌的文字,真诚动人。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散文?
马晓丽:散文我只是偶尔为之,一般都是被人或事触动之后,心绪涌上来了不写不行。可能正因为是偶尔为之,没有计划、目标、任务等外在因素干扰,所以就少有应制之作,基本都算是应心之作吧。我以为散文是得摸着心来写的。
舒晋瑜 :“光学之父”王大珩的传记,正在修订中,您如何看待这部旧作再版?
马晓丽:王大珩先生那代人,无疑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一代人。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不掺杂一丝杂念地为这个国家付出。他们这批人是值得被书写的,是值得被这个民族记住的。我当然很庆幸写了王大珩先生的传记,很高兴这本书能一再重印、再版。
舒晋瑜 :您觉得小说家写报告文学是否更有优势?
马晓丽:这可不一定,要看写哪一类纪实文学(我更愿意说纪实文学),更主要的还得看写作者的视野、格局、知识结构,甚至包括个性气质。比如茨威格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就具备以上所有的优勢,所以他既能写出细腻动人的精彩小说,又能写出大气磅礴的纪实文学。当年我看《历史上的十四个瞬间》,也就是现在翻译出版的《人类群星闪耀时》,简直爱不释手。顺便说一句,我更喜欢原来的书名。茨威格善于从细微处入手,准确拿捏历史的关节处,把真正具有历史意义、能够改变人类格局的瞬间事物、人物展现出来,读来令人叹为观止。茨威格又被称为人类最会写传记的作家,他为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尼采等众多名人做过传。我想,茨威格的传记之所以写得好,应该与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有很大关系。读他的《一个政治家的肖像——约瑟夫·富歇传》,就如读小说般引人入胜,我特别喜欢。
舒晋瑜 :尾章《科学无价》中,您对于王大珩获得百万奖金后的复杂心态把握得非常好,能谈谈您的创作经过吗?
马晓丽:我对王大珩先生很有感情。写这部传记之前,我多次去先生家进行采访,常常在他家蹭饭。先生的老伴顾大夫是上海人,菜做得特别好。至今我还记得她用豆皮包住肉馅下在汤里,告诉我这叫“包袱”,还记得她精心煮了好几个小时的地道的罗宋汤。我还陪同先生一起去过长春,在他建立的中科院长春光机所进行采访。先生来大连参加活动,也会专门抽时间来我家见面。记得有一次我一时兴起,还拉着先生跑到一个陶艺家那里去看陶艺。接触时间长了,我俩几乎无话不谈,他甚至可以给我讲他从前的初恋,也给我讲他新近得到的小愉快。他晚年最愉快的就是在八十二岁那年,自费去漠河观看了上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在那之后先生有一次来大连参加活动,就特地把在漠河的照片揣来拿给我看。我现在还保存着很多采访先生的录音带,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有价值的。
记得我写完初稿拿去让先生看时,心中特别忐忑。我对先生说,您千万不要用审读论文的方式来看这个书稿。我自认为自己是个很严肃的作家,我的写作一定是基于事实的,但您得允许我在您记忆中断的地方,用合理想象来进行补充。几天后,先生来电话说书稿已经读完了,让我去他家一趟。我一进门,先生就迎了上来,说我想拥抱你一下可以吗?我知道先生是个很绅士的、从不轻易表达感情的人,他这样的举动足以表达了对书稿的认可,几天来悬在我心头的石头一下就落地了。先生那天特别高兴,非要请我出去吃饭。听说我有事马上要走就急了,扒开兜让我看他装在兜里的二百元钱,说我跟顾大夫把钞票都要来了。中关村新开了家肯德基,我想请你去那里吃。
我最遗憾的是,没能去参加先生的葬礼。我很感谢顾大夫,让先生的秘书从亲属这边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但主办方不同意。我提出自己可以自费前去参加,不用接待安排,但仍旧没有得到可行的回复。我只好放弃了,再次感受到真情实感面对现世的式微和薄凉。
把握女性题材悠游自在、出神入化
舒晋瑜 :作为为数不多的军旅女作家,您如何看待军旅文学中女性视角的创作?
马晓丽:我不太习惯这样谈论文学创作,这样的分类探讨似乎更适合评论家。作为军旅女作家,我的文字其实挺中性的,甚至常有人说我的作品里有阳刚之气。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知道自己是该为此高兴呢,还是该为此沮丧?让我多少有点放心的是,毕竟我的《云端》还是很有阴柔之气的。我想,如同男性视角不是男作家的专利一样,女性视角也不是女作家的专利。选取哪个视角并不完全取决于性别,比如作为男作家的毕飞宇就很女性视角,尽管他的女性表达常会令女性感觉不适。
舒晋瑜 :您认为怎样才能摆脱写作中的精神束缚?
马晓丽:我不知道。我一直没停止也没想停止阅读思考和写作,或许就是在寻找摆脱的方法。但我一直没能完全摆脱精神束缚,没能进入更为理想的写作状态。究其原因,除去外部因素外,自身最重要的就是功利写作问题,我认为功利写作一直是我自己也是我们军事文学面临的最大困境。
谈到功利写作,这个概念有时显得很模糊。从宏观上讲,无功利的写作是不存在的,任何写作都带有很明显的功利目的,无论你是从个体出发还是从人类出发,无论你是从物质需要出发还是从精神追求出发。问题是,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功利写作,我们怎样才能不断地从狭隘的功利写作中超拔出来,进入更高一层的写作境界。这其实是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需要面临的问题,也是一个写作者毕生都要面临的问题。
当下的世俗社会充满了对写作者的诱惑,总有各种各样由写作带来的利益在向我们招手,这里除了物质利益诱惑之外,更有名目繁多的社会性文学倡导的诱惑和不一而足的文学奖项的诱惑。狭隘的功利写作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遮蔽我们的目光,使我们丧失感受真实和表达真实的能力。
我希望自己能够不断地从目前的功利写作中超拔出来,进入更高层次的写作状态。我希望自己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文学品格,进入相对纯粹的文学境界。
舒晋瑜 :在创作上您是顺其自然还是有明晰的创作规划?
马晓丽:顺其自然。对于我这样一个懒散的人来说,即便制定了目标和计划,也没有毅力完成。我只能顺其自然,情绪来了就写,不想写了就放下,所以我写作量很少。每当有人提及这个话题,我都感到特别不好意思,挺惭愧的。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拿自己也没办法。
兴致勃勃的尝试让写作有更多的期待
舒晋瑜 :在写作中您会遇到哪些困难?怎么解决?
马晓丽:我最大的困难应该还是在学识方面,因为没有系统的知识储备,所以缺乏哲学思维能力、缺乏用哲学目光关照现实的能力,这就导致了我的眼界、格局、认知受限。我一直希望能通过读书和思考进行一些弥补,无奈先天不足。人在精神成长期能汲取什么质地的营养很重要,有些东西在你最好的时候错过了,过后再想弥补就很难,需要花费数倍的精力去甄别、置换,我只能尽量努力吧。
另一个困扰我的问题就是懒散。我是一个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没有自制力的人。我很讨厌自己的这副样子,也曾经多次咬牙切齿试图改变自己,但終究还是拿自己没办法。今年六一我看到好多作家都在转契诃夫的一封信,信上说“没有钱用,但又懒得去挣钱。请您给我寄一些钱来吧!我决不食言,我只懒到5月份,从6月1日起我就坐下来写作”。这封信令我愉快得要死,看到伟大作家也有懒的时候,心中顿生德不孤必有邻的快感。尽管知道人家契诃夫一生创作了四百七十多篇中短篇小说和十几个剧本呢。
舒晋瑜 :您对自己的小说语言有怎样的要求?
马晓丽:首先应该是准确吧,尽量避免词语障碍,减少传递中对原意的损耗。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尽量放纵个性,让语言从规范中跳脱出来,自由些,灵动些,最好能仅凭语言而不是情节,就能牵住读者的手行走下去。
我对自己的语言没有风格化的追求,我既喜欢那种看似平淡,甚至有点笨拙,但内里蕴含意味的语言;也喜欢那种机智幽默、充满知性的语言。我希望自己能掌握更多的语言方式,能使用更多样的语言进行写作。只是我力所不逮,常常背离所愿,最终还是会落入自己的语言习惯。但我喜欢这样的尝试,这样至少会让我有兴致,让我的写作有更多期待。
舒晋瑜 :您有没有最崇拜的作家?
马晓丽:我提到的和我没机会提到的很多作家,都是我最崇拜的作家。如果硬要说一个的话,那就算茨威格吧。
舒晋瑜 :您认为哪一本书是所有作家的必读书?
马晓丽 :这个我可说不出来,我是个瞎读书、乱读书的人。应该没有这么一本通吃作家的书吧?等等,有,用正儿八经的方式说,就是社会这本大书。
舒晋瑜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马晓丽 :那就带两套总想读,总也读不下去,一直没读完的书吧,《资治通鉴》和《追忆似水年华》,再带一本保罗·策兰的诗集用来调剂口味。
舒晋瑜 :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马晓丽:那得找几个好玩的人,比如塞万提斯、哈谢克、凡尔纳、巴尔扎克、阿加莎·克里斯蒂、马克·吐温、海明威、卡尔维诺、阮籍、吴敬梓、王小波、王朔,还有我的朋友刁斗,当然还得有毛姆,得让他来主持。
舒晋瑜 :如果您可以成为任意文学作品中的主角,您想变成谁?
马晓丽:孙悟空。
舒晋瑜 :您目前是怎样的创作状态?听说还在带学生,能谈谈具体情况吗?
马晓丽:带学生是个意外。前几年辽宁作协实行导师制,让我当导师,给省里带几个学生。我其实是没有底气当导师的,而且这很可能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没名堂、没经费、没报酬,但我很痛快就应下来了。为什么?我对我的学生是这样解释的:我之所以同意给你们当导师,主要原因不是你们需要我,而是我需要你们。随着年纪的增长,我感觉到自己的周边环境越来越老化、越来越固化了。这让我很忧虑,担心自己这样下去保持思维敏感度和新鲜度的能力都会退化。所以我抓住了这个当导师的机会,希望能在帮助你们的同时,也得到年轻的你们的影响,共同营造一个有益的文学生态小环境。我说,拜托,你们得帮我!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几年来,我们这个六人小集体里的每个人进步都很大。其中有获得茅盾新人奖的班宇,有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的姚宏越,还有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胡月。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学生们对我的帮助也很大。他们不断地打破我日趋固化的边界,为我推荐年轻人喜欢的新书,把我的阅读范围拓展到近年来的韩国文学、越南文学等方面,特别是他们对思想类读物的关注和解读,让我格外为他们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