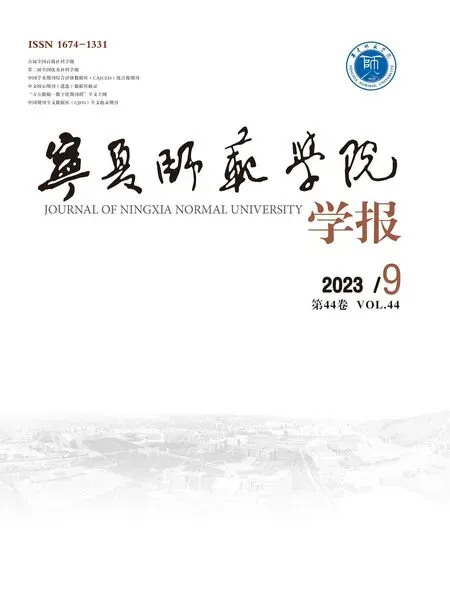比较文学视域中的维谢洛夫斯基
李 琪
(大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
作为一门学科、一门科学,以及一种可以上升为方法论的研究方法,比较文学的学理在百年多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得以提出、夯实,也不断被挑战、质疑,比较文学在磕磕绊绊中完成了自身的蜕变与转向。在这门学问百余年沿革中,学界涌现出诸多杰出的学者,除了公认的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功不可没之外,德国审美历史主义者也为这片领地贡献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一点尤其可以从诸多德裔美籍学者的学术成果上得到印证。同样,俄苏学者则在这片领域里勤奋耕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这些学者中,毫无疑问,最耀眼、最杰出的一位就是被公认为“俄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谢洛夫斯基(Alexander Veselovsk,1838—1906)。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与语言的隔阂,加之维谢洛夫斯基著述表达之艰深难懂,长期以来,中国学界虽然也有对俄苏比较文艺学派和维谢洛夫斯基的学术思想进行专门译介与研究的著述,但是研究成果并不丰富,且更多研究者将笔力集中于维谢洛夫斯基之后,即绕过维谢洛夫斯基谈问题,学界至今尚无从比较文学学理的角度,对维谢洛夫斯基的比较文学或比较文艺学成就予以系统梳理的研究。
一、“俄国比较文学之父”:维谢洛夫斯基的学术成就概览
维谢洛夫斯基是俄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也是一位语言学家和语文学家,同时还是俄国和西方中世纪文学的出版者和译注者。
阿列克赛德罗·尼古拉耶维奇·维谢洛夫斯基1838年生于莫斯科一个中等贵族家庭。父亲是莫斯科一所武备中学的军事教员,一位“经常关注俄国和欧洲科学、文学界的一切杰出事物的”富有教养的人,母亲是一位德裔医生的女儿。受家庭影响,维谢洛夫斯基从小便掌握并能够熟练运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和西班牙语,从童年时代起对文学极感兴趣,这为他日后从事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值得一提的是,维谢洛夫斯基的弟弟阿·维谢洛夫斯基(1843—1918)也是一位蜚声学界的文学史家,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他的观点对后来的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有很大影响。
维谢洛夫斯基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攻读期间(1854—1858),正值俄国这所最古老的大学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也是革命民主派同纯艺术论者、斯拉夫主义者就俄国社会和文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展开激烈论战的时候。维谢洛夫斯基的导师布斯拉耶夫教授引导维谢洛夫斯基研究古代俄国文学和民间文学,引导他去了解格林学派影响下统治西欧和俄国科学界的理论;当时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与实证主义也吸引着维谢洛夫斯基。
1858年,维谢洛夫斯基结束大学生活并留校做升教授的准备。他渴望去国外深造,以深化对他所感兴趣的西欧文学的了解。因为经济拮据,他通过给俄罗斯驻西班牙公国公使戈利岑公爵一家做家庭教师的机会,到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英国逗留,开阔了文化视野。1862年,维谢洛夫斯基获得公费资助到国外专门学习。他在柏林大学听了德语和拉丁语文学方面的讲座,为他日后教授德语和拉丁语打下更好的基础。同时,这些经历也使他了解了史诗理论问题。在布拉格和塞尔维亚的访学,使维谢洛夫斯基深化了斯拉夫学领域的知识。意大利岁月(1864—1867)则使维谢洛夫斯基开始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当时意大利卓越学者和诗人的友谊,成为维谢洛夫斯基社会历史宇宙观发展的动力。维谢洛夫斯基在自传中说道:“思想和机会全是在意大利产生的。”
莫斯科的师友们惦记着维谢洛夫斯基的返归。维谢洛夫斯基接到邀请,要他去新的大学开设总体文学教研室。回到俄国,维谢洛夫斯基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之后,被选为彼得堡大学教授。由于他的首倡,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之下建立罗曼—日耳曼部,总体文学不再是俄国文学教学的辅助课程,而是成为专门课程,用以培养西欧派语文学家这样的新型专家。1885年,维谢洛夫斯基组建新语文学学会。这个学会在以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成为俄国的西欧文学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中心。维谢洛夫斯基后来又以通讯院士、研究生、院士等头衔被吸收到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部工作(1876—1881),1901年,维谢洛夫斯基成为这个部的主任。维谢洛夫斯基的研究兴趣则从大学教学期间的语言和文学研究逐渐转向俄罗斯和斯拉夫语文学问题。
根据维谢洛夫斯基的学生日尔蒙斯基的考证,维谢洛夫斯基的文学遗产包括280多篇论文和书籍;他留下的未完成的集子大约26卷。这份巨大的学术遗产可以分为四个系统:第一,文艺复兴时期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意大利;第二,中世纪文学和民俗学(情节“流传”)研究;第三,历史诗学;第四,俄国浪漫主义。这些基本课题互相更替出现在维谢洛夫斯基的全部创作时期中,虽然出现时间或早或晚,但是都自觉地运用了比较的视角,尝试将文学史建成一门科学。维谢洛夫斯基于1863年第一次出国旅行时在日记中写道:“文学史究竟能不能成为科学的对象?我谈论文学史,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是文化思想史,而不是编年排列并夹杂以美学评价和风俗图景的文学事实的清单。”[1]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是整个历史的有机部分;而文学史的任务,就在于揭示文学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从而以此建立作为一门科学的文学史。
在文艺复兴研究方面,维谢洛夫斯基具有代表性的著述包括:《意大利小说与马基雅弗利》(1864)、《但丁和天主教象征诗》(1866)、硕士论文《关于〈阿尔贝济的乐园〉研究》(1870)、《布鲁诺传》(1871)、一篇论拉伯雷的论文(1878)、《英国文学史》(1888)、《薄伽丘,他的环境和同代人》(1893)、《在康左纳拉诗歌自白中的彼得拉克,或译《诗体自白——〈歌集〉中的彼得拉克》(1905)。此外,他还写作了许多短文章,维谢洛夫斯基还是多次重版的优秀译本《杰卡梅龙》的译者。
在中世纪文学和民俗学方面,维谢洛夫斯基的研究包括:壮士歌、教会诗、民间故事,基督教传闻和伪经,民间仪式和信仰,中世纪传奇及故事。重要著述有:博士论文《关于索隆和吉托弗拉斯的斯拉夫传说和关于莫洛里甫和梅尔林的西方传说》(1872),总标题为《基督教传闻发展史研究》的系列论文(1875—1877),《俄罗斯教会诗研究》(1879—1891)、《南俄壮士歌》(1881—1884)、《壮士歌短评》(1885—1867)、《传奇和故事史摘要》(1886—1888)等,还有一些长短不一的著作,发表在专门性的科学出版物上。
历史诗学方面的问题,在维谢洛夫斯基从事科学活动一开始,就同他顺序进行的个别专门问题一起出现在他的研究视域中,重要著述包括:《寻路者日记摘录》(1859)、《作为科学的文学史的方法和任务》(1870)、《诗学》系列论文(维谢洛夫斯基去世后统一收集在其文集第一卷中,1913)、《历史诗学引论摘要》(1894)、《修辞语史摘要》(1895)、《作为编年因素的叙事性复沓》(1987)、《心理平行现象及其在诗歌体裁反映中的形式》(1898)、《历史诗学三章》(1899),等等。维谢洛夫斯基还在彼得堡大学开设了与历史诗学相关的课程,例如《文学史的理论导引》(《历史发展中的诗歌类别问题》),这门课程分为三部分:《史诗史概论》(1881—1882)、《抒情诗和戏剧学》(1882—1883)、《传奇、中篇故事、民间书籍和短篇故事史概述》(1883—1884)。维谢洛夫斯基每年还在大学开设各种不同名称的历史诗学课程:《诗歌类别史引论》(1888—1889)、《诗学理论课程》(1892—1893)、《诗歌形式的历史发展》(1893—1894)、《诗学引论》(1894—1895)、《历史诗学》(1986—1897及以后)、《诗歌情节史》(《情节诗学》,1897—1903)。最后一门课程内容的手稿,由希仕马廖维放入维谢洛夫斯基去世后出版的文集第二卷刊出的《情节诗学》未定稿中。
在俄国浪漫主义方面,维谢洛夫斯基的重要著述包括:《民间传说以及莱蒙托夫故事中的达马拉女皇》(1898)、《“阿廖沙·勃波维奇”与茹科夫斯基的“弗拉基米尔”》(1902)、《茹科夫斯基以及安德烈·屠格涅夫的新资料》(1902)、《茹科夫斯基:感情与“心灵想象”的诗歌》(1904),以及未完成的研究普希金的专著。
俄国科学院院士弗·米·伊斯特林高度肯定维谢洛夫斯基的毕生努力:“他像一个神话般的人物出现在远处。我们观念中产生了一个魔术家的形象,他坐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在凡人们被禁入内的魔术域内,埋首于汗牛充栋的著作之中,他从其中为自己获取对常人来说是难以获得的智慧。”[2]
二、维谢洛夫斯基的比较文艺史观
如前所述,维谢洛夫斯基的著述围绕着四个系统展开,这些基本课题互相更替出现在维谢洛夫斯基的全部创作过程中,维谢洛夫斯基以大量丰富的文学实例,从比较的视角,对具体或总体问题进行分析,并尝试揭示受制于社会历史发展总规律的历史——文学过程的规律,欲使文学史成为科学的对象。虽然《历史诗学》最能体现维谢洛夫斯基的比较文艺史观,但实际上维谢洛夫斯基的比较文艺史观是贯穿于他的全部著述的。
首先,维谢洛夫斯基持整体的、总体的、历史的比较文艺史观。他认为:“文学史,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这是一种社会思想史,即体现于哲学、宗教和诗歌的运动之中,并用语言固定下来的社会思想史。”[3]“语文科学实在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不能置于科学史、诗史、神学问题史、经济制度史和哲学体系史这些定义之下?”[4]由此可见,维谢洛夫斯基既强调文学与哲学、宗教的互动,也注重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学体现在文学样式、语言风格、艺术的本质等方面的演进,他在对文学实例进行大量而丰富的对比基础上,在广泛比较分析各民族文学现象的前提下,尝试总结文学规律,并由此构建他的诗学大厦。这种以文化—历史原则为基础的文艺观,意味着维谢洛夫斯基将文学发展同整个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将文学规律纳入广阔的社会发展规律之中。比如说,维谢洛夫斯基认为,被视为典型的俄罗斯世界观对俄罗斯而言并非典型,即使它表现了某种特征。维谢洛夫斯基认为,这种特征并不能说是种族的,也不能是民族的,更不是特定文明的,而应当是某种文化时期的特征,而一旦这种时期具备相应的条件,这种特征会在不同民族那里重复出现。而这些特征重复出现的原因,维谢洛夫斯基则从历史的、宗教的、民俗的、修辞的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剖析。
其次,维谢洛夫斯基持动态的、辩证的比较文艺史观。他认为:“我们对文学演变的观点是建立在历史远景之上的,而每一代人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所积累的比较分析对这一远景进行修正。”[5]这种观念实质上指向了对作品、作家、社会,以及接受者和文化语境等多个维度,涉及历史、文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范畴,这是一种立体的、多声部的、内核和外延呈现出动态的批评方式,显示出维谢洛夫斯基巨大的甚至是无与伦比的批评才华。这种观念与稍后出现在欧洲的接受批评有相似之处,然而维谢洛夫斯基的理念更加彰显大气宏阔的气质。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民族性”是国际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产物,是因为文化彼此交融混合之后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并没有所谓一成不变的、独特的民族性。比如,维谢洛夫斯基认为,修饰语史的背后有着悠久的历史心理远景,有着借喻、比喻和抽象观念的积累,是整整一部从有益的和心愿的观念直到分化出美的概念的趣味和风格的演变史。如在研究诗歌中的心理对比法的反映形式问题时,维谢洛夫斯基提到否定对比法多见于立陶宛与近代希腊的歌谣中,而在德国歌谣中较少见到;在大俄罗斯歌谣中发达,而在小俄罗斯歌谣中欠发达。维谢洛夫斯基进而认为,这一文体手法在斯拉夫民间诗歌中的广泛流传为某些概括性见解提供了依据,即在心理上可以把否定模式视为摆脱对比法的一种出路,而对比法的肯定格式则被假定为已经实现了的格式。
最后,维谢洛夫斯基持人民的、民主的比较文艺史观,在“是谁创造了历史,是谁推动了文化的进程,又是谁改变了文学的面貌”这类问题上,维谢洛夫斯基强调人民性。他认为:“应当在这里(历史发展过程中)探寻历史进程的隐秘动因,随着历史考察的物质水平的降低,重心转向了人民生活。如今伟大人物成为群众中所孕育的某一运动的或明或暗的反光,其亮度取决于他们对待这一运动得到表现而定。”[6]维谢洛夫斯基反对卡莱尔和爱默生的“英雄、领袖、人类活动家们的理论”,他认为要以人民的和日常生活的各种色彩为底色进行文学创作,进而,他提出,才华出众的人物之所以创作了杰出的作品,乃是因为他们更有力地接受和反映了他们同时代的历史思想运动,“诗人的内心世界越是丰满,反应越是细腻,那么旧的形式便越是充满了活力”[7]。从人民性出发,维谢洛夫斯基从史诗开始回溯无名氏、佚名、普通人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尤其试图证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伟大作家,例如在彼特拉克、塞万提斯、但丁、莎士比亚和他们的同时代人之间,他们的同时代人并不总是充当画蛇添足、为伟大人物的宝座当垫脚石的可怜角色,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恰恰相反,“近年来这种充当主要角色的背景的地位显著地提升了,不仅衬托伟大人物,而且解释他,并在很大程度上自身由他来解释”[8]。刘宁曾经指出:“文学的民族性、人民性不仅成为俄国批评理论界从各个不同角度和层面不断进行探讨和阐释的一个内涵丰富的基本概念,而且成为评价文学作品的审美文化价值的基本尺度。”[9]我们必须知道,这种批评方法的源头之一便是维谢洛夫斯基在历史诗学中倡导的。
总之,维谢洛夫斯基博学非凡、视野开阔、无与伦比的创作积极性与罕见的理论概括才华,使他成为欧洲和俄国学术界比较文艺学最著名的代表。维谢洛夫斯基在俄罗斯与斯拉夫语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在西欧文学方面的研究都博大精深,他在广泛比较分析和综合研究世界各民族文学和文化史料的基础上,尝试建立科学的总体文学史和历史诗学体系。因此,正如我国维谢洛夫斯基研究专家刘宁先生所评价的那样:“这就为他在广泛比较分析和综合研究东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吸收各文艺学派学说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历史诗学理论体系和总体文学史的任务和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0]
三、俄苏比较文学之滥觞:维谢洛夫斯基学术思想的重要价值
维谢洛夫斯基被视为欧洲和俄国学术界比较文艺学最著名的代表、跨世纪的文化巨人,他的学术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正如日尔蒙斯基所评价的那样:“由于自己的科学眼界,由于自己的知识的极度广博和理论思想的深刻独创性,他大大超过了同时代大多数人,无论俄国的还是外国的。”[1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维谢洛夫斯基的思想宝库形成了某种召唤结构,20世纪以来,包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俄国形式主义诗学学派、巴赫金、弗列登别尔格、普洛普、洛特曼等很多文艺学流派、团体和学者带着自身的治学兴趣和期待视野,从维谢洛夫斯基的学术遗产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营养和启迪。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维谢洛夫斯基的思想价值进行梳理。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维谢洛夫斯基的思想观念突破了欧洲中心论。这种去中心化的多元研究路径,将俄国文学、将东方文学引入西方学术视野,同时也为中世纪文学、民间文学、副文学、无名氏文学、边缘文学研究赋予本体论的意义。维谢洛夫斯基以对欧洲文艺复兴问题的研究起步,但他并未止步于此,他的眼界不断扩展,他对最新科学发现的了解和掌握,使他能够不断吸收更广泛的比较资料。例如,在对诗歌起源问题研究上,维谢洛夫斯基聚焦原始诗歌在起源上的混合型,即有节奏的舞蹈动作同歌曲音乐与语言因素的结合。他认为,未开化民族的诗歌以合唱的、游艺的混合艺术形式出现,他在这部分论述中还提及了中国演员组成的整个剧团都会参加与狩猎生活有关的歌舞哑剧演出;维谢洛夫斯基认为原始诗歌也包括体操游戏、进行曲、劳作时唱的合唱曲和轮唱曲,他顺带谈到了《木兰诗》:“在维吉尔的笔下,涅瑞伊得斯(希腊神话中的海中仙女,即海神涅柔斯的50个女儿。她们的名字表现了宁静而温柔的大海的各种品质)在纺织时唱着关于阿瑞斯和阿芙洛狄忒的爱情故事的歌曲,就像中国纺织工的歌谣讲述某个女战士的英勇事迹一样。”[12]虽然对《木兰诗》有明显的误读,但这也说明,维谢洛夫斯基对古老的东方诗歌的关注。
其次,维谢洛夫斯基的思想突破了“英雄中心说”,将人民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伟大的力量引入到文学史与人类历史。这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思路, 即以一种崭新的方式重审文学史甚至历史,为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后的文艺理论开辟了一条崭新之路;一方面将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重新估量,将他们与时代、与人民群众、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进行全面剖析,从而凸显人民才是历史的动力,也是文化的缔造者。维谢洛夫斯基在从事学术活动之初便宣告:“请告诉我,人民是怎样生活的,我就告诉你,人民是怎样写作的。”[13]早在1895年的一篇日记中,维谢洛夫斯基写道:“社会产生诗人,而不是诗人产生社会;历史提供了艺术活动的内容;孤立地发展是不可思议的。”[14]他强调:“如果把英雄人物作为整个时代的体现者来谈论,就意味着赋予他以巨人卡冈都亚那样超自然的伟岸,忘记了历史思想的丰富多彩,而一个人是无力实现这样的思想的。”[15]他在论文中写道:“诗人诞生了,然而他的诗的材料和情绪是由群体准备了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彼特拉克主义比彼特拉克更早。”[16]这也解释了维谢洛夫斯基在研究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拉伯雷、茹科夫斯基等作家的创作时,也格外关注他们的历史时代的原因。
再次,维谢洛夫斯基的思想避免了影响研究的狭隘性与平行研究的浮泛性,究其实质是对二者之间存在的分歧与对立的一种充满辩证精神的调和。大师不囿于学派。考虑到维谢洛夫斯基从事学术活动的时间远远早于比较文学学界内部的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之争,我们不能不赞赏钦佩维谢洛夫斯基在学术上的洞见。他将文学史引入广阔的历史语境中,以更好地去理解文学规律,从具体个别的文学现象入手,或从修饰语角度切入,或以心理对比法入手,或用情节与母题构建诗学体系,使不同时期、地域、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学在哲学、宗教和诗歌的交互运动中得到更充分的理解,从而“在广阔的历史概括中将高乃衣和莎士比亚调和起来”。维谢洛夫斯基能够以比较的视角从民族或国别的文学现象中揭示规律,从规律中探寻共性,从共性中发现个性,从个性中寻找差异,达到对文学与文化规律性与差异性的认识。例如,维谢洛夫斯基在运用比较法研究文学史上的“重复”现象时,将它们的相似、重复、雷同性,归因于三种情形:第一,神话说,即作品起源于同一个祖先;第二,移植说,即一些作品受到另一些作品的影响,或者受同一类作品的变异形态的影响;第三,自生说,即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在历史上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社会模式和心理结果,造就了作品上的相似性。维谢洛夫斯基并未明确提出“影响”或“平行”字眼,但在他看来,这三种学说并不互相排斥,反而可以相互补充,这就为他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灵活而又坚实的方法论。
最后,维谢洛夫斯基的思想体现出一种开放的、高屋建瓴的智慧。他尊崇科学而又不唯科学,推举实证而又不唯实证,他通过“诗意意识及其演变的形式”出发所研究的包括体裁、情节、语言、诗人的作用、灵感等问题,实际上涉及作家、作品、世界、读者等多个角度,它们互为中心,形成多声部,交织成文学—历史的多种空间;他对民间文学、神话传说、古代文学,以及人种学、民俗学、文化史等方面的文献进行挖掘整理、综合考证,实际上揭示出文学文本的开放性,并意味着对边缘文学、副文学、亚文化的高度关注,它们互为主体,形成交响乐,演奏出文学—历史的丰富维度,最终达到对文艺规律进行总结的高度与深度。这些深邃思想的形成,有赖于维谢洛夫斯基对俄国和欧洲神话学派、历史文化学派研究成果的批判吸收。日尔蒙斯基考证:“维谢洛夫斯基在从实证论者那里接受对于19世纪进步社会思想来说是如此有特征的历史发展思想的同时,维谢洛夫斯基善于改善资产阶级实证论和进化论特有的局限性。因而,他激烈反对生物学规律转用于历史过程,反对孔德和博尔克的社会机体理论,反对泰纳的自然条件(种族与气候)影响艺术发展的学说,反对进化论新教徒布吕纳季耶的虚构的达尔文主义。”[17]同时,维谢洛夫斯基的思想也闪烁着天才的独创性。伊斯特林说:“像维谢洛夫斯基这样的天才,几个世纪才会出现一个,并且在通常情况下直接的继承者是不可能有的。他的意义还不仅仅在此。他竭力证明的思想和方法,使周围的研究者深受其益。不仅仅影响着这些学者们,同时为研究者们指出了一条今后探求学术宝藏的道路。继续沿着伟大天才的道路前进,意味着确定了他在这一科学发展中的意义,他为这一科学奉献了自己的一生。”[18]
总之,正如苏联科学院院士弗费希仕马辽夫所说:“我们经常运用现成的思想和原理,有时甚至完全不了解或者忘记了这些思想和原理都源自维谢洛夫斯基。”“我们都是维谢洛夫斯基的学生或是他的学生的学生。”[19]维谢洛夫斯基的学生日尔蒙斯基从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立场出发,强调维谢洛夫斯基是“将俄国研究置于国际文化和文学交流的中心,将它引出民族隔绝状态的最早者之一”[20]。实际上,正如维谢洛夫斯基是一位比较学者但不仅仅属于比较文学界一样,他表达思想也不仅仅是为了将俄国研究引出民族隔绝状态,而是要构建科学的世界文学史的宏伟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