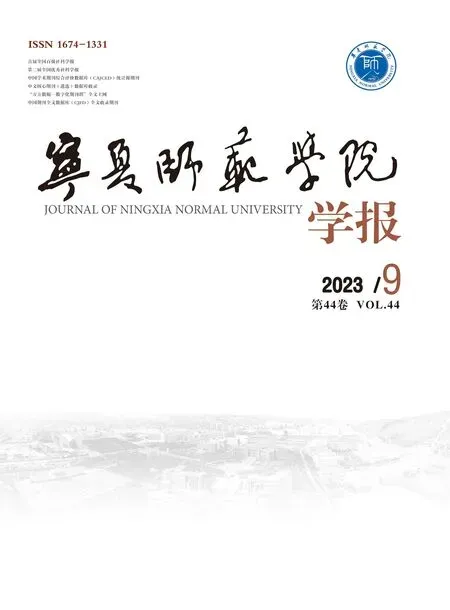城市化视域中女性心理和情感的伦理观照
——谈计虹的小说创作
李生滨,吴佳丽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计虹近年来以小说为主的文学创作引起人们的关注。自2018年发表《老苟的狗事》以来,接连推出了两部小说集,第一部《刚需房》收录了《老苟的狗事》《日子像流水》《浮世清欢》《码头》《折腾》《沙发客》等13篇小说;第二部《半街香》收录了《变脸》《煎炒烹炸》《苏菲的小酒馆》《小嫂子》《空集》《身无分文》《阁楼男女》等12篇小说。总览并细读,能够发现,计虹小说写作的真正力量是她对身边奔波于城市生活的人们“心心念念的牵挂”[1]。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时光沉淀过往的庸常,计虹敏感地体察时代变动中人们承受的种种艰难,悲悯女性情感和心理的负重,自觉地用文字刻画了城市化生活里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
一、持守传统而本分的女性形象
相较于乡村的同质与单一,城市滋生更纷繁的人生样态。与大部分耕耘乡土牧歌的西部作家不同,计虹以自己生活的西北城市银川为坐标,寻找小说题材和人物谱系,开辟了自己的叙事领域。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本经济和家国一体模式中,劳动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主力是男性,自然形成了基于男权伦理的专制思想和体制。女性成年后的职责是相夫教子,家庭有着“显而易见的性别针对性和性别专制意味”[2]。在家庭日常生活和话语权力的支配下,“三纲五常”的要求决定了女性“贤妻良母”的从属地位。正因封建伦理和家庭专制,女性在某种意义上亦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从古代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到现代小说《白鹿原》,文学书写的集体无意识深刻揭示了这一点。而计虹笔下新世纪书写北方小城同样如实呈现:《浮世清欢》中的高子健奶奶因迟迟没有生出儿子被人非议、被家人责难;《我们的岸》中的芳姐也因没有孩子被家人议论、被同事取笑。在城市生活中,乡土伦理思想依然在影响人们的家庭观念,如《浮世清欢》中高子健母亲解构的是肖梅的虚幻和悲剧,《四季如春》中李妈妈生活虚妄的镜中参照是徐太的假面和寂寥。高子健母亲是家庭主妇,靠高子健父亲一人的工资维持捉襟见肘的家庭生活。持守传统而本分的李妈妈则完全失去了活着的尊严和生存的保障。与徐太精致保养的身材相比,生养了几个孩子的李妈妈身材早已走样,更不要说照顾老伴和儿孙辈的辛苦和劳累了。然而当她让老伴和儿子帮她缴三万五千元的养老费时,自己的丈夫和儿女竟然都不愿意。如此境域下,李妈妈又因过度辛劳突发脑梗,半身瘫痪。这是当下许多城镇家庭中比较普遍的伦理矛盾和人性悲剧。
的确,计虹擅长在家庭矛盾和人情伦理的比照中揭示女性的生存困境。如《日子像流水》里林晓芬“不惑之年”选择了杜穆伟并小心呵护婚姻围城却一地鸡毛。生活的反讽在于林、杜夫妇领养李想的儿子无意中完成了杜家老太太要孙子的传宗大事。又如《折腾》讲述了三位女同学不同的人生状况,苏芳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我”守着工作在等待着命中注定的人出现,而“活着,就得折腾”[3]则是李梅生活与情感浮沉的真实写照。《沙发客》聚焦公务员田文和妻子之间的猜忌,却以温馨的方式化解夫妻感情危机。城乡转换,作家也塑造了向上向善的女性,譬如《小嫂子》中的小嫂子家境贫寒却能吃苦,不仅孝顺公婆,还拿出自己的打工积蓄替丈夫家还债,持守勤劳、善良和顾全家庭等传统美德。同时,她见过世面并能理解他人,不仅设法化解兄弟妯娌之间因拆迁而引发的矛盾,而且目光长远地将两套住房换为营业房,筹划开饭馆做生意。就城市生活的直面和谋划,女性显示出比男性更强的适应能力,原因在于“她们良好的随喜性”[4]。
计虹小说所写的女性人生世相和情感状况,大都陷入家庭伦理关系而矛盾重重,或与丈夫与子女的关系剑拔弩张,或任劳任怨承担家务却无法获得真正的尊重。当然,作家也并未站在单一的女性立场上去架构故事,还试图从客观写实的角度出发,探寻消费时代两性关系发生的异变。譬如《日子像流水》中的杜穆伟、《浮世清欢》中的肖梅以及《空集》中的张志刚对婚姻的不忠,在对两性关系的伦理解构中针砭了人性的乖张和灰暗。在农村向城市的转变过程中,身怀六甲的“小嫂子”突然意外身亡,这依然是工业文明和城市生活的梦魇左右了小说求实的内在指向。简言之,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技术缩短了男女在社会生产上的差距,从家务和生育中解放了女性,促使女性从父权文化的禁锢中挣脱出来。然而城市会重新塑造女性,两性关系依然是女性内在自我和情感伦理的“囚笼”,城市化的悖论使持守传统道德的妇女会失去家庭伦理的空间和尊严。
二、生活困境中心理变异的女性形象
现代文学语境中“女性”是启蒙的发现,也是存在主义哲学的观念。就中国思想现代性的发生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女性”得以凸显并具有了话语力量。但需要明确的是,女性书写与书写女性有着本质的差别。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典型的女性形象都是由男性作家塑造的,如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茅盾笔下的章秋柳、曹禺笔下的繁漪、沈从文笔下的萧萧、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等。男性作家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服务于启蒙反封建的主题,具有历史针对性。也就是说,女性是五四新文学启蒙者整体性反传统的武器,但现实生活中女性的边缘位置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新女性也多是社会合法性的建构,少了内在确定性。199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大多是深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影响的自觉反省,部分知识女性和都市女性有了展示自己内心欲望的叙事张扬。在以张爱玲到王安忆的市民小说的递延嬗变中,池莉和方方也写到了世俗生活里女性的婚姻和情感,但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造成的更普遍的生活困境中心理变异的女性依然没有得到真切的观照。中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当下,女性的情感和家庭困境更加普遍,主要表现在从家庭内部争取女性独立并没有真正完成,“个性解放带来的苦闷和彷徨总是多于喜悦”[5]。也就是说,虽然女性能够感受到社会和家庭地位的不平等,但根深蒂固的伦理思想和男权话语造成的心理情结无法真正打破并消除。
从农业社会走向城市化的过程中,身处生活激流和经受经济压迫的女性,内心也多有变异。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家庭是“扩大了的家庭”[6]。女性嫁入一个家庭,按照丈夫家血缘划分亲疏,形成“扩大了的家庭”。城市化生活改变了熟人社会的道德规约,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少了,以夫妻为核心的家庭格局被强化。但传统家庭观念要退出历史舞台绝非易事,必然伴随着双重的嬗变和撕裂。《变脸》与《空集》深刻地描绘了“扩大了的家庭”关系带给进城夫妻的种种负担和羁绊。《变脸》中罗阳的母亲是教师,父亲是邮电职员。他们也是“从农村考学出来,下半辈子才洗干净两腿泥的人”[7],必然少不了对“扩大了的家庭”的责任担当。在《空集》中,张好的父母自觉地扮演着长兄如父、长姐如母的角色,“就这样成了两个家庭的主心骨”[8]。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为女性提供了独立生存的资本和条件,夫妻关系趋于平等。由此构成现代家庭丈夫与妻子之间权利博弈,而非传统家庭的“夫为妻纲”。女性在自我意识强化的过程中,会自觉地将自己与娘家亲属捆绑在一起,形成夫妻“话语”对峙的家庭新格局。因此,罗阳的父母人前表现得优雅而矜持,回到家中却恶语相向,成了人前人后“变脸”的“阴阳人”[9]。而“空集”是一个数学概念,却成为城市化生活中伦理困境和心理变异的隐喻象征。
出离与回归的选择,使得女性心理在精神自由与家庭伦理之间极易发生异变。原因在于城市虽然为女性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多种渠道,但社会结构并没有因此从根本上改变。也就是说,当下女性的生活处境有所改善,但传统伦理思想和文化心理依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女性的自我判断。即使是有了工作机会的女性,为了家庭和“相夫教子”,部分也会选择退居回归家庭,如《码头》中婆婆设法让小慕回到家庭,以便完成传宗接代的“工作”。《我们的岸》中,姚姐依靠老公调动工作而自愿沉沦家庭,她虽然拿着工资但不自觉地认同了女性以家庭为主的传统伦理。《码头》中小慕与同事告别时所说的一句“我们的终生依靠不是这里,这里再好,我们也是过客”[10],也暗含了叙述者对女性自我实现路径的悲观意识。《长颈鹿躲雨失败》则以妥协和温馨的方式化解了城市生存带给女性的各种压力,方舒的心理得以舒缓和调适却依然没有逃脱家庭伦理的无意识规约。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揭示出家庭中的主妇自我价值的来源,她认为家庭中的主妇自觉地将家庭视作世界的中心,而当她们在家庭中寻不到自我价值时,便会“处于近乎变态的疯狂状态,一种虐待——受虐待狂的状态”[11]。《空集》中的李兰香就是典型的“处于近乎变态的疯狂状态”,她对丈夫同意与前妻合葬这件事怒不可遏。过分执着地在家庭中寻求自我价值,使李兰香心理产生了变异,心理的扭曲又使她的面貌发生了可怖的变形。除此之外,作者也设置了双重的女性心理探测,如《变脸》中罗阳眼中的母亲及《空集》中张好眼中的母亲,日常化情感失衡的心理变异极为典型。这类女性在家庭中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但对家庭的依附心理使她们难以真正冲破家庭的桎梏,甚至通过在家庭琐事中计较得失和同化自己的女儿来证明自我价值。计虹写实向度的追求也造成了家庭内部视角的大量选择,特别是以女儿的代际目光审视母亲,既描绘暗示了女性心理的异变以及生存的恐惧,也深刻触及城市生活中两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情理纠结。
三、走向自我独立的女性形象
上述两类女性形象之外,计虹小说也对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经济向好的城市生活中具有独立精神的现代女性有同情的肯定和塑造。如《经过春天的时候》中洁身自爱的苏芳芳,她在得知男友彭帅调查她开房记录的事情之后,果断分手,维护女性的独立和尊严。这类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中的良好表现,亦说明了现代女性追求自我的精神风采。当然,笔者认为计虹无意识塑造的真正独立的女性当属《折腾》中的李梅,她敢爱敢恨,在城市的生活里冲浪,有失败,有疼痛,却又坚挺地独立生活着。《长颈鹿躲雨失败》中方舒也可以算是比较独立的女性,但被生活的流程和法则塑造成“贤妻良母”了。罗阳、张好等是另一类具有独立精神的女性,她们家族观念相对淡薄,努力脱离原生家庭而独身生活。这是有客观原因的,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实施使家庭内部的人员骤减,家庭结构日趋简单。“中国城市的家庭将只保留下来三种关系,即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祖孙关系。”[12]罗阳、张好都是独生子女,同代之间的横向关系大幅度减少,个人的发展几乎不会受制于宗亲间的依赖。罗阳见证了父母被无休止的家庭琐事挤压变形,对婚姻不由得产生恐惧。张好享受独处的快乐,自由地读书、品茗,虽成了他人眼里的“空集”[13],却有着丰盈的内心世界。二人不婚不育的独身主义行为显然是对传统家庭观念的颠覆。但这种女性追求独立生活遭受的外来压力并不小,作为父母唯一的“孩子”,终究无法逃离社会、女性、家庭和伦理的特别规约。
计虹小说中也刻画了一些可望而不可即的职业女强人形象,如《我们的岸》中的乔安母亲,《两个世界》中的鲁南母亲以及《四季如春》中的徐太等。乔安的母亲与鲁南的母亲看似强大,实则外强中干。乔安的母亲是位财务能手,其雷厉风行的作风在家庭中也一以贯之。而鲁南的母亲是高级会计师,自尊心极强,性格古板且霸道,即使半身瘫痪,也不会在儿子面前显露出自己的柔弱。乔安母亲和鲁南母亲都具有“雄化”的形象特征,“女性雄化”是女性追求独立和自我的一个必然过程,在男权社会话语体系中,女性只有通过模仿男性才能取得话语权。“女性雄化”也是对男权社会标准的内化和认同,这会导致女性身份的缺失以及自我定位的模糊。如乔安母亲对丈夫和子女极强的掌控欲导致她与儿子乔安之间的嫌隙,而在鲁南母亲光鲜亮丽外表下潜藏着丈夫不告而别的隐痛。作家对这类职业女强人的刻画并没有停留在粗线条的勾勒上,而是巧妙地揭示了其内心的真实和孤寂,揭示了女性的另一种“异化”。《四季如春》中的徐太则兼具刚柔之美,这一人物形象无疑最接近叙述者对独立女性的特别想象。不同于当红作家的欲望化凝视,计虹小说女性视角所强调的徐太的身体美是女性对自我性别的真正认同。如果说女性雄化是女性解放的必经之路,那么女性之所以是女性,优雅则是女性更重要的自我肯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财富的占有比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没有收入来源的李妈妈只能依赖家庭而卑微地生存,经济独立的徐太则能追求自己的精致生活。同样,物质也会侵蚀个人的精神世界。在《苏菲的小酒馆》中,沈菲菲在出国学习服装设计,将房子与车库都交于好友苏曼打理。苏曼将车库改造成高档酒馆,采取高格调的经营策略。后来光仔背着苏曼改变了酒馆的经营策略,以便获得更多的利益来支撑沈菲菲在国外的开销。物质财富是个体生存的基础,粗鄙的日常生活侵蚀了苏曼的诗意与浪漫,她的人生理想也在城市生存的经济压力下变得支离破碎。在精神向物质、高雅向低俗的转变之间,作家真实而残酷地揭露了城市生活的物质化对个人理想与人际关系的颠覆性改变。
四、消费时代的两性关系与家庭矛盾
计虹小说对于生存困境的探索并不止于女性,并非站在单一的女性立场上去架构故事,而是采用多重内视角观照城市生活、两性关系和家庭矛盾。
首先,如《身无分文》叙事视角在丈夫刘飞龙与妻子李晓红之间切换——叙述视角的变化实现了对中年夫妻的双重聚焦,由此更加真实客观地呈现出年轻男、女深陷经济窘困的生存现状。而在《浮世清欢》中,高子健与妻子肖梅原生家庭带来的生活习惯的差异,在消费主义的现实语境中自然被放大。这种生活深层的幽暗力量,许多身处其中的人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包括计虹在自己求实的写作中,也没有充分意识到消费主义观念在严重侵蚀人们的日常情感和心理状态。在传统的大家庭和农本宗社生活中夫妻之间必然会保持一定的伦理空间,而现代城市化的生活会直接撕裂人性的本真和丑陋。计虹从切入夫妻关系和家庭空间的叙事视角,更加真实地揭示当下普通人两性关系的种种危机和病象。如何才能达到两性和谐?作家在《两个世界》中借鲁南已故女友之口似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让自己快乐的不是占有他,而是每时每刻都能享有他。”[14]但鲁南及其母亲的情感故事本身就是一个掏空细节真实的想象。当然,作家也会以温馨的方式化解夫妻间的矛盾与误会,如《沙发客》中田文与妻子的相互谅解,《日子像流水》中杜穆伟与林晓芬最终的默契,《长颈鹿躲雨失败》中方舒似乎认命的妥协,等等。“我们还能温习一下我们人类曾经有过的无比美好、无比温馨、让人带着感伤去怀念的神圣婚姻。”[15]总之,计虹并没有刻意强调女性的立场和女性的悲剧,而是在贴近生活的写实描绘中也体现了浓浓的世俗情怀,以及普通人对正义和亲情的悲悯坚守。
其次,作家将个人、家庭与群体放置在消费主义的现实语境之中,探究他们在家庭与职场中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并跳脱出了女性私语化写作,转向社会公共叙事。“文学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下面三方面的问题: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16]文学与社会密不可分,作家计虹对消费社会语境中两性关系的刻画沟通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这既真实地记录了当今城市男女的生存现状,也体现了作家对消费时代的社会反思。消费时代两性关系大多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物质资料的占有率往往成为男女之间结合的先决条件。如《刚需房》中,林俊与女友在上海生活,由于女友意外怀孕,两人加快了结婚的步伐,但女友的母亲坚持结婚的前提是在上海有房。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让·波德里亚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消费真相:“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物品/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17]即大众消费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面子需求的符号价值。在城市化过程中,房子作为人居住的使用价值是次要的,而更多体现个人在城市的身份和地位。中国人“大都市地主心理”[18]既是土地情缘的现代性转化也是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所以,林俊的父母虽然无法支撑高额的房价,但将县城里的房子卖掉凑齐了“刚需房”的首付。同样,《码头》中原本抵触生育的小慕却因婆婆奖励的貂皮大衣而喜悦地默认了再生一个的事实。不可否认的是,貂皮大衣并不具备太大的实用价值,但它作为物质符号,却能成为被尊重的女性地位的显证,自然也满足了消费时代一个女性极为虚荣的心理期许。
在消费时代的社会生活中,人的欲望被放大和肯定。计虹几近写实的小说中,城市生活里婚姻契约的责任守护不堪一击,如前所述,《我们的岸》中芳姐的老公酒后乱性,《日子像流水》中的杜穆伟爱上好友的妻子,《浮世清欢》中的肖梅与高中时期的班长旧情复燃,《空集》中的张志刚出轨单位的实习生……两性伦理在消费主义的冲击下不再是内在自我约束的规则。当然,在消费时代物欲横流的生活里,作家也难能可贵地探寻呵护“古典式”爱情。如《煎炒烹炸》中的佟峰虽然一直想要孩子,但他并没有因为妻子丧失了生育能力而横生怨言,而是掩藏自己内心的渴望,守护夫妻之情。如《两个世界》中鲁南的女友多年前意外去世,他却坚定地守望心中所爱,还买了双坑的墓地,期望与女友在另一个世界重聚。《阁楼男女》里,学生时代喜欢的女孩意外离世后,步天放弃了北京的高校,选择女孩曾向往的南方城市,以此心求与女孩共存。不同于短暂、浓烈的“快餐式”爱情,“古典式”爱情展现出传统两性伦理的古朴与纯真,它代表了最普遍的爱情期许,超越了现代都市功利化的情爱观念。对两性伦理遭遇城市化困境的探寻既是作家对欲望化的两性关系的抗拒,也是一种建构现代和谐家庭和两性平等关系的文学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作品对城市中两性关系的探究融入了作家本人的日常经验和生活感受。“艺术的生活方式代表作家与现实的想象性关系;消费的生活方式则体现了作家与现实的关系。”[19]也就是说,从小说文本的叙述人称和叙事结构,我们可以窥见作家的现实立场。如《影子》中“我”的两任女友小丽与小蓝对两性关系的看法截然不同:小丽认为爱情是两性结合的原因,所以,小丽对待男友“我”温柔体贴,将真心都交付于“我”;而对小蓝而言,利益大于爱情,所以,为了创办律师事务所,她会刻意对“我”示好,利用“我”帮她疏通关系。但小说并未展现出对前者的同情以及对后者的批判,小蓝律师事务所兴盛起来的结局也间接说明了作家的现实立场。虽然作家想挣脱消费主义的桎梏,又不自觉地在消费的镜像下自我认同,写作被现实生活同化,这也许就是作品过于温和、批判性不够的原因。但这也恰恰说明了小说忠实于生活或作家心怀悲悯的包容性。
五、结语
相较于2019年结集的《刚需房》中作品的碎片式记述,2022年出版的《半街香》中的作品叙述比较沉稳,多了故事人物的选择和情节的洗练。可以说,计虹的小说大多通过描写女性在家庭和职场砥砺前行的生存现状,真实呈现了自己亲历的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人们的心灵挣扎,还有女性的隐忍和伟大。上述的城市化语境中三种女性的心理和情感状况并不是截然分明的存在,而是相互映照和相互补充的流动不居。作者自己认为:“集子里的作品在我看来,是小说是故事,也是记录。”[20]也可以说,20多篇小说通过城市化视域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真实地再现了世间百态和人情冷暖,还原“生活感与当下感”[21],也对女性为主的两性情感空间多了理性的审视和观照。虽然从小说叙事的琐碎和随意的穿插可以看出作家对叙事技巧运用还不够娴熟,却能超脱宏大叙事,立足于个体的人,透过城市化生活的繁复表象,烛照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内心的真实、人性的灰暗和沉沦,从而形成自己的叙事特色和文学坐标。此外,作家在文本书写中会无意识地受到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但并没有用这一价值观主导人物的命运走向,而是乐观地透视城市化生活里中国人对情义和伦理的特别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