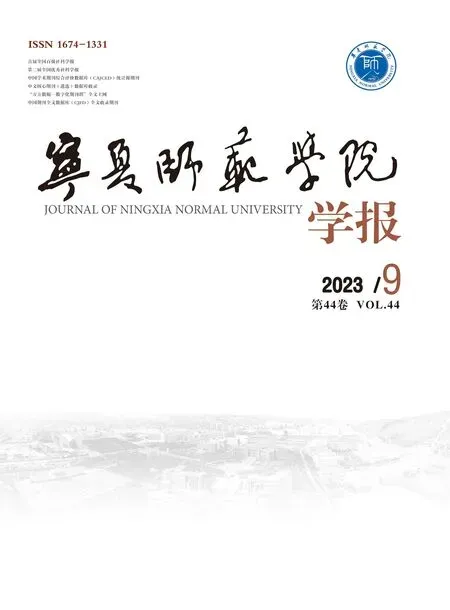空间·群像·物事:《化骨绵掌》中小城书写的三个面向
赵永辉,罗立桂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宁夏女作家马金莲写作初期根植于西海固地区的乡土文化,以简约委婉的叙事风格和宽厚悲悯的写作情怀折射出乡村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与悲欢境遇。在2021年出版的小说集《化骨绵掌》中,马金莲的目光从乡土记忆投向城乡变迁背景下的小城生活,以充满个性的散文化叙事凸显出小城空间复杂的日常景观,并通过小城人物群像的典型塑造,呈现他们在社会、家庭与婚姻中的生活困境与精神困境。作家在小说中精心构造物象与事象,展现出日常生活诗学的审美内涵,反映了小城生活的多重向度。马金莲对小城生活的文学书写,呈现出日常生活的繁杂现实与个体伤痛的生命诉求,寄寓了求真向善的人生态度。马金莲注重小城日常生活本身的重要价值,她延续以往有距离地观照乡村日常的写作经验,更加理性地审视当代城乡变迁下的城镇生活。《化骨绵掌》中的9篇小说皆以城乡变迁背景下的人和事为描写对象,在西北小城的文学书写中体现了作者对于日常生活细节的敏锐捕捉与精准观察,她以文学的形式在乡土与城镇、传统与现代、记忆与现实之间构筑起小城生活,显示出马金莲小说创作的新变。她以更加成熟而内敛的笔触深入生活,从人的生存权利出发来寻求人的生命自由路线。
一、小城空间:文化记忆的情感载体
《化骨绵掌》中的小城介于现代文明的都市与传统文明的乡村之间,具有过渡阶段的特殊性质。马金莲对小城这一特殊空间里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乃至自然文化的描写”[1],准确地挖掘出在时间与空间交织下的小城多面形象。马金莲作为由乡村进入都市生活的作家,在《化骨绵掌》中塑造出一座处于新旧变化之间的小城,带有深刻主体性经验的同时,安静沉稳地构建着小城空间,以及生活在小城空间中的众多个体。面对熙熙攘攘的小城,马金莲在看似平和淡然的写作态度背后呼之欲出的是对于小城空间现状的深刻反思,带有浓厚的文化隐喻意味,以文学这种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形式来观照小城世界,记录着与个体同行的历史。
在《化骨绵掌》中,马金莲营造出一个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扩张的西北小城形象。在乡村到都市的变迁之中,小城作为一个调和的中间环节扮演着特殊的地理角色。马金莲在小城空间的建构之中,并未事无巨细地去刻画小城的物质空间,而是在众多日常事件之中还原出一个复杂的小城。《榆碑》中豪华的太阳花园建造在以前荒凉贫瘠的盐碱地上,拥有全城最高的房价,在新城区的规划中繁华而新潮。在主人公老董看来,自己曾经熟悉的地方却变得陌生起来,他在无所适从的环境中变得落寞,昔日贫苦的大滩地村变成如今的高档小区,周围也矗立起了许多高楼大厦和商家店铺,以全新的形象迈向都市现代生活。《公交车》中对于公交车站牌的描写代表性地展现了小城交通生活的巨大转变,以前简陋的站牌变成现在的座椅、站顶及巨大玻璃宣传栏,规范乘车秩序后解决了之前嘈杂混乱的状态。而在《绝境》中,因为城市的疯狂扩张,人们在等待拆迁的房屋里拥挤聚居,所以生活环境显得脏乱、无序而嘈杂。小城狭窄的空间拥有着高级小区、平房区及郊区,苏李在山坡上俯瞰小城时感受到个体身在其中的渺小,将小城中的路比作“迷宫”和“棋盘”,小城变得弯曲和复杂,而生活其中的人显得更加无助。作者以不同小说中的“高档小区”“公交车”及“城乡接合部”等具体空间聚合起一座处在急剧变迁中混乱浮华的小城,在有限的小城空间里充斥着众多个体的生存欲望。
在小城空间形象构建之外,作者也以小说人物的空间记忆与身份认同展开对小城空间行为的文化呈现。小城空间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场域,在变化之中会产生新旧空间的深刻记忆以及自身应对的文化态度。《榆碑》中的老榆树是大滩地村最年老的树,在时间的流逝中占据着自身应有的空间,见证着大滩地村今非昔比、物是人非的历史进程,最终却被泼硫酸并惨死在小区主管手中,被制作成带有文化意味的“榆碑”,放置在小区之中。老董之所以对老榆树怀有特殊感情,是因为老榆树作为大滩地村唯一的物证,它承载了无数人的往昔生活和文化记忆。可以说,以老董为代表的原住居民与老榆树的结局殊途同归。他们从这片土地的主人转变为寄居者,对于自身身份的困惑,让其在对新建造的豪华小区生活与自身所处的底层卑微现实中形成巨大的落差,最后沦落为小城的漂泊者。《公交车》中的苏苏在感慨乘坐公交车的过往经历中寄予了自身深刻空间记忆的体验,在她搬家的过程中,是最后一次乘坐公交车,以宣布对于过往人生的告别。作者一针见血地借苏苏的想法指出公交车是一个缩小的社会,从公交车的变化亦可窥见一座城市和时代的发展。苏苏在公交车的设施、乘客的穿戴、人们的言谈举止及周围空间的变化中深切感受到自身的生命如同所生活的小城一样,处在无限延展而直面未来的空间之中。马金莲擅长在平淡克制的叙事之中深入剖析人物的心灵,精确动人而富有笔力地显示出小人物在小城空间转化之间的现实境遇与微妙心灵,他们在小城过往与现实空间产生的荣辱记忆令人信服而感叹。
马金莲在小城空间书写之中暗含了对于小城发展的现状反思与个体生命的意义探询。她在乡村生活中培养的深切的乡土情感在其《碎媳妇》《长河》《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绣鸳鸯》等作品中发挥到极致。而由乡入城后,她对于小城生活的旁观和考量发生很大转变,由排斥拒绝到介入现场,再到理性反思。一方面,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只会更加迅猛,并且势不可当,马金莲真实地写出了小城的进步与发展;另一方面,马金莲将重心投放在城乡变迁中的现状与个体生活质量上。以老董为代表的底层人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茫然、胆怯、失落与无助的心境尽显其中,而小城郊区每一寸空间都被完全利用,人们处在拥挤、狭窄及肮脏的生活环境中努力生存,“密密麻麻的院落和房屋,像需要取暖一样挤得很紧很紧,真让人担心那些房子里居住的生命,人类,人类豢养的宠物,是怎么生活,怎么呼吸的,会不会每呼吸一口,都是艰难的”[2]。城市在乡村的尸骸上扩张,个体的生活质量面临严重的挑战,反映出作者对于小城空间内人的生活的持续关注与深度忧虑。马金莲与沈从文在乡土与都市的互构书写之中颇有契合之处,皆是将乡村与都市视为二元对立的关系,让乡村质朴美好的诗意世界与城市丑陋萎靡的病态文明形成鲜明对比,以此达到对城市生活现状的批判,但“城市化所带来的乡村人与乡村空间本身的变化,归根结底是人性的异化,城市化时代的日常生活,也是一种异化的人生图像”[3]。因此,马金莲执着地在小城空间变化内寄托自身对于小城发展现状的独特看法,并呼吁提升个人生活质量。
马金莲的小城空间异于大都市与农村,特殊的生产方式决定小城特殊空间的产生,它并不只是现实地理上的客观空间,亦是在生存空间、身份认同与文化性格等方面的社会历史文化空间,而最终指向生活在这一空间中的人。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写道:“城即人,只有在文学发现了‘人’的地方,才会有‘城’的饱满充盈。”[4]马金莲对于《化骨绵掌》中小城空间的构建,融入了自身复杂的情感体验。她追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时代步伐,在日常生活的纷繁事件中构造出小城空间生活的全新面貌,将众多个体的生存权利作为重心,来寻求个体生命的非凡意义。马金莲在个性化叙事背后,充分展现了这座西北小城裸露的生活现状,反思小城发展之下人的生活困境与精神向度。《化骨绵掌》集中于表现小城日常生活,以个体经验再现审美意义上的艺术生活,在力求反映城镇的变化与深描个人的灵魂中“重构人类在身与心、人与物上的统一性”[5]。
二、小城人物:悲悯情怀的群像塑造
马金莲在《化骨绵掌》中塑造出典型的小城人物群像,展现出他们在庸常而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的各色故事,以此描摹世界与人生。人们的日常态度即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同时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因而作者塑造出小城日常生活之中不同性别、年龄、职业与社会阶层的人物,通过小事来展现他们的悲欢离合。小说中既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保安,也有相亲的女教师与已婚的家庭女性,更有退休了的老人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作者在对他们不同人生的呈现之中把不可言传和交流的事情推向极致。虽然“日常生活就像瓦格纳的歌剧,错综复杂、深不可测、晦涩难懂”[6],但是作者用心呈现这出丰盈的人生,进而显示出生命深刻的困感。生活的现代性问题不仅要从社会经济结构来把握,也要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马金莲正是在芸芸众生的描绘之中映照出人生的多重境况与终极意义。
首先,《化骨绵掌》中展现了以老董、大个子及缸子等为代表的底层人物的困苦命运。《榆碑》中的老董原本是大滩地村的农民,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耕作的土地,最终成为小区保安,表现出对于曾经赖以生存的地方的百般留恋,与老愉树的惺惺相惜之情。作者有意将老榆树与老董写成互相依存的关系。老董在奋力保护榆树的同时也是在捍卫自身与大滩地村的尊严,他虽身处底层,被人欺辱仍保持倔强宽厚的品格,但在无能为力保护榆树而悔恨、懊恼与无助时,使这个人物充满悲壮色彩。老榆树被制成“榆碑”后,老董的职业生涯也就此结束,他最终以自己的生命奔向榆碑的底座,在生命的破碎中安葬了失去灵魂的榆树与自己。以老安、老刘、老谭等为代表的老人在小城残酷的现实面前最终迫于生计忍辱负重,而老董的命运在孤立无援中也随之葬身于繁华的小区之中。《拐角》中居住在农村的缸子与父亲大个子相依为命,从小遭受同伴的孤立与侮辱,每次在父亲的哭泣相劝下去城市寻找另安新家的母亲讨要生活费,在最后一次找母亲的过程中发现母亲已另有孩子,积攒许久的厌恶、悲愤与委屈的复杂情绪令他崩溃。在小说的结尾,缸子提着母亲的鞋子跑出房子,往父子约定的拐角处奔去。缸子自小缺乏母亲的关怀与呵护,他内心渴望母爱,但是现实中无法实现,只能拿着象征“母亲”的鞋子,来缓解心中的委屈与不甘。父亲大个子虽然身体残疾,却深爱缸子,坚强地生活。作为孩童的缸子遭遇了现实诸多不公,在城市拐角处的父亲并未等来他们家庭生活的“拐角”,而缸子在无法承受生命之痛中面对的将是更加无助和悲哀的人生现实。马金莲在诸多难以用社会准则衡量的事件之中呈现出人物自身的矛盾与痛苦,潜入生活最深处抚慰那些受到创伤的心灵。
其次,《化骨绵掌》中联结不同小说中的苏姓女子形成一组小城女性群像。马金莲将苏昔、苏苏、苏李、苏于与苏序这一组苏姓女子自身的隐忍爱欲诉诸小城生活之中,她们在社会、家庭与婚姻困境中奋力挣扎,最后清醒过来作出选择。作者以悲悯的目光注视着女性内在精神世界的困顿,以细腻精微、流畅自然的叙事风格深入当代都市女性内心深处,揭示她们幽微困苦而不断觉醒的精神世界。小说中突出女性自身作为母亲与妻子的双重身份,她们在社会、家庭与婚姻当中受到种种规训与压制,在看似和谐而稳定的日常生活中却面临着巨大困境。《化骨绵掌》中的苏昔与《公交车》中的苏苏二人的家庭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苏昔为去参加同学聚会,在下班之后赶忙回家做饭,在面对儿子教育上的不同分歧,以及丈夫老王对苏昔事无巨细的掌控,使苏昔压抑而沉闷。苏昔怀着曾经的同学情谊去参加同学聚会的愿望被丈夫看似同意实则拒绝的态度彻底打断,她辛苦为家庭付出的背后却早已丧失了自我,在被家庭捆绑的阴影之下失去了一个女人的权利。苏昔最终觉醒,选择与丈夫离婚,迎来了自己的新生活。而苏苏愿意被丈夫王建设“统治”,习惯在丈夫规定的生活框架里程序化生活,尽管被影响和限制自由也无所谓。在外人看似恩爱和谐的家庭生活下,两人实际的感情生活出现了裂痕,而苏苏也怀藏着留恋给她停车的公交司机的秘密。苏昔和苏苏皆是处于外表和谐相处的家庭之中,但是不同性情造就她们在自我身份认同过程中的不同选择,苏昔做了出走的“娜拉”迎来新生,而苏苏则依旧沉溺于丈夫为她编造的特定空间内看似自由地生活。《绝境》中抓奸的苏李胆小、温和又怯懦。一个不会捉奸的女人,却奔走在捉奸的路上,社会飞速进步的节奏,锤炼出她与时代相匹配的精明。苏李面对丈夫的出轨感到无能为力,在人生的绝境之中无法脱离,成为当下社会某些家庭婚姻的真实写照。《良家妇女》中,苏于因女儿生病在医院陪伴,与一个中年男人的相处之中而重新回味自己的人生,在病房碰见符合自己曾经期许的男人之后,唤醒了她心底曾经的梦想。但是清醒而克制的苏于并未有任何行动,“她为这样的坚强庆幸,同时也有苦涩。所有被赞美的坚硬外衣下,谁又仔细摩挲过层层褶皱掩盖的独自愈合的伤痕”[7]。马金莲深入个体精神世界反省女性成长经验,表现出赤诚而热忱的女性关怀意识,在自我确认的空间内书写女性内心隐秘的情感与欲望、成长的疼痛与忧伤。
最后,《化骨绵掌》展现了以马圆、老黑及老白等亲朋友邻之间的日常生活交往,借此贬斥小城日常生活中的丑恶事端与不良现象。小说《众筹》以马圆为同学虎丽丽的父亲在网络平台众筹捐款事件为核心,牵引起马圆伴随这个事件所产生的一系列行为动作和心理活动,借此揭示现代社会中人际交往的自私冷漠与薄凉无奈的现实情状。马圆为人热情善良,内心体贴细腻,她考虑到虎丽丽的妹妹虎梅花与自己是少年好友,加之虎家的经济状况不佳,便生恻隐之心,前后捐款一千元,而且动员自己的兄弟姐妹捐款,努力帮助虎家姐妹。但是马圆真诚的善意最终被现实的冷漠所消灭,虎家姐妹并未对她表示任何的感谢,一切都好像是在感动自己,她成为可悲的受骗者,幸而最终醒悟并牢记教训。而《蒜》中的老黑与老白互为邻居,老黑夫妻因回老家给他送来一坛腌蒜并请他帮忙看护自己的房子。而老黑因租客小刘的吵嚷严重影响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两家人因租客事件而疏离,老黑夫妇最后又重返自己家时,见家中脏乱才知道一切原委,而另一坛子蒜原封不动却早已变臭。小说以送一坛蒜开始,以打开另一坛蒜结束,勾勒出老白老黑二人之间因租客而生分的纷争与疏远事件,批评日常生活中的不良行为。日常生活“就是一日复一日的、普普通通的、个体享有的‘平日生活’”[8],因此作者才能入木三分地对人际关系及邻里友谊极尽刻画。马金莲以细致入微的人情事态为中心,在细碎而微妙的小事之中塑造出合乎现实的日常人物,借此拥抱友爱而真诚的人际关系。
马金莲基于日常生活体验,以平等淡然的姿态体察小城人物的生活,在小城生活的世俗中深描出各类人物。小城人物在现实的生活中不断流逝的不仅是年岁与容貌,更是精神世界的萎靡与庸碌。马金莲在看似隐忍而内敛的人物塑造之中,重点突出人物的心理活动,饱满的个体形象包裹着温厚的生命力,同时也是作者探索世界和人生的重要窗口。她在塑造的小城人物群像之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中年家庭女性。作家充分挖掘小城生活中个体的状态与困境,对于人物成长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展现出马金莲对于日常生活现实世界的整体把握与认知。作家以精妙的手笔展现出小城中的芸芸众生,建立起精神内省的人生书写。
三、小城物事:超越现实的审美呈现
小城生活包罗万象、纷繁复杂,马金莲以审美视角将日常生活纳入小说之中,“现实作为一个整体,也愈益被我们视为一种美学的建构”[9]。马金莲在小说《化骨绵掌》中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塑造日常物象与事象,构成内在心灵与外化事物的统一。马金莲凝望那些在时代与社会发生巨大转变中的人,展现他们的日常生存与生命体悟,将个体庸常而烦恼的处境、沉默而曲折的心事以一种深婉精丽的美学特质呈现出来。作者将看似平常的物象与事象赋予特殊的文化意味,以日常审美映照并超越现实生活,将细微、琐碎的物品与事件作为生活纪念,使得人与物的羁绊愈加紧密。马金莲精心塑造典型意象来强化对于现实感性生活的刻画和表现,来彰显生活内部难以用理性逻辑思维来衡量的含混审美质感。
如何准确而有深度地书写小城生活是一个难题,因为日常生活处处充满矛盾与悖论。小城生活虽然看似普通,却又有其超脱之处,马金莲用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内涵丰富的物象塑造描绘出多层次的小城日常生活画卷。在《化骨绵掌》中,苏昔因为丈夫的长久压制而未能如愿去参加同学聚会,丈夫老王不让她去时,她心中的念头像一锅就要烧滚的水里忽然冒上来的活鱼;在厨房做饭时,看到面片下锅亦像无数条鱼在水中翻滚,而窗外的雪也如层层叠叠的白鱼;她给同学说明自己不能去后,在手机上删除信息时文字也如同黑色的小鱼,还有她因年龄增长眼角长的鱼尾纹,这一系列关于“鱼”的物象描写展现出苏昔强烈想要逃离却又无可奈何的生活处境,家庭和婚姻给她带来隐形的压抑,和睦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地位不均衡的长久压迫。苏昔正如一条清醒却又无法脱离痛苦的鱼,永远被禁锢在家庭这个“大鱼缸”之内。《良家妇女》中,苏于女儿因病住在医院,同一病房的另一个住院的男孩总是在玩手机,苏于劝男孩的奶奶少让孩子看手机,否则对眼睛会有严重的影响,但是奶奶劝不住自己的孙子,任由他拿着手机不放手。作者在此以“手机”这个物象,一方面折射出当下儿童过度使用电子设备而产生的不良现象,另一方面也批判家长教育的缺失与不足。男孩缺乏父母的关爱与呵护,奶奶溺爱并纵容孙子养成不好的生活习惯,引发出一系列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家庭教育问题。在小说《蒜》中,作者借老白的视角对于老黑老婆腌的蒜进行详细描写,老白在品尝蒜的过程中回忆母亲做的蒜,议论老黑老婆的为人,自己也开始腌蒜,最终在自家腌蒜的失败中产生对于不同家庭生活与夫妻关系的深刻感悟。“蒜”这个物象贯彻小说全篇,巧妙牵引出老黑夫妻、老白夫妻及租住老黑房屋的青年夫妻等人,并以老黑自家剩存的一坛腐臭的腌蒜结尾。“蒜”既见证着老黑和老白两家人的可贵情谊,也映射出不良租客的丑恶心理,又蕴含着老白的亲情回忆,寻常事件的背后却拥有着多重内涵。作家在百味杂陈的日常伦理与人际关系的书写中蕴含着生老病死的悲喜常态。马金莲在丰富的物象描写背后,显示出她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挖掘与精确深化,“深入到生活内部,发现密布在肌理层次下的更为细小琐碎的器具”[10],在俗世的细微之处展现别样的生活美学。
同样,马金莲也选取事象来建构小说,通过事件的发生传达出文学对于日常生活所应汲取的美学经验,在审美层面上认识平凡个体与琐碎事件所拥有的重要意义。《听众》中的苏序离婚后去中学当教师,另一个男老师为她积极安排相亲,在“相亲”这个事象之中完整呈现了苏序的情感变化历程。在与各色男人相亲过程中,有人看重苏序的教师身份而方便教育子女,有人将苏序视为生育工具,有人瞒哄苏序骗吃骗喝,有人嫌弃苏序的姿容装扮,从来没有人以真正平等而真诚的态度寻找一起生活的妻子。苏序在平庸的小城生活中不断浮沉,自身的生活条件和孤僻疏离的性格造成她在感情事业上的坎坷不平,最终发现真正值得相亲的人在自己身边,与帮助呵护自己的才子走到了一起。小说《众筹》以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众筹”为事象。马圆参与了虎丽丽和虎梅花两姐妹前后众筹捐款的全过程,热心的物质帮助最后只剩下自己气馁而懊恼的心情。马圆在“众筹”事件中既是一位帮凶,也是一位受害者,她不辞劳苦地积极向周围人宣传转发,别人或多或少的捐款也是她努力的结果。但被众筹欺骗的背后,也有人性的冷漠与自私。马圆的一番好心终究成为黑色幽默的笑话,在虎家父亲出院以后,姐妹俩开心热闹的背后没有丝毫对她表示感谢和回报。“众筹”这一事件具有典型代表性,代表了以马圆为代表的热心人在难以言说的复杂心理背后产生的人际信任危机,反映了当下某些利用别人善意的人的丑恶嘴脸。《绝境》中的苏李三番两次前往抓奸,但是她并没有如读者所希望的闯入宾馆里现场大吵大闹的情节,诸如苏李这样的中年知识女性在时间的辗转与生活的摧残中形成隐忍、妥协而静默的性情,始终没有勇气去撕开现实的残忍事实。她在捉奸的来回中遇到了另一个男人,使她与丈夫离婚,但她却始终被束缚在这个生活迷局之中,并未得到自己想要的理想生活,而是在现实家庭泥淖中周而复始,继续自己的矛盾人生。“抓奸”这一带有戏谑和无奈意味的事象背后,映照出苏李本人苍白、无助而孤寂的内心世界。作者以事象为纽带,通过展现小城生活中人际现象,进而渴望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充实人的生命深度,使每个人的生命变得丰沛。马金莲将“每日观察记录的素材聚集在一起,组合成了这样一个意象,在这个意象中,每日的生活中的诸片断逐渐形成了有意义的关联”[11],而这些有意义的关联连缀起了整个世界与人生。
马金莲在《化骨绵掌》中展现的小城物事,即是借助文学的审美功能与认识功能来参与日常生活的质询与改造。在小城日常生活之中,“人和世界保持着统一性,这是一个有人参与其中的,保持着目的、意义和价值的世界”[12],人在这个世界中认识并建构个体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作者通过《化骨绵掌》中设置的物象与事象,一方面复原了小城生活的本真面目,另一方面通过日常生活审美化,赋予小说中小城生活的审美意蕴。马金莲在意象的选择与塑造中奋力向小城生活内部深掘日常人事,以恰如其分的形象隐喻人物自身的性格特征,打破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界限,以审美的目光呈现小城生活。作者从最真实而矛盾的困境出发来阐发主体深刻的生命体验,使纷繁的小城生活向多方面进行生发延展。
四、结语
马金莲在西北小城的书写中,小城日常生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既是诗学在创造性层面上对于日常生活的重新激活和审美呈现,也是丰富复杂且永不枯竭的日常生活对于文学发展的坚强支撑”[13]。在文学与小城生活形成紧密关系中,小说真正揭示出人性的微妙复杂与生活的庞杂广博。马金莲以个人沉稳而独特的文学叙事构筑起当代西北小城中的日常生活。在小城空间的文化记忆写作之中,展现出真实而自然的小城生活状态。她以小城生活的人物作为重点刻画对象,潜沉日常生活之中揭示小城人物在社会、家庭与感情中的微妙状态,从而传达出对于各色人物复杂命运的人文关怀。作者以审美视角展开的物象与事象的典型意象形塑,使其小城生活书写富有审美意味,展现出小城生活内部鲜活而幽微的生命景观。马金莲恪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一种适合女性身份并熔铸主体经验的散文化叙事展示小城世界的广度与生命的深度,捕捉小城世界中繁杂个体独有的生命镜像,在自我与他人、生命与时代之间达成微妙平衡,进而展现人生的多重价值,反映生命的鲜活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