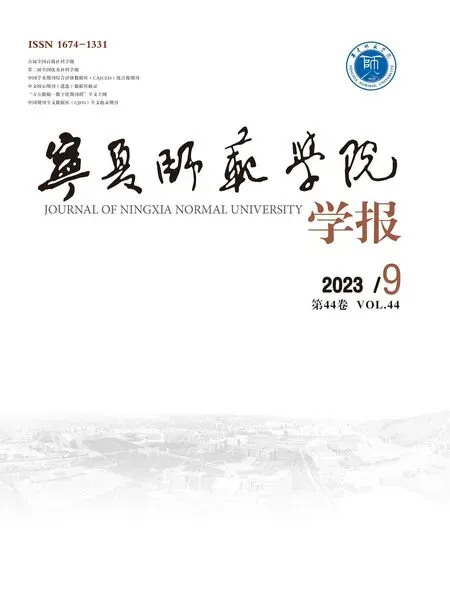海原大地震灾害研究的历史考察与未来之思
程玄皓
(1.宁夏大学 民族与历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2.宁夏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宁夏 固原 756000 )
1920年12月16日,发生于当时中国甘肃省海原县(现今隶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的8.5级特大地震,造成了重大人员损伤和物质损失。海原大地震是我国20世纪以来破坏性最大与伤亡人数最多的自然地震灾害,当地震灾害发生后,由于震度之高,损害之重,震惊世界,引起世人瞩目,史称“寰球大地震”。此次地震自发生以来,就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学者们对此孜孜不倦的学术探究。如今,距离地震发生已逾百年,百年以来相关学术研究持续不断,成果颇丰。回溯梳理与总结评价过去之研究,不仅有利于廓清已有关于海原大地震灾害研究的学术路线图,而且有利于澄明海原大地震灾害研究的进思路径,以期未来之思。
一、海原大地震灾害发生后初期社会实地调查及其价值
有关海原大地震灾害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对海原大地震灾害的“在场性”实地调查与感性的社会观察。但由于当时北洋政府政权凋敝、交通阻隔及信息闭塞等客观因素,直至1921年3月上旬,方有国际饥饿救济协会的霍尔(J.W.Hall)、克劳斯(U.Close)等人开始进入地震灾区考察,对地震灾情进行了初步实地调查,并于1922年在美国《地理杂志》上发表了《在山走动的地方》,对地震灾情和地震滑坡做了描述,并附有地震灾害照片,为后来研究者认识与分析海原大地震灾害提供了珍贵直观的一手资料。[1]
尔后,1921年4月15日,北洋政府组织了由翁文灏、王烈、谢家荣等人组成的科考团队前往灾区分工协作开展地震灾害实地调查。除对灾情、地震原因、地震特点、防灾减灾等进行调查总结外,科考人员还率先利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此次大地震的频度、烈度、余震、震中等地质详情做了科学的分析与研究。[2]翁文灏详细分析了此次地震共造成246004人的死亡,其中海原、固原、靖远、隆德、通渭、会宁、静宁七县死亡人数最多,均在1万人以上,而海原县死亡人数最多,为73030人。[3]这一惊人的死亡数字背后是由于黄土高原地区地震活动频繁,地质结构不稳定,窑洞建筑往往建立在山坡上,一旦地震发生,土窑坍塌,造成人员大量伤亡。[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人们需要采取更加科学的建筑方式和建筑理念,加强地震灾害的预防和治理,提高人们的防灾意识和自救能力。[5]
另外,1921年6月23日,王烈在上海《晨报》上发表了《调查甘肃地震报告》一文,对地震灾害发生的地质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冲积层土质松散、缺乏黏性等是导致地震发生的主要地质原因,当地震发生时土块容易震落,导致建筑物倒塌和人员伤亡。同时,该地区山脊“每多甚峻”,加之土质风化疏松,丛集建造于山脊之上的土窑一震即倒,伤亡众多。[6]这是因为山脊上的土窑土属于脆性土,当地震发生时,由于土窑的结构和强度不足,容易倒塌,导致人员伤亡。与此类似的,1922年谢家荣又单独发表了《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此报告中认为地质与地形是影响该地区地震灾害的重要因素。在地震发生时,由于该地区地质构造脆弱,导致地下岩层的突然断裂,进而引发地表剧烈震动。[7]
总之,以上这些关于海原大地震发生后初期的社会调查和观察,为后来海原大地震灾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和研究基础,同时也开创了中国地震灾害科学研究的历史先河。
二、自然科学领域下海原大地震灾害研究多维度考察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海原大地震灾害的持续性科学分析
首先,1958年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组织专家对海原大地震地表破裂带和断裂带等展开研究。[8]这些研究为地震预警和抗震减灾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也为认知地震灾害的形成特征和机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中郭增建、阚荣举、李玉龙、康哲明等专家学者对于民用建筑抗震性能的评估,极震区位置的确定以及海原断裂带左旋走滑特征的实地查明,具有重要的意义。[9]以此为基,1980年出版了《一九二〇年海原大地震》一书,对此前海原大地震科考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理论层面的提升与总结。[10]
其次,20世纪80年代,随着“3S”技术(1)“3S”指遥感技术(Remote Sensing,简称RS)、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和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简称 GPS)3种技术的有机结合。和大比例尺航片判读的引进,以及14C测年法、遗传算法、考古、大地电磁探测、释光测年、卫星影像识别等方法的多元应用,海原大地震自然科学领域的调查研究工作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尤其在关于海原大地震形成机理、震害特征、诱发的地质灾害、预测预防等方面有了大量且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1]其中包括获得了大量地震形变数据和图片信息,撰写了数篇研究报告,确定了断裂带左旋水平位移量,发现了地震断层多次形变数据和古地震现象,完成了海原活动断裂带1∶50000大比例尺地质图,以及对海原断裂带的结构、形成、发展、演化进行了再研究。[12]1990年国家地震局地震研究所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局在对此前调查报告成果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出版了《海原活动断裂带》[13]一书,此成果在1992年11月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最后,21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关于海原大地震极震区及其周边地质灾害情况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化。2003年,宁夏地质环境监测总站开展了“海原县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项目,旨在对海原大地震及其地质灾害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和分析。[14]2004年,袁丽侠在宁夏海原县、西吉县等地对地震滑坡进行了调查,通过实地观察、数据采集和分析,发现了地震诱发黄土滑坡的耦合机制,以此提出了预防和治理地震诱发黄土滑坡的建议,为当地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15]2006年,宁夏地质调查院组织专家对地震遗迹进行了针对性考察,涉及地质、地貌、水文、气象、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16]总之,21世纪以来围绕海原大地震开展的一系列地质灾害调查研究,不仅为海原大地震极震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地质灾害提供了重要的预防建议与治理措施,也为该地区地震灾害研究与地质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对于科学认知地震灾害发生的原因、特点、规律及其科学有效地制定地震灾害应对措施,开展地震救援与重建工作提供了重要的镜鉴价值。
(二)对海原大地震灾害成因溯源的科学探讨
地震灾害形成的成因是地震学领域关注的重心与焦点,因为对地震灾害成因的科学分析与研究,不仅有利于科学解析地震灾害发生的内在规律和机理,也可以为预防和应对地震灾害提供科学依据。海原县及其周边地区地处青藏高原、鄂尔多斯、阿拉善三个块体交接部位,在三个块体的相对运动下,使得该地区的地质构造复杂,地质活动频繁,地震频发,海原大地震便是这一系列复杂地质活动的结果。[17]加之地质冲积层土质松散,缺乏黏性,一旦遭遇强震,便很容易导致灾难的发生。[18]陈家超等认为,从板块构造来看海原县及其周边地域承受着来自“南北结合带”和“北祁连复活古俯冲带”的挤压,再加上自身垂直作用力,从而引发了强震。[19]这些围绕海原断层活动的观点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支持,认为海原大地震的发生是由于地球内部的挤压和摩擦所导致的。然而,向光中认为此次地震的发生与海原断层无关,而是与地球内部的NS向和EW向深度构造有关,指出这种构造与地球自转和自身分层不均等有关,进而“制约了软流层物质的活动及其所引起的大地热流沿经、纬向的变化”[20],从而引发了地震灾害。显然,学界对海原大地震的成因目前没有定论,相对存有学术研究争鸣,但已有研究无论是从海原断层方面还是从地球内部复杂构造和运动方面展开的分析,都体现了自然科学界对海原大地震灾害研究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和治学精神,也说明了科学研究地震灾害发生原因的重要性。
(三)对海原大地震灾害特征认知的科学分析
一是从海原大地震灾害孕育特征层面来分析。郭增建等人发现,此次大地震具有明显的来自水平向力和垂直向力的运动,二者共同构成了海原大地震的孕育力源。该地区从1638年发生7级强震直至1920年8.5级特大地震的发生,其间中强地震活动频繁,却未发生破坏性地震,出现了大范围、长时间、大震级的地震活动“空区”的显著特征。此外根据震后震源区60年来没有6级以上地震发生的事实,预估今后一定时期内震源区发生6级以上强震的概率较小。[21]
二是从地震破裂特征层面分析。海原大地震的破裂具有左旋走滑断裂特征,破裂带呈狭长槽形状,“形变现象丰富,构造类型多样,组合形态明显,地貌景观醒目”。[22]闵伟等进一步指出海原大地震灾害是“沿全断裂的破裂事件”[23],因此与其他地震灾害相比,海原大地震破裂能量更高、区域更大、下切更深、滑动速率更高、位移幅度更大。[24]三是从地震造成的滑坡特征层面来看。当地震发生时,地震波由西北向东南方向传播,因此,滑坡往往发生在地震波传播路径的相对方向,呈现出黄土滑坡面积大,并多伴有堰塞湖形成的明显特征。[25]四是从地震破坏性构造特征层面分析。由于此次地震震源深度浅和地震波传播速度快,加之该地区特殊的地质条件,因此地震发生时,引起了严重的地质灾害,如黄土滑坡、地面塌陷破裂等。翁文灏在调查报告中指出此次震害具有死伤惨重、山崩巨大的显著特征。[26]王兰民等人基于对震害分布特征的分析,指出断裂带周边和断裂带东南侧的黄土塬梁区分别是房屋损毁和黄土滑坡的主要震害区,这种分布特征可能受到了“发震断层上盘效应和黄土塬梁地形及其厚覆盖土层放大效应的显著影响”[27]。综上所述,研究者从不同层面对海原大地震的发育特征、破裂特征、滑坡特征、震害特征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深化了海原大地震灾害特征的科学认知。
(四)对海原大地震灾害诱发黄土滑坡的科学认知
黄土滑坡是海原大地震灾害中最为主要的地震地质灾害类型,不仅范围广、规模大,而且破坏性强,给震区人民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损害。科学分析与研究海原大地震黄土滑坡对地震灾害危险性评估和防灾减灾具有积极意义。海原大地震黄土滑坡形成的原因是地震引起的地壳运动,当地震产生的震波到达地壳时,受地形构造、地貌特征、水系分形结果以及黄土动力学特性等影响,导致黄土之间的缝隙变大,黄土开始下滑。[28]袁丽侠认为,黄土液化是诱发海原黄土滑坡的重要因素,黄土液化是指在黄土中由于水分渗透之原因,黄土中孔隙压力消散,形成黄土失稳。当地震灾害发生时,叠加重力诱发黄土体振动,从而导致黄土滑坡的发生。[29]海原大地震灾害过程中的黄土滑坡基本类型包括黄土—红色泥岩双层结构滑坡与黄土滑坡。其中,黄土—红色泥岩双层结构滑坡是较常见的类型,它是由于黄土和泥岩接触面的变形和下滑而形成的;黄土滑坡则是由于黄土上下两层无明显界线,导致黄土垂直层面容易产生滑动而形成的。[30]邓龙胜等对黄土滑坡的破坏类型及其成因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黄土滑坡破坏类型主要有四种:一种是由于黄土的易损性,导致的滑坡体振动软化——剪切破坏;另一种是由于黄土斜坡在地震作用下孔隙压力迅速增加,导致的滑坡体振动液化——流动破坏;还有一种是由于黄土块体在地震的作用下发生块体旋转滚动等,从而导致滑坡体振动崩塌破坏;最后一种是由于黄土结构的破坏所导致的震后蠕变破坏。[31]李为乐等发现,黄土滑坡受高程、坡高、坡度、坡向的影响较大。高程是指滑坡前方的高度,如果高程大于滑坡的下滑极限,滑坡亦将无法发生;坡高是指滑坡的坡度和坡向,如果坡高大于滑坡的下滑坡度,则滑坡将无法发生。[32]综上所述,海原大地震诱发的黄土滑坡研究表明,黄土滑坡的发生与地震活动密切相关。通过研究地震与黄土滑坡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科学认知黄土滑坡灾害,有利于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五)对海原大地震灾害震区预测预警的科学研究
地震预测预防是减少与弱化地震灾害损失的重要措施。目前,关于该地区地震预测和预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是研究者们通过分析地震构造、地质断裂特征等,预测地震的发生概率、时间、地点和震级等。例如,宋方敏等研究发现西华山北缘断裂带8.5级大震重复间隔为417年和428年[33]。刘百篪等研究发现今后一定时期内海原断裂带西段毛毛山—金强河断裂段发生7.7级左右大地震的概率较高[34]。这些研究发现对于加强防灾减灾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冉勇康、邓起东提出了分阶段、分级取值的方法,用于预测地震危险性,认为在海原断裂带,应将地震危险性预测分为多个阶段、多个等级,每个阶段与等级根据地震的构造特征、地质特征等因素,取不同的值来预测地震危险性。[35]三是郭增建等从陕甘宁地区发生≥8级地震的频度、时间间隔等方面分析,指出几十年内该地区有发生大震的可能性,呼吁加强特大地震防灾减灾研究。[36]四是冉洪流的预测备受关注,他分别根据大地震多样性重复特征和古地震资料预测了海原断裂带发生6.7级及以上大地震的概率,认为海原断裂带处于地震活动带上,未来百年发生6.7级以上地震概率为0.035。[37]五是郭星与潘华则认为海原断裂带百年内发生6.8级及以上地震的概率为0.0586。[38]研究者们通过研究地震的破坏性,提出了多种预测预防方法。对于加强特大地震的预报指标[39],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建筑物的抗震能力,提高人们的应急准备,因地制宜开发利用滑坡地貌和进行防灾减灾具有重要意义。[40]
总之,自然科学领域的海原大地震灾害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海原大地震的发生过程和机制及其特征。有利于科学认知和预测地震的发生时间、地点和震级,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预警和救援。
三、人文社会科学视角下海原大地震灾害研究多维度考察
“灾害不仅是一种自然事件,还是一种社会和文化事件。”[41]即是说地震灾害虽然是一种自然灾害,但当地震灾害发生后,又与人类社会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与地震灾害的斗争已然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并在人类社会文化系统中留下烙印。因此,研究海原大地震灾害不仅是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课题,也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课题。与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相比,人文社会科学对海原大地震的研究起步较晚。21世纪以降,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人文社会科学方才逐渐兴起对海原大地震的研究。研究主要聚焦于历史学、文学、民族学、人类学四大学科领域中。具言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历史学领域下的海原大地震灾害历史研究
在历史学研究领域,海原大地震赈灾及其应对策略的探讨,始终备受关注。在若干领域颇有贡献,着重集中在关于灾后赈灾救济、呼吁报道、灾害损伤原因分析及其地震灾害所引起的社会问题等方面的分析。
1.对地震灾害后赈灾救济与应对的历史研究
王长征、彭秀良[42]指出新闻媒体和民间组织在海原大地震抗震救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认为社会媒体不仅提供了及时报道,还积极参与救灾行动,通过宣传和呼吁,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救灾。熊婧娟[43]考察了海原大地震的救济情况,通过对《申报》中的地震灾害报道分析,发现《申报》不仅报道了地震灾害后的灾况,而且从其报道中可看出当时北洋政府面对灾情态度漠然,尚未开展有力的赈灾措施,救灾重任让渡于地方政府和民间慈善捐助。崔艳红[44]研究表明,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媒体在此次抗震救灾中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指出地方政府通过募捐、开仓救济、以工代赈等方式对抗震救灾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媒体对地震灾害的报道,成为外界了解此次灾情的重要通道,也为后人认知与研究海原大地震灾害积累了史学资料。尚季芳指出震后民国传教士身体力行,记录灾情,同时积极投身于抗震救灾过程中,为社会赈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45]此外,他与张丽坤还揭示了民间力量在救灾中的作用,即通过自发行动与相互协作,有力地降低了灾害带来的影响。[46]姜振逵、刘景岚[47]的研究则关注了社会组织在抗震救灾中的作用,指出社会组织力量在海原大地震赈灾中发挥了重要的协调和组织作用,为抗震救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还揭示了社会组织在中国的慈善活动中的转型轨迹,为理解中国近代史上的赈灾应对提供了新的视角。
综述而论,海原大地震赈灾及其应对策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即面对重大灾害,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仅需要民间的救济行动,更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救济。[48]如是,才能更好地应对灾害困境。
2.对地震灾害造成的延伸性社会问题的历史语境分析
海原大地震损失惨重的原因也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除自然科学视域的研究外,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部分学者们基于地震灾害的“社会历史境况”探讨了诸多问题。一是损失惨重的社会历史归因分析。尚季芳、张丽坤认为,之所以海原大地震灾害导致损失惨重,与震后缺乏有力的组织领导息息相关,从而延缓了救灾进程,或因指挥不力致使赈灾工作陷入混乱。另外由于北洋政府救灾态度漠然,加之交通破坏、邮局全毁、灾后疾病蔓延和继发性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了灾区人民的苦难加深和惨重损失。[49]二是人口伤亡与流民饥荒等社会历史问题的分析。张思源在研究中围绕海原大地震灾害中的人口伤亡情况,通过对以往历史资料的汇总和讨论分析,认为海原大地震灾害造成27万人口死亡的数字更符合实际。[50]郑正伟对灾害后社会历史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海原大地震灾害的发生衍生出人为造成的饥荒、流民、匪患等社会历史问题,加深了社会危机,致使天灾向人祸的嬗变。因此,对于地震灾害的研究,不仅要考虑地震灾害本身造成的社会损害,还要考虑在地震灾害发生的历史境况中,所衍化出的社会危机和伴生性灾害。[51]
(二)纪实文学中的海原大地震灾害之历史叙事
文学叙事中呈现的海原大地震灾害,虽因文学化语言表达而“生动丰富”,也能体知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灾害时,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首先,王漫曦的《1920年海原地摇了》是一部较早的关涉海原大地震灾害的纪实文学。通过对震前、震时、震后三个阶段的纪实生动描写,展现了人们面对自然灾害时的真实反应和坚韧不屈的精神。在震前,当地流传着一种预警性的歌谣,人们并未将其与地震灾害联系起来,反映了人们面对潜在自然灾害时的一种无助,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微妙关系,“万物静默时,人自然无知”。随着地震灾害的发生,一切都改变了,即当山走了,地动了,人们突然从日常生活中惊醒,这种变化让人惊愕,也让人感到无尽的恐惧。然而,也就是在灾害的恐惧中,人性的光辉得以展现,互相帮助、互相支持,这种坚韧和勇气让人动容。
震后,火灾、饥荒、匪患带来的二次灾害,使人们的生活再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即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人们依然表现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与艰难的生存环境顽强斗争的精神让人深受触动。[52]王漫曦生动地描绘了人类在灾难中的真实面貌。这部作品不仅是对海原大地震灾害的真实“文学书写”与“历史记忆”,也是对“人性光辉”的颂扬。让我们思考诸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性向善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其次,石舒清的《地动》一书,也是关于海原大地震灾害的纪实性文学书写。石舒清以幸存者的口述史为线索展开叙述,塑造了不同人在共同命运下的生命遭遇与心路历程。这部作品被认为是继王漫曦的《1920年海原地摇了》后,又一部关于海原大地震灾害“非虚构文学作品和个人史文献的写实”[53]相互结合的作品。作为一部以真实历史灾害事件为基础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他通过刻画人们在灾难前的反应、灾难中的挣扎和灾难后的求生历程,深入挖掘了人的内心世界和生命遭遇。作品中叙述的各类主体人物形象各异,不同阶层、地位、职业、身份的人之间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深刻的生命苍凉图景。石舒清通过对现实具体的人的生命历程及其命运遭遇的关注,表达了人类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脆弱和无助,以及对生命顽强品质的价值肯定。同时,他也在作品中展示了社会各界主体对这场灾害的真实反应,从而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和思考这场地震灾害。[54]
最后,季栋梁的《海原书》是一部在纪念海原大地震灾害一百周年时创作的作品,仍旧是一部具有历史价值的纪实性文学作品。以海原大地震灾害百年来的历史变迁为主线,描述了幸存者刘鸿儒家族四代人在海原大地上的生存变迁史。在海原大地震发生后的一片废墟上,刘鸿儒家族开始了长达百年的艰苦奋斗,他们从祖父辈开始,不断地努力重建家园,顽强地生活。但是,灾难并没有结束,他们一次次地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难但并不放弃,坚定地在平凡生活中自我超越。作者以刘鸿儒家族的百年生存变迁史为“窗口”,实质是在表达海原地区人民百年艰难生存变迁的缩影,面对各种灾害与困境,从未放弃,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在逆境中“向阳而生”,书写着可歌可泣的生命之歌。总之,《海原书》真实地反映了海原地区人民的百年生存变迁和乡土原色,它让人们更加深刻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和文化之变迁,也让人们更加感受到生命的珍贵和坚韧的力量。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社会学著作。[55]
综上对三部关于海原大地震灾害纪实性文学作品的梳理,具有重要的学术启示价值。即是说,在理性化的学术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的当前,关于这场地震灾害感性表达和具有生命感的书写较少,如“人的情绪、人的感受、人的诉说呼号、人的遭际命运”[56]之表达与书写却是处于“空白之处”。然而,纪实性文学叙事与书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域来记忆和反思这场灾害灾难。诸如苦难的记忆、对逝者的回忆、对家乡的思念及人之内心世界痛苦、挣扎和希望之情绪情感,跃然于纸上,可感可触。
(三)民族学人类学视域下海原大地震灾害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变迁探讨
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较,民族学人类学对海原大地震灾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灾害历史记忆和文化变迁方面。王晓葵对比了海原大地震和唐山大地震,考察了国家权力和地域社会文化对灾害记忆建构的影响,他发现在唐山大地震中,国家权力对灾害记忆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海原大地震中,地域社会文化对灾害记忆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7]这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背景下,主导灾害记忆的主体和建构方式存在差异。温小兴着眼于“震柳”文化遗存的价值,对民众和官方文化记忆建构的差异性问题进行了探究,发现民众主体将灾害记忆“圣神化”,而官方主体将灾害记忆世俗化,这种差异看似对立,实际上都遵循着同样的文化内核,即对震柳顽强生命力的歌颂与崇拜。[58]这表明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灾害记忆的理解和建构方式也存有差异。雷天来则基于“文化记忆”理论,探讨了地方精英、地方政府等不同主体对灾害文化记忆的建构路径,发现地方政府遵循当前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但是这种建构因脱离民间日常生活语境,面临失效的挑战。[59]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海原大地震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对家庭结构、社会秩序、人之心理、人际与族际关系、居住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催生了人们对自然灾害的认识和自我生活方式的转变,即是说人们面对地震灾害,会催生自我调整生产生活方式以满足新环境的要求。[60]总之,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海原大地震灾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化记忆及文化变迁方面,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方式。然而对于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及其震后文化回应方式等现象的探讨,仍然有很大的学术研究空间。
四、推进与深化海原大地震灾害研究的未来之思
综上所述,以往关于海原大地震灾害的研究已经关涉到了三个维度的研究:地震灾害初期的社会实地调查,自然科学领域下的地震灾害成因溯源分析、灾害特征认知、灾害黄土滑坡等科学探究,及其人文社会科学视域下的历史分析、纪实文学叙事书写、民族学人类学层面的灾害文化变迁与历史记忆等主题。这些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从不同层面推进海原大地震灾害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以此为思考的支点,推进海原大地震灾害研究的未来之思,兹以镜鉴,具有如下之径。
(一)关注受灾群体本身差异性的研究
对海原大地震灾害的研究还应关注受灾群体本身及其差异性、复杂性的讨论,探讨不同性别、族群、收入状况和亲属关系的受灾群体在海原大地震灾害中的表现和回应力,以及这些因素对灾后重建进程和资源获取的影响。例如,女性在这场地震灾害中比男性表现出更为脆弱的反应,这可能与其身体条件、社会地位和家庭角色等因素有关。在传统的家庭角色分工下,女性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因此在地震发生时,可能会因为照顾家人而无法迅速逃生。另外还可能因为身体条件上的限制而在地震中遭受到更大的伤害。此外,不同族群和收入状况的群体在灾害中的回应能力和灾后重建进程中获取资源的能力也不同。这些差异可能受政治、经济以及受灾群体的社会地位、文化传统和家庭关系等因素的影响。更多地研究和真实地反映海原大地震灾害受灾群体差异性、复杂性,或许是我们在今后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二)拓展海原大地震灾害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范围
关于海原大地震灾害的研究,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赈灾、文化记忆、文化变迁等方面,还需要拓展研究的主题和范围。首先,关注文化回应研究。以海原大地震震区为田野考察重点,可以基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视域,分析海原大地震灾害中的文化回应方式。通过这种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灾害文化与人之主体、社会生活、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性。其次,关注口述史研究。口述史是记录历史的一种重要方式。尽管地震灾害造成的苦难是相似的,但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却总是不一样的。这其中有个体和社会层面的原因。我们需要搜寻亲历过这场灾难或隔代人的口述史,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和应对,挖掘地震灾害与人的社会性之间的关联。再次,关注灾害记忆研究。尤其从集体记忆以及创伤记忆的角度有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和意义。最后,关注文学叙事研究。从理论角度出发,探究文学叙事中如何记忆和书写这场灾难,挖掘记忆和书写灾害的空间。
(三)走向多学科视角下的海原大地震灾害研究
除了自然科学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对海原大地震灾害的研究也极为重要。目前,历史学、文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学科,都为我们提供全新的视角和理解。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应拓展多学科视角下的海原大地震灾害研究。首先,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海原大地震灾害。防灾教育是灾害预防和应对的重要一环,而如何传承海原大地震灾害记忆,更是教育学需要思考的问题。如不能仅仅将这场地震灾害的记忆停留在形式化的纪念和知识化的防灾教育中,应在自助教育、共助教育以及情感共鸣中与受灾的主体即人构筑联结,共同走向应对未来的全新挑战。其次,海原大地震遗迹的开发和保护,是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地震遗迹的开发和保护,进而更好地保护历史,让后人更好地了解历史,让历史教育更为多元、丰富。这需要我们思考,如何将海原大地震遗迹与当地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最后,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海原大地震灾害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也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地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人类如何适应和应对这些影响等需进一步思考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