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孩子在写诗
焦晶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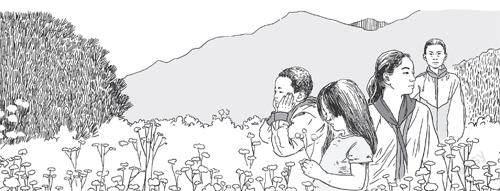
“诗歌很重要”
对于一群贵州深山里的孩子们来说,写诗和摘苞谷一样日常。
诗意可以诞生在任何时刻。一次放学后,他们小心地绕过庄稼和烤烟苗,踩在嘎吱作响的松果和杉木叶上。那时正值傍晚,远山连绵,炊烟飘进云里。原本在人群中内向、瘦弱的男孩袁方顺,漫不经心地吟起剛作的诗:“金黄的夕阳/天空无处藏/眉眼形如弓/坐着剥莲蓬。”他解释:“云朵是太阳的眉眼。”
他是班上最“高产”的“小诗人”,3年里用掉了10个诗歌本。他的母亲和父亲离婚已经两年,他不愿再提起对妈妈的想念。但他还是会读自己写的那首诗:“以前你是春天的光彩/可你离开了我/我在柳树上贴着‘妈妈我想你了/流水像你的头发随风飘扬/鹅卵石也有你的微笑。”
他所在班级叫“六年级”,71名学生刚刚好挤满教室。3年前,语文老师龙正富开始在班上教诗歌课。从此,每天都会有人把新写的诗悄悄递给他。
如果只从学习上看,他们并不算优秀:4个乡镇的35个班中,他们成绩并不理想,语文和数学的平均分在60分左右浮动。有老师形容授课像“牵着蜗牛散步”。
他们脸上总带着泥土和“高原红”,课间玩耍时看起来无忧无虑,但他们会写沉甸甸的诗,有关死亡、离别和思念。班里有39名学生没有父母陪伴,他们的父母或离异,或去世,或全部出去打工。
在这里,诗可能随时诞生,也可能随时消亡:有的孩子的诗歌本被爷爷点烟时烧了;有的孩子本子掉在地上忘记捡,被同学扫进了垃圾桶;曾经有场暴风雨吹开老旧的木门,把贴在图书室后墙的诗全打湿。但他们总说“诗歌很重要”,就连一名坐在最后一排、经常上课睡觉的女孩,也说自己“懂诗”,会给其他人提建议。“那些写出来自己真实心情的(诗),我觉得才是好的。”
他们说,诗歌是光,是相机,是日记本,是好朋友。
“诗歌就像一个游戏”
课堂上,龙正富很少输出观点,只是不停发问,“你看到了什么?”“你喜欢他的表达吗?”“所以别人喜不喜欢重要吗?”
40分钟过去,PPT还停留在第一页的图画上。不停有学生站起来分享自己的观察。
下课后,孩子们追着给他看诗。龙正富坐在厚厚一沓本子旁,轻轻读出声,拍照,然后慎重地写上批语。即使有些句子平平无奇,他也会画上波浪线,在旁边点上感叹号。评语大多无关好坏,多是一些他对诗里情感的回应。
有孩子写:“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房里/使我每天都露出了/牙。”他批:“老师也开心。”有孩子写:“我走在路上/发现/我的影子一直/悄悄跟着我。”他写:“当我们停下脚步,留心周围,也就开始关注自己,关注生命。”
开始上诗歌课前,龙正富没读过什么诗。接触诗歌课源于一次偶然。2019年,公益组织“是光”和黔西市教育局合作,给当地的乡村教师提供诗歌课程和培训。申请表发下来,老师们“都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龙正富边想边填,直到晚上才填完。
之前,老师们要用尺子才能让这个班安静。龙正富没用过。他让孩子们读泰戈尔、纪伯伦、希尔弗斯坦、谷川俊太郎、金子美玲,在早读、课间或者是午休时。他不要求齐读,而是让他们七嘴八舌地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味道”。
龙正富班上的孩子们语文基础不好,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创作。碰上不会写的字,有的孩子口述、让同学“代笔”,有的则用手机语音转文字,再自己抄下来。
“诗歌就像一个好玩的游戏。”一位男生说。他是班上最调皮的男生之一,成绩不好,但劳动的时候很积极,主动拿着铲子去厕所掏粪坑,“每个人不是十全十美,也不是一无是处”。
“是光”组织会定期遴选孩子们的诗,颁发奖品。这个男生的诗没得过奖,他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是看到一只陌生的小狗被撞死后写的。“当我的小狗出车祸时/我会用我的手/轻轻地/抱起来/当我看见它的身体时/我的泪眼/瞬间掉在我的心上。”
“在诗里,我可以自由地表达”
龙正富说,如果没有诗歌,他很难获得孩子们的信任。之前很多孩子的情绪会在某一天突然变化,比如,突然不说话,或者在课上掉眼泪。他问孩子为什么,孩子什么也不说。
3年前他开始上诗歌课,他带着孩子们读诗、写诗。一学期结束,孩子们写出的只是“流水账”,但他耐心地给每首诗拍照、写评语,之后的2年里换了3部手机,每部手机里都有几千首诗歌。
慢慢地,孩子们放下了防备。一个孩子原来总是上课睡觉,拿刀片割手臂,从不和龙正富说话。一天深夜,他突然给龙正富发信息,说自己反锁了房门,想从楼上跳下去。
后来龙正富了解到,他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不到一岁母亲就离开了家,父亲正准备再婚。那段时间母亲想见他,却又托人说,见面时要装作不认识她,要喊她“阿姨”,因为她的新家庭不知道她有过孩子。“我30多岁,如果遇到这种事我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你让一个孩子去承担,怎么可能呢?”龙正富说。
林怡是班上的第二名,从3岁起,她就习惯了送别外出打工的父母。她高高瘦瘦,话少,每天回家,爷爷奶奶干农活还没回来,她老练地烧水、煮饭,水烧开,作业也做完了。
一个人的时候,她花很多时间发呆。当太阳落在山尖尖上,她就站在猪圈旁的葡萄藤下,望着山,直到太阳的影子从山上消失。“我会想山那边的人,看太阳会不会很近很近?还是说他们面前也有座山,太阳其实是从那座山落下去的?”
想要看懂她很难。她有两个诗歌本,一个写记录心情的诗,一个写给老师看的诗。在那个没人看过的本子上,她把孤独和悲伤化为竹子上的雨珠、踩在脚下的泥土。她说,即使是一些看起来快乐的诗,背后也有不开心的“秘密”,“在诗里,我可以自由地表达。”她很满意大家都读不出来,“我也不想他们知道。”
“这是诗歌独有的力量”
龙正富希望能通过诗歌,唤醒孩子对生活的感知力,“回到生活中”。渐渐地,孩子们的表达发生了变化,“在慢慢接近他们所看到的、真实的东西”。
班上有位“问题”女生,原来总喜欢恶狠狠地瞪人,和母亲吵架、离家出走。开始写诗后,有次她和母亲去种苞谷,看到母亲忙碌的手,有密密麻麻的褶皱,指甲剪得很短。于是她写:“我跟妈妈去玉米地了/我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妈妈的那双手。”
“我们教孩子写诗是为了培养心灵,不是为了培养诗人。”诗人朵渔说,“也许有人说,你写诗又考不上好学校,有什么用?但如果他从写诗里得到的成就感和快乐足够大,他就不会受到外界的伤害。”
龙正富带过很多次六年级,但第一次认真设想他们毕业后的未来,“他们会遇到怎样的人?又会怎样努力生长?”他打算把班里孩子们的诗做成诗集,在毕业晚会那天发给每一个人。
总有学生问龙正富:“如果我以后还写诗,能发给你看吗?”龙正富从不担心,孩子们会不会继续写诗。
班上最“高产”的“小诗人”袁方顺说,成为初中生后,他不想写以前的诗,“要写快乐的诗”。即使现在他包里装着10多分的英语卷子,即使那些崎岖的山路,还将会是他一个人走。
(摘自“冰点周刊”微信公众号,本刊有删节,范李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