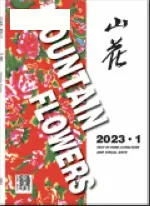北纬30度左右的雪线
凌仕江
米拉日巴的野草
雪野上,到处是花。红的,白的,黄的,蓝的,紫的,密密匝匝,璨若星河。一个穿着草青旧迷彩、头戴青兰尼龙雪帽、鞋子破得露出血斑脚趾的年轻人,不修边幅地漫步在雪野上。他酽黑的面孔,表情麻木得叫不出一朵花的名字。
而那些花朵也锁紧眉头,歪着脑袋,不悲不喜地望着他忧郁的胡子。当一只雪豹悄无声息地涉过雪线,撞见那颗正在闭月含蕊的贝母,花儿们像是一窝蜂接到一个信号,于是纷纷收敛微笑,不再为一个忧郁的年轻人绽放花心。
冰山消融的水,流经野草遍地的山岡、河流,漫过干枯的苔与石,上面走来一个满头白发的牧人。那沾天吻地的牧歌,在上空萦绕盘旋,划破冰凌,直冲云霄,迅即落入波浪起伏的宽广山林。牧人停在黑牦牛踩过的雪窝里,掏出鼻烟壶,望着雪原之上那个忧郁的年轻人,不紧不慢地把鼻烟壶放在鼻尖上,呼呼地吸了又吸。烟雾如一面破碎的镜子,照不清年轻人黑乎乎的脸,更照不见一颗孤独光明的心。只见那年轻人狂乱的步伐,在原地踩不出骄傲的足迹;他节外生枝的眼神,冲牧人口出狂言,指指点点。
牧人什么也不说,也不再看他,只抬头眯缝着眼,掩嘴哂笑,然后直视着大地上清幽蔓延的野草,一声叹气。
太阳照常升起。
他的神情在帐篷前愈加忧郁。
这个年轻人叫苏兰基·帕南特。他从小生性孤僻,因为家贫如洗,十五岁就进入地空部队,靠职业兵身份养活家人。苦涩的回忆里,找不到多少快乐的细节来支撑他的孤独。来到这座蓝色帐篷之前,秘密训练营里的人,从未听他谈论故乡维沙卡帕特南乡村。白天,他一个人无所事事地徘徊于岩石地带,看四脚蛇睁着眼睛做白日梦,看雪癞在枯黄的草地,立起身向他作揖。可他懒得蹲下身,真诚地握一握雪癞的手。连一个回应动物的微笑,他也没有。其实,他是在找寻人不如动物的生存答案。在异乡的高原之上,他烦闷时总会拾起锋利的玛尼石,朝远处狂乱飞翔的秃鹫猛烈地掷过去。一块接一块地掷过去。可那些秃鹫从不畏惧一个人的攻击。他越是掷秃鹫石头,秃鹫的数量就越是多,那些把像心撕碎了唱出的尖叫声,几乎淹没了他脑海里刚要想起,偏又忘记的事情。他的心早被风雪吹到视野另一端的陌生世界了。
晚上,他则一个人坐在月光铺满的帐篷里,心急火燎地望着天窗外的星河发怵。
毕竟这是他一个人驻防的帐篷,无聊与失落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
有一天,阳光照得白雪瑟瑟发抖的午后,他忽然被一阵温暖柔和,且不失张力的吉他声吸引。这是他来到帐篷的第十天。吉他弹奏的声音,在雪花静止的天空,如棉朵从枝丫飘落,婉转激越的和弦撞击雪峰的声音,经狼牙石漫延到他身边。他欲伸手抓住那激荡人心的和弦,于是迈开步朝音乐的方向快速跑去。那么多花儿追赶他的背影。他像一只四脚蛇,趴在狼牙石上,透过密杂的野草,睁大眼睛——那个怀抱吉他的哨兵,坐在蔚蓝的海子边,微闭双眼,陶醉于太阳和雪沐浴的旋律。
他心跳的节奏失去了规律。原来怀抱吉他的哨兵,竟是他初上高地望远镜中发现的那个哨兵。他虽然会说几句中国话,但他还不知弹吉他的哨兵叫什么名字!他侧过身,把耳朵紧紧贴在狼牙石上,静默地聆听哨兵的歌唱——
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
才能被称为一个男人
一只白鸽要越过多少海水
才能在沙滩上长眠
炮弹在天上要飞多少次
才能被永远禁止
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荡
……
哨兵唱的什么意思,他不大明白,但他已被哨兵歌声深深吸引。他觉得吉他和弦解了他的烦恼。在没有近距离接触弹吉他的哨兵之前,他身边活跃的只有四脚蛇、雪獭、秃鹫,还有一些叫不上名的动物。那时,他一度承认自己神经陷入麻木与死亡的状态。哨兵的歌声,好比让他参加了一场偶像的演唱会。那飞翔的弦丝,穿过他苏醒的心灵,令他回味无穷。直到歌声消失,吉他声戛然而止,他们目视哨兵背影,迟迟不肯离去。
从此,他习惯趴在狼牙石上静静聆听,尽管哨兵并不在场,但他盼望哨兵出现。于是他天天趴在狼牙石上等待,常常换来一身雪花。哨兵怀抱吉他坐过的海子边,除了一丛叶边呈獠牙状的茂盛野草,唯有一只硕大无朋的秃鹫在张望。太阳从东山升起,又从西山落下,吉他伴随的歌声,不再响起。他像秃鹫一样,痴痴地守候着,心里一遍遍回放那熟悉又陌生的旋律,寂寞无聊偷袭他的思绪。他用还没溜顺的口哨,翻卷着舌头,寻找哨兵唱歌的感觉。
海子边的哨兵,在坚固的哨所里,听见他音不顺、腔不圆的口哨,如雪獭一样朝天露出半个头,捂着嘴笑得比秃鹫的尖叫声还要清脆。哨兵将食指与大拇指伸进嘴里,吹了一声响哨,表示回应对方。尽管他们都是哨兵,但他们不可能成为知音。
日子归于无限的寂静。一个哨兵窥视另一个哨兵,成了从帐篷到狼牙石必修的功课。每天如此,守时如滴水穿石。
今天还能听到热血沸腾的吉他和歌声吗?
苏兰基·帕南特见到过那个弹吉他的哨兵,可能就二十三岁的样子,只比他大几岁。哨兵怎么可以把吉他带到哨所来呢?哨兵的领导对他可真好。苏兰基·帕南特既羡慕又自卑,因为自己不会弹吉他,也没有哨兵动听的歌喉。苏兰基·帕南特这辈子休想成为哨兵的朋友,他注定无法触摸哨兵的吉他。尽管他们看似离得那么近,之间只有一方狼牙石与一汪小小的海子,他却没有勇气用母语喊出对方的名字。
他和他存在一定的语言障碍,好在音乐无国界!
苏兰基·帕南特第一眼从望远镜里见到那个哨所,心里就产生了巨大疑问。海子边彩色的石头房子,像城堡那样美丽。而自己的帐篷,只是蓝色的帆布,遇到暴风雪,帐篷就像一个移动靶子,在空中摇晃。苏兰基·帕南特猜想他是出于什么原因而来到一个人的哨所。望远镜里的哨兵,有一张干净得看不见胡子的红扑扑的脸,雪白的牙,沙漠迷彩服,背上的枪刺辉映出蓝雪般圣洁的冷光。是犯了错被部队罚到这荒无人烟的云端之上?还是因为哨所冰封四季、雪打霜裹,待遇高出其他部队两倍?苏兰基·帕南特当然属于后者,只有那样,他才能拿到更多的津贴,养活维沙卡帕特南的亲人。
每次窥视,苏兰基·帕南特换来的不过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和一堆思想疯狂生长的石头。无法获悉对面哨所的具体情况,而哨兵淡定的表情,似乎根本没在意苏兰基·帕南特的存在。一度认为自己荒唐无趣的苏兰基·帕南特,常常失眠、惆怅、难过,又感到好笑。每每看到哨兵同太阳一道升起那一面鲜红的国旗,唱起嘹亮的国歌,苏兰基·帕南特就深感自己没有安全感,更没有存在感,于是他拼命想要创造奇迹。因为他是受过奇迹感召的人。那些先于苏兰基·帕南特撤离帐篷而创造奇迹的人,让苏兰基·帕南特深受鼓舞,并且渴望超越他们的奇迹。
苏兰基·帕南特头顶的星辰,犹如天堂里的花朵。无论坐着,躺着,走着,还是站着,他总感觉有一种无限的紧迫压力,如野草在眼中燃烧,像石头压在胸膛般沉重。他很想知道对面的哨兵有没有这样的情绪。此时,天上的星星每一颗都在窥探苏兰基·帕南特的心事。他仰望星空,觉得自己并不是罪人,却有犯罪的负累。他没有得罪星星,也没得罪海子边的哨兵,更没有得罪雪野上猖狂的秃鹫,他究竟得罪了什么?哨所的天空如此稀薄的空气,为何还能滋生他莫名的恨?自从申请来到这个帐篷,苏兰基·帕南特看这世上的一切都不顺眼。尤其是望远镜里的哨兵升旗、唱国歌的仪式带给他的冲击。他绞尽脑汁地想对面的哨兵,是否同他一样心中也有恨?哨兵是否也有他一样无处言说的孤单寂寞?哨兵有妻儿吗?哨兵的母亲是否也在盼着儿子活着回去?哨兵故乡有没有甜甜的玉米糖?
一个人的帐篷度日如年。
无人理睬的生活,苏兰基·帕南特无可选择地把眼前所有事物都假想成石头,他的世界仿佛只剩下石头——包括那个近在咫尺,却一言不发的哨兵。还有草地上的牧人和牦牛,他们都是无情焦灼的石头——木讷的石头,不长眼睛只长翅膀的石头,坐怀不乱的石头,从天而降的石头,子弹穿不透灵魂的石头,枪支扛不起的石头——遍地都是威胁他审美的石头……偶尔有一瓣雪从石头上飘过,夹带着秃鹫魔鬼般的笑声,他眼睛闪过一丝寒光。他用扫描大地的目光,在秃鹫监视的眼睛里,调转着不同维度,却未能捕捉到敌人掠过的痕迹,只发现一只四脚蛇,蠕动丑八怪的身条越过狼牙石,来到他的活动范围。他的反应速度比四脚蛇更快,手上的刺刀哗啦一声,指向四脚蛇的脑袋,血顿时染红了雪。在野外生存的秘密训练营,他早吃过了如此山珍美味。他能以遥遥领先的考核成绩,远涉世上最高的帐篷,不仅枪法和体能都是第一,而且他的野外生存能力历经了吃活蛇、与虎搏斗、同野牦牛厮杀的重重难关,最终让他过关斩将,成了大家瞩目的独守望帐篷人选。他知道身后的将军和士兵,都在等待他的奇迹。他三下五除二剥掉四脚蛇的皮,将它丢进一个空罐头盒,夹在两块石头之间,背着风擦燃火柴。半根柴禾还没燃尽,山珍就去了他胃里。似乎他并不满意这样的美餐,他幻想如果能天天陪着哨兵弹吉他,一起歌唱舞蹈,异乡生活就不会让他变成一块因恨意而滋生麻木的石头。
夕阳的影子,在雪山上来来回回地移动着。苏兰基·帕南特忽然关闭帐篷的天窗,暗自抱起沉重的狼牙石,像一个参加抱石运动的种子选手,三步并作两步,拼尽洪荒之力,一屁股坐地將狼牙石移到让他视线更远的位置。流星在天上看见他流星般闪回帐篷,他打开天窗不停地瞄向海子边的哨所。他不知如此举动意味着什么?他仅仅十七八岁,也想瞒天过海,把对奇迹的渴望,设计得天衣无缝。他的主观意识里,没有一双雪亮的眼睛,可以在这样的夜晚,发现他的妄为。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说月光是贼,他自欺欺人的妄想,以为他比月光更贼。他明知故犯地欺骗了自己,但他永远骗不了月光。如此天下大白,没有月光不知道的秘密,除了月光,谁也糊弄不了月光。
第二天醒来,狼牙石居然在原来的地方,岿然不动。
一夜之间,狼牙石的体积像发酵的面包,增肥了不少。他歪着头看了又看,发现这事有些魔幻。狼牙石像在直视他的不安与骚动。他心底满是石头,可是当他想要再抱起狼牙石,却怎么也发挥不了力量。不听使唤的狼牙石在原来的位置纹丝不动,任凭他怎么用力或变换姿势,它仿佛根深蒂固的一棵大树,牢不可摧。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狼牙石的反作用力,让它居然不长眼地砸在他脚上。他趔趄几步,一屁股栽倒地上,忍不住疼痛地叫出了声。
当苏兰基·帕南特如梦初醒,狼牙石畔忽然站立一个人,是弹吉他的哨兵。他揉揉眼,惊恐地看着对方,但亦有兴奋之光,在眼里不停闪耀,转动。
世间无声胜有声。
两人对视良久,野草听见了他们彼此清晰的呼吸。要不是天上的秃鹫捣乱,两个闪闪发光的青春灵魂,在离天最近的地方,完全可以紧紧拥抱在一起。可哨兵只是将一包家乡的玉米糖,递给苏兰基·帕南特:“新年快乐!”
苏兰基·帕南特怔怔地后退了几步,疑惑着,犹如在梦中。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了新年致辞的声音。
两个陌生又熟悉的哨兵脸上露出了微笑。
“你的吉他和歌声很美。”
苏兰基·帕南特竖起大拇指,几步闪回帐篷寻找糖,可他最终找来的是一袋干果。他递给哨兵:“新年快乐。”
哨兵谢过,转身离去。
苏兰基·帕南特突然失去理智将狼牙石,推向哨兵。哪知不动声色的哨兵,一个反掌将石头推回了原地。
挥动乌儿朵的牧人,站在不远处,嚅动嘴唇,亮出一口白牙:“哦呀,原来石头也会走路呀”。
牦牛竖起耳朵,鼓起眼睛,齐刷刷地望向天边的苏兰基·帕南特。
晶莹的雪花,从不同方向飘来。苏兰基·帕南特耷拉着脖子,为狼牙石怒气冲天。一根根亮晶晶的银绳,如同月亮的鞭子,不偏不斜地抽打在他的身体上。苏兰基·帕南特的脸在发热,心在发烫。
不管白天黑夜,他都在搬石头。
他在梦里搬不完满世界的石头。
即使在梦里,他也在呼唤石头,并期望会听他的使唤。他当然想通过石头赢得奖赏的筹码。他如同西西弗推着狼牙石又上路了。一样的月光,照着一样的他;一样的他,幻化成无数个他。狼牙石离开了老地方,他窃喜自己获取了成功,长久的灰暗和憋闷,终于使他心中,轰地炸开了一股奇迹出现的惊惧。他弹了一下指头,狼牙石离他越来越远,头顶上钻石般的星子,为他闪开一条星光大道。他想呼喊,就像胜利的果实摆在眼前一样地呼喊。他环顾四周,海子边的哨所,此时唯有一粒红豆似的灯火亮着,像天河之上的一盏明灯般安详。他想那个弹吉他的哨兵此刻一定进入了梦乡。他扭动屁股喊叫了一声,星子们都在打量他的表情,他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他用力拍打着沉重冰冷的狼牙石,手背和脚趾在野草的麻醉中,如火烤,似椒辣,血迹在皮肤上如蛇般游走。他呼喊的声音,如同月光捆住的木头。他跳起了欢快的瑜伽舞,借着流星划过的亮光他看见牦牛也在扭动屁股,学他的瑜伽舞。
一排排牦牛整齐有序地站在草地上,屁股和脖子扭得天旋地转。牦牛的舞蹈,顿时让他兴奋不已,但随即他便觉出山呼海啸的声音朝他撵来。牦牛突然变换了方阵,他被狼牙石从山坡上倒撵回来,他怎么也挡不住来势凶猛的石头。不只是那一方石头,而是千军万马般的石头,挡住他的去路,让他无法闪躲。石头在飞,他不再喊叫!他分不清那些石头,是不是牦牛的化身,可眼见为实的牦牛那撼天动地的舞步,让他定下神来。漫天星光下,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必须像弹吉他的哨兵,用沉默的方式,在这里陪日月安顿自己。
他终于喘过一口气,重新认准狼牙石所在的方向。但他失败了!石头居然推向了他理想的反方向。他来不及后悔,天空已经亮了。他的手和脚布满了一道道血痕,除了手脚发痒,他并不觉得疼痛,因为牦牛一直在对他微笑。
天亮了又黑,黑了又亮。他就像一个干渴的黑客,大口大口地吞咽着白雪。忙活了一夜又一夜,他没有水喝。单薄的帐篷囤物已所剩无几,那些被雪獭偷吃残余的干果,此时也成了他嘴里最后的津津有味的东西。唯有吉他哨兵馈赠的那一包玉米糖,散发着家乡的味道,那味道里盛满了一个哨兵对另一个哨兵的祝福。他把玉米糖拿在手上看看,忍不住又放回携行包。他想让家乡的亲人尝尝异乡的味道,可他尚未创造出家乡人们期待的奇迹。
他对自己的不满,只有石头清楚!
此时,几头披着雪衣的牦牛,已逼近他的目光。秃鹫在空中盘旋出几道弧线,一只接一只地落在离他不远的海子边。他双手捡起地上的石子,像甩飞镖,一手朝着牦牛掷去,一手同时指向秃鹫。石子在湖面上荡起涟漪。牧人瞅了秃鹫几眼,并没有吱声,只是缓慢地从怀里掏出一支鹰笛,扭过头背对他,盘腿而坐。那苍凉空灵的笛声,在雪山与河谷之间,起起落落,时缓时急,时长时短。牦牛们纷纷点着头,奔驰在牧人的笛声里。五分钟内,它们便全部集结在牧人周围。
秃鹫也在笛声里嗖嗖地远去。
苏兰基·帕南特踮起脚尖,像失去了一个世界,心中充满极度的痛苦。他飞沙走石般扑向草地,牦牛回头对他微笑,花朵黯然失色,秃鹫纷纷朝他做着鬼脸。他愣在原地,有些垂头丧气,鹰笛声中舞蹈的牦牛,他一头也追不上。他大把大把的心力已被风雪解散。当他向着蓝帐篷的方向折返时,那几片单色的帆布,遭遇了大风的强拆,雪花刺骨,风沙弥漫,他初次明白了个人拥有的力量微乎其微。他高估了自己对这片神奇高原的所有认知和想象。他瘫坐在废墟覆盖的狼牙石上,张望高远的天空,一次次抚摸弹尽粮绝的枪支。当他鼓足力气,朝自己脑袋开枪却无子弹时,哨兵的吉他歌声像针一样刺进了他的耳朵。那是一个人在风雪咆哮中歌唱,也是一群人在歌唱。他被歌声的力量加持,一次次从雪地站起,希望和信念从哨兵的歌声中升起。他出神地趴在狼牙石上定睛地看着海子边的哨所城堡。山下正走来一位穿着崭新迷彩服的哨兵。远远地,他们挥着手,喊着彼此的名字,俩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哨兵将吉他搭在另一个哨兵肩上。
眼看,他们就这样完成了换防交接。
苏兰基·帕南特还是那么单纯地喜欢哨兵的吉他歌声。他要单枪匹马逃脱这废墟,即使山无崖,谷太深,千里迢迢,他也要活着返回他的故乡,那里有他的家和他的妻儿。他在奔跑的雪花中,想象母亲和妻儿闻到玉米糖香的笑脸。可是以他年轻的经历,怎能想到帐篷与哨所的距离,如此温柔又残酷。
“跌秀啦——”(藏语,请过来的意思)。
他放慢脚步,停下来。这样的语言,他或多或少能懂一点。能到高原上的高地创造奇迹的人,不精通三种语言是不行的。
风在吹,雪在飘,鹰笛声在追赶秃鹫的突围。牧人终于站起身,面对海子;残阳从山巅跌落,洒满湖面。野草在疯长,浑身长满了肉眼看不见的绵针般的毛毛。牧人握着鹰笛的手停在空中,无孔不入的野风,穿过牧人凌乱的白发,穿梭在鹰翅骨雕刻的三个音孔中。笛声随风,如浪如云,在空中东飘西荡。牧人转过身对他说——
年轻人,知道这是哪儿吗?
他茫然地看着牧人。
在你没来之前,世界的喜马拉雅,一直就在这儿。牧人指着草地上点头微笑的牦牛,捋着随风扬起的发际。牧人想起曾经这块高地上,有不同语言的人,用酒祭奠青春,为彼此的身体取暖。
“给,年轻人!拿去暖暖身子——”牧人从怀里掏出皮囊温热的青稞酒。
他愣在原地,一只手接过牧人的皮囊,一只手伸向空中,久久未能收回。他很想摸一摸牧人的白胡须。看着牧人若即若离的影子,他认真又缓慢地打开了皮囊盖子——嗯,比家乡的酒更香。他深吸一口气,禁不住仰头将小皮囊里的酒一饮而尽。
牧人又问年轻人,“这一饮而尽的豪爽,你可知甘露酿自哪里?”
见年轻人无动于衷,牧人手指天边的雪山——“孩子,那就是那喜马拉雅呀!”
“牦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可你知道它吃的是谁家的草?”
他更加茫然。
牧人背著手,看着雪地上长长的影子,指着废墟上生长的草儿说,“这不是谁家的草,这是米拉日巴的野草。不信,你伸手去试试。如果你的手完好无损,就当此地你没有来过……”
米拉日巴是谁?他脑海里充满迷惑。这个刻在经书或山岩上的名字,这个神一般存在了几千年的名字,他想了半天,眼睛里全是陌生。他着实搜索不到答案,欲从地上拔出一棵野草,可他止不住心惊肉跳,使出满身力气,那草依然在原地丝毫未损,颜色越发的鲜绿。
他浑身在颤抖。
手心手背痒得生疼,继而肿胀不止。
他尖叫般的呻吟响彻了天空和河谷。
比雪更白的哈达,绕过雪山的脖子,如同所有高高在上的生命,听见圣洁的召唤;不可忽略的青春尊严,在风中日夜飘荡。
不远处,那个把身体捆在石头上站岗的中国哨兵,坚定地目视着远方,雪花落在哨兵平静如水的睫毛上,哨兵满脸坚毅的表情,装满了河山、风月、落日、野花,还有暗夜里一只垂下眼帘锁住它的目标的狼。
切玛咧那古
他正在草地上,追赶一只切玛咧那古(黑蝴蝶)。
我和他相遇时,他仅八岁。旺澹草原,一片连绵金黄,把雪山染得柔媚暖眼。见我横在草地上的影子,他停顿脚步,缓慢地侧过身,抬眼发现我肩上背着的枪,抖动了一下脖子,满眼惶恐。
“金珠玛(解放军),请不要向我开枪,我可不是坏人。”他机灵地辩解道。此刻,我真没心思理睬一个追赶蝴蝶的小男孩,但我强装笑意,淡定地看着他的眼睛,视线被悲伤拉直,锁定在他脸上,算是默认了他的解释。
“你在想什么?金珠玛。”他又问。
“孩子,大人想的事情,你不懂。”我把眼睛移向天边的火烧云,懒得再看他一眼。
“谁说孩子就不懂大人的事呀!金珠玛,你在想死去的战友吗?”
“谁告诉你我战友死了?真是的!”我心情沮丧到了崩溃边缘,双手用力揪住小男孩的羊羔皮衣领。要不是“童言无忌”四个字提前在脑海闪现,我真可能将他高高举起,一拳打倒在地。
“金珠玛,你放开我吧,不是我说的,真不是我说的!”小男孩一边挣扎一边大叫。
忽然,眼前一团黑得发亮的魅影,像是磁力,吮吸着我的睫毛。小男孩翻着白眼,指着它说:“是切玛咧那古。”
“什么?黑蝴蝶告诉你的?你在胡说什么?”
“是切玛咧那古。嬷拉(奶奶)讲,只要看见切玛咧那古飞,就会有不好的事。”
那只切玛咧那古,在我和小男孩的头顶翻飞、盘旋、薄如蝉翼的翅膀,透着圈圈圆圆的斑纹,闪着金属的光芒。“切玛咧那古,我不想再见到你!我和嬷拉,还有阿爸,都不喜欢你,你快快飞走吧!我想金珠玛也不想看到你!”小男孩蹲下身,双手胡乱抓起两把枯草,一股脑地抛向空中,极力阻止它靠近我们。
“你,可是你并没问金珠玛,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切玛咧那古呢?”我看着他的眼睛。
“这,这,噢,噢,金珠玛……”他支支吾吾 ,摸摸脑袋,半天想不出答案的样子,让我很想笑。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他。
“丹增。”他迅即补充道,“我已经八岁了,这里的牧人都叫我丹增尼玛。”
嘿,丹增尼玛,挺有意思的名字。在这苍茫的高原大地上,叫尼玛的人多如草原上的羊群,这个意为“太阳”的称谓,契合了高原人对光明神灵的膜拜,用来作为人名再吉祥不过了。
纳闷的是,我在这里执行任务半年,对丹增尼玛却没一点印象。
至于丹增,其实我一点不陌生,甚至可以说再熟悉不过了,毕竟他和我在哨卡共同驻守了两个多月。当兵的人有句俗话,亲不亲,同年兵。有时,人不得不相信缘分这件事情。我与丹增都是有着十二年兵龄的老兵。因为执行守卡任务,我们从不同单位临时抽调到了旺澹,对于彼此的过往,都是空白。那时,窗外的月光,像一朵白莲花落在哨位上。睡在我上铺的丹增,睁着牦牛般深邃而透亮的大眼睛,望着那朵子夜微蓝的莲花告诉我,藏语涉及的意思可丰富了,隔一座山,或跨一条河,人们讲话都有区别。丹增说长辈给他取的名,寓意着“继承”“发扬”。我难过地想着颈部被刺刀捅破的丹增,却为眼前这个小男孩好听的名字,大声地说道:“丹增尼玛啦,你长得真俊呀!”
他露出雪白的牙,咯咯咯的笑声,被草原的风传得好远。近处的黑毡房,一缕上升的炊烟托起几块熟睡的云朵,宛如圣境。刚刚打完酥油茶的阿佳(大姐)走上草坡,嘹亮的歌声让高高的雪山沉静,让弯弯的小河轻柔,让低头啃草的羊群频频举头张望。
丹增尼玛朝羊群挥挥手:“金珠玛,我得先走了,希望下次还能遇见你。”
望着丹增尼玛小小的背影,我将一块小小的石子,踢飞得老远,可并没有踢走沉沉的心事。心如刀割,血流成河。丹增颈部手指长的伤口,是否会被时间缝合?自从牧人们把他转运下山,是生是死,消息全无。那些未经证实的传言,常常绞杀着我的愧意。事件突发在雪花飘飘的傍晚,要不是丹增挺身冲上去,那道鲜血直流的伤口,就应该落到我的身上。就在那一瞬间,丹增使劲一掌把我攮到身后。他双手叉腰,怒目圆睁,用浑身充满的洪荒之力,对警告无效的闯入者大声呵斥:你们再无理取闹,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睛!丹增上前几步,两脚踹掉闯入者设立的乱石线,谁知对方蜂拥而上,将丹增步步推搡,疯狂扭打起来。见势不妙,我赶紧跑到山口,向近距离的牧人招手疾呼。待我们的人马赶到,丹增已倒在血泊中。
几个星期过去了,保障车辆的到来让人欢喜让人忧,却没有带回丹增。除了驾驶员和一堆物资,只剩一个名叫阎辉的上等兵。他刚下车就开始尖叫和感叹:啊,这旺澹的风和阳光太猛烈了,千万不要把我吹回拉萨呀!
面对第一次上哨卡的阎辉,我常常无话可说。他也是从外单位抽调来的,我们之间相差了十年兵龄。
在太阳掉进雪山深渊的一刹那,繁星迅疾地聚满草原。
阎辉似乎与繁星有得一拼。我想说,天边的星星再多也沒有阎辉话多。比如,雪猪会来哨位上陪我们站岗吗?喜马拉雅迷路的雪人,会不会带我们去见外星人?比如,玛尼石开出的虫草花,会不会长出一双撬动地球的眼睛?面对阎辉无止尽的话唠,我越加沉默地念起丹增。在抵达哨卡之前,我是连队鼎鼎有名的孤独客,除了必须回答他人的问题,十天半月我也不说一句话。不懂我的人越来越多,懂我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哨卡走了一个比我话少的人,却又来了一个比我话多的人。在我眼里,丹增算不上“孤独客”,至少他还掌握独门特技:口哨。大家给丹增的一致好评让我嫉妒。我必须给他差评,其中有一句“逼他说话比逼我说话更痛苦”。丹增的好评如潮,可能任何人都没法取代,人们公认他是“旺澹通”。哨卡人巡逻方圆百里的地方,他简直如数家珍。他口中的那些牧人故事,就像是他家里发生过的一样。哪座帐篷里的酸奶口感最爽,谁家的奶酪吃了还想吃,海拔几千米的山泉最养胃,哪条山谷的杜鹃开得最迷人——这些优势无疑是他开展驻防工作的资本。同这样的人一起执行任务,倍感阳光和幸福同时打在头顶。在必须入乡随俗的旺澹,我暗自把丹增作为随缘而安的精神陪伴。
我给阎辉交代好洗碗和整理内务的事,穿上防寒风衣,独自来到草场察看动静。草地依然枯黄着,只是比昨日的颜色深重了一些;近在咫尺却触摸不到的雪山,散发着一半清冽一半温暖的气息。日光从不同方向射出的剑,撞在数不清的雪线上,多维度的天空呈现出爆炸式的美,在蓝与白的缝隙处,有蛋壳或蛋清,还有一些灰如发丝的紫和血,在时间的天河里晕染,如子宫里的婴儿,游移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生命通道里;又像是被雷电击碎的果皮,在宣纸上落荒奔走,只为连接岁月的蛛丝马迹。而无声无息的,永远是放眼望不尽的蓝,在耀眼的黄与黑的雪絮之间,在高原空白处,大面积的蓝像沉睡的海绵,却一直处于无声流淌的状态,让人半梦半醒,百看不厌。
“哇,又见佛光。”我用数码长镜头,对准天庭里奇妙的画廊,忍不住兴奋。
丹增看我一眼,只顾扭过头偷着乐。偏偏我要问个究竟,他却什么也不说。
后来,我认同了丹增的说法。高原之光,对于生活在高原上的人来讲,无论白天或者黑夜,不管它怎样的绚烂,都不足为奇,因为他们早已看惯了。反之,外来者要一厢情愿地指认那是佛光,也不会有人来刻意反对,毕竟他们还没看够。谦逊的丹增,他解释不好佛光,并不代表他辨识不了酸奶和奶酪的味道。忙里偷闲的时光,他拉着我进入牧民的帐篷尝鲜闻香。牧人与他眉飞色舞交流了些什么,我一概不管不问,只顾津津有味地品尝,一饱口福。时间久了,我当然也能用简单的藏语,叫出那些牧人的名字。
眼下,除了几户转场的牧人,离我们哨卡最近的是边巴大叔。我随意扯根枯草里的青草,衔在嘴里,嚼不完的思绪,难以阻挠丹增影子的兀自突现。从草地上收起盘腿,我站起身向边巴大叔的毡房大步走去。掀开白色布帘的瞬间,眼前的小男孩顿时让我吃了一惊。
“金珠玛,你好!”
很诧异,又疑惑:“怎么会是你,丹增尼玛。”
还没等到他说话,边巴大叔与丹增尼玛对视一眼,抢先道:“哦,他是我的亲戚呢。学校放假,他就来这里了。”
“加通(喝茶),金珠玛。”丹增尼玛双手毕恭毕敬递给我一杯甜茶。我用微笑替代了对这个小男孩礼节的赞赏。
边巴大叔拿给我几块布满了辣椒面的风干牛肉,称所有的羊群都集合好了,马上要去草原上剪羊毛。毡房里只剩下丹增尼玛和我。
我品尝着香喷喷的牛肉干,问丹增尼玛“你不用写作业吗?”
“写,来这里之前,我都写完了。”他俏生生地看着我。
“那你到这里最想做的是什么?放羊?还是去山顶挖虫草?”
“不!”说完,他低着头,有些后悔,连忙加了一句,“我就想追赶切玛咧那古,把它们统统赶走。”
“切玛咧那古聂滴儿普儿定吉(黑蝴蝶在这里飞翔),有什么不好呢?”我心里暗自嘀咕着。
我们走出毡房。一把巨大的水壶,在太阳能灶上冒着滚烫的白汽。草地上,阳光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丹增尼玛咕咕叽叽讲了很多黑蝴蝶的不是,总之那是不祥的飞翔物种,令他有些憎恨。在毡房旁的一个密室里,布面的墙上画满了色彩缤纷的壁画,内容包括雪山、草原、河流、马牛羊、牧马人、藏獒、鹰、雪猪、子弹、虫草、石头,还有金珠玛。我没有赏够这幅巨大的壁画,丹增尼玛就把我拉到一座土雕像面前,小心翼翼地看我的表情。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怎么都觉得兵雕像一个我熟悉的人,不是一般的像,简直是神气活现。
“是你雕刻的?”
“当然是我。”
“壁画也是你作品?”
“嗯,金珠玛,都是我画的。”
“你认识他吗?”我对视着兵雕,就像对视往日的丹增。
丹增尼玛答非所问:“冰块是去山下的冰河里背回来的。”
“这需要多少冰块呀!”我轻轻地抚摸着比我高出半个头的兵雕,那高高的鼻梁,英气逼人的大眼睛,脸上还有两团逼真的“高原红”。我摸了摸他冰凉的手掌,感觉他的眼神像是在和我说话。
“好多次,好多次,究竟去了多少次冰河拿冰,我也不記得了。”
丹增尼玛说的那条冰河,是我和丹增去过的地方。那时,我们每半个月都要去走一趟那条曲曲弯弯的路,为了取冰化水食用,我们相互用背包绳,将体积沉重的冰块,绑在对方背上。来来回回,一趟至少需要一个半钟头。累了的时候,丹增余音绕梁的口哨,便引来蝴蝶一路伴随。再长的路,有了蝴蝶,我们也不觉得枯长。寂寞荒原上,与蝴蝶作伴的人,若再与他人大谈孤独,我觉得不仅是可耻,更是罪过。作为守卡人,从某种职业意义上,我很自觉地把蝴蝶隐喻为和平的象征。战士自然是花朵,不管白蝴蝶,还是黑蝴蝶,只要它愿意在战士的世界里飞翔,就意味着我们的热血没有被世界吞噬,我们心灵的角落没有被春天遗忘,只要有蝴蝶飞过的高原,我们活着的心,就不会死!蝴蝶与战士同行,恰好代表了战士对和平的渴望!可此刻,我无法将自己对蝴蝶的理解,传递给一个只有八岁的孩子。看着在兵雕左右翩翩起舞的蝴蝶,我的心情放松了许多。
“切玛咧那古,快快飞走吧,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身着氆氇的丹增尼玛,挥舞着一只长长的空袖,努着嘴,很是生气。
那只切玛咧那古,紧紧贴在兵雕的嘴唇上,像一枚亲爱的“吻”。
丹增尼玛看着我欣赏兵雕的神情,不假思索:“如果金珠玛喜欢,我就把这座兵雕送给你。”
“喜欢,当然我喜欢,不仅我喜欢,我保证我们所有的守卡人,都喜欢你的兵雕!”
丹增尼玛双手合十,开心地欢呼道:“太好了,太好了,我知道有了他,金珠玛就不会孤单了。”
我心花怒放地点了点头,表示愿意接纳丹增尼玛的心愿。
我跌跌撞撞地跑回哨卡。虽然毡房离哨卡不到一公里的路,但我如同跑了往日几倍的距离。背后似乎有切玛咧那古追来,绝对不止一只,千只万只,反反复复,千遍万遍,萦绕耳旁。
阎辉听了我对兵雕的描述,什么话也不说,如同一支跑马英雄射出的利箭,向着边巴大叔的毡房一刻不停地飞去。我来不及阻拦,伸出的手臂,与他的背影总是若即若离,终于哗啦一声,扯破了他的衣衫。
“别拦我,我只想去看看我們的丹增英雄,他是不是复活了?”
“你这个新兵蛋子,尽是打胡乱说,我们的丹增老兵,不是转运到部队医院去了吗?”
“我不清楚,连队派我来哨卡时,指导员让我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有新闻讲丹增英雄,已转移到重庆,几十个军医专家,围着他会诊呢!小道消息说的与新闻不一样,老兵丹增颈部破裂的血管太多太多,可能已经……”我根本不想理睬阎辉的话,在我们的吵嚷中,毡房外的丹增尼玛已远远望见了我们。我真希望他雕刻的不是丹增,而是任何一个长着金珠玛脸谱的人。哪怕是阎辉这张年轻却又不够周正的脸也好。
阎辉上气不接下气,总算跑到兵雕面前,久久伫立,默默指认,然后举起手,向兵雕行了一个军礼。边巴大叔,丹增尼玛和我,也情不自禁举起手,向兵雕敬礼。
“自从来到草原,娃就不停地雕呀、刻呀,一天也没闲过!”边巴大叔眼里蓄满了泪花。
“边巴大叔,没事的。丹增转运下山时,你是护送者。关于他的伤情,你应该最清楚。”
“原本,我答应过丹增,这事不告诉金珠玛。你知不知道,丹增牺牲了,丹增尼玛没有阿爸了!”边巴大叔恶声恶气的话,如同晴天霹雳,顿时把我惊得目瞪口呆,只觉得喉咙被一根鱼刺插得好深,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波拉(爷爷),别说,别说,你别说!”丹增尼玛捂住边巴的嘴。
我和阎辉簇拥着丹增尼玛。阎辉急切地思索着,想找些话来安慰这位失去父爱的孩子。可这一切太突然,阎辉搞不明白,我也难以置信丹增尼玛竟是丹增的儿子。我与丹增一起守卡,两人结伴同行,他从不提及自己的家庭成员。我只知道他的家在工布,那里有美丽的尼洋河。丹增的快乐,也许大多建立在空灵的口哨声里。这样的口哨绝活,至少是他家三代相传的,因为它转调太密集,我像鹦鹉学舌,一周也没把嘴型比例分配到位,腮帮子胀痛了,吹出来的旋律却远不是那么回事。丹增吹的口哨,名叫《格桑花调》。只要此调从他口中出,就有蝴蝶自然而来,真是神奇得令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格桑花调》好听不好吹,但却能在动听的口哨里,让人感知格桑花香。工布尼洋河,开不败的格桑花,丹增吹起口哨,脸上便有酒窝。格桑花生长的土壤,除了高原,是否也可开在别的地方?比如我平原上的故乡。这样的问题可能有点烧脑,丹增从不肯回答。只是他承诺,待换防休假,带我去看格桑花。
“你们把兵雕运回哨卡去吧,这也是孩子送给你们的一份礼物。”边巴大叔的声音开始冷静下来。
阎辉从牧场上找来一辆大推车。银丝如雪的嬷拉,从毡房里取出一叠哈达,我们携手将兵雕包裹得严严实实,生怕风吹疼了他冰冷的皮肤。
丹增尼玛从密室里跑出来,手上提着一个小小的棕皮袋子。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金珠玛,阿爸给你留下一个东西。我一直顾着为阿爸雕像,差点忘了这事呢。阿爸有交待,我记着视频那天,头上缠着绷带的阿爸,声音好小好小。阿爸反复说,不能随随便便去哨卡妨碍金珠玛,更不能随随便便给别人讲,咱们一家都是守防人。金珠玛,长大了,我也来陪你一起守防。”
懂事的孩子!我摸了摸丹增尼玛的头,没有说话。
后来,我将棕皮袋子里面,那细碎得近乎残渣的米粒般大小的种子,埋在兵雕周围。
似乎一夜春风,它们便可开满哨卡的每个角落。
眨眼之间,切玛咧那古就会布满格桑花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