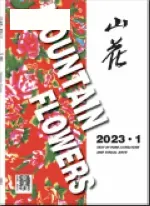莱茵故垒与巴黎拱廊
丛子钰
每天走路的人通常会忘记走路的感觉,除非他的腿或脚受了伤。眼睛也是如此,双眼形成的视觉和单眼是不同的,似乎任何机能都要在故障中才能理解自身的用途。我想,语言是否也是如此呢?只有白话文诞生了,文言文的问题才是个问题。只有当沟通成为一种不可能的时候,我们才思考语言的含义。审美陷入危机的时候,正是思考美的时刻。
门前有一条长街,平时说不上车水马龙,因为附近没有学校,也没有商场,整条街唯一的商店卖的是寿材。街的两边是小区和元大都遗址公园的土坡,如果从元代算起,那这个土坡至少有八百年的文化史了。以前遗址公园的土坡经常因为下雨而产生淤泥,这两年来治理效果显著,街边的百年树荫和土坡相映成趣,倒成了一道景观。我有一个并不年轻的习惯,就是喜欢早晚在这条街上散步,散步的时候,便想起宗白华先生来。众所周知,宗白华先生在八十年代初出了一本著名的《美学散步》,其实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跨越几十年的美学论文,按照今天的学术机制来看,这些文章更像是随笔。随着“美学热”消停下来,这本书里的文章虽然也进了中学教材,但读的人是变少了。不仅是因为今人的审美越来越成问题,更直接的问题是:大家哪里有闲情去散步呢?
美学散步不一定是真要散步的,但思考审美问题,往往跟行走有关,或者说,跟走在路上看到的景观有关。或是看到婆娑树影、溪山雾月等自然景物,或是看到车水马龙、琳琅满目的摩登事物。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探讨的大多是东西方对自然美的遐思,而与他同龄的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在《单行道》和《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中则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所创造的审美现象。本雅明所创造的“闲逛者”形象,与宗白华所说的“散步”有怎样的关系?这是个值得玩味的话题。
宗白华和本雅明相差仅四岁,一九二一年宗白华转学到柏林大学学习美学时,本雅明大概刚从伯尔尼返回德国,计划写他的教授资格论文。若说二人此时最大的相似处,可能是都在思考两个名字里带“德”字的德国人,一个是康德,一个是歌德。对本雅明来说,《歌德的〈亲和力〉》正是用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所做的尝试,如果说这个时候本雅明有了什么重大发现的话,就是发现了美的事物所必然携带的假象特征,“真正的艺术作品只有不可避免地再现为一个秘密时,才是可以理解的。”美总是披着一层面纱,美本身是永恒的模糊的,这层假象的面纱反而使美变得能够理解,脱下假象的面纱,美就变得赤裸而模糊。本雅明后来在布莱希特的影响下,抛弃了自己的这一态度,认为美可以像真理一样赤裸,这或许是一个遗憾。宗白华对歌德的关注主要在歌德的人生观,他认为歌德“对流动不居的生命与圆满谐和的形式有同样强烈的情感”,这或许倒装过来便是宗白华自己对于艺术的态度,即通过欣赏圆满谐和的艺术便可通达一种流动不居的生命,以静观动。他热爱浪漫主义诗歌的寂静,却是以东方的方式去欣赏的,他在歌德《海上的寂静》中看到“一切宇宙万象里有秩序,有轨道,所以也启示着我们静的假象。”似乎宗白华心中的“宇宙谜”就在于宇宙明明是生生地运动,却呈现出这一“静的假象”。人生即是生命的运行,死亡不过是它的假象之一。民族也是如此,衰朽只是一种暂时的假象,等待新生才是它的真相。所以在宗白华心中,爱国与爱人生内在是一致的,因为宇宙贵在运动,生命贵在创造,国与民相似,“我们可爱的中国不是已有,还须创造。我们亲手备历艰辛创造出来的新中国,才是我们真正可爱的国家。”所以他才要创建“少年中国学会”,他认为爱要在困苦中、在亲身体验中找寻,单靠认识是达不到亲和力的,这就体现出了散步的可爱来,它虽仍是一种静观,却是在行动中的静观而非冥想。
于是我们便读到了宗白华笔下的晋人之可爱,他们的艺术与人生观同样清澈、澹泊、超脱。无论是王羲之的字、陶渊明的诗、嵇康琴曲还是顾恺之丹青,都“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更重要的是他们一往情深的人格魅力,此所谓“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与宗白华热衷于健康的生命意象相对,本雅明迷恋着波德莱尔式的死亡意象,他将时尚视为“捍卫尸体的权利”,商品拜物教是一种恋尸癖,但现代性美学又是建立在这种死亡意象之上的独特的美学,《恶之花》是“充溢死亡的田园诗”。宗白华与本雅明都强调“现在”的重要性,但前者看到了“在刹那的现量的生活里求极量的丰富和充实,不为着将来或过去而放弃现在价值的体味和创造”;后者则忧郁地描述了历史天使的形象:“他回头看着过去,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整场灾难。”
同样用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去观看世界,为何得出如此不同的答案?一方面是东西方文化差异构成了二人审美体验的不同背景;另一方面,或许是走路方式和观看这些与身体直接相关方面的方式的差异,让他们产生了不同的结论。童年当然起了很大作用,本雅明出生的城市在他两岁时建成了帝国的象征性建筑:帝国议会大厦。在他的童年记忆中,柏林已经是一个到处是商品意象的现代大都市。这些意象构成了他的无意识,也造就了他的想象力和愿望。正如他所说,“时尚不仅支配了日用品,也支配了宇宙”。但是这种支配作用在宗白华的南京童年里是不存在的,他既然总谈到“宇宙的真相最好是用艺术表现……最真确的哲学就是一首‘宇宙诗”,那么我们或许应该首先看到宗白华与本雅明对于宇宙的看法,在直观上就有不同。宗白华的宇宙总是关于自然物,“月的幽凉,/心的幽凉,/同化入宇宙的幽凉了。”(《流云》,一九二二年四月写于柏林)在这宇宙中,虽然有天上的星星、月亮,但更多是诗人用来照见自己内心的镜子:“一会儿,/又觉着我的心,/是一张明镜,/宇宙的万星,/在里面灿着”“心中的宇宙,明月镜中的山河影”。一九二二年夏天的兩首诗《秋林散步图》和《柏林之夜》是很好的证明,证明了宗白华的散步是在自然的景致中进行的。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巴黎,自然才使他感到不隔,“莱茵河上的故垒寒流、残灯古梦,仍然萦系在心坎深处”;而他对城市景象的观看则是隔的:“楼窗外,/电车,马车,摩托车,/商人,游女,行路人;/灯光交辉,/织成表现派的图画”,或者是在大都市的街道上关注到类似中国乡村的风景,“田家的女儿,/在斜阳罢耕后,/待着你的歌声起舞。”而本雅明看到的是“土星光环变成了铸铁阳台,土星居民在那里晚间纳凉。”城市的楼房是对天空的遮蔽,光与电遮掩了星空与月色,这些都阻碍了宗白华观察自然时的幻想,所以他感到“都市里没有好风景”。或许城市里的这些现象确实也造成了本雅明的忧郁和悲观,他自己也认为,“大城市……以宽阔的视野唤起他们对始终警觉的自然力量的意识……不是通过自然景观,而是通过无拘无束的自然中最令人感到悲痛的东西:翻耕的土地、高速公路,鲜明的红面纱再也遮挡不住的夜空。”
若是认为宗白华只看重自然美,显然是窄化了他的美学;同理也适用于认为本雅明只是一味地美化城市。对宗白华来说,自然之所以美并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圆满,而是“向着美满方面战斗进化”,也就是自然本身的运动性,所以他特别称赞罗丹的雕塑。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宗白华的美学格外重视的是运动与静止间的辩证性。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他对前卫的视觉艺术涉猎不多,加上本来就有的美学观念,让他难以接受摄影的艺术性,认为照片里的真实不如美术中的真实,这或许是散步所达不到的理解。散步的人在美学享受中追求着个体人格的完善,他在自然之镜中照见自己與宇宙的相似。闲逛的人所做的是一种西西弗式的劳动,他在注视橱窗里的商品时,透过橱窗的玻璃照见自己,发现自己也是一件等待着出卖劳动的商品。闲逛的人以审美的眼光观看商品,就是在剥离商品的交换价值,他同时也是在徒劳地救赎自己的灵魂,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劳动力。在波德莱尔的诗中,这些闲逛的人总是具有英雄色彩,比如拾垃圾者,“在那像华盖一样高悬的苍穹之下,/他陶醉于自己大智大勇的气概。”即使不是在闲逛的时候,城市视觉也常给人带来不愉快的经历,本雅明听过课的齐美尔就指出,“在十九世纪公交车、铁路和有轨电车发展起来之前,人们不可能面对面地看着,几十分钟乃至几个钟头都彼此不说一句话。”我想这种体验在今天已经普及到每个人身上了,在一线城市早晚高峰通勤途中,恐怕就很难思考人格的完善了。很多人都是独自一人,挤在无数人之中,面前车窗上是飞驰而过的广告,可能在一个地产广告下面还写着王维的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但在本雅明的闲逛对当代人来说引起强烈共鸣的同时,宗白华的散步却显得更为珍贵。
这让我想起去年夏天到苏州旅行的经历。张继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无人不知,如今亦是寒山寺最响亮的广告。所以只要是节假日,寺前排队的海量游客总能让人产生哲学之问:我是谁?我在哪?想起宗白华所说,“我并不完全是‘夜的爱好者……我爱光,我爱海,我爱人间的温爱,我爱群众里千万心灵一致紧张而有力的热情”,我不免陷入迷茫。离开景区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熬夜”的爱好者们开始聚集起来,在商场,在酒吧,汇聚起他们“紧张而有力的热情”,但那真的是热情吗?还是无处宣泄的无聊与烦躁?最可怕的莫过于被某种不自然的事物包围起来,即使是本雅明的闲逛者,也不是被包围着,不然还哪里称得上“闲逛”二字?只能说是忙逛。大自然是不大可能将人包围起来的,唯一能想到的可能是落水——被湖水包围也算是一种包围吧?那也是一种极为恐怖的体验了。所以我想,距离对于美来说还是很有必要的一个东西,无论是空间上的距离,还是想象中的某种距离。比如散步和闲逛,就是和日常生活与工作拉开距离,身在其中是很难体会到美的。人类的眼睛是一种不算特别发达的器官,跟很多动物相比,我们能看见的事物都更为有限,而且在看非常近的事物方面这种缺陷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明显。所以把散步和闲逛看作是人类视觉与身体机能相适应的一种策略,或许也是种不错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