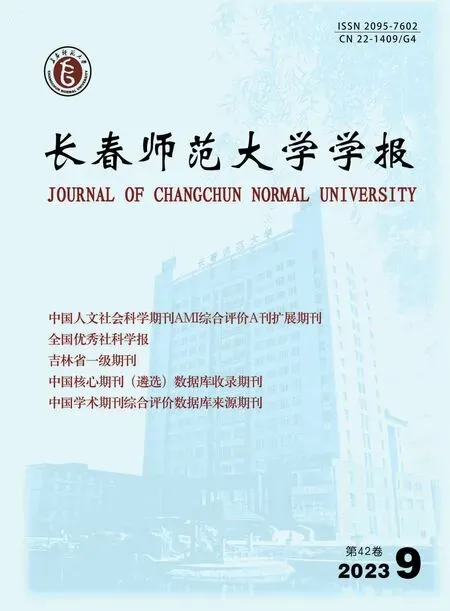卡夫卡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
李佳颖
(齐齐哈尔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卡夫卡的小说具有典型的现代主义特征,他既赓续了传统现实主义作家关注现实世界的传统,又在表现形式上不断地尝试立异出新,小说揭示现代人的精神结构与生存危机。他的小说具有显著的双重性特征,既缠绕着丰富的现实细节,又因想象和变形而带有明显的荒诞特征,在充满悖谬性的叙事中流露出对现实的敏锐洞见和哲性思索。
一、寓言化的空间叙事
纵观卡夫卡文学创作的全貌,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奇异的事实,即对时间的淡化与对空间的重视并行在他的创作中。对线性叙事时间的有意悬置,使卡夫卡的小说呈现出显著的空间特征。具体的物理空间连结着人物的心理空间,象征着广袤的社会空间中发生的变迁,以寓言化的方式折射出创作主体对外部世界投射的观照。
列斐伏尔的“空间转向”深刻地影响了卡夫卡的空间观。他擅于通过封闭空间的搭建揭示人物的精神结构,以具体的空间形式寓言化地对人物的心理世界进行写实。《地洞》中,卡夫卡以“非人”的视角还原了动物挖掘栖身的地洞的经过:“我”为保存食物布设了各式各样的陷阱,终于将狭小的地洞打造成内部畅通无阻、外部坚不可摧的“堡垒”。但“我”依旧惶惶不可终日地担忧外界的危机,任何缝隙传来的响动都能够引起“我”心灵的抖震,担忧这地洞中的安谧生活即将因敌人的侵入而走向终结。封闭的空间形态不仅象征着现代人住宅的空间形态,具有封闭、独立的空间特征,而且以空间状态和秩序描绘现代人的关系的空间分布,表征现代社会中日渐疏冷、自顾的人际关系。《变形记》中的空间叙事也具有显著的封闭性,动态地呈现了格里高利·萨姆沙居住空间的变化,反映了主人公自我认知逐步变形的经过[1]。在变形成大甲虫之前,格里高利的房间带有显著的个人特征,桌子上高高堆放的衣料样品揭示着主人公的职业属性。在经过荒诞的变形后,他依旧尽职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与家庭义务,却没人再度承认其“人”的身份。当冷漠的家人将他房间内布设的家具撤走时,格里高利却舒适地感觉这更利于自己的爬行,而后这件居所被改造为脏乱的杂物间,彻底表现了家人对他的放任自流的冷漠态度。这竟然令他感受到更多的乐趣,体会到了更多的舒适。从“人的居所”到“虫的巢穴”的转化,无疑具有高度的象征性。空间属性的置换暗示主人公人性的逐渐消散。小说以空间形式完成了人物的心理投射,使接受者不得不反思现代工具理性给个体的自我意识带来的压抑。
同时,小说中的具体空间也成为卡夫卡透视并反观外部世界的“窗口”,卡夫卡并不以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对社会生活进行还原化的写实,而是以空间叙事书写关于社会历史的寓言。如《临街的窗户》中的空间建构带有半开放性的特征,主人公认为自己的屋舍必须在临街的那面敞开一扇窗户,这样特殊的空间形态表征着现代社会中个体对归属感和隐私性的双重追求。“临街的窗户”既能够使主人公通过敞开的窗户接触到窗下如流的行人,融入群体并寻得身份的归属感,同时又能够通过闭合拒绝来自外界的窥视,保留属于自我的空间。窗户的一敞一合象征着人物心灵的敞开与封闭,使空间形象地表现出个体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掌握的游刃有余的尺度。《审判》中的空间规划更富有象征性,卡夫卡着意选择了纵向的物理空间:楼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森严秩序的具象表征。当希冀踏上通往迪托列里的狭窄楼梯时,随着体力的消耗,他愈发感觉到空气的稀薄,感到头晕目眩。卡夫卡着意以物理空间内稀薄的空气象征最高权力机关对个体施加的无形压力,又以个体在楼梯空间中的攀爬运动揭示了在社会阶级的跃升活动中个体必须付出的艰苦努力。物理空间形态成为社会秩序的隐喻,传递出卡夫卡对人类社会结构的理性观照,以及将其寓于空间叙事的创作巧思。
对时间存在感的淡化使卡夫卡的空间叙事挣脱了线性时间的桎梏,使其小说文本的解读不再受到社会学与历史学实证研究方法的阈限,而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2]空间的建构形式反映着作家精神世界的复杂沟回,凸显了其对现代社会中个体精神结构的透辟理解,以及对人类社会架构的整体性反思。
二、复杂变幻的叙事视角
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揭示了叙事视角的择取具有的巨大叙事潜能。内外视角的敞开与遮蔽以及叙事主体的不同,决定了接受者能够从文本中获得哪些信息,带入怎样的情感态度及道德立场。可以说,叙事的视角表现了作者在文本中最本质的意图。卡夫卡小说中叙事视角呈现出复杂变化的特质,他善于将各异的叙事视角嵌入不同的叙事内容中,以实现最精彩的叙事效果。
具有限知性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是卡夫卡小说中最为常见的叙事视角。视角聚焦的主体通常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而叙事的声音却来自于文本之外的隐含作者。视角的限制形成了对文本信息的有效遮蔽,使接受者不自觉地按照创作主体的叙事意图进行“有组织的参观”。《城堡》便采用了第三人称叙事,将叙事视角聚焦在主人公K的身上。随着K乘着夜色来到城堡周围的小镇并打算拜访城堡的官员克拉姆,整体故事便缓缓拉开帷幕。随着K与客栈老板娘、侍女佩碧以及奥尔嘉等人的相遇,K逐渐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了各种有关克拉姆的事情。然而,几个叙述者的话语之间隐含着彼此冲突的成分,他们诉说信息的真伪,又没有方法加以鉴别。于是,随着K从他者的口中所摄取的信息流越多越庞杂,他主观想象中的克拉姆的形象便越神秘与模糊,似乎笼罩着一层永远无法揭去的面纱。正是限制性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对有效信息的遮蔽,才使原本简明的故事情节变得疑窦丛生、波澜起伏。[3]《在法的门前》中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更具有戏剧性特征,主人公在“法的门前”徘徊不去,却始终无法进入。守门人为何表示这扇门是在为主人公而敞开?既是为主人公敞开,却又为何阻止其进入?接受者在对主人公的自我代入中体验着与其一样的困惑和迷茫,从而使文本在有限的篇幅中制造出层次丰富的情感体验。
同时,卡夫卡也着意在小说的叙事中探索各种“非人”的视角,以殊异的叙事主体制造奇异化的美学效果,同时以视角带来的立场转变引导接受者观览现实的不同侧面。《一份为某科学院的报告》中,卡夫卡以混入人类社会的猴子的视角展开叙事:“我”为了逃避沦为试验品的命运而乔装改扮,不断模仿人类的行为习惯与形貌特征,以混入人类社会的形式,变相地获得梦寐以求的自由。在实现蜕化的过程中,“我”身上的动物习性不断地与逐渐形成的人性相抵触,令“我”既嘲弄人类社会的丑陋行径,又在所难免地受到人类社会各种新奇事物的吸引。动物视角对现实社会的介入提供了新的观照现实的角度,令接受者得以透过新的视野重新反观他们熟稔的日常生活并获得新的体验,同时也对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人性的终极本质有了更深的理解。《变形记》的叙事视角也具有显著的特殊性,文本对格里高利的逆向蜕化过程的讲述交织着内外双重聚焦的叙事视角。小说以格里高利的内聚焦叙事视角为主,讲述了其变为甲虫后的个体经历,细致地铺垫了其变形之后家庭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其自我认知在断裂中重塑的艰难过程,使接受者透过其内聚焦视角的敞开体味到主人公渐渐沦为异类的孤独感。同时,卡夫卡有着意以外聚焦视角下的讲述推进情节的发展,描绘格里高利实现蜕化的整个过程,使小说的外部结构更为明晰,有力地实现了对内聚焦视角下心理叙事的支撑[4]。
视角的复杂变换使卡夫卡的小说具有多元的美学特质。无论是通过叙事视角操纵文本的信息以制造叙事的波澜,还是通过引入特殊的叙事视角为接受者制造陌生化的美学体验,都能够使我们看到卡夫卡作为叙事者具有的出众的文学才赋,以及其对小说叙事形式的实验和创新。
三、荒诞离奇的悖谬艺术
卡夫卡的小说叙事始终具有浓郁的矛盾特征,它作为一种深层的思维方式存在于卡夫卡的小说建构中,使文本充满了冲突的美学张力。悖谬艺术的密集呈像,使卡夫卡的小说富于矛盾的魅力,形成了“迷宫式”的审美体验。
卡夫卡在文学创作中俨然深谙“二律背反”原则的魅力。他擅于通过情节的突变与陡转建构背反关系,从而在前后对照的矛盾性中形成独特的张力。如《变形记》中变身为巨大甲虫的格里高利·萨姆沙,不断地寻求家人的宽容与善待,执着地寻找重归人身的方法。他的人性却愈发难以抵御甲虫的动物本性的召唤,最终困居在甲虫的外壳中悲惨地死去。主人公的主体愿望与现实遭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无声地指控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异化。《诉讼》中约瑟夫·K为了摆脱莫须有的罪名不断地奔走求告,在案件的眉目逐渐厘清并有了洗脱罪名的希望时,却束手接受了法官的审判。小说的结尾与开头构成不协调的反差,情节的陡然转折引起了接受者惊异的审美感受。《饥饿的艺术家》中艺术家所表演的行为艺术充满悖论性的特征,艺术家竭尽气力地忍饥耐渴是为了“获得适合口胃的食物”,然而他越展示自己的真诚与用力,便越疏远自己与观众间的距离。这种行为与结果的背反具有浓郁的荒谬性,引发接受者不自觉的同情。
《城堡》无疑是卡夫卡的作品中最具有悖谬意味的文本。小说的对话体的叙事策略颠覆了传统叙事的线性时间结构,以主人公K为叙事的轴心,连绵不断地引入新的人物,并通过密集的对话推动情节的发展。K本来对自己土地测量员的身份笃定无疑,然而在桥头客栈老板娘、巴纳巴斯、弗丽达和汉斯等人的质疑中,也逐渐陷入身份自疑的泥淖中不可自拔。冗余繁复的多声部对话最终形成了“无解的线团”,将有关主人公K身份的真相缠绕其中,不见天日。主人公K为了进入城堡,不惜引诱城堡官员克拉姆的情人弗丽达。城堡虽近在咫尺,但主人公K费尽周折奔波得筋疲力竭,至死也未能进入城堡。这使本是来城堡担任土地测量员的K本身都产生了自我确证的疑虑,发出了充满困惑的呼声:“那么我究竟是谁?”[5]这种充满了悖谬的叙事形成了闭合的环形叙事结构。卡夫卡不断地将真实的细节织入文本叙事的语流,使读者因卷入其中而无法识辨各种信息源的真实性,从而更深刻地觉察到其中存在的悖论与荒谬。
“悖谬”的叙事手法使卡夫卡的小说消解了客观现实的唯一确定性,从而令小说呈现出多元的美学样态,使接受者在叙事的迷宫中不自觉地以自我代入的方式找寻答解,从而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过程[6]。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悖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所谓的“荒诞”,它凸显了卡夫卡对矛盾美学的哲性反思。主人公K来到城堡,费尽周折却无法觅得入口,只能徘徊在城堡之外虚度人生,进行着“徒劳无功的圆周运动”的荒谬故事,实际上是卡夫卡对世界运转逻辑中的粘滞感的隐晦表述,展现出作家对现代精神荒原中深刻的生存危机的先觉与警醒。接受者一面对这场无休止的闹剧深感可笑,一面又联想到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各种矛盾,使他们向外投射的视线逐渐回归对自我的审视。这种“悖谬”的叙事艺术显然带有果戈里悲喜剧中“含泪的微笑”的艺术风格,使小说因痛苦与幽默、忧郁与滑稽的交织而呈现出怪诞的风格。这种喜剧形式与悲剧内核的结合迸发出强大的艺术魅力。
悖谬的叙事艺术使卡夫卡的小说创作流露出崇高的悲剧感,具有内与外的双重向度。这种充满悖论与荒谬的概念,正是现代社会整体意识形体的写照。卡夫卡以充满悖谬性的方式,重新感受并表现了整个世界,其中渗透的正是作家敏锐的批判意识和反思冲动。
四、结语
卡夫卡的小说创造了不同于传统叙事的新美学范式,他的小说常因叙事形式的实验而被施以晦涩难懂的评价。然而,他对空间叙事的开掘以及对叙事视角的创新,为现代派文学的后继勃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小说中的悖谬艺术更是对现代精神荒原的别样表现,深切地展示了作家对人类命运和现实社会的关注,实现了其小说创作的经典化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