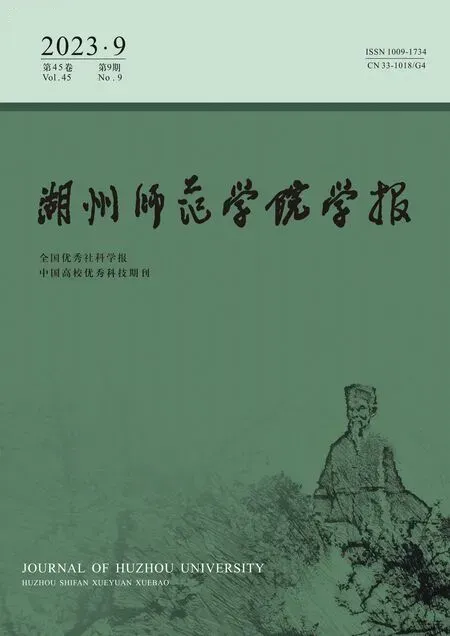“借剑时欲斩妖狐”*
——多元文化交涉视域下的晚明长兴甲子元日之变
杨小婷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甲子元日,湖州府长兴县知县石有恒与主簿徐可行被杀,时称“甲子元日之变”。对此事件,言人人殊,《长兴县志》等地方志持私人报仇说,丁元荐等东林党人持“群凶之隐谋”说,来华传教士寄回教廷的年信(《耶稣会一六二三年年信》)(1)Adrian. Dudink,Christianity in Late Ming China: Five Studies,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eiden,1995.pp. 244-245.注:《耶稣会一六二三年年信》,虽名为“一六二三年”,但实际上,所记之事的范围,应延至一六二四年四月或五月。强调无为教杀人说。事变不久,大儒许孚远之子许大受,立即将其反天主教著作《圣朝佐辟》献给德清知县。这使得该事件蒙上了一层“文明的冲突”色彩。本文拟钩沉史料,从明末历史语境出发,力争还原这一事件中各方观点的历史缘由。
一、扑朔迷离的长兴甲子元日之变
天启四年(1624)甲子元日,湖州府长兴县,即许孚远的门生、许大受的姻亲丁元荐(1560—1625)的家乡,发生了县令、主簿被杀一事。事发后,长兴县陷入了屠城之说中,民众四处逃窜,全城人心惶惶。在刘宗周笔下,县令石有恒被杀一事,乃叶朗生余党吴野樵所为(2)(明)丁元荐:《尊拙堂文集》卷十二,清顺治十七年(1660)丁世浚刻本。《刘宗周全集》中,名为《正学名臣丁长孺先生墓表》,且记有写作时间为崇祯戊辰(1628)十二月。(刘宗周著,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85页);但显然当时流行着一种(私人)报仇说,然丁元荐对此说予以否斥。不过,《长兴县志》则恰恰呈现的是私人报仇说这一叙事:
长兴邑侯石有恒,名宦也,侯素与族弟不协,至是乃结游侠徐山永、吴野樵等投朱无赖家,诡言劫库以饵之。天启四年(1624)甲子正月朔,山永纠聚凶徒,潜伏署左右,乘侯祝圣之际,凶徒将乘拥住,山永竟害有恒,曰:“我事毕矣!”主簿徐可行力格之,亦遇害。时,丁慎所(按,丁元荐)先生以礼部主事家居,闻有此变,先生奋不顾身即时率家丁二十余人,鞭骑至县。时,盗已匿,先生即命役吏,将石、徐二公之尸归于内堂,遂细讯官从役吏,皆言盗杀非民叛也。……
有一老吏居城东北隅,役罢回家,晚馔,其老妻相与言曰:“今晨闻杀了石老爷,约已牌时分,有十数人手持钢刀,身衣血衣,一伙而入朱无赖家去也,余在楼窗隙中见之。”老吏曰:“果有此事否?”其妻曰:“宁虚语哉?”朱无赖者,向以赌博为事,泼酒、好事,不轨之人也。老吏即密报丁侯,侯即时点捕快、民壮及守城卒等,约一百四、五十人,各执器械,理刑(按,冯可宾)与丁侯率领登时到城北朱无赖家左近,揭门而进,朱无赖正同诸盗呼五喝六,即时索手,一贼不遗,拷实通详,达部题奏,奉旨将首逆即时凌迟,将为从即时枭首示众,其无罪良民一无株连。释事之日,耆老士民焚香载道者,数十万人。未几,天子以冯可宾、丁元荐血诚任事,召可宾为给事中,起丁元荐为刑部检校尚宝司少卿,各赏赉优嘉。莫理斋记盗杀石侯事。(《长兴县志》)(3)(清)《长兴县志》卷二十七,清嘉庆十年(1805)刊本。
《长兴县志》对此事所记极详,其中包括丁元荐为安抚长兴县民心所出的诰示内容,以上引文仅摘录两节。在县志的叙事中,此事的真正元凶,则是石有恒的族弟,其因与石有恒不和,遂钩连游侠徐山永、吴野樵与朱无赖(即朱元孙)(4)参见(康熙)《长兴县志》卷四《弭盗》,(乾隆)《长兴县志》卷二《弭盗附》。等,以劫县库为饵诱之;于是,徐山永纠聚众凶徒,并选择在元旦祈福活动时行动。虽无法确定这伙人最初的预想是什么,但就县志用语来看,游侠徐山永“竟”害有恒,可能最初只是试图劫库,然不料混乱中竟杀了石有恒。此叙事亦提供了凶手被抓的详情,以及后来官方的处理结果:“拷实通详,达部题奏,奉旨将首逆即时凌迟,将为从即时枭首示众”。在《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中,亦是将此事定性为私人报仇说:
盗杀长兴县知县石有恒、主簿徐可行,随获贼首吴野樵、徐山、施立甫、石二房,及窝盗许画匠,寘之于法。有恒族人来县干谒,有恒薄待之……于除夕五鼓,乘其拜牌,执而杀之,并杀其主簿。天明,民兵渐集,贼无所徃,从县舍后逸去,随获正法。(高汝栻辑:《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5)(明)高汝栻辑:《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卷十二,明崇祯九年(1636)刻本。
据《长兴县志》这一叙事,真正杀害石有恒的是徐山永,而并非吴野樵。
但是,奇怪的是,东林党人的相关记载中,皆是以吴野樵为元凶,且皆认为此事背后蕴藏着极大的谋逆,丁元荐、刘宗周、高攀龙、魏廓园、姚希孟等皆持有此说。以姚希孟写给杨大泓的书信为例,他就称吴野樵为“首祸之人”,更是声称石有恒被杀一事为“群凶之隐谋”:
首祸之人名吴野樵,此叶朗生之党,盖浙西数郡不靖之徒,响年搜捕不尽者,纷纷窜伏,其狡谋未尝一日熄,直欲待时而动;而素惮长兴威望,谓此人不除,大事尚未可图。此其端倪,曾泄之一年前,云岫(按,即石有恒)亦微知之。直谓忠信甲胄,不甚提防,故遂及此。若言劫库之盗,则库终未劫;且外救云集,群盗亦欲自脱,正当挟生令以为奇货,而遽断其脰,此何意哉?
丁慎所(按,即丁元荐)诸公倡率讨贼,云岫灵爽不昧,野樵束手就擒,则其主谋、其窟穴、其徒党,皆一讯可得。而彼中流言,乃谓石氏有族人来抽丰者,其欲不餍,衔恨思报,欲得而甘心焉,遂将贼党中一人,今被民众杀死者,本名徐山永,以其楚人也,号为石姓,因其死无可证,遂指为族人报仇,以乱其真。倡此说者,无非欲宽贼党,见其事不甚大,不烦深求耳。
嗟乎!以一生砥砺,四载循良,近则一方之保障,远则连郡之干城,如石兄者,挺身死难,其死也,为一邑死,而其所以死者,实为数郡而死。盖石在则畏缩不前,石亡则狓猖无忌。此群凶之隐谋,而有吴野樵为之渠魁,此尤明白易见,奈何轻之而言劫库,又轻之而言报仇,欲以此抹煞死事之公案哉?昨见嘉湖道爰书,虽不提出报仇二字,而徐山永姓石名石某,其语故在,讹以承讹,将来未知作何结局。(姚希孟:《杨佥院大泓》)(6)(明)姚希孟:《文远集》卷十,明清閟全集本。
据此信,吴野樵一党最终并未劫库,且亦未挟持石有恒以便于脱身,其目的似乎就是杀石有恒。对此,姚希孟将此解释为,群凶认为“此人(按,石有恒)不除,大事尚未可图”。同时,姚希孟亦透露时人有“见其事不甚大,不烦深求耳”之观点,可见吴野樵一党并未有后续行动。在此信的最后,姚希孟还提到了如何安置石氏的“寡嫂孤侄”一事,对此,他将“与丁慎老(即丁元荐)经纪之”。高攀龙则更是指出此事,就是吴野樵为叶朗生报仇所致,目的是攻陷长兴,并非仅仅劫库:
长兴之宼,吴野樵是叶朗生事内钦犯第二人。近日之举,欲据邑,非劫库也。彼自以朗生事报仇杀石令。(高攀龙:《与魏廓园·四》)(7)(明)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八下,崇祯五年(1632)刻本。
明廷对此事的处理,可就天启四年(1624)二月二十二日,南京山东道御史刘渼之疏观之:
(二月)二十二日,南京山东道御史刘渼疏《请早赐彰瘅大示劝惩以肃人心》,内称:“长兴知县石有恒,死于吴野樵之手,而臣直谓其死于叶朗生之党耳。朗生谋为不轨,令首发其奸,所谓深恨而欲甘心焉者也,故吴野樵等未尝劫库,而止于杀令,盖意不在库也。且朗生之党,讵鼠窃狗偷?比者,从宜兴、真州直窥金陵之语,即无活口可质,而开天元师之三印固在也,乃转设为抽丰之说,则其党脱卸之词耳。
臣思朗生之逆,非减于东省之妖贼也,东省诸臣待其变而仅胜之,石令乃先其变而图之。待其变而胜之受赏,先其变而图之者不录,岂有恒之死,为自取贼杀乎?观其挺然骂贼者,堂堂数语,足对天日!是宜加殊宠,以作忠义之气者也,故曰:‘有不可靳之恩’。”(《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8)《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大明实录》。
就此疏来看,距甲子元日之变两个多月后,如何定性石有恒遇难一事,应仍然存在着争议,刘渼因而上疏请朝廷早赐殊荣,最后还提出“有不可靳之恩”,即恳请朝廷勿吝惜对忠臣之赏赐。同时,就“即无活口可质”一语来看,可见《长兴县志》所记“将首逆即时凌迟,将为从即时枭首示众”之“即时”,所言不虚。
总之,有关甲子元日之变,东林党人的叙事否定了私人报仇说,且均强调甲子元日之变的元凶为吴野樵;实际上,真正关键的是强调吴野樵是叶朗生的余党,即是以叶朗生一党的性质,为甲子元日之变定性。有关叶朗生之变的性质,我们放在第三节讨论,我们先来看东林党人的叙事。
二、“群凶之隐谋”:东林党人的集体“制造”
前已提及,徐山永聚集一众人等,且石有恒亦是被他所杀,而吴野樵为何却成为东林党人所言的“首祸之人”。这一疑问,在姚希孟写给石有恒长子石确的一封回信中,可得以解密:
昨尊伻以大揭至。……夫以数十人突入官舍,杀才名久著之贤令而去,此岂寻常绿林客?名为劫财,而财实无所劫,恐其志亦不在财也。丁长孺先生所折其胫者,其人既为昔年乱党,则我知其所由来矣。此在长兴为目前之祸,在江南为将来之祸,而乃首钟其祸于尊公一人之身,此正曹操杀孔融之故智,不意鼠辈亦能办此!地方事自有地方诸公任之,老侄可以弗问,老侄所宜亟问者,家仇耳。赵娥一女子,尚能剚刅于仇人之腹,数十群凶不一一虀之、醢之,尊公之目不瞑,而老侄之责亦未酬,上告下诉,良不可已。
……
其吃紧处,在始而见执终而被害,铺张摹写,有一叚慷慨骂贼、赴死如归之意,使千古而下,读者犹觉眉须直竖,方不负尊公一死。至于威名久播,为远近所慑伏,群盗有所举动,知尊公不独一邑保障,且足为江南保障,石令不除,大盗小盗具碍手不得逞,故必欲除之而后快,此尊公得祸之因缘。如此说起,则题目大而死者有光,徒言劫库便是庸贼,即区区保全库藏,而以一身殉之,亦是邑令本分事,不足道矣。幸于此揭,猛着精彩,老侄复仇之公案,即异日显亲、扬名、忠孝之公案也。……
老侄则守灵柩朝夕恸哭,凡见官长、乡绅,以迨士民,一味击颡呼天,必欲啖其人之肉而后已。俟群凶胥正典刑,然后率合邑之人大地缟素、陈丧路祭扶衬言归,此一时也,又必有哀号动地、血泪崩城之象,乃不枉石云岫一死!(姚希孟:《石年侄确》)(9)(明)姚希孟:《文远集》卷十,明清閟全集本。
石有恒长子石确,在事发时曾受伤。石确受伤之因,《东林列传·石有恒传》记为曾被挟持以逼石有恒就范。在写给其父至友姚希孟的信中,石确应诉说了事件的详情。不过,姚希孟在回信的第二节,则先是委婉地否定了石确提供的叙事,接着,他教石确如何“上告下诉”:其“吃紧处”,是对石有恒“始而见执终而被害”一节,要“铺张摹写”,体现出其父“慷慨骂贼、赴死如归之意”;而另一关键处,则是教他如何写“尊公得祸之因缘”。由此可推知,石确前揭中应该是写其父石有恒是为保护县库而死,所以,姚希孟才会说,倘若如此叙事,则凶手便仅是劫财的庸贼,那么,石有恒的遇难,便只是分内之事,也就不足道也。至此,他告诫石确要提供这样一种叙事,即要将石有恒死因归于:为江南群盗所忌惮,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姚氏强调,“如此说起,则题目大而死者有光”;最后,他又叮嘱石确一定要“幸于此揭,猛着精彩”,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石确日后“显亲、扬名、忠孝传家之公案”。由于他不能立即前来,他叮嘱石确要与丁元荐多所商榷。
但是,这恰恰透露出石有恒被杀的一个真相,即是在保卫县库的争斗中被害;同时,石确的最初叙事中应也透露了“名为劫财,而财实无所劫”;而这一冲突,实际上恰可在《长兴县志》的叙事中得到解答,即盗贼之目的是报仇兼劫库,所以才杀之而去。同时,据“杀才名久著之贤令而去”,且完全未提及夺县令之“印”等事,可见,盗贼并未有据邑造反之迹。
至于吴野樵究竟是在何时被抓,据《长兴县志》以及姚希孟的此信,应是丁元荐在朱无赖家将其捕获,丁元荐选择了将吴野樵视为首犯定罪并杀之。又据姚希孟此信可知,由于吴野樵是叶朗生的余党,丁元荐应是选择了将此事与天启二年(1622)叶朗生之变的性质相关联,尽管吴野樵此次并无叶朗生当年之行径。也就是说,丁元荐极为警惕此事的严重性,在这一警惕性思维主导下,姚希孟则接着丁元荐所提供的朗生余党之信息,再次有意将此事与江南诸郡的安全性相连。至此,长兴甲子元日之变的“群凶之隐谋”这一叙事,拉开了序幕。而在后来的东林党人的各种“上告”中,这一叙事得以确立。
后来,东林党人在有关甲子元日之变的书信中,皆是围绕姚希孟所提供的这一叙事而展开。可见,石确最后的“上告下诉”,应是按照姚希孟所教而行事,尤其是姚希孟所建议的“其吃紧处,在始而见执终而被害,铺张摹写,有一叚慷慨骂贼、赴死如归之意”。因为据相关文献来看,石确的确是如此写的,以《东林列传》为例可一窥:
(石有恒)叱曰:“草贼!敢叛天子,杀王臣耶!”索印,不可;强之行,不可;以刀伤其长子确,亦不顾;贼拥之出仪门,有恒曰:“头可断,此限不可逾也!”遂被害,血上喷,移时不仆。(陈鼎:《石有恒传》)(10)(清)陈鼎:《东林列传》卷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提到索“印”,即是要将盗贼目的与据邑造反相连。这一叙事,在东林党首高攀龙的《祭长兴令石云岫》一文中,更可看到长篇大论:
呜呼!长兴之变,非始于长兴也,甲子元旦之变,非始于甲子元旦也,其所从来者久。发于长兴者,官真则盗畏也。官真,必为国家安地方,除盗贼,盗安得不畏?安得不思除之,以便行事?故长兴之盗非劫库盗也,欲据邑叛也。公逸,则盗恣屠杀焚掠矣,民鸟兽散,盗有城矣。不意公直身当之也。彼以为得令,无不得志焉,不意劫狱,狱囚无从叛者,皆曰宁死不背石爷。士民且动地起,盗于是思挟令出城,又不意公视死如归也。杀一簿,持首示之,公恬然曰:“吾为令,乃护盗,吾即活,何颜见长兴父老?”于是,盗知事不成,杀公矣。
夫以公之明,闻难而不乱,岂不知脱身避盗,可以擒盗?然公避而邑残矣,盗势张矣,盗势张,即事不可知。于斯时,将出城乎?否乎?出城则弃城,不出城则死。与其不死而成盗之事,孰若使盗事不成而死,而盗亦遂堕公计中。夫杀贪污吏者,或可倡乱,公则民之天也,胡可杀?杀贪污吏者,或可逋窜,公之死,则为明神者也,胡可免?甚矣!盗之愚也!
公三楚豪杰,国家方倚为栋梁柱石,而天之生公,仅以殉长兴之盗,完长兴之民,何耶?节莫大于致身,致身惟义所安耳,义无小大也。抑天之意若曰:“兹盗也,擒则星星,纵则燎原,非公不能殄也。”特委公与?今天下万姓膏原野,其初起于一人畏死,委而弃之,以成大难,特以公示之式与?夫盗之杀公,不过以公能捕大盗,靖一方,杀公而吏无复有捕大盗者。不知公不死,盗尚活,公死,盗获,是盗之杀公,自杀也,何益之有?而他盗或自此悔而为良民与?然则公一人之死,免万姓之死,欲使天下无二心之臣,无二心之民,其志大矣!其功大矣!其死大矣!非国家所倚为栋梁柱石,天所以生豪杰之意与?哀哉!(高攀龙:《祭长兴令石云岫》)(11)(明)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十一,崇祯五年(1632)刻本。
在高攀龙此祭文中,显示出石有恒有三次可求生的机会:最初可以逃跑,然石有恒选择了“直身当之”;接着,盗贼试图挟知县令全县,然石有恒不配合;最后,外救云集,盗贼因而试图挟持石有恒出城以便逃亡,但石有恒仍不配合,最终被害。或因时人对最后一次有关逃生机会的叙事存有质疑,因而,在此祭文后两节,高攀龙以充满辩护口吻指出,这可视为石有恒的捕盗之计,如随盗出城,“与其不死而成盗之事,孰若使盗事不成而死,而盗亦遂堕公计中”。这一计的关键是,若随盗贼出城,则石有恒或可求生,然盗贼则逃逸之,石有恒拒斥随其出城,则料到盗贼必将杀他,而杀朝廷命官后,明廷必然会追捕之,则盗贼杀石有恒,无异于自取灭亡。因此,高攀龙说石有恒“志大矣”。
但东林党人的上述叙事充满漏洞与冲突。如倘若是“群凶之隐谋”,必欲除石有恒而后快,缘何石有恒具有多次求生机会?倘若是欲据邑造反,为何杀县令后却逃走,并未有造反之迹?而且,姚希孟与高攀龙的说法又相互冲突,姚希孟说,“外救云集,群盗亦欲自脱,正当挟生令以为奇货,而遽断其脰,此何意哉?”据此,盗贼并非尝试挟持其逃亡,而是杀县令后而逃。但高攀龙的祭文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个挟持县令逃生的故事。
高攀龙的用意,是想借甲子元日之变,树立石有恒忠义之士的形象,达成挽救士风之期待。他全文的后两节,便是围绕石有恒之“义”与某些官员之畏死而展开叙事,所谓“今天下万姓膏原野,其初起于一人畏死,委而弃之,以成大难”之语,就是将江南官员石有恒与山东官员余子翼对举,以彰显江南士大夫对秘密社会的警惕性之高,以及遇变而殉的大义与大智。天启二年(1622)徐鸿儒的白莲教起义(12)有关起义过程,可参见《平徐鸿儒(附王好贤、于弘志)》,《明史纪事本》卷六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首个攻打之地为山东省郓城县,此时,余子翼为此县县令:
山东白莲教逆党徐鸿儒、于文启,攻郓城,破之,知县余子翼逃于汶上,贼杀其二子,并典史。先是钜野县有白莲贼,杨子雨兄弟各倡异教,曹州亦有李太、张世等,聚众千人,持挺拒捕,具已就擒,而余党未散;钜野复有教首徐鸿儒,号众数千,径围魏家庄、郓城县,又有教首于弘忠,纠党千余围梁家园,梁家园距县二十里,县官新任,不知设备,城上无人固守,贼至城,四门举火,城中亦举火,满路皆红巾,杀人如草,戴红巾者皆是白莲教所暗伏死党之人也,里应外合,知县逃去,城陷。(高汝栻:《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录》)(13)(明)高汝栻:《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录》卷十一,明崇祯九年(1636)刻本。
《大明实录》只记载了官员上疏要求严惩余子翼。相较之,在《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录》中,还能看到具有些许“同情”之色彩的理由:“县官新任,不知设备”。也就是说,余子翼是郓城县刚上任的新知县。巧合的是,在石有恒赴任长兴县令前,上一任的长兴县令恰恰就是余子翼。《长兴县志》记载:余子翼,万历四十七年(1619),赴任长兴县令;石有恒,天启二年(1622),赴任长兴县令(14)(乾隆)《职官》,《长兴县志》卷七。。事实上,在高攀龙写给后来的东林六君子之一的魏廓园的一封信中,他便明确表达了这一用意:
此良吏所以为保障也。门下为贵乡,当特题一疏请优恤,最可鼓天下靡靡怕死者。(高攀龙:《与魏廓园·四》)(15)(明)高攀龙:《与魏廓园(四)》,《高子遗书》卷八下,崇祯五年(1632)刻本。
他建议魏廓园为石有恒请优恤,认为石有恒如能获此优恤,则此结果本身,可鼓舞明廷士大夫的忠义之气,尤其是那些“靡靡怕死者”。
总体来说,甲子元日之变,只是一个私仇引发的谋杀而已,所谓的隐谋性,则是东林党人集体“制造”出的一个“假象”。这一“制造”,就直接目的来看,是为了助力东林党人石有恒能够获得“优恤”;就引申目的而言,则掺杂有因山东徐鸿儒白莲教起义、湖州叶朗生之变而牵引的无意识的过度紧张,如丁元荐、姚希孟等担忧的是整个江南的安全性,而高攀龙则还附加了借此来鼓舞士人持守忠义气节的期望。
当然,如何定性长兴甲子元日之变,将其政治价值发挥得更大,也成为东林党人这一“制造”的一部分。
天启四年(1624)的政局,东林党与魏忠贤党的斗争已然白热化,且东林党人危机四伏,而如何借甲子元日之变将东林党的政治力量扩大,这与如何给甲子元日之变定性紧密相关。
事实上,甲子元日之变成了助力丁元荐被起用的重要事件。天启初,许多东林党人被起用,但却一直将丁元荐“格于例”“不召”。据《大明实录》,从天启二年(1622)正月,东林党人就持续上疏,要求“录用清议名贤丁元荐”(16)《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十八。:
天启初,大起遗佚。元荐格于例,独不召。至四年,廷臣交讼其冤,起刑部检校,历尚宝少卿。(《明史·丁元荐》)(17)《明史》卷二百三十六,列传第一百二十四,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朱国祯亦言:
甲子元日之变,时方四鼓,……凡三日,始小定,意气自如。有归功者,曰:“吾何忍以地方大祸博此名?”是时岁在甲子,已有赐环之命。(朱国祯:《明故奉直大夫尚宝司少卿慎所丁公墓志铭》)(18)(明)丁元荐:《尊拙堂文集》卷十二,清顺治十七年(1660)丁世浚刻本。
丁元荐有自谦之语,但朱国祯的“有归功者”,也说明了当时展开着“归功”的政治运作。是时,霍瑛所上呈的《时事可忧疏》(19)(民国)《马邑县志》卷三,民国七年(1918)铅印本。,更是借甲子元日之变,两度力荐起用丁元荐。终于,至天启四年(1624)四月,丁元荐起刑部检校(20)《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四十一。,天启四年六月,升为“尚宝司丞”(21)《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四十三。。
总之,从“鼎革之际”到天启五年东林党祸大作,尤其是在形势严峻的天启四年,借助甲子元日之变,东林党人一直在试图荐举丁元荐。惜乎,就时局而言,“比东林险穽,公(按,丁元荐)一起一仆”(22)丁元荐:《尊拙堂文集》卷十二,清顺治十七年(1660)丁世浚刻本。,丁元荐于天启年间再被起用,然尚未发挥作用,魏忠贤一党已然权势日炽,天启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就再次被削籍,“丁元荐……仍照察典革职回籍”(23)《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大明实录》。,而“公已病甚,又有长子之戚”(24)(明)丁元荐:《尊拙堂文集》卷十二,清顺治十七年(1660)丁世浚刻本。,丁元荐的生命之烛已燃至末端。
对于弟子丁元荐,许孚远当年曾以“刚”字称之,丁元荐虽在朝时间不长,然多年来与东林党人多通信交谈,就时局共商之,如朱国祯就曾提及:
共游敬庵许先生门之,先生以“刚”字称公,颇谓余任道欠勇。以余稍淬厉退,而得公之提醒实多。(朱国祯:《明故奉直大夫尚宝司少卿慎所丁公墓志铭》)(25)(明)丁元荐:《尊拙堂文集》卷十二,清顺治十七年(1660)丁世浚刻本。
刘宗周更言:
当是时,庙堂之上党论初起,兄首以直道见锢,退而隐于合溪之上,惓惓乎世道之忧、生民之计与桑梓之图,必于弟发之。弟因得廓其蒙鄙,以坚定其志气,出处进退,惟兄之指。林皐之业,相劝于吾浙之东西者十年。所不终以其身为小人之归者,兄赐也。(刘宗周:《祭丁慎所先生》)(26)(明)丁元荐:《尊拙堂文集》卷十二,清顺治十七年(1660)丁世浚刻本。
如上,朱国祯将丁元荐之逝世与东林党祸之烈相关联,并因而又将东林党人之命运与明朝盛衰治乱之世运相关联,因而言:“其存没关世运何如哉!”(27)(明)丁元荐:《尊拙堂文集》卷十二,清顺治十七年(1660)丁世浚刻本。其中自然充满对亡友的盛赞,但也代表了东林党上层对于其此时逝世的痛惜之情。(28)(明)丁元荐:《尊拙堂文集》卷十二,清顺治十七年(1660)丁世浚刻本。但即使在丁元荐逝世后,东林党人围绕甲子元日之变的叙事,仍然不乏政治博弈之色彩。(29)(明)高攀龙:《祭丁慎所》,《高子遗书》卷十一,崇祯五年(1632)刻本。
三、无为教与白莲教:假象催生下的想象
甲子元日之变的第三种叙事,也就是耶稣会士所听闻的石有恒是被邪恶教派无为教所杀,这是从何而来呢?实际上,还存有一种同类叙事,即被白莲教所杀。明人高汝栻所辑的《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录》中,将吴野樵称为白莲余党:
盗杀长兴县知县石有恒、主簿徐可行,随获贼首吴野樵、徐山、施立甫、石二房,及窝盗许画匠,寘之于法。有恒族人来县干谒,有恒薄待之,因与白莲余党吴野樵等结连,于除夕五鼓,乘其拜牌,执而杀之,并杀其主簿。天明,民兵渐集,贼无所徃,从县舍后逸去,随获正法。(高汝栻辑:《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30)(明)高汝栻辑:《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卷十二,明崇祯九年(1636)刻本。
天启二年(1622)五月的山东白莲教起义,使得明廷颇为慌乱,此后,明廷极为警惕地方的秘密社会。倘若发生于湖州天启二年(1622)的叶朗生之变、天启四年(1624)的甲子元日之变是白莲教所为,而东林党人要为石有恒请优恤、为丁元荐请功,却不将叶朗生、吴野樵等暴乱直接定性为江南的白莲教起义,这是不合情理的。
实际上,东林党人反复称此为“群凶之隐谋”,却未给出进一步解释,但这种“上告下诉”之法,却易诱发时人生出此种联想,即其与天启二年(1622)的山东白莲教起义存有关联。不过,就东林党人的叙事来看,直接文献中均未提及具体教派,亦可见党人手中所掌握的证据,并无白莲教之“实”,甚至连“名”都没有。事实上,在时人蒋德璟(1593—1646)的《大司寇苏公传》一文中,提到的却是叶朗生一党,最初是以“攻白莲为名”:
天启二年(1622)五月,山东白莲教起义后,叶朗生一党,最初是以“攻白莲为名”而敛财于湖州。据此,还可推知第三种叙事的另一来源的可能性。有关叶朗生,在多个文献中,他被视为天启二年(1622)发生于湖州的祸乱的党首。丁元荐记有“叶朗生之变”:
猝有叶朗生之变。朗生无赖,以医诡游缙绅间,自诧解遁术,师马道人。鼓煽嘉禾、云间、金阊诸恶少,肆言无忌。缙绅有呼为英雄者,佁子弟至倾囊或称贷,长跽而奉之,冀以免祸。朗生大喜曰:“我生尔一家”。数年前,嘉善一友人谈避世事,不佞幸苕霅(按,即湖州)(32)“苕霅”即湖州境内的苕溪、霅溪二水的并称,因而指代湖州。间有永无兵火之谶,友人曰:“鼠辈方以而郡为壑”,叩之,故曰:“起事非吴兴不可,即不幸败,由太湖遁入海,飞棹可脱也”。未几,竹林、天罡诸会,起恶少年为政,使君闻而稍稍芟薙之,不欲竟法,至壬戌(1622)难作,告密者一缙绅,迫而出首者一、二武弁,使君度事亟,挟劲卒猝缚朗生等数人,面鞫之,尽得诸不法状。朗生大言不讳,就狱犹昂首诡诸卒:“我党尚多,必有来篡取我者。”人情摇摇,二三世家挈妻子远遁,或移家舴艋,观望行止。(丁元荐:《赠郡侯杜太公祖实膺臬台新命序》)(33)(明)丁元荐:《尊拙堂文集》卷四,清顺治十七年(1660)丁世浚刻本。
丁元荐提到叶朗生通医术,且自夸掌握逃生术,在嘉兴(即嘉禾)、松江府(即云间,今上海松江一带)和苏州(即金阊)活动,当地多有游手好闲的年轻子弟跟随,且长跪而奉之,叶朗生则许此承诺:“我生尔一家”。叶朗生一党,与竹林会、天罡会存在关联,曾试图怂恿地方的无赖子弟“为政”。在最初,杜乔林只是“小治”,并未法办;然不料到了天启二年(1622),这些人竟然有了更进一步的谋划。在此序最后,丁元荐提及杜乔林的治术,“不竟法于竹林、天罡诸会也,而告密者出,正法于渠魁,而胁从者末减,乌鼠散者,置弗问,安之也”(34)(明)丁元荐:《赠郡侯杜太公祖实膺臬台新命序》,《尊拙堂文集》卷四,清顺治十七年(1660)丁世浚刻本。。可见,叶朗生就是竹林会、天罡会此类组织的党首,杜乔林则对于被迫跟随其者,予以减刑处理,对一般民众,则并未进行惩罚。
竹林会尚未见有记载,而有关天罡会,很多记载中都展现出其是一种帮会组织。《葛中翰遗集》呼为“天罡恶少”,高攀龙则有“天罡地煞打行把棍之类”(35)《高子遗书》卷七,明崇祯五年(1632)钱士升等刻本。一语,巡江御史张继孟的《江防八要》中,称为“喇虎天罡”。互参可知,“喇虎”指凶恶无赖,“打行”即“结党立盟”,实际上指的就是一种替人充当保镖、打手的行帮,这一行帮中混杂了各种地痞无赖。对于此类帮会之徒,地方官员的治理之术,则是将其“填入善恶簿内”,送官严究;同时,还要“置木扁钉其门,明书某棍某人之家”(36)(明)高汝栻:《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录》卷十三,明崇祯九年(1636)刻本。。事实上,甲子元日之变的窝藏犯朱无赖就曾被处以此惩罚:(37)参见(康熙)《长兴县志》卷四《弭盗》,(乾隆)《长兴县志》卷二《弭盗附》。
熊令讳明遇莅任时,邑有朱元孙者,年才十四、五,令大书榜其门曰:“恶人”,后令忽某幼穉,无能为也,除之。甲子之变,元孙实为逋逃,主虽诸凶,以次就擒,而孙独为漏网。夫刑罚本以诛戮罪人,奈何因其岁齿宽其标榜,养痈贻害,不可叹哉!(《长兴县志·弭盗》)(38)(康熙)《弭盗》,《长兴县志》卷四。
朱无赖在其十四五岁时,就已被长兴县令熊明遇施以此惩,后人在感叹甲子元日之变时,还曾遗憾当年这一惩罚未严格执行。实际上,到了清代,这一组织仍是一种帮会性质。直至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清廷正式审查江西宜黄县的天罡会,据审查结果来看,此地天罡会仍为帮会性质,所供应之神为“天罡星神”。所谓天罡星神,属于中国民间固有的信仰体系,并非新生之异神或异教;同时,就《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三的审讯实录来看,这些帮会虽有所祀之神、所抄道经,但“并无符呪经谶”(39)《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三,清内府钞本。,可见直至清代嘉庆年间,天罡会的宗教色彩并不浓,仍只是一种帮会性质的地下社会。
丁元荐说“朗生无赖,以医诡游缙绅间,自诧解遁术,师马道人”,蒋德璟则记叶朗生师从“马文”,“马文”即“马文玄”。此外,还有两处文献提及的是“马文元”与“马闻玄”,不过两者实则一人而已,“”“元”皆为讳康熙帝玄烨之“玄”而改,“闻”则为错写。而丁元荐等人说叶朗生师从马道人,这也可能是“白莲余党吴野樵”这一说法的来源之一。明人方孔炤所辑的《全边略记》中,又唯一一次出现了对吴野樵等人身着“白巾黄袴”的描述:
(天启三年1623)十二月三十日,浙江有白巾黄袴贼数十人,乘夜入长兴县。(方孔炤辑:《全边略记》)(40)(明)方孔炤辑:《全边略记》卷十一,明崇祯(1628—1644)刻本。
当时的直接文献均未提及着装,方孔炤这一说法可信性极低。不过,马道人以及白巾这两个信息,却易使人联想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发生于湖州的以马妖道为首的“白包巾之变”。据《乌程县志》所记:
(嘉靖)三十六年,有白包巾之变。马妖道匿霞雾山中,倡白莲教惑众,皈依者伪授职衔,即识白包巾为号,蒋鹏等克期四起,内外响应,九月十四日也。十二日,乌程邬采密报主簿田本渭,闭城收捕,人情汹汹。乡官唐枢亟令开门,以消内激之变;且决策安抚为上,勦捕次之,生擒为上,斩首次之。自是胁从者稍解,贼首蒋鹏尚收余党屯乌镇。军门檄府督同千户苏金、蔡懋恩、李钺擒之。唐公痛民之信佛堕愚,特请于官,鞫之,释所获百余人。(《乌程县志》)(41)(明)《乌程县志》卷四,明崇祯十年(1637)刻本。
嘉靖三十六年(1557),有一马妖道,在湖州乌程县山中传白莲教,这一组织举事时,以头裹白巾为号。当时参与处理此变的则是湖州大儒唐枢(1497—1574),即许孚远的老师。《乌程县志》将马妖道记为白莲教。明人徐復祚的《花当阁丛谈》则载道:“马道士者,愚民所称马祖师者是也。”(42)(明)徐复祚编:《花当阁丛谈》,清嘉庆刻借月山房汇抄本。可见,嘉靖年间的白包巾之变的党首马道人、马祖师、马妖道,就是同一人。马道人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秋,曾活跃于苏州、常州等地,后来或还前往了杭州传教,最后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秋,于湖州府乌程县山中传教,传其精通盆水照影之术,江浙之地中,湖州信徒最多,且多有士大夫崇信之。田艺蘅将马道人所倡之教归为白莲教:

田氏补充了马道人之后的“踪迹”,似乎马道人前往广西传教了,照此来看,马道人传教的地域极广,未知是否确实。无论如何,“马道人”已然成为某种妖术的象征符号。在清人查继佐《罪惟录》的《马祖师》一节里,其他所记皆与明代文献相同,但第一次出现对嘉靖年间的马道人的妖术的溯源,可视为对于嘉靖年间的马道人被传为白莲教的解释:
马祖师者,不知何许人,传正德中妖贼李福达之术,以盆水照影,文武冠带男女具备,马即因其影,署官爵大小高下不等。走愚氓,即士大夫家子弟,往往惑之。(查继佐:《罪惟录·叛逆列传·马祖师》)(44)(清)查继佐:《列传》卷三十一,《罪惟录》,四部丛刊三编影手稿本。
也就是说,嘉靖年间的马道人用来惑众的妖术,与李福达的妖术相同。《罪惟录》只提到了盆水照影之术,据《大明实录》天启三年(1623)九月的一则记载来看,自永乐时,剪纸人马就被认为是白莲教的象征:
永乐时,山东蒲台县妖妇唐赛儿,聚众作乱,自称佛母,能剪纸人纸马相战,旋即破灭;近日,山东妖贼徐鸿儒,亦以白莲伏诛;此皆借神说以倡乱者也。(《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45)《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三十八,《大明实录》。
首先,天启年间的这位“马道人”,必然不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就已在江南倡教的马道人(马祖师)。假设马祖师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时三十岁,叶郎生之变时(1622),马祖师则已近百岁老人,不可能还”挟“人逃亡。当然,可能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湖州一地一直存在着嘉靖年间的马道人的教派组织,一直绵延至天启年间,叶朗生一党即属于此教派。不过,这一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实际上未看到任何文献提及嘉靖年间的白包巾之变与天启年间的叶朗生之变有直接关联。如上曾述,倘若可以将吴野樵上溯到叶朗生,又能再次将叶朗生上溯到嘉靖年间的马道人,并将其定性为白莲教,那么这样的一种叙事,将使得叶朗生、吴野樵一党的危害性陡然上升,尤其是在刚刚才结束的天启二年(1622)的山东白莲教起义后。但是,就天启年间这两“变”的一手文献来看,无论是叶朗生之变,还是甲子元日之变,均未看到白莲教三字。此外,亦未有文献对叶朗生一党的宗教活动予以描述,亦未提到此派的宗教观念、宗教体验以及宗教制度。当然,以一种现代的宗教定义去衡量明代的叶朗生一党是否属于宗教,可能存有一定武断性,但是,至少不能将其直接等同于白莲教。实际上,就研究明代宗教的荷兰学者田海(Barend ter Haar)的《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来看,在明、清历史上,民间的妖术现象以及各类民间宗教,往往容易被统一概之以白莲教之“名”,而往往并无此“实”(46)[荷]田海著,刘平,王蕊译,《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其实,在许大受的《圣朝佐辟·自序》里,许大受曾提及“西吴赤子之危”一事:
辟者何?辟近年私入夷人利玛窦之邪说也。何言佐?草茅凉德,不敢主辟——而目击乎东省白莲之祸与吾西吴赤子之危,念此邪徒祸危实甚;而窃儒灭儒,人所叵测,日炽一日,靡有底归。(许大受:《圣朝佐辟·自序》)(47)[法]梅谦立、杨虹帆校注,赖岳山校核:《〈圣朝佐辟〉校注》,高雄:佛光文化,2018年,第82-83页。
据年信来看,作者在邻县官员被杀后将适时已完成的此著上呈,可见此著完成于长兴甲子元日之变前。而据许大受将“西吴赤子之危”记于“东省白莲之祸”后,即西吴赤子之危发生于天启二年(1622)五月后。所以,“西吴赤子之危”指的就是1622年听闻山东白莲教起义后,在湖州作乱的叶朗生一党,这也就是刘宗周笔下的“苕溪有叶朗生之衅”(48)刘宗周著,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85页。,“苕溪”“西吴”皆指湖州。而许大受此述,亦传递出两个信息:一是西吴赤子之危与东省白莲之祸并非同一性质;二是西吴赤子之危亦具有“邪说”“邪徒”之因素,即存在妖术惑众等行径。前曾提及,天罡会等帮会亦有所祀之神,而“天罡”一词,也常出现在道教相关的文献中,所以,叶朗生一党是否是无为教呢?
有关无为教,许大受在《圣朝佐辟》中曾提及:“慨自罗祖、白莲、闻香等妖辈出,而男女以混而混。”(49)[法]梅谦立、杨虹帆校注,赖岳山校核:《〈圣朝佐辟〉校注》,高雄:佛光文化,2018年,第138页。所谓“罗祖”就是指无为教,其创始人为罗清(1442-1527),后世信徒尊称其为罗祖、无为教祖、无为居士、无为道人等。罗清本人的宗教思想体现在《罗祖五部经》(又称《五部六册》)中,卷三批判白莲、弥勒等为害人邪法。专门研究无为教的学者濮文起指出:“到万历年间(笔者注:1573-1620),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无为教教义思想体系,这就是以无生老母为最高崇拜,以真空家乡为理想境界,以龙华三会与未来佛即弥勒佛为信仰核心,主张三教归一,注重内丹修炼,以及规范化的入教仪式等。”(50)濮文起:《明代无为教与其教义思想简论》,《贵州大学学报》第26卷第2期,2008年。僧界与明廷,对无为教则皆持否斥态度。万历初期,佛教高僧云栖祩宏、憨山德清、密藏道开等都曾斥责无为教义,如密藏道开曾言,“此其教虽非白莲,而为害殆有甚于白莲者乎”(51)(明)密藏道开:《藏逸经书标目·五部六册》,《大藏经补编》第14册,蓝吉富主编,台北:华宇出版社,第444页。。明廷亦持禁教态度,万历四十三年(1615)六月,礼部上疏《请禁左道以正人心》,“有罗祖教、南无教、净空教、悟明教、大成无为教,皆讳白莲之名,实演白莲之教。有一教名,便有一教主。愚夫愚妇转相煽惑”(52)《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五百三十三。。可见,无为教在万历年间的发展,曾被认为与白莲教“名异实同”。
不过,耶稣会士所传闻的是被邪恶教派无为教所杀的这一叙事,则未见有任何文献可以支持。这种叙事的源头,也许可以追溯到如下之说:如传闻吴野樵为叶朗生一党,而叶朗生所师的马文玄,又被称为马道人,“道人”一词,则可能使得其易与无为教相连,如无为教主罗清就被称为无为道人;又或因无为教曾一度反白莲教,因而叶朗生一党“以攻白莲为名”的行为,便被有人传为是无为教。此外,耶稣会士的年信中,没有必要讳白莲教之名,这其实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民间并未传闻叶朗生、吴野樵一党是白莲教。
可见,东林党人集体制造出来的甲子元日之变的“假象”,很可能又借助了吴野樵的叶朗生背景,进而是马道人背景,催生出一种想象,这一想象最终在耶稣会士那里,则传为甲子元日之变是无为教所为,在高汝栻那里,则传为是白莲教所为。
四、“借剑时欲斩妖狐”:许大受献《圣朝佐辟》
许大受正是在上述集体制造出的假象与想象中,将他刚刊行不久的《圣朝佐辟》,上呈给了德清县令。事实上,天启年间的明廷,险象四伏。仅就丁元荐在谈及天启二年(1622)的叶朗生之变时所言,就可一窥天启初的明廷局势,以及东林党人极其紧张的缘由:
不佞近过金阊,谒一尝事者,卒问叶朗生事,云:“何微”,意以为发之似骤也。不佞默然久之曰:“旁发而滋蔓,不时扑灭,无论淮徐、邹鲁、黔、蜀之变,即曩者汤毛九、江天祥狂竖子,尔钩连株引,谁任其责!”当事者唯唯。未及返棹,齐庶人变,又突发于毘陵矣。此中正人及大老,岌岌乎不能安枕,当事者又何以弭之。杜使君宽猛互调于局外,定有深心,非皮相者所能窥。(丁元荐:《赠郡侯杜太公祖实膺臬台新命序》)(53)(明)丁元荐:《尊拙堂文集》卷四,清顺治十七年(1660)丁世浚刻本。
江苏、山东、贵州、四川先后有变,又有汤毛九、江天祥之乱,湖州又起叶朗生之变,紧接着,常州(毘陵)又起齐庶人之变。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李应升(1593-1626)在所上一疏中记有:“哀怨之气,上通于天,大江南北连省通圻所在以地震告,盗贼既作,水旱随之,倘复有徐鸿儒、叶朗生、史八舍、陈鼎相之徒,一呼而起,实可寒心。”(54)(明)李应升:《缕诉民隐仰动天心乞实行宽恤以固邦本疏》,《落落斋遗集》卷一,明崇祯间刻本。然而,这些都还只是内忧而已。事实上,就在不久前,努尔哈赤的铁骑早已令明廷极为慌乱,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二到三月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以近六万人大败明军二十万人,此战关乎明与清之存亡,乾隆就曾称此战为“大清亿万年至丕基业,实肇乎此”(55)(清)《胜迹略》,《抚顺县志》(不分卷),清宣统三年(1909)铅印本。。许大受在《圣朝佐辟》中,就流露出“杀奴哈赤”之强烈愿望(56)[法]梅谦立、杨虹帆校注,赖岳山校核:《〈圣朝佐辟〉校注》,高雄: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8年,第118页。。“奴哈赤”即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1626)。在天启四年(1624)甲子元日之变后的这封上疏中,霍锳便说“外患内忧一时并烈,天下岌岌乎有瓦解之势矣”:
今天下大患,莫过于夷狄、盗贼两者。夷狄目建酋(按,“建酋”即努尔哈赤)发难以来,东西交讧,旋伏旋张,迄无宁日,以至于今,且非如向者,志在抢掳图饱谿壑而已也;改元建号,略地攻城,目中已不复知有中国!盗贼自白莲煽祸而后,南北相应,旋灭旋起,迄无宁宇,以至于今,且非如何者,志在货财,鼠窃狗偷而已也;称王称帝,建将设官,目中已不复知有君父!甚至今日,贵州以截虏抚臣报,长兴以戕杀县官报,外患内忧一时并烈,天下岌岌乎有瓦解之势矣!(霍锳:《时事可忧疏》)(57)(民国)《马邑县志》卷三,民国七年(1918)铅印本。
当今天下之势,“目中已不复知有中国”“目中已不复知有君父”,与霍锳等东林党人的担忧相同,许大受的《圣朝佐辟》,亦是就中国与君师之存没而作:
夫堂堂中国,岂让四夷?祖宗养士,又非一日,如能为圣人、为天子吐气,即死奚辞?(许大受:《圣朝佐辟·自序》)(58)[法]梅谦立、杨虹帆校注,赖岳山校核:《〈圣朝佐辟〉校注》,高雄: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8年,第82-83页。
但与霍锳等所担忧的夷狄与宗教的对象不同,在许大受的认知中,他认为天主教这一“夷”之危害,远胜过中国历史上曾出现的所有“夷”与“妖”,且兼具“蛮夷”与“魑魅”之“两毒”:
嗟嗟!周之猃狁、汉之冒顿、唐之突獗、宋之女直,夷氛虽恶,天下尚知其为夷。蚩尤之雾、胜广之狐、黄巾之占风、白莲之诅社,妖祸虽煽,天下尚知其为妖。唯此一邪流者,直谓三五不足尊、宣尼不足法、鬼神不足畏、父母不足亲,独彼诳邪为至尊至亲、可畏可谄;是以新莽天生之狡智,肆蛮夷、魑魅之两毒者也。(许大受:《圣朝佐辟》)(59)[法]梅谦立、杨虹帆校注,赖岳山校核:《〈圣朝佐辟〉校注》,高雄: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8年,第160-161页。
就湖州一地的社会管理而言,地方儒者唐枢、丁元荐,是以直接参与地方的治安实务为径,与之不同的是,许大受则呈现了一种思想论战的路径,即从思想层面予以条分缕析,之后则刊行此书,并选择甲子元日之变这一时机,将此书上呈官方,以期影响德清乃至整个明朝的天主教活动。相应而言,在思想史的长河中,许大受的《圣朝佐辟》则将持续产生着思想本身应有的价值,这从明末的反教运动,即崇祯十年(1637)出版的八卷本的《圣朝破邪集》将《圣朝佐辟》收入且独作第四卷,便为一证。
以上,各种思想(含信仰)力量、政治力量,在天启年间展开着博弈,人斗之时,天灾(旱灾、地震)随附之,江南便开始流传明廷已生“季世之象”。在天启四年的上疏中,周忠愍写道:
江南祖宗陵寝之地,财赋数百万所出之区,此地安危,天下治乱之候也。而今日天时人事有大可忧者,江左不素尚风流重儒雅乎?近乃好谈兵语乱伏。睹皇上锐意求治,臣等方以为是中兴之象;而左道妖言狂妄不逞之徒,见边事尚急,派征无艺,且曰是季世之象,偏袒而奋白梃之秋也,转相愚惑,遂渐构逆萌,虽各各就捕,而余党岂尽消灭?臣即条教与刀锯并行,未便回心向道,不可不谓人心之变也。
又去岁七八月,忽旱,垂黄之颖转为半实之穗,棉花则半颗不结,而岁征布缕,皆谋转鬻于中州;各河道处处干涸,即孟河、太湖之间,素汪洋澎湃,且枯涩不可行舟。货物柴薪一时涌贵,父老皆以为百年未见之异。……有此二变,而地震随之,臣等又虞其召灾于将来也。震后不十日,而浙之长兴遭大盗惨变,此亦其征应也。(60)(明)周忠愍:《周忠愍奏疏》卷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由上可见,以天启年为核心,后金铁骑、各种形式的起义、天灾与党争,以一种共发之态浮出水面。以上,借天启年间发生于湖州的叶朗生之变与甲子元日之变,可一窥许大受完成、刊行以及向官方上呈《圣朝佐辟》时的历史背景。而在这一历史背景中,许大受亦具有特殊的个体背景。
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庚申(1620),即天启元年的前一年,许大受家乡德清县建立了天主教的住院,且是湖州府的第一个住院。法国汉学家荣振华(Joseph Dehergne,1903—1990)在出版于1973年的RépertoiredesJésuitesdeChinede1552—1800(《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有《明末(1644)中国基督徒分布图》一篇,记录了明末的住院情况,所谓“住院”,即“属于传教区所有的一所房子”,“所有住院都拥有一个教堂或祈祷室”,其中浙江的“住院”情况记录如下:
杭州于1611年创建住院,富阳于1642年,仁和于1608年创建住院。
(湖州),湖州的德清于1620年。
(嘉兴),高山于1640年,塘栖于1642年,崇德(石门)于1629年,桐乡于1615年(?)。
金华于1644年之前为住院(1645年没有提到)。兰溪于1642年(后来于1656年成为多明我会士的住院),东阳于1628年。
宁波(1650年左右?)于1638年,五井村于1628年,定海于1642年,慈溪于1637年。
绍兴于1586年。
温州于1646年,瑞安于1638年。(荣振华,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61)[法]荣振华,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855页。
荣振华统计了浙江七个府创建“住院”的情况。据此,德清应该是湖州府第一个拥有教堂或祈祷室的县,同时,这也说明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德清的天主教发展已成一定势力。
明熹宗天启二年壬戌(1622),据丁元荐的《祭许太夫人》(62)(明)丁元荐:《尊拙堂文集》卷十一,清顺治十七年(1660)丁世浚刻本。、茅元仪的《上朱嘉兴相公书二(壬戌)》(63)(明)茅元仪:《上朱嘉兴相公书二(壬戌)》,《石民四十集》卷六十,崇祯刻本。和《上邹南皋总宪书(三)(壬戌)》(64)(明)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七十一,崇祯刻本。,许大受独自一人往返数千里,从德清前往北京,为以其父大儒许孚远为核心的许氏家族争取荣誉:
兹启敝郡许恭简公敬菴先生,其道德抂天壤,仪范抂人心,品行抂相公之藻,鉴今其长君以补赠、请谥二事走控明庭。(茅元仪:《上朱嘉兴相公书二〔壬戌〕》)(65)(明)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六十,崇祯刻本。
明熹宗天启二年壬戌(1622)五月,山东徐鸿儒白莲教起义。
明熹宗天启二年壬戌(1622)六月,许大受被准赠“承荫注选”:
天启二年六月……命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顾秉谦、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周如磐,具教习庶吉士。准赠南京兵部尚书许孚远男大受承荫注选。(《明熹宗哲皇帝实录》)(66)《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二十三。
此年六月,许大受准赠“承荫注选”,这意味着许大受至少在六月前已抵达北京。准赠后,他应该还需要在北京停留一段时间,接受这一注选程序。也就是说,天启二年(1622)六月后,许大受有可能仍在北京居住过一段时间。或正因这一年往返南北的经历,可推导出他后来所写的“目睹东省白莲之祸”之“目睹”,应并非一虚词。
明熹宗天启二年壬戌(1622)五月徐鸿儒起义后,许大受的家乡湖州生“叶朗生之变”,其以“攻白莲为名”举事,告密者出,叶朗生一党被抓。
明熹宗天启三年癸亥(1623),许大受母舒氏去世。此年七、八月,江南大旱,作物不结,河道干涸,被认为是“百年未见之异”,十二月,又“地震随之”。
明熹宗天启四年甲子(1624)元日,姻亲丁元荐所在的长兴县的知县、主簿被杀,“(地)震后不十日,而浙之长兴遭大盗惨变”。与此同时,关于官员被杀的各种“真相”流传于坊间。值此,许大受将《圣朝佐辟》上呈给德清县知县。许大受逝于明亡不久,乱离之际,惜其墓志铭未见,不过,在丁元荐墓志铭中,朱国祯言道:
借剑时欲斩妖狐,报国可判老头颅。仕涂偃蹇色常愉,讲道问业德不孤。长虹吹气何昭苏,乾坤不毁有吾徒。(朱国祯:《明故奉直大夫尚宝司少卿慎所丁公墓志铭》)(67)(明)丁元荐:《尊拙堂文集》卷十二,清顺治十七年(1660)丁世浚刻本。
不妨说,东林党人借长兴甲子元日之变所进行的政治操作,许大受借此上呈《圣朝佐辟》的举动,都可借“借剑时欲斩妖狐,报国可判老头颅”(68)注:“借剑”一词,原指廷臣犯颜直谏,请诛奸邪,不过,本文此处则均借用其字面意;“判”通“拼”,指的是甘愿舍弃。一句来理解。虽然二人试图斩的“妖狐”不同,但甘愿抛颅洒血之心却可相通。作为许孚远门生的丁元荐,以及作为许孚远哲嗣的许大受,此二人皆无愧于先人,用朱国祯评丁元荐的话来说:“遇夺朱者,片语挂角,听者皆竦,盖始终不愧师门云”(69)(明)丁元荐:《尊拙堂文集》卷十二,清顺治十七年(1660)丁世浚刻本。。
长兴甲子元日之变,作为一个地方官员的被害事件,竟有着三种不同的叙事,厘清真相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借此可一窥晚明天启年间多番力量间的隐秘的角斗。从考察儒生许大受与来华传教士间的文明之争切入,发现《圣朝佐辟》上呈官方的时间点背后的故事,而有关此“变”的官方叙事的成立,则又关涉到东林党与魏忠贤党间的政治斗争。一个地方性的案件最终牵扯着明廷上层的权力搏斗,东林党人试图借此扩大东林党的力量,削弱阉党的势力,以实现东林党人的政治理念;东林党首高攀龙还试图通过强调石有恒的“致身惟义所安”,以羞煞天下靡靡怕死者,达到挽救士风之期望。而这场斗争的社会背景,顺着时间线上溯,则又充斥着各种民间思想、宗教运动,如白莲教、无为教,包括帮会性质的天罡会等。在近四百年后的今天,这类争斗不仅未熄火,甚至可以说正式拉开了序幕,亨廷顿将其称之为“文明的冲突”。无论是中西文明的相遇,还是一种文明内部的多种宗教文化间的相遇,都亟待从它们的最初相遇开始认真考察,而考察《圣朝佐辟》上呈官方的背后的故事,也提醒着我们,在每一场文明之争的背后,往往又隐藏着多番力量的共时角斗。
----论戴·赫·劳伦斯的哲学随笔《天启》的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