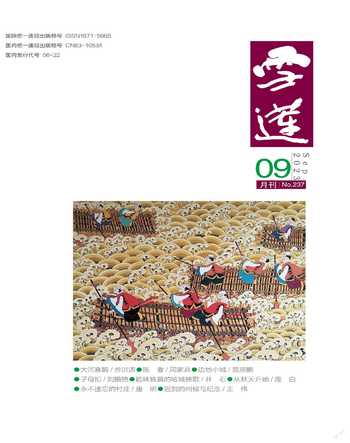边地小城
【作者简介】黄恩鹏,满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十月》《人民文学》《青年文学》《中国校园文学》《天津文学》等刊物发表非虚构散文和小说等。著有《到一朵云上找一座山》《撒尼秘境》《边地笔记》《阳光陪伴成长》《过故人庄》《时间的河》等作品。获全国文学奖励多种。现居北京海淀。
勐 烈
夜幕归还给了勐烈镇。勐烈河畔,华灯初上。夜赋予了树木神秘感。河道两岸有浓郁的潮湿气息,空气中弥漫着水、植物和青苔的味道。
沿着勐烈河散步,走累了,就坐在河边的石凳上看对岸山坡上的小房子。这边岸上不远,一个小伙子蹲在一块石头上“拍鱼”。他左手拿着一个电筒照着河面,右手拿着一个小木棒,看见水中石片上活跃跳动的小红鱼,就用小木棒拍一下,快而准,力道拿捏得恰到好处。他的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小网,其实就是一个小笊篱,是细铁丝网子,其手柄是以一小节竹竿做成的,把木棒拍晕了的鱼,用小网捞上来。他不停地拍,看来鱼不少。石头发出啪啪啪的清脆声响,就像山雀凿着树干的声音。有的小鱼,被拍出了血,直接昏迷或者被拍死。小鱼与小蟹有趋光本能,见到光亮,从石缝里游出,停在亮处不动,极易捕获。一个小时光景,弄到小半盆儿,端回家,挤肠除泥,清洗干净,加几根酸笋、两片黄姜、两根小葱,上灶煮汤,汤煮好,加点儿小雀辣子,开胃下饭。
十多年前,我在江城县城见到坡坝之上古朴的农房,也在东边的农田里看到普通的村落,宁静,简陋,是那种吊脚楼,不比山上的房屋大多少。那一天,我坐在勐烈河北岸,看南山坡的农人们劳动归来的情境。我在那里一坐就是一个下午。从午饭后我就坐在那里,树荫下的凉爽和惬意,那是很少有的舒适了,何不多呆上一段时间,与其回到闷热的宾馆,真的不如呆在这里。全是植物,连河岸之上也生有大片大片的密匝匝的灌木。一些树根从土壤里裸露了出来,青筋般突出,河岸有原始森林的感觉。那是二月份,天气最舒服的时节,没有蚊虫也没有甲壳小虫,偶见几只背负着厚重大壳的蜗牛(与内地所见的螺旋形小圆状蜗牛不同),抻着柔软脖子和带着触角的头,慢慢从眼前落叶爬过,留下了一道道不太清晰的湿润水痕。凌晨下了一场小雨,所有植物叶子上还有雨水,阳光下闪烁着光泽。所有植物干净整洁,路边也没有车辆过往时旋起的尘土。
我用高倍相机镜头将对岸的房屋拉近,看见青白屋檐之下,农具应有尽有。农人下田劳动,带上自制的密眼小网,歇活时,挽起裤脚,进入溪涧,网几尾小鱼,捉几条水蜈蚣,掏几枚小田螺,装入塑料袋儿带回家。一些农人即便从乡下搬到了城区,闲暇的时候,也要到桥下溪边,捉几尾小鱼,回家煲汤。
用这种方式捕杀小鱼,毕竟残忍。有些小鱼会破碎。也因此拍打小鱼力道要刚刚好。大概小鱼游得太快,一瞬间,就钻入了石头片和石头块下面,尤其在水中,像一枚枚快速飘转的树叶,在水下游来窜去,如不细察,极易被忽略。用小网拍鱼,速度要比小鱼的反应快,才能成功。小鱼儿太小了,不能等长大再捕吗?我问。
这种小鱼儿已是最大的了。在这种溪沟里,全是石缝鱼,长不大的。最大的,有小手指头粗细,生于溪水里的草根下。繁殖极快。还有更小的马糠鱼,筷子粗细,就一小条儿,还像铅笔头儿。与小红鱼、花尾巴鱼比,肉质粗硬,挑出来,喂猫喂鸭喂猪,还可以送到小饭店,曬成小鱼干,煎炸,也挺香脆。他像似对我普及鱼的知识,耐心跟我说着。
李仙江沿岸有许多与山连接的箐沟,远远看,就是密密麻麻的褶皱山缝。这种箐沟是干净的,留不住树叶和杂草,因为水流湍急,许多落叶和杂草,只能随着江水流到和缓处,然后冲上滩涂。一些柴木被渔人收走燃火填灶,或堆在岸畔供夜宿的渔人升火烧饭。先前有渔人图省事儿,弄一些竹片,编成一道坚固的“挡鱼坝”。江水湍急时,大鱼被激浪冲到这里,猝不及防,被坚硬的竹片撞破了背脊,擦烂了尾鳍,死亡了许多鱼。江岸之上,经常遇见被撞死、被擦碰的半死大鱼。发大水时候,江滩之上,到处都是死鱼。有的鱼,在江水退位时,挂在了树杈之间,就被天上的绕鹰、雀鹰和鸦鹊们吃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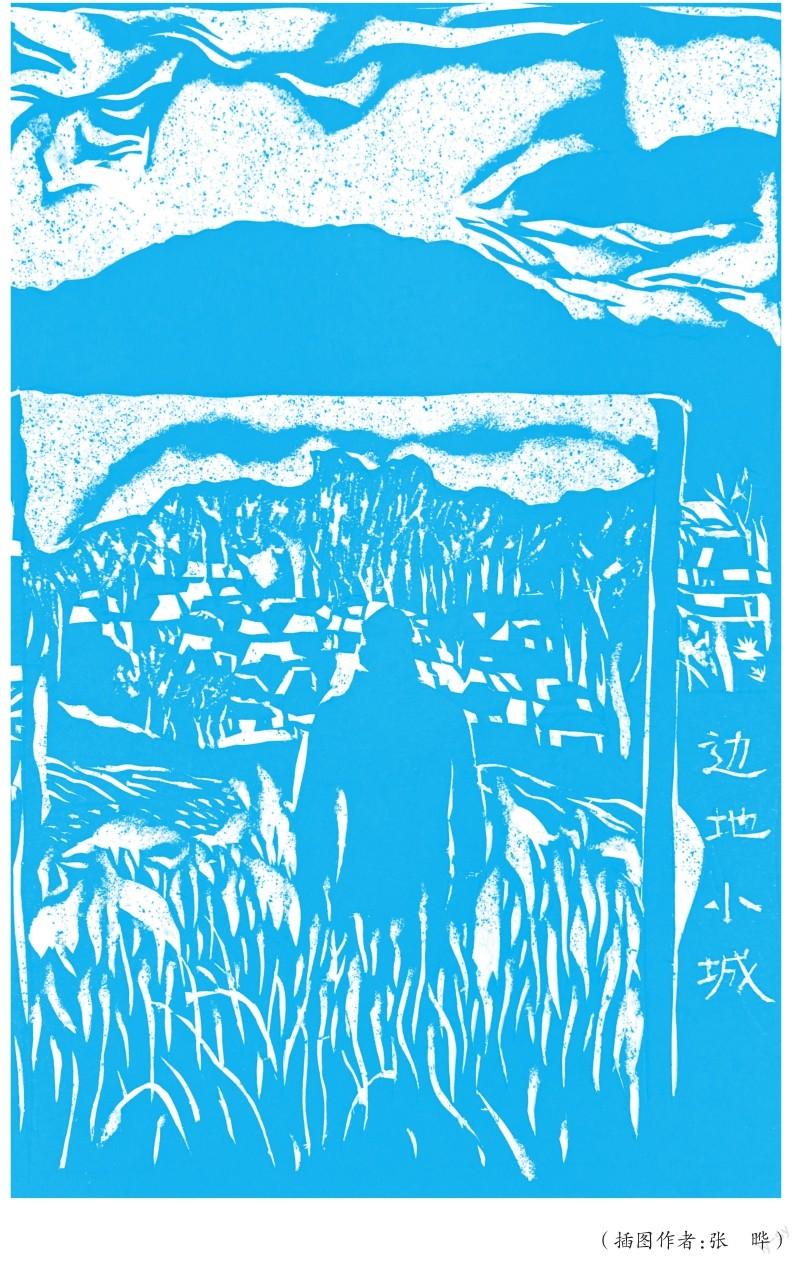
农人不吃遗留在滩岸上的死鱼。撞死在滩岸的鱼,肉里面有沙子,不新鲜了。再大的也不能吃。留给山林里的鸟儿们吃,或者给大兽小兽们来吃。过去,用硬竹片编成的挡鱼坝,是一种非常省事儿的获鱼工具,却极具破坏性,也给生态带来了污染。后来禁绝了。
太阳偏西的时候,到达了普洱市江城县城所在地勐烈镇。打了个的士,到以前住的金一水酒店。这个酒店的对面是一座中学的大操场,视野开阔,能看见对面青山的一大片茂盛的竹子,很是不错。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换了一件干爽的衣服,与同伴老钟到街上找车。
街上的车子很少,最后终于找到了一辆。司机是一位黑汉子。我说要去瑶家山那里,司机有些吃惊,说这个时间去瑶家山,今晚恐怕回不来了吧。他好心建议我们,明天一早去瑶家山为好。上午去,下午就能返回县城。
真的那么远吗?老钟说,怕啥啊,去看看嘛。他以为司机不愿意拉我们。司机看出来我们的想法。说,你们这个时候,到瑶家山,到了就黑了。我自己倒是不怕,开车能回来,也是赚钱呢,有钱不挣,何必不拉?就是觉得,那里山谷没有住宿地方。晚了,无车,真的回不来了。一般情况,都是上午早早出发,下午这个时间,路上有车,能够返回。
司机很直率。
那么现在,我们又能去哪儿转转呢?司机说,可以在县城转转啊。他向我们推荐了县城西边刚刚开发了不久的一块湿地。不收门票,去湿地看看,也未尝不可。老钟一听湿地,来了精神。问是否有鸟儿?司机说,鸟儿,多的是。早上最多。晚上也有。三只老鹳在那里住的,不怕人,江城所有人都认得它们。这位司机说老鹳,就像说家里来了三个亲戚似的。
司机将我们送到了城西湿地。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湿地,水泽清澈,草木碧翠。找了半天,却未见到三只老鹳。倒是见到一群白鹡鸰和一群栗头雀鹛。当然了,大白天的,自由自在的老鹳们,绝不会在那儿傻傻等着我们,或许早飞进了附近山林深处觅食去了。这让专门来此拍摄鸟儿的老钟有些失望。为了拍摄老鹳,他将长焦镜头从拖箱里拿了出来装上机身。现在只能扛着,就像扛着一座小型钢炮。
跟内地县城相比,整个江城城内城外并不太大,甚至小之又小。但江城有江河溪涧、茶山、森林、香蕉、红米稻、玉米和中药种植园。特别是四周的森林,先天的优越环境,空气负氧离子密度高。东城西城,虽说平地面积有限,却能依河建造楼房,形成了一个狭长的城廓,从而让这个小山城,更有一种小型威尼斯之雏形。事实上,我与老钟初来江城时,纯属一次偶然的闯入。我惊异地发现,江城食材十分丰富。另一个同伴、即将到了退休年纪的老驴子非常看好这个不大的山城,果断在一个叫东城佳苑的公务员小区买了房子。他说这个边地小城,将是未来的大理、丽江。其实我觉得更有点儿像贵州黔东南的镇远。
站在后山坡观景台,可以看到小县城的全貌。
远处是老城,近处是新城。新城是以两块新楼盘为标识的。观景台有个亭子,几个男孩子在玩扑克,谁输就起身脱了上衣,光着膀子,往山坡下跑二十米,再跑上来。这种带有惩罚性的游戏,让孩子们兴奋不已,气氛一度热烈。受此感染,老钟咧开大嘴笑个不停。天气太热,我穿的高腰登山鞋,有些捂脚,汗涔涔的,也不管不顾了,脱了鞋子,让汗湿的脚,获得一点儿凉意。
老钟第一次来江城,感觉一切新鲜,他用小相机拍坡下开得正旺的野花,我倚亭子喝水嗑瓜子,看孩子游戏。输者一遍遍重复下坡跑,胜者赢了也不再欢呼,而是低头洗牌,似乎这胜利来得太容易不值得庆贺。或许是看到有两位与他们父亲一样的长者在旁有些不好意思。但他们的快乐令我们感动。这里没有嘈杂,更没有烦忧。这花草遍坡的地方,是他们的自由王国,悠然自得地玩耍,欢乐来得直接、真实。
玩累了,孩子们比赛速度,跑下山。一会儿就跑到山坡下的大街上了。山坡立即幽静。起身来到横栏前,看着远处的楼群出神,无意间,手摸到了一行凸凹的字,低头细看,是似一把小刀刻下的歪歪扭扭的字,漆下露出了白腻子粉底的字痕:
阿蜜诺,我爱你!
女孩儿阿蜜诺,彝族的一个糯米糌粑般的名字。要比内地的一些阿芳阿兰阿莲阿凤不知要靓秀多少呢。这种告白,直截了当,浪漫无比。简单的乡村爱情,胜过万语千言。刻字的,是否刚才那四个男孩儿中的一个?但从这个名字,我会想到女孩儿的美丽:黑黑的圆脸、大大的眼睛、扑闪的长睫毛、挽起的头髻、穿着筒裙的纤秀身材……是的,这里有一个女孩儿叫阿蜜诺。这里有一个深爱阿蜜诺的男孩。阿蜜诺。我从这三个字中,读到了乡野美人的意蕴,仿佛爱情小说的某一个细节。那明亮的,是盈盈飞动的雅致,心灵呈现金子般的光泽,闪烁在一个不知名的山上,像山坡山谷开着诸多不知名儿的野花,幽香、朴素、醉人。
晚餐到以前去过的一家饭馆吃。点了三个菜:辣子炒酸筋、清炒菜根儿、刺五加肉片煮汤、米饭。店家沏上生普洱茶。吃饭、喝茶。天黑了,再上山坡,看看夜景,老钟用广角相机拍。我懒得再拍,看万家灯火。山风吹来,凉凉的,拂着身体。下山,依然走去年和老驴走的勐烈河岸。看不见河水,听不见水流。这个季节并非雨季,水量少了些。边地城市江城,河流遍布,此时虽说不是雨季,但河道深宽,冬天的水,也是充盈的。
江城有许多榕树,有的还用铁架子支着,有的根部培上了土堆,那些树只是一个弯弯的树干,有的发出了嫩芽,一看就知是新栽种不久的。也许未来的江城縣城,将是一个葳蕤葱郁的榕树世界。过马路到广场。闲人寥寥,几盏灯,沉静地亮着。
老钟跑到那边拍灯柱去了,我躺在一个长木凳子上休息,仰面看着漫天星辰,闪烁着璀璨的光芒。边地的星光纯净、明亮。不远处有老人拉二胡,曲子是我熟悉的《江河水》,老人拉得很慢。老钟走过来,他买了两根甘蔗,给我一根吃。江城的甘蔗汁多,吃起来放不下,解渴。
入夜,我躺在酒店大床上,想着这个边地小城有个不知长啥模样儿的女孩儿叫“阿蜜诺”。
瑶家山
一夜窗幔没拉,临窗而卧,不知不觉,月照床头。按着月历,正月十六,月亮最圆,正月十七,月亮最亮。这天是正月十七,月亮把对面的山峦照得明亮,远远的,能分辨出山林轮廓。这个房间是6楼,视线较好,我特意选的房间。窗子外是学校操场,操场外是蓊郁的的山林。拉开窗子,清风卷着浩大月光涌了进来,山的气息、草木的味道,把满屋子的浊气冲尽。天地静谧,鸡鸣起伏,几粒小星浮现,似开在天上的小花,又似游动的鱼儿闪烁的鳞片。楼下的树和花,浸着月光,散发出淡淡清香。这座山城和月亮,把所有香气,全给了我。
冷了。裹紧被子再睡。凌晨再起来看月,这次月亮的角度正好,清澈、碧透。唐宋诗人王维、李白、张若虚、苏东坡等等写月亮,美轮美奂。月之意境,填满了时光的缝隙。江城的月亮,幽邃、明亮。如一只舟船,静泊天河,浅云飘浮,轻漪闪光。再过一会儿,外面的天变黑了,月亮落到山的另一边了。这是黎明前的黑暗,神仙也要安眠一小会儿。
轻雾渐起,来去无迹。也许再过一会儿,雾会随太阳的升起飘散。鸡鸣此起彼伏,悠远、绵长,弥漫浓重的乡土味儿。这是我喜欢的泡在月光里的声音,是融在月光里的意境。在这里生活的人,在享受城区生活便捷的同时,也能体味乡村的温馨。我看见山巅上那三两粒小星互换了位置。街道有汽车驶过,起早的清洁工,开始清扫街道。
老钟急着赶往东站,只用几分钟时间就收拾完毕,迅速背上相机包,步子飞快在前面走。到东站,打听到勐康的车12点才有。怎么能等到12点?和老钟商量了一下,租个车吧。先吃饭再说。在小摊上吃了碗米线,到那个标志性的“奔牛”雕像等车,一会儿就来了几个人问租车否,我说去勐康,司机说100元。我去年去过,你要得太多,我说。一对等车的夫妻告诉我,这时间无车,只有小面包组合去,这样会省钱。
男人向对面招了下手,来了一个中年男子。问我坐不坐“皮卡”?皮卡就是前面有座后面像卡车装货的那种,车轮大,底盘高,马力强。他说这车是四人座,再坐上两个人就可以走了。他说每人25元,两人50元。这个价能接受,钟也同意。我坐后排座、钟坐副驾。那司机就到那边与几个人说话。正着急时,司机领着一个戴鸭舌帽的黑胖子走过来。我开始以为那个黑胖子是客人,没料想那黑胖子与司机是朋友,黑胖子坐进了驾驶室开车,那个中年男子坐到了后面与我并座。我犯嘀咕,这到底是谁的车?没多想,那黑胖子已将车开动。
客人只有我们俩。车开得飞快,转弯不减速。在经过浓雾路段时不减速。我抓紧扶手,心提得老高。黑胖子,满脸的凶狠,眼盯着路,双手灵活转动方向盘。虽然很认真,但坐这种飞快的车,又是弯路多、雾气重,让我胆颤心惊,几乎魂飞天外!车到路边的一个村寨,突然停车,黑胖子跳下来,左手重重关车门,谁都不理,像生谁的气似的,一言不发走了。
中年司机从后面下车,再上了驾驶室开车再行。老钟说:“这家伙,太快了,吓人呢!”
司机哈哈一笑,说:“他是我小时候的伙伴,有蛮劲,爱打架,爱喝酒,喝多了就生气,就得找个人打一架,因为闲得难受。今天本来我要再等两个客人,他非要走,还要开车。他昨晚喝醉了,住在城里,今天开我车回家。他想开车啊,我要是不让他开,他就会说‘有什么了不起,你这破车!’心情好了还好说,不好的话,要踹车一脚。只好让他开了。”
我和老钟不但没害怕,还哈哈大笑起来,觉得这黑胖子有趣儿。司机见我们高兴,话就更多了,還告诉我们回来时可能没车。要是到路边等车,恐怕很少,就得走一段路,然后到公路边等小面包了。坐小面包每人只需要8元。这里的面包车很便宜的。走路,很辛苦。
勐康口岸是中国和老挝的边境,在两山的夹缝处。山体巍峨,森林蓊郁。中间一条宽道,是来往贸易边民的通道。今天人特别少,我和老钟在7号界碑拍照。半小时撤出。因为我惦记着瑶家山,想到那里多转转。但我的脑子太浆糊,竟然记不得哪条山路通向瑶家山。
瑶家山不在这里,它似乎隐藏在一个半山腰。
这里有一个村子叫大关下坝卡村,是一个“移民村”。都是从昭通那边迁移过来的,二十世纪末建村。下坝卡村的房子都是清一色灰色空心砖房,房子墙下堆积着木柴。村子被茂盛的植物围裹,植物的气息扑面而来。清澈阳光照着房子下的几畦蔬菜。
老钟用他的“大炮”瞄准远处的下田农人。我拍几个玩耍的孩子和在自家门前劈柴的农人。一些农人开始有些戒备,但看我似乎对他们身边的房子或身后的山岗、田野和村子感兴趣,就放松了警惕。那些把孩子装进篓篼背着下地干活的年轻母亲,那些在自家门前爬墙的孩子,那些三两个在一起纳着鞋底儿的妇女,那些倚在墙边叼着旱烟的男人,被我拍了下来。
村子里唯一的水泥路上,铺晒着许多木薯。铺在路上是为了让车辆辗碎喂猪。木薯营养丰富,猪吃了增膘儿。再往前走,又看见有农人往水泥路上堆放大块木薯。
我在拍摄村口的大木瓜树时,一位老汉热情地与我打招呼,他女儿正在路边烤糯米粑粑,拿来一块粑粑给我吃,烤得热烫,很香。一户人家门前,一位妇女正纳鞋垫儿,老钟想买,那女人说是给孩子纳的,太小了,没有适合他的。老钟很失望。出村子来到路口等小面包车。路口有几个摊位,有老挝人有云南人,大多是饮料、小食品、烟酒和日用杂货品等。有几个女人孩子坐在土堆上吃粑粑。临近中午,阳光明亮,山谷一览无余。天空碧蓝,几朵云飘荡,那些云就在身边,那些雾状的白色,在掠过山林的刹那,我分明听见细密的声响敲打树叶。路边树叶嫩绿,春天的气息溢满整个山野。
沿来时山路,向勐康路口走。开始与老钟走,他拍鸟儿,总是说我把他的鸟儿惊扰了,不是说话声音大了就是脚步太快了。我只好与他保持距离,一会儿他在前面,一会儿我在前面,我们拉开距离走,边走边欣赏山路边民居,他边走边瞄准树梢上不停啁啾的鸟儿。路过上坝卡村,路口有标示牌,上面标明是新农村试点村。这个上坝卡就是刚才在下坝卡看到的。这个村寨很富裕。还有上坡下坡,速度时缓时急,两只脚走得灼烫。大卡车和摩托车一辆接一辆从身边经过,老钟抬手示意停下,但没有一辆愿意停下。估算了一下从勐康口岸7号界碑到勐康镇、普洱、江城的交叉高速路口,有15公里。忽然看见前面有个小卖店,进去,一位老汉在,我买了两瓶矿泉水。看营业执照上的地名:康平乡勐康村报木冲社。
老汉是哈尼人。我问老汉到“路口”还有多远?老汉问旁边正在修理拖车的一个青年,那青年回答“太远了”。老钟赶上来了,稍坐了片刻,他便又朝前走。老汉说帮你们找个车吧。可找的是摩托车。我说摩托车我们不坐。老汉说那也只好步行了。看我说得坚定,老汉直佩服,说这段路太远,连他们也不常走。我心想,今天就要来个“刺激的”行走,在满山嫩绿的山路快走,总是美好的。
老钟将我远远甩在身后。我快步追赶,走到二官寨。人们躲在树荫下乘凉。在一个甘蔗摊前,老钟正在吃甘蔗,我坐下,他给我一根。甘蔗很甜,刚割下来的。吃完甘蔗,开始找车,找了几辆都不去路口。只好再踏着干热的路向前走。一直走到路口。算来,走了两个多小时。一会儿有一过路小面包车,我上前问能否去瑶家山,开车的是一个年轻人,他也不知道瑶家山在哪里?我给他看地图,他让我上车,说应该就在前面,好像有个是瑶家山检查站。然后直奔而去,还真是有些远,一刻钟后,车开到那个叫瑶家山的检查站。付费,下车,缘路上行,问路边修路工,说瑶家山就在前面一个水泥坡路上去就是。我欣喜万分,不顾满头大汗,拖着疲惫的脚步进入瑶家山寨子,却怎么看怎么不像去年的瑶家山。
进村子,有狗儿吠叫。一户人家门前有个妇女在织布,我递上瑶家山人的照片,那妇女立即认出,说是瑶家山六家社组——怪我没记清还有个“六家社组”,也让刚才的小车司机懵菜,要是说六家社组,都会知道的。在这里人们不说瑶家山。这事只能怪我,如同上次去西盟边境的岳宋,社与组,是分散的。我和老钟从寨子出来,往西走,继续寻找六家社。这一走不要紧,又走了四十多分钟,累得不行。终看见路边有一个木板标牌:瑶家山六家社组。
土路斜坡、晾晒染布的木楼。只是不见了穿靛蓝青衣头戴银饰的瑶家人、不见了头戴小圆帽脚穿小绣花鞋的孩童。村子静静,能听见鸡群在草丛里觅食行走的声音。
见到第一家。拿出一叠照片让一个男人看,他马上说:“有我家4张——我老婆、我娘、我儿、我弟媳。”我细看他老娘,正端坐在小院子的板凳上晒太阳呢。是这个老人,我说。他老婆看到自己纺线照片,很高兴。进屋给我和老钟倒了两杯水,拿出小凳子。我们坐下,寒暄几句。男人说他叫张志平,那年到外面打工了,没有参加“度戒”。他老婆,也就是眼前这个女人参加了,还有他儿和他娘。他儿子就是那个“执杖拦路”的少年。
时间紧张,不能耽搁时间,起身寻找另外的人。一位手臂受伤的叫张朝林的农民,自告奋勇当起了我的向导。他领我和老钟挨家送照片。我见到了去年在路口第一个敬“进门酒”的姑娘,然后见到了穿小红衣的7岁女孩张金萍,看到了那个向我扮鬼脸儿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正在飞跑,我叫了他一声,他站住了,给他拍了两张,这次正好洗出带来了。
时间不早,我不能一一送到。我把余下的照片交给了张朝林,让他转交给村里的乡亲。
曼 滩
曼滩在一个深深山谷里。山根下的田野里,有一个神秘的黑褐色东西在活动。那是一个巨大的动物,头上高举一把奇异的刀戟。我用镜头拉近了看,是水牛,慢腾腾吃草。水牛将整个大地踩得倾斜。水牛在绿草丛中,像一只静泊绿湖的小船。远近景致,妙不可言,纤细村路、古旧石桥、傣家木楼、山坡竹篁、芭蕉和凤尾竹、寨子里的大榕树……
我和老钟在小吃部买了两块面包,吃完进寨。走在熟悉的村寨,到大榕树下拍傣寨全景。上面是巨大的树枝,下面是黝黑的屋舍。老钟胡乱拍几张,心里全想着那些啁啾的鸟儿。
中老8号界碑就在寨子的田野边,这个界碑南北已然无法分清哪边是中国哪边是老挝了。
循坡而上,山顶就是寨子。向村寨的东边行走,忽见一块阔大的空地,空地里长满了青草。有一座小木房子矗立那里。小木房子里放置了一只硕大的木鼓。只有祭祀鼓神时才有人前来。我和老钟在木房子外面隔窗子向里面看,除了大木鼓外,还有佛像一尊,香炉若干,置放在供台上。平时有人打理,房子干干净净。人们不能随意进入。就连这一区域,也不能建房搭棚。若是建房,需远至几十米开外。因此,这一区域就成了空旷之地。
又见到了此前见到的那个傣家小女孩,前年她只有三岁,今年又长高一些,小圆脸儿小嘴小眯眯眼儿,扎两个小辫儿,一笑一排小黑牙。她正和比她大一岁的一个小女孩在路边玩耍。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失误:没有把这个小女孩的照片给带来。当时不知道傣族小女孩就在曼灘,还以为她与母亲是来赶集的呢。
小女孩的母亲正在田地里支锅做饭,锅下是燃烧的木柴。一户人家正在盖房上梁。我问小女孩的母亲是谁家盖房?她说是她哥哥家。另外的小女孩肯定是她哥哥的孩子了。小女孩母亲邀我和大家一起吃饭、喝酒,我说还有事情。我说前年遇到了她的女儿,就在前面的集市,也拍了孩子的照片,可惜的是先前没有计划来曼滩,照片没有带来。说出这话时,我觉得自己虚伪,人家能信你说的话吗?
两个小女孩有些拘谨地看着我,阳光照在她们毛绒绒的头发上,反射出金色的光泽,测光正好,我蹲低了位置,用连拍又拍了小女孩好多张。照完相,就在寨子里拍民居。梨树簇拥屋舍,母鸡小鸡欢跑,小黑狗儿小黄狗儿从身边跑过,只扭头看,不吠不叫。
老钟在这些鳞次栉比的傣家木楼间窜来窜去,感叹这建筑的独特。走着走着,他决意要进一户人家的木楼看看。他是建筑工程师,研究傣族吊脚木楼的结构。一边游走一边自言自语说这木屋子,生火做饭在哪呢?主人很热情,将我们领进他家看看。吊脚木屋的屋顶是石瓦。木栅门。木板楼梯。木板二层小屋。屋里摆沙发、电视机、被褥、桌椅之类。过窄通道,上了一个小露台。小露台不大,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平台,有自来水和水池,洗衣洗菜淘米都在用这个台子。一枝含苞待放的梨树从下生长,枝柯高过木楼露台。一位身穿傣族筒裙的中年女人抱着小孙子在剥豆荚。孩子害怕生人,躲在奶奶身后。我走在台子的边缘,看四周的房屋,所看到的是黑色的屋顶和屋檐。这样的傣家屋子多年前就在西双版纳曼伞寨子见过。这么多年了,曼滩的农人除了屋里的物件改变之外,其他的没有改变,仍然保持着原生态的民族风格建筑,这让我欣喜。老钟用小相机不停地拍,这对他的建筑学有用。
临近中午,天气热了起来。早晨因为天冷穿得多,衬裤如同长在腿上的皮一样捂得浑身是汗。我对老钟说,尽快找一个无人的树林脱下衬裤。忽想到东边村子边上的土路往东有片竹林,那条往东走的土路两边,有竹篱笆夹成的小路,顺小路向山里走,进入一片茂密而粗壮的毛竹林。二人遂到竹林换了衬裤,真是凉爽。走路顿时轻盈了许多。
竹林的竹子高大、茂密,沿被杂草淹没的山道上坡,再往上走,忽听老钟惊呼一声。我抬头,透过竹子,猛见十几米开外的坡上,生着两棵高大榕树,不声不响耸立竹林之中,好似两员老将,周围十万兵卒,孔武、严峻,不怒自威,居高临下。这大树少说也有几百年。竹林里的小鸟儿成群,鸣声动听,宛如仙子轻吟。老钟按捺不住激动,在这附近拍起鸟来。我坐在离大榕树不远的山坡,享受这幽静的竹林。想起了王维的《竹里馆》。于是就独坐距大榕树不远的坡上。坐累了索性躺下。面前是葳蕤的草丛、灌木叶、竹叶、大榕树叶。朦胧中一个句子冲荡而出:“我站着,竹子比我高大。我坐着,灌木比我高大。我躺下,花草和竹笋比我高大。”我没有王维的潇洒,不发长啸,只能轻吟。尔后,我睡着了,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株草木,将根深扎泥土里,那纤细的根蔓延,与泥土搅在了一起,与时光的厚层搅在了一起……
从曼滩出来,在集市等车去整董。这个小小的集市上,只有一个小菜摊子。新鲜的蔬菜在大榕树的木架子上放着,却无货主。也无人来买这些蔬菜。不远处,有一家人正在街边炒菜。另一边,一位母亲正在为女儿洗头。画面温馨。半小时后搭上一个小面包车到路口。从路口得走两公里到整董镇。还是无车。四周是大片香蕉林。今年大旱,香蕉的底叶大多焦枯,也不知蕉农的收成怎样?我走着,脚趾的水泡被鞋挤得疼痛,脱下鞋子一看,先前的小泡变大吓人。松开鞋带儿,这鞋子,完全变成了趿拉着走路的拖鞋了。
整董镇这天是集市,可惜散了,只剩下几个摊位还在那里,傣族“赶街”从清晨开始,到了午后,街上的人明显少了许多。住得较远的农人,早早完成了买卖后,就踏上了归家的旅途,剩下的人是没有卖尽货物的,总不能再将货物带回去,特别是水果或者食物等。
我不知道在镇上能不能遇到玉凤和玉尖丙姐妹或者玉波。她们都是大青树村的人。也是那次参加傣族祈福节少有的几个高个儿姑娘。在街上走了一个来回也没见到她们。我对老钟说,还是去大青树村找她们吧。我的包里带着给玉凤玉尖丙姐妹拍的照片呢。
整董、曼滩和大青树村都是典型的傣族村寨。除了整董镇子有一些楼房外,曼滩和大青树都还保持着傣族建筑风格。我截了一辆小包车,司机抄近路直奔大青树村,几分钟就到了大青树村。进大青树村口,见一群妇女倚坐在一个吊脚楼下聊天。其中的一个姑娘冲着我笑。我看出来是去年参加祈福的一个姑娘,不知她叫什么名字,比玉凤姐妹矮些。合影的照片里有她,我给了她一张,周围的女人围上来看照片,嘻嘻哈哈的。我问姑娘,玉凤玉尖丙姐妹和玉波在不在?她说“在呢在呢,玉波在那个小卖店,玉凤玉尖丙姐妹两个在家。”一个小伙子自告奋勇领我们去,一溜儿小跑,带我们到玉凤和玉尖丙家。
玉凤和玉尖丙两姐妹身材很好,个子都有一米七,丰满匀称,是标准的模特,玉凤和玉尖丙两姐妹有一个爱笑,没说话就先笑了。去年祈福节时见到她们两姐妹,泼水时见我拿着相机,我让她别泼我,怕把相机弄湿了。她们就没泼,还告诉玉波和一些姐妹不要泼拿相机的人。我一见玉凤姐妹就觉得她们有英国人的血统。此地区有基督教堂,多年前有传教士在这里生活过。从玉凤玉尖丙的高大母亲的照片上看,绝对有这种可能:高高的鼻子,柳竖的眉毛,深陷的眼眶,大大的眼睛,瘦削的脸颊。年轻时绝对是个美人儿。
但我不能区分谁是玉凤,谁是玉尖丙。
走在吊脚楼下,我喊:
玉尖丙!玉凤!
木板露台一阵脚步响,传出了一个女子的声音:黄师傅,你来了啊。
我说:玉凤?还是玉尖丙?
玉尖丙哈哈一笑:我是玉尖丙呀。玉凤是我姐姐。
玉尖丙爱笑,说话也笑,玉凤矜持些。这时玉尖丙朝屋子里喊了声:姐,黄师傅来了。说完玉尖丙就急速下楼迎我们。没见到她们高大的母亲,还有楼下的大黄狗儿。我问玉尖丙:“妈妈呢?大黄狗儿呢?”她说妈妈到香蕉地里干活了,大黄狗儿不知跑哪玩了。上楼,玉凤正在洗衣服,站起来说:“黄师傅你这是从哪里来啊。”我说从北京到昆明从昆明到普洱从普洱到江城从江城到整董从整董到这里。
玉尖丙抹了下沾在前额上的一缕汗湿头发,说“没想到黄师傅你还能来我们这里呀”。我哈哈一笑,拿出照片,这叠照片里,玉尖丙的最多。
玉凤过来看照片,这里只有她一张,是全家还有村里几个参加祈福节的女人一起的合照,玉凤有些伤感,说她那天光忙着给大家倒茶水了,照片不多,倒是妹妹照得多。
我有些歉意地对玉凤说,现在给你多照几张吧?玉凤有些害羞说,现在全身泥土啊,下次泼水节吧。你能来吗?我说能来。玉凤转身进屋取出两个苹果,又给我和老钟沏茶。
玉尖丙结婚早,嫁本村的,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16岁了,现在上了初三,個子和她一样高,1.7米了,小女儿12岁。姐姐玉凤几年前在城里打工,认识了一个广东人,与之结婚,育有一女,也是12岁,现在上了小学。玉凤男人回了广东,现在他们是两地生活,女儿在云南长大,一次去奶奶家过年,听不懂广东话,只能听懂“吃饭”一句。
玉凤玉尖丙她们一家子,分家不分地,主要是种植香蕉。
说话间玉尖丙不停呵斥里屋两个12岁的孩子不要看电视,要做作业。女儿很调皮,哼哼两声又继续看电视。
下楼时遇见了玉尖丙家的大黄狗,吼了两声。我说,你这个家伙,不认识我了,我是黄师傅啊。大黄狗便不吭声走到一边趴下了,但眼睛还时不时地翻瞪着我。
然后到小卖部找玉波,将照片给她。
从大青树村出来,来到公路边,没有客车经过,只好和老钟向前走。村口距公路几米外有棵大榕树,树冠茂密。像一个百岁老人,形只影单。
继续前走,几辆小车呼啸而过,招手不停。看来又得走回整董镇了。
和老钟拉开几十米距离,我在前,他在后。
有一辆包车经过,老钟招手,司机不理不睬继续向前开。开到我身边时,我招了下手,喊:“老乡,去整董!”那车慢了下来,晃晃荡荡向前滑行了十几米,终于停了下来。我赶紧招呼老钟。司机拉开了车窗,说他不是拉客的。又问我到哪里?我说去整董。司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上车吧。我打开副驾的车门坐了进去,老钟坐后座。
这才看清司机是一个面颊黝黑胡须虬生的汉子,穿着军队的迷彩服,一只眼睛有点斜,但是笑容和蔼。我判断这人一定是个退伍军人,或许他的眼睛是在部队训练时受的伤,从他的神情看绝对是。我不便问他是不是退伍兵。
多少钱?我出口的,是这么一句。
不要钱。他说。
那怎么行呢?我说。
顺路。他说。
然后汉子一言不发开车。老钟在后面不停地说给钱、给钱,我向后摆了下手,让他不要乱说话。在边地,老百姓都真诚好客,有时中午或傍晚,路过村寨,都会问“吃饭了没有?”如果你没吃饭,他们会邀请你到家里吃饭。我在云南行走了近二十多年,遇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事。他们不要钱,如果你坚持付费,在他们看来,就是瞧不起他们了,他们因此会生气。眼前这个汉子,如果我坚持给他钱,也就是说我们坐了你的车也不会领你的情,因为付了费。这种做法,有违人家好意。但也不能以貌相判断,虽说满脸虬须眼睛乜斜,内心却是善良。
汉子是曲靖人,在江城上班,这次是到这里来办点事。我说曲靖那边,我多年前去过。我问他家人是不是还在曲靖,他说老婆孩子父母亲还在曲靖,他独自一人在江城工作。
看得出来,司机还是愿意与我们聊天的。
整董镇到了。
向司机道谢。攀坡而上,坡上就是整董。上了坡后回望,老钟忽然说,瞧啊那边,也有条路,那司机拐上那边的路。
人家特意给我们送到了整董!
这位不知道姓名的司机,真是个好人。也没问问他是不是退伍军人,但凭直觉,一定是的。但转念一想,是不是退伍军人也不一定。再说,人家的车在路上跑,忽然路上有两个内地来高大家伙招手要坐车,还有一个肩扛着“大炮”,万一是歹人怎么办,谁敢拉这样的人?
广场里边就是整董标志性的大榕树群。去年在这里举行了祈福盛会。我让老钟到大榕树下歇脚,我去前面看有没有去江城的车子。这其实是个妄想,因为去江城的车,肯定是在曼滩与整董的路口处才会有。这里的车要去的话,价钱会高得离谱。果然,我问了几个在那儿停的车,都说太远不去,要去也行200元不讲价。
我在一个水果摊买了一大包刚刚摘下来的柑子,农人让我尝尝,有些酸。一称5斤半,1.5元/斤,我给他10元,零钱不要了,农人坚持从车上抓了两个柑子塞进袋子。拎着这重重的柑子回到大榕树下,坐下来,与老钟大吃起来,吃了好多。然后拍大榕树,让老钟当参照物,以衬托大榕树的壮硕。但大榕树旁的几个灯杆影响了大树的自然美观。整董的大榕树群是标志性景点,许多摄影师拍过。再难拍出新意。除非有祈福节,或能拍到精彩场景。
回到广场蓄水池边,老钟去找车,问了当地人都说无车。只好徒步返回曼滩、普洱和江城的三岔路口等过路车。老钟执意走一段,于是从整董镇出发回走那片香蕉林路。2.5公里。到了路口,两人都大汗淋漓。30分钟后,来了一辆中巴车,是墨江至江城的车。司机是个年轻小伙子。车里还有一个女孩,坐在副驾,加我们两个,三个乘客。女孩与司机有说有笑,看来是常坐这趟车的。车里的座位被阳光晒得炽热,坐下更加发热。
车子突然发出轰轰声,抛锚了。小伙子说可能是油不好,将油管堵了,顶不上了。修了一会儿,发动机突突响了起来,车行缓慢,行了二百余米,又熄火停下。小伙子掀开车子内箱具修油管,再开,连续折腾了好几次,走走停停,极其缓慢。
老钟和我都有些着急。不知道今晚能否早些赶回?问小伙,小伙却很自信,说能修好。干脆跳下车钻到了车子下面大修起来。我下车站在路边拍很远山谷里的小房子,那小房子孤独地隐在绿树丛里,不细看还以为岩石。大概半小时,浑身是油污的小伙子从车下钻出来,拍了拍衣服说:这次不会坏了!
车开动,一路慢行。
老驴着急了。打电话过来,问我们何时能到?我问了司机,说大概7点左右。老驴说他已到了东城的观景台那里一家饭店,菜都上来了,酒也打开了。老驴在电话那头还向我和老钟报了点的菜。当然,不能没有当地的李仙江水煮李仙江大面瓜鱼蘸油辣子和酸笋炖土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