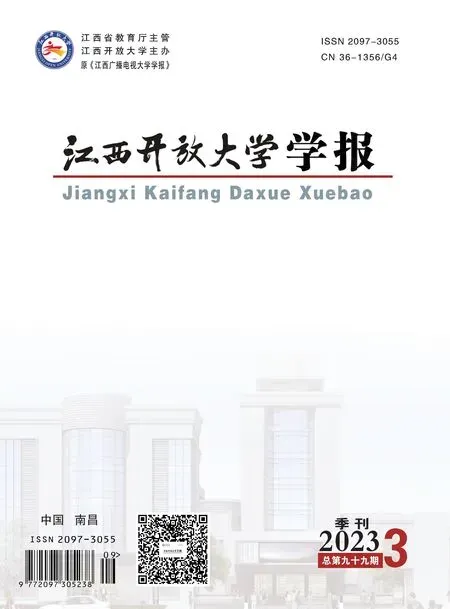论书院经费的历史特点及其意义
蔡慧琴,张劲松
(南昌师范学院a.书院研究中心; b.教育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2)
书院经费,是指为了保证书院开展正常的活动而投入和消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和,是书院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1]32“7学校之政,必先于教养。教养之具,必资于金谷”。[2]卷十五·送李国用引书院教养活动的基础是经费,教养活动开展的要素,如师资(山长)、藏书、院舍(讲堂、斋舍、庖湢、楼阁等建筑),以及肄业生徒的膏火资助、考课奖励等都依赖于经费,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经费,便没有书院,所谓“养士不可无田,无田是无院也”。[3]62经费在书院发展中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制约着书院的正常运转,影响着书院功能的发挥,是书院生命周期循环往复的内在决定因素。[4]
基于书院经费重要性认识,学界对书院经费开展了较全面的研究。宏观研究方面,杨慎初等在《岳麓书院史略》中称“学田为书院‘三大事业’的经济基础,是书院经费的主要来源,它是书院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强调书院经费的主要来源及其重要性。[5]14陈谷嘉、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专辟“书院的经费及其管理”一章,对书院经费及其分类、筹措、管理等进行研究,并以岳麓书院为例,探讨了书院经费运行的有关问题,提出清代岳麓书院经费的一些特点,如教学人员与管理人员的薪金悬殊、师生与行政后勤人员的经费分配比例恰当等。[1]428张劲松《教养相资:书院经费研究》为书院经费研究的专著,著作对书院经费的重要性、经费的来源与构成、经费的使用、经费的保护与管理、经费存在的问题、经费的特点与启示等作了全面、系统研究。[6]历时性研究方面,学界研究的焦点在明清书院经费上,内容主要包括经费来源、筹措、使用等方面。如孟雪在其学位论文《清代书院经费研究》中,以清代书院政策为背景,分析了清代书院的经费来源、经费支出、收支差异以及书院经费与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的辩证关系。[7]东甫从官、私二个层面列举清代书院的经费收支,尤其是用于生徒支出部分的经费,并称其为奖学金制度。[8]蔡志荣在清代书院经费运作特点的研究中指出,清代书院经费的来源为多途径、其管理为官民共营、经营为多元化、使用为服务教学等,清代书院经费在运作中形成的这些独特体制促进了清代书院的繁荣。[9]著名书院史学家李才栋先生在《清代书院经济来源变化及其意义》中指出,书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书院的经费从最初依靠土地资源(学田)的田租,发展到清代一些位于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附近的书院逐渐以典息、店租乃至自办企业的利润为主,这意味着“儒与商的靠拢,预示着书院制度本身即将产生巨大的变化”,揭示了书院经费的历史演变及其价值。[10]此外,林枫、陈滨、赵连稳、王丽娜、江超、张显运、周郁、崔来廷、袁仕勋、贾勇、李科友、屈乾娜、吴洪成、王列盈等对明清时期福建、北京、陕西、徽州、河北、河南、长沙、黔东南、汉江流域及白鹿洞书院、雷阳书院等区域与个案书院的经费进行研究,探寻其运作规律等。[11]值得注意的是,既有的书院经费研究,虽不乏对其重要性、运作运营及历时性、区域性的关注,但长时段的研究仍显不足,而从早期书院代表中唐江州(今江西德安)义门陈氏东佳书堂割田二顷以赡学,到晚清时期作为区域教育文化中心的各省会城市书院,如江西南昌豫章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等,常年经费稳定在上万两白银,变化的不仅是不同时空中书院经费的多寡,更反映出从中唐至晚清时期,我国古代书院整体教养活动中经费的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包括书院经费的来源、组成形态、数额差异及伦理价值等,在既有历时性、区域性、个案性书院研究的基础上,长时段的书院经费研究确有必要,它们既是观察书院教育的重要视角,也可为当代教育尤其是民办高校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经费来源:多样性并存
古代书院从中唐时期起源直至晚清退出历史舞台,延绵千年,其发展路径有官私两途,在官府与民间力量共同加持下,成为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重要机构。虽然官方力量是推动书院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总体而言,书院没有制度化地纳入官学体系,不是官学的组成部分,书院更多地表现为既不同于官学与私学,同时又兼具官学与私立特征的较为复杂教育文化机构,这一特殊性反映到经费上,表现为书院经费来源的多样性。
书院经费来源的多样性,指书院经费既有官府的拨予,也有民间绅众的捐赠,还有书院的自我经营,此三类来源对个案书院而言,既有可能并存,也可能仅有一类来源,经费来源因书院性质不同而不同。如天下书院之首的庐山白鹿洞书院,自南唐时期为庐山国子监之始,直至晚清,一直是官方经营,管理权为官府所有,因之经费也主要源自官府。典型的如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8),著名理学家朱熹(1130-1200)在知南康军任上兴复白鹿洞书院,离任前遗官钱给继任钱闻诗作为修复书院的经费。史称:“岁壬寅,朱子提举浙东,复遗钱属军守钱闻诗建礼圣殿,并两庑绘孔子十哲等像。越二年,军守朱端章加板壁,绘从祀者像,而以浮屠诡名没入田七百余亩益之”。[12]21明清时期,白鹿洞书院屡获官府拨置的学田,如明弘治十三年(1500),“巡按陈铨收市寺田九百亩,提学苏葵置建昌田五百一十八亩有奇,塘五十一亩有奇”,清顺治十二年(1655),巡抚蔡士英与按察使李长春置田619亩有奇,[12]1094等等。再如清代江西余干(今江西余干)东山书院,为官立民助的区域中心书院,其经费既有官拨也有民捐,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书院获得绅众捐田144 亩3 分9 厘,可得租谷160 石,这些捐田分布在县治周围,如缪坊村田40 亩6 分4 厘,分别为缪定南、缪福庆、王邦佐、彭正亨、余斌等捐与。道光元年(1821),余干知县捐银58 两7 钱与书院,道光三年(1823)等,江西巡抚程含章捐廉银100两助书院膏火。道光二十九年(1849)知县常山凤倡助书院膏火制钱5 千2 百串,存典铺按月以一分为息,每年可获息钱624 串。除县令外,章应霞、张滨、张峘等地方人士66 人亦捐六百、五百、十串不等。[13]卷六与庐山白鹿洞书院、余干东山书院不同的是,部分不由官立或官为经营的民间书院,其经费主要由民间捐赠而来,如晚清时期江西义宁州(今江西修水、铜鼓)仁义书院、培元书院、聚奎书院、崇德书院、泰交书院、奎光书院等乡村书院群均由所在乡都图绅众集腋成裘、乐为捐助而成,官府则不与分文。[14]132-137
书院经费来源的多样性可成为我们判断书院性质的窗口,如清代,对于会城书院、道府、州县一级的区域中心书院而言,其经费主要来自官府,书院的性质也为官方经营的模式;而位于乡都图的乡村书院,其经费则主要来自民间捐赠,此类书院为民间所有、地方经营。正是在不捐细流、不弃微尘的过程中,以多样性的来源保证了书院经费总体的恒常稳定,使书院得以千年绵延,弦歌不辍。
二、经费构成:多元化共存
传统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院有田,则士集,而讲道者千载一时。院无田,则士难久集,院随以废,如讲道何!”[12]1284学田是农耕时期书院的主要资产,地租是书院经费的主要组成部分,学田租收入是书院经费的主体。但在明清时期,一些土地有限及商业活动较为发达的区域,除地租收入外,书院还有将银钱交商生息、购置店铺出租等经营活动,从而改变了经费为单一地租的局面,而形成了地租、息钱、租金等混合的经费构成,书院经费出现多元共存的现象。如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吉安白鹭洲书院,“息银、田租历守相承,垂百余年”,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知府李源将本银解省,交省城监埠行息。本息折实贰仟陆佰伍拾肆两壹钱,每年分息银叁佰捌拾肆两肆钱捌分。”[15]111-112安徽旌德县(今安徽旌德)毓文书院,清嘉庆年间(1796-1820)主要经费有二:一是邻邑宣城县天门山庄田50 亩5 分5 厘,一是捐钱3 千5 百两。该书院在规条明确“议得生息银两,自应就近发交本地典当,或殷实铺户,具领存案。遵照前藩宪态批示,以一分二厘行息,设立经折,发交董事,四季支利,备用其事。”[16]509从毓德书院的田、银比看,3500 两生息银是书院主要的经费来源,其一年的息银收入可达4200两之多,相比而言,50亩学田一年租入则不到息银的零头。除息银外,部分书院还有店铺的租银收入,如江西武宁县(今江西武宁)正谊书院于咸丰年间(1851-1861)购买县治坊市铺面一所用于出租,“每年额租钱三十二千文”。[17]卷十七再如都昌县(今江西都昌)南山书院同治时期“旧存书院店屋十八间,坐署东南,租银伍拾肆两,折钱肆拾捌千陆百文。又二间,租银若干,为每年修理之费”,[18]卷六从数字上看,南山书院店租产业颇为丰裕。
事实上,在清代徽州、山西等土地资源不足、商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书院主要经费为典银、息银、店租的现象较为普遍。[6]71书院经费从传统的单一地租发展到租谷与银钱的混合经营具有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一、提高书院资产运营效率,息钱、店租等货币与实物经营可获得比地租更高的回报;二、书院经费由单一的实物收入变为实物与货币共同构成,便于书院的各种支出;三、有利于改变书院资产只有单一土地的局面,减少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歉收影响,分散经营风险;四、有利于书院经费的运营。书院学田因分散四乡不易管理,放佃与收租,耗时费力,且容易受到猾吏、豪绅、刁佃等各种势力侵蚀,地租收入存在侵吞、隐没的风险。发商生息及店租相对简便,便于书院经营者就近控制、就近使用。不过,即便经费构成实现单一到多元的嬗变,仍应看到地租收入是我国古代书院经费主体的局面并未根本性改变,田地租佃仍是绝大多数书院经费的主要来源。同时,生息与店租虽分散了书院经费风险,但由于战乱、经营不善、侵吞、挪占等因素影响,息金甚至放息本金及店租并非一劳永逸、高枕无忧,清代书院中时有息银化为乌有、店铺惨遭兵燹的情况,令人叹息。
三、经费差异:个案的不平衡性
我国古代书院经费在个案中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经费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同时期的不同书院,其经费规模大小相差悬殊。如光绪时期(1875-1908),山东省属三所县域中心书院经费数额差异极大:位于山东半岛中部的昌乐县(今山东昌乐)营陵书院,光绪二十四年(1898),每年除县拨柜规银400 两外,另有捐项京钱14000 串发商生息,其中1万串息钱为生童膏火,2千串息钱为宾兴经费,2千串为岁修等费,全年经费有银400两,息钱2000 余串①由于文献缺乏,未知营陵书院放贷年息、月息多寡,以同时期较常见的1分5厘年息算,统共一年息钱有2100串。。[16]789位于山东北部的利津县(今山东利津)东津书院,光绪年间(1875-1908),地租收入约380 千文,另有铁锅规银和布商捐输费,“岁收若干,尚无定数”;光绪七年(1881)因锅规寖止不行,运司拨银600两发商生息以益公费。本年统共收银子90两,②与营陵书院相似,由于文献缺乏,亦未知东津书院其年息、月息多寡,以较常见的1分5厘年息算,统共一年息钱有90两。制钱380千文。[16]794位于山东半岛东部的栖霞县(今山东栖霞)霞山书院,光绪年间,有生息制钱、房租制钱、地租制钱等,按1 分生息,通计各种收入全年共135串有奇。[16]795同为山东省域内地理位置接近毗邻的县级书院,昌乐营陵书院的经费是东津书院、霞山书院的10倍以上,其间悬殊之大,令人浩叹(见表1)。

表1 清光绪时期山东省三所县治书院经费一览
书院经费的不平衡还表现在书院内部支出的差异。书院经费主要用于教养,其他辅助性开支则少之又少,教养费用中又以山长束脩与生徒膏火奖赏为主。民国时期,刘伯骥先生在《广东书院制度》一文将清代广东29 所书院的经费开支列表,从表中可看出书院经费主要用于山长束脩与生徒膏火的总体趋势,如清嘉庆三年(1798)定安尚友书院,全年总支出银46两,钱257600文,其中掌教脩金46两,生徒膏火19000文;再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肇庆端溪书院全年总支额为银3004.5两,其中掌教薪脩为794两,膏火为1468两,奖赏为460两,掌教与生徒经费占支出开支比约90.6%,其他行政经费等所占比例极小。[1]407。
书院经费主要用于教养而不是岁修等建设,其目的在于使有限的费用服务于主要事业的开展,彰显书院的教育功能,保证书院经费教养兼资职能的发挥,无一例外,这是书院经费支出的主体,这一基本原则在书院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偏离,值得充分肯定。
四、经费取向:金谷的伦理性
“夫士之籍田以养,道之籍士以兴,其义一也”,[3]62田养士,士兴道,学田为儒家之道勃兴的基础,学田与“道”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因此,书院经费被赋予强烈的伦理价值。在传统书院的话语中,经费从来都不仅仅指银钱,而是具有教育意义的要件,无论是捐输还是使用与管理过程中,经费都有着超越货币、赀费的道德价值,而与善行、善政及道德修养、师法圣贤有关。经费作为贯穿书院日常全过程的重要因素,与官员捐廉、绅众乐捐、山长束脩、师长节敬、生徒膏奖、士子的宾兴、儒先祭祀及讲学、读书、考课等一起构成了完整的书院教育活动,甚至一直延伸到书院士子仕宦之后对书院的回报。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吉安知府何其高兴复白鹭书院,拨罚没充公之费为书院购置田产,并命之为“学田”。时人在解读太守称书院田为“学田”时称其中寓有深意,“公之以学名田也,欲使士食焉而思其学也,学至乎道焉尔矣。是故士之道也,犹农夫之于田也。农夫欲治其田,则不可废耕稼之务;士欲求志其道,而可忘学乎哉?”[19]卷五·尹台.学田记书院的院田虽主要供给师生束脩、膏火等,但其义当不止于此。士人志于道,犹如农夫耕作于田。以明道为业,犹农夫耕稼,早作夜息,一日不可废学。因此,士人食于饩田,应明晓其之所以为学之道,“士饩乎田不由是说以进于道,殆食焉不思其学者也。然则公之创是田也,岂以待夫士之食焉而不思其学者乎?”[14]在此作者明确提醒士子肄业于书院,有出于学田之膏火津贴,当知其为学者,当思学者志于道的意义、价值与路径。因此,书院田产冠名于学田、学田之于学者当不止于货利、经费而已,学田的租额、生徒的膏火、奖赏、花红、资斧,等等,都具有崇高的道德意义,是构成学者之所以为学者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圣人的遗训、经传、史籍等一样有着重要的伦理光环,是书院建设中金谷的伦理价值表现。
在重视书院学田等经费伦理价值的同时,书院经营者还注意到肄业生徒中汲汲于功名利禄的错误倾向,有意通过阐述经费的意义而对这一不良现象进行纠偏,从而端正士子求学的远大志向。明万历年间,江西提学冯景隆对肄业白鹿洞书院的士子贪图微末之膏火,不思进取的现象提出严肃批评,认为这一倾向十分可耻,“白鹿洞乃先贤讲学之地,其进修规则,皆入圣阶梯。今设立文庙,诚重之也,非他书院比。此惟身履德义、入斯洞而无愧于圣贤之徒者,方可与焉。彼以考案居优取入者,已非养贤初意矣。近因该府置田赡来学,而远近诸生不自揣学行何如,惟利其饔飧之资,漫焉求进,漫焉收之,将视斯洞为济贫之所,甚可耻也。”[16]662无独有偶,认为志在经费为可耻的不仅有冯景隆,清道光年间(1821-1850),两江总督陶澍(1779-1839)为江阴(今江苏江阴)暨阳书院增置沙田以充膏火撰记时,亦认为惟膏火是鹜者甚为可耻,“书院之设,所以佐学校、广教泽也。......夫膏火不继,无以示奖励,未能养而言教,司牧者之责也。若奖励之资已裕,而学之不进,行之不修,贸然惟膏火是骛,则亦诸生之耻也。”[19]1785书院经费养士的终极目标在于士志于道德而师法圣贤,若士舍此而热衷于科名利禄,则养之不谓养,士亦非士。清嘉庆时期,江西广信(今江西上饶)知府王赓言在为《鹅湖书田志》撰序时,亦清醒地指出学田的教育意义,“夫书田之设,所以养士也。今之士犹古之士,今之学犹古之学乎?猎取科名,溺情利禄,其志于道德者百不得一二焉,然则养士者其果徒为士之科名利禄计乎?......夫而后书院之兴有以教,书田之设不徒养也。若迺玩惕荒惰,卤莽灭裂,利其廩食,乐其驰骛,为之师者不以教,为之弟者不以学,是窳士也。朝廷亦何取乎斯士而养之也哉?故书之简端,以为多士朂焉。”[20]王赓言.鹅湖书田序
对士子不能正确对待膏火等书院经费的现象,书院管理者既从经费的道德理性加以说教,也从制度规章中对少数生徒中存在的希图哺啜的现象予以限制,如河北遵化燕山书院于光绪年间规定,“常年膏火原为培养攻苦之士,生童自应按课呈文,以期进益。近有考取甄别,常年住斋并不考课,实属希图哺啜,贻笑素餐。以后内课生童,官课点名不到或斋课连次不交卷者,立即扣火除名,另由外课选送,不准开复。”[16]56这一规定与坚持经费伦理性互为表里,一脉相承。
五、古代书院经费的现代启示
书院教养相资的优良传统不但在古代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书院经费的筹措、管理等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对于今天的学校教育尤其是民办高校具有启示作用。
(一)应高度重视经费的基础性作用
历史上,如果重视书院经费的作用,注重经费的筹措、强调经费的持续稳定来源,有意识地规划经费的支出与使用,并在此基础上出台具有约束力的管理制度,在富有责任心的管理者的经营下,一般而言,书院就能得到较好的发展;反之,没有经费,或即使是筹措到建设经费却没有维护正常运转需要的日常经费,诸如热衷于政绩工程的建筑物的美轮美奂而忽视延师聚徒,诸如无学田来源而“开课太速”,等等,则书院难逃时兴时废的厄运,经费的重要性对于书院而言是其存在的基础,“无田即无院也”。
从书院经费的特点看,今天的学校教育,尤其是与书院一样,经费来源主要来自民间筹措的民办教育而言,应将经费问题放到办学的重中之重地位。在经费的管理中,除建设费用外,更应立足长远,提前规划保证学校持续运营的日常经费来源,在经费的支出与使用中确保资金链安全,避免学校建成后续无力,办学难以持久,或资金链断裂,出现学校难以为继的局面。
(二)构建多渠道的经费来源
书院的经费有多渠道的来源,即使是纯民间管理的书院,有的仍积极争取官方的支持。由政府经费、民间捐助经费、自我运营经费(自我产出经费)等三部分组成书院经费来源的三个主要渠道,多渠道的经费来源对于包括书院在内的教育机构而言有着重要价值,它最大程度上避免因单一来源出现问题而使书院运营出现中断的风险。
与书院相比,我们注意到当前民办教育的经费存在着来源单一的问题,对此应引起足够重视。我们试以民办高校为例,通过对相关学院的研究,可以发现民间捐助经费在民办高校中所占比重较少,政府经费相当有限,其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学费收入,收入来源的单一性使民办高校的抗风险能力大大降低。如2019年在香港联合所上市的辰林教育披露,其主体民办江西应用科技学院(位于江西南昌)2016、2017、2018年三年学费和住宿费收入分别占比87.6%、86.4%、80.5%,而2018、2019 年各截止到本年度5 月31 日的学费和住宿费占学校全部收入占比分别为89.5%和87.4%;[21]另据立德教育(香港上市公司)披露,民办高校黑龙江工商学院2017、2018、2019 年8 月31 日止,立德教育收取的学费分别占公司总收入的约92.1%、92.1%及92.5%,住宿费收入占比分别为7.9%、7.9%及7.5%,学校的全部收入来自学费和住宿费。[22]再如上海建桥教育“截至2016 年、2017 年及2018 年12 月31 日止,年度来自政府辅助的其他收入及收益分別为人民币0.7百万元、人民币10.9 百万元及人民币15.1 百万元,其于收取后确认。截至2018 年6 月30 日及2019 年6月30 日止六个月,于收取后确认来自政府补助的其他收入及收益分別为人民币3.4百万元及人民币1.5 百万元”,[23]相比学费和住宿费收入,其来自政府的收入微乎其微。而辰林教育、立德教育则完全没有这部分经费来源,来自社会捐赠也几乎为零。
诚然,当代的民办教育与传统书院有着天壤之别,书院可称之为义学,而民办教育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费教育,书院与今天的民办教育不可同日而语。但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其目的主要在于提示民办教育的经营者,从传统书院经费筹措的经验中认识到经费来源多样性的意义,从而有意识地建立校友基金、社会基金等平台,为民间资金助力学校的发展提供通道。同时,也使其充分认识到经费来源单一性的可能面临的风险与困难。
(三)发掘经费的教育意义
书院教养相济活动的实现有赖于经费,书院经费超脱了物理形态的谷物银钱,而具有重要的道德教化意义,这也是理解民间持续捐助书院的角度之一。在这一过程中,土地、银钱等书院经费具有崇高的道德意义,经费不仅具有工具理性,更是价值理性的产物。
在传统书院文化中,经费是服务于教育的,教先于养,养服务于教的宗旨,最后形成了教养一体的模式。今天的民办教育从书院经费中可以师法其道德意义,无论是收取学费,还是相应的建设、设备购置、人员经费等都应首先明确其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尤其是在用于学生的奖、助学金及各种扶助性质的津贴、补贴发放中,更应彰显经费在教书育人中的意义,使受助者通过经费的帮助下,进一步端正学习动机,明确学习的目的,立志成为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时代的合格公民。如此,则如书院经费一样,今天学校教育的经费也具有超越了单纯的金钱价值而成为一种具有广泛道德意义的教育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