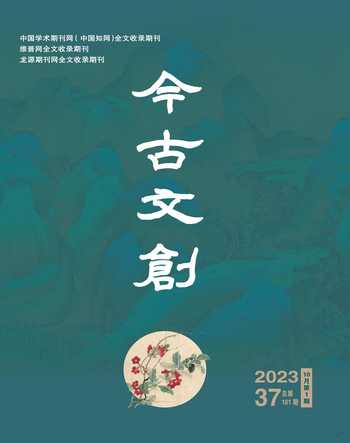纪录片的真实性和观赏性之关系及融合方法刍议
吕慧瑾
【摘要】本文从前期策划、中期拍摄和后期制作三个创作阶段分析“真实性”和“观赏性”在纪录片中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关系和相互融合的方法,并试图探讨纪录片如何超越呈现真实而进行观点表达与价值塑造。
【关键词】纪录片;真实性;观赏性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7-008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7.026
诚如希区柯克所言:“在故事片中,导演就是上帝;在纪录片中,上帝就是导演。”生活本身就因其丰富的不确定性而具有记录价值,尤其在影像获取如此便捷的今天,抓住精彩的真实瞬间并非难事,但如何呈现得出彩却不再容易,这就考虑到在进行纪录片制作时对其真实性和观赏性的要求了。很多人凭经验之谈认为两者从“记录”的概念上就是相互矛盾的—— “真实”便意味着对冗长、枯燥事件的无条件接受;“观赏”则有人为、刻意的干扰之举。但记录并不代表对无意义的一味接受,纪录片也可以在不篡改事实的前提下做到十分精彩,这便需要认识到“真实性”和“观赏性”在纪录片中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关系,而如何做到将两者融合得从纪录片的前期策划、中期拍摄、后期制作分别说起。
一、前期策划:寻找有趣的选题
在前期策划之初,就应该将真实性和观赏性有意识地统一纳入创作的思考范畴中,如果选题本身具有足够的吸引力,纪录片便不用刻意去营造一些所谓的“看点”。反之,如果最初没考虑纪录片最终效果的呈现,只随事态发展刻板记录素材,若事件本身寡淡无味又强求其一波三折,那便是将纪录片的“真实性”和“观赏性”对立了起来。所以,创作者们应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和挖掘题材的内涵、外延,为观众提供更为新奇有趣的感官体验。①
有趣的选题首先需要有趣的人,有趣的人需要是鲜活的。他们可以是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大人物,也可以是来自少数群体的边缘人物,例如讲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和展现跨性别者潦倒一生的《二毛》。镜头对准的人物,并非只为单纯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而存在,更因为他们或承载生命之轻,或肩负职责之重,是具有色彩、重量和矢量的,例如《我在故宫修文物》,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让这些看起来和身边人无异的古董修缮师傅一旦进入到工作环境就变得与众不同起来;而在《摇摇晃晃的人间》里,脑瘫诗人余秀华虽没有职业光环傍身,却因在病痛中开出诗之花而具有“生”的重量和高度。
有趣的选题自然还离不开事件的支撑,除了满足观众对影像趣味性的期待之外,事件的攫取还要考虑公共价值的发生。以《超大号的我》为例,导演摩根主动进入镜头,以身体作为实验品,观察自己连续吃三十天麦当劳后身体发生的变化,无论是完全拿捏大众好奇心的选题,还是仿佛真人秀一般的戏剧性过程,整个纪录片看上去都像是一次纯商业驱使的行为,但它最终还是回归到致力于探讨社会饮食健康问题的主旨上,在充分展现观赏性的同时发挥出纪录片“真实性”背后的公共价值。
还有一些纪录片选择将镜头对准自己,毫不避讳隐私,大胆直面观众的窥探心理。《当我望向你的时候》是一部由青年电影人黄树立拍摄的独立影像,作为Z世代独生子女的性少数群体,他用坦诚而亲密的语气倾诉自己对于成长的寻根以及面对代际沟通无解的迷茫,在他超8毫米的胶片镜头中,带着柔光的故乡充斥着梦境般细碎的生活琐事和母亲忧心又无奈的责备。该影片一经发表就得到了大众社会的广泛讨论,并一举斩获第7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国际酷儿金棕榈奖最佳短片奖。
像这样的私纪录片,创作者以“私”作为立足点和选题指向,将镜头对准私密的个体或者一段亲密关系中,坚持自我表达,强调自我体验,有一种去宏大叙事的倾向。不同于大多数纪录片展现出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观望,私电影坚持的是一种向下直抵心灵精神世界的姿态,因此它无疑是真诚且真实同时又极具可观赏性的。仍以《当我望向你的时候》为例,导演的本意起初是谈论自己的情感困惑,但他的作品一经发布就获得了广泛关注与支持,他亲密坦诚的分享首先引起了同样是性少数群体的共鸣甚至是情感慰藉,因为有些秘密是不能与亲人分享的,但他们却能借助这部私电影找到逾越相望和对话更接近彼此的方式。而对于普通观众,这部影片以极其私密的方式在满足“窥私欲”的同时又促使他们迁移了对自我认同和成长轨迹的回望与思考。
二、中期拍摄:处变不惊的参与
既已论证纪录片真实性和观赏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那么在记录真实事件时,想要达到具有观赏性的预期和效果,一些设计的参与和助力便必不可少,这并不违背纪录片创作的初衷和宗旨。
(一)摄影机背后的良性互动
在纪录片发展早期产生的“电影眼睛理论”派看来,摄影机是比人眼更强大的观察工具,因为它无所不至,拍摄角度可以极尽变化,更可以筛选剔除人眼观察时难以避免的多余杂质,从而使得影像表达具有简明扼要的观赏性。在他们的宣言作品《带摄像机的人》中,记录画面会不时插入摄像机和摄影师的工作状态,在对摄影技术的有意揭秘中包含着无限赞美。或是受此启发,陆庆屹在导演《四个春天》时也常常从摄影机背后跳到画面中参与父母的对话,虽然他用微微仰拍的镜头进行封闭式构图,将日常生活的图幅做了审美化处理,打造了一个充满仪式感的生活大舞台,但他仍试图进行偶尔的自我解构,不断跨越记录者和参与者的身份以求达成观赏性和真实性并重的艺术效果。
相比让摄影机背后的主体不避讳地参与到记录过程中,以“真理电影”派为代表的一批观点则要大胆许多,他们主张发挥摄影机的“催化剂”作用,不安于静待事件的发展,而致力于主动促成非常状况的发生,创作者公开地与被记录者互动,或是加速事态的升级,或是消除拍摄对象过分防范、过分期待的封闭因素,从而使真相得以浮现。例如《北京的风很大》,记录团体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无差别地主动向随机路人询问同一个问题,大家各种各样的表现被镜头真實记录下来,充满意想不到的趣味性。梅索斯兄弟的作品《灰色花园》记录了一对母女的纠葛,其中女儿迪伊因为镜头的介入格外具有表现力;讲述中国春运的《归途旅程》也有一场女孩和父母吵架的内容,他们的争吵因为摄影机的存在而得到激化……
如果能使人物的表达和事件的发生更加自如,那么摄影机的介入便不意味着削弱真实,这种良性互动反而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得以离真实更近,也让被记录的事件会更具有观赏性一些。因为有时候,如果没有镜头的刺激,很多话并不会被讲出,很多事也未必会发生。但反过来,如果摄影机和背后的记录者没有拿捏好介入的程度,过分干扰事件的走向,又或者被摄对象面对镜头被激发出表演型人格,这也是需要规避的问题,不可为追求观赏性的效果而舍弃纪录片真实性的初衷。
(二)适当的组织搬演和推测再现
纪录片在发轫之初就有组织搬演的习惯,世界上第一部纪录片—— 《北方的纳努克》就搭建了一个剖面的雪屋,用来让纳努克人表演他们平常的生活方式,这部纪录片后来又安排了一场原始捕猎大戏,为达到理想的镜头呈现,导演因使用了死掉的海豹而使整个纪录片陷入极大的争议中。尽管受条件和设备限制,弗拉哈迪不得不采取组织搬演的方式完成部分影像的表达,但他却尽可能真实地展现了纳努克人的日常生活状态,让更多人有机会得以了解这个少数民族族群的同时也肯定了纪录片的这种表达方式。事实上,在拍摄纪录片时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事发偶然或素材丢失都有可能导致重要内容的错过,只要并非虚构,适当的组织搬演无可厚非,甚至可以提升纪录片的观赏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纪录片的发展,新纪录电影又提出:“纪录片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一切虚构手段与策略以揭示真实” ②的理念。如果事件已经过去多年,甚至当事人已经不在世,素来尊重“纪实真实”的纪录片是否就难以发挥其作用了?《细细的蓝线》解答了这个困惑,该影片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对于一桩发生在11年前的杀人冤案进行模拟重建,以各种虚构方式使不可再现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因极具风格化和观赏性而成为纪录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当所谓的“真实”不足以取信时,纪录片《浩劫》选择凭借当事人的口述重塑犹太集中营的历史现场,从而展现真实的另一种可能和关注姿态。
《关于克拉拉·海德布雷克的流言蜚语》的主角是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一位老人,当镜头关注到她时,这位老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导演通过细致分析她多年以来的收支试图描摹其生前的生活状态,虽然纪录片做出的推测未必就是真相,但镜头真诚展现导演和警方还原老人生平的全过程,又不失为另一种真实,观众跟随推测曾渐次靠近老人的生活,在真相周围徘徊,这也使得影片具有一定的参与感和观赏性。而后,纪录片又发展出“数字再现”“扮演再现”等多种模拟再现的方式,在观赏性大幅提升的基础上,纪录片对真实的探索也得以朝更久远的时空迈进。
(三)危机结构制造和个性化影像表达
有一部分纪录片理论学派不认同摄影机应该介入到事件中参与叙事的观点,例如“直接电影”的态度就是不干涉、不影响、不采访、不解说、无灯光,排除一切可能破坏原生态的主观介入。创作者只知道要拍摄什么人、什么事, 或什么人的什么事,基本知道拍摄目的,但是基本不清楚拍摄结果,也无法知晓成片将是个什么样子③。但值得注意的是,直接电影倾向于选择生活中本就具有戏剧冲突的题材,并通过不介入的方式制造危机结构,营造矛盾冲突。伊文思导演的《新的土地》以围海造陆为主题,通过架设海、陆、施工队三个摄制组,构建出三个阵营并产生对话关系,使影片在保证真实的前提下充满如故事片般具有观赏性的“危急时刻”。
有些纪录片,摄影机虽然没有明显地加入事件的叙述中去,却用自己独特的镜头语言和个性化影像表达传递了真实性之外的一份独立思考和情感表达,带给观众不一样的审美体验。卡瓦尔康蒂“第三先锋派”的代表作《只有时间》通过精巧迷人的视觉、节奏等元素呈现出对巴黎时光“通感”般的记忆,将纪录片的观赏性和美学价值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鲁特曼在另一座城市拍摄的《柏林:城市交响曲》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几何形构图与交响乐的交相辉映,一场精彩的城市漫游由此展开。以及2014年的韩国纪录片《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导演拍摄的主角是一对高龄老夫妇,镜头却总是对准一条江水,江水的流速与清浊都被赋予了对生命的象征:在两位老人相濡以沫的日子里,江水缓缓前行,象征着时间的流动和生命的慢慢逝去;老人生病时,江水是混浊激涌的,仿佛表明老人的生命正在快速走向终点;当老爷爷离世之后,江水又复归于平静,就像起起伏伏的人生,或急或缓,终将不停歇地奔赴终点。
三、后期制作:赋予记录以时间
纪录片是以时间为基础的影像叙事艺术,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时间叙事的处理直接影响纪录片的基石——真实性,同时也影响着其叙事与审美。④任何事件一旦被赋予时间都会变得有价值,因为时间本身是珍贵的,琐碎的事物经过时间的沉淀便拥有了重量,在纪录片相对较短的单位时间内得以看到时间飞速发展留下的痕迹也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
《龙哥》是导演周浩的一部独立作品,他跟拍三年真实记录了瘾君子阿龙是如何在危险边缘游走并最后堕入黑暗深渊的。龙哥既是城市里走私、吸食毒品的毒瘤,又是身边人的“活菩萨”,不同于其他吸毒者萎靡不振、麻木空洞的模样,龙哥衣着干净保持着最后的体面,他还有些许的人情味,会接济同伴,帮助和他一样落魄的人,他說自己是“垃圾中的精英”。龙哥总是明日复明日地表达自己要戒毒的决心,结果换来的却是他开始一次次找导演借钱却始终交不起房租,只能跑出去偷东西又被打得浑身是伤地送回来,后来龙哥抛下女友消失得无影无踪,导演最后一次听到龙哥的消息是他在云南运毒被抓进监狱判以死刑。周浩将深入吸毒者窝点的这三年时间最终化成104分钟的影像,我们同他一起见证了一个尚存良知之人被毒品摧毁人格后的快速堕落,这一切是那么突然但又那么真实而残酷,令人触目惊心。
鸿篇巨制《人生七年》记录了来自英国不同阶层的十四个7岁孩子,摄制组每隔七年对他们的现状进行一次回访,至今已有56年之久。在这十四人中生活最具有戏剧化的当属于Tony,他15岁辍学参加过三次骑马比赛,因没能成为骑师最终转行为出租车司机;25岁父母双亡,兼职了六年临时演员;35岁与小舅子尝试开酒吧,一年后倒闭;42岁参加电视台剧集补贴家用;49岁生活有起色后搬到西班牙度假屋准备筹划一番新事业;56岁因全球经济危机,西班牙的事业计划泡汤;63岁,他卖掉西班牙的房子重返出租车行业,却遭受到UBER带来的行业冲击……在此期间Tony还主演了一部以自己生活为蓝本的电影。对于其他大多数被拍摄者而言,每隔七年的采访会谈到的可能大多都是工作家庭上的小事,有人按部就班地平步青云,有人始终在找寻人生的意义。但把他们的人生放到半个世纪的维度里,观众却可以得到某种关于人生的启示:7到14岁的人生或许尚可以被预测,之后的时光却是充满未知且极具个性的,但到了63岁,所有人又回到了对相同问题的思考——疾病、家庭和死亡。用一段影像的时间,看完14个陌生人的大半生,这样的纪录片是极其厚重且具有观赏性的,时间行至第八个七年,它甚至拥有了一种治愈的力量。
四、结语
生活是上帝导演的一场大戏,可生活将要驶向何方,有时连上帝都不知道。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纪录片里,绝对的真实从来都不存在,“真实”只是对客观存在不带评价的呈现,是否具有“观赏性”也只是呈现方式的一种选择,但纪录片要背负的却有更多,它的最终目的是要超越真实表达观点,将“正在发生的历史”保存下来,留给千秋万代去做评价。
注释:
①赵莹:《浅谈电视纪录片的选题与策划》,《大众文艺》2022年第5期,第105页。
②林达·威廉姆斯著,李万山译:《没有记忆的镜子——真实、历史与新纪录电影》,《电影艺术》2000年第3期,第124页。
③邵雯艳、倪祥保:《类型、方法、主题的交互相关:“直接电影”再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115页。
④潘可武、董金迪:《长时间跨度纪录片的影像形态特征及人文价值——以〈人生七年〉系列纪录片为例》,《电视研究》2021年第05期,第90页。
参考文献:
[1]赵鹿鸣.私纪录片的概念梳理与公共性刍议[J].电影新作,2020,(02):109-115.
[2]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3]杜晓峰,游欢.私纪录片《四个春天》的公共传播价值与伦理困境[J].声屏世界,2020,(16):68-69.
[4]王家东.从真理电影到真实电影:纪录观念的继承与革新[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8,(03):9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