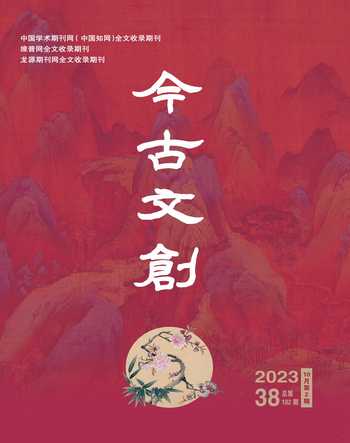刘长卿“吏隐”思想探析
沈佳迪
【摘要】刘长卿诗多有对隐逸的向往,而浙西严子陵钓台又以隐士严光著称。因此当刘长卿身处浙西时,严子陵钓台便时常会引起刘长卿的隐逸之情。刘长卿之隐为吏隐。诗中之隐是自然之隐,睹山水而羡幽静自在的生活;是现实无奈之隐,弊端丛生,逐臣无用,聊以慰藉;是难以实现之隐,子陵高骨,辅明君光复汉室,功成拒官,刘长卿生不逢时,抱憾终身。
【关键词】吏隐;刘长卿;严子陵钓台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8-003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8.011
基金项目:浙江省新苗人才计划实施计划资助项目“诗路文化带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振兴状况调研——以浙西四古村(镇)为例”(项目编号:2022R409A022)。
有唐以来,以文取人的科举使寒门子弟得以有治国平天下的可能,入仕而兼济天下成为读书人的选择。然而长久以来,以隐为尊的风尚和和文人诸多的个人原因使隐居备受士子追捧。因此,出与入、穷与达不仅代表了中国士大夫典型的双重人格,也是他们的矛盾。对于深受儒家入世价值观影响的读书人而言,传统的避世隐逸虽然获得了个体自由,但完全放弃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也不无遗憾[1]。而若一味关注社会责任感,在个人情感和精神的完满上便有缺失。于是他们的诗作中便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吏隐。
“吏隐”一词究竟起于何时,已不能确考。从现有文献看,它在唐初已开始使用。宋之问《蓝田山庄》有“宦游非吏隐,心事好幽偏”之句[2]。目前学界对吏隐的概念界定和使用还十分模糊。就笔者而言,更赞同将“吏隐”大致分为“兼吏隐”和“隐于吏中”两种。前者兼有为官恪勤政事的济世情怀和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后者则淡化为宦者的责任感,以“隐于吏中”求禄存身[3]。进一步说,前者是向往山水园林,但心中难忘官职责任的身心分离,后者是悠游山水,不为官职责任所困的身心合一。因为“吏隐”的对象不是身居显位的高官,而是官卑位低的风尘吏,或迁谪外放的地方官,所以“吏隐”概念更多时候指前者。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考证[4],刘长卿在浙江的仕宦经历分别是肃宗至德三年正月,摄海盐县令;大历十年秋至大历十一年秋间,除浙西睦州司马,在任约四、五年。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5]另有肃宗宝应二年,刘长卿量移浙西某地;大历四年,越州之行,再巡浙东、浙西诸州。故刘长卿与浙东、西结缘不浅。根据考证可知,刘长卿多在浙西地区活动。而浙西以富春江显,富春江以东汉隐士严子陵名,所以严子陵钓台在刘长卿的浙西诗中也出现最频繁。
因刘长卿在两唐书中均无传记,故历来学界对其生卒年多有争议。闻一多《唐诗大系》认为其出生于709年,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一文则定为710年或725年前后,储仲君在《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定为726年。虽然其生年众说纷纭,但无法否定的是刘长卿的青少年时期至少在开元盛世度过,受过盛唐文化的熏陶,存有强烈的由文事立致卿相的功名愿望。但安史之乱爆发后,民生凋敝,国力衰微,刘长卿又经两次受诬贬为闲职。此时,隐逸便成为逃避现实和内心痛楚的最佳方式。故本文主要以刘长卿的严子陵钓台创作为具体分析对象,以“隐”为中心,探析其“吏隐”思想的内涵。
一、浙西嘉景,向往之隐
浙西的好山好水自古以来饱受文人赞赏,孟浩然在睦州建德作“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杜牧在睦州作“有家皆掩映,无处不潺湲。好树鸣幽鸟,晴楼入野烟”等。刘长卿在浙西所作虽多为送别诗,但其所写之景多含隐逸之情。
奉使新安自桐庐县经严陵钓台宿七里滩下寄使院诸公
悠然钓台下,怀古时一望。江水自潺湲,行人独惆怅。
新安从此始,桂楫方荡漾。回转百里间,青山千万状。
连崖去不断,对岭遥相向。夹岸黛色愁,沈沈绿波上。
夕阳留古木,水鸟拂寒浪。月下扣舷声,烟中采菱唱。
犹怜负羁束,未暇依清旷。牵役徒自劳,近名非所向。
何时故山里,却醉松花酿。回首唯白云,孤舟复谁访。
该诗作于大历四年春,刘长卿越州之行,再巡浙东、浙西诸州。此时,他在浙西美景中摆脱了十年宦海沉浮的杂务与缠累,得到了个人世界中短暂的精神满足,因而生隐逸之情。其一,诗中以“夕陽”“古木”“寒浪”等词,突出环境之隐。此“隐”并非是陶渊明的山村之隐,而是山间幽静、清寒之隐。寂静是指古木千百年来未曾被伐,可见人少有踏足。清寒是指落日将坠,暖意渐消,寒意渐生,“寒浪”更显其寒。其二,通过“自”“独”等词,突出心境之隐——孤独。环境之隐是鲜少与人接触,几乎与世相隔的物理外在世界。而心境之隐则是执着于精神的休憩与享受,不以尘世功名为转移的心理内在世界。心境与环境之隐在一定程度上为刘长卿建构了远离尘世的个体空间。其三,“钓台”“古木”等词突出体验之隐,即个体心性的超验与自我情感的完善。“钓台”传说为严子陵垂钓处。《后汉书·严光传》载:“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光乃变姓名,隐身不见。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6]前两“隐”均是诗人执着于现实中的“隐”,而面对浙西之景,怀念东汉隐士严子陵的刘长卿则已经跨越历史、时空,与严子陵的“隐”共鸣,以弥补现实中失落的情感,达到对个体心性情操的超越。诗中“清旷”表明他对隐居生活的向往。“清旷”本源自《后汉书·仲长统传》,有“以乐其志”之意。但于他而言,山水只能自娱,绝不能乐志。虽然刘长卿有意以隐为志,但据后文分析,他终究不愿主动放弃尘世功名。他的“隐”更多是一种逃避。
二、逐臣有志,无奈而隐
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吐蕃乘虚入侵,社会动荡不安;宰相无谋,将帅失策,宦官误事,朝野混乱。虽然中唐的士人们曾积极参与时政以阻止社会颓势,以求裨补时弊。但社会种种危机已显,挽救不过杯水车薪。出于对仕途政治的失望,中唐士人有了强烈的归隐意愿,这是他们对世事的疏离和对政治的离心倾向。
对酒寄严维
陋巷喜阳和,衰颜对酒歌。懒从华发乱,闲任白云多。
郡简容垂钓,家贫学弄梭。门前七里濑,早晚子陵过。
大历十一年秋,刘长卿受诬再贬睦州司马。该诗为大历十二年春,刘长卿至睦州任所所作。在诗中,一方面以“陋巷”“郡简”“家贫”等词写出生活清贫。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四月二十八日厘定京、外官月棒标准。上州司马的月俸为50贯,其余“中州、中县已下,三分减一分”,即为上州、上县同名职事官的三分之二[7]。除日常增俸,刘长卿月俸应在16至50贯间。安史之乱后,平常米价大概为两三千文一石[8],因此生活并非如诗人所述般拮据。但他有意突出贫寒和隐,并以“衰颜”“华发”等点明韶华已逝,笔者认为其意蕴丰富。
一是不满怀才却被贬为闲官睦州司马,“隐”是不得已的隐。司马到手俸禄略高于同级官员,但手中无实权,平常工作比较闲散。刘长卿只有两条路。如果辞官,失去睦州司马的官职表明他自行断绝谋生的经济来源。因为建中初年,米价两百钱一斗,比战前起码贵了四五倍[8]。又加之连年的赋税,这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根本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接受任职,消遣时日的生活方式有二,如纨绔子弟纵情享乐以麻醉本心,如隐士安贫乐道,逃避现实。刘长卿既然无法接受放浪形骸,也只能选择无奈隐居。二是明白无力改变现实后,有意疏离朝政。“隐”是对现实的逃避,对内心创伤的抚慰,对朝廷含蓄的不满。他本身所追求的不是实在的隐逸,而是一种既为朝廷竭力盡忠,又不放弃个人修养的“隐”。很显然,朝廷将刘长卿贬入远地的用意之一是拒绝他尽情施展才华的机会。那么,刘长卿以“隐”来隐藏才能,曲折地发泄对朝廷的不满。而刘长卿为舍心中烦闷,享受逸乐而吏隐。有了逸乐,便可以忘归。他以“吏隐”来抚慰心中不受重用和战乱带来的创伤。
却归睦州至七里滩下作
南归犹谪宦,独上子陵滩。江树临洲晚,沙禽对水寒。
山开斜照在,石浅乱流难。惆怅梅花发,年年此地看。
此诗亦作于大历十二年初春,刘长卿至睦州时。七里滩北岸富春山相传为东汉严光隐居垂钓处,即严子陵钓台。而“谪宦”实为刘长卿“隐”最重要的原因。
天宝中,刘长卿进士及第[9](参考傅璇琮考证,原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存疑),而当时他已为棚头,即国子学生或崇文、宏文两馆诸生之应试者,推声望者为棚头,足见其当时文采斐然。不过,“念旧追连茹,谋生任转蓬。泣连三献玉,疮惧再伤弓。”满腹才华却接连不第,反映出当时有才之人受到压抑的黑暗的科场。待终于及第,授官以来,仕途也是坎坷。第一次被贬潘州南巴县,其被贬案件之因已不可考;第二次因性情刚直,得罪吴仲儒,被诬告贪污,贬为睦州司马时。独孤及谓刘长卿“曩子之尉于是邦也,傲其迹而峻其政,能使纲不紊,吏不欺。夫迹傲则合不苟,政峻则物忤,故绩未书也,而谤及之。[10]”可知刚而犯上的“罪名”将刘长卿的政治才能与政绩涂抹殆尽。但作为刘长卿缺陷的“有吏干,刚而犯上”,实际上是自古文人治国兴邦,名垂青史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第二次被贬睦州司马时,刘长卿受诬为一原因,刚而犯上也是一因。因此,“谪宦”可以是刘长卿的自嘲和自我排解。因此刘长卿被逐不是无才,而是与吏治腐败,官员趋炎附势的官场相悖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心境下,刘长卿是面对弊端丛生的社会,无能为力而隐,是逃避现实世界来抚慰创伤,缅怀盛世而隐。
三、客星严光,欣羡其隐
作为最受推崇的古代隐士,严光身上凝聚着唐代士人对“隐”的追求。汉代严光之隐,是以绝意功名为前提的保持疏狂高逸个性的适意遁世,其精神境界在士人心目中是最高层次的,他的隐逸纯洁无瑕,成为超脱于世俗的名利荣辱的自由人格的象征和高情逸趣的楷模[11]。严光拒绝功名的隐与节操高骨是刘长卿等一众唐代文人无法求得的追求。但唐代文人追求的严光之“隐”未止步于此,更重要的是“隐”背后的深层内涵。
严陵钓台送李康成赴江东使
潺湲子陵濑, 髣髴如在目。七里人已非,千年水空绿。
新安江上孤帆远,应逐枫林万馀转。古台落日共萧条,寒水无波更清浅。
台上渔竿不复持,却令猿鸟向人悲。滩声山翠至今在,迟尔行舟晚泊时。
该诗作于天宝中,李康成赴使江东,刘长卿所赠。虽为送别诗,但全诗围绕严陵钓台及其周遭景物展开,具有很浓的怀古色彩。诗中最后一句意谓无论滩声山翠,犹似昔日,先贤遗音,仍在于此,此即君流连不前之因。诗中所叙对象虽为李康成,但实为刘长卿自白。流连不仅是因严陵钓台的风景,也是怀念物是人非的严陵钓台,凭吊已逝的严子陵。诗中“鱼竿”是因严子陵以垂钓七里滩为隐,故鱼竿为其象征物,而后世诗歌中也多以鱼竿、垂钓等代表自己的隐居意象。但七里滩山高水急,非垂钓之所。然前贤垂钓,意不在鱼,只是表示隐逸的人生态度,而隐逸绝非如此简单。
前文已述,史书称严光少有高名,与刘秀同游学,便无下文。以二人客星冲座而笑应之的情谊推之,严光的辅佐与提点在刘秀光复汉室中占重要地位。但刘秀即位后,严光至死拒官,因此严光之隐是功成身退,泛舟五湖。所以“隐”首先是助帝王平定寰宇的雄心与功成名就,其次才是归隐山林后个人的充盈和心灵的释然。而刘长卿便是“隐”背后的功成名就。
《后汉书》载:“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6]傲视王侯,长揖君王的严光在帝王刘秀面前依旧我行我素的性子是历代文人咏怀的集中点,但潜藏根底的仍是帝王对臣子的宽容和大度。《唐才子传》中评价刘长卿“清才冠世,颇凌浮俗,性刚,多忤权门,故两逢迁斥,人悉冤之。”[12]以刘长卿性情刚烈,常不附庸权贵或直言不讳以致两次遭贬的根本原因来看,权贵不容他人忤逆,不愿听从劝谏与光武帝对严光的待遇实际暗含刘长卿对善于知人的明君的期盼。刘秀多次请求严光接受官职,不惜亲自拜访,严光屡次拒绝后仍得善终的结局的辅证,同样暗示刘长卿渴望明君知人善用,自己能受重用,根本上仍是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四、结语
总而言之,刘长卿的“吏隐”思想最根本的仍是仕与隐的矛盾。首先,刘长卿因山水之景而生隐逸之情,向往幽静而自在的隐居生活,注重自身体验的完满,但又无法与现实斩断羁绊。其次,所谓现实,是安史之乱,国势将倾,官场腐败,空有才华,受冤被逐。在生不逢时的境遇中,他受到青少年时建功立业思想的影响,渴望以自身才能挽救将倾大厦,但无权无势,只能被迫闲散度日。而隐逸便是在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后,逃避现实、抚慰创伤的药剂。最后,他所追求的隐逸绝非普通的隐,是功成名就后的隐,是明君知人、大度的隐。正是如此,刘长卿一生都在吏与隐之中徘徊。
参考文献:
[1]朱曙辉.论唐宋隐逸文化的新发展[J].兰台世界,2014,(27).
[2]蒋寅.古典诗歌中的“吏隐”[J].苏州大学学报,2004,(02).
[3]李红霞.论唐诗中的吏隐主题[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6(06).
[4]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
[6](南朝宋)范晔著,李立,刘伯雨选注.后汉书[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
[7]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修订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8]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9]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唐)独孤及.毗陵集 四库唐人文集丛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1]李红霞.唐代隐逸风尚与诗歌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2.
[12](元)辛文房撰,徐明霞校点.唐才子传[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