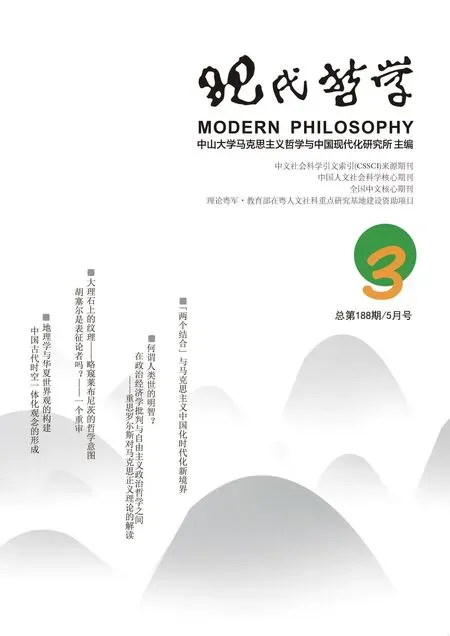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在晚明中国
谭 杰
晚明时期,作为西学之核心的西方哲学,由利玛窦(Matteo Ricci)等耶稣会士大规模系统译介入中国。彼时欧洲处于文艺复兴末期,伊比利亚半岛经历了经院哲学的复兴(1)See John P. Doyle,“Hispanic Scholastic Philosoph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enaissance Philosophy,ed. by James Hanki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 250-269.,耶稣会士来亚洲之前在伊比利亚半岛所受的大学哲学教育,是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主体的经院哲学。其大学哲学课程教材“可英布拉评论”(Commentarii Conimbricenses),乃是基于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评论,涵盖了逻辑学、自然哲学、灵魂论、伦理学等各方面的近10部拉丁语著作。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在晚明时期通力合作,主要基于“可英布拉评论”,陆续译出《灵言蠡勺》《寰有诠》《空际格致》《名理探》《修身西学》等中文著作,首次较为系统地呈现了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当下学界对此多有关注。(2)See Thierry Meynard,“Aristotelian Work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Monumenta Serica 65 (1),2017,pp. 61-85;[法]梅谦立(Thierry Meynard):《从邂逅到相识: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相遇在明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在主流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之外,经过数百年来人文主义学者的努力,古希腊罗马经典已重现天日并在欧洲知识界为人所熟知,其中便包括柏拉图主义哲学。后者与主流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一道,在晚明藉由耶稣会士的著述来到中国。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学界少有人涉及。本文将分神学、创世说和灵魂论、伦理学三个方面,探讨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思想在晚明中国的传入。
一、通往上帝的道路
在首刻于1603年的《天主实义》首篇,利玛窦以六个论据论证天主乃万物的主宰者和创造者,然后以一段长文进一步解释天主之所是。这一段长文首先阐述“四所以然”(四因说),论证天主与世间万物不同,乃世间万物的“作与为之所以然”(动力因与目的因);接着讲述一对西方古代君臣的对话,阐明人无法理解无穷的天主,并论证人无法以理解世间万物的“是”“有”来理解天主,只能用“非”“无”来理解天主;最后论证天主乃无始无终、全能全知全善之存在。(3)参见[意]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法]梅谦立注,谭杰校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85-90页。这指明了通往天主的三条道路“原因-否定-卓越”(causa-negatio-eminentia),完整再现了代表经院神学之正统和巅峰的阿奎那的标准论述。(4)See Thomas Aquinas,Summa Theologiae,Ⅰ.q.12.a.12;Gregory Rocca,Speaking the Incomprehensible God:Thomas Aquinas on the Interplay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Theology,Washington,D.C.: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2004,pp. 49-55.其中,第二条否定的道路(via negativa)精确还原了两个方面:人无法理解天主(incomprehensibilia),且人也无法认识到天主自身的本质(quidditas)。(5)See Rocca,Speaking the Incomprehensible God:Thomas Aquinas on the Interplay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Theology,pp. 27-48.
一般认为,阿奎那关于通往天主的三条道路的论述,直接继承自公元5-6世纪伪迪奥尼索斯(Pseudo-Dionysius the Areopagite)的《圣名》(DivineNames),后者是融合柏拉图主义和天主教思想的关键人物。继续往上追溯柏拉图主义的谱系,“三条道路”的雏形最早见于公元2世纪中期柏拉图主义者阿比诺斯(Albinus)的论述,且其论述中的两条道路都可以直接溯源到柏拉图的著作。第一条“原因”道路与“类比”(analogia)直接相关,所比较的是太阳、视觉与第一心灵(First Mind)、我们的心灵:正如太阳是视觉及其所见的原因,第一心灵(后来则是天主)是我们的心灵及其所知的原因。这一类比直接来自柏拉图在《理想国》(Respublica)中的太阳与善之间的类比。第三条“卓越”道路则与上升有关:从身体的美上升到美、善等理念,并继续上升到卓越的神。这是柏拉图在《会饮》(Symposium)中所描述的上升之路。第二条“否定”的道路,可以追溯到稍晚的公元3世纪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他认为天主无法以肯定谓词描述,超越了范畴。(6)Ibid.,pp. 9-10.至于利玛窦在第一条道路中未提源自柏拉图的“类比”说,改以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诠释“原因”道路,则可能因为早在伪迪奥尼索斯的论述中,“原因”已取代“类比”,成为第一条道路的核心概念。除第一条道路之外,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的上述思想,经由经院哲学关于通往天主的“否定”和“卓越”道路的论述,在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中被呈现给中国士人。
在《天主实义》第二篇末尾,利玛窦引述多部中国先秦古籍,向“中士”证明,天主即中国古籍中的“上帝”,中国上古已有对天主的信仰。(7)参见[意]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第99-101页。这一著名段落向来被认为是利玛窦适应策略(accommodation strategy)的代表性论述。有论者认为,利玛窦是通过自然神学(theologia naturalis)的方式在中国布道:《天主实义》前七篇均以理性辩论铺陈天主之道,仅以第八篇陈述耶稣的启示事迹。其后耶稣会由自然神学转向古代神学(prisca theologia),则有待近百年后《中华帝制历史年表》(TabulaChronologicaMonarchiaeSinicae,1686)和《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SinarumPhilosophus,1687)的问世,其中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尝试建立中国历史编年,将中国历史纳入圣经历史,证明中国人乃诺亚的后人。至于在此之后的索隐派(Figurist),则可视为历史神学的滥觞。(8)See Giuliano Mori,“Natural Theology and Ancient Theology in the Jesuit China Mission”,Intellectual History Review,2020,30 (2),pp.187-208.柏拉图主义者费奇诺(Marsilio Ficino)被公认为流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古代神学思潮的发明者,他建立了一个自赫尔墨斯(Hermes)至柏拉图的历史谱系,试图证明耶稣诞生之前的古代世界已存在对天主的信仰。就建立历史传承谱系这一点来说,柏应理对中国历史所进行的编年工作,当然更符合费奇诺的古代神学思想。尽管利玛窦并未进行这种系统的历史谱系工作,但他通过诉诸中国古籍将天主(上帝)引入中国历史的做法,已部分超越了纯粹以理性证明天主存在的自然神学之路,可视为其后继者构建更系统的编年史神学的先驱式尝试。
利玛窦的适应策略受到来华传教士的诸多批评,由耶稣会士陆若汉(Joao Rodrigues)与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所发动的译名之争,以及后来由道明会和方济各会所发动的礼仪之争,均表明耶稣会内部和天主教其他修会有不同的声音,反对利玛窦的自然神学和适应策略,认为人无法只凭借败坏的理性认识天主(这点与否定神学直接相关:正由于人无法凭借理性完全认识天主,人类才需要历史启示)。有趣的是,这一奥古斯丁主义观念同样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永恒理念超越人的理性。支持利玛窦一方的耶稣会士所做的编年史神学构建,正是为了回应以上反对思潮。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的不同部分,经由不同的解释和再解释,构成来华传教士针锋相对的两大神学观念的基础,并最终合力促成了明清时期中国传教士由自然神学向历史神学的转变,这一点着实耐人寻味。
二、创世说与灵魂论
在否定神学和古代神学方面,柏拉图主义思想殊为正面,充当了通往上帝的道路的基石。在译介入晚明中国的创世说和灵魂论方面,柏拉图主义思想则是作为被批驳的靶子而出现的。
刊刻于1637年的两卷本《寰宇始末》,是一部论述天主创造天地万物的宇宙学著作。在此书上卷第四章《寰宇非太极所生》开头,高一志(Alfonso Vagnone)写道:“上古西域有士古略,稽寰宇之初,自立别学,云一元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谓此论复见于中华,曰: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兹理须详究之。”(9)[比]钟鸣旦等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册,台北:利式学社,2009年,第178页。在此之后,这一章的内容主要批驳中国的太极创世说。“古略”此处“一元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说法应化自老子《道德经》,高一志无意严格引述“古略”的观点,而是借其引出太极创世说以详细批驳之。此处“一元”生出万物的创世说,以及“古略”的译名,让人想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创世说。在普罗提诺的创世说中,世界来自绝对简单、自足的太一(The One),从太一中流溢出心智(the Intellect),心智进一步产生了灵魂(the Soul),最终灵魂产生了世间万物。普罗提诺的创世说向来被天主教视作“从无中创造”(creatio ex nihilo)的正统创世说的一个典型异端,高一志在此章中引述“古略”之说驳斥“寰宇由太极所生”的中国本土观点,实乃应有之义。
与“从无中创造”的创世说对应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一生万物”的异端之说类似,在灵魂论中,与“从无中创造”的正统学说相对应的异端之说,同样来自柏拉图主义。这一点反映在刊刻于1624年的《灵言蠡勺》的以下段落:“何谓从无物而有?以明非天主全体中分予之一分也,亦非他有大灵魂分彼而予此也。”(10)[意]毕方济、徐光启:《灵言蠡勺》,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东传福音》第2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500页。在这一章中,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首先陈述了“亚尼玛”(灵魂)的九个特性,然后依次解释这九个特性。“从无物而有”乃“亚尼玛”的第六个特性,毕方济对其的解释在于陈述与“从无物而有”相对应的两个异端之说。第一个异端之说乃“(亚里玛)非天主全体中分予之一分”,这显然对应上述普罗提诺的“流溢”(emanation)说。第二个异端之说乃“他有大灵魂分彼而予此”,指的应是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的“世界灵魂”概念。在解释了“从无物而有”之后,毕方济接着解释:“何谓成于赋我之所、赋我之时?以明非造成之初先造几许灵魂,原居天上,与天神同,或他贮,随时取用也。”(11)同上,第500页。这里所批评的是柏拉图《斐多篇》(Phaedo)中的灵魂观念。奥古斯丁在《论灵魂不朽》(Deimmortalitateanimae)中继承了这一观念,但并未被后来的天主教会所接受。
由上可知,在创世说和灵魂论方面,与欧洲本土一样,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相关学说是作为正统学说的异端靶子,出现在晚明中文译著中的。
三、“证道故事”中的柏拉图形象
在神学、创世说和灵魂论方面,柏拉图均隐于晦涩的观念之中,未现其名。一旦关涉到伦理学,柏拉图便不再“匿名”,而是亲自现身,铺陈道德教诲。
就笔者所见,柏拉图之名在中国的初次出现,应是在高一志与中国士人合作完成、刊刻于1632年的《童幼教育》中。这部书比拟儒家童蒙教育著作朱熹的《小学集注》而成,以西方古代名人的言与行来阐述童蒙教育之道。全书可分为父母和教师的教育之道、童幼诸品格之培养、童幼在饮食和衣裳等方面的习惯之养成三个方面。(12)参见[意]高一志:《童幼教育今注》,[法]梅谦立编注,谭杰校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21-122页。作为“上古大贤”的“罢辣多”,在此书中十余次出场,以其言行佐证童幼教育之道。
在《童幼教育》第一部分论述教师、父母等诸角色的教育作用时,高一志数次提及“罢辣多”:“罢辣多,上古大贤也,尝谓天主之广泽、父母之养育、贤师之教习,三者必不可测,并不可报,岂不信哉?”“昔者厄肋济亚文学名国,有一童习于罢辣多名门,久之学成而归,适睹其父诟厉异常,大怪曰:‘侍罢辣多未闻如是也,久于此,恐吾所修悉亡矣。’”“罢辣多大贤常戒乳母,勿使乱述虚传及井市邪言,曰:‘夫童之心若蜡焉,印之易于成迹。’”(13)同上,第166、167、171页。以上第一条格言很难归于柏拉图名下,应是由高一志冠以柏拉图之名。第二个故事则确有出处,可追溯至于塞涅卡(Seneca)的《论愤怒》(DeIra)。至于第三条格言中“罢辣多”所述儿童之心的蜡喻,可在柏拉图的《法律篇》(TheLaws)中找到出处,但将其用于乳母之戒,则又是高一志的发明。
第二部分论述童幼应修习仁孝忍智四德。除针对天主的“仁”德之外,“罢辣多”在其他三种德性均现身说法,教育幼童。关于孝德,“罢辣多”有如下两条格言:“罢辣多,上古之大贤,其治国所叮咛者,惟是奉敬天主第一、事奉父母第二。盖曰:‘天主之恩大,而父母之恩亦大,故施仁于天主者,无不施仁于亲;不施仁于亲者,可谓施仁于天主乎?’”“罢辣多治法禁曰:‘诸长者勿轻慢之,否将得罪于天主,而为国家之戮矣。’”(14)同上,第183、188页。以上第一条格言显然接续了第一部分托名于柏拉图的第一条格言,在此所强调的则是孝德。
即使就天主教式的忍德而言,“罢辣多”亦堪作表率:“罢辣多久习此学,计继其师之美业,则避华美之地,而于荒僻之处设帷焉。志者解其意之妙曰:‘诸幼易肆志纵欲,莫如景丽之地也。’”“由是罢辣多录治国之美法曰:‘幼者所宜常从者二,于恶即羞、于善即勤而已。’”(15)同上,第191、196页。这两段同样可见于柏拉图的生平和著作中,但高一志将其抽离了本来的语境,用以阐明童幼应节欲和羞恶。
至于智德,“罢辣多”则有更多阐发:“罢辣多氏,古文名宗,谓真者乃众善之帅也,进即群德从之,退则群德并退。”“罢辣多氏禁工人无得造赝物,犯者罚正值。”“故罢辣多尝云:‘国家之幸,莫大乎使持政者务于文学,或务于文学者持国政也。’”“是故古学名宗罢辣多治国妙术,凡著述正道之书,必重酬之;著述非道之书,必严罚之。”“罢辣多尝于邪书之害,譬之毒泉流行,推万民而毙之。”(16)同上,第202、205、208、212、213页。“罢辣多”不仅重文学和教育,更重于区分教育中的正书和邪书。“罢辣多”的这一形象,显然可追溯至其在《理想国》中将诗人驱逐出城邦的著名论述。在柏拉图看来,诗人之恶在于以花言巧语扰人心智。对天主教来说,文学最为紧要之处在于其所承载的道德教化。扰人心智的文学是坏的文学,正人心智、引人向善的文学则是好的文学。耶稣会之成立,正是为了对抗欧洲北部宗教改革之邪说。高一志秉承天主教的文学教化观,将柏拉图的诗与哲学之争,不动神色地引申和转化为正书与邪书之争。值得一提的是,“罢辣多”有“上古之大贤”“古文名宗”“古学名宗”等头衔。在耶稣会士初入中国的晚明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妇孺皆知的先贤在中国显然无人能识。因此,高一志必须再三强调“罢辣多”为“大贤”“名宗”,以建立起其言行类似于《论语》中“子曰”的道德权威性。
最后,在童幼的交友和闲戏习惯方面,“罢辣多”仍有所阐发,虽然其言与以上多条格言一样,并无历史凭据:“故罢辣多曰:‘父卒而遗宝资之重于子,大不如遗善友之众。’”“罢辣多尝曰:‘无事之时,为幼之所当谨也。’”(17)[意]高一志:《童幼教育今注》,第234、236页。
“罢辣多”于1632年在中文世界的首次现身堪称华丽:《童幼教育》十余次引述其言其行,对童蒙进行道德教化。要充分理解这一点,需要追溯欧洲文艺复兴伦理学的两个传统。由阿奎那在中世纪建立的经院伦理学传统,以简洁的语言、严密和细分条缕的论证为特征,乃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学伦理学教育之标准,直到17世纪末都有着持续的影响力。作为对经院哲学的反动,人文主义者倡导文辞优美、以民众道德教化为目标的人文主义伦理学,并在数百年间推动了古典著作的普及。(18)See David Lines,“Humanistic and Scholastic Ethic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enaissance Philosophy,pp. 304-318;David Lines,“Aristotle’s Ethics in the Renaissance”,The Reception of Aristotle’s ‘Ethics’,ed. by Jon Mill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p. 171-193.晚明来华耶稣会士所受的伦理学教育,结合了以上两大传统:受人文主义传统影响,在中小学时期,教师会在拉丁文和修辞学等课程中教授西塞罗、塞涅卡等古罗马作家文辞优美的道德哲学著作;(19)这一点可由高一志所受的教育窥见。(参见[意]高一志:《童幼教育今注》,第53-58页。)在历时三年的大学哲学课程的最后一年,伦理学教师教授伦理哲学(philosophia moralis),即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基础的经院伦理学。(20)See Ratio Studiorum:The Official Plan for Jesuit Education,trans. by Claude Pavur,Saint Louis: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2005,pp. 101-104.耶稣会士译介的西学伦理学,同样覆盖了以上两大传统:《修身西学》是唯一一部系统译介经院伦理学的译著;《交友论》《童幼教育》等十余部著作,则以“证道故事”(exemplum)的写作方式撰就,以寓言、世说、神话、传说等多种体裁阐明道德教训。耶稣会士偏爱译介人文主义伦理学远甚于经院伦理学,除风靡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潮对其的影响之外,也在于利玛窦很早便敏锐地发现,“证道故事”以故事和格言来进行道德教化的方式,与《论语》等中国先秦经典通过“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21)参见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来进行教化的方式相契合。(22)关于以上所论更为详细的论述,参见谭杰:《中西德性教育思想的融合——晚明传教士高一志德性教育思想研究》,《现代大学教育》2018年第4期;谭杰:《文艺复兴伦理学思想在晚明的译介》,陶飞亚主编:《宗教与历史》第1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19-145页。
鉴于此,我们便能理解,由于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主流地位,与欧洲本土类似,在晚明西学典籍中,与“束格辣德”(苏格拉底)、“比达卧辣”(毕达哥拉斯)等其他众多古代哲学家一样,柏拉图并非以抽象的概念和思想体系,而是借由人文主义的方式,以自身具体的言语和行动来进行道德教化的。我们也能够理解,何以“罢辣多”之所言所行(特别是所言),有相当一部分并无出处,或与柏拉图本来的历史形象多有出入。一方面,批判的历史观是启蒙时代的产物,对文艺复兴晚期的欧洲人来说,古代经典中记载的轶事本来就是“历史”;另一方面,耶稣会士撰写“证道故事”之目的在于进行道德教化,古代轶事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可进行涂抹的工具。(23)参见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85-192页。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耶稣会士所塑造的“摈弃邪书”的柏拉图形象。将柏拉图的诗和哲学之争与人文主义和经院哲学两个伦理学传统对观,我们能够发现,“证道故事”式人文主义伦理学传统正是以华丽的言辞来论道,与柏拉图深为摈弃的诗多有契合;而经院哲学中被斥文辞干瘪的概念和论证,正是柏拉图对话中所赞赏的苏格拉底式辩证法。当高一志有意或无意地将柏拉图的诗与哲学之争引申和转化为正书与邪书之争时,他并未意识到以下的悖谬:以“罢辣多”(以及其他西方古代先贤)之言行来进行教化的人文主义论道方式,恰好与柏拉图本人将诗人赶出城邦的提倡相抵牾。
四、结 论
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在晚明已有十分系统的译介不同,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系统译介,最早似乎只能追溯到民国以后。本文的分析表明,在早于民国数百年的晚明时期,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已点缀于主流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译著和各类其他西学著作中传入中国。源于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的通往天主的三条道路和历史神学,已融入向来被视为自然神学典范的《天主实义》,这与欧洲本土的发展是一致的: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主流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已融入诸多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要素。当然,仍有相当一部分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与其时的神学主流不相容:普罗提诺的“流溢说”和柏拉图的灵魂论,便是作为正统创世说和灵魂论的典型异端被引入中国的。最后,受人文主义影响,在“证道故事”类著作中,“罢辣多”多次现身说法,以故事和格言的形式在童蒙教育等方面进行道德教诲。
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已随着主流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在晚明时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文艺复兴时期随人文主义而复兴的其他哲学流派亦如此。斯多亚主义向来受天主教青睐,并对其影响颇深,利玛窦的《二十五言》便是直接译自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名篇《手册》(Encheiridion)。未来的晚明时期西学东渐研究,在关注主流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之东渐外,亦可将目光投向柏拉图主义、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Epicureanism)、怀疑主义(skepticism)等少数哲学流派之东渐,以呈现晚明文艺复兴哲学东渐之全貌。
最后,对于汉语世界的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研究来说,西方经典的翻译与研究,当然仍是首要之务,而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在明清和民国时期的译介与传播研究,亦能在此之外为传统的研究提供新的方向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