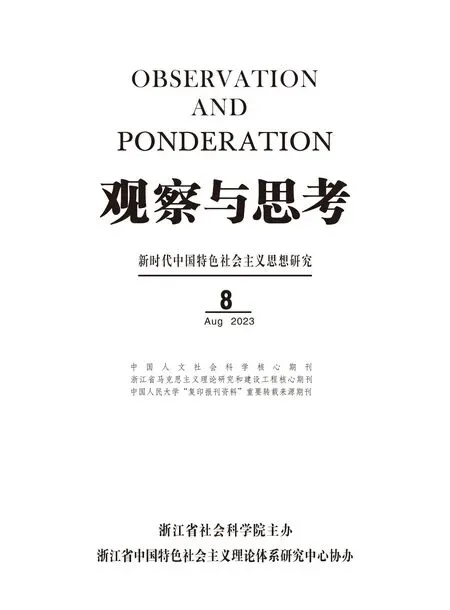“现实的个人”对“抽象的人”的批判性超越*
——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宫留记 李静
提 要:“现实的个人”作为马克思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出发点,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跨越青年黑格尔派用哲学词句所堆砌的“抽象的人”的思想武器,其不仅在反驳“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人学空场”的同时开启了人学研究的唯物史观视域,也在揭示人类解放的两大要素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追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秉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关怀,成为当今探索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因此,全方位把握“现实的个人”思想,不仅是在增强文本与现实对话的基础上理解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应有之义,也是指导我国在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
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原则。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多年来,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党的二十大也将“人民至上”作为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贯穿于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中。那么,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缘何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又缘何倡导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除了是对“民惟邦本”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价值观的一脉相承,还得益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的个人”思想的哲学启发。“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否认历史前提而沉浸于思辨世界这一做法进行拨乱反正的基点,也是推动唯物史观问世的出发点。由此,这一思想在开启人学研究的唯物史观视域的同时,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解放意蕴。因此,从《形态》这一文本出发来探赜“现实的个人”的基本原理,不仅是在增强文本与现实对话的基础上全方位理解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内在要求,也为当下在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指南。
一、反思与批判:“抽象的人”缘何为“现实的个人”提供了超越可能
探赜“现实的个人”思想的生成脉络,需要从《形态》所批判的特定思潮——青年黑格尔派的“抽象的人”出发。那么问题在于:青年黑格尔派缘何成为《形态》的批判对象?“抽象的人”又缘何为“现实的个人”提供了超越可能?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梳理清楚青年黑格尔派关于“抽象的人”的理论溯源与特征。在19 世纪的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因不满黑格尔过于强调客观实在性而忽视人的主体性,便无不例外地宣称自己的哲学已然打破了黑格尔哲学的抽象藩篱。其中,鲍威尔举起了“自由意识”这一思想武器。鲍威尔将“自我意识”奉为人类存在的绝对实体,指出只有具备“自我意识”的独特个体才是改造社会的主体力量,而那些缺乏“自我意识”的群众则被他视为导致历史走向衰亡的消极力量。于是,他在论及人的解放问题时指出,人们只要脱离了头脑中的宗教束缚而获得“自我意识”,就可以实现政治解放乃至人类解放。事实上,这种哲学在本质上是将人规定为“自我意识”的抽象外壳,而没有对人的本质给予任何现实规定性。因此,即使鲍威尔试图通过“自我意识”来克服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仍旧无法逃出黑格尔用“理性统治感性”所建造的哲学“囹圄”。于是,鲍威尔便展开了对“自我意识”的批判的反批判,并将这种批判的批判视为一种推动历史发展的超验存在。事实上,鲍威尔若没有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物质领域,那么这种批判怎么能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本质力量呢?正如诺曼·莱文的论断,即“如果仅仅局限于理论领域,批判将被终结;批判只有在实践领域才能实现”①[美]诺曼·莱文:《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周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272 页。。总的来说,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不过是黑格斯思辨哲学的“翻版”,因为这种哲学既没有深入德国现实社会中去,也没有将“自我意识”的思想维度上升到批判现实的实践维度,最终将被隐匿于用“关于现实问题的哲学词句”所堆砌的观念世界之中。不过,将批判与群众相对立的鲍威尔由于混淆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却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其“自我意识”哲学的破解,即“这种自我意识的本质不是人,而是观念,因为观念的现实存在就是自我意识”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340 页。。
“感性直观”原则是费尔巴哈用来跨越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重要基石,也是他用来认识周围世界的根本方法。费尔巴哈由于不满抽象思维便诉诸“感性直观”,并指出只有人才具有真正的“感性直观”,因此费尔巴哈哲学又被称为人本学唯物主义。不可否认的是,“感性的个人”为通往“现实的个人”搭建了理论桥梁。这是因为,正是由于费尔巴哈过于强调人的“感性直观”,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将“感性直观”原则改造为“感性活动”原则,由此阐发了“现实的个人”的存在方式。费尔巴哈之所以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而没有深入社会领域来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究其根本,是因为被荒芜的社会现象所蒙蔽而无法对社会本质进行透彻思考,仅能静止地、孤立地把握事物的直接存在,而无法动态地、历史地把握事物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与社会联系。这导致他仅能基于“我”与“你”的相互叠加、“男人”与“女人”的相互需要来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57、155 页。。此外,“感性直观”原则在克服抽象的思辨理性中也是不彻底的。这种不彻底性主要体现在:对现实社会的非批判性将无法解释“存在”与“本质”之间的非一致性。由此,费尔巴哈便不得不求助于二重性的直观,即“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57、155 页。。然而,戴上“哲学家眼镜”的费尔巴哈由于无法理解周围感性世界实际上是工业与社会历史的产物,从而导致人学研究再次陷入思辨哲学的沼泽之中。
“唯一者”哲学则生成于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破解过程中。在施蒂纳看来,费尔巴哈将最高本质由神推衍至人而生成了一种人学宗教,并指出这种宗教把对人的禁锢由彼岸世界拉回到了此岸世界,从而使人的本质再次被思辨迷雾所笼罩而无法完成对形而上学的最终批判。由此,施蒂纳便把剥离了一切形而上学的抽象规定的“唯一者”作为自己哲学的起点。施蒂纳从个体的主体性视角出发,强调“唯一者”首先是一个纯粹孤立的个体,且这一个体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事物和思想并将他的个人利益置于一切之上”③[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年版,第14 页。,这样个体的需要和行动便可以不受任何条件制约而成为唯一,由此也就可以完成自我价值的自我实现过程。“唯一者”哲学是施蒂纳旨在摆脱现实社会附加于个体之间的种种联系,并试图通过建构“唯一者”来使个体冲破一切异化统治而凌驾于众人之上,这彰显了施蒂纳对个体遭受异化统治所作出的哲学反击。然而,施蒂纳的“唯一者”是以利己主义原则为建构基点,并用个体的主观世界来定义客观世界,看似是将个体利益君临于一切事物来强调个体性,实际上却是浮于观念层面而脱离一切社会关系的孤立者。这是因为,“依靠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理论武器,是不能理解这些人的经验的物质的行为的”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261 页。。此外,施蒂纳主张通过建立利己主义者的联盟取代现存社会、国家等形式存在的共同体,指出联盟中的个人之间有且仅有一种“利用”关系,因此联盟的唯一目的是确保个体能够以自我为中心而生存发展。然而,这种联盟在其本质上不过是基于现代资产者相互竞争的异化环境中,对现代资本主义所张扬的个人至上主义的重复,这也体现了施蒂纳寄以跻身于资产者行列的愿望。应当承认的是,施蒂纳的“唯一者”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本思想。但是随着他们对这一思想的深入剖析,发现施蒂纳竟把历史基础从人的实践活动偷换为人的意识,由此揭示出施蒂纳最终无法在批判建构维度中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症结所在。因为只有揭示出费尔巴哈“类本质”哲学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才可以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这种哲学的社会土壤。
综上,踌躇于德国社会的“副本”而没有深入“原本”的德国青年黑格尔派认为,推翻不合理的德国现存社会仅仅通过头脑中的观念变革即可完成,体现了他们思想中具有一定的启蒙价值,这也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具有启示价值。然而,不论是“普遍意识”,还是“感性直观”,抑或“唯一者”,实际上始终是围绕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兜圈子,即仅仅抓住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单个范畴抑或是世俗化名称大做文章,这导致对人的回答不是泛化其本质就是窄化其能力,更毋庸提从尘世世界出发来理解人本身。究其根本,是因为传统人学基于本体论角度而混淆了“存在”与“存在者”,因而其实质是湮没人的本质的生成变化性的形而上学。①参见[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版,第63-68 页。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否定历史前提的做法进行了拨乱反正,并在同这一学派的思想剥离过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新世界观的现实出发点——“现实的个人”。
二、“现实的个人”:马克思第一个伟大发现的现实出发点
从古希腊人文主义精神的萌发到德国古典人学思想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哲学家们对人的认识皆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从总体上看,传统人学研究始终囿于历史唯心主义而将“现实的个人”置之度外。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用“现实的个人”替换《形态》底稿中的“现实的人”,除了受到青年黑格尔派极致强调个体性的影响外,还因为“个人”比“人”更加具体,因此从“个人”出发则成为理解社会历史的现实出发点。那么,何谓“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此作出了清晰界定。“现实的个人”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这是第一重规定。“现实的个人”不同于费尔巴哈戴上哲学家眼镜所观察到的“德国人”,亦不同于披上神秘外衣的施蒂纳的“唯一者”,而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那么“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46、161、520 页。,也就是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中把握人的生命实践的两大特征:能动性与受动性。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表征了人与自然是处于接连不断的交往状态中。于是,与宗教意义上的“神人”不同,“现实的个人”有着吃喝住穿等生存需要,而满足这些需要的感性对象则离不开自然界的馈赠。这是因为,“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46、161、520 页。,感性对象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由此“现实的个人”必须同其他自然物一样,首先与自然界建立联系并依靠自然界提供的感性对象来满足自身需要。
感性对象在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同时也使人从事感性活动成为可能,由此揭示出“现实的个人”的第二重规定。反观青年黑格尔派关于人的认识,始终停留于纯粹自然的感性直观,而没有深入物质实践层面理解人的感性活动,这就导致他们的人学研究必将带有神秘的思辨色彩。于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前提——物质活动的生产入手,从而规定了“现实的个人”是以感性活动为存在方式的人。虽然人们可以通过意识、语言等要素与动物划清界限,然而人真正区别于动物的关键在于人开始生产生活资料。诚然,动物也生产,但是它与它的生命活动是融为一体的,而只有人才能使生命活动成为自由的活动。这是因为,人从一开始就通过“物质生产物相化来塑形和构序新的社会历史负熵质”④张一兵:《一定社会性质的物质生产、现实的个人与社会观念——马克思中晚期经济学研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 年第2 期。。也就是说,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46、161、520 页。,感性活动是不断实现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的重要手段,人类历史也是人有意识地通过感性活动所创造的。正因为“现实的个人”可以通过感性活动改变自身存在的社会环境,这就决定了人可以不用和动物一样被动地听从于自然世界,而可以在合理运用自然规律的同时根据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将自然改造为属人的自然,由此人的实践活动也就实现了自然与社会的统一。因此,“现实的个人”就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感性直观的自然存在,也是以感性活动为存在方式的社会存在。
生产以交往为前提,因而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也会生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是“现实的个人”的第三重规定。青年黑格尔派试图用异化的空洞思想代替一切社会关系而固守人的自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则把人放在现实的历史环境与实践活动中来探究人的社会性。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为了生存而必须从事生产活动,然而,无论是人生产物质资料满足自身发展的过程,还是人通过生育、繁衍后代的过程,都是在社会交往中进行的,于是便会结成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在自然界中,人们不是被动地听任自然界的摆布,而是可以自主选择生存的地点、生产劳动的工具以及实践活动的方式。他们的活动方式规定了活动内容,也决定了人在社会中的表现,由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也就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另外,在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形式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有所不同,这表征为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契合性:①参见万光侠:《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唯物史观审思》,《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 年第1 期。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端落后,单个人无法实现独立生产而需要依赖他人来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此时社会关系呈现为人身依附关系;在“虚幻的共同体”中,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人虽然从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但为了生存又沦为物的附庸,此时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隐藏于“物与物”关系的背后;而在“真正的共同体”中,随着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从事生产活动,并可以自由发挥自身的才能与特长,此时的社会关系呈现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之所以人们在不同共同体中而缔结出不同的社会关系,究其根本,是源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原理,而生产关系作为最基础、最本质的社会关系,便影响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何种方式呈现。因此,只有把人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显现与确认人的本质。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知“现实的个人”思想包含“有生命的个人”“以感性活动为存在方式的个人”及“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三重规定。而把握“现实的个人”思想的内在规定性,不仅是科学回答人和人的本质问题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唯物史观得以问世所不可回避的必要环节。
三、推动“关于现实的人的科学”的真正出场:“现实的个人”思想的唯物史观意蕴
人是哲学的根本,哲学史上关于人的本质的探讨数不胜数。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体现了对人的关注的广度与深度。但是由于古希腊哲学家们将目光更多地投射在世界本源问题上,并且随着宗教的兴起,人便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沦为上帝的奴隶。到了近代哲学兴起时,批判神学并奠定人的地位成为新的理论方向。然而,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却将人置于绝对精神的笼罩下,这使人学研究又陷入抽象思辨窠臼中。费尔巴哈的进步性在于用“感性直观”原则恢复了人的地位,但他是以二重性的直观来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便为青年黑格尔派贩卖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留下了空间,即不论是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还是施蒂纳的“唯一者”哲学,其本质上都再现了黑格尔关于人的本质的思辨特征。总体来说,青年黑格尔派由于割裂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而陷入抽象人学的理论困境中。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则在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剥离过程中把人从抽象范畴中解放出来,并对人的理解还原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并进行感性活动的有生命的人。因此,重新回归《形态》这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诞生的重要著作,研究并把握其中蕴含的“现实的个人”思想,既是辩驳理论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人学空场”的有力反击,也是推动唯物史观真正出场所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
“现实的个人”在人学研究上开启了唯物史观视域,打破了传统人学研究的本体世界。传统人学往往借助构建一个超验于现实的本体世界,试图通过范畴叠加或观念变革来回答关于人的本质问题,这就使得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将会不自觉地忽视现实世界。这种传统人学的研究视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如:柏拉图将世界二分为“物质世界”与“理念世界”,并指出前者因由物质构成而处于流动变化状态中是有缺陷的,后者因由知识组成而处于恒定不变状态中是完美的,因而人们需要在高出现实生命之外的理念世界中找寻人的存在本质。到了德国古典哲学时期,黑格尔固守思辨哲学领域中而将人视为绝对精神的产物。费尔巴哈比以往哲学家们在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中前进了一步,他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但遗憾的是他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因此费尔巴哈的人学研究仍旧无法摆脱观念领域而践踏了人的现实生命。可见,传统人学研究由于忽视人所身处的现实世界而成为抽象的哲学体系,而这正是因为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①参见[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3 页。基于此,探索一条通往人所处的现实王国的存在论道路,则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所不能回避的现实课题。于是,他们在澄清历史前提中发现了从思辨王国通往现实王国的阶梯,这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由此将人学研究视域从精神世界拉回到了现实世界。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学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其不仅打破了沉浸于精神世界的哲学家们关于人的本质的无稽之谈,也在解答哲学上的“斯芬克斯之谜”中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现实的个人”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哲学前提。“现实的个人”由于有着维持自身肉体生存的现实需要,因此需要从自然界中找寻满足这些需要的生活资料,而在这一过程中与自然界所结成的关系就被称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则为“现实的个人”在感性活动中与他人缔结的社会关系。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生产力——无疑是第一性的,这是因为人们只有从自然界中寻找生活资料才能维系自身的肉体生存;也是人们得以创造历史的首要规定,由此便揭示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这一基本规律。那么,如何评判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这就需要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即每个人能否自由全面发展是评判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重要尺度。原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从根本上呈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与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的矛盾。而“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61、163 页。。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只有在一方没有体现“为我”才会出现。③参见汪信砚、李志:《“现实的个人”:唯物史观的入口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个人概念及其意义》,《哲学动态》,2007 年第9 期。然而,随着分工的出现与发展,“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61、163 页。。正是源于这一矛盾,共同利益逐渐排斥个人利益而虚幻为一种抽象利益,而为了掩盖其脱离个人利益的事实,便诉求披上“共同体”的法衣,于是便形成了“虚幻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的生产方式下,人不论是与自然还是他人所结成的关系,皆呈现出一种异化关系而不是“为我”的关系。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可以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根本矛盾。因为“真正的共同体”是建立在拥有发达生产力的共产主义自由王国中,人们便可以打破旧式分工藩篱而自由劳动,由此结成的关系必然体现为“为我”的关系。以上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质上是“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也表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是迈向“真正的共同体”,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追求。
四、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追求——“现实的个人”的人类解放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①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8 页。可以说,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追求,也是区别以往哲学的最大异质性。而人类解放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与目标的统一,因此,“人类对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②张骥、耿直:《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理论导刊》,2021 年第11 期。。在《形态》语境中,青年黑格尔派将“现实的个人”置之度外而没有找到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而缘由恰恰符合日本学者平子友长的论断,即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没有将个体的人理解为客观世界的能动主体。③参见Tomonaga Tairako,“Philosophy and Practice in Marx,”Hitotsubashi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Vol.34,No.2,2002,pp.47-57.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立足“现实的个人”,阐明了真正解放的两大要素,由此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追求。得益于此,我国也在坚持“人民至上”中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期为探寻人类解放提供可行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价值关怀和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彰显了对“现实的个人”思想的一脉相承,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在21 世纪的现实阐发。
“解放”一词通常被定义为消极和被动的术语,是指从他人的控制或法律、社会或政治限制中解放出来的过程。④参见Michiel Meijer,“Articulating Better,Being Better:Ethical Emancip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Motivation,”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Vol.25,No.1,2022,pp.107-122.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生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性弊端的反思过程,是探讨如何将人从异化统治解放出来的学说。然而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人的本质被分解为一个个的抽象范畴,如:鲍威尔抽象地将人视为“自我意识”的人、费尔巴哈将人狭隘地定义为“感性直观”的人、施蒂纳将人曲解为“唯一者”。基于这种人学认识中的人类解放也只能是观念中的解放,因为这种做法不过是将人从词句的镣铐中解放出来,可是人却一刻也没有受过词句的镣铐,其实质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提供了有力证词。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现实的个人”为了生存发展而不得不从事生产活动,这种活动实际上是一种被奴役化的生产劳动,自由的是资本而不是人。也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65 页。,这种驾驭并摧毁人的异化力量就不会消失。而这种异化力量,究其根本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所造成的。因此,“现实的个人”的解放,必须要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这种生产方式背后的私有制。那么,消灭私有制何以可能?这就需要将“人”从天国拉回人间,使这种“现实的个人”意识到自身的真正需要并肯定自身的本质力量。《形态》指出了真正解放的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即“个人在自己的自我解放中要满足一定的、自己真正体验到的需要”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347、347 页。。也就是说这种需要是个人在实践活动中真正体验到并迫切渴望的,而不是在被资本逻辑主导下所塑造的虚假需要,即阿多诺所言:“伪个性”在消费者的选择中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错误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文化产品日益标准化的差异化基础上选择了真正为自己选择的东西。②Fabian Arzuaga,“Socially Necessary Superfluity: Adorno and Marx on the Crises of Labor and the Individual,”Philosophy &Social Criticism,Vol.45,No.7,2018,pp.819-843.第二个要素是“在谋求自身解放的个人身上至今只作为天资而存在的那种能力,现在被肯定为真正的力量”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347、347 页。。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个人被迫从事机械式的生产劳动,其生存发展的需要皆被忽视,且谋求解放的个人才能也被严重遮蔽,由此,“现实的个人”的解放则需要将这种个人才能恢复为主要力量。总而言之,解放是对异己力量的排除与抵抗,这要求“现实的个人”首先要感觉到自己的真正需要并肯定自身力量,才可以实现彻底的解放。
沿着《形态》语境中“现实的个人”解放的逻辑理路,可以得知:人类解放依赖于“真正的共同体”的形成。这是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99 页。。然而,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还是当前我们所处的环境,都没有达到“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条件。因此,我国需要在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中探寻出一条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这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正以一种关注全人类前途命运的世界视野和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关怀,成为当今通往“真正的共同体”的实践必然,从而为实现人类解放指明了现实方向。而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一,从哲学维度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人类”彰显了主体的世界范围,“命运”彰显了对主体生存状态的现实关怀,“共同体”彰显了实现主体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归根到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围绕社会主体即“现实的个人”,揭示出了人类解放之路的主体力量。其二,从现实维度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然成为当今各国交往模式的现实写照。接踵而至的全球性挑战与发展性难题,唯有各国共同应对才能予以解决,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这表明各个国家犹如一个个器官内融于一个生命有机体中,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当下理想状态中的有机体,各个国家应自觉坚持“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540 页。的发展机制。当前,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各国发出了合作共赢的最强音,秉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价值理念,不断探索国家之间的利益契合点,为实现繁荣昌盛的美好世界提供了现实出发点。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现实的个人”思想的时代阐发,将蕴含其中的价值关怀落实到当今世界的实践行动中,探索出一种应对全球危机并建设美好世界的新交往模式,由此书写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新篇章,并为实现人类解放探索出一条现实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