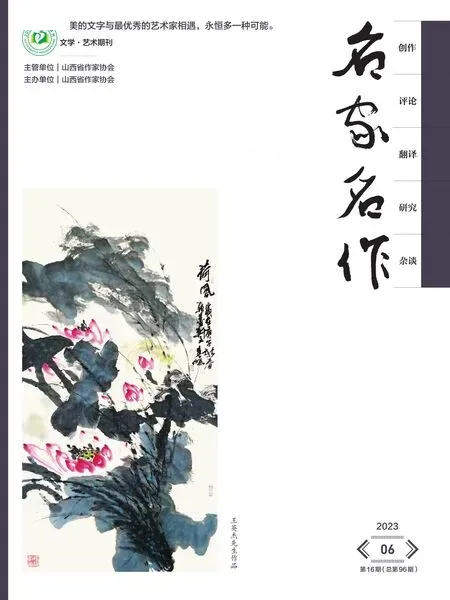《安提戈涅》中的女性与权力
熊桑煜
《安提戈涅》作为索福克勒斯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剧作主要讲述了安提戈涅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坚持将哥哥波吕涅科斯埋葬的故事。其核心冲突通常会被看作伦理习俗与城邦法律的对抗,但克瑞翁的独断令他不能作为城邦正义的代表。权力的争斗被隐藏在社会与神的表面之下,克瑞翁使用权力令波吕涅科斯曝尸荒野,以暴力威胁人民不敢违反,安提戈涅的无权令她只能孤身埋葬。安提戈涅被看作是家庭伦理的代表不是因为她为了埋葬哥哥宁愿付出生命,而是因为她作为女性被禁止踏入政治领域,她除了求助于神别无选择。
一、克瑞翁与权力
克瑞翁在拒绝埋葬波吕涅科斯时不止一次提到城邦的整体利益,认为不应该埋葬攻打城邦的敌人,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真的像自己说的那样,是为了维护城邦的利益吗?还是他为了掩盖仇恨而找的借口?
克瑞翁的语言是矛盾的,他曾以宙斯起誓,“至于我自己,请无所不在的宙斯见证,要是我看见任何祸害——不是安乐——逼近了人民,我一定发出警告”。[1]克瑞翁以宙斯的名义强调了自己地位上和行为上的双重合理性。如果说克瑞翁是真正出于对城邦的爱,坚持宙斯的正义,但当等到先知忒瑞西阿斯出场,以失败的占卜劝说克瑞翁时,克瑞翁却一反常态,不仅痛斥先知忒瑞西阿斯卑鄙无耻,还将“宙斯”这个借口彻底抛开,“但是你们不能把那人埋进坟墓;即使宙斯的鹰把那人的肉抓着带到他的宝座上……我也绝不因为害怕污染,就允许你们埋葬。”[1]克瑞翁真正想做的是“禁止埋葬波吕涅科斯”这件事,他不在乎自己曾经说过什么,用了什么借口,如果这个借口被强有力的事实反驳,他可以立刻违背自己的誓言。
而面对先知的警告,克瑞翁不屑一顾,他将对众神的敬仰赶出政治生活,认为众神没有权利插手他的决定。为此克瑞翁甚至攻击了先知整个群体,“你们那一族预言者都爱钱财……你知不知道你是在对国王说话?”[1]克瑞翁的傲慢令忒瑞西阿斯大怒,他揭示了克瑞翁的未来,克瑞翁将拿自己的亲生儿子作为赔偿,“拿尸首赔偿尸首”[1]。
克瑞翁对权力的迷恋从未改变。在《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曾怀疑克瑞翁买通先知,诬陷自己是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克瑞翁为此向俄狄浦斯澄清,自己从来不想夺取他的王位,因为自己想要的是“无忧无虑”,而不是权力的副产品,责任和那最高位置上令人生畏的“担惊受怕”。[2]
正如歌德所说:“克瑞翁的行为并不是从政治道德出发,而是从对死者的仇恨出发。波吕涅刻斯在他的家族继承权被人用暴力剥夺去之后,设法把它夺回来,这不是什么反对国家的滔天罪行,以致死还不足赎罪,还要惩罚无彰的死尸。”[3]剧作中的每个人都在反对克瑞翁,从守兵到他的儿子,城邦的人民也不支持他的行为,但克瑞翁还是坚持如此。可见克瑞翁的禁葬令不是为了城邦整体,而是出于对波吕涅科斯的仇恨,他憎恶他人挑战他的地位,要将权力牢牢把控在自己手中。因此波吕涅科斯试图争夺权力的行为,即使失败了,在克瑞翁眼中也不可饶恕。他将波吕涅科斯曝尸荒野,让城邦的居民看到争夺王位的下场是什么。同时,羞辱波吕涅科斯的尸体也是克瑞翁权力的体现,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处理上一任国王的血亲,民众的意见在克瑞翁眼里不值一提,没人有能力可以推翻他的决定,因为没人的位置比他更加高贵。
虽然有人认为安提戈涅从伦理的角度埋葬她哥哥是正确的,但却未曾表达过她反抗国家是正确的。“合唱队崇尚她的行为,但同时他们也不赞成她违抗克瑞翁的法令。先知忒瑞西阿斯也是如此。”[4]
但值得注意的是,歌队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一开始他确实表现出了对违反禁葬令的人的厌弃,“我不愿这个为非作歹的人在我家做客,不愿我的思想同他的相同。”[1]在安提戈涅说出“凡人的命令不可废除天神的律条”之后,歌队也表示,她的行为不可理喻,可能是发了疯了。[1]但直到结尾,安提戈涅在墓中自尽,海蒙自杀,忒瑞西阿斯的预言成真,歌队在结尾终于说出了剧作的主要思想:“千万不要犯不敬神的罪;傲慢的人的狂言妄语会招惹严重惩罚。”[1]将歌队看作僵化的思考者,实则是对索福克勒斯作为一名优秀剧作家的实力的轻视,一开始反对越强烈,后期情绪的转变便越令人敬畏。因此,总的来说,克瑞翁的禁葬令是不公正的,他的行为违反了当时希腊的礼法,他的傲慢也让他遭受了厄运。
二、安提戈涅在政治领域的死亡
剧作中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为什么安提戈涅要以死抗争?她身为克瑞翁儿子的未婚妻,前任国王俄狄浦斯的长女,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于安提戈涅极端的行为,可用另一部同样以禁葬为主题的作品——欧里庇得斯的《请愿的妇女》作为对比,理解安提戈涅是否还有别的选择。《请愿的妇女》同样以七将攻忒拜不幸战死为背景,讲述了得胜的忒拜王不允许埋葬尸体,将领们的母亲便前去祈求雅典国王忒修斯,求他从忒拜王手中夺回儿子们的尸体,以进行葬礼,使灵魂得以安息的故事。[5]
在剧作中,将领们的母亲和阿尔戈斯的国王阿德剌斯托斯,共同来到雅典国王忒修斯面前,恳求他“让死人得到应有的坟墓和葬礼”[5]。在当时的希腊,丧葬意义重大,不仅是阿德剌斯托斯屈从的态度,从忒修斯的母亲埃特拉的语言中也可以看出,埋葬尸体既是对神的敬重,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必要准则。“现在你要知道这将使你得到多大的名誉……因为那联系人们的城邦的就只是这个,便是在于大家尊重那些礼法。”[5]埃特拉将葬礼看作是“联系城邦”的基准,其原因首先在于,古希腊人笃信灵魂不死,认为如果没有妥善地安葬死者,死者的灵魂便不被冥王接受,因此成为孤魂野鬼,乃至给生者招致不洁和灾祸,从而殃及整个城邦。
其次在于,葬礼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俗,不仅使死者的亡魂得到安息,个人情感得到宣泄,更使生者之间的纽带更加紧密,家族集体之间的传承不至于断绝。克瑞翁的行为伤害了母亲们的个人情感,也毁坏了长期以来的习俗和伦理标准。
葬礼的重要性在其他作品中也可见一斑。如在《伊利亚特》中,帕特罗克洛斯死后出现在阿基琉斯的梦里,责备他没有及时将自己安葬:“埋葬我,越快越好;让我通过哈得斯的门槛!那里的亡魂、幽灵把我远远地推开,怎么也不让我过河加入他们的行列。”[6]
安提戈涅可以效仿这种行为吗?显然不能。一方面,她无法效仿将领们的母亲,她没有恳求的对象,因为下禁葬令的不是别人,而是安提戈涅的舅父,如果恳求舅父,最坏不过是遭到拒绝,但恳求外邦人,则是叛国。没有人愿意帮助她,人民因为恐惧而噤声,即使是她的亲妹妹,也畏惧克瑞翁不敢反抗,安提戈涅没有同盟,只有自己。另一方面,她无法效仿忒修斯,后者不是同忒拜城讲和,而是率兵以武力夺回。
安提戈涅作为未婚的公主,没有可以和克瑞翁宣战的兵力。实际上,她甚至没有继承王位的政治地位。古希腊民主政治时期妇女地位低下,从出生开始就受到男性监护人的掌控,活动空间被限制在家庭,极少有外出的机会,就算可以出门活动,也需要戴上面纱,有他人陪同。妇女在雅典的理想状态是隐身,除了生育与纺织等之外,在公共领域中完全“不存在”,对此伯利克里公开声称,无论好坏,不被男人提起的女人才是最好的女人。[7]同时,雅典法律规定,女性没有继承权,她不能同他人签订契约,不能上法庭作证,亦无权立遗嘱,决定自己的财产赠予谁。[8]雅典妇女在法律上同毫无自主权的儿童一样,她们没有对经济的掌控权,一切经济事务将全部由男性监护人负责,除了自己的衣物与装饰品之外,雅典女性没有任何形式的可支配财产。
虽然古希腊女性除了家庭还可以参与宗教,并在其中通常担任较为重要的职位,比如传达神谕或主持祭祀,但就算在宗教活动中,女性也受到诸多限制。女性经期和怀孕都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因此在经期的妇女或者接触过产妇的人均不能接近祭坛,以防造成污染。[9]
安提戈涅虽然贵为公主,但她实际上并没有政治身份,她没有继承权与财产权,实际拥有的只是自己的生命。没有强劲的政治力量,使安提戈涅的语言终究只是语言,但当克瑞翁命令士兵将她关进墓室时,她依然无法反抗。
索福克勒斯显然也没有考虑过让安提戈涅同克瑞翁争辩应该由谁来继承王位的问题,在他以及当时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都认为女性本身就不可能掌权,或者说不应该掌权。因此尽管古希腊神话中有很多强力的女神,但这些女神都不可能使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分走男性权力,神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更多的是警示,而随着古希腊人理性意识的觉醒,哲学家和科学家对自然的了解逐渐加深,神的作用也在城邦中渐渐消退。没有实际权力的女性,如果想要维护自己的权益,除了依靠男人,或者诉诸神,没有别的方式。就像在《请愿的妇女》中忒修斯所说:“因为凡是谨慎的女人,一切事由男人去做,那是顶合宜的。”[5]
那么安提戈涅可以通过婚姻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果非要依附于男人才可以解决,安提戈涅是否能为自己挑选另一个丈夫。可惜不能,古希腊女性的婚姻没有自主权,她们的婚姻通常由父亲决定,如果父亲在婚前去世,为她们选择配偶的人则变成兄长。也就是说,失去父母兄弟的安提戈涅,其婚姻的支配权已经转移到了克瑞翁手上。如果安提戈涅想试图通过自己找一个好丈夫,那么她要面对另一个难题,即没有人可以支付她的嫁妆。古希腊女性结婚时父母须为女儿准备丰厚的嫁妆,金钱财物会为女儿带来声誉,也会让她得到丈夫的尊重。[9]比如《伊利亚特》中赫克托尔的妻子就被形容为“嫁资丰足”。[10]很显然,支付不了嫁妆的女性很难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好丈夫。而且,虽然雅典妇女在出嫁时会得到家里给予的一大笔财物,但这笔财物婚后不由女性支配,她的金钱会完全归属于丈夫,并且在丈夫去世之后,由于雅典妇女没有继承权,这些财产只能由其男性子嗣,或者她改嫁的新丈夫继承。
除了依附男人与神之外,是否还可以依靠阴险的诡计?比如杀子的美狄亚。美狄亚遭受了丈夫伊阿宋的背叛,后者想要抛弃她和两个孩子,同科任托斯国王的女儿格劳刻结婚。美狄亚为了报复伊阿宋,不仅设计杀死了公主,还杀了自己和伊阿宋的两个孩子。
但美狄亚是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孙女,她可以向公主献上淬了毒药的袍子,“我也帮助你做这件困难的事:我要给她送点礼物去,一件精致的袍子、一顶金冠,叫孩子们带去。”[5]且不会因此受到惩罚,结尾美狄亚乘坐龙车离开了科任托斯,没有任何报复在她身上显现。
但是安提戈涅可以吗?她没有巫术,没有高贵的亲戚,只是一个普通人类。而且美狄亚的弑亲行为没有动摇男性统治的根本,她不渴望取代丈夫的位置,其行为只是出于对丈夫变心的怨恨。安提戈涅作为一个没有政治身份的女性,她既无法去冒险,赢得自己的荣耀,也无法通过治理国家来赢得称赞。世俗已经无法给她解决办法,她寻求帮助的对象便只剩下神。
安提戈涅作为一个没有政治身份的女性,世俗已经无法给她解决办法,她寻求帮助的对象只剩下神。不管后世为安提戈涅赋予了何种身份和哲思,比如正义对暴政的反抗;[11]或者在历史逻辑中遵守习俗者与城邦法律的颁布者之间正义原则的冲突,双方之伦理诉求都有其充分的辩护理由。[12]又或者是安提戈涅对正义、永福问题的质疑。[13]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安提戈涅没有权力。无权导致了她的脆弱,同时也导致了她的局限性。她之所以被当作是家庭伦理的代表,不仅在于她为了埋葬哥哥而同君主抗争,更在于她被隔绝在政治活动之外,不是主动而是被动地进入家庭领域。安提戈涅在政治意义上是绝对的孤立无援者,她的父母兄弟接连死去,唯一的直系亲属只剩下一个妹妹。安提戈涅无权继承王位,作为女性她只能依附另一位男性。男性可以同时存在于城邦政治和家庭伦理两个世界,她的父亲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成为忒拜的国王,同时又在家庭内部的伦理意义上受到诅咒,使他弑父娶母,陷于流亡;她哥哥们的争斗是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同时也在亲缘关系上被俄狄浦斯诅咒,两个人必将杀死对方,权力的斗争引发了家庭内部的震荡,但安提戈涅却被局限在家庭,她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对政治领域产生任何一点影响。
克瑞翁的悲剧是个人的,他的政权不会因为安提戈涅的死亡而被人民推翻,如果不是因为海蒙深爱安提戈涅,愿意与她一同死去,安提戈涅也无法对克瑞翁造成任何伤害。与其说是正义,或者先知说的阿波罗,或者安提戈涅自己说的“宙斯的法律”,报复了不敬神的人,倒不如说是爱神阿芙洛狄忒报复了克瑞翁。“爱情啊,连那些伟大的神律都被你压倒了,那不可抵抗的女神阿佛洛狄忒也在嘲笑它们。”[1]
三、被禁声与被剥夺权力的女性
虽然安提戈涅没有政治身份,无法同克瑞翁站在平等的位置上,但她依然选择站起来反抗。索福克勒斯最初或许只是想表达习俗守卫者对强权的反抗,他没有料到,当安提戈涅试图踏入政治领域时,她的身份变动会引起那么大的震荡。一旦她行动起来,大声呼号,同克瑞翁争辩。在发现细沙被守兵拂去后,波吕涅科斯的尸体再次暴露在旷野之中,她发出了“尖锐的声音”并“做出诅咒”[1]。安提戈涅不再沉默,也没有隐蔽在黑夜和黄沙背后,而是出现在众人面前,她必须要让众人看见她的面孔,听见她的声音。
而克瑞翁对安提戈涅的惩罚体现在对其表达权力的剥夺。克瑞翁在反驳不了安提戈涅所说的正义之后选择隔绝她的声音,将她投入墓室,让其在暗无天日的洞穴里丧失任何抗争的力量。克瑞翁的决定不仅是他作为独裁者的残暴,更是他意识到了,安提戈涅之所以诉诸神的正义,只用语言同他抗争,是因为她无路可走,她无法用更强大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安提戈涅向克瑞翁暴露了她的脆弱,克瑞翁也准确地发现了这一点,他何必反驳安提戈涅的语言呢,杀死她就够了。
克瑞翁不愿意听到安提戈涅反抗他的话语,也不愿意让她继续出现在众人面前,他将安提戈涅投入墓室的行为是他希望安提戈涅闭嘴,他法令的权威性在安提戈涅对正义的叙述之下遭受了重大的挑战,必须要尽快让她闭嘴,最好是让她消失。
掌权者为了防止不利于自己的声音出现,会以各种方式对话语主体进行禁闭。克瑞翁不仅作为掌权者对安提戈涅进行囚禁,同时也作为男性对试图反抗自己的女性进行囚禁。他并不从法律上否定安提戈涅,而是针对她的性别,坚信女人绝不可胜过男人。“所以我们必须维持秩序,绝不可对一个女人让步。如果我们一定会被人赶走,最好是被男人赶走,免得别人说我们连女人都不如。”[1]克瑞翁这样说的前提是他认为男性与女性两种性别有完全不同的含义,男性应该执掌权力而女性不行,他曾坦言“没有一个女人能管我”[1],因为自己是男人,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女人制衡。这种地位的高低不在乎财富或出生,仅仅只是因为性别。克瑞翁将安提戈涅挑战权力的行为赋予了男性色彩,认为权力这种独属于男性的东西绝不可以由女性获得,要是她的挑战行径获得成功,那么必然是因为她获得了男性气质。“要是她获得了胜利,不受惩罚,那么我成了女人,她反而是男子汉了。”[1]
男性对女性的厌恶,以及防止女性得到权力的可能,使他们对女性在各方面进行禁闭。在生活中是将女性囚禁在家中,剥夺女性的继承权和经济权,同时否定她们的声音和观点;在作品中,是以各种方式对女性进行教导,比如埃斯库罗斯在《七将攻忒拜》中,借厄忒俄克勒斯之口,重复说了许多次 “城外的事情由男人管,女人不得参与。你待在家里,不要惹出祸害!”[15]剧作家潜移默化地将男性眼中的理想形象灌输给阅读和去剧场看戏的女性,并赞美抬高这种理想形象,令女性不去思考不平等的根源究竟为何,自己没有参与政治的可能,只希望乖乖待在家中织布,获得男性的称赞。
而在神话故事里,亦有许多男性作为掌权者对女性话语进行禁闭的例子。宙斯看上了一个名叫伊娥的人间女子,为了不让赫拉发现,将伊娥变作母牛。伊娥无法说话,很难将自己的遭遇表达,即使来到自己的故乡,见到自己的亲人,也没有办法同父母姐妹说话。[16]
人作为可以言说的主体,通常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想法,但当伊娥被变成母牛后,她便从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变成被动接受他人意志的物,她的一切行为都不再带有自我意愿,他人的语言和辩解代替了她主动的言说。男性为了逃避合法妻子的指责,将自己强行占有的女性禁闭。阻绝她的声音,不仅是掌权者对无势者的掌控,更是一种对女性想要表达自身不公正待遇欲求的否定。神话故事禁止女性使用强大的语言力量,只展示沉默的理想形象,即使她们想要说话,也用尽办法隔绝她的声音。
但就算男性对女性的隔绝如此残暴,也不可能完全磨灭女性的声音。忒柔斯因为对自己妻子的妹妹菲洛墨拉见色起意,便将她骗走,囚禁在密林之中。菲洛墨拉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她的意志也被囚禁在与人隔绝的禁闭空间之中。菲洛墨拉曾同忒柔斯争斗:“我要亲口把你的所作所为说出去!如果你不让我走出森林,我就让森林响彻我的怨诉,让众神听见我的怨诉!”[17]忒柔斯害怕自己的行为被发现,便割掉了菲洛墨拉的舌头。这是对隔绝女性声音最血腥和直观的表现,如果无法通过潜移默化或囚禁使女性闭嘴,那么便割掉她的舌头。话语是构建权力的最好方式,不仅可以强化权力,也可以削弱权力。忒柔斯深知如果菲洛墨拉成功地将自己的遭遇告诉她的家人,他的权力一定会受到威胁。但即使忒柔斯已割去菲洛墨拉的舌头,让她无法通过语言表达,也无法阻止她将自己的遭遇织在一件长袍上,偷偷寄给在外的姐姐。就算她的声音被隔绝了,她也还是要说。
正如忒柔斯一样,安提戈涅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她疾呼、奔号、争吵、和克瑞翁对着干,她没有屈服于家中的男人,即使她的生命消失在昏暗的墓室之中,但正如伊利格瑞所说,安提戈涅的反抗使她的这种行为成为一种声音,“那种与人民,与奴隶,与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反抗主人的人们团结起来的声音”[17]。
伊利格瑞明显看到了安提戈涅被隔绝在政治生活之外的境况,她将安提戈涅的抗争看作是对男性掌控的政治生活的超越,她的行为动摇了家庭与国家之间的稳定关系,突破了原本应该互不干扰的两种生活之间的边界。她尖锐的声音也向女性展示了另一种可能,尽管她的行动为她招来了死亡,女性在父权制中做出的反抗会付出巨大且惨痛的代价,但依然无法影响她行动的主动性。
四、结语
古希腊时期女性的地位低下,被隔绝在政治生活之外,在古希腊作品中试图向权力发起挑战的女性,比如安提戈涅与克吕泰涅斯特拉,无论成功与否,她们的故事都有着不可动摇的内在逻辑:这样的女人必须被剥夺权力,赶回到她们应在的地方去。不管是杀死她们,还是贬低她们,绝不可让她们长久地行使权力,即使是她们发出疑问的声音都要被剥夺。女性哪怕在传说或者神话中正当合理地运用权力,都会令现实生活中的男性统治遭到质疑,因此男性即使是无意识的,也要将女性赶出权力领域之外,维护以男性为主导的统治的合理性。
同时,比起“女性”,她们更倾向于被男性作家描绘为“有男子气概的”,她们的行为不是女人可以做出,而是在精神上同男人相似,才使她们如此坚韧,不仅在权力上和男人画上等号,所有正面品质也只有在女性失去女性气质时才能获得,男人可以驾驭权力,而女性的跨越不仅会给生活带来混乱,也会使她们自己遭受毁灭。
但正是男性这种日复一日的规训,在剧作和神话中不厌其烦地一次次杀死挑战权力的女性,反而使她们反复出现在观众眼前,她们的声音和语言哪怕被染上了男性幻想的色彩,她们的行动也不会被磨灭。无论如何阻止女性说话,否定女性的声音,她们也绝不会听从,她们会反抗、疾呼,“发出尖锐的声音”。女性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寻找自我,挑战男性的话语权,坚持扭转自己被凝视和被规定的他者地位,构建自己的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