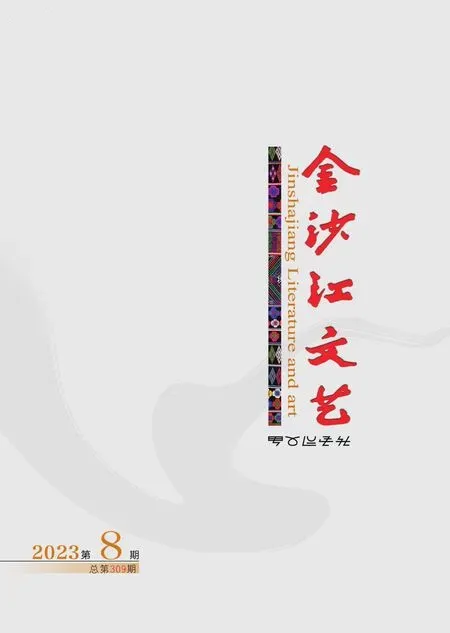画
◎木非可
这一刻,我忘了我是谁。打破脑袋也想不起来。
湖水湛蓝,天空湛蓝,永安湖包裹在一片蓝色中。一只鱼鸟飞来,停在芦苇上,它喜欢这蓝色,更喜欢湖里的鱼。鱼还在自由地游着,并未感到眼前的危险。湖面掀起一丝涟漪,我没有看清鱼鸟何时出手。它已飞入天空,口里叼着和它一般大小的鱼。
我向湖边靠去。湖水是一面镜子,照出我。长发,双眼皮,厚唇,还有强壮的胳膊……看上去那么陌生,不像我。我盯着她看了好久,还是觉得不是我。但我应该长什么样子,我又想不起来。恍惚中,水里的影子向我招手。像被赋予某种魔力,她开始变换姿势,吸引我,勾引我。我闭上眼走了过去,想与她融为一体。只一瞬,湖水便灌进了我的耳朵、口鼻。
脑海里出现一些奇怪的画面。一间破旧的画室挂了一张破旧的画。画上是一间破旧的画室。画室里有一张破旧的桌子,沙发上坐了三个看不清五官的人。我回头,想要看更清楚些。脑中所有的画面却转瞬即逝,消失在一片虚无里。
我失去了意识,身体迅速往下坠落。
我又醒了过来,睁开眼便又看到那片湛蓝的天空。我缓慢地抬起身子,眼前冒出一个男人,戴一顶草帽,皮肤黝黑,犀利的双眼像两把锋利的匕首,好像随时都能从我身上割下两片肉。但是,他没有看我,而是看着天空。我也不害怕。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哪里会怕一个眼神。我这才注意到男人的手,手掌宽大,手指又粗又长,手臂在阳光的照耀下显现出古铜色。
我说,是你把我救上来的。男人把视线从天空移过来,说,凡事想开点,何必一心求死,死又能解决哪样问题。我无感激之意,挣扎着站了起来,说,我寻死跟你有哪样关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说完,又踉踉跄跄地往湖边走去。身上的水,就窸窸窣窣地掉了下来,把身后的影子打湿。
很快,我又走到湖边。男人扯着嗓子喊,像你这样的人我救得多了,你若真一心寻死,我不会再打扰你。但你在跳之前,再好好想想,你死了没关系。但你的家人呢,他们怎么办?
男人话没说完,我便又一头扎进湖里。男人也顾不了那么多,几个箭步冲了过来。
我再次醒来。这时,我不想再跳湖了。甚至,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跳湖。打破脑袋我也想不出来。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又出现画室的画面,但关于画室更多的信息却又想不起来。我像一条鱼,只有七秒的记忆。跳湖前的事,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睁开眼,将目光停留在男人身上。男人不知什么时候点起了一根烟。一个烟圈吐了出来,正好挡住他犀利的眼睛。我说,谢谢你救了我两次,我现在不会跳了。男人说,你能想开就好,啥也别说,快回家吧。全身都湿透了,换身衣服,别着凉了。
家,我的家在哪里?我开始头痛,陷入漫长的沉思。我使劲拍打自己的脑袋,还是想不起来,我为何来这湖边。想不起自己的家。我有家吗?
怎么还不走,起风了。男人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已经收拾好了钓具,今天只钓了三条,两条草鱼和一条鲤鱼。见我迟迟没有动静,男人接着问,你家在哪里?远不远?要不要送你?男人边说边走了过来。
我回过神,说,你可能不信,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想不起来我家在哪里了。男人说,你再好好想想,怎么会想不起来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不可能忘的。你想想你是咋个来的。丈夫在哪工作。孩子叫什么名字……男人不断地帮我回忆。
我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男人不忍心把我单独留在这,更担心我还会再次跳湖。只好把我带回他家。又找了妻子的衣服给我换上。他的衣服也湿了,在他换衣服的时候,妻子回来了。妻子一进门,便看到沙发上的我。她径直走向卧室。男人还在穿衣服。紧接着,一记响亮的耳光从卧室传了出来。随后便是无休止地争吵。男人说,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这样。妻子说,都已经这样了,还怎么解释……
我在慌乱中离开。
再次见到男人已是第二天。男人穿着睡衣,看着窗外,不知道在看什么。我在他楼下的一棵大树下,向他招手,不知道他能不能看见。很快,他就离开了窗户。我坐在树下,风一遍遍袭来,不停地有几片叶子往下掉落。掉落的叶子正值青绿。我觉得它们不应该早早离开树的束缚,它们应该茁壮成长。我把这一切怪罪于风。是风,不停地侵袭它们,甚至,勾引它们。男人这时候出现在我眼前。他把衣服递给我,说,你那天留下的衣服,干了。我接过衣服,说,那我身上的怎么办。男人摆摆手,说,你穿着得了。反正,她也不会再要了。我说,你妻子是不是误会了。他点点头没说话。我当时被吓到了,就跑了。需不需要我去解释一下。男人又摆摆手,说,都过去了。
在男人的叙述中,我得知了那天发生的事。我走后。男人的妻子更加怒了,直呼其名,李政,现在你怎么解释,她要是问心无愧,咋个会畏罪潜逃。男人也怒了,抱起一个花瓶狠狠地往地上摔,马晓梅,你不要无理取闹。马晓梅是他妻子的名字,结婚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这样撕心裂肺地喊出来。多少有些无奈。他本来只是好心,哪里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误会。他清楚,这事啊,难于解释。他看向妻子。妻子坐在沙发上,嘴里喘着粗气,两只手按在茶几上,还在气头上。这时候,他就想,我刚走,肯定没走远。只要找到我,就能证明他的清白。他把手上的烟头熄灭,就向门口走去。
站住。妻子站了起来,你要去哪,是不是要去找那贱人?男人说,她现在还没走远,我这就把她找回来对质。妻子说,你到现在还想着她,这日子没法过了。男人停住脚步,这时他想起我换下的衣服还在阳台,便拉着妻子到了阳台,你看,衣服还是湿的。这足于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妻子说,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你怎么证明你们到家没有发生点什么。毕竟你救了她,她要是想报答你呢?再说就算被水淹了,怎么就想不起自己的家呢。这不明摆着想要报答你嘛。男人急了,说,我对天发誓,我和她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妻子说,就算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她换衣服的时候,你难道就没有想法。要不是我及时回来,你敢保证你们之间,什么都不会发生?
最后,妻子还是原谅了男人。但是,妻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自由。比如不让他再去钓鱼,甚至不让他出门,给他买了一大摞书让他在家里看。而且还说,准备给男人找点事做,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在家里闲着。这令男人感到压迫,就像是被软禁了。这时候,他就觉得,妻子并没有真的相信他。
男人看了一眼天空,又朝远处望了望,退后了两步,才又看着我,说,你找到你的家了吗?我摇摇头,然后说,但我好像又想起一些事,在我跳湖的头一天晚上,我好像被人打了。那人有可能是我的丈夫,可是,我想不起来他为什么打我,也想不起他长什么样子,还有他叫什么名字我也想不起来。我边说边撩起后背上的衣服,你看,是不是还有几条深深浅浅的伤痕。男人点点头,说,赶忙把衣服放下来。我接着说,我还想起来,我有个女儿,叫小雪。只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上学。
男人问我接下来怎么办。我说,你能不能借我点钱,我现在只能想起你了。男人从兜里掏出一些钱,递给我,说,你先找个地方安顿一下,希望你尽快找到你的家人。
我离开村庄,走着走着就到了城里。我的女儿好像是在城里上学,我隐约觉得。但是,我在街上走了几天,也没有找着学校。眼前的街道、人群都显得陌生。有时路人一个怪异的眼神都会令我害怕,有时我会突然听到有人在喊我,但周围却一个人都没有。这天,我坐在一棵树下,盯着一群觅食的蚂蚁。忽然听到蚂蚁在开会,它们在策划一起谋杀,谋杀的对象便是我。我知道了蚂蚁的整个计划,在蚂蚁实施前,捡起一根树枝。我将手中的树枝变成一把剑,不断地发起进攻。蚂蚁的身体慢慢变大,我刺出的每一剑都命中一只蚂蚁。在我疯狂地进攻下,蚂蚁溃不成军,四处逃散。我看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我手中的剑也有浓浓的血腥味,甚至还冒着热气。
打了胜仗,我异常兴奋,却又觉得饿了,便起身去找吃的。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到了哪里。当我在一家包子铺停下的时候,有人从后面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以为是刚刚逃跑的蚂蚁找我报仇,便将手中的剑往后刺了出去,才慢慢回头。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小女孩。杀错人了,我慌乱地丢下手中的剑。左右张望,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杀人。但是,周围早就围满了人群。我准备逃跑,鼎沸的人声开始袭击我,在我体内装了一万斤炸弹,马上就要爆炸。
一切如幻觉。小女孩突然抓住我的手,说,你为什么杀我,我就算做成鬼也不会放过你的。我看到女孩的脸渐渐变成了一只蚂蚁。我吓得跪在地上,说,我不是故意要杀你的,求求你不要找我报仇。小女孩又将我抱住。这次,我听到她说,妈妈,我总算是找到你了。你这几天都跑去哪了,边说边哭了起来。
包子铺前的人越来越多。一个男人走过来将我扛在肩上,说,大家都散了吧,她脑子有些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反抗。
我被关进了一间屋子。记不清在床上躺了多久,我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床头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我艰难地坐到椅子上,从抽屉里找到一张照片。我觉得照片上的女人有些眼熟,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我使劲地回忆,奈何脑海里没有半点有关她的记忆,只好放弃。我继续在抽屉里翻找其他东西,便找到一张十年前的旧报纸。我认出头条上的几个大字——×××××。
天快黑的时候,我又找到一张病历单。琢磨了很久,才认出病历单上的名字,刘小琼。我觉得这个名字也很熟悉,自己一定认识她。我一会抓脑袋,一会拍大腿,终于,我想起来刘小琼就是我自己。我高兴极了,我终于想起自己的名字了。我又将目光停留在桌下的照片上,照片上的女人穿着一条黄色的裙子,头上戴了一朵花,穿一双白色高跟鞋,身材极好,既不胖也不瘦,极具韵味。甚至有些性感,是最能吸引男人的那种。我突然想起照片上女人的名字,刘小琼。刘小琼不就是自己吗?我露出满意的微笑。要是有面镜子就好了,我想好好看看美丽的我,性感的我。
凌晨三点,我听到一阵脚步声。我睁开眼,想从床上坐起来,身体却不听我使唤。男人身上的酒味向我袭来,我眼睁睁看见男人脱下外套,在我旁边停了下来。一个巴掌随之而来,我听到巴掌接近时发出的风声,想躲闪身体却动弹不得。挨了一巴掌后,我发现自己的身体能动了,当下一掌过来的时候,成功躲了过去。却因此激怒了男人。男人用了更大的力气和速度,这一次我躲闪不及。男人趁势而上,边打边说,遇见你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我这一生全被你毁了。男人拳脚并用,我也开始反击,两个身体扭打在一起。从床上打到了地上,身上的衣服被撕得破烂,我露出的肌肤,被男人用手揪住,强烈的疼痛感伴随着惨叫,由内而外。
我不知道房间是什么时候起火的,当火势凶猛的时候,我和男人还在地上厮打。突然男人停止了手中的动作,起身跑了出去。我一点力气也没有,瘫软在地上,看着火一点点向我靠近。我开始燥热,而后口干舌燥,身体里的水分不断被蒸发。在我快丢失意识的时候,我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女孩的呼救声。我瞬间充满了力量,从火中站了起来,向女孩的房间冲去,把女孩抱了出来。在我被掉落的木头砸中的时候,我将女孩从一楼窗户扔了出去。
我倒在了火海。脑海里又出现了那间画室,还有一个男人。这间画室在楚城的郊外,原本是一家废弃的农舍。我和男友周桦都是学画画的,一次采风的时候发现了这里,便决定把它租下来。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农户,经过商量,农户以五千块钱的价格卖给了我们。我们花了两个周末,把里面清扫了一遍,又重新装修布置,让其充满艺术气息。从此,这里便成了我们的画室,每个周末,我们都来这里画画,然后在沙发上做爱。直到周桦带来了另一个男生。周桦向我介绍,他叫李漫,我俩是发小,也是学画画的,他在楚城的另一所大学,和我一样,都是大四。我首先注意到李漫的长发,随性又不失艺术气息,随后才被他精致的脸庞吸引,其若隐若现的胡茬无形中又给他在别人心中的印象增添了几分神秘感。我最后才打量其穿着,一件格子衬衣配一条牛仔裤。
李漫确实是一个随性之人。比如他喜欢赖床,又会在起床后不洗漱就抱着画板去找阳光,有时也会把自己关在画室,忘我地创作,累了趴在画室睡觉,醒来又接着画。但更多的时候他喜欢抱着画板在田野晒太阳,什么也不画。当然,这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而周桦与他却截然不同,他生活规律,且原则性极强。比如,他每天晚上十一点必须上床,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吃早餐,然后看一个小时的国外杂志,才开始一天的工作。周桦平日里话不多,但每句话都像是在下命令,而李漫却活泼开朗,无话不谈。有时,我就怀疑,这么多年这两人是怎么相处的。后来事实证明,我的怀疑完全多余,两人不仅相处得很好,而且很愉快。甚至周桦每天和李漫说的话比和我都多,让我觉得自己才是多余。但也怪不得自己,周桦和李漫每天谈论的那些国外画家,不是我不主动关注,是我根本没听说过。虽然我也是学画画的,但每次都是听他们谈论完,才去网上查找资料,但很多时候就连网上的资料也很有限。有时我也奇怪,他们为什么会喜欢那些既小众又没什么名气的画家。
自李漫来了之后,我和周桦的关系似乎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很微妙却又说不上来。最直白的一点就是刚开始觉得三个人一块画画也还好,但时间一长,我就觉得李漫的到来,严重影响了我和周桦的私人空间。有时我也想和周桦做一些更为亲密的动作,但一想到不远处还有一个人,只好选择放弃。关于这一点,我也私下跟周桦提过,但周桦的答复是,李漫是他的发小。还有一点,我发现周桦似乎在有意疏远我,但也有可能是我的臆想,毕竟没有证据。而李漫对我的关心却过于热情。或许,也是我多想了,别人只是无心。事实也证明,确实是我多想了,因为李漫不仅关心我,也一样关心周桦,甚至对一只猫、一朵花都极具呵护。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月。一天,李漫提议在画室搞个Party,时间定在第二天的下午。我问,都有哪些人参加。李漫说,就我们三,还有一只猫。经过一天的精心准备,Party于下午六点开始。一开始我们分别介绍了自己最满意的一幅作品以及创作动机,另外两名对其进行点评,然后对其艺术风格进行讨论。随后,我们三人又共同完成了一幅画,画的内容便是此刻的场景,并将这幅画叫作 “晚餐”。最后才艺表演与喝酒同步进行。那天晚上我唱了三首歌,跳了一支舞,我酒量不好,没喝多少就醉了。躺在沙发上,迷糊中听到周桦和李漫在交谈,但具体谈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周桦就消失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电话号码也变成了空号。我的世界一下子就黑了。
后来,我在李漫的口中得知,他们一家移民了。我要去找他。李漫将我抱住,说,他们不会再回来了。你不要再傻了。这一晚,我们喝了三瓶红酒。上头的醉意让我丧失理智,将我推向李漫的怀抱,也推向了深渊。是我主动的,我只想发泄,将两瓣唇贴了上去,如雨点般发起了进攻。李漫的心被撩拨,然后沦陷,发起更为猛烈的攻击,我得到前所未有的快感。
随后的很多个日子里,我们每次来画室,不画画,只做爱,然后在天亮时离开。李漫不止一次地对我告白,让我忘了周桦,一起去另一座城市。我没有拒绝,也没有给他明确的答案,只是用身体回应着他。我心里清楚,一开始不是因为爱,现在也不是。我很想结束这种关系,却又上瘾般迷恋这种感觉,像星星划破夜空,更像飞蛾扑火。
那晚,当画室被熊熊烈火包裹的时候,我们才从梦中醒来。楼外聚集了附近的村民,他们从不远处的水塘挑来水灭火。由于是木质结构,火势燃烧很快,眼看小楼快支撑不住,李漫用被子将我裹住,从窗户扔了下去。我在泥里滚了一圈,眼睁睁看着楼层倒塌。村民挑的水并没有及时把火熄灭。火灭的时候,这里只剩一堆堆灰,和一阵阵飘向天空的青烟。我没在火中看到有人走出来,却在远处的黑夜里看到一个身影,熟悉又陌生。
那晚大火后,我被农妇收留。但神经开始失常,没过多久就嫁给了农妇的侄子,还生了一个女儿,叫小雪。一开始,男人对我很好,每天对我嘘寒问暖,照顾有加。再后来,有人传言,曾看见我和别人在被烧毁的房子里,是破鞋。男人不仅质问我,还整日喝酒,对我越来越冷淡。在小雪两岁的时候,男人发现小雪不是他亲生。每天晚上喝酒回来,对我家暴,我整日活在阴影里。
梦里的火熄灭了。我从床上坐起,四周漆黑。我的脑海不再空白一片,很多段碎片开始攻击我。但无论我怎么努力,都不能将这些碎片,拼成一张完整的画。它们毫无逻辑,无规律地四处乱窜。
几只吵闹的麻雀把天叫亮。一个女人走了进来,穿着白色的制服,还戴着口罩。她走到床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笑了下,说,我叫刘小琼。我还有个女儿,叫小雪。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你帮我找找。女人打断了我的话,一边翻看着手里的几页纸,一边说,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叫马芬,刘小琼是你隔壁床的病友,上周刚出院。请记住你的名字,不要再忘了。我翻下床,说,你才是马芬。我叫刘小琼。请记住我的名字。来,我们玩个游戏,我考考你,二加三等于几。女人没有回答我,走了出去,和门外的另一个女人说,她的病情很严重,加大药量。
我走出门外,大声嚷道,你们才有病呢。女人没有回我。院子里,树下的几只蚂蚁爬了几步停下,说,你们有病,你们都有病。
我闭上了眼睛。周围全是湖水,我踩在一朵云上。后来,我又看到了那幅画,以及那个救过我的男人,戴着草帽,在岸边,我只看了他一眼,他手中的鱼竿迅速提起。中鱼了,他稳住鱼竿与鱼较劲。鱼线发出的 “嗡嗡”声向我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