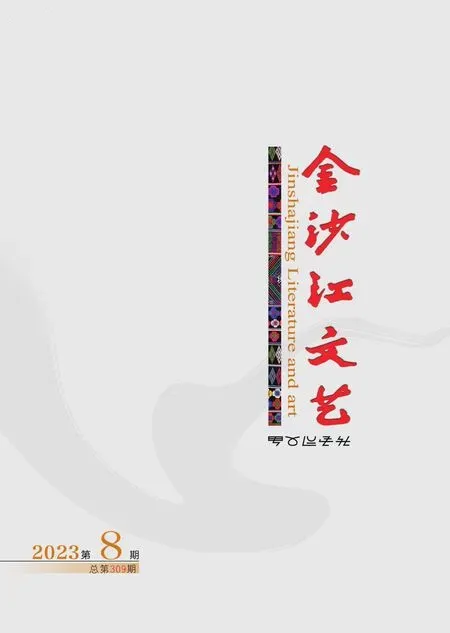嚎叫
◎钱静
1
夜晚,钟平坐在地埂下,蜷着脚等待,目光灼灼,如虎。头顶上是地埂斜长出的清香树蓬,影子如伞一样罩着他,以更深的夜色给他提供掩护,来人只有走到面前才能发现。右边五米外是一条小路,有棱角的石头半截埋在路面下,高低不平,只要路人不小心,被它绊个狗啃泥毫不费力。这条路往上一直通到斜坡上的果林。他下面二十多米远是一条柏油路,六年前修的,像一条用旧了的布,颜色淡了。左边的柏油路下,一条一米宽的砂石路斜斜插进一道木门,那是余如艳家。右边从公路伸出一条通往村里的小路,起伏着往下蜿蜒,在房屋间爬了一截,迎面撞上一个足球场大的水塘。水塘除了东面,其他三面都被村庄围着。
他处在高处,能看见从沙石路走上来的人影,如果月色很好,从体型和模糊的面貌能看出是谁。如果没有月亮,人影会用手机照明,从手机反射的微光也能大致看出是谁。通常用手机照亮的是余如艳,他爹七十多岁,不大黑夜出门,即使出门也只用手电筒。今晚有点月亮,浮在西边,弯弯的,很浅。夜色像一副盔甲,小虫可以大胆鸣叫。从集镇方向传来拖拉机突突的声音,半分钟后,消失了,只剩虫子们唧唧叫。
余如艳个子不高,比他瘦,高颧骨,大眼睛,嘴皮外翻,常板着脸。钟平想结结实实见他一面,结实到以后无须再见。这种见面,能改变余如艳的命运,而他的命运不受干扰,稳步前行,如平缓的河流。要做到这点,得有个好时机,除了神仙,没人知晓。余如艳回村后的开始几次,在路上遇见他,扬着下巴,睖着眼,十多年牢狱捆缚,还是像一头想顶人的牯牛,钟平也使劲用眼神顶回去。后来,余如艳远远见他,低着头,避开了。他有点奇怪,这牯牛怎么不睖了,难道裤裆里的东西被捶掉了?
他右手边是一把锄头,锄把刚换上的,一米五左右,锄口平直,银白铮亮,约二十五厘米宽,高比宽长一点。除了田地里除草,挖泥,他还用它修剪树枝,吓一吓恶狗,也办一些事,比如现在。空闲的时候,他把它拿到石头上磨,磨得晶亮,锄口锋利得手指只敢轻轻往上碰,似乎担心惊醒它,猛咬一口。他用它宰杀过田鼠和蛇,一锄下去,身体就齐整地分开,四肢还在毫无意义地乱弹,似乎要弹去疼痛。看着它们扭动的样子,他就想到余如艳,想到母亲。
母亲干活是把好手,动作快,在田里点蚕豆,手枪似的按桩在板结的泥上嘟嘟嘟戳出一个个眼,左手紧跟着在眼里摁进豆子,片刻,身旁就长满嵌着豆子的眼睛。他慢,母亲点三颗他才能摁进一颗, “你太慢了。”她说, “种庄稼要有点性子。”他也想快,可就是快不起来。他试过,按桩戳得快,深度不够,且间隔不均匀。他不想为了速度不讲质量。
很多人家都在上田埂点豆子,下田埂让下一块田主点,余如艳不这样,他既要使用上田埂,也要占用下田埂。他说: “我的田埂为什么就不能点?”似乎有道理,但违反了大家都在遵守的规矩,母亲不容它肆意乱来,去上田埂点了豆子。他不高兴了,也去点,两家的豆子相互穿插,不分彼此。
村里的灯光,映到水面上成一条白凉的路,这条路还没延伸到水塘中央,就弱了,暗了,像沉入水底。他的路不想沉入水底,要越走越亮,余如艳是他心上的坎,得跨过去。身边小虫在叫,一刻不停,似乎是绷紧的夜色鼓弹出的小孔,给夜呼吸。今晚,余如艳会不会出门,他不知道。头顶的树影慢慢往里缩,右脚露在浅淡的夜色里,他把它缩回来。
钟平已经来这里等了几个晚上,余如艳出来过两次,一次是九点多,骑摩托带着十二岁的女儿到镇上,他回家开了面包车去路上等他回来,可快到凌晨一点没见踪影。后来听说,他姑娘得了白血病,去镇上医院打针,打完针在镇上的亲戚家住下了。另一次余如艳八点多出来,开着手机电筒,他提着锄头下去。余如艳往下进了村子,迎面走来一个男人,和他打了招呼。钟平不想让男人认出来,岔进一条小路,从小路出来,没看到被跟踪的人。他怀疑是不是余如艳发现后躲起来,但随即否定了这个猜想,自己跟得并不紧。
他把手机捂在夹克里,低头看时间,快到十半点。十点半以后,村里几乎没人出门。他等了一会儿,扛着锄头回去。
他回到家,父亲还没睡。父亲知道他出去干什么。余如艳入狱后,钟平知道他十多年后会回来,心里有不甘,没想让他永远消失,只让他后半辈子离不开床,而自己又能毫发无伤。父亲不这样想,说: “做十三年牢,太便宜了,要让他见阎王。”得知余如艳减刑快要出狱,只做十一年牢后,父亲就更坚决了: “要让他见阎王。咔咔。”他咳起来,带有咻咻声,好像肺通了几个洞,风穿洞而过。父亲在钟平面前说了多次,钟平原来的决定也悄悄发生了变化,接受了父亲的想法。他想,彻底完结,可以眼不见心不烦。父亲总念叨,自然是要他去解决。
屋里亮着灯,父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右手搁在膝盖上,手指夹着烟,烟灰吊得老长。电视放的是抗日剧。这些年抗日剧很多,只要打开电视机,随便调两个频道,就能蹦出一个。父亲说马华来过了,说完咳了一声。马华是钟平堂姑妈的女婿,十六岁时曾在村里把一个十三岁的男孩踢了三分钟,还边踢边笑,仿佛遇到世间最快乐的事。男孩父亲在巷子里以同样的方式招呼了他。人们说,他被踢时的叫声如雨夜鬼哭,能长大健康活着,都觉得是个奇迹。农活上,他偶尔让马华帮个忙,来往不多。马华嘴碎,碎到一只杯子上有一朵花,能说到一大堆杯子上的图案,话头像火,燎到哪儿算哪儿,脑子里窖着的话没几句。钟平不喜欢多说,觉得说多了没意思,说十遍不如做一分钟。为此,妻子不让他去城里找工作,嘴不甜,吃不开,便独自出门给别人带孩子。
他问马华来干什么,父亲说:“他说安山有个医生,医术高明得很,好多癌症都能治,医药费高了还免,让你带我去看看。”父亲咳了两年多,时好时坏,吃药打针无数,还是治不好,他犯愁,担心拖长了得癌。癌症能治他还是第一次听说,有点不相信,但可以免费,有些动心。只有一个父亲,且从没打过他,他希望他好好活着。他决定去问问到底是不是真的。
天刚亮,他走进往北的巷子,转过两个弯,到了马华家院门前。门半开着,他刚要推门,身后听到有人喊表弟,转过身,马华从二十米外的厕所门口过来。马华个子不高,瘦,头发焦黄,四十岁出头,笑起来,眼角周围的皱纹像杂草一样浮起。他递过去一支红梅烟,问跟父亲说的是不是真的,马华说是真的,语气诚恳,看不出胡说的样子。钟平问医药费高到多少能免。他说超过两百的部分,可以模仿一些叫声。他浅笑一下,掏出打火机给马华的烟点上。他问他怎么知道有那样一个医生,马华说一个朋友去看过病,还说了医生名字。他问有没有医生手机号,他说有,掏出手机翻找。钟平按手机号打过去,对方声音厚重,岁数可能六七十岁。老医生说他父亲的咳嗽能治,说法跟马华差不多。
不知道那些叫声有什么标准,会不会让人笑话,马华的那张嘴,传出去难听。想想,还是决定去,父亲的病要紧,不就是学动物叫么,又不会掉一块肉,万一父亲的病严重到治不了,学驴学猪叫都挽回不了。他离开马华,看看天,有几朵云浮着,一块一块的蓝把它们推来推去,像挡了自己看地面的目光。他回家告诉父亲,问过马华了,是真的。早早吃了饭,他带着父亲,开着那辆二手面包车赶去五百公里外的安山。
2
他和父亲下午三点半到安山县城。钟平在城里问了几个人,他们都不知道,最后问到一个开商店的中年妇女,才知道老医生住在离城三公里外的一个村里。也不完全在村里,离村大约一百多米,单家独院,东面四间平房,南面一幢三层钢混楼房,二楼的阳台挂着晾晒的衣裤,一条枕巾在微风里晃荡,像招客的手。
院门口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的跟老医生说的差不多,超过两百元的医药费可以用学狗叫、羊叫或人叫代替。旁边是一块小一点的牌子,上面写着先听后叫的步骤,在 “听声室”听声音,然后选两种声音到 “嚎叫室”叫唤,人声必选。注意事项:听声不得少于十分钟,进入 “嚎叫室”不得少于八分钟,否则不能免医药费。十分钟左右,他觉得不是太难熬,让他不安的是后面的提醒:可能会有噩梦,但会慢慢消失。噩梦他做过,有时醒来心脏还咚咚跳,全身汗水淋漓。父亲的病有点严重了,医药费一次六七百都有可能,能省去那么多钱,做几个噩梦算不了什么。
诊室在平房的南边一间,另三间从北至南分别是 “听声室” “嚎叫室” “药房”。有隐约的呼叫声从“嚎叫室”传出来,对外面的人没造成大的干扰。诊室前的屋檐下,摆着两排盆栽植物,有万年青、绿萝、紫薇,绿的葱郁,粉的娇艳。老医生有两个助手,一男一女。男子三十多岁,矮个,微胖,小眼睛,脸上无喜乐,管理着 “听声室”和 “嚎叫室”。没人的时候他坐在厦台的长沙发上,钟平见到他时,正低头剪指甲,专注如考古学者。女子清瘦,神情柔和,鼻孔膨开,像两个隧道口,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给病患抓药。
他和父亲走上三级平缓的石阶,“嚎叫室”的门开了,一个宽脸庞的青年男子走出来,手上戴着一副奇怪的手套,眯着眼,慢慢走到沙发上坐下。他和父亲去了诊室。老医生七十岁左右,穿一套有点暗沉的白色太极服,精瘦,高个子,站着像个简易瓜架,高鼻梁,头发灰白,下巴留着一蓬旺盛的黄胡子,目光平静和蔼。诊室的三面墙上挂满锦旗,有 “再世华佗” “妙手奇术药到病除” “妙手回春,治好我的白血病”等等。父亲在老医生对面的高椅上坐下,老医生问了症状,让他张嘴看看,又让他伸出右手,把瘦长的食指和中指搭在他手腕上。半分钟后,在一张药方上开了四包草药和两盒中成药,共四百三十六元五角。老医生问钟平要付费还是喊叫,他没有犹豫,说喊叫。 “你做吧?你父亲病着。”老医生说。他给父亲开了一张 “嚎叫单”,顶头填上父亲的地址和姓名,下面是四条打印好的注意事项。钟平让父亲坐在厦台长沙发上,把 “嚎叫单”递给矮胖男子,男子看一眼单据,把它放在沙发间的矮桌上,用一根青色的两指宽的石条压着,从矮桌下拖出一个纸箱,拿出一副灰色皮手套。这手套跟刚才那男子戴的一样,掌心和手背都安着浅黄色三根手指粗的胶条,胶条间有凹槽,指套部分呈方形,指尖也是方形,五个指套中间是连着的,像鸭蹼。矮胖男子给他戴上手套,轻声说,进那道门,右手指了指最左边的门,钟平进了 “听声室”。
半拃厚的木门,门框边是褐色的橡皮,关上门严丝合缝。室内空气混浊,似乎被煮过,尚有余温。天花板上一个葫芦形灯泡,发出黄白的光亮,墙面像病人的脸。见到这样的灯光,即使精神昂扬的人也会委顿下来。天花板的东北角,贴着一个黑盘子似的东西,西、北、南三面墙脚摆着长沙发,铺着宽大的深棕色布巾,灯光撒上去,像蒙着一层灰尘。
他轻轻坐在靠门的沙发上,等待着。没过三秒,声音响起来,清晰,伴有轻微的电流唧唧声,显得苍老破旧,仿佛经历了千山万水和悠悠岁月。他仰头看,声音是从那个黑盘子似的东西播撒出来的。它传出狗的哼叫声,声音不大,慢慢变得凄厉、尖锐,如一把锋利的刀,是那种脑袋上打了一棒的痛苦呼叫。他脑中似乎看到一条狗趴在地上,嘴巴张着,眼睛微闭,头顶流血。渐渐地,狗声短促下来,微弱,最后停止。接着,响起羊的叫声,拖得很长,像一条绷紧的皮筋。这条皮筋越来越紧,越来越薄,透明到一吹就破。大概是一把刀插进了脖子,声音似乎是心脏痉挛时迸发出来的。然后是哼叫,还是拖得很长,到结尾有嘶哑,似乎嗓子已经破裂,满是绝望、悲苦。第一声时,他的心脏紧缩起来,仿佛刀子捅的是自己的身体,手不自觉在身上摸。第二声,感觉心脏就快碎掉。他闭着眼,抱着头,全身每个毛孔在颤抖,肌肉抽紧,身体蜷缩着,尽力抵挡哀鸣声对脑神经的撕扯。他感觉自己就是那只奄奄一息的羊。他捶打着胸口,让呼吸更顺畅些,想把耳朵堵上,发现方形指套无法塞进耳孔,用手掌去捂,胶条撑着耳郭,留着空隙,不能隔音。他这才知道,戴这个手套就是阻止听声者堵耳。他想脱下手套,但五指相连,且指尖方形,无法脱下。只好继续忍受。
羊叫声结束后是人的哀号。开始是一人在叫, “啊”声拖得很长,到后面细下去,最后成游丝,然后接着第二声第三声,高而尖,像一支威力无比的箭往高空飞驰,越过山峰,进入大气层,往上,往上。那支箭渐渐失去力量,变得缓慢,更慢,折身往下坠落,最后掉回地上,安静地躺着。然后是一个男人粗哑的叫声,肉体受外力捅刺或击打才会发出。叫声里伸出一只只无形黑手,把他的胸口紧紧抓住,也搅动他的脑神经。脑中浮出一个男人被捅刺的画面,男人嘴大张着,脸上的五官聚拢在一起共同抵抗疼痛。如果他们就在眼前,他会不顾一切去解救,以结束心被挤压的滋味。身体在发抖,似乎要把身上的肌肉重新组合。紧接着,嚎叫的声音多起来,很多种,有尖细的,有宽厚的,有娇嫩的,有苍老的,有柔美的,等等,不管是哪一种,都带着坚硬的哀号,大约有二三十个人在嚎叫。脑中是成片的尸体,凑近看,胸口汩汩冒血,眼珠不动,嘴微张,脸色渐渐变灰。他看到了倒地的母亲,脖子上汩汩流血,嘴张着,艰难地呼吸。似乎还有话语声,叽里呱啦,他不知道是什么语言,但几乎都是吼叫出来。模糊间听到一声 “啊”。
他的心脏激烈跳动,似乎要冲出胸口,全身发紧。他不想再听下去,但又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个声音突然想起:已经十一分钟。他如得救一般起身,拉开门出去。世界安静了,雪白的阳光斜射在院子里,但那些哀号还在脑子里萦绕。他跌跌撞撞走几步,伸手扶住厦台上的一张长椅,坐下去,头靠着墙,双手耷拉在两侧。矮胖男子给他脱手套,他身体瘫软,随他脱。
厦台尽头的父亲看着他,神色疑惑。为了让父亲放心,他把身体坐直。他活了三十多年,听到过男人脚趾被石头砸的叫声,听到过狗被打中脑袋的哀号,和羊被宰杀时无助的呼喊,可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些搅动脑髓的声音。他怀疑刚才听到的不是现实里的惨叫声,而是比它们更纯粹,仿佛就是寻常惨叫里提炼出的精华。
周围没有人声,也没有风声狗吠,院里的花在阳光里静静地开着,一切对他刚才身心遭受的风雷毫不知情。脑子里还有尖声嚎叫在盘旋,他甩甩头,它们还在顽固地叫着,似乎永远住下了,还生儿育女。大约休息了十分钟,他脑子里尖锐的叫声弱下来,稀疏了。
他走到矮胖男人前,确认是不是选两种嚎叫,男人面无表情但柔和地说,是的。他转身走向 “嚎叫室”。这次没有戴手套。他不知道 “嚎叫室”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是否能坚持住。不安攫住了他,但又必须面对。他推门进去。同样是厚厚的门,门边沿是多层灰黑色橡皮。灯光比 “听声室”要亮些。靠墙是两排沙发,地面铺着暗红色地毯,中间一朵筛子大的红牡丹,长期被人踩踏,落满灰尘,认真辨认才能看出。
他回想着刚才听到的叫声,抓取每个细节,力图让呼叫具有真实性。首先学的是羊叫声,他张了张嘴,但没有声音,他清了一下嗓子,第二次张嘴才发出来,很轻,似乎在试探。声音很陌生。慢慢地,嗓子好像被打开了,声音大一些。一声声,他感受到羊被捅一刀或烙铁灼身的痛苦。他觉得自己就是一只黑山羊,被两三个男人摁在地上,一个男人把一片亮晃晃的刀捅进他的喉咙,似乎感觉到那刀片的清凉。他摸摸喉咙,完好无损,心里宽慰一些。嗓子已经喑哑。他停下来,捏捏喉咙,学人的叫声,是那种疼痛的叫,啊——。脑子里出现许多人被棍棒捶打、被刀子捅刺的画面,都大张着嘴,眼睛和鼻子紧缩在一起。砍杀的人有二三十,他们脸上狞笑着。他出现在他们中间,他和同伴的每一声嚎叫,都能引出砍杀者的兴奋。他的嗓子哑了,发不出声音,脑中的画面慢慢消失,他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屋子里。有一个声音说,已到八分钟。睁开眼睛,他发现自己跪在地毯上,脸捂在那朵筛子大的牡丹花上,眼眶已经潮湿。身边一片红,他吓了一跳,莫不是身上的血流出来了,右手摸一摸脖子、胸口,没有伤口,心平稳下来。他缓缓站起,身子晃了一下,终于站稳了。他开门出去。外面的世界风平浪静,连太阳都没挪一下身。
后来的好多天,他才慢慢领悟到,听声是激发出生活里所经受的割伤与砸伤记忆,并让它们鲜亮,嚎叫是加强它们在身上的感觉,使其渗进骨髓,以便储藏。
矮胖男子把一张纸递给他,他接过来看一眼,是那张 “嚎叫单”,右下角有一颗红色的圆形章印。他晃着身子走近父亲,父亲像个傻瓜一样看着他,过几秒才问: “不咋样吧?”他说,没事。他走向老医生的诊室,付了两百元,取了药方,再到药房拿药。
他和父亲当天就回来,到家时已近夜里十二点。本来可以更早一点,可路上停了好几次。他不得不停下来,因为他的脑子总有狗、羊和人惨烈的叫声,那些叫声任凭他怎么驱赶,还是顽固地挤进来。有几次在转弯处,面包车差点跟对面的小车相撞,父亲的脑袋差点碰到挡风玻璃。“小心点开。”父亲责怪着,右手紧紧抓着车顶上的把手。 “那些叫声在脑子里转。”他解释说。父亲体贴地说:“开慢一点。”为了赶走那些叫声,他不停抽烟,眼睛直勾勾盯着前面的路。它们就像一群蜜蜂,被烟草味赶走一些。父亲右边窗子大开着,说,连我都受不了这烟味。回到家,他的嘴巴又干又苦,灌了两杯茶水下去才好一点。
他煮一碗面吃下就躺到床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很多烟雾,遮住了整个天空,他和一些人在一个山坡上,子弹都打光了,手里只有刺刀,山下是密密麻麻的敌人向他们爬来。他们冲下山,对方开枪,战友纷纷到下,他也中了枪,胸口一疼,但能走,身上还有力气,提着刺刀一个一个戳,惨叫声像要撕碎他们的身体。很多人围过来,他身上一齐被戳了好几刀,身上吱吱疼,也很害怕,疼和怕把他摇醒。一个梦,杀敌之梦。脑子清醒后,没有一点睡意,看看手机,凌晨四点十八分。他把枕头立起,背靠上去,被子盖到胸口。
过了一会儿,他才迷迷糊糊睡去,还好,没有做梦。
3
他醒来天已大亮,天光从玻璃窗涌进来,把屋子灌得满满的。
他从屋子出来,父亲用一把长扫把扫着院子,缓慢而有耐心。他问父亲昨天拿回的药吃了没有,父亲说吃了。他洗了一把脸,扛着锄头走出院门。
院墙下就是家里的烟地。烟已经烤完,齐腰高的烟杆只剩顶上几片小叶。从烟叶上散发的焦油味腻腻的,带着潮气,比燃烧的烟味还难闻,他皱了一下鼻子。从地头开始,他一锄锄齐根铲掉烟杆,它们在身后倒成一片,切口微斜。无须太用力,它们就一根根倒了。他一时感觉,那些嚓嚓声,是疼痛的呼叫。这种疼可能很轻微,轻微到被人忽视。
砍烟杆是在消灭,点豆子是为了生长,可母亲的生命却在点豆时被掐断。出事的前一年,余如艳在那条埂上点蚕豆,母亲也点,每个人都在扩大自己的领地。父亲对母亲说,让他点吧。母亲说,能收到六七斤豆子呢,况且上埂本就是我们点。钟平说他太欺人,不能让着他。事情发生那一年,他二十四岁。
后来余如艳在法庭上供述,开始隔着二十多米相互咒骂,后来他提起地头母亲用来淘沟、铲草的锄头,走到母亲身边,母亲不认为他敢用锄头打她,还说,你有本事就打下来,被她的话一激,他抬起锄头往她脖子上一挖。
钟平赶到母亲身边的时候,她的五官挤在一起,倒在田埂下,鲜血湿透肩膀和前胸,左手还捏着几根坠着豆果和绿叶的杆。母亲没送到镇医院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余如艳判了十三年,在狱中表现良好,多次减刑,最终十一年后出狱。出事时,他姑娘半岁多,妻子两年后丢下女儿另谋生路。听说,那姑娘整整哭了三天。他出狱后,父亲跟钟平说: “太便宜他了,你咽得下这口气?”他说咽不下。
烟杆继续倒下去,他砍的似乎是一个个脑袋,嚓嚓声让他感到它们身上血管破裂。他的锄头慢下来。脑中出现这样的画面:狗在撒欢,摇尾,羊睁着温和的眼睛,转瞬间,血光四射,哀号声起,一条条生命躺在地上,心脏下垂,呼吸迟缓。余如艳也会这样,五官紧缩,身体扭曲,由热变冷,血液凝结;蛆虫蠕动,曾经的音容笑貌化为尘土。他停下锄头,抬起锄口,阳光照上去,反射着银白的光。锄口薄薄的,还是很锋利,他伸出拇指,还没碰上,感觉它已经被切割,想象中的疼灌满整只手臂,他电击似的缩回手指,摇摇头,努力驱赶脑中的疼痛和身体的不适感。
在去安山之前,他没有这些感觉,锄头砍下的嚓嚓声听来悦耳,别人的哀号与己无关,似乎隔着千山万水,还有一些看戏时的赏玩心态。现在不一样了,任何身体的扭曲、脸部的紧缩和声音的哀鸣,都能让他感到心脏在收紧,血液流速的滞涩,仿佛他们身体的不适快速传到自己身上来。
太阳钻进灰云,空气凉了些。锄头继续起落,很少停,羊、狗和人的嚎叫声偶尔在脑子里冒一下,每次冒出,锄头慢下来。
烟杆快砍完的时候,院墙下的路上有个上年纪的老人背着一个竹篓走过,篓里是四五个青南瓜,身后是一个女孩,手里捏着一把镰刀。老人是余如艳父亲,身后的女孩是他的孙女。女孩比同龄人矮一些,头发黄黄的,在脑后用一根黑色橡皮筋束着,脸瘦瘦的,显出青黄,因为瘦,眼睛显出大来。脚上一双白色球鞋粘了泥点和污渍,鞋面也破了。钟平从没跟女孩说过话,对他来说,她是陌生的。她扭头看他一眼,眼神凉凉的,似乎含着悲苦。他的心荡了一下,一团气似乎在胸口徐徐散开。
“砍烟杆啊?”老人说,脸上露出浅笑,似有一丝讨好。
“嗯。”他答。儿子进监狱后的前六年,老人见了他低着头,也许是愧疚,近几年会打声招呼,他含糊应一声。他想过,一定是儿子要出来,老人担心算旧账才想跟自己缓和关系。他便顺水推舟,应一声,让老人以为儿子出来后没事;另外,害了母亲的是他儿子。他爹是他爹,他女儿是他女儿。
4
晚上,他扛着锄头又来到树蓬下。月亮宽厚了些,公路上驶过的车能看出明显的颜色,不过,这乡镇的夜间公路,车辆很少,更多时候被寂静笼罩。空气清凉,带着微微的清香。小虫发出一片唧唧声,不知道来自哪个角落。
随着小虫的声音,他的思绪飞扬开来,飞到那个满室鲜红的密闭房间,他在嚎叫声中抽紧、颤抖,室外的人却一无所知。思绪飞到余如艳上。锄头下去,余如艳的五官挤缩在一起,身体像软泥一样摊在地上。白血病姑娘一脸愁苦,看到父亲倒地,摇晃他的身体,哇哇哭,声音嘶哑,瘦弱的小手仍死死抓着他的手臂。她随后的日子,永远没有了那个给她洗衣、送她上学的男人。她在阴雨中,孤独地行走,张眼四望,雨雾茫茫,头发被雨水打湿,一绺绺粘在脸颊上,一双破了的球鞋粘了许多稀泥,磕磕绊绊走向荒野的坟堆。离开坟堆,她坐在山坡上,面对迷雾缠绕的远山呜呜哭泣,哭那个永远回不到身边的父亲。越哭声音越大,最后变成嚎叫。他的心脏微微收紧,呼吸也缓滞了。
公路上驶过一辆小车,响声驱散了他脑中的画面。
一片黑云在移动,挡住月亮,四周暗下来,公路上如果有人走动,只能看到黑影。大约过了十分钟,黑云过去,月光再次现身,铺展到路面和屋顶上。
一个女孩的哭声传上来,柔弱而纤细,一缕风就能把它吹走,仔细听是从公路下的院里传来的。接着是一个男人轻声呼喊 “小宝”的声音,后面的话听不清,但可以听出是那个男人在说话。女孩还在哭,男人柔声安慰,声音轻软、甜馨,像个女人。
哭声渐渐平息,院子里传来踏踏声,是脚步轻跑。 “小宝,好不好玩?”院子在低处,一股风把男人的声音送上来。 “我学狗叫很像,你听听,嗷,嗷,嗷。”是狗挨了一棍的叫声。如果他现在出现在面前,我会不会把锄头往他脖子上砍下去。他垂下头,不能确定。
男人牵着女孩在院子里慢慢走,嘴里还在哄逗着孩子。 “他会不会出来?”他暗自说,看看手机,时间到了九点五十五分。他起身,扛起锄头离开树蓬,向公路走去。脚步很快,像在逃跑。
他顺着公路往下走,进了田间小路。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从余如艳家那个方向来的。回到家,他把锄头靠在屋檐下北边墙脚——这是它常待的地方。父亲半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见他进屋,坐直身体,问他咋回来得这样早?他说他可能不会出门。过了几秒,他问咳嗽减少了没有,父亲说少了,胸口不像以前辣疼。
“你要记着你妈是怎么死的。”父亲说。他说记着呢。
“我再年轻十岁,用不着你动手。”父亲说。他还没见过父亲做过一件激烈的事。给他减十岁,会不会真的去做,难说。母亲生前常骂他,说他胆小怕事。山林被占,对方说,村委来量时没量够,所以要挪出一米。母亲让村主任去看,村主任说,量的时候多一点少一点在所难免,不要计较,可对方就是不让,主任没再说什么。父亲跟对方吵,最后说: “你等着。”对方倒是等着了,他却迟迟不去。母亲见父亲没有行动,连夜把对方石头砌的地界往外挪了一米,白天手提一把杀猪刀守着,守了三天,对方来跟她吵,骂她母猪后离开了,从此,偃了旗息了鼓。
在钟平看来,父亲和母亲年轻时也许感情很深,但被岁月漂洗,不说有多厌烦,至少已经暗淡无光,再加上父亲仅停留于威吓的性情,是否能为母亲去处理余如艳,他始终怀疑。
夜里,他又做了梦,在一个山坳里,捆绑着一群穿着军服的人,在地上跪成两排,两个瘦瘦的黄头发高鼻梁的军人各提一把长刀,像砍葫芦一样,向跪着的人头砍去。还没被砍的人发出哭喊声,曾露出狞笑的嘴扭曲如破瓢。但两把长刀并没有因为哀号而停止,反而迅速摁灭那些叫声。醒来,身上沾满汗水,黏黏的,连床单也濡湿了。他有点厌烦,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做关于战争的噩梦,仿佛自己曾上过战场,曾经历血雨腥风。
5
他又来到地里砍烟杆。天空布满灰白的云,太阳在云里被收了金光,成了失血的白月亮;空气温温的,即使是轻巧的劳动,也容易催出一身汗。嚓嚓嚓,周围除了呼呼的风声就是锄口割开烟杆的声音,他身后一根根烟杆倒伏在地。往后,它们被太阳晒着,被风沙吹着,一天天失去水分,变黑,变干,最后成为虫子的家,成为烧饭的柴。
他停下手中的锄头,长长叹一口气,手掌在额头上揉了揉,似乎要驱散烦人的思绪。他仰头看看天,又低头看脚下,一只蚂蚁顺着扑满灰尘的裤脚爬上来,手指一拍,掉落到地上,他抬起脚想踩下去,最后还是把脚放到一边。他继续砍烟杆。锄头砍了好几块地的烟杆,有点钝,好多天没有磨它了。
远处传来啪的一声响,他停下锄头抬头看,一百米远的地边,有两个男人一人赶着一头黄牛向这边走来,一人扛着犁,另一人扛着耙。细看,扛着犁的是马华,手里捏着牵牛绳拍打牛屁股,走在后面扛着耙的是余如艳。不晓得是谁帮谁干活。余如艳坐牢前,马华就和他处得好,收谷犁地互相帮衬着,杀年猪也来往。这马华,以后别跟他来往,钟平心里嘀咕了一句。他脑中回响起马华少年时候杀猪般的叫声。那件事后,马华的生活平静流淌,仿佛累了,需要几十年的调养,大概后面的日子,还是这样。
两人离他二十多米,他低头砍烟杆。 “钟平,今年烤烟卖了不少钱吧?”马华的声音,他直起腰说不多,也就两三万。马华说不错了,随即问他带父亲去安山看病没有,他说去了,拿回两包药。余如艳向他浅笑一下,没说话,他没搭理,还是冷着脸。
在他的记忆中,余如艳很少笑,脸像一块铁板,眼珠子一睖一睖的。现在却笑了。脸一笑,人就软和了。他想起余如艳在院子里牵着女儿叫着小宝小宝的情景。
他们走过去了,他仍站立着。母亲脖子上汩汩流淌的血,紧闭的眼睛,永远长眠,而他,只坐了十一年牢,毫发无伤地回来了——余如艳也会嚎叫、流泪,那个带着母性的声音,还有那个瘦弱女孩的哭泣,一生都在哭泣。他紧紧抓着右耳上的头发,一下一下撕扯,似乎要把它们拔下来。
西边群山,笼罩着青蓝的氤氲,最远的那座山后是另一个省,那个省有一部分沙漠。这里到处都是山,村庄就如布片一样铺在山坳里,一眼看出去,山就堵在面前。要走出这些山,得依靠弯弯折折的狭窄公路,父辈的很多人,看到重重叠叠的山就退却了。他想到母亲手里的那一把蚕豆秆,他不知道她在地下是否还牵挂它。
他看看身后躺成一片的烟杆,有点难看,放下锄头,弯腰把它们收拢,抱到上地埂靠着。他留意着脚下的烟桩,不让它们绊到。马华和余如艳已经走远,看不到了。身上有微汗,他坐在地边的一个石板上,掏出烟来抽。余如艳为什么要对自己笑一下呢,是表示友好,还是嘲笑,笑自己不敢动他?不会,他应该知道自己对他的恨,猜想到会搞他,便用笑来软化他。这是求饶,是示好,看来,他也怕死,怕被人搞。他对着余如艳消失的方向狞笑一下,摁灭烟头,起身拍拍屁股,继续把烟杆收到地埂上靠着。
6
太阳在西边山顶上空,把光芒斜斜射下来。他在院子里用锄头砍去石榴树多余的枝杈,绿色的枝条落在树根旁,铺了厚厚的一层,树干上的切口显出新鲜的米黄色。锄口钝了些,粗一点的枝杈得砍两次。
裤兜里的手机响了,他放下锄头,掏出手机,一个陌生的号码。他喂了一声, “钟平,我是余如艳。”对方说。他问什么事,语调平静,但硬还是从平静中刺出来。
“我想跟你说说过去的事,在公路上边的果林里,你能不能来?”语调平和,是商量的口气。也许是伪装出的亲切,包括地里做出的笑,只是想让我放松警惕,他想。
“好,我去。”他说。可能想做个了断,不想把日子过得像走钢丝,他都主动出击了,我还犹豫什么,看看他要耍什么把戏。他换上一双黑色的球鞋,鞋带重新勒紧,拿了一只电筒,走到屋檐下,抓起靠墙的锄头扛在肩上。父亲从厨房出来,问他去哪儿,快吃饭了。他说出去一下,让他先吃。父亲问去干什么,他说肚子不饿,去地里走走。他不想告诉父亲,告诉他也帮不了,可能还会劝自己这人毒得很别去送死,也许会叫一两个人跟他去。不去和找帮手都显得窝囊,窝囊一次,别人就想把它接连送给你,像帽子一样,以为你愿意戴。最好自己解决,见机行事,何况,手里还有一把锄头。
他没有走村中的小路,而是沿着水塘边往东走,从田间小路上去,到了公路。太阳靠近西边起伏的山顶,与山顶相碰的一刻,一定血光四射。他从夜间蹲守的树蓬旁小路上去,走一百多米就是果林。树木稀疏,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石头,有平地,有浅沟,灌木丛生,沟渠边一尺多高的草在夕阳中显出金色,来一阵风,晃了晃,安详而舒泰。它们看不到人生活的样子,或者无心理睬,他想。钟平远远就看到余如艳,他站在几棵梨树围着的一块平整的地上,手里什么也没有,也许,对付钟平的东西可能放在身上。西边的彩霞殷红,如惨烈的战场。走的是缓坡,他微微有点气喘,也许是将面对的事引起的。他放慢脚步,尽量让气喘平静,不想让对方看出任何貌似心虚的迹象。
他走进平地,向余如艳走过去。余如艳穿着灰夹克蓝裤子,裤子的膝盖处发白起毛,黑色运动鞋的鞋面脱了皮,鞋带粘了几根干了的金针草。颧骨高耸,眼眶深陷,狭窄的脑门横着浅淡的条纹,浅笑着,手没有放进衣兜。钟平面无表情,离余如艳三米远停下脚,把锄头放下拄在地上。即使他露出狰狞面孔,钟平也不想硬碰,但面上的硬还是挂着。
余如艳看一眼他手里的锄头,“十一年前的事,我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家,我是彻底的错了,叫你来就是想跟你道歉。”他说时低下头又抬起。钟平没说话,手紧紧按在锄头把的顶端。 “为了表示我的诚心,我向你跪下。”他只跪不磕,眼睛看着他手里的锄头。
他还是没有说话,脸色依然硬硬的。太阳被山顶衔着,天光暗了许多。
“如果你还不能原谅我,那你就把我当成一条狗。”他说完,嗷嗷叫起来,然后是狗脑袋上打了一棒的叫声。声音变了,带着血丝,带着身体遭受到的剧烈疼痛,嗓子像快要被撕破。这是他在安山听到的狗垂死的叫法,虽然不太像狗声,但那种疼痛还是被他喊叫出来了。他停了狗叫,变成人的叫声,啊——,被刀捅的声音,身体趴在地上,叫声回荡在上空,缠在果树枝头,久久不散,似乎要永远挂在上面。钟平的心脏又有了那种被抽紧的感觉,似乎身体的疼痛记忆被唤醒。按着锄把的手松了些。余如艳大约嚎叫了两三分钟,停下来。太阳似乎被他叫落了,完全没入山后。
余如艳站起来,叫声抽空了脑中的氧,身体微微晃一下,脑门的皱纹更深了,目光疲软,脸色暗淡,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如果以后他不会哀号,忘记哀号,自己可以让他真实体验一次,到阴间里牢记到永远,后悔到永远,但钟平不想告诉他这一点。钟平看向左侧的沟渠,青草在晚风中摇曳,平和安详。他放松表情,浅浅地问: “你姑娘的病好一些了吗?”
余如艳笑了一下,似乎为自己的嚎叫收到效果而高兴: “好一些了。医生说,要一年后才能完全恢复。”他又说: “听马华说,你带大叔去安山看过病。大叔好些了吗?”他微微点了头,嗯一声,随即问: “你去过?”他低头默然两秒,抬起头说去过。
夜色开始弥漫,他抬起锄头扛到肩上,往山下走,摁亮手电。路凹凸不平,得小心脚下。他有些轻松,又有点失落,似乎还不圆满。流血的脖子,渐渐变灰的脸。他眼里含着泪水。
回到家,走进厨房,父亲弯腰把烧壶里的水灌进暖瓶,然后给他热冷了的菜。他去堂屋,在一个杯子里放进茶叶,去厨房倒进滚烫的水。他把茶杯放到饭桌上,问父亲安山拿的药吃完没有,父亲把一碗闪着油光的腌肉端到桌上,说只剩一天的药了。他说后天带他再去安山拿药。父亲说可以,这药有效,一天最多咳两声。
他舀一碗饭坐到桌旁,扒一口进嘴,慢慢嚼着,目光盯着碗里洁白的饭粒,脑中闪过母亲手里的那把豆。后天到安山,他想让父亲去密闭的“听声室”和 “嚎叫室”,他的嗓子应该不会受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