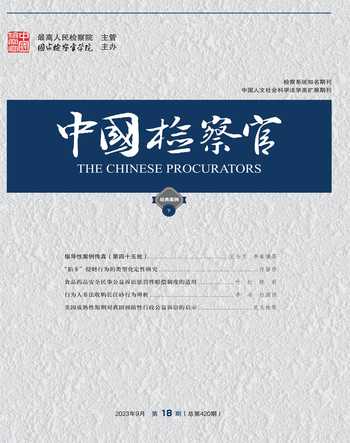行为人非法收购长江砂行为辨析
李冰 杜国伟
一、基本案情
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王某(另案处理)利用参与长江水域疏浚清淤工程之机盗挖江砂,并雇用仲某(另案处理)运输江砂。王某在运输江砂的同时,还利用运输船直接实施非法采砂活动。薛甲、薛乙、方某三人系长江沿线码头从事砂石生意的商人。薛甲与王某事前通谋,由薛甲、薛乙、方某分工配合出售上述非法采挖江砂。直至案发,薛甲等三人合伙向王某购买6船江砂共计2万余吨出售给某混凝土有限公司,支付价款人民币80万余元,从中获利约人民币50万元。其中,为逃避执法检查和便于销售盗采江砂,仲某为王某提供盖有疏浚清淤施工企业印章和相关信息的工程弃置物来源证明。另查明:薛甲、薛乙、方某均曾因共同涉嫌非法采矿罪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2022年12月5日,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以薛甲等三人非法采矿罪提起公诉;2023年2月10日,法院以非法采矿罪,判处薛甲等三人有期徒刑1年至2年10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判处对被告人薛甲、薛乙退缴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二、分歧意见
2016年11月28日施行的“两高”《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非法采矿罪的罪状“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情节严重”“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等予以规定。其中,该《解释》第7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矿产品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实施前款规定的犯罪行为,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司法实践中,江砂收购人通常以对非法采砂行为主观上缺乏“明知”或已尽“注意义务”为理由进行辩解,以便割裂与上游非法采砂行为的关联,否认参与实施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在该类犯罪中,对部分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影响着行为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成为司法实务界争议焦点。本案中江砂收购人薛甲、薛乙、方某的行为定性,在审查起诉阶段存在如下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薛甲、薛乙、方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在案证据显示,王某向薛甲等三人提供了“江砂来源证明”,该“证明”足以阻却三人的主观故意,即有充足的理由认定上述三人购买江砂的来源具有合法性,进而收购销售行为亦具有正当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薛甲、薛乙、方某的行为应认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在案证据显示,薛甲等三人长期从事砂石买卖经营,根据生活阅历和从业经验足以推定他们对于王某采砂的非法性“明知”。根据《解释》相关规定,依法应认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第三種观点认为,薛甲、薛乙、方某的行为应认定构成非法采矿罪。本案中王某提供的“江砂来源证明”不具有合法性,系仲某非法提供。江砂具有自然资源属性,属矿产资源,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采砂,侵犯了国家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根据薛甲等三人关于江砂的交易过程、交易习惯以及前科情况,足以推定该三人对于王某非法采矿行为不仅主观上“明知”且与王某达成非法采砂的“事前通谋”,依法应认定为王某非法采矿罪的共犯。
三、评析意见
本案中,薛甲等三人作为王某运输盗采江砂的收购人,对王某非法盗采江砂行为是否“明知”以及是否系与王某“事前通谋”,是对上述三人在案行为准确定性的关键。针对上述争议,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即薛甲等三人依法构成非法采矿罪(与王某系共同犯罪),主要理由如下:
(一)关于主观“明知”他人非法采砂的推定
在长江流域实施采砂行为,从业者需要技能、设备等作为支撑,同时“采、运、销”等环节所需技能相对独立、设备各不相同。为了盗采江砂获取经济价值,非法从业者经常在每一环节结成“链条”,形成上下游关系,并结成“攻守同盟”逃避打击。为掩盖犯罪逃避惩罚,非法售、买江砂的双方往往心照不宣、形成默契;一旦案发,千方百计寻找借口加以隐瞒,极力辩解自身对于采砂等上游行为非法性并不知情。面对该司法困境,司法机关往往只能通过经验法则及与行为人主观“明知”高度关联的客观事实判断相关行为人是否具有“明知”的主观故意,即适用“推定”。特别是,在“长江大保护”以及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形势之下,对巧借名目掩盖非法采砂行为等新型犯罪加以甄别、打击,是公正司法的内在要求,也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职、保障“绿色发展”的职责所在。
客观行为是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外在表现,认定行为人主观方面时应根据在案供述和有关证言等,并结合行为人的任职情况、职业经历、专业背景、培训经历、本人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对于非法采矿案,特别是在长江流域采砂这样具有高度专业性以及区域特点的非法采砂案件,可结合行为人的生活背景、与上下游行为人的关系、涉案物品的性质等因素来甄别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明知”。
一方面,立足“一般人”标准来审视,即“认定行为人对规范性因素的认识,采用世俗的标准,即用一般社会文化背景中普通人所持的符合法律规定的看法,就足以做出正确的判断”[1]。长江砂所具有的不同于一般普通物品的“显著性”特征,是“推定”行为人主观“明知”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在案证据中的证人证言等证实,长江砂与获得许可通过长江航道运输的其他砂石在感官上存在明显区别。长江砂“平舱、带水、黑色”特征在行业内部已经形成普遍共识,长江砂已成为专有名词,是具有“行话”性质的固定表述。基于行为人所具有的行业知识及行业内针对长江砂的一般性认知,足以推定行为人关于长江砂具备主观“明知”。另一方面,关于行为人主体特征方面,应结合行为人所具备的专业属性进行判断。对于江砂交易的熟悉程度,是推定主观“明知”应考虑的关键性因素。薛甲、薛乙、方某三人长年从事砂石收购生意,需要具备一定的行业知识背景。这些因素决定了上述三人对上游采砂行为的认知程度较高。特别是三人均曾与非法采砂者有过非法交易行为,并因共同涉嫌非法采矿罪被取保候审,足以“推定”其三人对上游非法盗采长江砂具有主观“明知”。
(二)关于推定行为人主观“明知”的逆向证明
本案中,司法机关能否依据行为人接受物品的时间、地点、品种、数量、价格等与所涉罪名的关联因素“推定”行为人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的“赃物”?实践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交易习惯往往具有类似性,即选择深夜及比较隐蔽的地点或低于市场价格交易“赃物”。而本案中薛甲等人系白天以与市场价格相近的价格进行江砂交易,这成为认定薛甲、薛乙、方某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犯罪的障碍。
笔者认为,上述“推定”考量因素虽具有通常性,但不应一概而论,在审查个案时需要具体分析时间、地点的隐蔽性等因素。本案行为人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具有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即长江浩瀚、江面宽阔,行为人具有实施非法行为的天然的隐蔽性;同时江上船舶具有流动性,不同于其他刑事案件的“环境”。在船舶密集的江面上实施犯罪,被发现的难度大。其犯罪时机的选择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一般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从作为行为人犯罪对象,即所采购砂石的属性来分析,在长江流域收购砂石,关于砂石来源基本存在两种可能:一是通过长江航运运输的来源于其他区域的砂石;二是被他人盗采的长江砂。如前文所述,长江砂与普通砂具有显著外部差异;在用途以及获取经济利益方面无显著差异。对于非法采矿罪的实施者而言,如果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进行江砂交易,不仅会影响收益,更是欲盖弥彰,易暴露其犯罪意图;采用正常市场价格进行收购,反而可以更好地隐瞒长江砂与普通砂的差别,进而实现非法获利的犯罪目的。
(三)关于“被蒙骗”能否成为违法阻却事由的判断
本案中,薛甲等三人均否认主观“明知”王某出售的江砂来源违法性,辩称王某对其出具“江砂来源证明”,认为这些砂石具有合法上岸资格才收购王某江砂,收购过程中已尽注意义务。开展疏浚作业的企业所提供的“江砂来源证明”足以让他们确信收购的江砂来源合法。经查实,三人所述“江砂来源证明”即为工程弃置物来源证明(盖有疏浚清淤施工企业印章以及注明船主姓名、船舶編码、物品种类及数量、起点及终点等内容),系仲某为逃避执法检查购买所得。由此,关于“江砂来源证明”是否合法,成为认定薛甲等三人“被蒙骗”情形是否存在、行为人违法阻却事由是否成立的前提。即,行为人如果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便可成为其主观故意“明知”的违法阻却事由。
关于行为人提出的上述违法阻却事由的认定,不能仅仅孤立地审查“江砂来源证明”书证本身,还应审查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以及上游犯罪实施者实施的行为是否违反有关行政法规。对于被盗采江砂的收购者而言,其上游犯罪实施者行为明显违反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行政管理法规,可以作为推翻其违法阻确事由的依据。本案中,薛甲等三人曾因共同涉嫌非法采矿罪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其三人对采矿领域的行政监管规定应当具有相当认知。为避免江砂滥采,长江全域内禁止采砂,采砂行政许可非常严格,需经特定行政许可才具有开采江砂的资格,相关采砂机构、运砂船只等均应明确对应。疏浚清淤施工企业出具的证明仅能就疏浚废物的来源予以证明,并不能当然成为长江砂可以上岸交易、被收购的依据。同时,出具证明的企业并非公权力机关,其出具的证明不具有法律效力。即便薛甲等三人对“江砂来源证明”效力不具有辨识能力,而在案证据能够证实多个“江砂来源证明”所载明的运输船只编号、运输物品种类及数量等与实际明显不匹配,只要进行“一般人”注意便可发现“证明”有问题。因此,薛甲等人的已履行注意义务、被对方蒙骗、不知情等事由的辩解不能成立,无法阻却行为违法性。
(四)在案证据足以证实行为人与上游犯罪实施者存在“事前通谋”
根据前述内容,本案中薛甲等三人与非法采砂的王某之间是否存在“事前通谋”,即关于其对王某非法采砂行为“明知”程度是否足以认定为“事前通谋”,是认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还是认定非法采矿罪的关键。薛甲等三人多次供述证实,三人多年从事砂石生意且有过曾因共同涉嫌非法采矿罪被取保候审的经历,且有书证等证实三人曾多次收购通过长江航运的其他合法砂石。这表明三人存在这样的心理状态。即对犯罪结果的认识不确定,同时对犯罪对象性质不确定,反映出行为人没有积极推动犯罪,对于结果是一种不排斥也不希望的心理态度,基于这种心理事实支配下实施的犯罪应当属于间接故意。[2]对于间接故意是否可以构成共同犯罪,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168号)“刘岗、王小军、庄德志金融凭证诈骗案”指出,“作为共同犯罪主观要件的共同犯罪故意,指的是各共同犯罪人通过犯意联络,明知自己与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犯罪会造成某种危害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3]。由此可见,司法实务认为故意犯罪中共同故意包含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类,间接故意亦可以成立共同犯罪。
本案中,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调取的微信记录等电子数据证实,薛甲等三人在事发前与王某等人多次沟通砂子是否到位等内容,在时间及人物关系上可以证明其存在一定的犯意联络。无论是否联络成功,均不影响薛甲等三人对王某和自身行为危害结果的预见,薛甲等三人主观上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均满足共同犯罪故意的实质内容。即,在犯罪故意内容上,薛甲等三人参与非法采砂并不要求与王某完全一致,也不应要求其具备非法采矿罪主观要件的全部内容,只要与王某的犯意相互连接、相互促进,便具备共同构成非法采矿罪的主观要件。
绝大多数非法采砂案件中,非法采砂已经形成了“采、运、销”完整的黑色产业链。在案证据能够证明,本案中薛甲等三人对非法采砂的犯罪结果未必持积极追求的态度。但在案证据足以证实,薛甲等三人明知王某实行非法采砂行为,却仍然提供运输工具积极配合,进而实施购买、销售从中获取非法利益,是王某实现非法采砂获利行为的延续性有机组成,足以认定其参与非法采砂犯罪。这种行为本身说明,薛甲等三人具有“明知”的故意。因此,应依法认定上述三人与王某构成非法采砂行为的共犯,构成非法采矿罪。
综上所述,作为矿产资源的江砂被非法盗采,严重侵犯国家的矿产资源保护制度。长江流域的非法采矿案件,不仅侵犯了刑法保护的法益,更是给长江流域生态安全以及航道安全带来极大隐患。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背景下,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运砂犯罪的同时,对于作为长江砂“采、运、销”黑色产业链条一环的非法收购行为,也应根据案件情况,在立足罪刑法定原则基础上,从主客观方面予以分析,正确认定,依法予以打击,彰显司法公平正义,进而推进全链条治理。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215600]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五检察部三级高级检察官[300101]
[1] [意大利]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陈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转引自周光权:《明知与刑事推定》,《现代法学》2009年第2期,第110页。
[2]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8月版,第107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刑事审判参考》 (总第25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